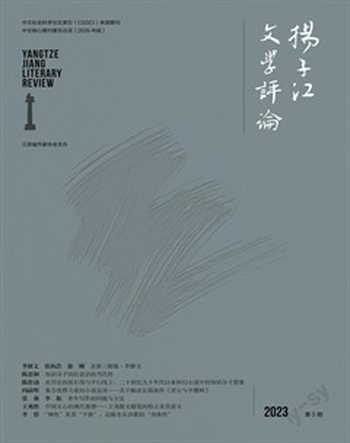论波德莱尔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
韩亮
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经由1957年《译文》杂志选登的波德莱尔的译诗及评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诗人中激起了意想不到的诗学波澜。一方面,波德莱尔用严整的形式和“矛盾修辞”来表达复杂情感状态的手法,让先锋诗人迅速找到了为自己不安的灵魂“赋形”的方式;另一方面,他关于绝对意义上人性与伦理之“恶”的洞见,对先锋诗人的“人观”形成了冲击,瓦解了他们原有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些影响为当代先锋诗带来了鲜明的现代性特质,使其与同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产生了明显的分野。到了1980年代中期,当代诗人接触到的西方现代诗学资源激增,波德莱尔显得不那么“现代”了——这从1984年的《世界文学》将其归入“古典文学”栏目就可见一斑。然而,“年迈”并不意味着影响的消失,“老”波德莱尔仍然对中国当代诗人产生持续的影响。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敏锐地觉察到物质进步的负面后果:“我们将在我们认为活着的地方死去……进步将使我们全部的精神性部分衰萎。”a在普罗大众眼里,现代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蓬勃发展或许是劳动的硕果与生活的胜利,但对一部分敏感的诗人而言,这种进步包含了物绞杀人的负面后果:“物大于人,对物的消耗,对物的追求,以及对物的占有,成了人类的神,物成为了神。人类自己的欲望成了神,人的精神性被剥夺。”b主体被压抑的情状,成了写作者所需面对的新的精神现实,诗人化身为“终日迁徙穿越巨大人性荒漠的孤独者”c。
回到中国当代诗的历史语境中看,在1980年代之后开始写作的第三代诗人感受到的生存状况与朦胧诗人有了很大不同,社会政治的压力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现代性困境。现实的语境类同给了他们与波德莱尔产生深度共鸣的可能性。本文将以海子和张枣为例,追踪第三代诗人与波德莱尔的精神联系:一种与外界关系紧张对立的诗人身份伦理——“我”与当代世界的张力如何呈现,怎样消解,又展现出何种美学特质?这不仅是当代诗的问题,也是当代人的问题,因为“诗的危机就是人的危机;诗歌的困难正是生活的困难”d。
一、阅读波德莱尔
外国文学的接受往往与具体的译本联系在一起。不同语言感觉的译本,可能会在诗人那里出现“蜜糖”与“砒霜”般的霄壤之别。陈敬容的波德莱尔译诗曾被北岛、多多、食指等诗人激赏,但她的译诗在第三代诗人那里并没有点燃多少诗学火花,甚至还引起厌恶。因此,爬梳出第三代诗人接触并喜爱的译本是必要的,这将还原他们走向波德莱尔的小径。
“新时期”以来较早刊载波德莱尔译诗的是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1979)。这套选集按时间划分为“古代部分”“近代部分”(上、下)“现代部分”,其中“近代部分”(下)择取1957年7月号《译文》杂志中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诗九首:《朦胧的黎明》 《薄暮》 《天鹅——致维克多·雨果》 《穷人的死》 《秋》《仇敌》 《不灭的火炬》 《忧郁病》 《黄昏的和歌》。作为“高等学校文学教材”,这套外国文学选集对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诗人来说不可谓不熟悉。
流布更广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丛书。它由彭燕郊规划、组稿和校阅,既再版了重要的民国译本,又纳入了一些新的翻译,其中有五本收入了波德莱尔的译诗:《梁宗岱译诗集》、陈敬容译《图象与花朵》《戴望舒译诗集》、程抱一译《法国七诗人选》、施蛰存译《域外诗抄》。
《图象与花朵》(1984)为陈敬容所译的波德莱尔与里尔克诗歌合集,共有38首波德莱尔译诗,包括了1957年《译文》杂志刊载的诗九首和对于1940年代作品的翻译。《梁宗岱译诗集》(1983)收入波德莱尔的《祝福》《契合》《露台》《秋歌》。这两个译本的风格截然不同,陈敬容以充满张力的语言复现波德莱尔诗歌的强度,梁宗岱追求平和、圆润、和谐的风格。张枣对二者有明确的臧否:
朦胧诗人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他(笔者注:应为“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e
张枣的评价未必客观地反映了两种译本的高下,他其实是借译文喜好传达自己的诗学观,从中可以窥见第三代诗人与“朦胧诗”一代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
《戴望舒译诗集》(1983)的编者是施蛰存,他将戴望舒40年代所译的《恶之华掇英》整本选入,包括梵乐希(瓦莱里)的《波德莱尔的位置》(代序)、24首波德莱尔诗的翻译和译后记。施蛰存在编者序中写道:“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脚韵来了。”f的确,戴望舒的译诗力求克服两国语言组织的差异,在汉语中尽可能地复现波德莱尔诗歌的音乐性。这一极具特色的译文不乏当代知音,朱朱《小城》开头所引的波德莱尔诗句“一切只是整齐和美,/奢侈,平静和欢乐迷醉”g最为接近的是戴望舒的译文:“那里,一切只是整齐和美,/豪侈、平静和那欢乐迷醉。”h虽然字句微有出入,但也足见戴望舒译诗的句式和用词给朱朱留下的深刻印象。施蛰存也在《域外诗抄》(1987)中收入《腐尸》《鬼魂》《枭》《棕发的女丐》四首自己翻译的波德莱尔诗歌。
程抱一翻译的《法国七人诗选》(1984)收入波德萊尔的《老妇们》 《静思》 《伊卡尔》 《死亡》 《猫》和《腐尸》,其中大部分译诗在他更早撰写的《论波德莱尔》(1980)中已经出现过。这篇文章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其引文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小型译诗合集,包括《邀游》 《七个老头子》 《忧烦》 《老妇》 《静思》 《伊卡尔》 《死亡》 《凉台》 《猫》 《人与海》 《对应》等。相比于成集翻译,《论波德莱尔》里的译诗或许带给诗人更多的灵光,第三代诗人柏桦回忆自己的阅读感受:“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美的历险”。i
可以说,“诗苑译林”丛书在1980年代中期集中呈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作品。除此之外,王了一(王力)出版了用古典的五言、七言和乐府诗的形式翻译的《恶之花》(1980),其中除了43首诗为新译外,大部分篇目为民国旧译,曾连载于1940年代林文铮、叶汝琏主编的期刊《中法文化》上。但这部文言译诗集并未在第三代诗人那里激起反响。钱春绮也译有《恶之花》,从篇目的搜罗上较以往的译本更为全面。
上述翻译均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至于散文诗集,仅有亚丁翻译的《巴黎的忧郁》(1982),包括原作开篇的《给阿尔塞纳·胡赛》和50首散文诗。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对波德莱尔文论的翻译。如伍蠡甫《西方文论选》(1979),节选译介了波德莱尔的《随笔》《一八四五年的沙龙》《一八五九年的沙龙》。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1987),收有27篇波德莱尔的文论,包括了《论泰奥菲尔·戈蒂耶》 《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 《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 《一八四六年的沙龙》 《一八五九年的沙龙》 《现代生活的画家》等名文。这些文论让当代诗人对波德莱尔的阅读不仅仅局限于诗歌作品,而且还包括思想和诗学观,从而形成更为深入、立体的认识。
二、酷烈的生命风景
诗人柏桦注意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波德莱尔的文学启迪作用:“接下来,波德莱尔这种影响并未消退,如在海子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j柏桦所引诗句出自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乌云密布的天空》,1957年《译文》杂志选登的评论文章中,阿拉贡以此句作标题,纪念《恶之花》出版一百周年。他以诗人的感性描述这独特的感受:
这是平淡无奇的一年。但是我们有“恶之花”:我们在路上偷来暗藏的快乐,/把它用力压挤得像只干了的橙子……我要谈的就是这一种快乐,而绝不是别的快乐……正是因为这一道黑色光芒是那么炫耀夺目,出现了一百年之后,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波特莱尔带来的无可比拟的珍宝……只有波特莱尔能给我们这样的东西: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k
阿拉贡提炼出了波德莱尔诗歌一个至关重要的特质:高强度的、毁灭性的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人性的暗面,生发于剧烈的创痛,甚至是自戕与自毁。本雅明对其生成机制有精准的分析:“它(笔者注:指《恶之花》)的独特主要在于:能从安慰的直接无效,热情的直接毁灭和努力的直接失败中获取诗意。”l诗人穿越现实的失败与沉痛,驶向酷烈的生命风景——以其阴暗和疼痛刺激了我们的神经。正如有人偏要撕开刚结痂的伤口,或者非要挤出疮口中的脓血般,麻木生命中震悚的那一激灵难道不正是快感之所在吗?这种快感还带着明知不对、不好,却非要为之的偏执,它根植于人性的复杂:
在每个人身上,时刻存在着两种诉求,一种朝向上帝,另一种朝向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性,是一种上升的欲望;祈求撒旦或动物性,是一种下降的快乐。m
人性中截然相反的两种诉求让波德莱尔始终处于“撒旦主义”和“理想状态”的扭结之中,反映在诗歌里,超量的“矛盾修辞”(oxymoron)出现了。例如,“我啜饮你的呼息,呵,蜜汁,呵,毒液!”n“天空又愁惨又美好象个大祭坛!”o波德莱尔用对立的词语反映人与世界复杂性的手法,曾在根子、多多、北岛等诗人那里引起广泛共鸣。p在第三代诗人中,最集中呈现这种表达方式的是海子。“九月的云/展开殓布”q,将秋高气爽写得如丧考妣,就是典型的“矛盾修辞”。“我是黄昏安放的灵床:车轮填满我耻辱的形象/落日染红的河水如阵阵鲜血涌来”r,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的诗句:“迷人的黄昏到了,它是罪恶的帮凶;/象个同谋犯似的蹑足走来;天空/有如巨大的卧室慢慢合上,/人,心烦意乱,野兽般疯狂。”s二者都将安详宁静的黄昏与恐怖和死亡联系了起来。再如“温暖而又有些冰凉的桃花/红色堆积的叛乱的脑髓”t,颇有波德莱尔“沉重的肠子流在大腿上”u的刺激感。海子还常常将“矛盾修辞”中相反的两端推向极致:
在青麦地上跑着
雪和太阳的光芒v
你在一种较为短暂的情形下完成太阳和地狱
内在的火,寒冷无声地燃烧w
雪/太阳、地狱/太阳堪称冰冷与炽热、黑暗与光明的两极,海子迅疾地完成了极性两端之间的滑动,将“矛盾修辞”的张力推向顶点,这带来了富于破坏力的强大势能。诗人在高强度情感张力的推动下,如火山喷发般宣泄主体与外在的极致对立和高度的自我分裂,表现出诗人对于“生命本体论诗学”x的理解:
整座城市被我的创伤照亮
斜插在我身上的无数箭枝
被血浸透
就像火红的玉米y
一把斧子浸在我自己的鲜血中
火把头朝下在海水中燃烧
……
火光明亮,我像一条河流将血红的头颅举起z
在对自身肉体的戕害中,抒情主体获得了残忍的极乐,他与外界、与自身撑得紧紧的网被划开,鲜血淋漓中有一种自在和放松。“恶魔诗人”可谓是波德莱尔身上最为惊世骇俗的标签之一,《恶之花》也被称为是“恶魔主义文学的某种形式”@7。与波德莱尔一样,海子对自己的恶魔诗学有充分的自觉,他曾多次发表充满“魔性”的宣言:
是我,魔。魔王魔鬼恶魔的魔
万物之中所隐藏的含而不露的力量
万物咒语的主人和丈夫
众魔的父亲和丈夫。众巫官的首领
我以恶抗恶,以暴力反对暴力
以理想反对理想,以爱抗爱。
我来临,伴随着诸种杀伐的声音,兵器相交@8
海子还将“魔”唤作“我的母亲,我的侍从、我的形式的生命”,并對自己“困在烈焰的牢中即将被烧死”的终局做出预言。@9实际上,无论是对波德莱尔,还是一百年后的海子来说,恶魔主义都是浪漫主义诗学遗产的现代表达。波德莱尔曾将其指认为“浪漫派的分支”#0,它不是某种文学流派,而是对魔鬼及其相关话题的书写。在此,“撒旦”拥有充沛的渎神激情,因而成为反抗英雄,它代表的“恶”在文学中不再是负面的。这种文学类型并非始于波德莱尔,却在他的创作中达到高潮。在《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中,波德莱尔梳理了自马图林、拜伦、爱伦·坡以来的恶魔主义传统,认为这些作家“在扎根于每个人心灵的潜藏魔鬼身上,投射了灿烂而耀眼的光线”,甚至断言“现代艺术有一种本质上的恶魔倾向”。#1
诚然,我们不能将海子身上的恶魔主义诗学元素全然归于波德莱尔的影响,他的文学偶像(如爱伦·坡)也携带着这种文学基因。需要指出的是,海子对波德莱尔的智性面向兴趣不大,他曾对现代主义诗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试图展开“对从浪漫主义以来丧失诗歌意志力与诗歌一次性行動的清算”,尤其是“对现代主义酷爱‘元素与变形这些一大堆原始材料的清算”。#2海子写下了给波德莱尔的献诗,却并未将其列入自己钦佩的诗歌王子中,也就不难理解了。波德莱尔吸引海子的,是他对浪漫主义余晖的重新表达,而非那些更为现代的元素。
究其影响得以发生的契机,还是两者颇为相似的诗人身份伦理。在《公爵的私生女——给波德莱尔》中,海子将与波德莱尔的相遇定义为一种偶然的、精神性的投射:“我们偶然相遇/没有留下痕迹。”他们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都颇为紧张,后者于他们,是“躲也躲不开”的“庸俗的故事”。在与世界的关系上,二者深度契合:
我们的生存
唯一的遭遇是一首诗
一首诗是一个被谋杀的生日
月光下 诗篇犹如
每一个死婴背着包袱
在自由地行进
路途遥远却独来独往#3
这是一次波德莱尔笔下“我不知你何往,你不知我何去”#4那样的相遇,颓废的氛围和无处不在的紧张感暗示我们两位诗人在观察视角上的相似。如果说生命是无法重复的风景,那么,仅有一次的相遇意味着微缩生命的展开和结束,“诗”是其中唯一的内容。因此,诗歌在此成了“唯一的”存在本身,创造诗的人就具有了造物主的意义。《太阳》中,波德莱尔在诗人、太阳、慈父、国王间画上等号。海子也有几乎相同的表达:“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5
相较而言,让“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的海子在伦理关系上比波德莱尔更为紧张,“去建筑祖国的语言”为何一定要让刀口划向“万人”#6?这说明诗人的自我定位是语言王国里唯一的立法者和评判者。正是这种定位,让诗人的“自我”紧闭,无法向他人敞开,无法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反过来说,也唯有保持紧闭状态,诗人才能在自己的王国里为所欲为。奚密敏锐地将这种现象与当代先锋诗的某种“诗歌崇拜”联系起来。“诗歌崇拜”以浪漫取向为基础,以“世俗/神圣”“物质乞丐/精神贵族”“主流/边缘”等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为核心。在她看来,“个人的疏离或异化”既是重要主题,又“导致一种反果为因的倾向,认为疏离、孤独、受难是创作伟大诗歌的必要前提”。#7
从这种意义上说,上文所论及的恶魔诗学是“诗歌崇拜”的题中之意。魔鬼“撒旦”(Satan)意为“敌对者”(adversary),这意味着对立结构的存在。在最好的时候,恶魔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批判性力量而存在,譬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包含着对全能上帝的批判。可若是取消了批判的对象,它就会变成自身情感的无节制释放,对抗性的力量和价值消失了。过分地沉浸于自我,就意味着拒斥他人,而文学从来无法仅仅属于个人。宣称只为自己而写,表达的其实是对读者的藐视。如果诗人陷入自我的极致分裂与对立,那么,诗歌所能表现的内容绝不会超出自身——最重要的问题无非生死,对死亡的超量书写就出现了。换句话说,如果自我宣泄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实际上是在自我设限。
三、走出焦虑之海
海子的写作一直让生命处于紧张状态,“恶魔”与“天使”仿佛昼夜交替一般在其写作中轮番出场。这种二元对立的动力装置尽管在很多时候是强有力的,但有时也让写作显得有点简单和极端。而在张枣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对待波德莱尔诗学遗产的方式——在深刻认识基础上的选择性回避。在张枣那里,对生存紧张感的克服,终究要在“生”之中完成,他提供的途径是:一方面,将消极事物唯美化;另一方面,在走进“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对话”诗学。他以此将那些坚固的对立与焦灼感受,用“写”的动作磨成“芬芳的尘埃”#8。
从张枣的诗论来看,他对波德莱尔相当熟悉,多次谈及波德莱尔对现代主义诗学的贡献:
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范围里,有一个公认的坐标,那就是波德莱尔的出现,因为他代表了一个现代心智(the modern mind)的问世,这个心智显然是十分自觉地将忧郁的主体作出一种“恶之花”似的矛盾修饰法似的呈现,使得象征主义以来的任何现代抒情方式有了一眼可辨认的主要特征。#9
也就是说,“矛盾修辞”是现代主义抒情的显著特征,它来自忧郁的现代主体,即被空白、人格分裂、孤独、丢失的自我、噩梦、失言等消极元素所包围的“消极主体”。消极元素催生并强化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又连锁反应般地引发了普遍的生存忧郁感——“正是这种忧郁缔造了现代书写的美学原则”$0。这些判断,实际上涉及诗人在面对自我与世界时,如何转化(而非回避或沉溺于)消极感受的问题。其间所需要的能力,接近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它引领诗人客观地面对负面感受,将其制作成具有现代美感的诗意单位。波德莱尔使用的“矛盾修辞”,使这种美感形式更为立体和丰富。可以说,将消极事物唯美化是一种“丑的美学”$1,也是对消极事物的重新命名的过程。
纵观张枣的创作,他并没有写下过给波德莱尔的献诗。不过,我们仍能发现那些带着“恶之花”气息的诗句:
突然的散步:那驱策着我的血,
比夜更暗一点;血,戴上夜礼帽,
披上发腥的外衣,朝向那外面,
那些遨游的小生物。灯像恶枭;$2
死亡之血戴上了高雅的“礼帽”,光明之灯却仿若“恶枭”,这是一组典型的“矛盾修辞”。实际上,张枣的不少诗句中都笼罩着这类“世纪末的迷雾”$3。他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体察与波德莱尔颇为类似:“我们是裂缝中的人/裂缝是世界的外形。”$4为了恢复被物质世界挤压的主体感受与精神向度,张枣广泛使用了一些由波德莱尔发扬光大的诗艺,如跨行(enjambement)、联觉(synesthésie)等——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成为现代主义诗学的“传统”技能,《断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是一个什么夜晚?
别离时分,未闻骊歌
声动。醉舟乞求变成
中心,被万物所簇拥
十二点。时间又发明
一颗彗星。春蚕入眠
而客车却继续跑动
是呀,宝贝,诗歌并非——
来自哪个幽闭,而是
诞生于某种关系中$5
骊歌/声动、变成/中心、簇拥/十二点,诗人将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做了灵活的跨行处理。既营造出陌生、新奇的表达效果,又强调了放在行首的动作、空间和时间。诗人在开头发问:“那是一个什么夜晚?”这是象征之夜、万物感应之夜,也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命名与召唤之夜。“命名在召唤”$6,诗人一声令下,骊歌、醉舟、彗星、春蚕、客车鱼贯而入、彼此呼应,与永恒而确切的时间发生奇妙的联动。这让人联想到波德莱尔那首著名的《应和》。能够听懂无声万物的语言,辨识其中的彼此呼应,既恢复了被现代理性所压抑的心灵世界,也为短暂、匆促、孤独的现代性困境开出安慰剂。张枣在最后点明了那个关键词——“关系”。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彼此感应、彼此连结的深度关系,它复原了人与世界的亲密性。
构建“关系”,成为1990年代张枣“对话”诗学的基石。明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他的《蝴蝶》与波德莱尔《露台》的近似性。曾与青年张枣“连朝语不息”的诗歌挚友柏桦,念念不忘梁宗岱翻译的《露台》对自己的启迪,张枣也在众多译本中对梁译赞誉有加。《露台》是波德莱尔写给理想女性的献诗,这在他的诗歌中并不多见:
暖烘烘的晚上那太阳多么美
宇宙又多么深!心脏又多么强!
女王中的女王呵,当我俯向你,
我仿佛在呼吸你血液的芳香。
暖烘烘的晚上那太阳多么美!
夜色和屏障渐渐变成了深黑;
我的眼在暗中探寻你的柔睛,
而我畅饮你的呼息,多甜!多毒!
你的脚也渐渐沉睡在我手心。
夜色和屏障渐渐变成了深黑。$7
在此,“我”与“你”是一种缱绻和柔情的深度关系。我“呼吸你血液的芳香”“畅饮你的呼息”意味着二者身体距离的极度拉近。在张枣的《蝴蝶》中,我们看到了相似的表达:
如果我们现在变成一对款款的
蝴蝶,我们还会喁喁地谈这一夜
继续这场无休止的争论
诉说蝴蝶对上帝的体会
那么上帝定是另一番景象吧,好比
灯的普照下一切都像来世
呵,蓝眼睛的少女,想想你就是
那只蝴蝶,痛苦地醉倒在我胸前
我想不清你那最后的容颜
该描得如何细致,也不知道自己
该如何吃,喂养轻柔的五脏和翼翅
但我记得我们历经的水深火热
我们曾咬紧牙根用血液游戏
或者真的只是一场游戏吧
……
现在一切都在灯的普照下
载蠕载袅,呵,我们迷醉的悚透四肢的花粉
我们共同的幸福的来世的语言
在你平缓的呼吸下一望无垠$8
抒情主体和“蓝眼睛的少女”幻化为蝴蝶,“我”和“你”亲密无间,“用血液游戏”。“血液”和“游戏”似是一组“矛盾修辞”,充满了爱欲的复杂张力。而当“我们”抵达来世,宁静和开阔的迷醉呈现:“我们共同的幸福的来世的语言/在你平缓的呼吸下一望无垠。”无论是你“血液的芳香”,还是我们“血液的游戏”,都指向爱欲与死亡交缠的深度亲密性。它让诗人暂时走出封闭的自我,正如波德莱尔意识到的那样:“性爱,就是渴望进入另一个人中,而艺术家从来走不出自己。”$9对诗人来说,“走出自己”极具伦理意味,这也意味着某种化解孤独和疼痛的救赎性力量:
我得跟你谈一谈痛
痛绝非来自你本身
最糟的时刻是正午
当世界,含着水仙,像
玻璃球,透明。痛之手
在款步中繁衍;痛让
我多颗牙;最糟的
是我的心,充满虚幻%0
在“我”和“你”的谈心中,“痛”被客体化、对象化了——它并非来自“你本身”。這就提供了易于观看的视角,对“痛”的审美活动由此展开。“玻璃球”的隐喻十分有趣,这是一个凸透镜,用它观察的时候,能呈现出远景倒立的像。经由这个透镜所看到的“痛”将会被倒置,这隐喻了“痛”向“不痛”的转化。但“痛”终究不可能完全外在于生命,而是会引起“我”的联觉反应,这是一种象征主义式的关系表达。从“痛并非来自你本身”,到“痛让/我多颗牙”,“你”“我”并肩,共享生命之痛。张枣意识到古典诗“知音美学”的意义:“知音带来的美要大于沦落感,给了一个宽慰,在沦落中找了一个好东西——交流,共同俯瞰生存的深渊。”%1经由这种安慰,“我”获得了与自己和解的可能,分裂的主体得以弥合:“我便朝我倾身走来”%2,进而与世界握手言和。
从这种意义上看,尽管张枣吸收了不少波德莱尔的现代诗艺,却对他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波德莱尔纯粹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诗人,但杜甫不是。杜甫许多伟大的作品写的是处境和现实之恶,但是他最后依然落实到赞美,因为他觉得生存就是一片绿色。西方只有最具智慧的哲人和艺术家才赞同帕斯卡尔的话——生存无非是一片大和谐。讽刺使诗人丧失赞美的能力。%3
实际上,波德莱尔是否“二元对立”另当别论。张枣借此表达的,是对波德莱尔“英雄化”的诗歌姿态,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抗性美学的拒绝。这种对抗性正是朦胧诗人与波德莱尔的汇合处。钟鸣有敏锐的观察:“‘英雄化(这和世俗化走向或精英走向无关)却恰恰是八十年代诗界最愚拙的表现之一,他们一面否定着意识形态的英雄化,而一面却不自觉地实现着美学的英雄化……那些英雄化的切口和术语,里尔克自然也是要列入其中的。在中国知识界,大概除了波德莱尔,他恐怕是最具影响力的了。”%4可以说,波德莱尔并不试图与现实和解,他致力于在诗歌中强化对抗性的力量。而张枣则为当代诗歌带来了另一种的气质:从对抗到对话,寻求一种圆润、甜美的声音,去化解生存之痛,以求得“对其自身孤独困境的解救”%5。
由此,诗人面对世界的紧张得到了抚慰,高度对抗性的警报暂时解除——尽管冲撞永远都不可能消失。北岛那句振聋发聩的“我——不——相——信!”%6到了张枣这里,变成了虔敬的低语:“因为我相信。我——相——信。”%7张枣持有和史蒂文斯相近的观念:诗歌不是现实的对立物,而是其内蕴物,因此,生存本身至关重要。正如他对“另一个海子”的劝慰:“你千万别像他那样轻生/……你要时刻警惕/自己,别撒手/揪紧自己就像揪紧气球。”%8这对当代先锋诗一度狂热的“诗歌崇拜”而言,意味着必要的矫正性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张枣对波德莱尔的选择性拒绝是重要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明智的作家接受影响时就是学会回避某些东西,或者说,最好的接受某种影响的方式就是不去接受这种影响。”%9这并非诡辩,而是意味着诗人接受影响方式的更新:从被影响源渐染、同化转变为更具主体性的研判与创造。张枣的拒绝为当代诗的写作引入了一个明确的否定性面向,也为当代诗人处理与自我及现实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对抗性诗学的限度显现之时,引入柔性的“对话”诗学,以期走出现代生存的“焦虑之海”^0。从百年新诗史的角度看,自早期的语言革新者李金发,到食指、北岛、多多等诗人与《译文》杂志上的波德莱尔译诗相遇,惊叹诗歌原来可以这么写,再到张枣对波德莱尔的“英雄主义”对抗诗学的拒绝,时间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由惊叹、模仿到批评、回避,这意味着接受主体自身的强健和成长,不再随着“西方的舞步”^1回旋——尽管作为学习对象并非没有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说“不”,是真正意义上平等对话的前提。
结语
波德莱尔活跃于19世纪的法国,与我们当下的世界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他也并非第三代诗人最为追捧的诗歌偶像。然而,他庞大的诗学体系具有相当的丰富性,足以持续激发当代诗人的写作潜能。青年波德莱尔曾置身于法国浪漫主义的鼎盛时期,他从雨果的领地出发,去开拓属于自己的诗学蓝海。一方面,他将雨果提出的“审丑”美学发展为在负面经验中汲取诗意的现代主义诗学手段,让“恶”绽放花朵,并将浪漫主义的黑色分支,亦即恶魔主义诗学推向了表现的极致。另一方面,他高度认同雨果对诗人身份的设定:诗人是“被遗弃者”(paria),即在悲惨世界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同时也是对这个世界最敏锐,对不公保持着最大警惕的人。相较于雨果通过德性的力量托举“被遗弃者”,赋予他们某种英雄主义气质而言,波德莱尔则强调真正的诗人是被埋没和误解的天才,他们极度脆弱和敏感,能够感知“花朵以及沉默万物的语言”^2,他进而从美学的角度完成了诗人身份的英雄化。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海子在短暂的生命中始终对现代主义诗学持有疑虑,但是波德莱尔的“魔性”面向和诗人身份的认定却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契合又与海子对雪莱、叶赛宁、荷尔德林等具有疯狂才华与悲剧气质的诗人的高度推崇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具有反叛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强力主体,把握住“现代汉语的诗性”^3。这接近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言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4的“摩罗诗人”,其诗歌呈现出高度的对抗性和某种“强度美学”。张枣则渴望走出如失去土地的“焦黄的老虎”^5似的现代性困境,他对波德莱尔钻研颇深,却坚定拒绝其对抗诗学。波德莱尔焦灼、孤绝的面向成为张枣有意识回避的图景,张枣反其道而行之,在后期的作品中走出封闭的自我,恢复“我”与自然、与他人、与古典诗学传统的联系,达成他早年提及的愿景:“嘹亮的蓝色老虎走出暗喻。”^6可以说,海子和张枣,代表了创造性转化波德莱尔诗学遗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前者渴求“极痛”、走向撕裂与毁灭;后者向往“不痛”、寻求生之和谐与欢悦。如果将视野扩大,在柏桦、朱朱、孟浪、尹丽川等诗人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波德莱尔的身影闪现。法国学者让-尼古拉·伊鲁兹曾说:“波德莱尔去世于1867年。但世纪末的每一场潮流都依靠了他的声望和财富,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所寻觅的‘现代性”^7,这意指波德莱尔对帕尔纳斯派、象征派乃至超现实主义的启迪,也同样适用于评价他的世界影响。从朦胧诗人到第三代诗人,波德莱尔持续为中国当代诗歌的美学现代性赋能,詩人们各取所需,灵活择取他的美学素材,转手搭建自己的诗歌世界,成了各自时代中“现代生活的画家”^8。
【注释】
a Charles Baudelaire, ?uvres complètes Ⅰ,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Claude Picho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5, p.665.
b%1张枣:《艾略特的一首短诗:Morning at the Window》,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70-71页。
cCharles Baudelaire, ?uvres complètes II,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Claude Picho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6, p.694.
d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e欧阳江河、张枣、赵振江:《访谈三篇·诗歌与翻译:共同致力汉语探索——欧阳江河、赵振江、张枣对话录》,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235页。
f施蛰存:《〈戴望舒译诗集〉序》,见戴望舒:《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g朱朱:《小城》,《我身上的海:朱朱诗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32页。
h[法]波德莱尔:《邀旅》,戴望舒译,《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比照其他翻译,如“那儿,只有美和秩序,/只有豪华、宁静、乐趣”(钱春绮译),“那里,是整齐和美/豪华,宁静和沉醉”(郭宏安译),朱朱所引应为戴望舒的译诗。
i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j柏桦:《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2辑。
k[法]阿拉贡:《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恶之花”百周纪念》,沈宝基译,《译文》1957年7月号。
l[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5页。
mCharles Baudelaire, ?uvres complètes Ⅰ,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Claude Picho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5, p.682-683.
nos[法]波德莱尔:《露台》,《图象与花朵》,陈敬容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24页、47页。
p笔者在《波德莱尔与中国当代先锋诗的发生》中对波德莱尔与朦胧诗人的关联有详细论述,参见《文艺研究》2023年第3期。
q海子:《九月的云》,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页。
r海子:《两行诗》,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页。
t海子:《你和桃花》,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页。
u[法]波德莱尔:《西尔特岛之游》(片段),沈宝基译,参见《比冰和铁更此人心腸的快乐——“恶之花”百周纪念》的引文,《译文》1957年7月号。
v海子:《麦地与诗人》,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w海子:《桃花时节》,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x张清华:《生命本体论的价值归属——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之二》,《文艺争鸣》2023年第1期。
y海子:《马(断片)》,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z海子:《月全食》,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7Max Milner, Le diable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Paris : José Corti, 2007, p.11.
@8海子:《太阳·弑》,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844页。
@9海子:《日记》,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2页。
#0#1Charles Baudelaire, ?uvres complètes II,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Claude Picho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6, p.531,p168.
#2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8-1049页。
#3海子:《公爵的私生女——给波德莱尔》,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4[法]夏尔·波德莱尔:《给一位过路的女子》,《恶之花》,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5海子:《夜色》,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
#6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7奚密:《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8张枣:《秋天的戏剧》,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9$0张枣:《秋夜的忧郁》,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118页。
$1张枣:《〈野草〉讲义》,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2张枣 :《卡夫卡致菲丽斯(十四行组诗)》,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3张枣:《与夜蛾谈牺牲》,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4$5%0张枣:《断章》,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138页、146-147页、143页。
$6[德]海德格尔:《语言》,《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页。
$7[法]夏尔·波德莱尔 :《露台》,梁宗岱译,《梁宗岱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30-31页。
$8张枣:《蝴蝶》,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124页。
$9Charles Baudelaire, ?uvres complètes Ⅰ,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Claude Picho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5, p.702.
%2张枣:《海底被囚的魔王》,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页。
%3张枣、白倩:《访谈三篇·环保的同情,诗歌的赞美》,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233页。
%4钟鸣:《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5余旸:《“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6北岛:《回答》,《履历:诗选1972-198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页。
%7张枣:《一首雪的挽歌》,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
%8张枣:《给另一个海子的信》,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页。
%9张枣:《销魂》,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0Charles Baudelaire, ?uvres complètes II,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Claude Picho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6, p.222.
^1郑敏:《新诗百年探索與后新诗潮》,《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2Charles Baudelaire, ?uvres complètes Ⅰ,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Claude Picho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5, p.10.
^3高玉:《论汉语的诗性与中国文学的“文学性”》,《当代文坛》2023年第2期。
^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5海子:《太阳·土地篇》,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页。
^6张枣:《题辞》,颜炼军编:《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7Jean-Nicolas Illouz, Le Symbolisme, Paris :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aise, 2004, p.23.
^8Charles Baudelaire, ?uvres complètes II,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Claude Pichoi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6, p.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