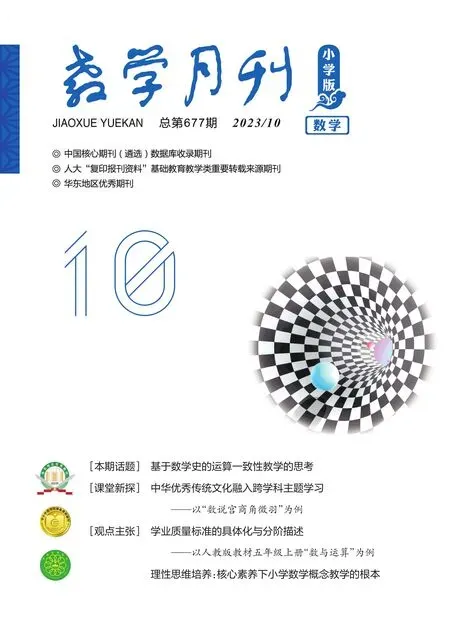基于数学史的运算一致性教学的思考
□岳增成 林永伟
自《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颁布以来,“数的认识与运算的一致性”备受关注,很多研究者对其内涵以及教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具体落实新课改理念带来诸多启示。[1-2]但有关运算一致性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在运算一致性的定位及其与算理、算法的关系上。数学史呈现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历程,数学运算的演变历史及其关键节点的突破,能否为数的运算一致性的教学带来启示呢?
一、对运算一致性的再认识
(一)运算一致性是作为学习结果,还是作为学习手段
数的认识与运算的一致性的基础都是计数单位。数的认识的一致性是从计数单位的角度审视数的构成,建立自然数、分数、小数之间抽象的联系,从中抽象出的计数单位是认识自然数、分数、小数共同的基础。数的运算的一致性就是计数单位之间的运算和计数单位上的数字之间的运算。虽然自然数、分数、小数的计数单位不同,但各类数的加减乘除运算最终均可化归为基于计数单位的运算。从这个角度看,运算一致性应被视为一种学习的结果,是学生学完相关内容后,在教师的引导下从各种运算中抽象概括出的数学规律,是嵌入到学生认知系统中的数学结构。当然,运算一致性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材中数的运算的编排均从计数单位之间的运算开始,因此需要教师持续渗透一致性的理念。教师可从整数的加减法入手,借助小棒、计数器等学具,让学生体会到整数加减法就是计数单位之间的加减法;借助现实情境图、点子图、面积模型、小棒等学习材料,让学生感受到整数乘除法就是计数单位之间的运算和计数单位上的数字之间的运算。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将运算一致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导学生从计数单位的角度分析运算过程,从运算一致性的角度理解运算过程。如“两位数乘一位数”的竖式出现后,教师会引导学生分析计算过程:第一步是用第二个乘数乘第一个乘数个位上的数字,计算的是有多少个“一”;第二步是用第二个乘数乘第一个乘数十位上的数字,计算的是有多少个“十”。另一方面将运算一致性作为一种学习支架,在学习运算新知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从运算一致性角度思考问题解决的方法与策略。如学习“分数除以分数”时,学生观察除法算式后感觉无从下手,教师便询问学生无从下手的原因,引导学生思考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在相同计数单位的基础上进行包含除的运算。在这个过程中,运算一致性被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学生将已有除法运算一致性经验迁移到“分数除以分数”的问题解决过程中。
综上可知,运算一致性是学习结果与学习手段的统一。在运算教学中,要让已有运算一致性作为分析工具、学习支架在不同类型的运算中迭代,帮助学生建立运算整体上的一致性,让他们能从运算一致性的视角重新审视运算过程,更好地理解数学本质。
(二)运算一致性与算理算法的关系
算理与算法是运算教学绕不开的话题,从注重算法到强调算理与算法的融通是课程改革的重要转变。那为何要将运算一致性引入运算体系?运算的一致性与算理、算法的关系如何?
从演绎体系的逻辑来看,需要从定义、公设、公理出发,借助已证的命题推导需要证明的命题。运用这个逻辑审视数的运算的过程,在进行数的运算时,首先要对参与运算的全部数或部分数进行拆分。由于采用的计数系统是十进位值制,整数、小数的拆分一般会基于数的认识的一致性进行。其次要运用运算律对拆分后的数进行重组,这一步指向的是算理。重组的目的是将数的运算化归为计数单位之间的运算和计数单位上的数字之间的运算。最后计算出结果。运算中数的拆分、运算律和运算一致性都是运算的基础,而数的运算的目的是将其化归为计数单位间和计数单位上的数字间的运算(日常教学中一般不会回到数的运算的一致性这一基础上,如在“两位数乘两位数”的教学中,教师会让学生先得到乘法笔算竖式,再引导学生分析运算的第一步计算的是有多少个“一”,第二步计算的是有多少个“十”,正因为如此,数的运算基于其一致性衍生出了多种算法),并计算出正确的结果。由此可知,化归的依据是运算律,运算律操作的对象是拆分后的数;基于拆分的运算律确定算理,算理是数的运算的一致性的根,而算法是基于数的运算的一致性结出的果。
从数学本身看,将运算一致性引入运算体系完善了运算的基础,使运算体系更完备,同时联结算理与算法,让基于算理的算法具有可操作性。
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看,运算一致性关涉知识本质,不仅有利于学生对运算意义的理解,还有助于学生在运算的各种转化中发展推理意识和运算能力。
从课程内容与教师教学的角度看,对于运算基础中的数的拆分(“数的认识”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数的组成)和运算律,教材会编排专门的章节进行教学。而运算一致性的地位并未凸显,无论是教材编写,还是教师的教学,都未关注到这一点。
综上所述,运算一致性与算理、算法的关系密切,将其引入既有重要性,也有必要性。
二、数学史中的运算一致性分析
从数学发展的史料看,与整数的乘除运算、分数的四则运算相关的史料较为丰富,与整数的加减运算、小数的四则运算相关的史料相对匮乏。笔者将以与整数的乘除法、分数的四则运算相关的史料为基础,分析数学史料中的运算一致性。
就整数乘法而言,历史上的计算方法十分多元,比如古埃及的“倍乘法”、中国古代的“算筹乘法”、古印度的“格子乘法”、收录于《计算之书》中的“对角线法”等乘法计算方法。[3]但这些计算方法拆分的方式、运算的顺序与书写格式极为相似,共性是乘数的加法分解。特别是十进位值制被发明和广泛应用后,乘数以计数单位为标准被分解为一位数、整十数、整百数等的和,由此在运算律的基础上,将多位数的乘法转化为多位数乘一位数(由于十进位值制的存在,多位数乘一位数实际上计算的是有多少个计数单位)或一位数乘一位数(在十进位值制中,计数单位乘计数单位产生的新的计数单位最先被确定,因此一位数乘一位数实际上计算的是有多少个新的计数单位)。
就整数除法而言,虽然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古埃及利用除数的加倍与减半试商得出运算的结果、中国古代的算筹除法、现代竖式演变过程中的各种代表性方法[4],但共性是在试商的基础上对被除数进行分解。同样在十进位值制被发明和广泛应用后,基于试商的拆分将被除数分解为商是不同计数单位个数和的形式。如现代竖式演变(如图1)中的后三个算式,被除数732 被拆分为600+120+12,其中600 是能够被除数6 整除且结果包含最多个“百”的数,120 是732-600 后能够被6整除且结果包含最多个“十”的数,12 是732-600-120 后能够被6 整除且结果包含最多个“一”的数,最终得到的商为1 个百、2 个十、2 个一的和。从这个演变过程看,数学史上并未明确提出整数乘除法运算的一致性概念,但古代整数乘除法的运算确实是在对参与运算的全部数或部分数进行拆分后,运用运算律,围绕计数单位之间的运算进行的。

图1
东西方国家都有对分数计算的记载,其中中国是最早形成分数理论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进行分数运算时发现,多个分数没有统一标准,因而无法运算。如《九章算术》在对分数加法的注释中提到:“数非一端,分无定准,诸分子杂互,群母参差。粗细既殊,理难从一。”[5]意思是说:分数不只一个,分数单位也不是同一个标准;多个分子相互错杂,多个分母参差不齐;分数单位的大小既然不同,从道理上说难以遵从其中一个数。因此,古人发明了“齐同术”来进行分数的加法、减法、除法运算。“同”即参与运算的各个分数的分母相乘,使各个分数有统一的分数单位,保证运算的可操作性;“齐”是用每一个分数的分子乘参与运算的其他分数的分母,保证分数的大小未发生改变。由此可见,在分数运算中,中国古代已有了运算的一致性思想。
三、基于数学史的运算一致性的教学建议
(一)基于数学史开展前后测,以测评驱动运算一致性的教学变革
历史的相似性告诉我们,数学史可以帮助教育者预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认识障碍和容易出现的错误,并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6]学生的这些认识障碍和容易出现的错误往往是教学的重难点,因此有必要在厘清数学史的发展历程及关键节点的前提下,通过前测精准定位教学的重点及学生学习的难点,帮助教师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以使学生突破认识障碍、减少错误的出现。如通过对历史上笔算除法的考察,发现被除数的拆分方式多元、运算书写格式多样,这反映出历史上的数学家也在积极寻求笔算除法的最优方法,由此推测学生在学习相关内容时,也会在拆分被除数、运用竖式运算时出现“挣扎”。因此,教师可以在教学“笔算除法”前,利用前测,让学生尝试通过动手操作和竖式表征解决“54÷3”这样的退位除法问题,以此了解学生的认知起点,设置多元表征的数学活动,促进学生理解算理和提炼运算的一致性。也可以在教学后通过后测及对教学结果的分析,对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进行反思,并采取补救性的教学措施或寻找新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有效实现所学知识的内化。如历史上分数除法的算法易得易记,很多国家很早就有“除以一个不为零的分数等于乘上这个数的倒数”的相关记录,但这一结论的推导却相对滞后,由此推测分数除法算法的获得过程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因此,教师可以在学生学完分数除法后进行“计算,并写出计算理由”的后测(也可以将其作为前测),分析学生是否理解了包含利用算理得出算法在内的推导方法。实践结果表明,无论是后测还是前测,学生在公式推导方面的情况都不容乐观。这就需要教师借助数学史,在拓展课、复习课中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分数除法背后的原理。
(二)基于多样的算法,促进学生理解算理与掌握算法的统一
数学学习是一个顺应、同化的过程,学生要将所学知识通过提炼、反思、总结纳入已有认知结构中,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因此学习的结果是获得有意义的精致化的数学结论,如笔算乘法的学习结果是步骤最少且保留过程的简洁竖式。但精致化的数学结论往往会掩盖学生火热的思维和思考过程,教师在教学相关内容时,也常常会直指精致化的数学结论,如教学一位数除两位数的笔算除法时,教师往往会忽略学生多样的分小棒方法,直接借部分学生先分整、再把整零合在一起的操作方法引出教材竖式。虽然这样的教学安排效率较高,但学生对于由一种算法得到的算理、提炼出的运算一致性的理解不深刻。历史上针对某一种运算的算法往往较为多元,多元的方法内蕴不同的思考方式。如整数乘法运算中,不同的方法可能涉及不同的乘数拆分方式、运算顺序、运算格式;但通过对比不同思考方式下的多样算法的异同,学生较易发现运算过程中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往往指向算理与运算的一致性,因而经历这样的学习过程得到的数学结论更为深刻。因此,在进行运算教学时,可以基于历史上多样的算法重构教学,比如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就可以在拓展课中直接呈现历史上的各种方法,供学生理解、对比、辨析,也可以在新授课、拓展课中以历史上多样的算法为原型,设计借助操作、图式、竖式等表征方式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理解算法的活动,并通过多种算法的对比、联系,帮助学生理解算理,构建对运算一致性的认知。
(三)选择关键的史料,适配相应的课型与教学活动
前文已经介绍,与整数的乘除运算、分数的四则运算相关的史料较为丰富。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要促进学生实现运算的一致性,教师需要考虑怎样选取数学史料、选择课型和设计教学活动等问题。目前,拓展课是应用数学史的常用课型,教材中也编排了相关的主题与素材。比如“格子乘法”,它是帮助学生理解运算的一致性的理想素材。从表面上看,“格子乘法”只通过乘法口诀就计算出了多位数乘多位数的结果,但它的实质其实是揭开隐藏在背后的运算的一致性,即计数单位与计数单位相乘,计数单位上的数字与计数单位上的数字相乘。此外,教师更需要在新授课中尝试借助数学史,促进学生对运算的一致性的理解,因为这样的尝试不仅能够促进课程内容的整合及教学目标的达成,还能改善教师对数学史教育价值与应用方式的看法。比如“除数是一位数的笔算除法”的新授课,同时也是一节单元整体设计视角下的种子课,教师教学时应参照长竖式这一历史原型和现代竖式的演变过程,结合学生的认知基础,通过设计实物操作、图式表征、竖式表征及多种表征之间的关联等数学活动,充分暴露学生的思维过程,丰富学生对竖式意义及算理的理解,帮助学生感悟运算的一致性。
综上,本文对运算一致性进行了定位,对算理、算法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基于对数学史料的分析,提出了借助数学史进行运算的一致性教学的建议。可以预见的是,作为人类长期积累的成果,有关运算的数学史势必会对运算一致性这一新理念的落实产生积极影响,由此,也为借助数学史落实新课改理念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