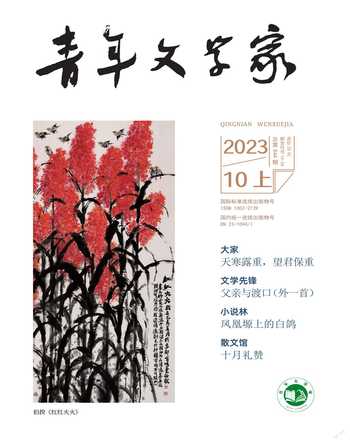山路弯弯
木言
急景流年,往事前欢,不免萦绕心间。依稀故园,香炉紫烟,偏惹离人……
—题记
我喜欢山,非景点名山,仅是一堆堆土山,由故乡的漫漫黄土堆积而成—是岁月无声的印记,而非某某到此一游的喧哗,无声胜有声。它们并不高耸,也无峻拔之姿,更多时候,反而是一种舒坦自适的圆润,毫无剑拔弩张的威凌。连绵起伏,层峦叠嶂,一重又一重。
陕北高原的山,大多时候是荒芜粗犷的,带着原始的尘土气,像时刻可以追本溯源般清醒。然而,每每遇雾,升至半山腰,远观,山群倒更像一朵朵开在地平线上的笨拙而厚重的石头花—几分朦胧里,难得几分娇媚,镌刻几分硬朗,随着雾气的攀行,化作眼前的一枝独秀。而山路,便成了这些花朵的脉络—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每一片叶,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每一粒沙,每一只行走的动物,乃至每一个人,都独特且唯一,但又不可为遗世而独立的孤美,是以,海纳百川,百川百貌,百貌百姿……
我家的院子,背靠一座山,门前又是一座山,都是相对较高的山。背靠的山叫脑畔梁,门前的山叫小疙瘩。两山的中间隔了住户和一条大沟壑,成遥相对望之势。巧合的是,两座山的山顶各长了一棵老槐树,经年累月,一棵长成了窈窕淑女,另一棵长成了健硕君子。
平凡里的不平凡,要算玉凰山。玉凰山比之前两山又高许多,是方圆十里难得一遇的黄土高山。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玉凰山山脚到山顶的那条路,叫“十三”。
这条路承载了太多命与运的更迭,交织过太多时间与空间的记忆,也荡涤过太多来与去的足迹。这条路像所有的山路一样,是从无到有,被乡民一脚一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对于憨实的高原人而言,给山路取名“十三”,是便于记忆。因为,要攀爬十三个弯儿,才能从山脚爬到山顶—登高望远,总要经历从低到高的一个艰辛过程。而山与路,变成某种意义上的阻隔,抑或某种意义上的过程,翻过去,爬上去,会是另一番景致。
玉凰山高耸,其坡度较陡。这条路的弯儿,是因攀爬困难才得以存在—直上“云霄”不光难,也危险。于是,弯儿,于一些特定时刻变成了迂回的智慧。而另一个不得不存在的理由,是半山坡以下的大面积耕地。
奶奶在世时,我年纪尚小。她无交通工具,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在这陡峭的十三弯儿,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何况她也不会骑。当时,出行都靠两条腿和一双千层底布鞋。因此,后来我时常将千层底布鞋与如今的各类时髦皮鞋作比较,将老旧的飞鸽牌自行车与现代交通工具作比较,那些高跟鞋踩不到十三弯儿,那些小汽车无法经过十三弯儿,想想,它们可抵达的,原来也是有限的。但双腿和双脚呢?那一双双不起眼的千层底布鞋的疆域或界限又在哪里呢?
每月逢五逢十的集市,离家大约十公里。翻过两座山,越过两条河,方可到达。而这条通往集市的路,我跟着奶奶,因赶集走过很多次。她背着买回来的稀少货物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抑或我跑在前面,她蹒跚地走在后面,一前一后,是我们的常态。而现在,她在身体上,再也无法走在我的前面,这亦是我们的一个常态。但另一层意义上,她的静止,是一种静观其变的领跑,于我,亦是一个她给的常态……
“十三”并不是唯一通往集市的路,但它是最近的一条路。只是因为弯儿太多,山路又陡,也便没有多少人愿意走了—路面太窄,只能独行。某种意义上,像走独木桥。偶尔赶集的乡民为了热闹,相约一起走在这条酷似大地臂膀、盘旋而上的陡路上。远远看去,像一串连在一起的彩色铃铛,风微微一摆手,它们就轻轻响应起来,叮叮当当,绵绵不绝……
我后来也总想,为什么当时年迈的奶奶愿意带着我走那条弯弯曲曲、陡峭难行的路呢?她要告诉我什么?她又希望我通过走这条路得到些什么?又或者,她想在这条路上留下些什么?其他人呢?那些曾经踩过“十三”之身的乡民,是否也在某一处不为人知的高点,回望曾经翻山越岭的身影?
他走了,她也走了,他们的子孙后辈,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从这条路上走过各自的命运……而后来人的路,是平坦還是跌宕,都无法预测—未来对于现在,永远迷幻而不可知。他们更不会知道,有多少后辈能在这条路上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开阔广大的世界……
脚步声响起又消失。一代又一代人,留在山路上的欢声笑语,以及他们走过的时光,他们曾经的离合悲欢,都已经定格在那一瞬,像一朵花的开落,短暂或长久,都已不再重要。
生命有止息,延续方有价值。唯有“十三”,无昼无夜,无悲无喜,在大地上,躺成一个永恒的姿势,固守着某些无声的印记……
一直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去走,不管世事沧桑如何变迁,它始终在那里,一如我与奶奶的常态,一如世间百态,一如玉凰山,千秋万年,它只是静默无言,无关岁月,无关更唱迭和……
而今,故乡的山,依旧静定从容;故乡的路,依旧绵延永恒。人生,便在山与路之中。而我,只是故乡的某一座土山,或者某一条土路上的某一粒微尘,它们皆是大地之子。我,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