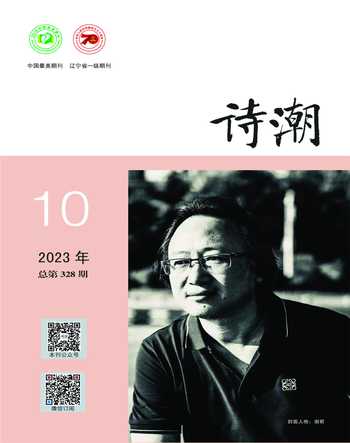构成
明月在上升。我分明看见
另一輪明月在沉没,
并迅疾覆盖我的内心,而不是覆盖
我所走过的乡村和城市。
那儿白茫茫一片,仿佛潮退后的海。
它由我的泪水和我身上的石头构成。
[林忠成赏评] 明月是农耕文化的重要词像,承载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寄托了太多浪漫主义乌托邦,其最大特征是僭越常态价值。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浪漫主义者们跟卢梭学会了轻蔑习俗束缚——最初是服装和礼貌上的、小步舞曲和五步同韵对句上的习俗束缚,然后是艺术和恋爱上的习俗束缚,最后及于传统道德的全领域。”
“明月在上升。我分明看见/另一轮明月在沉没,”显然,作者体察的重点不在那颗自然主义的明月,而是在沉没的“另一轮明月”,它已被形而上学化,属诗人心像的投射。诗人在他肉身缺席之处看到这轮明月,“我就在我并不在的那个地方,亦即某种让我看见的阴影,它使我在我所不在的那个地方看到了自己——一个镜式乌托邦”(福柯)。这个心像投射“迅疾覆盖我的内心”,诗人站在明月的中心位置,洞悉了历史黑暗,据辩证法,太阳内部、明月内部反倒是最黑暗之处,那里没有一丝光线,人只有在超越肉身局限的前提下,才能穿越阴影,看见镜式乌托邦。
朱大可在《先知之门》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挤满了无数缄默的目击者,他们为黑暗的极端性所惊骇。”“目击者的诞生,是午夜时分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使闭抑的存在获得了敞开的契机,黑暗向眼睛,也就是观察者打开了它的本性:它的元素、结构、功能和历史……他必须拥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光线,以便在极度的黑暗中获悉世界景象的各个细节。”浪子便拥有这种内在的智慧光线,诗中那轮形而上的明月向他提供灿烂光芒,帮助他洞悉历史镜像里的狰狞细节。“我所走过的乡村和城市。/那儿白茫茫一片,仿佛潮退后的海。”他清楚,明月还可充作权力隐喻,在它普照之下,只允许光明,不允许黑暗,只允许华饰、充盈、盛大、勃发、欣欣向荣、鸟语花香的图像。
诗的结尾说“它由我的泪水和我身上的石头构成”,进一步证明,诗人作为午夜的见证者,被大面积灼伤并泪流满面。朱大可对先锋诗歌这种见证式努力评价道:“高指数的反诗歌压力是峻切的床,黑暗的巢,从中涌现出大量语义暧昧的而形式精致的意象,以表达一种难以言喻的痛楚经验。这是先锋诗歌运动的苦难灵魂,夹在意象的骨架里。”
——让心理描写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