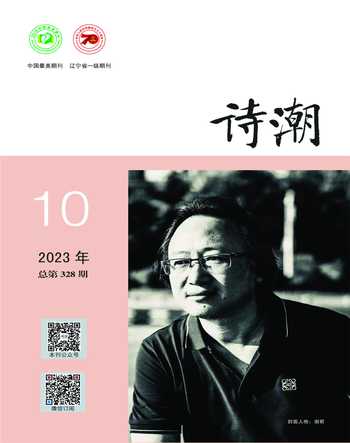学习燕子
袁勇
亚里士多德说过,终止于一日之春景的
就是很悲哀的燕子。人的一生
不会有燕子那么轻,越走杂货越多
也不会像燕子那样找个暖处筑巢
最多是建一座水泥钢筋库房
刷上花花绿绿涂料,把所有的杂物放进去
很多人无暇驻足,最多半日春景
所以,人在世上的存活时间
甚至比不过一只命短的飞燕
上天嫌一个人太孤苦,就造出一群
嫌一件杂物太少,就从土里水里
淘来一堆又一堆。人又嫌线性时间太单调
就启动多维时间,结果迷失于方圆
其实人最重要的,是要活得比燕子轻
要学会用泥巴而不是用欲望做窝
最最关键的是,要学会燕子的生存术:
不要与人处得太远或太近
把自己当个小不点就能活很久:虽然春景不长
[林忠成赏评]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物色》),这是古典文学出牌的套路。这首感逝伤怀之作亦不例外,从一只燕子衍射开去,慨叹人生易逝,“所以,人在世上的存活时间/甚至比不过一只命短的飞燕”。这类诗,“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刘勰)除此,诗人还敏锐地感受到存在之重,“人的一生/不会有燕子那么轻,越走杂货越多”,给整首诗铺设了阴霾的调子。“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这一直是文人的浪漫主义传统。对于人本主义,以及终极价值的思考,古人似乎比今人更自信,“夫人相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刘勰《序志》),说得多么昂扬!哪像本诗那么悲观。
悲观的根源,在于作者洞悉了存在之外的虚无,他心里有一个和莱布尼茨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却不在?”人类永远无法掌握存在之外的奥秘,那一大片黑暗领域,叫无。掌握失败之余,黑格尔索性断定:“存在与存无是一回事。”本诗的张力,就在于从“有”至“无”的衍射,把触手探入“无”的辽阔领域,从遥远的理想主义场域回眸、反思人的存在,“有”赖以立足的根基。
从“有”追问到“无”,必然涉及另一个永恒的哲学母题:时间。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转述康德的观点:“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主观的,是我们知觉器官的一部分。”诗中写“人又嫌线性时间太单调/就啟动多维时间,结果迷失于方圆”,时间的长短,完全是人类经验主义的产物。于人,六十岁嫌短;于蜉蝣,一天太长。蜉蝣活不过一天,所谓朝生暮死。人类探究时间奥秘的结局只能有两个:迷途不返、削发出家。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时间母题进行多向度拷问。他认为,没有抽象的时间性,时间与“自为的存在”不可分,只要“自为”存在,它就是时间的进行。过去总是只对人才存在着,只有人才会提出关于自己的过去这个问题,过去只对现在的存在有意义。对于从来不追问自己存在的自然界,客观上是没有任何过去的。诗中的燕子,就从来不追问自己的过去,从不思考什么“自为”“时间”“无和有”之类的问题,更从不感逝伤怀,所以,本诗结尾诗人倡议“最最关键的是,要学会燕子的生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