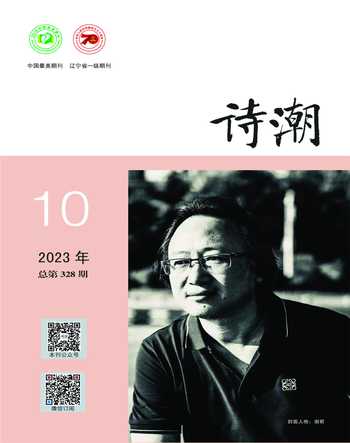换锁记 [组章]
陈俊
换锁记
一把钥匙因用力一扭而折断了脊梁,无奈找开锁匠换锁。
锁匠推荐了不用钥匙的锁。指纹解锁,人脸识别。
钥匙下岗失业也就没有再次扭断的担忧。
你只需朝摄像头里望一眼,或者将手指轻轻一按,门锁就打开了。
中间少了一个物,你只好与自己为伴。
想到曾经朝夕相伴、挂在腰间的钥匙,竟有些不适。
你一直对钥匙充满信任,相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它忠诚,默默奉献。多少年如一日,守护着家的安宁,如今它年老腰折,你却狠心抛弃。
手指一按,我便听到锁里咔咔转动的声音,算计的声音,屏幕数字闪烁的声音。指纹或眼神替谁守着秘密?
没有了钥匙扭动的声响,一切都变得暗箱操作。不那么可控,不那么真实。
每天开门、关门,用尽自己。
年轮一点点长进门缝里。一扇紧闭的门要靠饥饿的指纹唤醒。
门外站着什么人?门里关着什么人?
用手指摁住门上的指纹扣,
我听到里面一群空躯壳的人走动的声音。
像一群惊起的野鸭,在水塘上
乱飞乱叫,那么陌生。
我们耽于日常,却猛然发现
门后面睡了一个神,我对它一无所知,
它对我无所不知。
我的身体在打开门的瞬间惊得冰凉。
它无须试探,无须交流,无须问答,一下捏住了一个人的七寸。是或者不是,转换成开或者不开。我们活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里。
我们是不是又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上帝。
生一場病,不再给盛夏贴金
盛夏需要贴金,标志醒目。一场病生得不是时候,却电光一闪,一下延缓了我贴金的行动和愿望。
一场病里时间回复了原态,一秒,一分,十秒,十分,十分珍贵而艰难地经过我,而不是快乐时瞬移,没有深度和味道。
一场病里,不再为世事贴金,时间回到汗水味,药水味,针尖味,骨裂味,钝刀味。百味俱尝。
6月29日,一场病里的烈日,停在了我放下贴金笔的头顶,我放出自己。
运 气
关心自己的人未必得到春天,关心运气的人未必得到运气。不必矫情,也不必担忧,挂在春天易于凋谢,燃烧冬天方才炽热。正如爱,雪来过,覆盖虚无,我们坚守阵地,在春天复活,将身体高高举到开花的枝头,香气溢满自身。经历是运气钟情的唯一方式,就像从泥胎到瓷器,必然经过高温的锤炼,经过火的锻打,那种成器的釉彩是一种运气。而运气是另一种时间和爱。
苍 凉
苍凉是一个人的脸,有几条皱纹,有几处疤痕,有几处黄昏。当然也可以有几朵暖月花开,几处雾色发芽,几条空河无尘。有几处埋了泪,几处藏了笑。
朝朝暮暮,生生死死,挣扎,渴望,轻盈,沉重,混凝土一样搅拌在一起,就有了凝结的痛,就有了收缩的酸楚,就有了爱恨交叠的棱角和多面。
有些鸿来雁往,有些青鸟勤飞,但更多的是暮鼓千山,烟霏云敛,日沉人散。
人在囧途
太多的不知道,太多的不知道因何因困于困境。
不知道一颗炮弹呼啸而过生命困于呼吸而要用空气凝住天空。不知道一架飞机一头栽下困于无路而要用短促的呼救凝住地平线。不知道一个奥密克戎伪装在哪一处眼神而要用长长的辨认凝住人间。
人们在静态的画面里挣扎,挣扎显得那么笨拙可笑。
有的人感受到雨,淋下来,不给自己一处干净的地方。有的人感受到黑暗,一点一点包围,一点一点嚼噬,不给自己一丁点光亮。
大面积水泥混凝土在浇筑,时空在车辆间速冻而凝结而坚硬,时间坚硬。
光线绕行或退出,夜幕过早地在山峡中罩下来。
我试图对快速退出视线的光说声晚安,这个世界说一声晚安已不容易。
冬天的理想
一个人留在冬天太久,就需要一个冰面镜子,藏起行迹。他看着天空张开大口命令雪花从天而降,无言地把冻云撕成片片碎裂,内心陡然升起一股英雄气概。怒发冲冠。
一朵梅花站直,一朵雪花擦亮。
他毫不犹豫立即现身。
流浪,让一阵风带走。
峭拔,有一首诗呐喊。
轮回,春天是吹哨人。
金蛇般的电闪,是夏天的替身。
银蛇般的山舞,是冬天的标题。
阴沉是一种边界,反对它是一种希望。
一支小小的火烛,可以烧掉相隔的纸墙。
披衣振起,他的热血冲冠,他的啸声俯瞰天地,他的思想融化在寒潮之中。
寒潮的怒吼,
从长城起步,横扫江山万里。
一场风雪删减了多少颓废与萎靡,嫩芽才在地下一步一步拱走了冬,迎来了春。
没有冬的肃杀,怎会有春的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