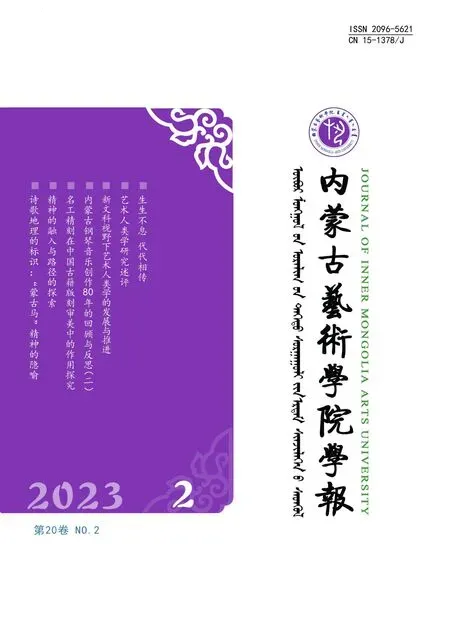内蒙古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特征研究
赵香连 刘尧晔
(1.2.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蒙古剧①作为一个新兴剧种,其名称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演变。在20 世纪中叶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后,它被称为蒙语歌剧,代表作为《血案》。1959 年出版的《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内蒙古卷》中,使用的剧种名称为“蒙族戏”,收录了蒙古剧初创期的代表作《慰问袋》。之后,《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内蒙古卷》等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中,使用“蒙古戏”为该剧种命名。
1985 年,由其时的内蒙古哲里木盟(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乌兰牧骑编演的科尔沁蒙古剧《安代传奇》大获成功,“蒙古剧”这一概念逐渐成为文化主管部门和学术界所认可的剧种名称,沿用至今。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中国戏曲剧种全集》编撰工程,在收录的350 个全国各地方戏曲剧种(含皮影、木偶)中,内蒙古自治区入选的4 个剧种为二人台、东路二人台、蒙古剧和漫瀚剧。蒙古剧榜上有名,至此,它已正式列入国家公布的地方戏曲剧种中。本文所有“科尔沁蒙古剧”这一概念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内蒙古自治区白翠英等学者提出:蒙古剧是20世纪20、30 年代诞生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科尔沁草原地区的戏曲剧种;其二则是专指20 世纪的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主导的蒙古剧的五个分支(科尔沁蒙古剧、昭乌达蒙古剧、鄂尔多斯蒙古剧、察哈尔蒙古剧、巴尔虎蒙古剧)之一“科尔沁蒙古剧”。上述两重含义,也代表了蒙古剧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
关于蒙古剧的定义,依据王国维先生给中国戏曲下的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1](2)从蒙古剧创作演出实践来看,可借鉴上述定义,即:以蒙古族语言、歌舞乐形式表演有故事情节的戏剧即是蒙古剧。后又经过多次涉及蒙古剧理论的研讨会的讨论研究,使得专家学者们也对蒙古剧的概念有了统一的认识,达成共识,明确了蒙古剧的定义。蒙古剧就是以蒙古族的语言、歌舞乐等艺术形式表演各民族人民喜闻乐见故事的戏曲剧种。据《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载,“蒙古剧曾称为蒙语歌剧、民族歌剧和蒙古戏。形成于20 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主要流布于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②等蒙古族聚居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剧团、乌兰牧骑等专业艺术团体的传播,逐渐流布全自治区。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蒙古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诺丽格尔玛》《韩秀英》《达那巴拉》等叙事民歌相继被改编成蒙古戏进行演出……”[2](71)科尔沁蒙古剧是蒙古剧中重要的一支,据《哲里木盟志》载“科尔沁蒙古剧产生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在哲里木盟蒙古族民间歌舞、民间音乐、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创建的一个民族新剧种……”[3](1556)科尔沁蒙古剧流行于内蒙古通辽市、兴安盟一带。早期演出过的剧目有《嘎达梅林》《达那巴拉》《陶克陶胡》③等,新创编的科尔沁蒙古剧剧目有《诺丽格尔玛》《安代传奇》《韩秀英》④等。
方言和音乐,是区分中国各地方戏曲剧种的最根本、最主要的特征。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的形态各异,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地方剧种中的展示,自然就有了区别。蒙古剧作为新兴剧种,在剧本创作上以原创为主,较少移植外来剧目,其音乐成了凸显其作为独立剧种的关键特征所在,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即是对蒙古剧的分支之一的科尔沁蒙古剧的音乐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的探索之作,恳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蒙古剧及其音乐研究的前期成果梳理
(一)蒙古剧的渊源与发展脉络研究
有涉及蒙古剧形成发展问题的研究上,蒙古剧创作研究的知名学者达·毕力格图,尝试着从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到蒙古剧形成的轨迹线索。他认为,博(亦称“萨满”)文化,是蒙古剧形成的基础;陶力(英雄史诗)是蒙古族古老的戏剧艺术形式;而胡仁乌力格尔,是在陶力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具有戏剧表演特征的蒙古族说唱艺术。近代以来,又出现了《呼图克沁》《萨仁呼呼传说》《达那巴拉》和《黄花鹿》等为代表的游牧、定居双重经济文化模式相结合的过渡期蒙古剧种的雏形。20世纪八十年代末,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制定了近期和远期蒙古剧创编规划,提出率先创编科尔沁蒙古剧、昭乌达蒙古剧、鄂尔多斯蒙古剧、察哈尔蒙古剧和巴尔虎蒙古剧等五个地方蒙古剧种,其中科尔沁、昭乌达、鄂尔多斯三个地区试行的成果显著(相关内容可参阅达·毕力格图在《内蒙古艺术》2021年第1 期上发表的蒙古文论文《蒙古剧演变历史轨迹》一文之详述)。
进入21 世纪之后,优秀剧目剧本评奖、蒙古剧编剧培训班、蒙古剧调研创作活动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等大型文艺活动,对蒙古剧的创作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关于科尔沁蒙古剧的形成与发展方面的前期研究成果,白翠英、策·杰尔嘎拉、战丽等学者用力最勤。内蒙古通辽市原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白翠英研究员发文指出,科尔沁蒙古剧产生的因素,可追溯到蒙古族古老宫廷文化活动中的戏剧因素、科尔沁博祭祀仪式以及科尔沁早期的蒙古剧与民歌剧中(详细内容可参阅白翠英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 年第1 期上的《谈科尔沁蒙古剧的发生与发展》一文之详述);内蒙古大学策·杰尔嘎拉教授通过研究分析也认为,科尔沁地区的潮尔奇(演奏/唱潮尔者),在说唱《蟒古斯因乌力格尔》时,就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夸张地增加表演动作,以伴奏乐器为道具,站起身来模仿人物,这种化妆演唱使说唱艺术的戏剧表演内容得到充分体现(相关内容可参阅策·杰尔嘎拉在《内蒙古艺术》2019 年增刊上发表的蒙古文论文《浅谈蒙古剧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之详述);吉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战丽老师通过自己的分析研究,还初步确认:科尔沁蒙古剧的产生时间当为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详细内容可参阅战丽发表在2014 年第9 期《戏剧文学》上的《谈科尔沁蒙古剧中的音乐文化发展的研究》一文之详述)。上述学者们对蒙古剧的探索研究,颇具建设性,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借鉴意义。
到了20 世纪四十年代,科尔沁蒙古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诺恩吉雅》《韩秀英》等内蒙古东部草原上的叙事民歌,相继被改编成舞台剧进行演出。从博到陶力到胡仁乌力格尔再到游牧、定居双重经济文化模式相结合的过渡期剧种,这一渐进式的发展推进模式,为蒙古剧的形成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蒙古剧发轫的母体就是源自内蒙古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沃土这样的结论。
(二)蒙古剧音乐的理论研究
蒙古剧音乐的研究,同其他地方戏曲剧种的音乐研究一样,是我们涉及地方戏曲音乐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研究对象蒙古剧的音乐而言,研究的聚焦点,主要以蒙古剧音乐的定义与曲谱的记载、音乐素材的选用及唱腔特点的分析等内容为主。
首先,我们来梳理分析一下蒙古剧音乐定义与记谱的研究情况。
有关蒙古剧音乐的研究,其初期的研究重心,主要是集中在对蒙古剧音乐的定义与剧目的讨论辨析和创编收录上,收录于《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内蒙古卷》及个人作品集中。这些文献资料的结集出版,对蒙古剧音乐的语义界定、形成结构、曲谱记录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据《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载,“蒙古戏音乐是在蒙古族民歌、曲艺说唱和宗教音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蒙古戏的唱腔音乐、伴奏音乐尚无明确规范,就唱腔音乐的结构而言,可分为单曲体和联曲体两类……”[2](153)这一记载,对蒙古剧音乐的唱腔形成、音乐结构等提供了明确的介绍文字。
不可忽略的是:蒙古剧音乐选择性地吸纳地方传统音乐作为其音乐特色的支撑,反之,传统音乐文化以其丰富的内容与浓厚的民族风格,为蒙古剧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内蒙古卷》载“……蒙古戏的音乐结构尚未定型,仍处在试验阶段。根据各地编创手法,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蒙古族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为基调,或原封不动,或稍加改编,进而构成单曲反复和多曲联接;二是以蒙古族曲艺乌力格尔、好来宝等音乐为基调,兼收民歌素材,探索建立蒙古戏的音乐体制;三是以蒙古族叙事民歌和说唱音乐为素材,按不同人物性格和戏剧情节,借鉴新歌剧和西洋古典歌剧的主题发展手法创作大型蒙古戏音乐。”[4](973)
在蒙古剧曲谱的记录方面,个人作品集如格·恩和巴雅尔的《〈蒙古剧音乐〉选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2014年版)中,收录了格·恩和巴雅尔所创作的《忠勇察哈尔》《巴丹吉林传说》等两部蒙古剧完整音乐主旋律乐谱及其他优秀蒙古剧音乐选段乐谱。该书所收录的曲谱,以我区代表性蒙古剧剧目的音乐选段为主,这也为创作、演出、传播、交流、研究蒙古剧音乐,提供珍贵的曲谱资料。另外,在博·白雅拉格其主编的蒙汉对照版的《美丽其格戏剧音乐选集·上下册》(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也收录了小歌剧《慰问袋》、科尔沁蒙古剧《达那巴拉》、移植歌剧《红灯记》、民族歌剧《雪中之花》、蒙古剧《莉玛》、大型蒙古剧《满都海斯琴》的曲谱及有关蒙古剧理论、评论和采访录等文章。该书既收录了内蒙古地区早期创演、移植的小型歌剧,又涵盖了曾获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第六届中国艺术节金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荣誉的大型蒙古剧《满都海斯琴》的曲谱及相关评论文章,成为创作研究蒙古剧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次,我们对蒙古剧音乐的素材与唱腔的收录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下初步的分析探讨。
有关蒙古剧音乐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素材的选用、唱腔设计的特点及创作发展趋势的几个研究焦点问题上。有关蒙古剧的音乐素材与唱腔特点,据《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内蒙古卷》等文献记载,蒙古剧音乐是在蒙古族民歌、曲艺说唱和宗教音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唱腔结构可分为“单曲体”和“联曲体”两类。达·毕力格图先生认为,蒙古族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是蒙古剧的“母体”。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的刘彦君、刘祯等专家,在“2014 年全区新创蒙古剧会演暨理论研讨会”上发言时,也强调指出,少数民族戏剧剧种的基础,就是传统民族民间艺术。之后,福宝琳也提出,蒙古剧音乐是以民间音乐为基本素材,并继承民间音乐传统的演唱方法及表演形式(上述对于蒙古剧音乐研究的相关信息和内容,可参阅福宝琳在《北国影剧》1988 年第3 期、第4 期上连载发表的题为《从安代传奇的音乐写作看科尔沁蒙古剧的音乐特色》一文之详述),这些对蒙古剧音乐的探究和探索,对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创作和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李柏璐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美丽其格及其蒙古剧音乐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对内蒙古著名的作曲家美丽其格先生所创作的蒙古剧的音乐进行详细分析,提出了关于蒙古剧所面临的传承问题,当以突出民族特色并有取舍地借鉴其他优秀剧种为自己的生存发展之路的主张。另一位关注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理论研究的学者赵娜认为,蒙古剧具有体式、表演上的杂糅性特点与题材、音乐上的民族性特点(相关内容可参阅赵娜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6期上发表的《杂糅性与民族性:蒙古剧〈沙格德尔〉文艺性格探析》一文之详述)……从上述几位蒙古剧音乐理论研究者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分析中我们发现,蒙古剧音乐取材于民间音乐,唱腔上借鉴了民间音乐演唱传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在学界已达成共识。
检索梳理有关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专题研究情况,我们发现,研究者多是以剧目为个案分析其音乐特色,指出该剧目音乐的表演形式、曲谱创作方面的不足之处,此其一;其二,是将剧种音乐放置在社会生活的大文化语境下,结合文化背景分析其音乐,追寻音乐中的文化、文化中的音乐。从现有的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蒙古剧的理论研究对于蒙古剧音乐素材、唱腔设计与乐队配置等方面,缺乏理论层面的归纳总结与深入研究。鉴于此,笔者接下来的研究侧重点,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挖掘,从科尔沁蒙古剧的音乐素材、唱腔设计与乐队配置三个方面,对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特征进行进一步剖析,为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创作发展提供理论参照;其三,本文拟通过对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研究,使学术界更加关注和深入地研究蒙古剧音乐的诸多问题,从而有助于弥补内蒙古自治区戏曲文化研究中对剧种音乐研究的不足。
二、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特征
(一)音乐素材的民族性特征
音乐素材的选用,是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一个剧种来说,往往是通过音乐来表现其中心思想及界定剧种属性。
首先,科尔沁蒙古剧的音乐素材,多选用科尔沁民歌改编创作而成。早期的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唱腔设计,多为单曲体,即由一首民歌的曲调反复演唱构成的。其特点是民歌名称与剧目名称相同,人物角色同腔共调,全剧音乐直接采用民歌或无明显变化的简单旋律来构成。单曲体的科尔沁蒙古剧剧目,大多是根据内蒙古东部长篇叙事民歌改编而成,如《达那巴拉》《韩秀英》《诺丽格尔玛》等。有的初创的科尔沁蒙古剧剧目,虽然名称、唱腔旋律与原民歌基本相同,但其曲式结构,则根据戏剧性的要求出现了新变化,如科尔沁蒙古剧《诺丽格尔玛》,在唱段中间增加了发展部,形成了A+B+A 的结构。
另外,一个剧目唱腔中采用多首民歌,每个角色一般只用一首民歌,曲调的数量与剧中人物、剧情内容相关,此类科尔沁蒙古剧的唱腔,可称之为“民歌联曲体”。科尔沁蒙古剧的音乐创作,直接套用科尔沁民歌或运用民歌素材,再根据剧中每一个角色进行编曲演唱的情况比较常见。如当代蒙古剧音乐创作的奠基人之一的美丽其格老师所创作的科尔沁蒙古剧《达那巴拉》,就是根据内蒙古科尔沁地区的同名叙事民歌改编,并吸收了其他东蒙民歌及乌力格尔、好来宝等曲调,美丽其格老师还在创作中借鉴了其他民族及西洋作曲技法的某些元素,使之更加丰富完整,为科尔沁蒙古剧的音乐创作继承民族传统、保持地域风格、突出时代特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整部剧中音乐的旋律与人物的对话,完美地契合在不同的情景之中,将每一个人物角色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科尔沁蒙古剧音乐创作中,这种大量选用科尔沁草原上蒙古族民歌的素材,作为科尔沁蒙古剧音乐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和主体音乐框架的例子,充分显现出科尔沁蒙古剧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与地域民俗特征。
其次,是大量运用了科尔沁草原上蒙古族说唱艺术的音乐素材,如直接选用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等蒙古族说唱艺术的曲牌音乐,来直接改编创作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个科尔沁蒙古剧剧目里,也有全部采用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曲调联曲而构成的科尔沁蒙古剧音乐唱腔结构的例证。如美丽其格老师创作的科尔沁蒙古剧《扇子骨的秘密》(又名《算卦的秘密》)中,就大量采用了蒙古族说唱曲调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等曲牌形式,来构成科尔沁蒙古剧《扇子骨的秘密》的联曲体唱腔结构。整部剧的音乐结构自由,旋律起伏较大,保持了科尔沁蒙古族说书曲调的节奏感强、说唱相结合的音乐特点。在唱词的创作上,也强调了蒙古族诗词押头韵的这一韵律特色,这就使得整部剧在段落构成、剧情节奏和人物张力上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科尔沁蒙古剧《扇子骨的秘密》的整部剧中,大量运用了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短调民歌等诸多科尔沁蒙古族民间音乐艺术形式的元素,大大提升了该剧的民族性、地域性、艺术性与戏剧性特色。
(二)唱腔设计的杂糅性特征
唱腔,是指戏曲音乐中用人声演唱的部分,是语音的“乐化”,也是区分不同剧种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研究科尔沁蒙古剧音乐不同于其他地方戏曲音乐的特点,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科尔沁蒙古剧剧中人物的唱腔设计,包括调式调性、声部分配、人物音乐主题、人物音乐特征及全剧音乐的高潮和每一场音乐高潮的精心设计与合理安排等问题;其次,对整体音乐风格、民族特点、地域特色要有准确把握,才能确定采用什么规模的乐队编制、运用怎样的和声与复调技巧,以及旋法及配器手法等;再次,还要考虑在演唱音域、演唱技巧和演唱难度上,怎样充分发挥演唱者的有效音区、音色,包括演唱者的音乐修养和领悟能力等诸多因素,都是科尔沁蒙古剧音乐唱腔设计中必须兼顾到的重要方面。
与唱腔设计关联密切的是演唱风格,它是音乐的民族风格能否体现出来的关键所在。创作出颇具民族风格的音乐唱腔,必须通过演员的演唱,使该剧种的特色及民族韵味得以完美的体现与升华。科尔沁蒙古剧以地方文化题材、科尔沁方言和演唱技法为其显现剧种特色的主要标志。其唱腔设计,分长调和短调两种,通常的情况下,长调的唱腔设计及演唱,以接近演唱者自然嗓音的本色音色为创作依据,凸显蒙古族民歌高亢嘹亮的风格,拖腔与甩腔居多,行腔自由舒展,这些蒙古族传统民歌的演唱方法,成为科尔沁蒙古剧音乐创作与演唱的核心内容。实际上,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方法,在科尔沁蒙古剧的唱腔设计中,不占主要地位,仅是以一种技巧性的华彩唱腔的形式而存在,它既可以独立展现,也可以和蒙古族短调民歌唱腔配合使用。蒙古族短调民歌及蒙古族曲艺说唱的内容,在科尔沁蒙古剧的唱腔设计并演唱时应用最广,如科尔沁蒙古族的抒情民歌、叙事民歌、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等,都是科尔沁蒙古剧音乐创作的重要素材源泉。
从科尔沁蒙古剧的演唱方法上看,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内蒙古卷》载,“蒙古戏的演唱大多采用民族唱法……”[4](974)尤其是科尔沁蒙古剧中多采用蒙古族短调民歌的演唱形式,自然是以民族唱法为主。声乐演唱方法的民族唱法,主要包括传统的戏曲演唱、曲艺说唱和民歌演唱三大类,也包括新民歌的演唱和西洋唱法民族化的演唱等狭义的民族唱法。本文涉及科尔沁蒙古剧中的民族唱法,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蒙古族民歌演唱技法,同时,还吸收了西洋美声唱法的精髓,基本上是由两者融会贯通而成。
科尔沁蒙古剧的演唱方法,正如前文所言,即在继承传统的民歌唱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美声唱法,也就是声乐界俗称的“民美结合”的唱法。这一演唱方法的运用,也是由科尔沁蒙古剧文学剧本的内容及音乐曲调的风格来决定的。如早期的科尔沁蒙古剧《安代传奇》《达那巴拉》中,采用民歌演唱法最为常见,而近年来创作演出的科尔沁蒙古剧《巴图查干情缘》,就采用了以民族唱法及美声唱法为主。民族唱法与传统的民歌演唱方法不同,需经过演唱者的二度创作,融合了民歌演唱方法和美声演唱方法两种不同的诠释曲谱的演唱方法。
按照西方音乐的传统,是不能对经典的采用美声唱法的作品做过多的改动的,但科尔沁蒙古剧中的乐段演唱,有时并不能完全依谱来完成演唱。因为,科尔沁蒙古剧作品的音乐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若完全依谱演唱,便无法表现出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地域特色中浓厚的民族音乐风格及独特韵味;反过来,若完全采用传统的蒙古族民歌的演唱方法,也不完美。一是不能完整地诠释和呈现作品的内涵;二是要考虑到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时代的鉴赏需求。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更是人类特有的沟通方式。科尔沁蒙古族方言,为科尔沁蒙古剧的形成夯实了语言基础,也是赋予科尔沁蒙古剧唱腔特点的有力保障。在科尔沁蒙古剧中,运用美声唱法或民美结合的演唱方法,来表现其方言特色,具有局限性。因此,笔者认为,科尔沁蒙古剧的唱腔设计及演唱风格,在把握好语言的声韵与演唱的咬字、歌词的发音(声调)与音乐的旋律、歌词的断句与乐曲的节奏等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以传统的蒙古族民歌的演唱方法或借鉴通俗唱法的“新民歌演唱方法”为主,才能更好地表现出科尔沁蒙古剧的语言特色。
(三)乐队配置的地方性特征
早期的科尔沁蒙古剧伴奏乐队比较简单,主要有马头琴、四胡、三弦、笛子等弦管乐器和摇铃、碰钟、木鱼等打击乐器。用四胡和马头琴、笛子的伴奏来衬托唱腔,既无引子,也无过门,只是与唱腔的旋律相同音高、相同时长相互配合。如科尔沁蒙古剧《安代传奇》中,就使用了笛子、鼓、马头琴、号角、扬琴等乐器,为剧中人物的演唱来进行伴奏。在乐曲上,引用了科尔沁民歌《奔布莱》和《丁香姑娘》的曲调与旋律,来表现该剧人物的特点与故事内容。乐队的编制比较单一,旋律的发展也比较简单。
后来,由于专业剧团的相继成立,乐队的编制,也由小型民乐队发展为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混合编制组成的大型管弦乐队。目前,已创作演出的科尔沁蒙古剧,大多以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及电子软件制作的MIDI 作为伴奏音乐。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乌兰牧骑演出的科尔沁蒙古剧《巴图查干情缘》的音乐,在电子音乐为主的MIDI伴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马头琴、低音四胡、高音四胡、雅托嘎等民族乐器,而且还加入呼麦演唱,来演绎该剧的主旋律音乐。在乐曲上,引入了传统的好来宝曲调及古老的科尔沁长调民歌《四季》和短调民歌《春梅》等民族民间音乐元素,来突出科尔沁蒙古剧的剧种特色。
用软件制作的MIDI 音乐的伴奏特点,是电子乐器的种类多、音色丰富,音乐主题可有较大发展,擅长表现戏剧性较强的繁杂内容。但这种MIDI 伴奏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科尔沁蒙古剧之剧种特色。蒙古族乐器种类繁多、风格多样,且具有独特的功能特性,它“涵盖了以弓弦潮尔、锡纳干·胡尔、叶克勒、阿日森·胡尔、黑勒嘎森·胡尔、马头琴等潮尔类乐器和四胡为代表的胡尔类乐器,这一类乐器特点是音色淳厚、泛音丰富;以雅托噶、火布思、三弦、陶布秀尔、口弦为代表的擅长表现节奏型的弹拨乐器;以临布(笛子)、冒顿潮尔为代表的吹奏乐器及亨格日格、羊皮鼓、扬琴等为代表的打击乐器……”[5](283)等以其独特的演奏方法及丰富的表现力,为体味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乐器艺术的美的享受,增添了丰富的色彩。除此之外,“在传统社会中,蒙古各旗王府中大都有自己的专职乐队和戏班,而这些王府乐队的规模和乐队编制更加复杂和庞大。以流传于锡林郭勒察哈尔地区的‘阿斯如’合奏、科尔沁地区的‘东蒙合奏’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乃日合奏’最具代表性……”[5](316)如此编制的乐队合奏,多是根据各种乐器本身的功能特性和演奏特点,在进行合奏时彼此密切协作而展现出非常和谐的听觉效果的。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兰牧骑演出的科尔沁蒙古剧《万丽花》,在内容上选用了科尔沁民歌《万丽》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来演绎保护草原重视生态文明的故事。乐队配置上,使用马头琴、四胡、三弦、笛子等民族乐器,组成独具特色的民乐队配置来突显该剧的民族性特点和地域性风格。
为此,笔者认为科尔沁蒙古剧的乐队配置方面,使用上述真实有效的民族特色乐器,尽量少用或不用不真实的电声音乐或类似的音乐软件来配器,再借鉴传统合奏形式的编制,使乐团配器的每一个声部,都要符合管弦乐队和民族特色乐器的演奏法则,根据剧目的故事情节,适当加入呼麦伴唱,形成独具特色的科尔沁蒙古剧乐队编制,能更加突出科尔沁蒙古剧这一剧种的地域特色,同时,也为科尔沁蒙古剧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结 语
综上所述,科尔沁蒙古剧的音乐素材,具有民族性特征;唱腔设计,具有杂糅性特征;乐队配置,具有地方性特征。这三个鲜明的特征,孕育了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风格特色。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杨荫浏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写到“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也创造了音乐……”[6](1)他坚定地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民间音乐始终处于源头的位置,而后来创作出的各类音乐体裁,是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不断加工、改编、吸收、创作而出新的音乐作品,两者互相交流,互相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内蒙古科尔沁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与科尔沁蒙古剧的音乐创作与唱腔设计,在功能的需求上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理由如下:一是科尔沁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蒙古族叙事民歌,以其集民间叙事文学与民间音乐为一体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歌种,成为蒙古族近代音乐标志性体裁。并且,它将完整的故事情节,用比兴、衬托、复唱、排比、夸张、比拟、设问、旁描等艺术表现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主题,这为科尔沁蒙古剧剧本的创作,奠定了文本基础;二是科尔沁民歌的思乡歌、训谕歌、宴歌、情歌、赞歌等丰富多彩的题材内容,为科尔沁蒙古剧题材内容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三是科尔沁地区民族民间音乐,那婉转动听的旋律、巧妙的转调手法,在曲调中不仅有一般性的起、承、转、合逻辑递进,更重要的,是运用变化音、离调、转调、调式交替、色彩渗透等旋法的特点,为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多元的创作技法上的参照系。
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因其多元的体裁而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特点,这种不同的功能特点,对科尔沁蒙古剧音乐的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并刺激和推动了科尔沁蒙古剧创作的长足发展。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路应昆先生,在《戏曲音乐若干基本概念界说》一文中认为,“剧种”“地方戏”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尚未恰切,精密。因此,为解决此类概念存在的复杂性,要将研究重点放在戏曲及戏曲音乐的形态学、分类学方面(相关内容可参阅路应昆在《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 年第6 期上发表的《戏曲音乐若干基本概念界说》一文之详述)。路应昆先生在该文中还提到越剧、评剧等剧种,几乎遍布全国,传布极广,但它们都未因流传广泛而形成不同分支,这与它们的音乐属性有直接的关系。这说明音乐特征,是关乎一个剧种或“地方戏”区别于其他剧种的重要因素。本文首次对科尔沁蒙古剧进行音乐特征方面的分析研究,这对厘清科尔沁蒙古剧的概念、深化蒙古剧音乐的研究和创作发展,有着尝试与探索的意义,希望笔者的探索与思考,为推动少数民族戏曲剧种音乐的理论研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注 释:
①蒙古剧,即“蒙古戏”,早期蒙古语戏剧称之为“蒙古戏”,20世纪以后,内蒙古自治区将蒙古语戏剧统称为“蒙古剧”。本文所指,是一个剧种的名称,属专用名词术语;
②哲里木盟建置始于清初,明洪熙年间,称诺恩科尔沁或嫩江十旗,习惯上称科尔沁草原。后几经行政区划的变革,于1999 年由国务院批准撤销哲里木盟,设立地级市通辽市,现为内蒙古自治区辖地级市,地处内蒙古东部地区。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地区是著名的蒙古族地域文化——科尔沁文化的发祥地,文中所指的科尔沁是“文化圈”概念。蒙古语中,科尔沁是“箭骑士”之意 ,科尔沁草原所覆盖的地区为今内蒙古通辽市和兴安盟的大部地区;
③科尔沁蒙古剧《嘎达梅林》,于20 世纪50 年代由辽宁省阜新蒙古剧团演出;科尔沁蒙古剧《达那巴拉》,于1964 年由内蒙古民族剧团演出;科尔沁蒙古剧《陶克陶胡》,于1962 年由内蒙古民族实验歌剧团演出;
④科尔沁蒙古剧《诺丽格尔玛》,于1959 年由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文工团演出;科尔沁蒙古剧《安代传奇》,于1985 年由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乌兰牧骑演出;科尔沁蒙古剧《韩秀英》,于1985年由内蒙古哲里木盟歌舞团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