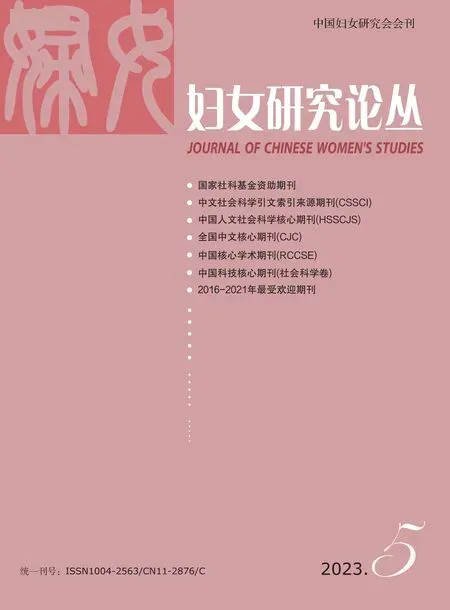“看见的看不见”:网络自媒体赋权农村妇女研究*
卫小将 黄雨晴
(1.2.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农村妇女是一个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的群体,她们表现出相对较强的内敛性与缄默性,其生命历程中的角色实践大致可分为女儿、妻子、母亲、婆婆[1](PP16-18)。这是一种以家庭为轴心、以照顾为特质的生存样态,在男性秩序中具有一定的弱社会可见性,即所谓“看不见的女性”[2]。当然,自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农村妇女的崛起和父权的衰落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她们私人生活领域的权力发生了较大变化,集中体现为择偶、彩礼交换和分家等方面的自主性[3](P179);另一方面,社会流动的“脱域”过程加速了父权制的衰落[4],打工潮将她们从家庭推向了公共领域。然而,这似乎还没有完全实现对她们的赋权增能。在私人领域,农村妇女的权力具有短暂性[3](P197)。在公共领域,由于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她们更多还是从自身家庭走向别人的家庭(家政服务),并没有完全摆脱“流动父权”的羁绊。因此,家庭、照顾和服务或许仍然是农村妇女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词,这也塑造了一种质朴、隐忍的群体气质,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疑为这个群体提供了权力转变的窗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智能手机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小屏时代”“短视频时代”,农村妇女借助各种社交媒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开始营造属于自己的舞台,平时沉默寡言的她们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却成为能说会道和能歌善舞的“女主播”。她们分享乡村生活、讲述独特生命故事,“在社会边缘”中找到了可以掌控的网络权力“微中心”。这无疑是对农村妇女的一种赋权形式,不仅增强了经济功能,提升了社会存在感,还强化了网络话语权。与此同时,随着短视频经济的蓬勃发展,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异化现象,如低俗、色情、造假、卖惨等,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有时候线上交换的都是虚拟的年龄、性别和身体特征,因此网络有可能变成(男性)欲望和个人梦想的承载体”[5](P325),农村妇女形象也不同程度地遭到集体性贬抑,因此,短视频等自媒体平台赋权农村妇女的实际效果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议题。
赋权是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而提出的概念,意在减低、扭转并消除社会主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负面评价与歧视定型。与直接救助不同,赋权意在增能而非拯救[6](P14),强调个体的内生性,鼓励当事人去觉察、分析、反省和行动,持续提高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最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政策和社会资源分配格局。赋权的三个层次——心理赋权、人际赋权、社会赋权[7]在此基础上提出,分别承载了个体增能所需的三种权力:个人权力、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即个人激发动机、独立思考和影响资源分配的能力[8],这成为赋权之“权”的核心内涵。赋权后来演变成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工具。自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以来,妇女通过成立组织、出版刊物、游行、集体行动等方式争取政治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生育权以及微观层面的政治权[9],极大地改进和增强了自身的权能。而网络赋权主要伴随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产生,这次女性主义浪潮由“科技定义”,社交媒体的使用成为女性赋权的关键,但对其实际赋权效果具有较强的争议性。目前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肯定互联网的赋权效果,认为它给妇女带来了虚拟增权(virtual empowerment)。增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妇女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构建起自我意识[10],提升了自我效能[11],获得了对于生活的掌控感,实现了心理赋能;(2)妇女加入各类线上互助小组,生成虚拟社区意识,强化情感联结和社会支持,实现了组织赋能[12];(3)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让女性能够挑战现实自我的各种文化限制[13],实现了技术赋能。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赋权女性具有虚假性。首先,技术平权是一种假象,技术女性主义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而是有明显的男性偏向,互联网新技术仍然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与性别相关的现实社会权力秩序被投射到技术世界之中。因此,男性掌握了互联网传播实践更多的主动权,而女性使用互联网并不会在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其的性别刻板印象,也难以获得性别权力的重新分配[14]。其次,女性数字化呈现出商品化趋势,“注意力经济”使得数字呈现演变为数字就业,女性为了吸引关注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具有较强“性色彩”的内容,强化了自身的审美和商品化,同时也生产所谓“美貌神话”(人造美女),进而引发女性的负面情绪和焦虑[10]。再次,女性主义对网络“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提出质疑,认为女性线上反对父权的行为并未履行其争取平等的政治承诺,更多是参与者的自我满足,同时还因取代传统线下参与而降低了总体参与的水平和成效[15]。最后,社交媒体赋权具有局限性,在西方国家,网络对女性赋权呈现出一定的阶级性与种族性[16],如有色人种等妇女常常被排斥在互联网赋权之外。
互联网对于女性赋权效果的争论也波及到了中国。当前,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端用户的增长无疑开启了中国短视频时代,各大短视频平台凭借“用户原创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模式及轻量化、扁平化、快速化的生产方式,使得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创作者,因此,吸纳了大批分享日常生活的个体加入。其中,抖音和快手是中国短视频的头部平台[17]。快手凭借其简单、平等与普惠的产品理念下沉乡村[18],成为大部分农村用户的首选,农村妇女成为使用较多的群体。而对于快手赋权农村妇女效果的探讨同样有两种对立性观点。肯定性的观点主要有:通过在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的展演及收获的受众认同,农村妇女积极进行着形象呈现与建构身份认同[19][20],这改变了因主体被遮蔽而产生的存在性焦虑,获得了虚拟空间里的本体性安全[21];通过“草根视频”的相关性联结,农村妇女形成包含共同感情联结和相互支持的虚拟社区意识[22],较好地扩展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影响[23];快手成为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广大农村居民生产亚文化资本以及实现资源转换的场域[24],她们通过“短视频+电商”的商业模式改善了自身的经济状况[25],提升了家庭地位。否定性的观点则认为,农村妇女的短视频实践背后隐藏着权力、资本的操控和渗透,农村妇女受到男性和城市人群的双重凝视,常常自我矮化以迎合男性的目光,这加剧了公众对农村妇女的刻板印象甚至“污名化”[26]。
综上,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工具促进女性解放的潜力或许已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但学界对其赋权的实际效果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持续存在着“实质赋权”与“虚假赋权”的争议。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可以发现,社交媒体对女性的赋权实质上是通过赋予其社会可见性或使其进入公共视野而起作用的。然而,可见性并非一种单维面向,对赋权效果的不同看法取决于研究者所关注的可见性的不同层次,如聚焦于“女性被看到”这一状态本身,容易得出女性获得关注与认同、支持与情感慰藉、社会关注度及经济能力等结论;当深入探究“女性被看到”的具体内容时,则易揭示出其形象被贬低、身体被窥探、身份被污名、角色被边缘的去权状态。由此,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可见性的具体层次及与之相关的权力意涵,建构综合性分析框架,以此探究短视频平台上农村妇女的权能变化,进而检视其实际的赋权效果。
二、理论视角:可见性与权力的关系
针对网络新媒体引发的公共空间转变,丹尼尔·戴杨(Daniel Dayan)提出“可见性”(visibility)的概念,意指能否被他人看见、能否获得他人的注意力,当获得的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时便产生了可见性[27]。可见性作为被看到和被关注的意涵并不新鲜,在学理上早有“凝视”或“监视”等概念的讨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把凝视这一观看形式看作现代社会一种有形、具体和无处不在的权力形式和软暴力[28],是社会监控和个体自我规训的技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基于自我发现和主体建构的角度,揭示出他人的存在对自我的结构性功能,或者说我的“为他结构”[29]。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进一步强调凝视的主体“他”不是具体某个人,而是“大他者”,即主宰并质询着个体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化了的符号秩序[30],个体无时无刻不处于“大他者”的凝视下,他以放弃能动者的立场为代价而宣称自己具有符号性的权威,从此成为社会秩序行动与言说所凭借的媒介[31](P152)。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不无讽刺地将此情形描述为“主人总是冒牌货”,被遮蔽的真实主体论证了他者无可怀疑的存在[32]。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则将凝视理论引入性别分析,指出观看分裂为主动男性的“看”和女性的“被看”,男性把他们的目光投射到依照他们的幻想形塑的女人身体上[33]。综上,凝视是一种有权力的建构关系[34],作为凝视对象的可见性总是“去权”的象征,意味着被驱动与主体遮蔽。正如拉康所说:“他人不在场的注视使我‘是其所是’。”[35]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可见性与新公共领域开始勾连,其赋权的一面逐步凸显:一是网络社会的可见性由权力行使对象拓展至权力行使主体,权力处于一种持续的公共注视(public gaze)之下[36](P134);二是在媒介高度社会化的过程中,可见性也超出了他者凝视的狭隘视界,拥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成为主体获取社会认同的象征之一,正如戴杨所说:“公众真正担心的是失去可见性,变得不那么显眼,可见证明他们值得存在,值得重视,隐身使他们重新变得无足轻重”;[27]三是新媒体不仅使公众获得了可见性,而且是“以他们自己定义的方式”(on their own terms)[27],这就使传统规制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分散化了,每个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个体都可以自己设定被“看见”的方式,真实的主体从“遮蔽性”走向“去蔽化”。
根据经典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论述推断,可见性可以包含驱力、审视、主体性、文化、意识形态、展演和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一般而言,从权力凝视下的可见物到新媒体平台上的自我呈现,主体权能的提升源于新媒体平台对可见性内涵的拓展。一是可见的主动性彰显。个体从被言说、被代理、被定义的状态挣脱,被看者是作为与凝视者拥有平等权利的主体,基于“显示自己,让自己被看到”[37](P701)的欲望以及对于权力、审美与价值的追求,主动进入公众视野。二是可见中主体的存续。可见—赋权的最大陷阱是在自己的可见中凸显他人的存在,如同女人们在海滩上穿泳衣,所展示的部位(涂指甲油的脚趾等)或许是为了迎合男性偏好而精心修饰的[38](P11),人们总是根据他者的凝视来表征和刻画自己[39],其结果是主体不断被涂抹、删除乃至消解。在此情境中,依靠可见建立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是虚假而难以维系的。当被看者不必通过“阉割”主体来获得观众认同时,可见的赋权效应才开始具有意义。三是可见的社会性扩展。在女性通过裸露的身体实践宣称其是自己的生活主宰时,许多人阐述这样的身体解放只是一种虚假解放,“一种对否定身体的社会的简单补偿”[38](P11)。因而,个体要避免将他者凝视的目光以及通过社会化媒体获得的公众关注不假思索地视作社会认可,甚至在这想象的认同中消弭了争取权能的动机。
当前,借助网络社会中更加开放与广阔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可见的个体控制力和社会拓展度等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可见性正由单向的被凝视发展为自主的呈现。通过释放既往凝视状态下被压制的主动性、被遮蔽的主体性和被束缚的社会性,可见显现出其赋权的一面。另一方面,虽然新媒体扩展可见的公共性是技术赋权妇女的重要过程,但如若仅仅提升妇女形象的能见度,无视妇女的再生产角色和社区角色,无视影响妇女权利的各种因素,可见也可能是以往权力的凝视的延续,再生产出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40],更强的公共性甚至放大其去权效应,如更广泛的代理、更彻底的形象扭曲、更强的麻痹性等。因而,可见性蕴含了权力的多种可能,既具备“突破凝视—赋权”的潜质,也有“放大凝视—去权”的风险。可见性对于个体权力是增强还是削弱,要视此时可见性是否实现了多维度发展。
基于可见性的理论溯源、学理内涵及实践策略,我们尝试将其分解为三个维度——可见的主动性、主体性及社会性,其组成了个体自主呈现的核心要素,与赋权之“权”(个人权力、社会权力、政治权力)一脉相承,是构筑个体权力的重要内容。因而,可见性与权力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三种要素的排列组合,不同的组合形成不同的赋权形态(见表1):只有主动性和主体性而缺失社会性,容易将个体与外在社会结构割裂并造成权力意识淡薄,即将当前不利处境全然归于自身禀赋不足而未进行结构化归因,难以觉知和改变不合理的结构设置,充其量只是部分赋权。只有主动性和社会性而缺失主体性,是个体放弃独立人格而完全服从规则秩序以换取符号性承认,即权力控制以知识、伦理和审美等形式隐蔽进行,个体在迎合主流话语体系和审美标准中再生产出弱势群体的独特文化、心智模式和生活方式,巩固并强化了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是一种“虚假赋权”乃至去权。此时的社会性异化为“关注即认可,流量即价值”的认同陷阱。只有主体性和社会性而缺少主动性,是一种当事人“隐身”的社会曝光,即习惯沉默、“无知”与无动于衷的个体将言说自身及争取权利的责任让渡出去,他人代为建构的主体易“失真”,导致认识论上的以偏概全,甚至引发误解和污名,是一种无效赋权。综上,主动性、主体性与社会性揭示出“可见性”的前提、关键和本质,不仅关注个体能动的赋权行动,也警惕其因失去主体而导致去权的风险,为探究短视频平台赋权农村妇女的实际效果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

表1 可见性的维度与权力状况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互联网极大地增强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可见性,使其从现实社会里一定程度上的“看不见的女性”走向虚拟景观中“随处可见的女性”。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快手、抖音活跃用户规模稳居短视频平台前两位[17](P29),其中快手短视频凭借更加简便的操作及下沉乡村的营销策略,成为聚集大量农村人口的活跃型网络社区,这也为在家庭内部较为缺少社会舞台的农村妇女提供了机会窗口。由此,我们选取快手平台上农村女性用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筛选检索共得到130名用户的资料,她们在快手上拥有大量粉丝,其中2名用户的粉丝量已超过千万、16名用户的粉丝超过100万、25名用户的粉丝在50-100万,绝大多数用户的粉丝在10-50万。我们着重对她们发布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发现大致涵盖了三方面的主题:唱歌跳舞、乡村日常生活分享、搞笑段子(1)“段子”本指大鼓、相声、评书等曲艺中可以一次表演完的节目,这里指的是主播按照剧本进行演绎的视频,包括自白、情景剧等多种形式,情节多转折、高潮迭起、风格夸张。,占比分别为33.85%、40.00%、8.62%。通过对这些用户发布的视频、直播互动、评论回复、媒体报道等资料的收集分析,并结合对其中7位主播用户的访谈(访谈者信息见表2)以及对2位主播所在乡村的实地走访,进一步梳理并检视农村妇女运用短视频的基本方式、主要内容与实际效果。

表2 访谈者信息
这里需要说明几点。其一,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一般的农村家庭妇女,她们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如没有固定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农业生产或家庭照护作为主要的工作,相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其研究结论只能解释农村妇女网络平台赋权状况,无法延伸至解释其他女性的状况。其二,本研究主要选取了拥有10万以上粉丝的女主播作为资料收集对象,主要考虑到粉丝多的主播其网络平台展演的内容更容易类型化,而粉丝量相对较少的女性网络平台展演内容更碎片化,且缺少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可能忽略了这些女性面临的问题。其三,鉴于研究对象及问题的复杂性,本研究没有面对粉丝群体进行访谈和收集资料,只是通过网络上的留言与互动情况来审视粉丝与博主之间的关系,或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料失真问题,对此我们尽量通过甄别来判断其真实性。其四,网络自媒体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行业,其展演的内容也处于流变当中,我们的研究只是在某一时间节点选取内容,不能穷尽所有内容,也不能涵盖其全貌。同时,对于农村妇女展演的内容的描述也是尽量保持原貌,不加主观评判,也不存在对于她们的“污名”。其五,农村妇女微信平台展演的内容与其他女性群体展演的内容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内容本身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本研究意在关注农村妇女通过现实的台下走到社会的台上,通过呈现这种变化来检视网络自媒体平台作为赋权工具的作用。
四、看见什么:农村妇女自媒体平台自我呈现与赋权后果
多元女性主义代表人伊丽莎白·斯佩尔曼(Elizabeth V.Spelman)在《无关紧要的妇女:女性主义思想中的排斥问题》一书中指出,传统女性主义的错误在于片面认为“只要对男性维持妇女的同一、又维持妇女之间的同一,就可以实现妇女解放”[41](P318)。黑人女性主义倡导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明确指出,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这些观点为我们回到具体情境中窥探被淹没在“大写女性”中的农村妇女提供了视域性工具。显而易见,自媒体平台为农村妇女开启了通向社会的展演舞台,她们同时承担了导演和演员的双重角色,但剧情却并不完全由她们决定,也不只是由观众的视觉所决定,而是受到“凝视”的左右——“论述性决定”,是社会建构而成的观看或审视方式[42](P2)。凝视中夹杂了传统与现代、自我与她者、性别与权力、资本与市场、身体与社会等诸多要素,这又决定了农村妇女并不能自由安排剧情,而是需要精心设计允许被看见或大众期待看见的内容。
(一)农村妇女自媒体平台呈现内容
通过梳理农村妇女在快手平台上发布的1300多条剧情和画面内容,我们发现虽然其形式上呈现出杂乱性与琐碎化,但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三大类型:第一种主要呈现劳作的身体,即彰显一种勤劳、朴实、善良与实干的特质,这也符合社会大众对于农村妇女形象的期待,占比约40.00%;第二种主要呈现“情色”或“暴露”倾向的身体,占比约33.85%,主要通过激发观众被压抑的欲望与潜意识,达到一种“虚拟在场”的满足;第三种呈现自我贬抑的身体,主要通过自嘲、自黑、搞怪及卖惨等反向作用引发观众的猎奇心理,占比约8.62%(另外17.53%的视频内容为独白、风景、晒娃等)。
1.再造传统农村家庭妇女形象
大多数农村妇女在快手平台上发布的视频为乡村日常生活,主要包括干农活、做家务、做饭炒菜、饲养家畜、缝制衣服及展示民间手工业艺等。“劳作不停”成为她们自我呈现的关键词,这种主题不仅唤起了都市社会中人们的“乡情乡愁”,而且满足了人们在商业化及生活外包中期待重塑家庭生活真实性的情感体验。
“乡村利姐”(2)遵从学术惯例,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均已做匿名处理。是快手名副其实的头部用户,粉丝量高达1463.8万。她今年38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家住河南合县普通农村,“做饭”是贯穿其所有短视频及直播的主题。她身着朴实家庭妇女装扮,干净利落,技法娴熟,打卤面、炸糖糕、鸡蛋灌饼、槐花包子、猪肉春卷,甚至是汉堡、酸奶蛋糕、西瓜冻……几乎就没有她不会做的。每次做完饭,利姐就高声喊上老大、老二(侄子)、老三、老四(利姐丈夫)、老五一起开吃……利姐在直播时曾告诉粉丝要用心、用爱给家人做饭,这样孩子才会爱吃,家庭才会幸福。她表示自己开始只是想满足孩子对食物的需求以及照顾生病的丈夫,自己最重要的角色始终是母亲和妻子。
在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图式中,女性主要扮演照顾者的角色,心灵手巧是履行好这种角色的必备品质,而男性则一直处于被照顾的家庭“舒适区”中。然而,随着家用电器及人工智能的普及、家政服务与生活外包的推进、更多妇女从家庭走向劳动力市场等,传统的性别分工图式被逐步地消解,许多妇女开始丧失传统的“家务技能”,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所谓职场妈妈“第二轮班”的双重压力。无论如何,社会大众心目中将妇女视为家庭照顾者的刻板情结并没有消除,利姐的表演正好迎合了这种大众的情感需求惯性,她也是大多数农村妇女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缩影,她们通过极力打造勤劳坚韧、贤惠朴实、无怨无悔的家庭牺牲者形象来迎合观众对于中国传统农村妇女的想象。正如一个高赞评论所说:“老四(利姐丈夫)娶了你,可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这么好的媳妇,又会做好吃的,又能操持家里,在梦里也找不着啊……”由此,农村妇女家务琐碎的视频有着广阔的社会市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大众(尤其是男性)“失衡心理”的变相满足。
2.打造性与性别化的女性形象
借助快手提供的自由舞台,许多妇女通过全新的性别实践打破社会大众对于传统农村妇女的想象。她们的话语和身体一反常态,开始变得“自由放纵”,借助田间地头及屋前院后的乡野独特背景,一人或三五成群,唱着“低俗”的情歌,穿着“暴露”或凸显身体曲线的紧身衣裤,即便面对一些观众的“侮辱性”或“露骨”话语也显得镇定自如,继续取悦着网络观众。
快手用户“农村姑娘艳儿”,家住甘肃农村,容貌和身材比较好,拥有139.7万粉丝。她的视频主要以黄土荒原为背景,身着露脐装、短裙、内衣、高跟鞋等明艳服饰,凸显身体曲线,舞步大胆,唱着挑逗性歌曲……甚至通过“打情骂俏”来吸引观众点赞和打赏。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中指出,上流社会的女性倾向于阅读、休闲与艺术,而下流社会的女性则更多喜欢“唱唱跳跳”[43](P151)。他或许没有觉察到在现实境遇中,这种“唱唱跳跳”并非一种阶层偏好,而可能是一种生存道义,因为身体展演是缺少社会资本的妇女唾手可得的生存资本,她们越是“身体越界”便越能吸引男性的目光,进而换取更多的经济来源。这里需要回应的是,为什么网络时代更强化了这种身体的越界和性别的激化,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网络社会相对于熟人社会具有更强的匿名性,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对于农村妇女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或镜头前的陌生人;二是作为一名以直播为职业的妇女,要学会面对男性凝视的系统脱敏,要学会在性与性别话题中周旋应对,更要学会将工作表演与日常生活道德区分开来。“其实就和平常人上班一样,我固定每天晚上8点上播两小时,内容就是唱歌和陪着聊天,这时候难免要表现得温柔一些,把我的观众捧开心了,他才愿意刷礼物嘛,但平时我都是很稳重的。”(CT1)无论如何,她们呈现出的是一种工具化的身体,或许也可被称为一种网络资本和男性秩序合谋下的“演员”。“最开始我们干农活都是真真正正地干,犁地、插秧、挑菜,结果累死了点赞数顶多500,现在穿得好看些(清凉性感)随便干点活,点赞量轻轻松松好几千。……拍视频就像打游戏,要有装备才打得好,我们的装备就是穿得好看。”(CT3)
3.构建夸张的女性形象
快手上有一些农村妇女以自我嘲弄和自我贬抑作为主要的风格,其短视频剧情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具有一定的怪诞性。这些剧情主要突出“以丑为美”,常常以一种夸大的手法将农村妇女塑造成愚昧、粗俗、刻薄、撒泼、贪婪、自私、物化、逆来顺受、不修边幅的反常形象。
“憨妹”的视频经常展现出被人欺骗和愚弄后还表示十分感激;“王四儿”的视频以吵架为主体,反复塑造出农村妇女的“泼辣”形象;“农村小妮”通过吃香蕉皮、吞芥末、吃肥肉、喝酒等获得过万点赞;还有的视频故意夸大女性的随地吐痰等行为。
农村妇女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展示,对其传统形象既有强化的一面又有颠覆的一面,前者形塑了劳作的身体和贤惠的特质,后者则沿着夸张的形象来勾勒自身。她们通过打破性别的社会界限而制造出一种反常的图景,不再热衷于追求所谓的女性的“美”,而是刻意去建构相反的女性的“丑”。从表面上看,这种自主的行为体现出她们对传统性别制式的一种挑战,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从赋予身体受控制展示的地位中看到了一种“解放”的迹象[44](P38)。事实上,具体到农村妇女在短视频上的展演逻辑,其背后是一种对流量和粉丝数量追求的“幻象”,换言之,她们为了获得流量而主动迎合大众的猎奇与审丑心理,将身体作为一种消费品,同时不惜自我贬损以博得眼球,即便是面对满屏讥讽与恶评也表现得毫不在乎,因为她们遵循一种纯粹的行业法则——流量为王,所以能微笑面对一切。“刚开始挣钱也不多的时候还会计较别人的目光,后面收益上来以后真的是完全不放在心上了。……我越大方地演,演得越夸张,人家越知道这只是表演。”(DZ1)
(二)农村妇女自媒体平台赋权效果分析
网络或许是人们能超越社会阶层而彰显出共同志趣的事物,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空间与社会阶层的区隔,实现了知识获取的便利性,推动了个体的自主参与和自由表达。不仅如此,个体通过网络形成的合力具有一定“社会变革”助推功能,一个视频通过网络发酵可以成为刺激社会有机体的“强心剂”,如网络防腐、网络推动政策调整便是很好的例证。与此同理,网络等自媒体平台无疑会推动农村妇女实现一定程度的赋权与增能,如经济利益的获取、独立性的增强、社会关注度和存在感的提升、通过互联网建立支持网络,有的还被纳入宣传体系中。但这些背后始终充斥着社会大众的“凝视”。从此意义上讲,农村妇女网络赋权具有虚拟性和虚假性,是一种赋权中的去权,是“看见的看不见”。
1.经济收入的“实”与“虚”
农村妇女不同于其他女性的显著特点是,她们是一个与家庭照顾捆绑在一起的群体,更多地游走于经济市场边缘或之外,也因其家务劳动没有用货币表现而被价值“贬抑”,这也造成了男女两性在职场上的“收入差距”和在家庭内部的“闲暇差距”[45](P15)。女性在两种差距中均处于不利的位置,而农村妇女因缺少就业机会而显现出更大的差距,她们照料家庭或就业的选择更多地参考了服务和保障男性就业的需要,这意味着必须接受更低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来获得工作时间的灵活性[46]。这种境况导致了农村妇女相对而言在家庭和社会地位的“双低性”,即便是经济收入提高也是一种反常或偶然现象,较难获得家庭和社会应有的承认。
短视频等网络平台为农村妇女提供了一种在家庭内部创造看得见的经济价值的机会。一方面,它借助数字技术使得随时随地生产画面和剧情成为可能,形成一种灵活就业形式,契合农村妇女因操持家务而被固定的空间和切碎的时间;另一方面,它的“用户生产内容”的生产模式、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及算法推荐使其极具包容性,任何内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受众。由此,农村妇女的日常劳作或自我展演也受到关注并转变为流量获得收益,进而提升了她们的经济收入。
农村妇女在快手上将流量变现的主要途径包括:(1)给商家带货赚取佣金,具体包括开通快手小店、通过短视频或直播宣传;(2)直播间的礼物打赏,直播结束后可即时将礼物变现。这两种途径都需要先通过短视频发布积累大量的流量。
大部分使用网络短视频平台的农村妇女源于“生存道义”,其丈夫的收入并不高,这也符合“道格拉斯—有泽法则”(丈夫的收入与妻子的劳动参与率成反比)[47](P4)。这种经济收入在“实”背后更有其“虚”的一面。一是短视频作为新事物发展前景并不明朗,随着使用人数增多竞争愈发激烈,收入浮动性较大,博主们随时会面临“过气”的风险,必须绞尽脑汁设计视频吸引流量,有的甚至采用自贬手段,这也使得农村妇女可能沦为流量的“客体”。即便如此,未来恐怕也难以摆脱网络事物“昙花一现”的宿命。二是拍摄短视频对农村妇女来说是“打零工”,并非真正的就业,她们的经济收入被解读为是靠“唱唱跳跳”取悦男性获得的“打赏”,也被指责为“为了挣钱而毫无底线”,这与她们的丈夫靠“勤劳”和“汗水”换来的经济收入似乎是不对等的。因此,农村妇女虽然创造了经济价值,但依然难以被家庭和社会尊重并承认。
今年是“王二妹”拍短视频的第四个年头,但粉丝量卡在10万怎么也上不去。据她说,之前为了增加播放量已经把自己的家长里短、人生经历拍了个遍,甚至“家庭大战”也“演”了几回,现在创意有点枯竭了。“拍普通生活日常根本没人看,而如果是拍吵架或是惊喜啥的,人家一看就说是有剧本,也不乐意看。”“王二妹”的账号已经停更2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她去学了美甲。“一方面是在累积视频素材,另外也是给自己以后留条后路。”(LD1)
2.虚拟的“中心感”与现实的“边缘性”
农村妇女作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更多地被一种“缄默文化”所形塑,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相较之其他被凝视的女性甚至缺少凝视的目光,亦缺少社会展示的舞台,自我效能感相对较低。短视频平台使其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中心感”,如农村妇女快手主页上的讨论基本都围绕自身展开,她们经常作为主体回应关注者的问题,她们通常称呼自己的“粉丝”为“家人”,不仅从“家人”身上体验到被关注的感觉,更在其肯定和关心中找到了存在感。乡村利姐说:“越来越多的‘家人’们关心我、牵挂我、在乎我,有时候我生病没有直播,‘家人’们会发私信问我怎么了,甚至是给我寄药,家人的牵挂让我非常感动。”[48]其他主播也有同样感触。“虽然明知道评论区有很多赞美和关心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我真的特别感动,这种感动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不管是不是虚情假意,至少有人在乎你。”(CT2)事实上,很多农村妇女在异性粉丝的吹捧中有一种处于两性关系中心的错觉,尤其是构建高度性别化形象的妇女,她们通过“挑逗”和“面对骚扰保持沉默”等方式与男性粉丝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迎合”男性的各种“诉求”,甚至承受着“网络性骚扰”,另一方面又享受诸多男性粉丝的追捧甚至争风吃醋,在主动与被动中建立了在两性关系中的优势地位。
“农村姑娘艳儿”最新发布的一条视频评论里全部是男性的夸赞,不仅有大量的玫瑰花、爱心等表情包,还有“我爱你”“跟我回家”等露骨的表白。在“艳儿”2020年跨年直播PK上,粉丝给其刷了大量礼物,“艳儿”挨着给每一位送了礼物的“哥哥”道谢,竟然还引起了粉丝间的争风吃醋——“昨天还感谢我呢,今天怎么就那么热情地感谢他们了”。
农村妇女从网络中获取的“中心感”也可以投射至现实生活中,转化为身边人的争先模仿和学习,但就像其短视频生涯的前景模糊和跌宕起伏,这种“中心感”短暂易逝,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得更加直观。“有一段时间做得确实不错,去赶集街坊都说我是‘网红’,基本上每天都有人从市里开车过来找我合拍。现在流量不行了,一些难听的闲话也出来了。”(LD3)可见,虚拟的“中心感”不仅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变现”,反而是堕入了以流量逻辑编织的另一种边缘:“没有流量,人家当你啥都不是。”(LD3)
更为根本的是,农村妇女短视频平台赋权后果呈现出一种看似中心的边缘性。一方面,“乡村利姐”等打造传统形象妇女的中心感是建立在以家庭为中心而自置边缘性基础之上,粉丝更多的是对一种默默无闻家庭照料者、无私奉献的妻子和母亲角色的认同,而不是对作为女性主体性的认可;另一方面,“农村姑娘艳儿”等塑造“性感”妇女形象的中心感依附于传统性别秩序基础之上。这便形成了一种中心感与边缘性的矛盾,农村妇女作为社会中的相对边缘群体寄希望于网络带来的中心感和获得感,而中心感的获得又是以复演男性期待的角色和迎合男性偏好为前提的,这形成了一种凝视下的展演,因此,她们通过网络强化中心感的同时更强化了社会的边缘性。
3.经济“接纳”与社会“排斥”的张力
网络极大地拓展了农村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空间,尤其是微视频平台将女性身体展演、商业与消费主义勾连在一起,使得乡村社会建设中的性别元素更加凸显。一定程度上,农村妇女相比男性在微视频平台上更具主动性、主体性与价值感,她们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通过直播带货等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和土特产行业的发展,彰显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她力量”。这也契合并充实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等国家话语体系的内涵,由此不同程度地得到宣传鼓励和政策支持,逐步走向“国家承认”。
“乡村利姐”或许做梦也没想到,县委统战部领导一行专门探望了她,鼓励她立足优势,发挥影响力,通过网络平台把县名优特新农产品推介出去,鼓励她为家乡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做出应有贡献。她还作为优秀代表被当地妇联邀请参加2021年黄河巾帼风采展示活动。对此,利姐表示,她会继续发挥正能量,带动和影响更多人,为家乡发展献计出力。
国家在场是对农村妇女在网络经济中发挥正向作用的承认,有的妇女还被赋予各种“精英”称号,这对她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赋权。然而这种承认还有拓展空间。一方面,自媒体等短视频领域目前还是边缘性职业,相对而言属非正规经济,对从业者一般不设门槛,再加上农村妇女所处的“屈从地位”,她们通过网络劳动创造的价值很容易被矮化,常被解读为是通过“唱唱跳跳”“不务正业”而获得的“意外收入”,在社会合法性上会大打折扣。“我对象不愿意在我视频中出镜,也不和别人说我是干这个的。原来拍视频收益可观的时候他没说什么,最近收益不行了,他就一直让我去找个正经班上。”(LD3)另一方面,短视频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内容,尤其是一些缺少社会资本的妇女选择通过“身体资本”吸引大众的关注,而这些妇女很容易被社会大众无限放大将其等同于所有参与网络视频的妇女,进而被贴上负面标签。这也导致许多丈夫虽然享有妻子拍摄短视频带来的经济收益,但内心却担心周围熟人对妻子的评价会给自己家庭带来“不好的名声”。正如一名受访妇女所说:“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瞧不上我干这个,他怕别人笑话,说自己抬不起头,但毕竟能有经济收入,他也没办法……”(CT2)她们在家庭中尚且如此,在社会中的处境可想而知。因此,农村妇女参与网络平台面临着经济接纳与社会排斥的非均衡性。
大庆(LD2)从2018年开始做短视频,到如今已经积攒有40万的粉丝,不仅在家乡农产品滞销时为其带货,还顺势建立起自己的食品加工厂,吸纳了村里闲置的劳动力,被媒体称为“乡村守护人”。当地政府本想复制大庆的成功,培育一批本土带货主播,但无疾而终。村干部解释说:“看大庆拍视频顺眼是因为她已经成功了,村里别的大娘每天正事不好好做,就拿个手机琢磨怎么拍,被村里人认为是‘不过日子’的人,她们家里人不乐意了,很快就消停下来。”
五、结论与讨论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Nicholas Abercrombie)认为,电视打破了穷人被排斥在信息和娱乐大门之外的局面[49](P3),而短视频等网络自媒体比电视更为彻底,它消解着影像传媒的神圣性,消弭着景观社会中演员与观众的区隔,制造出一个区别于现实社会的“视觉微社会”。基于短视频自媒体人人可用、人人可享的功能,社会边缘群体获得了走向网络中心的机会,尤其是平时在社会中“看不见”的农村妇女变得“随处可见”。相对其他女性而言,这个群体的“第二性”位序更加明显,她们始终处于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照护、辅助、缄默勾勒了其同质性的生命样态。而短视频平台使她们从“家庭内部”走向“社会舞台”,从经济依附性走向相对独立性,从台下的“观众”演变为舞台中心的“演员”。这种网络短视频催生农村妇女“蜕变”的过程即是一种赋权和增能,基于实际赋权效果的检视以及能否打造一个网络性别新秩序的追问,我们诉诸“可见性(凝视)—权力”分析框架,结合视频呈现内容,分别从主动性、主体性和社会性三个维度进行了剖析。首先,农村妇女网络视频赋权呈现出“主动的被动性”。一是她们使用自媒体平台并非基于意识觉醒和性别行动,而是基于一种生存道义,因为现实社会留给她们的就业空间有限,所以是一种“网络中觅食”的生存轨迹。二是她们进入短视频领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视频展演的“唱唱跳跳”与“成熟稳重、不苟言笑”的男性气质格格不入,这些为农村妇女让渡了尝试新事物的空间和机会。因此,生存—机会构筑了她们进入网络视频世界的主动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农村妇女定义自身和争取认同的自由表达和自主行动,但因生存逻辑的裹挟及短视频的“轻浮”气质,其主动性中有一定的强迫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其次,农村妇女网络视频赋权呈现出一种“主体的客体性”,她们对视频内容的设计、画面的掌控、自我呈现等都折射出了其主体性的一面。然而,这种主体性不是独立存在的,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框架内必然受到“凝视”的主导和左右,即她们以他人为对象而改造自己并形塑一种大众期待的形象,而这事实上是一种新的客体化,存在感并不明显,具体表现在农村妇女为收获更多认可的目光而在短视频平台上呈现出传统性别秩序中照顾者和性别化的女性形象。最后,农村妇女网络视频赋权呈现出一种“看见的看不见”,网络视频平台助推农村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并构筑属于她们自己的“视觉小社会”,然而,小社会的性别秩序和权力结构依然是现实社会的复制或投射,她们并没有形成一种“性别共同体”,虽然从“观众”成为“演员”,但却不是“导演”,更受到“观众”的凝视的形塑。短视频非但没有实现被寄予的话语平权以及撬动不合理社会结构的期待,甚至在再生产传统女性形象并赋予其更大可见性的过程中强化了既有的权力秩序。从此意义上说,网络视频中农村妇女的被看见可能是一种幻象,网络中越是被凸显现实中越是被遮蔽。
综上,网络平台以其技术可供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挣脱不可见的状态,显现出激发主动、彰显主体及建构社会的赋权表现,但传统性别法则和权力结构依然渗透进网络平台赋予的可见性中,引诱、压抑和控制着农村妇女的自我呈现,因而对农村妇女赋权或许是一种虚假赋权或部分赋权。由此可知,要促成农村妇女赋权式的自我呈现,既要依靠技术革命以实现广泛的可及性,还需要加强平台规制以规范农村妇女的自媒体使用,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持续的性别教育营造出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并促进农村妇女的自我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