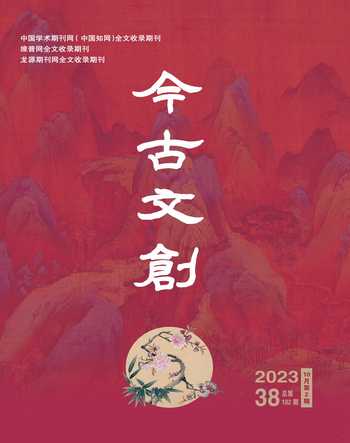云浮白话邪母读音类型的差异及成因
刘婉平


【摘要】云浮白话邪母的读音类型按照发音方法可分为“塞擦音型”和“擦音型”两种,其中云城、新兴和罗定白话的邪母字多读[ts]、[tsʰ],属“塞擦音型”,与广府粤语基本相同;而郁南白话的邪母则多读作边擦音[ɬ],属“擦音型”,与勾漏粤语一致。早期粤语的形成过程和云浮地区的移民历史显示,云浮白话邪母字读音类型的差异是壮侗语底层特点的保留及宋代共同语对云浮地区早期粤语覆盖不均匀所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粤语;云浮白话;邪母;读音类型
【中图分类号】H1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8-01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8.035
一、引言
云浮市地处广东省中西部,西江中游以南,东连珠江三角洲,西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于1994年设为地级市,辖云城区、云安区、新兴县、郁南县,代管罗定市,截至2020年云浮市户籍人口为302.11万人。云浮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多丘陵地貌,山区面积占比大,是典型的山区市,主要河流为南江和西江,历史代表文化有西江文化、南江文化和六祖禅宗文化等。云浮市主要有云浮白话、客家话、闽语及㑷古话四种地方方言,其中云浮白话是云浮市的通用方言,分布地区最广,使用人口约占全市人口的90%。詹伯慧(2002)将云浮(今云浮城区)、郁南、新兴、罗定的白话均划入粤语广府片[1]1。但其他学者对罗定和郁南两地白话的归属存在不同意见,如熊正辉(1987)则根据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是否送气,将罗定和郁南白话归入粤语勾漏片[2]161-162。由此可见,云浮各县白话方言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差异在语音上有多种体现,其中云浮白话不同方言点中古邪母的今读类型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
二、云浮白话邪母的读音类型
由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的《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曾对当时云浮市辖区下的云浮县(现云浮城区,包括云城区和云安区)、新兴县、郁南平台镇和罗定市(今属云浮县级市)的方言进行实地调查,详细地记录了云浮市各方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情况,描绘出了云浮方言的总体面貌[3]。本文以云城、新兴、罗定及郁南平台为方言点,以《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中记录的语音材料为参考,将云浮邪母的读音类型按发音方法分为塞音型和塞擦音型两种类型。其中云城、新兴和罗定的绝大多数邪母字今读为塞擦音,我们将其邪母读音类型归为塞擦音型;而郁南平台的邪母字大多读为边擦音,则将其邪母读音类型归为擦音型。
(一)塞擦音型
《方言调查字表》中共有中古邪母字47个[4],云城、新兴和罗定的邪母大多今读为塞擦音[ts]、[tsʰ],其中云城和新兴今读塞擦音[ts]、[tsʰ]的邪母字有39个,占总数的80%以上,只有止摄合口三等、山摄合口三等的邪母字以及“叙”“绪”“羡”共8个字文读作擦音[s];罗定的邪母也以读塞擦音[ts]、[tsʰ]为主,但其今读塞擦音的邪母字略少于云城和新兴,占总数的65%以上。云浮白话邪母塞擦音型的主要特点是今声调读阳平和阳上的邪母字基本都读送气清塞擦音[tsʰ],今聲调读阳去和阳入的读不送气塞擦音[ts],与广州话邪母字读音特点基本一致。因此,侯兴泉(2012)在讨论粤语从、邪母读音类型时,将云城、新兴和罗定的邪母读音归为“广州话型”[5]267,具体情况参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罗定白话的邪母读音存在与广州话读音不一致之处,比如今读阳去的“袖”在罗定白话中读送气塞擦音[tsʰ],并且罗定白话的一些原本应读为塞擦音邪母字,实际上却读为擦音[s],与同为“塞擦音型”的云城及新兴相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邪母读音“擦化”的特点。这种“擦化”现象主要出现在遇、止、臻、梗四摄,这可能是由于辅音弱化、塞音脱落所导致的擦化,也有可能是与郁南白话接触所导致的变异。但无论这种“擦化”是语言自身的演变还是语言接触的结果,目前绝大多数罗定白话邪母字仍读作塞擦音,读擦音[s]的现象只占少数,所以就整体而言,云城、新兴、罗定这三点的邪母读音类型归为“塞擦音型”是比较合理的,它们基本上与广府粤语的主要读法保持一致。
(二)擦音型
郁南平台话邪母的主要读音和云浮其他方言点都相去甚远,以读边擦音[ɬ]为主,47个邪母字里有34个读[ɬ],占总数的70%以上,只有少数字读作塞擦音[ts]、[tsʰ]或擦音[s],我们将其邪母读音类型归为“擦音型”。侯兴泉(2012)的研究表明,郁南平台邪母读法和相邻的肇庆封开境内的董罗粤语、广西梧州境内的藤县粤语及岑溪大业粤语等勾漏粤语的邪母今读完全一致,均读为边擦音[ɬ][5]271,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侯兴泉(2012)还指出,邪母今读为擦音或边擦音的方言区都是南方壮瑶等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这类读音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或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转用汉语所致[5]271。
简而言之,云浮白话邪母的读音类型的内部差异主要表现为云城、新兴和罗定的邪母读音类型为塞擦音型,和广府粤语一致;而郁南的邪母读音则以读边擦音为主,与勾漏粤语相同。
三、读音类型差异的成因
《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不同文化从相互隔离进入渗透和交融状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的迁徙,即移民。移民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6]12。”云浮白话邪母读音类型的差异的形成与由移民所致的语言接触密切相关,涉及粤语不同的历史层次,我们结合早期粤语的形成过程和云浮地区的移民历史,将云浮白话邪母读音类型差异的主要成因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壮侗语底层特点的保留
学者一般认为粤语的边擦音主要来源自少数民族的底层,麦耘(2012)曾指出壯侗诸语言中不少有[θ]/[ɬ]这类音,并且历史上一直有这类音,如壮语中被写作[s]的音,在武鸣壮语中的实际读音为[θ],在龙州壮语、剥隘壮语中则读作[ɬ][7]7。先秦时期,岭南百越人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古壮侗语。史载秦二十五年,秦始皇派大将王翦平定南越,后又派赵佗率兵远戍五岭,这些秦卒分驻岭南多处,这时中原与岭南的交通线是以水路为主的“湘水——灵渠——西江中游”一线,所以西江中游成为南来秦卒的主要驻扎和聚居之处。秦卒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中原汉语,而岭南土著操古壮侗语,由于秦人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征服者,其语言则成为该地的优势语言,当地人出于交往需要学习中原汉语,又因当地人是基于自己的语言系统来接受汉语,在语言转用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完善学习效应,将自己母语的一些特点带入其中,成为其“底层特点”。麦耘(2010)把这种自秦汉以来流行在岭南地区、与当时北方汉语相近、带有少数民族语言色彩的汉语方言称为“古代岭南汉语”,其此后不断受到共同语的影响演变为早期的粤语,其中精组读[*tθ]/[*tɬ]等是这种古代岭南汉语或早期粤语的底层特点之一[8]238。
云浮地区自古为百越地,北方中原移民的逐步流入该地区的开发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云浮通史(古代卷)》指出,秦军进入云浮市境时,当地越人转入丛林,南来秦卒虽然与越人杂处却未深入至云浮境域,再加上地理位置偏僻闭塞,郡县统治鞭长莫及,因此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程度并不高[9]2。南越国以后,因从军、落籍、流放、避难等原因流入的北方中县之民沿着“湘水——灵渠——西江中游”一线到达今云浮境内,并对深山进行改造和开发,与当地越人杂居往来,促进了云浮境内的汉越文化交融[9]37-38。这时,一部分越人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被汉化,他们在学习中原汉语时将自己的母语特点带入其中,边擦音[ɬ]因此作为壮侗语底层特点得以保留在云浮地区的早期粤语当中。
(二)宋代共同语的不均匀覆盖
麦耘(2009)指出,“中心区域的文化和语言对边缘区域长期保持着压倒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会把中心区域的语言演变结果一波又一波地传播给边缘区域,使那里的方言跟着跑[10]223。”在我国历史上,中原文化长期占据中心地位,中原汉语也往往作为覆盖面极广的权威方言使用,而粤语分布的岭南地区过去则是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缘区域,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原汉语往往通过移民等方式一波又一波地影响和改变着岭南地区的语言。因此,麦耘(2010)认为,宋代大批的北方移民经大庾岭来到岭南地区,并以粤北珠玑巷为起点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们的语言给粤语广府片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使之发生变化,从而与西部的粤语(如勾漏片)拉开了距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精组的读法。在宋代共同语的精组是读[*ts]等,而粤语广府片精组从早期读[*tθ]/[*tɬ]等到后来变成[ts]等,是受宋代共同语的影响的结果[8]228-229。本文所讨论的邪母字也属于精组字,由此看来云浮白话邪母字今读为塞擦音[ts]、[tsʰ]的类型,也是受移民带来的宋代共同语精组读音影响而成。
《云浮通史(古代卷)》指出,现存广东及云浮市的许多族谱和族源资料,多有记载其祖先多由北方迁至粤北南雄珠玑巷,后又迁往某地的历史。比如,云浮市云城区古宠村的《苏氏族谱》记载其祖先多从南雄珠玑巷南迁,并分散定居在新兴县云礼村、凤翔里、罗定大傍村等地。又如,罗定素龙三达祠谭井村的《梁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梁焘于北宋末年任尚书、丞相,后被贬南迁,定居于珠玑巷,梁氏后人遭变故又迁至康州泷水县(今罗定)定居等等[9]127,记录了这种移民历史的族谱资料还有很多。可见,南宋时期北人经珠玑巷或以珠玑巷为起点迁入岭南地区,其中一些北人迁入新州(今新兴)、康州泷水县(今罗定)等地区,这些中原移民一定程度上在今云浮市境内传播了中原汉语。此外,两宋时期,一些中原士宦从外地进入新州(今新兴)、康州泷水县(今罗定)、端溪县(约今郁南、云城中西部、云安北)担任重要官职[9]134,他们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力兴办州学和县学,使宋代共同语的读书音在云浮市境得以传播。由此,今云城、新兴、罗定地区的早期粤语不断受到宋代共同语的影响,其精组字的读音[*tθ]/[*tɬ]最终被宋代共同语覆盖为[ts]、[tsʰ]。
虽然宋代珠玑巷移民和仕宦兴办教育带来的宋代共同语会对云浮地区的早期粤语加以覆盖,但这种覆盖往往会因为受到阻碍而变得不均匀,而这种不均又会造成语言的内部差异。造成覆盖不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北人南迁路径改道的影响,大庾岭新道开发以后,岭南与中原的沟通的通道东移,自广西灵渠而下岭南的水道逐步被大庾岭陆路所取代,取道西江的移民变少,中原文化及语言对西江地区的冲击自然会减弱;其次是郁南地区在地理上则更靠近少数民族聚居的苍梧地区,长期与少数民族接触;另外郁南地形多山、闭塞偏僻,远离当时的州治新州(今新兴县),因此接受当时中原文化影响程度并不高,故难以受到宋代这一轮中原汉语的均匀覆盖,其古壮侗语底层中的边擦音[ɬ]得以较好地保留在其语言当中。
四、小结
云浮白话邪母的读音类型按发音方法分为“塞擦音型”和“擦音型”两种,其中郁南平台的邪母读音类型为“擦音型”,多读为边擦音[ɬ],和勾漏粤语邪母读法一致,边擦音[ɬ]是云浮百越先民在汉化过程中学习中原汉语带入本民族语言特点而保留的古壮侗语底层,也是早期粤语的底层特点,如今表现为两广交界地带的语言特色。而云城、新兴和罗定的邪母读音类型为“塞擦音型”,多今读为塞擦音[ts]、[tsʰ],与广府粤语的读法基本相同,这是由于北人南迁传播中原汉语以及入粤仕宦兴办教育,使广东包括云浮地区的邪母读法受到了宋代共同语的影响而同化,并且保留至今,成为现代粤语邪母最主要的读音类型。粤语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受到不同时期中原汉语(共同语)影响形成了不同历史层次,而各个历史层次的中原汉语(共同语)对广东境内各地早期粤语的覆盖不总是均匀的,其中边远偏僻的地区往往难以受到覆盖,容易保留其底层语言特点,最终导致了如今云浮白话邪母读音类型的内部差异。
总的来说,云浮白话邪母两种不同的读音类型反映出云浮白话存在广府粤语与勾漏粤语特征叠置的特点,所以云浮方言特色的挖掘和探究对两广交界地带粤语的语言接触及历史层次研究有着较高的价值。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特征的叠置实际反映出了文化间的融合,由此可见,广府文化和苍梧文化的融合是西江流域一带重要的地域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詹伯慧.广东粤方言概要[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2]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7,(03):161-165.
[3]詹伯慧,张日昇.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侯兴泉.论粤语和平话的从邪不分及其类型[J].中国语文,2012,(03):266-275+288.
[6]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麦耘.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A].麦耘.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1-24.
[8]麦耘.粤语的形成、发展与粤语和平话的关系[A].潘悟云,沈钟伟.研究之乐——庆祝王士元先生七十五寿辰学术论文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227-243.
[9]赖少雄.云浮通史(古代卷)[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21.
[10]麦耘.从粤语的产生和发展看汉语方言的形成模式[J].方言,2009,31(03):219-232.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