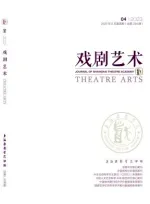中国当代“导演戏剧”类型论
杨 光
导演是戏剧演出文本的创作者,其地位直接左右着一个时期演剧类型的整体风貌。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创演从“剧本中心”转向“导演中心”,由导演催生的各种新型演剧形塑了当代话剧舞台。但是,比较特殊的是,中国当代“导演戏剧”并非单一的戏剧类型。这并不是说导演者的具体风格存在差异,而是说当代导演虽聚拢于“导演中心”的旗帜下,但其“中心化”的程度不尽相同,正是这种“中心化”程度的差异造就了“导演时代”的多元格局。如果忽略了这个层次的差异,笼统地讨论“导演中心”的利弊得失,很容易流于空疏。
一般来说,“导演中心”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舞台呈现开掘了剧本的思想纵深,扩展了剧本的思想容量,实现了剧本的思想潜力,导演赋予了演出以密集的思想和高浓度的人文品格;第二,导演者在戏剧生产中作为组织者的“集权”性越来越强,大有取编剧而代之的趋势。两个层次“导演中心”中的“导演”一词各有所指,前者指的是“现象学导演”,即演出显示出来的导演,后者则是指在现实或历史中创造出这个作品的导演。(1)杜夫海纳区分了“现象学作者”和“创造出这个作品的作者”,笔者对“现象学导演”的区分源出于此。杜夫海纳认为,研究审美经验主要是研究欣赏者的审美经验,即便是艺术家的经验,也应当主要研究作品中呈现出的艺术家,而不是历史或现实中的艺术家:“这里所指的作者是作品显示出来的作者,而不是在历史上创造出这个作品的作者。”(杜夫海纳: 《审美经验现象学(上)》,韩树站译,陈荣生校,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这个区分对于从理论上把握“导演中心”现象很有意义。过去,研究“导演”常常对“现象学导演”和“历史或现实中的导演”不加区分(陈世雄的《导演者: 从梅宁根到巴尔巴》是少有做了区分的著作,陈著以“导演者”而非“导演”“导演艺术”命名所强调的即是以“历史或现实中的导演”为研究对象),以“导演阐述研究”取代“导演研究”在话剧史研究中非常普遍。研究“历史或现实中的导演”有其价值和意义。但若研究戏剧审美问题,仍需以“现象学导演”(演出所呈现的导演艺术)研究为主,“历史或现实中的导演”(导演者)的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作为辅助和参考。不过,在“导演中心”的历史演进中,两个维度往往相互渗透: 一方面,通过开掘、呈现剧本的深度思想,导演群体建立起整个行当的话语权,成为公认的戏剧思想表达的指挥者;另一方面,通过行使已经形成的行业话语权,导演得以在剧目搬演中近乎偏执地将作品风格同化为导演风格。从具体实践来看,有的导演偏重于借助“前理解”同文学展开创造性对话,有的导演偏重于以个人风格对文学加以同化,更有导演直接对文学施以素材化、边缘化的处理。三类“导演中心”共同形塑了中国当代剧坛的“导演戏剧”。
一、 “思想开掘型”演剧与“剧本荒”的掣肘
当代导演在和文学的平等对话中形成了“导演戏剧”中的“思想开掘型”演出。“思想开掘型”是中国“导演戏剧”最早出现的类型,也是“导演时代”的主力军,它大致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为代表,90年代以来王晓鹰、查明哲、王延松、陈薪伊、廖向红、曹其敬等导演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思想开掘”的新路径。从艺术风格上来说,这批导演的风格底色仍是现实主义,他们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导演手法的借鉴和吸收拓展并深化着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
“思想开掘”是相较于过去“如实”呈现剧本的导演创作模式而言的。在传统的编导互动中,尽管也存在演出“高”于剧本的状况,也出现过焦菊隐这样的大师级导演,但就整体而言,演出的思想容量与剧本差别不大。导演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对文学语言的立体化,深度开掘比较少见。“思想开掘型”导演强调对剧本的“开掘”,在他们眼中,剧本思想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某种“潜力”,有其必要的张力和幅度。导演除了技术性地将剧本转化为“有意味的形式”之外,还要将剧本的思想幅度“撑”到最满,用导演的“解剖刀”加强对人物内在世界的开掘。胡伟民在执导《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前曾和剧作家通信沟通,他指出:“表面上看,你们讲了一个毫不新鲜的故事。可是,一条痴心女子寻找负心汉的主线,怎能散发出如此奇特、如此众多的信息量?这,实在令人惊愕不已。”(2)胡伟民: 《导演的自我超越》,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196—197页。胡伟民看似矛盾的阅读体验实际上显示了剧本内在的思想幅度: 既可是“毫不新鲜”的,也可散发密集的思想。作品上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导演的“开掘”功力,从“痴心女子负心汉”的老套故事到具有象征意蕴的灵魂典仪,这点睛之笔无疑源自导演。从这个意义来说,“思想开掘”的对象虽然仍是剧本,但搬演到舞台上已经打上了极强的导演烙印,成了不折不扣的“导演戏剧”。
“思想开掘”的另一种形式是对剧中人(尤其是主人公)的人文阐释,这在政府运作生产的主流戏剧中体现得最明显。众所周知,由官方主导的话剧创作常常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回避对主人公的日常书写,以凸显其英雄事迹。但是,如果舞台上只是“英雄事迹”的转述,只“可以为戏剧带来华丽和威严,却不能令人感动”(3)[德] 莱辛: 《汉堡剧评》,张黎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74页。,于是出现了“英雄事迹+有限度的情感生活/性格缺点”的创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英雄事迹”确保了官方需要的“威严”,“有限度的情感生活/性格缺点”则提供了普通观众需要的“感动”。这种创作模式在影视剧中也很常见,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亮剑》基本上延续的都是这一路数。在创演实践中,由于政策限制,剧作家很难在剧本中正面展开对“缺点”的描写,最多给以必要的暗示,所以,演出最终能否“令人感动”更多取决于导演。比如,在话剧《柳青》中,编剧把柳青当做伟人来歌颂。但在导演处理中,剧本对柳青的日常叙事在舞台上得到了加强。作品中,柳青有一系列崇高行为,比如让妻子随自己搬迁至农村,把公家配的汽车退回,把应得的巨额稿费全部支援给村里建设等等。导演处理这些场面时没有孤立地凸显崇高与伟大,而是以此为情境揭示柳青在夫妻关系、父女关系中更具人性的一面。这些“情感戏”相当动人,其情感浓度远远超过了柳青为农民排忧解难、执着写作《创业史》一类的“英雄事迹”。就剧本而言,全剧的高潮是柳青回村,村民纷纷向柳青致谢,这是全剧的“点题之笔”。但演出中,柳青和妻子在政治风波中的生离死别,妻子投井自杀的场面显然比“村民致谢”更具感染力。在这里,导演通过对“英雄”的人性开拓使戏剧演出从表层的“事迹真实”逐步触碰“人性真实”。
“剧蕴发掘”和“人文诠释”作为“思想开掘”的两种方式一般交叉运用,比如《桑树坪纪事》,徐晓钟从剧本的深层意蕴中凝练出“围猎”作为“形象种子”,把桑树坪上发生的多起迫害结合在一起生发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戕害”乃至“自戕”的悲剧性体验。同时,在象征化地展示“围猎”意蕴的过程中,徐晓钟也把对人物的诠释推向了一种高度。尤其是对李金斗的塑造,他亦正亦邪,是“被人抽打的羔羊,同时又是吞噬生灵的一只猛虎”,导演是站在人类学的视角以悲悯的眼光塑造李金斗这个“人”的:“作为一队之长,他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护卫着全村老小几十口的生计,他也常常出自‘好心’地为村人奔走婚丧嫁娶,然而他心里的封建宗法家族观念、婚姻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狭隘、闭锁等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以及他身上的‘左’的积习,使他可爱、可怜又可恨。”(4)徐晓钟: 《导演艺术论(上册)》,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160页。在演出中,导演一方面深挖李金斗的可爱、可怜、可恨,同时又以李金斗为“中介”完成“围猎”的象征化呈现,使剧本经由导演“思想开掘”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和思想高度。
但是,“思想开掘”并不意味着导演的处理总能“大于”剧本。作为一种戏剧类型,“思想开掘”本身不包含价值判断。在具体执行中,导演失手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有的剧本以人物塑造的丰富性见长,但导演却向其象征意蕴“用力”,或者剧本以文化反思见长,却被导演处理得过“实”。对于高质量的剧本而言,即使发生了“误读”,一般观众也未必能识别,但演出的思想含金量会大打折扣。比如,陈薪伊排演《原野》时声称希望观众看戏时不要太过于压抑,甚至要有一点笑声。但《原野》剧本的“底色”就是沉重: 一个人面对杀父之仇、夺情之恨、错杀之苦都很难笑出来。在演出中,陈薪伊尝试以各种方式冲淡剧本的晦暗底色。尤其是第三幕,导演直接把“铺满金子的地方”以投影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在金灿灿的稻田背景下,原作中的自杀被演绎成了主动求死,仇虎被导演艺术化地加工成了一个商鞅式的悲剧英雄。导演想用“亮”色的舞台处理来表达仇虎主动赴死的崇高性。不过,在曹禺的《原野》中,主动求死的崇高远不及一个在牢笼中左突右撞的灵魂更深刻。陈薪伊对剧本的错位解读导致她的种种舞台加工仅流于表面。类似“开掘偏差”的情况很常见,最糟糕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导演、剧作家和观众的“三输”。
不过,对中国当代导演而言,“思想开掘”面临的首要困境仍在于“剧本荒”。“思想开掘”的前提是“思想”,如果剧本本身思想浅薄,导演再用功也很难“掘”出洞见,正如导演查明哲所说:“那些贫瘠的、没有思想分量和情感浓度的剧作,二度(创作)再怎么使劲,最后都是虚的,空的,不具备思想和情感的撞击力。”(5)张弛: 《中国当代戏剧名家访谈录》,北京: 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因此,“思想开掘型”导演在剧本选择上相当“挑剔”,《桑树坪纪事》(编剧: 陈子度、杨健、朱晓平;导演: 徐晓钟、陈子度)、《商鞅》(编剧: 姚远;导演: 陈薪伊)、《父亲》(编剧: 李宝群;导演: 查明哲)、《荒原与人》(编剧: 李龙云;导演: 王晓鹰)、《兰陵王》(编剧: 罗怀臻;导演: 王晓鹰)等单凭剧本足以在当代文学的高原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为了保证剧本质量,一些导演在剧本写作阶段就积极提供建议,帮助剧作家完善构思,修改阶段更是积极介入。剧作家李宝群曾回忆同导演查明哲的合作:“讨论剧本,他发现问题异常敏锐,意见犀利切中要害,提出的建议则具体翔实十分有建设性,对剧本的提升帮助极大。”(6)李宝群: 《说不完的查明哲》,《从梦想到现实: 李宝群戏剧随想集》,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159页。
在原创剧本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思想开掘型”导演宁可放弃“原创”,从中外名剧中寻求资源: 查明哲的“战争三部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死无葬身之地》《纪念碑》)、王晓鹰的“灵魂拷问三部曲”(《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死亡与少女》)、王延松的“曹禺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作为他们的代表作都“脱胎”于经典剧作,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导演的开掘空间,不至于出现导演排戏时“力有余而剧不足”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导演对剧本的开掘及其呈现像一架蹦床: 演出最终所能达到的高度有赖于导演在剧本编织的“床”上“下沉”有多深,而导演能“下沉”的深度除了要看自身的功力外还要看剧本自身的“弹性”。
二、 “改编剧”与“唯新主义”的迷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导演通过经典改编强化导演的主体地位,以林兆华、田沁鑫、李六乙、孟京辉等为代表。导演改编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文学改编,戏剧文学改编的核心是文体转换(比如从小说到剧本),导演改编则既包括文体转换,也包括对原文本的解读,尤以后者为重。不少在戏剧领域被视为“改编”作品只是因导演在舞台上提供了对经典的另类读解,并不涉及文体转换。在“改编剧”中,剧本的总体阐释权以及演出设计的执行权集于导演一身,加之观众对经典题材相对熟悉,对“改编剧”的期待视野本身就聚焦于导演,因此,“改编剧”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导演中心”的美学意图。
由于缺少剧作家的“制衡”,“改编剧”已经触及了传统导演职能的边界。比如,在林兆华执导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被剥离出来成了人类生存的某种象征,“人人都是哈姆雷特”成了演出的“第二主题”。这一阐释已经完全有别于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寄托的对人文主义的困惑与反思。林兆华改编的方式很独特,他没有对莎士比亚的原剧本做修改,而是通过舞台呈现重构了“莎士比亚叙事”。在演出中,三位演员“角色换位”,轮流扮演哈姆雷特、克劳狄斯。舞台上的布景装置也参与了“改编”。舞台没有采用原作暗示的富丽堂皇的宫廷设计,整个空间近似于一片废墟: 灰黑幕布覆盖了舞台的主体,国王的宝座不过是一张老式的理发椅。舞台前区摆放着不能使用的老机器,上空悬置着破旧的电风扇。剧终,原本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极富仪式感的决斗以两人“大战”电风扇的方式被消解了。这里,哈姆雷特“大战”电风扇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产生了奇妙的互文效果,屠格涅夫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视为人类天性的两极:“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征,就是人类天性中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7)[俄] 屠格涅夫: 《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杨周翰编选: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66页。某种意义上,林兆华把屠格涅夫的这一认识舞台化了。无论观众接受与否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演出已打上了鲜明的林兆华烙印。
笔者将类似不改或少改剧本、主要靠演出对剧本的陌生化所做的改编称为“舞台性”改编。李六乙导演的《樱桃园》、何念导演的《原野》、孟京辉导演的《茶馆》以及青年导演王翀的“经典2.0”系列等都接近于这类。田本相先生指出:“导演可以有自己的创新处理,但是舞台的意象与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塑造、创作方法的特点是紧密联系的,如果你改造‘总体形象’,那么,势必提出人物的、故事的甚至戏剧场景的新的逻辑。”(8)田本相: 《新排〈原野〉: 解读与创新的偏离》,《北京人艺论》,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确实如此,“说不尽的经典”并不是说可以把一切阅读感受拿来为经典赋义。尤其对导演而言,新的“总体形象”需要借助“新的逻辑”才能生效,否则难免让观众心生疑窦。林兆华后来拼贴改编的《等待戈多·三姊妹》演出失败也多少与此有关。契诃夫的《三姊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时代背景、风格基调、主题内涵都不存在可比性: 《三姊妹》是传统贵族在当代庸常生活中的呢喃,其中夹杂着淡雅的抒情和忧伤;《等待戈多》是“迷失”情境的极致展示,其中蕴藏着苦涩与辛酸。林兆华只是随性抽取了《三姊妹》中的“等待”并强制性地将其和《等待戈多》杂糅在一起。由于缺少“新的逻辑”来连接两剧以致林兆华在舞台上大搞水池和孤岛,用静态表演(《三姊妹》)和游戏表演(《等待戈多》)的对比来呈现“等待”等一系列围绕“总体形象”的设计都显示出一种买椟还珠式的滑稽。
还有一类导演改编贯穿了剧本与演出,既在剧本中提供了“新的逻辑”,也在舞台上创造了新的“总体形象”,以田沁鑫为代表。在创作中,田沁鑫经常“编导合一”地“跨界”写剧本,待剧本改编完成后,再进行搬演意义上的“二度创作”。(9)徐晓钟的《桑树坪纪事》相对特殊。从工序而言,《桑树坪纪事》是最接近的“剧本性”改编剧。不过,在创作过程中,导演并没有预先为编剧设置思想栅栏,要求编剧为自己的思想服务,而是根据改编的剧本提炼、凝结、升华思想。单从导演的工作而言,更接近“思想开掘”。这种带有“剧本性”的改编剧与一般剧目以及“舞台性”改编剧在创演流程上的差异如下图:
与林兆华的改编相比,田沁鑫的改编保留了基本的叙事性,对人物的塑造在演出中仍有相当的分量。尤其与一味“造神”的某些主流演出相比,田沁鑫这些改编对人性的书写更为真实。以《赵氏孤儿》为例,史书记载的《赵氏孤儿》是一个宣扬忠义的故事,程婴为了天下大义救下孤儿,并将其抚养成人,助其复仇。但在田沁鑫的呈现中,原剧宣扬的忠义被解构了:“(《赵氏孤儿》)这个‘义’是什么?这个戏的精神何在?答案就是‘义是天下’,我当时查资料看到这一句时都绝望了。天下!多抽象的一个词,我对民族的根脉产生质疑。”(10)田沁鑫: 《田沁鑫的戏剧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为此,田版的演出将原剧中程婴和孤儿这两个“英雄”都拖下了神坛。首先,程婴救孤在田版中只是“因为一丝善念”,他没有过于崇高的动机,只是守护着平凡的世俗道德。其次,孤儿没有坚定地选择复仇,扮演“英雄”的角色。田沁鑫以孤儿为主人公,重点表现了他在成长中的困惑和迷茫,孤儿身上“混乱中的悲郁之情”隐约闪烁着少年维特的成长焦虑。原剧强调“孤儿之义”,田版凸显“孤儿之孤”,田沁鑫赋予了孤儿精神上的现代体验:“面对困境,我要选择。我不想选择,可是,我面对困境,”“我迷路了,我该向哪个方向走。”这是孤儿的困惑,也是“人”的困惑,它远比某些演出建构的虚假神圣更为真实、更具人性。
“剧本性”改编剧的主要问题在于“新而不深”。由于导演教学中的某些偏颇,当代导演的文学能力和文学修养尚有极大的提升空间,某些戏剧改编只提供了一套新的视角,却无力在这一视角下进行深度剖析,以致演出沦为“心灵鸡汤”的形象图解。剧评人“押沙龙在1966”批评台湾导演林奕华的改编剧时曾说:“这种思考无异于‘地球是圆的’‘太阳从东边升起’,太直白,太寻常,我根本不需要通过看一台演出来了解这种道理……诸如此类的‘说教’在林奕华的戏剧中频频出现,每一条都带着无需讨论的正确性。”(11)押沙龙在1966: 《要么往前,要么往后》,《上海戏剧》,2013年第10期。这番批评同样适用于内地,缺少思想锋芒的改编难免让人怀念传统的对经典的原教旨化呈现。其实,无论何种形式的改编都只是展示人物复杂性的支点和杠杆,莱辛在评价霍伊菲尔德改编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时就说过:“是卢梭的尤丽也好,不是也好,有谁会关心这些呢?只要她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人物就行。”(12)[德] 莱辛: 《汉堡剧评》,第49页。一旦跌入了“唯新主义”的陷阱,无视深刻地一味求“新”,无论是“舞台性”改编还是“剧本性”改编都很难孕育带有经典性的作品。
三、 “后戏剧”及其变体与剧场接受的困境
当代剧坛还有一种相对特殊的“导演戏剧”,即后戏剧剧场及其变体。在这类演出中,导演的“中心”性已经不局限在“二度创作”环节,就像牟森所言:“(1993年到1996年)我排戏基本上没用过一个文学剧本,也就是我的舞台创作不是对原作者一度文学创作的解释,我的舞台创作不是二度创作。”(13)魏力新: 《做戏——戏剧人说》,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8页。在这里,剧本的有效性遭到极大削弱——或不用剧本,或剧本已不具备提供“指令形式”的能力,戏剧的意义创造主要通过舞台来实现。
牟森导演的《零档案》以于坚的同名长诗为素材,牟森没有按照改编的一般规定先将诗作跨文体改编为具有行动性的剧本,而是直接把诗作作为演出的一个“声部”来“调度”演出。演出开始后,舞台上没有演员,随着长诗《零档案》的录音播放,男演员(吴文光)走上舞台向观众讲述他父亲的故事和他询问亲友、翻查档案的寻亲真实过程。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还有一位男演员在舞台上用切割机切割钢筋或焊钢筋,一位女演员播放《零档案》的录音朗诵和小孩心脏手术的纪录片。男演员(吴文光)的朗诵不断受到干扰,他提高音量继续讲述。最后,男演员将钢筋焊成钢架,开始起身和吴文光对抗讲述,女演员则把苹果插到铁架上。随着对抗加剧,两个男演员从铁架上拿下苹果,用虎钳压碎,并在舞台上狂奔。奔跑之时,男演员把压碎的苹果投入鼓风机,苹果碎末四溅。整场演出中,装置和演员的表演创造了特殊的蒙太奇效果,牟森试图借此表达“档案制”对个人生命的压抑。到了《与艾滋有关》,牟森连文学素材都“省略”了。演出中,舞台的主要演区有一个巨大的桌案,桌案四周围坐着现代舞演员金星、演员吴文光、诗人于坚等十来人。他们一边闲聊着日常琐碎的话题,一边拌肉馅、擀皮、包包子。他们聊的话题不是编剧事先拟定的虚构情节,都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实的事。于坚是“主聊”,话题包括他在农村插队的经历、荤段子等等。舞台右侧,一个男演员在冒着热气的油锅前炸丸子,边炸边和观众聊天,鼓动观众上来拿丸子吃。演出快要结束时,一群民工从剧场侧门排队进入。他们围在破旧的墙面附近,有的和泥、有的砌墙。干了不久,于坚邀请他们上台吃饭。这些民工就坐在巨大的桌案四周,开始吃包子和丸子。牟森解释说:“我不能告诉观众我要在这个戏里说什么,因为我没想跟他们说什么,只是展示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不同的观众可能会从里面得到不同的东西。从我个人来讲,我谈的不是艾滋,谈的是与艾滋有关的某些事情,但我觉得是展示生活中的某种状态,人的这种生活态度。”(14)汪继芳: 《在戏剧中寻找彼岸——牟森采访手记》,《芙蓉》,1999年第2期。
牟森之后,李凝的“凌云焰”剧团和陶冶的“陶身体剧场”以及青年导演李建军等延续了这一导演脉络。“凌云焰”一直致力于身体训练与表演,提倡“肢体写生和肢体再生”,强调通过身体的训练实现精神治愈。“陶身体剧场”不同于传统的舞蹈团体,正如其剧团名所昭示的,主创者希望通过戏剧与舞蹈的共融,创造出中国的“舞蹈剧场”。但与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相比,“陶身体剧场”的作品只见“身体”不见“剧”。在其“数位系列”的探索中,几乎大多是身体“高难度动作”的舞台展示。这一“演脉”中还有一些作品把探索集中在观众的参与性,比如李建军导演的《25.3 km童话》。根据现场参与过的“观众”描述,演出发生在指定时间和路线的公交车上,上车的乘客/观众中“混”有演员,待观众入场就位后,混迹其中的演员便开始和其他乘客聊天,彼此分享。
与“思想开掘型”和“改编剧”相比,这类“导演戏剧”为学界诟病最多。“导演中心”被化约为“反文学”“反思想”的同义语多与这类演出有关。但是,这里似乎存在某种错位。雷曼在阐述“后戏剧剧场”的观众接受时曾说:“后戏剧剧场结合了多种艺术形式,于是便也发展了,同时也要求着一种从戏剧典型模式和文学中解脱出来的接受潜能。所以,面对这种剧场形式,其他艺术门类(造型艺术、舞蹈、音乐)的爱好者经常比醉心于文学性叙述剧场的观众更懂得怎样去欣赏。”(15)[德] 汉斯·蒂斯-雷曼: 《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在这里,“导演”的职能已经迥异于过去,他不再是剧本文学叙事的缝合者而更接近空间造型设计师。观众的期待视野和艺术家的美学诉求发生了倒错。不可否认,对戏剧而言,以“观众”为尺度有其合理性。但是,戏剧在顺应观众的同时也应积极地塑造观众,其中有经有权,有恒有变,“不应该用戏剧剧场的文学标准来要求后戏剧剧场;不应该把后戏剧剧场的文学表现看作戏剧剧场的文学失败”(16)吕效平: 《释“后戏剧剧场”》,《戏剧与影视评论》,2020年9月总第三十八期。。对于这一类尚在探索中的“导演戏剧”而言,只要创作者本身是真诚的,就值得给其多一点耐心和宽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孟京辉。孟京辉初涉剧坛时的叛逆与先锋相当真诚,“如鲠在喉”的创作冲动是其日常心态:“有劲儿没处使,有精力没处发泄,有想法没处实验,有话没处说……就一天跟谁较劲似的。”(17)魏力新: 《做戏——戏剧人说》,第83页。因此,虽然这一阶段的作品从质量上来说存在各种问题,但其情感是真挚的,态度是诚恳的,常有“一优遮百劣”的亮点。随着商业上的成功,孟京辉从“边缘”走向“主流”。这一阶段,孟京辉的导演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遗憾的是,在导演能力日益纯熟的同时,孟京辉失去了早期导戏的真诚。当真诚成了“表演真诚”,当最初的“愤怒”“叛逆”成了招徕观众的手段,舞台上套路式的自我重复也就不意外了。
真诚的顽石远比虚伪的“套路”要珍贵,当代剧坛想培养出能制造高票房的商业导演并不难,有评论者曾戏谑描述过一个曾经怀揣梦想、意气风发的青年导演如何在当代戏剧生态的扭曲下一步步成为“商业大导”。(18)参阅押沙龙在1966: 《小明的故事——论著名导演的自毁之路》,《上海戏剧》,2014年第7期。相比之下,坚守真诚则要困难得多,商业的诱惑,政府的归化都可以轻易让包括戏剧人在内的任何从业者迷失。对评论者而言,站在普通观众的立场因“看不懂”而否定这类作品无可厚非。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人同样真诚地为这类演出做必要的普及和引导,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是宽容和耐心。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是元好问对李商隐的评价,这句话讲的是诗人们都喜欢李商隐的诗,却无人能为之注释。换个角度,此句话或可另作别解: 正是由于其作品幽深隐晦、无人作笺,所以对李商隐诗作之“爱”更多局限在相对专业的“诗家”。这或许能给创作者以启示,“对于‘后戏剧’来说,演出不应像当年现代派那样孤芳自赏,而要把观众的理解与解释作为前提”。(19)丁罗男: 《“后戏剧”与中国文化语境》,《戏剧艺术》,2020年第4期。只不过,对于当代观众而言,作为前提的“观众的理解和解释”不能局限于文学式的把握。当代观众已经在其他艺术乃至大众传媒中建立起全新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和阐释惯性。创演者在先锋探索实践中有必要考虑到这些“新传统”并加以利用,在“新传统”与先锋形态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从这个角度而言,向观众的靠拢丝毫不意味着先锋性的妥协,它给创作者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结 语
“导演戏剧”在中国呈现出相当多元的类型。不过,整体而言,无论何种类型,“导演戏剧”的潜力在中国都还未得以完全释放。客观上,“剧本荒”的制约,与观众审美惯性的磨合,让导演时常不得不屈就现实。但更应当警惕的是导演自身对思想的放逐。这同对导演艺术的误读有关,俄国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在《论导演艺术》中开篇就提出了导演行当的特殊性:“有的艺术,若没有专门技巧,马上就能露出马脚: 如造型艺术,钢琴艺术,以及对生命有危险的杂技艺术。而在我们这一行里,不是艺术家也可以混一辈子,甚至还能获得名声。”(20)[苏] 格·托夫斯托诺戈夫: 《论导演艺术》,杨敏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5页。随着20世纪以来“导演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导演行当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专门技巧”。这对导演艺术的发展本来是件好事,但在此过程中,一些导演为了强化“中心地位”,把“专门技巧”本末倒置地视为戏剧审美的全部。“导演中心”的实质是导演综合运用多种能力,以实现对戏剧的思想表达力、人文表现力的充分解放。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导演戏剧”呈现出的多元景观有些类似莱辛在批评伏尔泰时所做的一个形象比喻:“他摇摇摆摆地骑着自己这匹战马,猛烈地反复周旋。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活动只是毫无意义地扬起一片尘埃。”(21)[德] 莱辛: 《汉堡剧评》,第119页。如果“导演中心”只是满足于在“专门技巧”上悉心钻研,无意在更广阔的思想文化场域中扬鞭发力,那么“导演戏剧”的类型无论如何丰富,形态如何多元,最终都会在一袭狂奔之后为他身后扬起的四散尘埃所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