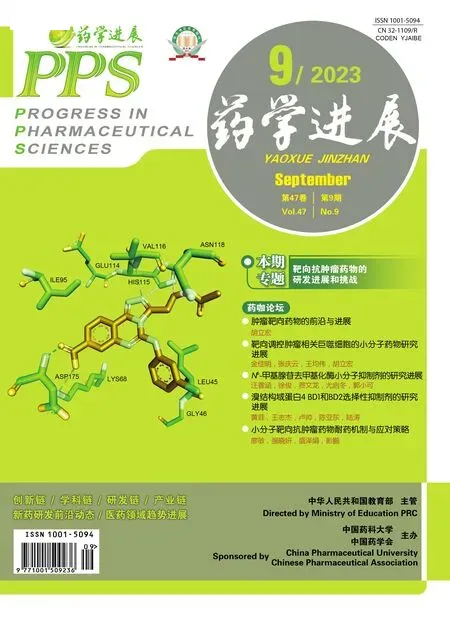绞股蓝皂苷治疗肝病的研究进展
梁骁爽 ,滕媛 ,赵志伟 ,张健,殷志琦
(1.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中药制剂系, 江苏 南京 211198; 2.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转化医学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46)
绞股蓝[Gynostemma pentaphyllum(Thunb.)Makino]隶属于葫芦科绞股蓝属,是一味临床应用历史悠久的药食两用的传统中药。迄今为止,已有300多种绞股蓝皂苷(gypenosides,GPs)及其苷元被报道,其药理学研究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长期的药效学研究发现,绞股蓝总皂苷或富含皂苷的部位显示多种良好的药理活性,如降血糖、降血脂、肝保护、抗肥胖、抗癌、抗炎、心脏保护和神经保护等。近些年GPs用于治疗肝病的研究层出不穷,尤其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肝纤维化等。因此,本文综述了近年GPs治疗肝病的研究进展,以期为GPs肝保护的深入机制探究及临床应用拓展提供参考。
1 代谢相关肝病
1.1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是排除过量饮酒等其他致病因素,以弥漫性肝细胞脂肪变性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慢性肝病[2]。NAFLD的全球发病率为25% ~ 30%[3],值得注意的是,NAFLD患者常伴随其他代谢综合征,如肥胖、Ⅱ型糖尿病、高脂血症,他们的患病率分别为51%、22%和69%。因此,NAFLD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寻找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是当今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目前公认的NAFLD发病机制是“多重打击”学说[4],该学说认为,胰岛素抵抗导致的肝脂肪变性,为“第一次打击”,可增加肝脏对肝内“打击”(如氧化应激、炎症)和肝外“打击”(脂肪-肝轴“打击”,如脂肪组织功能紊乱介导的炎症;肠-肝轴“打击”,如肠屏障功能紊乱和肠道菌群失调)的敏感性,且这些“打击”为平行进行,而非依次发生。由于肝脂肪变性是NAFLD发病和进展的始动因素,过去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肝内降脂和改善胰岛素抵抗。
GPs治疗NAFLD的研究始于绞股蓝本身的降脂活性。研究发现,绞股蓝改善高脂血症大耳兔血脂异常的同时,还可以改善75%大耳兔的肝脂肪变性[5]。此后更多学者致力于绞股蓝治疗脂肪肝的探究并取得一定进展(见表1)。GPs能显著降低Ⅱ型糖尿病合并NAFLD大鼠血清中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血糖(blood glucose,BG)和胰岛素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GPs在200、400和800 mg · kg-1治疗剂量下呈现了非常明显的剂量依赖性。另外,实验还证明了上述效果与降低肝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核因子-κB(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κ B,NF-κB)的蛋白表达,以及降低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γ,PPAR-γ)和细胞色素酶P4501A1(cytochrome P4501A1,CYP4501A1)的mRNA表达紧密相关,这可能是GPs能够减轻肝脂肪酸堆积,延缓炎症和氧化应激进程的机制[6]。NAFLD致病过程还存在着免疫功能失衡,表现为调节性T细胞(T-regulatory cell,Treg)和辅助性T细胞17(T-help cell 17,Th17)数目和功能上的异常。有学者探究GPs对NAFLD大鼠免疫调节的影响,结果说明GPs能剂量依赖性地改善NAFLD大鼠肝病变,其高剂量组(240 mg · kg-1)能显著增加外周血中Treg细胞比例,降低Th17细胞比例,同时减少肝中TNF-α、白介素17(interleukin 17,IL-17)等促炎因子,并增加白介素10(interleukin 10,IL-10)等抗炎因子的生成[7]。氧化应激被认为是NAFLD向非酒精脂肪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转变的关键因素,参与了NAFLD疾病发展的“二次打击”过程。有学者探究GPs对NAFLD大鼠肝氧化应激的影响,结果发现GPs能显著诱导NAFLD小鼠和人肝癌细胞(HepG2)中NAD+依赖性组蛋白去乙酰化酶6-红系衍生的核转录相关因子2(NAD+dependent histone deacetylase 6-erythroid derived nuclear transcription related factor 2,Sir6-Nrf2)抗氧化信号通路的激活,表现为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CAT)等抗氧化物质及Nrf2下游靶基因血红素加氧酶1(heme oxygenase-1,HO-1)、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醌氧化还原酶1(quinone oxidoreductase 1,NQO1)的蛋白表达水平升高。除此之外,GPs还能显著降低肝巨噬细胞标志物小鼠含生长因子样模体粘液样激素样受体(mouse EGFlike module-containing mucin-like hormone receptorlike 1,F4/80)的表达,降低IL-1β、IL-6、单核细胞趋化因子(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TNF-α,以及纤维化标志物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Ⅰ型胶原蛋白(collagen-I,Col-Ⅰ)、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的基因表达,这些结果均表明GPs能极大程度地阻止NAFLD向NASH的发展进程[8]。

表1 绞股蓝皂苷及绞股蓝粗提物对多种肝病的治疗作用Table1 Therapeutic effects of gypenosides and crude extracts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a on various liver diseases
NASH是从单纯肝脂肪变性向更严重的肝疾病,如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等转变的关键阶段,其中涉及到游离脂肪酸的调节。已有研究表明,GPs能显著下调肝固醇元件结合蛋白1c(sterol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1c,SREBP-1c)、碳水化合物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rbohydrate responsiv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hREBP)等转录因子及乙酰辅酶A羧化酶(acetyl-CoA carboxylase,ACCase)、硬脂酰辅酶Al(stearoyl-CoA desaturase-1,SCD-1)、丙二酰辅酶A(malonyl CoA)等脂蛋白合成酶的水平,从而显著降低肝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FFAs)的合成[9]。在探究GPs改善NASH的作用机制时,学者重点关注了法尼酯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介导的胆汁酸和脂质代谢通路,结果说明,GPs显著下调SREBP1、SCD1、脂肪酸合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N)等脂肪酸合成酶,同时上调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α,PPAR-α)、肉毒碱棕榈酰转移酶(carnitine palmitoyl transferase 1,CPT1)、脂蛋白脂酶(lipoprotein lipase,LPL)、微粒体甘油三酯转运蛋白(microsomal triglyceride transfer protein,MTP)等胆汁酸氧化酶、分解酶的水平。另外GPs还表现出了降低肝内总胆汁酸水平、下调胆汁酸合成酶细胞色素P4507A1(cytochrome P4507A1,CYP7A1)、上调胆盐输出泵(bile salt export pump,BSEP)的调节作用[10]。由此我们推测GPs改善NASH小鼠肝脂肪变性,可能与FXR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
研究还揭示了GPs对NAFLD的治疗作用与修复肠道屏障、调节肠道菌群和增加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CFAs)含量有关。已有结果显示,GPs改变了NAFLD小鼠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与代谢紊乱有关菌群的相对丰度,特别是厚壁菌门(真杆菌、白芽孢杆菌、梭状芽胞杆菌和乳酸杆菌)[11]。GPs能大幅下调肝微小RNA-34a(micro RNA-34a,miR-34a)的水平,比模型组改变了4倍以上(3 : 14)。相关性分析显示,miR-34a与肠道微生物群特别是厚壁菌门的变化有较强的相关性(r=0.796),与肝脂肪变性评分亦密切相关(r= 0.862)。此外,miR-34a的靶基因肝细胞核因子4α(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4 α,HNF4α)、NAD+依赖性组蛋白去乙酰化酶1(NAD+dependent histone deacetylase 1,Sirt1)和PPARα的水平也在GPs的干预下回调[12]。鉴于NAFLD诱导的肠道菌群紊乱会导致肠道屏障受损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向循环系统的流动,因此有学者评价了GPs对肠道屏障完整性的影响。结果表明GPs干预后的结肠组织微绒毛更整齐,紧密连接和桥粒损坏程度减轻,间隙变小,隐窝和杯状细胞变丰富,排列变规则。另外GPs对肝炎症、胰岛素抵抗和内毒素血症的治疗作用具有显著的剂量依赖性[13]。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SCFAs可抑制LPS驱动的炎症反应,还能抑制FFA的产生,维持宿主的能量和代谢稳态,因此学者考察了GPs对NAFLD大鼠肠道SCFAs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GPs促进有益菌的增殖和抑制有害菌的生长的同时,能显著提高短链脂肪酸(乙酸、丙酸和丁酸)的含量[14]。
临床研究中将绞股蓝总苷胶囊用于NAFLD患者,考察其对患者肝功能、糖脂代谢水平、肝纤维化程度以及氧化应激指标的影响,结果说明GPs与多烯磷脂酰胆碱联用后,对ALT、AST、γ-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ferase,γ-GT)、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HOMA-IR)、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HA)、Ⅲ型前胶原(procollagen type Ⅲ,PC Ⅲ)、Ⅳ型胶原(collage type Ⅳ,C-Ⅳ)和层粘连蛋白(laminin,LN)这些肝功能和纤维化指标的降低程度显著强于单用多烯磷脂酰胆碱组,同时GPs还能极大降低血清TC、TG、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c)水平,升高肝SOD、GSH、总抗氧化能力(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T-AOC)的水平,说明GPs能增强多烯磷脂酰胆碱的肝抗氧化能力、调节糖脂代谢能力、延缓肝纤维化进程[15]。而当GPs与红曲、银杏提取物联用治疗NAFLD时均能协同发挥降低大鼠肝内脂质蓄积的作用,且联用组药效要优于单用组[16-17]。综上结果推测GPs可能是NAFLD治疗的潜在有效药物。
1.2 酒精性肝病
ALD是长期饮酒过量导致的肝脏疾病,是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均酒精消耗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ALD在中国的发病率已达到惊人的4.5%,与美国(6.2%)和欧洲国家(6%)的发病率基本持平。酒精在肝分解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乙醇和乙醛,通过影响生物酶活性扰乱氧化还原平衡和肝脂质代谢,导致肝脂肪异常堆积[18]。有证据显示早期酒精性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炎的患者如果不接受及时、正确的干预会增加发展到后期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风险,但迄今为止还未有批准治疗ALD的药物上市。因此,寻找潜在的治疗药物显得很有必要。
研究人员研究了GPs对高脂高胆固醇饮食和酒精混合造模的脂肪肝大鼠的治疗作用,结果表明GPs能剂量依赖性地显著降低大鼠血清中ALT、AST、TC、TG、FFA和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的水平,显著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血清和肝中SOD活性,同时显著降低肝细胞凋亡率和肝组织细胞色素P4502E1(cytochrome P4502E1,CYP2E1)蛋白表达,以上结果揭示了GPs可能通过调节脂代谢和氧化应激发挥延缓脂肪肝进程的作用[19]。另有研究结果表明,GPs的干预能显著降低混合造模脂肪肝大鼠的肝脂肪变性程度和肝损伤评分,同时肝组织中NF-κB和TNF-α蛋白的水平也被GPs显著降低,而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的水平被显著升高,以上结果说明抑制氧化应激和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可能是GPs抵抗脂肪肝的机制[20]。单用酒精造模脂肪肝小鼠的研究也证明GPs可剂量依赖性地降低血清中ALT、AST、TC和TG的水平,升高肝中抗氧化酶或抗氧化物质SOD、CAT、GSH的水平,降低MDA的水平,同时观察到肝中Nrf2/NF-κB信号通路被GPs激活,表现为肝IL-6、TNF-α水平降低,HO-1、NQO1水平升高,这与混合造模脂肪肝中呈现的治疗效果类似[21]。此外,GPs曾被用于酒精性肝病的辅助治疗,当GPs与肝泰乐合用后能显著降低患者血清中ALT、AS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和谷氨酰转肽酶(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的水平,其改善肝功能的效果不仅优于单用肝泰乐组,更加优于凯西莱与肝泰乐合用组,揭示了GPs治疗此类脂肪肝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2]。
鉴于绞股蓝及其总皂苷治疗酒精性肝病的报道较少(见表1),未来可开展更多的研究确证GPs对于酒精引发的肝疾病的作用,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确定剂量范围和用药频次等,为治疗该类疾病提供参考。
2 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对不同病因的慢性肝损伤的一般反应,其中包括慢性乙型和丙型肝炎、NAFLD、ALD、药物诱导肝炎、免疫介导性肝病和胆汁淤积等[23]。如果不加干预,肝纤维化会发展成肝硬化,并伴有肝腹水、门脉高压和肝性脑病等,因此逆转肝纤维化是阻止病程发展的关键步骤[24]。TGF-β是促纤维化的最强有力的细胞因子,而TGF-β信号通路更是激活肝星状细胞和促进纤维生成的最关键的通路[25],因此抑制TGF-β信号通路的激活,进而减少细胞外基质的生成是有效治疗肝纤维化的策略。
扶正化瘀胶囊是唯一被美国批准进入丙型肝炎伴肝纤维化的Ⅱ期临床试验的中药,疗效显著[26],其主要活性成分为虫草菌丝多糖、GPs及苦杏仁苷,将以上物质配伍后和单独使用GPs组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单用GPs的药效略逊于配伍用药,但明显优于其他两个成分单用组,其作用机制与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2/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9,MMP2/9)、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2(metalloproteinase tissue inhibitor 1/2,TIMP1/2)及抑制TGF-β1/Smad信号通路,减少肝星状细胞的激活紧密相关[27]。另有研究表明,GPs能显著减少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诱导的大鼠肝星状细胞增殖,同时显著下调G1期特异性蛋白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D1)和CyclinD3的表达,机制研究表明,GPs抵抗细胞增殖的效应与抑制PDGF-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AKT)-p70核糖体蛋白S6激酶(70 kDa ribosomal protein S6 kinase,p70S6K)信号通路有关[28]。尽管在肝纤维化进程中关键的效应细胞是激活的肝星状细胞,但肝祖细胞的激活及向成纤维细胞的转化也能显著促进这个过程。GPs能显著降低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小鼠的肝祖细胞标志物SRY-box转录因子9(sexdetermining region Y box 9,Sox9)和细胞角蛋白19(cytokeratin 19,CK-19)的表达水平,同时降低大鼠肝上皮样干细胞(WB-F344)在TGF-β1刺激下由上皮细胞向间充质细胞的转化,这种效应与抑制TGF-β1-Smad2/3信号通路有关[29]。
近期研究表明,肝细胞凋亡不再与纤维化彼此分离,毫不相干,凋亡细胞可以通过旁分泌途径直接激活纤维化,也可以通过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间接激活。扶正化瘀的拆方研究结果表明,由虫草多糖(60 mg · kg-1)、GPs(50 mg · kg-1)和苦杏仁苷(80 mg · kg-1)组成的CGA配方治疗肝纤维化的效果与原方相同,结果还证明了CGA配方能通过下调内源性凋亡和外源性凋亡途径的水平缓解纤维化进程,表现为TNF受体超家族成员6(TNFRSF6/Fas)、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1,TNF-R1)、剪切的半胱天冬酶-3,8,9,10、细胞质细胞色素C、线粒体Bcl-2相关X蛋白(Bcl-2-associated X,Bax)蛋白水平的降低和线粒体细胞色素C、B-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2,Bcl-2)蛋白水平的升高。将GPs单独应用于抗肝纤维化研究,缺口末端标记法(TdTmediated dUTP Nick-End Labeling,TUNEL)染色结果表明GPs能显著降低阳性细胞的数目,且抗凋亡蛋白Bcl-2被显著上调,而促凋亡蛋白半胱天冬酶-7,9、Bax、Bcl-2拮抗剂(Bcl2 antagonist,Bak)被显著下调,这说明了抑制线粒体凋亡途径可能是GPs发挥抗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的机制之一[30]。
此外,GPs还具有抵抗血吸虫感染和白蛋白攻击造成的肝纤维化的药理特性[31]。以上研究结果揭示了GPs可通过抑制肝祖细胞向成纤维细胞转化、肝星状细胞增殖和抗肝细胞凋亡等多个机制发挥作用,这充分体现了GPs在治疗肝纤维化上的多靶点、多通路、多方位打击的优势(见表1)。基于以上GPs在抗纤维化方面的独特药理作用,值得国内外学者对其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进行进一步探索。
3 肝细胞癌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3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肝细胞癌的发病率急剧上升,肝细胞癌的死亡增长率比其他任何癌症都要高[33]。中国的肝癌发病率已上升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肝癌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34]。
GPs作为植物类抗肝癌药物,不仅可以调节细胞周期相关蛋白将HepG2的生长周期阻滞在G0/G1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同时还能升高细胞内活性氧(reactive oxygen,ROS)水平,通过死亡受体途径和线粒体途径诱导HepG2凋亡[35]。进一步探索GPs诱导肝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发现给予钙离子螯合剂、内质网钙离子释放拮抗剂或质膜钙离子通道抑制剂都可以显著降低GPs对肿瘤细胞的促凋亡作用,表明GPs能通过内质网和质膜钙离子通道介导的“钙超载”诱导肝细胞凋亡[36-37]。另有学者考察了GPs对肝癌细胞无氧糖酵解的影响,结果表明GPs可以显著抑制HepG2对葡萄糖的消耗,减少乳酸的生成,提示GPs能抑制肿瘤细胞的无氧糖酵解过程[38]。另有研究表明绞股蓝皂苷L (gypenoside L,GYP-L)除了能诱导肿瘤细胞衰老外,还能使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顺铂(cisplatin)等临床治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毒性增强[39]。基于GPs具有直接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和调节肿瘤细胞微环境,从而间接增强化疗药物的效力(见表1)。下一步学者可继续探究GPs抑制肿瘤细胞药物外排和肿瘤干细胞产生的可能性,为GPs进一步减轻化疗药不良反应、降低耐药性提供实验依据。然而,GPs抗肝癌的研究只停留在体外研究上,缺乏实质性体内实验的证据支撑,因此我们期待后续动物实验的进一步验证。
4 药物性肝损伤
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一种与肝毒性药物摄取相关的肝损伤,是急性肝功能衰竭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临床上DILI大致分为2类:一类与药物自身相关,分为与剂量相关的固有性肝损伤和与剂量无关的特异质型肝损伤;另一类是与药物本身毒性无关,而与药物作用于机体产生的作用有关,如检查点抑制剂对肝细胞介导的免疫损伤[40]。DILI的流行病学很难确定,因为它往往是一种排除诊断,导致临床上该类型肝病的发病率被低估。研究表明英国和瑞典DILI的发病率分别为每年每10万人中2.3和2.4例,法国和冰岛的为每年每10万人中14和19例,而根据中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亚洲DILI的发病率似乎更高,报告的年发病率为每年每10万人中23.8例[41]。
对乙酰氨基酚(acetaminophen,APAP)诱导的肝毒性是公认的造成肝衰竭最主要的原因,APAP诱导的肝损伤则是研究DILI最常用的模型。绞股蓝水提物可显著降低APAP诱导急性肝损伤中血清转氨酶的升高,并减轻肝组织结构破坏[42]。另有研究表明,GPs干预可加重APAP对小鼠的肝毒性,学者推测GPs可能诱导了肝药酶活性,使APAP代谢增加,从而加重肝毒性[43]。对比绞股蓝水提物的肝保护作用,单用GPs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致毒效果,表明水提物中的其他成分,如绞股蓝多糖才是真正对DILI有益的物质(见表1)。基于抗DILI天然产物的活性与机制研究进展,未来可从抗氧化损伤、抗DNA损伤和蛋白质功能障碍等角度继续探究GPs的药效,并从Nrf2抗氧化通路、NF-κB抗炎通路及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细胞生长及凋亡等信号通路和细胞色素酶CYP450等重要靶酶上探究作用机制,进一步加速三萜类化合物作为主要天然肝保护剂的开发利用。
5 其他类型
肝是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启动和发展过程中最易受损的器官之一,其脂质蓄积情况可直接或间接反映动脉内膜脂质沉积程度,研究发现,GPs可显著降低ApoE-/-小鼠血清TC、TG、LDL-c的水平、肝空泡化面积和肝Bax、细胞色素C、剪切的半胱天冬酶-3、剪切的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蛋白及mRNA水平,升高Bcl-2蛋白及mRNA水平,其机制可能与调控长链非编码RNA TUG1/miR-26a有关[44]。同时也有研究称GPs可显著升高ApoE-/-小鼠肝脏脯氨酰羟化酶(prolyl hydroxylase,PHD)、PPAR-γ的蛋白和mRNA的水平,降低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蛋白和mRNA水平,这说明了GPs能通过调节肝脂肪代谢,减轻肝脂质沉积,从而延缓AS进程[45]。肝是机体唯一能再生的实质器官,确保肝与体质量的比例始终保持在机体稳态所需的最佳状态,急性肝损伤后的肝再生对某些重大肝疾病至关重要。将大鼠肝部分切除后给予GPs治疗,结果表明肝分裂相数和肝再生度均有很大程度提升。肝脏缺血再灌注(ischemia reperfusion,I/R)模型在肝手术、失血性休克和肝移植术后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在进行I/R前给予小鼠GPs能显著降低肝的氧化损伤和肝细胞凋亡[46]。鸭甲型肝炎病毒(duck hepatitis A virus,DHAV-1)是一种由于没有有效的兽药治疗而引起的雏鸭急性疾病,将GPs及其磷酸化衍生物作用于鸭胚胎肝细胞,其中磷酸化的GPs抗病毒感染和抗肝细胞凋亡的作用明显强于原皂苷[47]。三甲胺N-氧化物(trimethylamine-N-oxide,TMAO)是胆碱被肠道微生物代谢后的氧化产物,是一种存在于循环系统中与肝毒性和心血管疾病相关的物质,GPs能显著降低高胆碱饮食造模小鼠的血清转氨酶和氧化应激指标,修复受损伤的肝[48-49]。
6 结语与展望
目前临床上常用保肝药主要包括解毒类、促进肝细胞再生类、免疫调节类和利胆类等,而肝疾病的治疗原则之一为用药宜简,即患者在已经有肝病的前提下用药不能超过3种,以免加重肝负担,GPs具备上述保肝药大部分的调节功能,将之应用于临床具有广阔的前景。
在绞股蓝的急慢性毒性实验中,单次给予大鼠5 g · kg-1的绞股蓝水提物(相当于绞股蓝皂苷300 mg · kg-1),14 d内绞股蓝干预组的内脏指标和形态特性均与空白组无异[50];750 mg · kg-1的绞股蓝水提物作用大鼠后长达24周的时间内,大鼠的血象、生化指标、体质量、内脏重量和各脏器的形态学描述均和空白组无差异[51],这提示长期服用绞股蓝的安全性非常高,跟其他临床用药相比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
上述大量动物、细胞模型的研究证据表明,GPs的确具有非常良好的保肝功效。然而GPs应用于临床研究资料较少,其对肝病患者的临床疗效缺乏实验证据。但伴随代谢性肝病患者日益增多,在天然药物中寻找安全有效的降肝脂、降低氧化应激的新型药物具有重要探索意义,凭借绞股蓝丰富的药材资源和持续不断的科学求证,相信随着实验的深入研究和临床的积极应用,GPs有望能带来更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