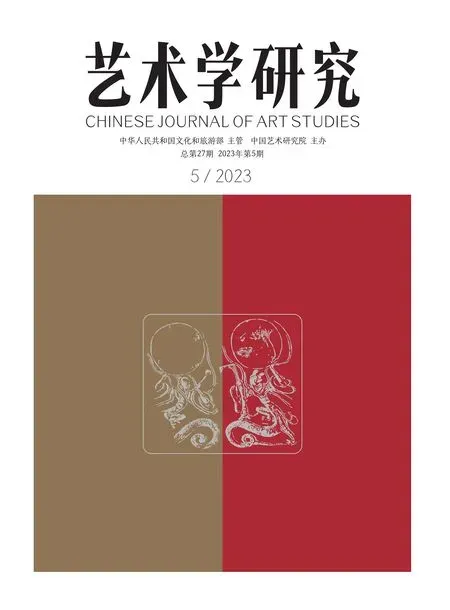版画4.0:科技巨浪中的危机与可能
王霄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
2023 年3 月14 日,ChatGPT 的 开 发 机 构Open-AI 正式发布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多模态大模型GPT-4,随后微软宣布将GPT-4 接入旗下一系列办公软件工具,称“人类与电脑的交互方式迈入了新阶段”[1]竞泰资本:《科技|GPT-4融入微软办公软件,AI 2.0时代已经来临》,https://it.sohu.com/a/657627174_121252519,2023年3月22日。。对于创作者而言,输入几个关键词,软件就能写出条理清晰的文章;输入几个提示词(prompt),就可生成精美的数字图像作品。面对不断进化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挑战,还在手持刻刀、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版画家们,也感受到了迎面而来的危机,这一切不禁令人回想起五六百年前那个视觉图像陡然繁华的印刷时代。
一、雕版印刷术与复制版画的辉煌时期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最重大贡献之一。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在其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绪论”中明确指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四种伟大发明(指中国四大发明——引者按)的传入与流播,在现代世界的诞生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形塑作用。”[1]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XIX.孙中山更于《实业计划》中指出:“据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质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也。”[2]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可见,印刷术作为人类早期传播科学思想的重要媒介,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在中国,雕版印刷术最初被用来印刷宗教文字与图像,这些图文并茂的平面作品可以被视为早期的版画。这一时期的版画以传播思想和复制图像为目的,以尽可能精准地还原“母本”供更多人阅览为核心要旨。当然,古代并没有现代美术意义上“版画”的概念,“版画”的存在形式非常多元,除了大量的宗教图像之外,还包括诸多图文并茂的劝善经典,如《圣迹图》《女范编》;工具类书,如《营造法式》《本草纲目》;书谱画谱,如《宣和画谱》《芥子园画谱》;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这些文化典籍、知识手册、通俗读物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生产、传播到不同阶层的人群之中。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书籍的需求大增,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各类带有插图版画的戏曲、小说书籍,《西厢记》流传至今的就有30 多个版本(图1);一些极尽雅致的诗笺画谱成为流传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高端文化商品,如《十竹斋画谱》《萝轩变古笺谱》;纪实和欣赏类的风景版画开始出现,如《湖山胜概》《环翠堂园景图》;还有大量张贴于百姓家中的年画,日常娱乐的纸牌叶子,以及近些年开始被学界研究、作为外销商品的姑苏版画,它们至今仍被保存于许多欧洲古堡的墙壁上,细致精美。这些形制多变、雅俗共赏的古代版画,上至宫廷、下达百姓,甚至远播欧洲,深刻地塑造了古代人的感官经验以及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图1 《西厢记》版画之《窥简》,明崇祯十三年(1640)闵齐伋制六色套印本,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同中国一样,欧洲的版画最初也是以满足宗教需求为目的的印刷品,随后广泛地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15 世纪,木刻版画业已广泛流行于欧洲各地;16 世纪,雕刻铜版画开始流行,除了印制艺术家的原创作品,还用于复制名家壁画和油画,以及制作书籍插图和画集,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丢勒是欧洲第一位将版画提升至艺术品地位的关键人物,他以极其精湛、丰富的技法,将原本简易、粗犷的木刻版画提升为可同壁画、油画相媲美的精美艺术品,“他以卓越的技巧,用这种诞生不到一世纪的印刷术,创作出能与传统艺术相媲美的艺术作品……他把金银匠的雕刀工,运用到木板上,用类似铜板线那样密集的平行排线和十字交叉线的衬影来加强形体的立体感和光感……丢勒犹如一个勇敢的旗手,把版画带向一个新的天地,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把版画的幼苗栽种在文艺复兴的沃土上生根开花”[1]张殿宇:《西方版画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16 世纪,工商业兴起,各种商业用途的版画开始出现,除了复制油画和壁画的作品,还有地图、地方景观图像、肖像画、民间版画、“小故事书”(Chapbook)等,这些大量刊印发行的版画成为当时人们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复兴以后,荷兰成为欧洲重要的印刷基地,主要是复制版画,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原创版画家,其中包括艺术大师伦勃朗,他将蚀刻铜版画发展为一种不同于油画的、独具魅力的创作媒介,并通过这些轻盈、便于携带和传播的版画作品,使自己在有生之年即名满欧洲[2]盛葳:《图像的旅行:版画、印刷与出版》,《美术》2023年第3期。。
15 至16 世纪,印刷文化在全球的兴起改变了知识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基本模式。相较于古老的、口口相传的文化传播模式,印刷制品的传播更为精确,效率更高;而相较于在昂贵的羊皮纸上手抄手绘的传播模式,印刷因能批量生产、价格相对低廉而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它就是那个时代的“新媒体”。正因如此,今天被称为“版画”的印刷图像的普及,迅速而全面地重塑了“艺术”的内与外,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艺术史的早期现代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旧媒介”与“新艺术”
19 世纪,欧洲人在传统印刷术基础上融入现代科技,发明了以机械操作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印刷术,尤其是平版印刷,迅速在全球得到运用。与之相比,手工雕刻印刷版画的人力成本高、产出率低,精细程度也远不及机械印刷出来的工业产品。以天津为例,据天津鼓楼北的印刷作坊“毓顺成”老板张芳田回忆,20 世纪伊始,石印年画在天津逐步取代了木版年画。1925 年天津年画市场上,石印年画销量已经超过7000 万张[3]金冶:《天津杨柳青年画考察》,《人民美术》1950年第2期。。在现代印刷术的冲击之下,手工雕版印刷行业迅速衰落。技术的落伍,导致“版”作为重要的复制、传播方式的核心价值被现代印刷术所取代,版画由新媒介沦为旧媒介。然而,历史常常出人意料,正如摄影术发明之后,人们认为绘画即将死亡,但绘画至今仍然活跃。与之相似的是,在版画的媒介价值被取代的危急时刻,历史上几个特殊的事件和运动,改变了版画史的走向。
丢勒通过精研版画技法,融合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创作出大量精美的木刻作品,并在全欧流传,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Morris T.Everett, “Revival of Interest in Etching,” Brush and Pencil 8,no.5 (Aug.1901): 233-246.。但在随后的17 世纪后期至19 世纪前期的美术史中,版画只是被主流美术脉络所遮蔽的一条忽明忽暗的分支,除了戈雅这样极少数的案例之外,版画主要被用于复制经典油画、壁画作品,以及制作、广告、票券等特定的商业行为。直到19 世纪中期,欧洲兴起蚀刻版画复兴运动(Etching Revival)。这个由艺术家、收藏家、画商、出版商等共同参与的运动,旨在提高版画的艺术地位。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版画逐渐脱离了复制图像的局限和作为附属性媒介的束缚,成为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现代艺术类型。巴比松画派的杜比尼、柯罗、米勒,印象派的毕沙罗、马奈、德加、劳德雷克,野兽派画家马蒂斯,表现主义画家蒙克、鲁奥,立体主义代表人物毕加索,现实主义版画家柯勒惠支、麦绥莱勒等都创作了许多独具魅力的版画杰作,成为美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与欧洲的蚀刻版画复兴运动遥相呼应,20 世纪初,创作版画运动(Sōsaku-hanga movement)在日本兴起。1904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报《明星》7 月号刊登了山本鼎的版画作品《渔夫》,作品介绍中第一次使用了“版画”的概念。随后不久,“版画”一词传入中国并沿用至今。中国的现代创作版画同样始于20 世纪初,留日艺术家李叔同回国后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乐石社”指导学生进行木刻创作。20 世纪30年代初,在鲁迅的引领下,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迅速由上海扩展至杭州、北京、广州,随后在全国蔚然成风,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版画因为能够迅速地复制,因此在各种革命运动中都承担着宣传的职能。延安时代画家们根本弄不到油画颜料和宣纸,只能用印报纸的廉价油墨和农村随处可以得到的梨木板来创作木刻,抗战木刻和救亡漫画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形式,更进一步把传统木版年画改造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新年画。欧洲也是一样,从英国的荷加斯开始就用版画来制作政治讽刺漫画,在历次社会革命中版画都是重要的宣传工具。”[1]邱志杰:《版画是科技艺术的重要源头》,https://mp.weixin.qq.com/s/0dTItSNI9sgJL4-Cstze_w,2023年4月20日。在革命年代,版画数次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最高效和有力的宣传媒介之一(图2)。20 世纪50 年代,随着新中国现代美术学院的建立,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均成立了版画系,开始进行专门的版画教学和创作。至此,版画被纳入现代美术学院的纯艺术系统,成为具有独立审美和收藏价值的“精英艺术”。
三、版画“4.0时代”
如果根据功能、形制的转变对版画的历史进行粗略划分,公元前3000 年苏美尔人的滚印、商周时期陶罐上的刻纹、战国时期的肖形印章,这些具有刻、印行为的“作品”,属于版画的雏形时代——1.0 时代;19 世纪现代印刷术发明前,主要用于复制、生产和传播图像的手工印刷版画时期,则可以被视为版画的2.0 时代;19 世纪末现代印刷术发明至今,版画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功能的纯艺术类型,缔造了版画的3.0时代;而近年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及其广泛的社会应用,则推动着版画进入4.0 时代。在新文科与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诸多既有的专业框架、知识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调整,版画技术与艺术科技的边界已变得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版画系统内部开始充斥着矛盾、反思与动荡。
从中国当代版画创作的核心阵营——美术学院系统来看,十几年前仍少见对“数码版画”的认同和实践,而如今成长于学院系统的青年版画家,对“数码版画”已怀揣着发自内心的认同,并能自由洒脱地运用数字技术创作版画。那些自幼习惯电子屏幕、虚拟图像的新一代年轻艺术家,或许并不认为纸质印刷品比虚拟图像的世界更“真实”。不过,就版画的经典定义而言,如果只是将手工制版、分版的过程转移到电脑中,借助数码技术将传统版画中的造型语言转换为虚拟图像,再经过打印机等输出平台印制完成,那么这样的数码版画创作在工作流程和底层思维方面实际上并无太多新意。新技术的应用与适配不当,以及对“数码版画”的过度使用,反而会使作为艺术品的“版画”概念被混淆,甚至被消融。面对汹涌的科技巨浪,作为“艺术”的版画,如何与新科技建立对话,彼此适应、相互协调,而不是被技术反噬甚至丧失其本体?版画艺术家、版画从业者将何去何从?近年来,不同的版画家给出了不同的回应。
四、升级装备——“媒介是人的延伸”
20 世纪60 年代,媒介研究兴起,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强调技术、社会和生物学的内在关系,把技术看作人类身体或感官在社会心理上的外延。他的认识至今仍然有效。20 世纪90 年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艺术品的媒体呈现方式以及人们观看艺术的方式日益丰富多元,艺术的展陈空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技术的迭代、艺术理念的更新,对作为艺术媒介的版画提出了新的要求。版画技术装备的升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数字技术、新媒介方法运用在创作过程中,作品的最终呈现形式仍然为平面版画;另一种则是从创作过程到作品的最终呈现,都进行了技术和形式的更新。
学界公认的最早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美术创作领域的案例,是1950 年美国数学家、绘图员兼艺术家本·拉波斯基(Ben Laposky)使用示波器创作的作品《电子抽象》(Electronic Abstraction),随之引发了人们对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美术创作的思考和讨论。经历了20 世纪60至80 年代数字化技术应用的起步和发展期,计算机绘画(Drawing Computer)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并迅速发展,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计算机绘画在我国也逐步兴起。对新技术颇为敏感的版画家陈琦,从那时开始就将电脑技术源源不断地嫁接、嵌入自己的版画创作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当代版画的新局面。陈琦的水印木刻版画作品《2012 生成与弥散》(图3),制作技术非常复杂,作品共有240 块印版,分7种颜色套印而成,二稿时使用计算机进行绘制、素材处理和效果预览。他在分版过程中借助矢量软件完成数字文件制作,在制版阶段使用高精度激光雕刻机进行雕刻,从画面语言上体现了数字化和科技化的逻辑。这件版画作品实现了技术与手工的高度契合,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水印版画。电脑分版、激光雕刻等数字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拓展了人的手、眼所能控制和涵盖的范围,将版画创作推进到实现巨大尺幅与高精密制作并举的新阶段。当这件长42 米、高4 米的水印木刻版画于2019 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出(参展部分长24 米)时,展场内的作品犹如一本展开的巨大经折装书页,步入其中仿佛置身于一片历史的汪洋之中,同时也与威尼斯水城的文化意涵相呼应。正如陈琦所希望的,“观众站在这幅作品前时,可以进入另一个场域,任由自己漂浮于主观意念的海洋,感受思之无涯,意之无垠”[1]薛浥尘:《陈琦专访丨水光之间,无所来,亦无所去》,https://i.cafa.edu.cn/cafaresearch/resc/?s=123381,2023年1月26日。。这件鸿篇巨制正是基于技术装备的升级,突破了版画表现力的极限,带给观众以强烈的感官震撼和浸没式的思考空间。

图3 陈琦,《2012生成与弥散》,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现场。
2009 年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的大奖获得者、波兰艺术家马格达莱纳·杜达(Magdalena Duda)的作品《我——现在/我——未来》(Me-Now/Me-Future)(图4),运用了照相制版和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将现在的“我”与未来的“我”(经过数字技术虚拟的)并置在同一画面中,带给观众的不仅是视觉上的震撼,还有对岁月变迁、时光易逝的生命哲思。青年艺术家侯炜国早期经历了版画炫技阶段,后来更关注如何把情感注入十分复杂的语言和数字技术体系中,让情感和思考的部分凸显出来,把语言的部分遮蔽起来。他近期的作品“夜的第三章”系列,采用了图像切入+ 数字生成/ 选取+激光雕刻+架上材料拼贴的创作方式,最终的作品呈现为一种激光雕刻的木板与金箔交相呼应的新的视觉样式。侯炜国认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新的技术、新的媒介都是认知世界的方式,他希望在更大程度上让非版画领域的技术与思维方式介入创作,以打破固有思维。

图4 [波兰]马格达莱纳·杜达,《我——现在/我——未来》,2009年,凹版,70厘米×100厘米×2厘米。
上述几件作品借助现代技术实现了版画创作在作品体量、制作精度、形制创新与空间转换等多层面上的发展,同时还有效避免了观众对过度技术化的反感,通过作品给观众带来的感官震撼与情感共鸣,引发观者对作品中人文关怀和精神内涵的思考。
五、层级与模块,编辑与传播
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有不少版画专业出身的艺术家。他们从版画出发并以此为基础,创作出许多突破版画范畴的作品,开辟了全新的艺术领域。例如徐冰的《天书》和《地书》,邱志杰的《京东AI 生成地图》,康剑飞的《版画漂流计划》等。他们的作品很难按照传统方式明确归类,然而究其创作理念,却又无不根植于版画的两套底层逻辑:核心技术概念——“层级”与“模块”,社会属性——“编辑”与“传播”。版画从单版单色印刷发展至多版多色套印,产生了分版,也即形成了“层级”这一技术逻辑;套色技术中使用的组合版块,类似于现代化生产过程中隐形的“模块”。可以说,“层级”与“模块”是版画在技术和艺术两方面的本质特征。康剑飞的《版画漂流计划》充分调动这种特性,邀请不同地区的参与者针对艺术家提供的一个个“版块”进行共同创作,最终再进行图像的聚合与展示。制作版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编辑、传播知识和图像,所以“编辑”与“传播”也是版画实现其社会属性的重要方式。徐冰的《地书》,邱志杰的《京东AI 生成地图》,运用的素材均能体现出艺术家独到的视角,方法和媒介也与先进的技术相关联,但其底层逻辑仍是基于版画的编辑和传播原理。
(一)层级与模块
“层级”源于版画制作过程中的分版与套色,它也是数字时代图像软件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譬如Photoshop、Illustrator 等软件中的“layer”。“模块”源于版画中可移动、组合的“版块”。雷德候(Lothar Ledderose)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模块化生产》一书中,将“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视为中国艺术从古至今的本质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代汉字系统、青铜艺术、画像砖石、建筑艺术中,也同样体现在明清时期的印刷艺术和文人画中。“模件体系并非中国所独有,可资比较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文化之中。然而,中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借助模件体系从事工作,且将其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水准。他们在语言、文学、哲学还有社会组织以及他们的艺术之中,都应用了模件体系。”[1][德]雷德候:《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页。正是因为模件的应用能够进行快速、高效的规模化生产,所以“模块”在现代社会中亦被广泛应用,如居民社区结构、流水生产线、集成芯片、乐高玩具、宜家家具、网络游戏、体素艺术(Voxel Art)等。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所使用的核心技术之一也包括人工智能模块。近期,美国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一份报告指出:“AI 产业飞速发展,‘技术扩散’速度超出互联网革命,其中模块化(Modularity)是AI 实现更快增长的关键。”[2]华尔街见闻:《如何投AI?全球一线VC面临的“三大焦点问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045571818380101&wfr=spid er&for=pc,2023年5月16日。合成生物学中的“生物积木”(BioBricks)也是基于类似的原理[3]参见百度百科:“生物积木”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生物积木 / 2080907?fr=ge_ala,2023年6月3日。。因此,熟知层级、模块工作方法的版画家很容易介入这些新兴的领域,将实体物质媒介和数字虚拟技术、人类情感进行“层级”与“模块”的分析、归纳与融汇,实现旧媒介与新技术的嫁接与创新。
2014 年,康剑飞将一件版画作品《林雪》分割成400 块,与策展人姚远东方一起,通过不同渠道征集了400 多位参与者,让他们带着免费领取到的“模块”在世界各地漂流,记录各自人生的重要时刻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目的地。2015 年7 月,其中的320 块版画重聚广州风眠艺术空间,以文字、图片和版画实物的形式呈现300 多位普通人与艺术家在一年之中的经历与创作。
(二)编辑与传播
“层级”与“模块”的分析、归纳与融汇,均源于版画重要的社会属性——“编辑”与“传播”。版画自诞生以来就与媒体的编辑、信息的传播紧密联结在一起。版画家们非常了解自己创作的图像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从创作伊始,作品未来的广泛流传就被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纳入构思之中。如今,虽然各种各样的电子屏幕在传播功能上取代了古代版画,但旧媒介的运行方式总是不断渗透在新媒介的底层逻辑中。对符号的编码与传播,使得版画专业出身的艺术家可以迅速融入数字化语境的探讨和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艺术逻辑。艺术家徐冰早年的成名作《天书》是对传统文字的“再编码”,近年来的作品《地书》则是一本可读的小说,是艺术家花数年时间搜集整理出的一套公共标识语言系统,能够让不同母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视觉符号顺畅沟通。此外,徐冰近作《蜻蜓之眼》也具有相似的逻辑,艺术家广泛收集各种监控视频,并将这些原本毫无关联的内容剪辑为一部叙事性电影。这些作品在整理、归纳、呈现方式上都使用了新的技术和媒介载体,但其作品的底层逻辑依然是基于版画编辑、传播的媒介属性。
邱志杰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地图作品。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地的早期地图,很多都是版画刻印完成的,从曾经纸质的地图到如今虚拟的Google 3D 全景地图,虽然媒介在不断演变,但本质上都是对于地理位置及其相关的图与词的归纳、编辑、呈现和传播。邱志杰将用水墨(旧媒介)绘制的地图与人工智能(新媒介)结合,开发出一款人工智能软件。当观众通过语音或文字输入任何有效单词时,程序会自动关联并构建出一个个不同的地图组合。观众的每一次输入,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再编辑、再传播的互动过程。“地图的演变是文本语义无限增长的结果。由于在文本语义层面的无限扩展,地图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自主增长系统。”[1]张桂森:《邱志杰:时隔十年,从“破冰”到“寰宇全图”的Mapper》,https://www.sohu.com/a/289868255_149159,2023年1月18日。这种旧媒介与新媒介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艺术家、作品与观众的深度互动。
徐冰与邱志杰都是出身于版画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早已超出某个传统“画种”或“艺术门类”的范畴,而开辟了各自新的语言系统。然而版画的“层级”与“模块”思维,以及“编辑”与“传播”的创作方式,仍是支撑其创作的底层逻辑,他们在此逻辑上实践出移动互联网上的“融媒”创新。麦克卢汉曾说:“媒介作为我们感知的延伸,必然要形成新的‘比率’。不但各种感知会形成新的比率,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形成新的比率……收音机、电唱机和录音机使我们重温诗人的声音,给诗歌鉴赏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1][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版画之所以被视为重要的“媒介”艺术,正是由于其游走于“画”“刻”“印”等多种创作方法与媒介叠合的“中间地带”。媒介(medium)一词的本义是“居间的(in the middle)”,版画恰恰正是这样一种“居间的”艺术形式。ChatGPT 时代,媒介与媒介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曾经的旧媒介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和替换,而是变成了新媒介的一部分,同时对新媒介产生影响。“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2][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第12页。4.0时代的版画,正是如此这般游走、渗透、叠合在不同艺术媒介之间,不断幻化衍生出新的形态。
六、去技术化、低科技
在一些版画家尝试新科技、升级系统的同时,还有一部分版画家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穷尽版画传统技术语言表达的可能性,例如方利民,多年来一直在水印木刻领域深耕,创造了《水印宝典》。这套《水印宝典》总结了现代水印木刻创作的诸多印法,在教学中广为流传,正如陈琦评价的那样,“除了操刀剞劂外,他一直着力于印法研究,在同一个版上实验各种印痕效果,努力挖掘印刷空间资源。在他的水印版画作品中,并置了丰富多样的印刷痕迹,浓、淡、干、湿、轻、重、枯、润,错综穿插,各得其所,有机地组合为具有现代视觉意味、动感丰富的画面”[3]陈琦:《中国水印木刻的观念与技术》,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页。。《水印宝典》将古代用作绘画教材的版画画谱进行了现代性的转换与创新,这种现代性的转换完全由手工制作实现,采用了古籍版本的装帧方法,为现代美术学院的水印教学谱写了新篇章。
还有艺术家使用“去技术化”的方式来挖掘版画的当代可能性。艺术家谭平2012 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一画”中最重要的作品《+40m》(图5)是他耗时6 个小时,用刻刀在木板上一气呵成刻制的。谭平说:创作《+40m》时,“我选择木刻的方式完成,这和我以往从事创作的经验有关。所有的人生经历、对艺术的理解,都在刀和木板接触的一瞬间体现出来”。谭平在刻板之前对画面效果没有预想,具体刀法完全没有设定。这是一种摒弃既有经验的“去技术化”创作方式。“刻刀与木板接触的瞬间如同锋利的刀划开皮肤,深深地,慢慢地行走,不断深入这块黑色平面的内部。六个小时刻刀在木板上抑扬顿挫地行走就像将我自己沉入生命的‘时刻’,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经历,对艺术的理解,包括我内心的挣扎,全部留在刀和木板磕绊的瞬间,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追求的精神境界。”[1]应妮:《中国美术馆主展厅首次接纳抽象艺术展〈1劃〉》,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2/12-08/4393332.shtml,2023年4月20日。这种“去技术化”的版画创作方式,强调的是手的动作在木板上的记录,“刻”的行为与艺术家的内心世界高度融合,每一个“技术”的瞬间都灌注了艺术家的精神与感情。

图5 谭平,《+40m》,2012年,中国美术馆展览现场。
此外,前文所述徐冰的作品《地书》是个不断发展的项目。“2016 年《地书》发展成了立体书,基本囊括了所有立体书的表现手法,如:翻翻、转盘、拉杆、轴杆等,标识符号与立体结构巧妙地结合反映出更强大的互动性和可读性,使这本世人都能读的书变得更加奇妙有趣。在纸质书籍没落的局面下承载着原始的阅读功能,寄托着人们对于翻动书页的情感体验,更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展现形式。在今天高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潮流中,徐冰却反向地寻找原始的、低科技艺术表达的魅力。”[2]雕塑热点:《解琐文化密码|徐冰的艺术作品和创作方法》,https://www.163.com/dy/article/GONCMTIE0534A312.html,2023年5月11日。《地书》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既运用了最新的媒介手段,又复原了手工制作带来的情感体验。在同一系列作品中,艺术家的创作如同弹簧,伸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这或许正暗合了4.0 时代的版画家的风格特点,基于同一个源点——“版画艺术”所探索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
七、偶然、无序、即兴
版画创作的过程理性、严谨,优秀的版画家身上常带有如科学家和管理者一般的气质,而艺术创作又需要感性与直觉的调动,优秀的版画家会将二者完美协调,形成一种规则之上的自由。这种状态类似钢琴的即兴演奏,在有限、有序的黑白键盘上演绎出美妙却无法复制的音乐。在科学史上,许多发明也诞生于实验中的偶然甚至错误。例如青霉素的发现源于久置的培养皿中的一块无菌区域,微波炉的发明源于雷达技术的研究。可以说,许多创新源自偶然、无序、即兴。在4.0 时代的版画创作中,不同媒介偶然、无序与即兴的混搭常常碰撞出有趣的作品,这类作品“反标准化流程”,甚至会故意“出错”,却具有不可思议的创新价值和启示意义。
笔者的作品《嫦娥奔月》(图6)将制作版画作品所需的原始物质媒介——绢、印版、基底三部分剥离,使用视频影像媒介记录、干扰、解构了创作过程的原始逻辑,将作为物质实体的“版”与虚拟的数字“版”叠加、渗透、共融,编辑、建构了“错误”的新逻辑。最终视频作品中的“版”有手工刻出的印板,有纯粹作为象征的物质介质(以银丝布隐喻月光),有手绘与影像结合的运动中的“版”,这些“版”实体与虚拟混杂,增强了视觉效果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本该理性、有序的版画创作过程变得偶然、不可捉摸。这是一种建立在技术、规则之上的即兴创作,在此过程中,“人”与“技术”体现出一种张力和博弈。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了技术与艺术的辩证关系:技术是理性、有序、归类的,正如版画制作的标准化流程;而艺术尤其现代艺术往往是无序的,创造性存在于常规秩序断裂后所生成的新逻辑中,这些无法预测、即兴与偶然的东西恰恰是艺术最迷人之处。在某些AI 生成并售卖作品的网站上,售价最贵的竟然是带有偶然性、出错的图像,每一次传播中的偶然性,甚至“错误”或许正是其独特价值所在。
结语
20 世纪70 至80 年代,在人们还热衷于谈论后现代时,批评家和文化学者们用这个概念表达出的是他们内心深深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新的电子和数字技术已经开始深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一个算法世界的零维空间里,一切都将无可挽回地终结在一条死胡同里。在这种论调的攻势下,人们开始对所有具有身体性的东西进行抽象提炼[1]参见[德]西格弗里德·其林斯基:《依旧出新:从早期近代通往未来的可能——评缪晓春的文艺复兴作品三部曲:〈虚拟最后审判〉〈H2O〉和〈坐井观天〉》,黄晓晨译,乌塔·格罗森尼克、亚历山大·奥克斯编《缪晓春 2009——1999》,德国杜蒙出版社2010年版。。来自柏林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迪特马尔·坎珀(Dietmar Kamper)在1989 年接受采访时,曾对这种世界观予以回应:“目前,对我们而言,致命的不是癌症,也不是艾滋病,而是我们将经历视听的死亡,将溺亡于图像的洪流中,而不是自己去更多地经验生活、以自己的身体去获取感官体验。”[2]Das Auge,Zur Geschichte der audiovisuellen Technologie.Narziss, Echo, Anthropodizee, Theodizee.Dietmar Kamper im Gespräch mit Bion Steinborn,Christine v.Eichel-Streiber,转引自[德]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依旧出新:从早期近代通往未来的可能——评缪晓春的文艺复兴作品三部曲:〈虚拟最后审判〉〈H2O〉和〈坐井观天〉》, 黄晓晨译,乌塔·格罗森尼克、亚历山大·奥克斯编《缪晓春 2009——1999》。
历史总在反复上演相同的剧本,如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同样的境遇。数字算法、虚拟图像已经悄无声息地将诸多实体艺术卷入一种更为虚幻莫测的文化交互界面。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4.0 时代的版画艺术家将怎样“突围”?如果是个体版画家的艺术创作,那么怎样创新和革命都不为过。然而,如果我们将版画放在美术学院、学术系统的大框架下,视其为“美的艺术(Fine Art)”的一个重要类型,势必仍需厘清版画的边界、内涵与外延。在讨论“数字技术”与“版画”的关系时,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如果不再区分数字算法生成的虚拟图像和印刷出来的物质化形式的版画哪个才是真正的作品,版画必然面临自我解构的险境。如果“印刷”的行为最终缺席,“版画”将彻底沦为由算法控制面板与屏幕组成的虚构场。反过来,如果死守传统版画固有的条条框框,那么,这种历史悠久的艺术最终必然会因为无法创新和跟上时代而成为历史的记忆和往昔的象征。对于当代版画家而言,无论是积极采用新科技创作,还是反过来强调非科技、反科技的身体经验,它们都是今天这个新时代的产物,无论它们能否成功,都是4.0 时代版画的重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