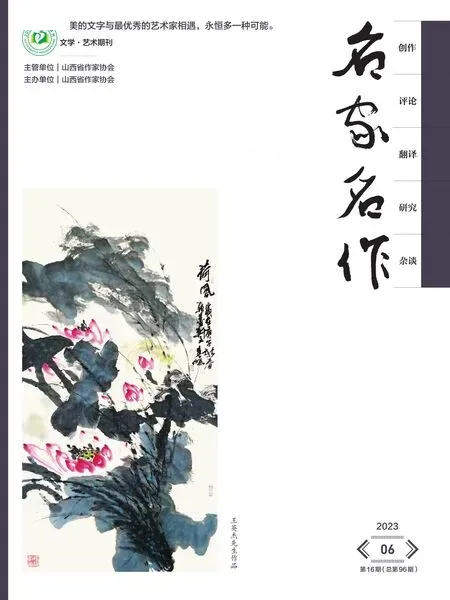元杂剧中的妇翁形象浅析
马燕茹
“妇翁”即妻父,妻子的父亲。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便有“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此处的“妇翁”便是妻之父的意思。长久以来,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妇翁形象并未受到关注,甚至极少出现。元杂剧作为元“一代之文学”,“它既属于俗文学的范畴,但又沾上了雅文学的灵光,正处于雅、俗文学交汇的交叉点上”。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一次巨大突破,使得俗文学开始以矫健的雄姿活跃在文坛艺苑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创作者来看,由于元杂剧的创作主体是“士失其业”的读书人,他们大多出身不高且长期居于民间,对市民生活有较多的了解,视角便在其中得以展开。而从接受对象来看,元杂剧面向的观众更多属于市井细民,他们在对王侯将相、狐鬼花妖等故事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自身的日常生活。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婚姻爱情、家庭伦理方面的杂剧应运而生并渐成风尚。
“所谓家庭剧者,乃属于伦理范围之戏剧”,即通过戏剧来展现家庭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及伦理问题。而有元一代,正处于以男性为主导的封建王朝之中,妇翁必然在家庭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是家庭一切事物的主宰,有高踞于家庭成员之上的种种特权”。妇翁角色的不可或缺,必然使得妇翁形象在婚姻爱情剧及家庭问题剧中占有一定分量的比重。笔者以元杂剧中的典型妇翁形象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元杂剧中涉及的妇翁形象类型
元杂剧内容极为庞杂、包罗万象,描绘和牵涉的范围极广,正如元人胡祗遹所说:“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可见上至达官贵人,下达市井小民,元杂剧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分布于各个阶层,并因为职业及身份的差异而均有不同。有元一代等级制度十分鲜明,统治者依照民族将百姓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阶层,并且出于职业身份的差异划分了不同的户籍,“元太宗乙未籍户时,正式划分了诸色户计。此后,诸色户计的划分更趋细密,有民、军、站、匠、屯田、打捕、淘金、灶、矿、炉冶、运粮船、儒、医、僧、道、阴阳人、礼乐等二三十种”。依照身份地位的不同,大致可将元杂剧中的妇翁形象划分为贵族型、平民型两大类,并可根据职业身份的具体差距再分别进行细分。
(一)贵族型
在以男性为中心、父系父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男性作为一家之主,似乎始终都扮演着严厉冷酷的形象,而作为一国之主的君王,譬如《晋文公火烧介子推》中的晋献公、《楚昭公疏者下船》中的楚昭公似乎更印证了“最是无情帝王家”的说法。以统治者身份出现的妇翁主要有《沙门岛张生煮海》的东海龙王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的洞庭龙王,二者都是源于传说的虚拟的君主形象。《沙门岛张生煮海》中的东海龙王起初因张生是凡人,对女儿琼莲与张生的婚事极力反对,但当张生遇见上仙、得授法宝,受到煮海的威胁后,只能被迫把他招请为婿,并尽心操办婚事。《洞庭湖柳毅传书》中的洞庭龙王为了报答柳毅帮传家书的救女之恩,便请了钱塘火龙做媒,想要促成龙女三娘与柳毅的婚事,即便被柳毅拒绝也并未选择用权势压人逼他答应。总的来说,以妇翁形象出现的两位龙王作为虚拟的君主角色,位高权重却并未仗势欺人,甚至呈现出善解人意、不重视等级观念的特点。另外,两篇有关帝王妇翁的杂剧都是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寄托了作者对圣主贤君的呼唤。
官吏亦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妇翁们的官吏身份必然也会对其子女的婚姻爱情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醉酒思乡王粲登楼》中的妇翁蔡邕身为当朝丞相,其女曾与王粲指腹为婚。王粲“胸襟太傲”,他为对其涵养锐气,有意进行了讽刺和挖苦:“拜下去,只怕污了你那锦绣衣服。”他暗中帮助王粲投奔荆州刘表,却因王粲“才有余而德不足”未能得到任用。直到后来王粲获封天下兵马大元帅,想要因之前的冷落对蔡邕“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时,在曹植的点醒之下才知岳父的良苦用心。《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中的妇翁王辅之作为府尹,对女儿的要求几近苛刻,严令其谨遵“三从四德”,在发现女儿竟私下将“开元通宝”赠予韩翃时大为恼火,后韩翃高中状元又经李白做媒,才得以促成婚事。再如《海门张仲村乐堂》中的张仲,本是年迈致仕闲居的县官,因女婿遭到陷害,险些替其顶罪,好在最终判案的府尹明察秋毫,才终得圆满。官吏型的妇翁形象数量较多,又因官位高低和个人品行的差异,在剧中起到的作用也都有不同,剧作者刚好借此联系元代社会,以虚拟剧本映射现实人生,从各个方面真实展现了百姓疾苦。
(二)平民型
而就平民型的妇翁而言,由于其职业和社会身份极为纷繁,对其的详细分类可参考在班固的《汉书》卷二四的《食货志上》中所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士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列为士、农、工、商四种,其中尤以儒士和商贾的形象最为典型。
《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窦天章是一位出身穷苦的儒士型妇翁,他因妻子亡故,还要上朝取应,为了能进京科考,只能靠出卖女儿以换得盘缠,将窦娥送予蔡婆婆当童养媳,间接导致窦娥人生悲剧的形成。《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刘从善积德行善,多年辛苦经营才成为家财万贯的商贾,赘婿张郎觊觎家产,赶走了侄儿刘引孙和他怀有身孕的侍婢小梅。最终他因“散家财”的举动得到好报,将家产平分给了女儿、侄儿、老生儿。该剧在塑造正面的商贾型妇翁形象的同时,还揭露了当时价值取向的畸形以及部分人为谋取金钱利益而罔顾亲情的丑态。
除此之外,其余的市井小民,譬如《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中的李社长重情重义,因与其父刘天瑞的朋友之情,毅然相信同女儿指腹为婚的准女婿安住,并为帮助他拿回家产四处奔忙,对准女婿极尽护佑。
总而言之,对平民型妇翁而言,相比于帝王型或官吏型的妇翁而言,他们因为力量更为微小,有时只能服从于命运安排与社会动荡,但因更接近于作者的现实人生,形象也更为生动鲜明。
二、元杂剧中妇翁形象的艺术功能
(一)妇翁对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在以家庭伦理或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元杂剧中,妇翁的形象都不是作为主人公出现的,但由于其处于封建大家长地位,必然对大多数婚姻爱情及家庭问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对故事情节的展开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关于妇翁形象对情节发展的作用,大致可分为两种,即解决困难或制造阻碍。
在元杂剧中,有些婚姻爱情一开始面临着诸种困难和问题,正是由于妇翁的帮助克服了这些困难,使问题终获解决。例如《赵匡胤智娶符金锭》中的汴梁太守符彦卿为人开明,在几人争娶符金锭的过程中,并未自行替女儿做主,而是依照女儿符金锭的心意为她选定夫婿。《朱太守风雪渔樵记》中刘二公的女婿朱买臣满腹文章却不思进取,为激励朱买臣考取功名,他一面令女儿玉天仙向朱买臣索要休书,对他各种奚落,一面又暗地里将白银锦衣交给王安道,用以资助女婿上朝取应。这一类型的元杂剧在故事开始便存在种种矛盾,但正由于妇翁的通情达理和良苦用心,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圆满大结局。
元杂剧中还有一部分妇翁,他们的存在给整个故事制造了逆境,使得婚姻爱情受阻。例如在关汉卿《王瑞兰闺怨拜月亭》中的妇翁王镇在得知女儿王瑞兰与蒋世隆私下结为患难夫妻后,嫌弃蒋世隆出身贫苦秀才,逼迫女儿抛下生病的蒋世隆跟他回家,给二人制造了婚姻爱情的阻力,到后来蒋世隆高中状元后才将其招为女婿。《鲁大夫秋胡戏妻》中罗大户的女婿秋胡成亲三日便离家当军十年未回,罗大户为偿还欠下的四十石粮食和获取钱财,逼迫女儿梅英改嫁李大户。这一类妇翁形象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当时的门第和金钱观念。
(二)妇翁对男主角形象的衬托
在现存160 余部元杂剧中,妇翁形象身为妻之父,几乎都是作为配角出现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婿”形象,则往往是剧作的男主角。翁婿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伦理道德关系,再加上妇翁与婿均为男性,这就使得妇翁形象在衬托和凸显婿形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好酒赵元遇上皇》中的妇翁刘二公,嫌弃赘婿赵元恋酒贪杯,对其动辄打骂,还放任女儿刘月仙与东京臧府尹生出私情,并通过派遣赵元递送公文的方式谋害他,赵元在途中因遭遇风雪延误半月,本该处斩却恰好遇上微服私访的宋太祖,与他结为兄弟。刘二公作为妇翁,当赵元离去送公文时,便迫不及待地催促女儿改嫁。他为人狠毒、目光短浅、唯利是图,这与赵元在斟酒浇奠时唱“一愿皇上万岁!二愿臣宰安康!三愿风调雨顺,天下黎民乐业”和为宋太祖三人付酒钱的做法形成对比,凸显了赵元的仗义贤良。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中的男主角崔通一朝高中,便背信弃义、停妻另娶,还诬陷原配张翠鸾为逃婢,将她刺配沙门岛。幸得翠鸾在途中与身居高位的父亲张天觉重逢,并请他主持公道。当得知岳父张天觉的身份后,崔通所云“我早知道是廉访使大人的小姐,认他做夫人可不好也”,更是衬托出他为人势利、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三、元杂剧中妇翁形象的文化意蕴
元朝统治时期,虽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占据中国几千年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仍根深蒂固。通过对元杂剧中妇翁形象的解读和探析,我们既能看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又能发现蒙元文化冲击下新时代精神的萌芽。
(一)儒家文化仍占据主流地位
儒家思想作为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春秋时期经孔子创立,后经不断完善和演变,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备受统治者推崇,在历代文人心中根深蒂固。高益荣指出:“不管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其主要的思想仍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重伦理、尚教化、追求仕进,在元杂剧中的诸多妇翁形象中均有儒家文化的烙印。例如《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中的王辅之、《闺怨佳人拜月亭》中的王镇都认为女儿婚姻应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剥夺了女儿的婚姻自主权。《萨真人夜断碧桃花》中的徐瑞重女子贞洁,因女儿碧桃与男子交谈便对其进行责骂,致其气愤而死。《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儒生窦天章更是一心追求功名仕进,将女儿典卖以换取进京的盘缠,间接导致窦娥的悲剧。
(二)蒙元统治带来新的时代精神
有元一代,游牧民族占据统治地位,把传统儒家文化撕开了一条裂缝,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带来新的时代精神。首先,在豪迈奔放的草原文化的冲击下,儒家传统出现断裂松动,意识形态上显得宽容自由。例如《赵匡胤智娶符金锭》中,汴梁太守符彦卿为人开明,在女儿择婿时完全尊重女儿意愿,超越了以往完全由父权操纵儿女婚姻的原则。其次,受北方民族婚俗的影响,传统的从一而终的贞节观被打破,不少妇翁支持女儿改嫁,例如《鲁大夫秋胡戏妻》中的罗大户、《好酒赵元遇上皇》中的刘二公,尽管此类型的妇翁并非一定是正面人物,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传统儒家贞节观念的松动。最后,因“重农抑商”的国策、“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导致商人长期处于被轻贱和歧视的境况中,而随着元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商人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不少以正面商贾身份示人的妇翁形象。例如《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刘从善、《朱太守风雪渔樵记》中的刘二公等,他们或是积德行善,或是用心良苦,俨然是值得称颂的商人妇翁。
综上所述,元代剧作家基于社会现实,塑造出一大批丰富多彩的妇翁形象。这些妇翁形象虽不算十分光彩夺目,但却广泛分布于婚姻爱情、家庭伦理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在官书、在正史里得不到的材料,看不见的社会现状,我们却常常可于文学的著作,像诗、曲、小说、戏剧里得到或看到。在诗、曲、小说、戏剧里所表现的社会情态,不仅比正史、官书以及‘正统派’的记录书更为正确、真切,而且活跃。”通过元杂剧中对妇翁形象的描摹和刻画,有助于我们透过这些渗透着时代气息的人物窥见当时的风情文化和婚俗传统,还原真实的元朝生活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