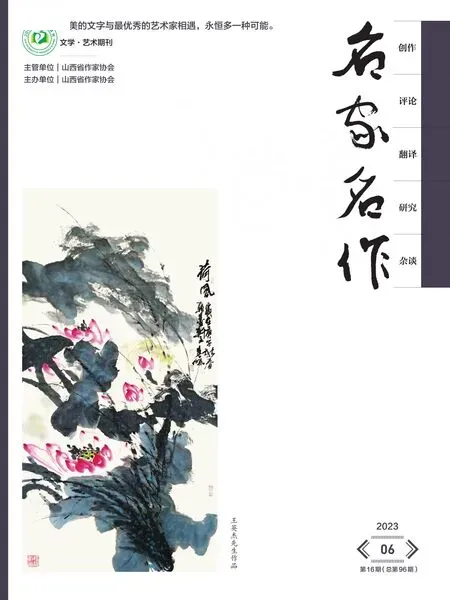从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看村上春树的反对阐释倾向
蒋 林
阐释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手段之一。苏珊·桑塔格在作品《反对阐释》中提到,在最早的艺术理论中,柏拉图提出艺术是模仿,是对现实的模仿。桑塔格认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西方对于艺术的研究、思考是建立在作品的本质是内容,形式是在内容的附属之上的。这种对内容的过分重视,导致阐释行为的不断扩张,在原本的意义之上寻找另一层意义,阐释极有可能变成改写、挖掘,甚至是破坏。桑塔格建议去“创作一些其外表如此统一和明晰、其来势如此快疾、其所指如此直截了当以至只能是……其自身的艺术作品”[1],并呼吁不要忽略作品带给我们的感性冲击,要更多地关注作品的形式。
从1979 年发表的《且听风吟》到2018 年发表的《刺杀骑士团长》,作品中的战争、暴力、心理治愈、后现代主义等特征与风格得到读者与学界的关注与解读。同时,也存在因无法阐释的情节和意象而产生的对作品的抗拒,这种无法阐释的风格在村上春树早期的创作中十分常见。年轻时代的“叛逆”与“不介入”世界的态度使村上春树的作品呈现一种“内向性”的特征,言说一种自我的消解与行为的无意义。读罢作品,村上春树没有为读者的疑问提供答案,他不过是把它们都写下来。在不断的创作中,村上春树增强了作品的可解读性,并在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介入中丰富了作品的主题。但是,部分情节的不可解读延续了村上春树一贯的风格与魅力,展现了作品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张力。
《刺杀骑士团长》的主人公“我”是一名中年肖像画画家,在接受妻子提出的离婚要求后,“我”进行了短暂的旅行并接受了好友雨田政彦的邀请,暂住在其父著名画家雨田政彦的一间闲置的屋子里。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神秘富豪免色涉,答应帮他与可能存在血缘关系的女儿秋川麻里惠建立联系。同时也在这间屋子里,“我”无意中找到了雨田政彦藏在阁楼里的画作《刺杀骑士团长》。在这之后,“我”被卷进了一连串复杂的事件中。
从反对阐释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洞穴中的铃、作为Idea 出现的骑士团长等情节与意象延续了村上春树无法阐释的创作风格;对画作做评价则是村上春树借小说人物之口明确自己的创作指向;另外,通过作品中对战争、暴力的书写进一步实现了村上春树要写一部“综合小说”的目标。
一、自我阐释:明白易晓的创作指向
《刺杀骑士团长》与其他的画作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与隐喻。在小说中,“我”在画画的同时,也在思考那些画作,所以“我”是如何理解这些画对于故事的进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村上春树2005 年出版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有一首同名歌曲——《海边的卡夫卡》,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隐喻,令人费解。但从头到尾,田村卡夫卡和演唱者佐伯女士都没有对这首歌的含义做出解读。读者所能知道的是歌词的表征与小说的情节有着互文的关系。“大部分对这部小说持否定态度的评论都抱怨这些形象令人摸不着头脑。”[2]无法阐释的情节和意象成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其进行自我阐释。
“我”在阁楼里发现了雨田政彦藏起来的画作《刺杀骑士团长》。画作本身和作画的技巧都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力,在“我”的眼中,《刺杀骑士团长》无疑是雨田政彦的最高杰作。但是“我”也由此产生了几个疑问:为什么这幅杰作要被藏起来?画作中的血腥与暴力意味着什么?雨田政彦为什么要画这幅画?经过免色涉的调查与雨田政彦的讲述,“我”大致了解了雨田政彦的经历。1936 年到1939 年期间,雨田政彦在维也纳学习油画,当时正值希特勒将势力延伸到奥地利的时期。雨田政彦与恋人、朋友组织了最终名为“Candela”的反法西斯组织,但是组织的行动以失败结尾。除了雨田政彦得到家族的庇佑被遣送回日本之外,他的恋人与朋友都遭到了迫害。回国后的雨田政彦由油画转向日本画,画下了《刺杀骑士团长》。小说最后,“我”对秋川麻里惠说,这幅画是雨田政彦“为自己,同时也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人们所画的画,换句话说,这是为了镇魂所画的画。为了净化许多流过的血而画的作品”[3]。接着“我”进一步解释这是一幅 “镇静灵魂,安抚悲伤,疗愈伤痛的作品”[3]。
对于村上春树的作品,有不少研究从疗愈的方向出发,但村上春树鲜少在自己的作品中解释其创作的指向。而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则以直白的话语将深藏于小说中的内核展示给读者。这种自我阐释不仅在对画作《刺杀骑士团长》的评价中得到体现,同时也可以在其他几幅画作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对于《杂木林中的洞》,“我”对将画作与弗洛伊德学说结合的解释方式表示否定,认为这是“无聊说法”[3];对于《白色Subaru Forester》,“我”通过安娜女士得知那是“让我看到自己心中的黑暗深渊”[3],是“我”内心黑暗的一面;“我”认为《秋川麻里惠的肖像画》表达了“没有任何东西能永远持续不变的姿态”[3]。
村上春树通过自我阐释,亦即明晰的创作指向减弱了前期创作中所谓“故弄玄虚”的创作风格,将主题清晰地传达给读者。但是,不可言说的风格依旧是他的创作特征之一,如果没有无法阐释的那一部分,村上春树的作品也将会失去一定的魅力。
二、无法阐释:功能性的荒诞情节
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存在不少无法释义的形象、情节和行为逻辑。比如《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山德士上校,以及谁才是真正杀死琼尼·沃克的凶手,在《1Q84》中天吾的父亲是如何找到青豆的住处,短篇小说《盲柳与睡女》中“我”的回忆与送表弟去看病之间的关系等等。在早期的创作中,“村上笔下的荒诞情节只表现出一种感受,其间真假难辨,庄谐并出,并没有确定的意义,也就无法加以阐释”。[4]村上春树写作至今,这种无法阐释已经成为一种风格。
除了画作《刺杀骑士团长》之外,铃也是小说中的重要物件。“我”将时常在半夜被铃声吵醒的事情告诉免色涉先生,并借助免色涉先生的力量挖开传来铃声的洞穴。洞穴中只有铃,没有他物,挖开洞穴这一行为将作为Idea 的骑士团长放了出来。在此之后,“我”将铃放在画室中,没过多久铃却消失不见。而当“我”穿越地下世界回到洞穴中时,铃又出现在那里,并成为“我”求救的物件。铃的出现仿佛只是为“我”服务,但同时“铃”也促成了故事的发展。铃与那四幅画作不同,它的意义是否仅仅在于其功能性呢?如果不去这样理解铃,那么这将是无法阐释的一部分。
当我们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作为Idea 出现的骑士团长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骑士团长能够穿行于各个地方,是他告诉“我”要去拯救秋川麻里惠,同样也是他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完成每一件事。同样,“我”潜入地下世界遇到的没有面容的男人是什么?为什么“我”的行为可以拯救失踪的秋川麻里惠?地下世界又在哪里?这些逻辑上的疑问不断在小说中出现,不仅是“我”的疑问,也是读者的疑问。村上春树并未就这些问题做出解释,但是当我们转变看问题的角度时,就会发现这些无法阐释都是功能性的,这种功能是为了使情节流畅。读者无法对作品中的超自然现象或者说是无逻辑的情节置之不理。这种写作的策略是村上春树毁誉参半的原因,但这种超脱自然法则的、无法阐释的情节是具有一定功能意义的。村上春树认为“事实和虚构应该是水乳交融”[5],在古老的物语中也有不少超脱自然法则的虚构。但是作为经典,它们仍在被人反复阅读。
这种作为功能性的、无法释义部分是村上春树作品的有机组成,是为小说情节的流畅性“提供的生动的即便失之狭隘的解决方式”[1]。大胆的设定虽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但是现实与虚构叠加、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互作用,使得文本的张力不断扩大,这种张力增强了其小说阅读的趣味性。
三、多元阐释:纷繁的创作主题
村上春树在早期的《且听风吟》《1973 年的弹子球》《萤》等小说中呈现的更多是一种无意义的写作。村上春树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是 “近似游戏的、超功利的创作态度,拒绝为某种目的的写作,拒绝形而上的意义的探求”[4]。而到了创作的第二个十年,在《奇鸟形状录》之后,村上春树一改之前的态度,试图在创作中加入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思考,这是村上春树“有意尝试了‘介入’他者式的创作”[6]。重要的标志是村上春树采访了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中的受害者与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他在采访后对材料进行整理集结,出版了《地下》。进入2000 年后,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1Q84》这两部作品中展现出自己对战争、暴力等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总而言之,村上春树的创作主题呈现出一种由少到多的发展趋势,并向着更多、更丰富的方向发展。在《1Q84》出版之后,村上曾表达过自己要创作“综合小说”[7]的目标,这一目标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得到了进一步实现。
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我”于阁楼中发现了画作《刺杀骑士团长》这件事,促使“我”与免色涉去回望那段残酷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对雨田政彦的理解,以及“我”对《刺杀骑士团长》的解读,村上春树反思了战争中的暴力行为,表达了自己对战争中所有受到暴力的人的关注。
同时,在涉及暴力这个问题上,村上春树并没有全盘否定暴力。作为原本弱势的一方用暴力反抗邪恶的情节在《海边的卡夫卡》《1Q84》中都有体现。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提道:“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8]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了高墙与蛋的含义,并说明哪怕作为“蛋”的一方是错误的,那也是由历史与时间去定义的对错,作为作家的自己绝不会向高墙屈服、为其写作。这里提到的“高墙”指的是强大的暴力机关,而“蛋”指的是手无寸铁之力的普通人。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我”在雨田政彦的注视下用刀刺向Idea 化作的骑士团长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雨田政彦年轻时的计划,也是他毕生的愿望,所以雨田政彦才能在不久之后安然离世。在村上春树看来,暴力不应被一味否定,作为正义的暴力有其存在的意义。村上春树通过书写战争,对暴力进行了辩证的思考。
除此之外,从成长小说的视角出发,小说中“我”进入地下世界,穿越了最为惧怕的黑暗,“我”在一系列的事件中获得了成长,体现了村上春树对于微小个体的关怀。另外,小说提及秋川麻里惠时,通过其父沉迷于宗教而对家庭的忽视表达了对于邪教的谴责。
“可以用‘物纷’理论作为理解村上春树的关键词。村上式的‘物纷’即是如实地、原生态地呈现人间生活的全部纷然复杂性,‘生活本就是这样,根本没有逻辑可言’。”[9]从主题方面对《刺杀骑士团长》的阐释可以是多元的,这里所说的多元阐释并非指暴力地、过度地对作品进行挖掘,而是在作品清晰明了的自我阐释基础上,找到作品主题的多元化。村上春树在创作中涵盖了当下日本的种种问题与现象,在创作“综合小说”的目标指引下,多元阐释同样回归到作品原本的面貌中。
四、结语
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惊讶”是阅读过程的最重要部分,是区分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标准。在阅读之前,读者会形成对文本的期待,但是当读者进入阅读之后,“期待”会不断地被打破,这件事情让读者感到“惊讶”。那么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拿捏这种“惊讶”就会成为一部虚构文学好与坏的关键点。当读者发现自己的期待距离文本过于遥远,从而导致读者无法顺利阅读时,读者就有可能远离文学。
村上春树的小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他对“惊讶”的拿捏。村上春树在写作中不断打破他人对自己的定义,不将自己局限于超然世外的写作风格中,而是通过确定的指向,表达自己作为小说家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他还在创作中延续了自己一贯的风格,作品中那些无法阐释的情节与符号不会随着读者的期待在村上春树的自我阐释中清晰明了,但是丰富的艺术形式与流畅、有趣的阅读体验则通过这些功能性的荒诞情节与符号展现出来。另外,村上春树又在文本的“间隙”,亦即一种不确定性的多元的阐释中进一步充实了小说的内涵。
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表示:“我们现在需要的绝不是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1]我们要做的是还原它本身。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让作品回归它本来的面貌,并向着自己创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以现实与虚构的书写回应了这个世界向一位作家提出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