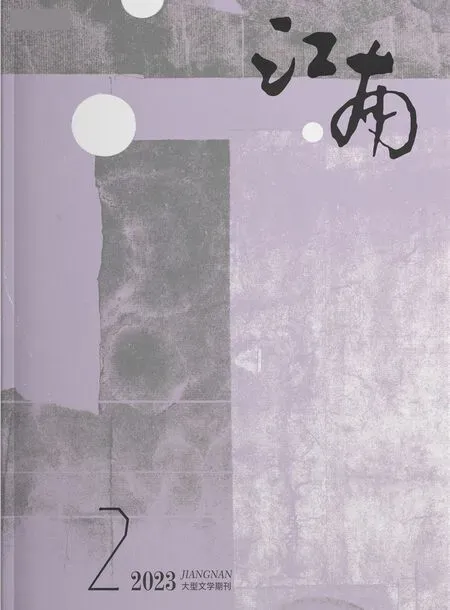炸 两
□周洁茹
有人给简做了个题:你去到一个森林里,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她说兔子。然后你再往前走了一段,又看到一个动物,你觉得是什么?简说是老虎。
你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你自己。出题的人说,第二个动物是你老公。
你就不像是只兔子嘛。文惠说,我看你倒像只老虎。
简笑笑。
吃什么?文惠说,炸两好不好?
我都行,简说。
实际上简和文惠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也许有过一次,家长们在校门口碰到,临时约了喝茶。简不想参加,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文惠邀请她,简就去了。
简和文惠是在一年级新生的第一次学校旅行认识的,去迪士尼乐园旁边的一个湖,而不是去迪士尼。简在心里面想这就是本地学校的操作吧。
在学校选择方面,简一直都有点茫然。简清晰地记得,刚到香港的那一天,坐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简发了半天的呆。也不是说房子有多大,而是由于新到,窗帘都没有,就显得房子特别的空,后来放了一张皇后床,又都满了,转身都困难。简清晰地记得,先生下班回家,用两根棍子,把一张床单挂在了窗口当窗帘,还挂歪了。
第二天一早,简坐在房子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电脑放在膝盖上,从网上找离得最近的十间幼稚园,一个一个地打电话。
第一个打的当然是楼下的国际幼稚园,既然是新入伙,学校也一定是新校。电话打过去,对方讲全满了,放你们在等待名单里吧。简说我们不会讲广东话,如果你们不收,我们就得去讲广东话的本地幼稚园,小孩会有适应的问题。实际上简讲的是简自己的问题,简不会讲广东话,简有适应的问题。对方坚定地说,你们在等待名单里。简又问了一句,请问第几位?第17位,对方礼貌地答复。
简后来问比自己早到香港三个月的芬妮,英文学校不酌情考虑英文学生,那么他们开设国际学校的意义又是什么?
芬妮讲你带你女儿去过迪士尼吧?
简点头。
芬妮讲香港迪士尼的演出广东话唱的你听得懂吧?
简说不懂。
芬妮讲,所以是香港迪士尼嘛,你去东京迪士尼,全日语,你更不懂。
只好看字幕。简说,但在东京看字幕也正常,在香港也要看字幕,感觉不太好。
那你学啊。芬妮说,赶紧学,天天看TVB,三天就七七八八了,至少买个菜没问题。
简三个月都没听懂。
简又给两间本地幼稚园打了电话,对方一听到她的声音就说full佐(全满了)。
简打第五个电话的时候突然就讲了英文,对方很得体地说,我们还有一个空位,您明天就可以来看看。
那是一间本地国际幼稚园,也就是说,又本地又国际,国际和本地分开两个班,国际班英文老师,本地班广东话老师,国际班比本地班更贵一些,但两班时间一样,十点上学十二点半放学,没有午饭,如果要吃午饭,得再加钱。
简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过了许多年路过那间幼稚园的时候女儿还跟简讲,老师叫她坐了三次思考椅。简的心都碎了。
简相信再过多少年女儿都不会忘记那把椅子。
简也没有忘记那把椅子。
第二个学期,简找到了另一间幼稚园下午班的空位,开始了一条颇具特色的上学路,上午就在本地国际幼稚园,中午接了赶紧换校服,塞几口午饭,送到另一间幼稚园上下午的课。
简在两间幼稚园都遇到颇具特色的家长,上午校有个小孩老打其他小孩,终于有一天打了简的女儿,简思来想去,要不要找那位家长谈一谈。那位家长倒主动找简了,在校门口拦住简,说,我家孩子就是凶,她在家也凶,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一个事实,我们全家和学校也都接受了这个事实。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下午校地铁站出来还要走一段,大概十五分钟的步行路程,碰到另一位家长,一起走了两天,第三天,那位家长一见到简,就简单跟简说,我返工迟啦!再见!一路小跑,跑了。简一句话也没来得及问,只能把那个小孩也一起带到了幼稚园,不带就是不负责任,带了又负不起这个责任。那一阵子,简每天都过得像拍戏。
后来上小学,就上了一个本地小学,既然幼稚园没上到国际学校,就接受政府派位系统,一路上本地学校。
简和文惠就是在小学认识的,一年级新生的第一次学校旅行,去迪士尼乐园旁边的一个湖。一个湖,确实没什么好看的。简一个人晃来晃去,太阳很旺,家长都聚集到一个凉亭,简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一个空位,正要坐下,一个家长看了她一眼,把包放到那个位,说,有人了。简走出凉亭,太阳越来越旺。
文惠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简后来想想,文惠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陪着她走了一圈,大太阳底下。后来文惠邀她一起喝茶,简也就去了。一桌家长讲学校的事,讲小孩的事,简想先走,又不好意思,挨到文惠叫结账,简给文惠钱,文惠说她请,简执意要给,文惠说下次,下次你来请。
这下一次就到了十年以后。文惠突然约简喝茶。
点什么?文惠说,炸两好不好?
我都行,简说。
文惠点了单,问简,这些年你还好吧?
简说还好。
女儿呢?
简说到中学终于换到一个还算适应的国际学校。叹了口气。
那就好,文惠说。
你呢?简问,老大已经大学了吧?
大学毕业了。文惠说,可是也不出去工作,天天待在家里。也叹了口气。
简看了一眼文惠,苍老了,许多皱纹,都是十年前没有的。
孩子都大了。文惠说,所以我出来做事了。
保险理财?
文惠点头。
简想过问一句文惠,当年辞了银行工作,照顾家庭,有没有后悔过?但也估到文惠一定是讲,不后悔,只有感恩,能够陪伴孩子成长。
所以简也没问,只是一句“感觉这些年你都没顾得上照顾你自己”,文惠的眼泪还是突然地涌了出来。
简有点后悔说这句话。
文惠埋头在包里找来找去,找不着一张纸巾,手抖得厉害。
简递了一张纸巾过去,再也不说一个字。
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心地说,我也是啊,这些年,我也没了我自己。
文惠抬了眼看简,眼睛擦得通红。
我就是吴太。简笑了一声,说,我只在你这儿是简,我在别的地方都是吴太,吴太要买餸,吴太要煮饭,吴太要照顾小孩,除了吴太的爸妈,吴太自己都记不起来自己是简。
文惠说不出来话。
我们也曾经是我们爸妈的小公举啊。简又说。
文惠终于笑了出来,眼仍是通红,又擦了擦眼睛。
炸两上了桌,简看了那碟炸两一眼,心想,肠粉包牛肉,叫做牛肉肠,肠粉包叉烧,叫做叉烧肠,肠粉包油条,却被叫做炸两,如果只包半条,又叫做炸一?都是想弄明白也是弄不明白的。
这个时候文惠的电话响了,文惠说我接个电话啊。
简点头。听到文惠说,你打开邮箱看一下啊。
看了。对方说,没有。
你拉到最下面,最下面肯定有电话的。
肯定没有,对方说。
我来找,然后发给你。文惠说。
电话那边没有声音。可能在等文惠找。
我现在在外边,信号有点问题。文惠又说,你能不能自己上一下网,查一查?
查了。对方说,就是没有。
简都要替文惠叹气。
到底是没找到。文惠放下了电话,说,我助理。
好像有点不灵活啊,简说。
慢慢教吧,文惠说。凡事都慢慢来。
你还是这么有耐心,简说。
以前可没这么耐心。文惠说,尤其忙家教会的时候,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人。
我只记得你号召力特别强。简说,说广东话、不说广东话的,你都能把大家凝聚了。
文惠笑笑,你还纠结广东话啊。
还是不会讲,都十多年了,我都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学不会了。简说,但现在没以前那么糟糕了,那时候还真有点步步惊心。
不至于,不至于,文惠说。
还有家长因为学校收了跨境双非学生而将孩子转学的。简说,还到网上去说,绝不跟说普通话的做同学。
我也记得那事。文惠说,现在也没人提双非了,都好多年前了。
我那时也去网上回帖了。简说,我就说了一句所有孩童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更招了一堆人上来骂。
文惠笑着摇头,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你当年没搞明白,现在也不用搞明白了。
简说对,搞也搞不明白。
突然就想起了芬妮的女儿,倒是一到香港就入到了国际学校,中学就去了英国寄宿。
你怎么舍得的?简问芬妮。
不舍得啊。芬妮说,但你算算,香港的国际学校一年光学费就30万,教学质量又实在不怎么地,就是个国外普通公立的水平,不如直接去国外上,一年也不过30万,全部生活费学费都在里面了。
不舍得孩子就得舍得钱,没钱舍了就得舍孩子,她又说。
简总觉得芬妮的逻辑不是很通,又说不出来哪里不通,只能笑笑。
可是简跟芬妮也是许久不见了,有一两年了吧。前天突然收到芬妮的微信,没头没脑一句,孩子在英国情况不太好。简马上秒回了,出什么事了?
面临选科,又回不来,只知道在电话那边哭,芬妮说。
那你赶紧过去啊,简说。
我也过不去啊现在。芬妮说,暑假到现在已经流浪了好几个寄宿家庭了。
孩子一定会扛过去的,简只好说。
可是我扛不下去了。芬妮说,我都抑郁了。
出来喝个茶好了。简说,见见人,心情也好一点。
我不出门,我不见人。芬妮说,我都一年没见过人了。
简在心里面咯噔了一下。我们通个电话吧?
芬妮没回。
简又发过去一条,你看医生了吗?
没,芬妮说。
那你不要觉得自己抑郁症。简说,我认得一个人,确诊抑郁症,天天吃药,后来离婚了,倒好了,不用吃药了。
简自己笑了一笑。
芬妮不笑,她要是离了婚,靠什么生活?
简顿了一顿,说,虽然没工作没收入,但是自己开心啊。简自己都觉得这一句弱,太弱了。
没工作没收入怎么活?她住在哪里?她有公屋住吗?芬妮连着打过来三个问句。
孩子都大了,入了大学了,她撑过这几年就行了。只好这么说,比上一句还弱。
可能政府会有些补助吧,芬妮说。
会有的吧。简说,可是就算物质安稳,精神不安稳,也算不得好好活着。
芬妮又没回。
我还认得一个。简说,离是没离,自己搬去了一个小出租屋,天天喝小酒,那个开心……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开心的。芬妮说,我整天都很焦虑,也很恐慌,不知未来会怎样。
而且我不想离婚,又说。
不是叫你离婚。简有点急了,是想叫你出门,喝点东西,开心一点。
我不想出门,芬妮说。
简叹了口气。
你女儿又转了个学校?芬妮说,我看到你朋友圈晒了她的学业奖。
你还看朋友圈?
看啊。芬妮说,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看朋友圈了。
孩子们都比我们上进。简说,我就躺平了,不奋斗了。
我现在也是一躺一天。芬妮说,觉得自己一天天不知道该干啥。
该出来见人,简说。
芬妮再次不回。
可能是还没到饿饭的境地吧。过了好一会儿,芬妮才说,要是真穷得一分钱都没有了,要饿肚子了,我就出来工作了。
我都到饿饭的境地了。简说,你出来见见我现在有多胖吧,不饿点饭都有点说不过去了。
芬妮打过来一个笑脸。又说,我不想出门。
简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特别无能为力。
我现在非常瘦。芬妮说,你就算见了我也不会认得了。我每天只吃一点东西。
我现在过来找你。简说,你马上给我出门。
千万不要。芬妮说,你就算过来我也不会见你的,而且我也搬家了。
什么时候的事?
有一两年了吧,芬妮说。
你若是突然胖了也不好,吃太多和不太吃,太胖和太瘦,都不正常。又说,你是不是不觉得我抑郁了但还挺有条理的?
简犹豫,到底抑郁还是不抑郁?简确实有点分辨不出来。
你先生的收入能够保证全家的生活吗?芬妮突然问。芬妮之前从未问过的。
还行吧。简说,你也知道的,国际学校一年30万,你当年没跟我讲的是,一季校服5000,学校旅个行1万。
芬妮也许笑了一声,我家现在过得很省的,所以搬家了。
学费的压力?
大学更有压力,芬妮说。
再坚持一下,简只好说。
还要供房。芬妮又说,我的一个朋友,这两年情况不好,她家用房抵押贷款出来,支持一家生活。
突然想起那谁了。简说,把小孩带到香港,又带回深圳了,都是一夜之间,都没跟大家说再见。
虽然人回深圳了。芬妮说,但房一直在香港,租出去了,不用卖。
有钱人。
也不能这么说。芬妮说,孩子在香港出生,回深圳就上不了本地学校,只能去上香港学制的私立学校,也挺贵的。
有钱就有许多选择。简说,没钱连选择权利都没有。
钱不多更难选择。芬妮说,没钱倒有没钱的活法,低收入就住公屋,孩子上政府派位的公立学校,照样过得好。我们这种,说有钱吧,一查家庭收入还真是高收入,政府不会管的。
实际生活质量不如住公屋上公立学校的,简想说。
其实我也不觉得英国的学校能够学到啥。芬妮说,花这个钱。
至少花孩子身上了,简说。
你还能找到工作吗?芬妮说,孩子大了不用你照顾了以后。
不能。简说,离开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坑就被占了,这个世界也好现实的。
两个人都有点笑不出来。
我也找不到一个方向。芬妮说,前半辈子做全职太太,尽心尽力带孩子,孩子大了离开了,后半辈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就是个自我感觉吧,完全可以干点自己想干的嘛,终于自由了不是?简说,我以前认得的一个女的,婚前父母养,婚后老公养,就没上过一天班,那个傲娇啊,声称自己就是个作家,也不知道写了些啥。
芬妮肯定笑了。
有的人,别人看她就是个妈,她当自己是个家。简说,我就只在乎自己在当妈方面的价值,在当妈的业余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兴趣点。所以你现在快找找兴趣点,你要去当作家我也支持你。
芬妮打过来三个笑脸。
也许有点信仰也好,很多人过得都不好,有了信仰就心安了,有了寄托,芬妮说。
也对,简说。
你跟我讲话是不是没觉得我有多抑郁?芬妮说。
不太抑郁。简说,但是生活状态确实太差了。
我倒有点担心你。芬妮说,再胖下去,你真要去看看医生,自己控制一下。
轮到简笑了一声,那你是省钱还是真的不想吃?
真的不想吃。芬妮说,而且也要省钱。
人活着也不是只为了吃饭,总要有点希望。简说,我也没啥价值,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但我们对家庭对孩子有价值吧?而且我可指望着孩子回报我呢,我就当是一个希望。
我不指望。芬妮说,孩子能顾自己就不错了,他们以后的路一定也很艰难。
不要去想孩子们以后的路。简说,我们把我们现在要走的路走好了就行。
我找不到出路。芬妮说,看到好多四五十岁在茶楼酒楼打工的女的,还有那些七老八十还在开的士的,只有我,高不成,低不就,无路可走。
不同人走不同路。简说,找不到就继续找,总会找到的,有一天。
找到了告诉你啊,芬妮说。发来一个加油的胳膊。
我找到了也告诉你,简说。如果有个拉钩的表情,简一定也会发过去。
文惠又接了一个电话,一边接电话,一边从包包里拿出一台小iPad,在上面划来划去。
简想跟文惠讲全家的保险都买过了,又开不了这个口,只好吞了一口炸两,不说什么了。
趁着文惠打电话,简叫了买单。
文惠放下电话和iPad,跟简争买单,直到简连说了三遍十年前说好的,我请。文惠只好罢了手,说多谢。直到最后挥手告别,文惠也没有提一句保险。
回去的港铁上简给文惠发了一条短信:如果你去到一处悬崖,要过一座桥,你看到的桥是什么样子的?A:破烂的危桥。B:坚固的石桥。
文惠回过来一个B,然后问,这表示了什么意思吗?
简又发去一条:你过了桥,看到了一个湖,你眼里的这个湖,A:又大又深。B:大但水浅。C:小但水深。D:又小又浅。
文惠回过来一个A。
可以揭晓答案了吗?
桥代表了你的事业和前途。简说,危桥说明你很焦虑,对未来迷茫,当下无法准确定位以后发展的方向;坚固的石桥说明你有坚定的内心,你也会有光明的前途,会心想事成。
听你这么说,我还有点高兴。文惠说,但是前途什么的也不是一道题就能测算出来的吧。
就当是个心理暗示吧。简说,湖的大小深浅代表了你交朋友的情况,又大又深的湖当然说明人缘好、朋友多,而且和朋友们的感情相当不错。
你选的什么?文惠问。
我选的C,湖小但水深,也就是朋友虽然少,但都对我很好,感情很深的意思。
那也祝贺你吧。文惠回了一条,感情深的朋友,一个两个也就够了。
简笑了笑,关闭对话,看了一条订阅的天文公众号,简对天文学一直有点兴趣。
“脱离速度,是指一个没有动力的物体,脱离一个天体表面,不再掉下来的最低速度。以地球为例,不考虑地球大气的情况下,一个物体要离开地球的脱离速度为每秒11.2公里,只要一个物体的速度超过每秒11.2公里,就会永远离开地球,如果小于脱离速度,就会再度落回地球。黑洞的脱离速度超过每秒30万公里,比光速还快,也就是说,一旦有星体掉入黑洞,就永远不能出来,因为连光都无法脱离。所以黑洞长大的方式,并不是主动掠夺其他星体,让它们直接掉入,而是星体们自己先在黑洞外围形成吸积盘,再慢慢从吸积盘掉进黑洞。”
看完这条,简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文惠发了一条,“前些年放弃了工作成为全职太太,有人问过我有没有后悔。我想了想,不后悔,因为陪伴了孩子们的成长,更珍贵。今天与一位旧友久别重逢,特别感念,原来说过的一些话,发生过的一些事,很小很小的事,都会有朋友一直地记得。多谢啊,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每一个人。”配图是那碟炸两,看起来还挺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