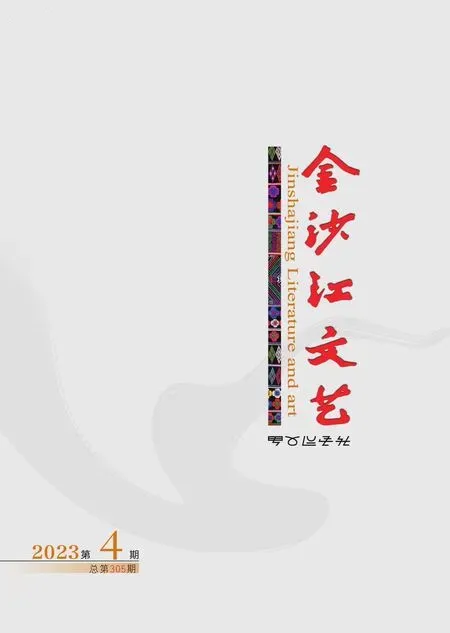吃食二题
◎潘新日(河南)
黄 豆
黄豆,是人的老亲戚,一生都在讲述陈年旧事,它对人的热爱,胜过了白花花的米,亲热劲足可化掉一个冰冷的村庄。
早春的黄豆地是头年特意预留的,带着庄户人家满满的期望。老人盘算收成,家里的土地都要早早经过谋划的。这些地,心,是敞亮的,流淌着漫长的期望。一入秋,就静静等待来年的黄豆落地,发芽、生根。
每年,黄豆的播种,有明星出场的味道。
父亲耙地,土都要耙得像筛子筛过一样才肯停下。他总要为大豆铺一床平展的大被子,让它们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之后,攒足了劲冲破泥土,举着自己茁壮的芽,在风里招摇。
黄豆从土里钻出来开始是顶着苞衣的,乍一看,好像是刚刚降落的伞兵。不几天,豆芽就会胀破苞衣,打开它们八字的绿瓣,仰着脸接纳四面八方的阳光。自此,一棵棵豆苗就成为田里的春庄稼,成了庄户人家的牵挂。
草,是黄豆的邻居,它一出场就和黄豆争吃的。土地的养分是均摊的,本来,它们相伴而生,是一种缘分。可是,偏偏不,野草偏生了贪念,嘴巴张得大大的,每棵草之间合起来,养分就跑到草那边了。草的茁壮,让黄豆的心慌了。
这时候,大人们开始锄地,他们的锄头,就是杀死野草的刀。我一直认为,刨地是个技术活,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才可以出手。而我们,完全是刚出道的生瓜蛋子,和大人一起刨地,仅仅是陪他们练手。站在田垄间,一不小心,草,没锄到,黄豆苗就成了野草的替死鬼。我不喜欢干这样的农活,一方面我不愿看到黄豆苗冤死,另一方面我也有懒心。可一看到父母都是那么专心于农事,我也只好举手投降,慢慢地学着做了。
春上,锄地是经常性的农活。娘爱说,千万不要等地荒了,让草吃了地里的黄豆。陪大人下地,我老是觉得自己的锄头不听使唤,锄草时显得钝愚,本来使着不是很顺手的锄头,碰到禾苗却变得无限锋利。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小心翼翼,越是会“滥杀无辜”,死去的豆苗牵着母亲的视线,一次次让她揪心。我无数次地惊恐于一棵小小的豆苗倒下的瞬间,甚至可以听到它们死去的声音,内心里,饱受着破坏庄稼的煎熬和恐惧,这种恐惧直到多年以后,还在我的心里落下阴影。
我不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把式,这点,我有自知之明。
住满庄稼的乡村里,黄豆因为不是主粮,势力范围极小。时常,它被麦子们挤到边角沟坎,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后来才知道,大人们这样做,不是它贱,是因为它泼皮。黄豆不择土地,一落地就可以生根发芽。
往往,一场春雨,黄豆就接上了地气,便能滋滋地生长。
上学的路上,可见大片大片的庄稼地,除了麦子就是它们。黄豆剑走偏锋,游侠一样被挤得远远地。它们就占领所有的边边角角,默默生长,一身的毛,像个小老头。不过大人们爱说,黄豆心齐,二十天就可以得势,这个时候,黄豆所抵达的地方,都是它们的天下。
一块田里,黄豆开出的花却是不同的。弯下腰细看,有紫色的、有白色的、有红色。一朵朵的小碎花仰着脸笑着,仿佛没有任何烦恼。
这些花,最是人们容易忽视的,好多人,在乡下生活,问起黄豆开花的事,竟然一脸的迷茫,那些花好端端的,被岁月一笔带过,成为生活的留白。
少年时,见到县城里的老画家画过黄豆花,那个老画家后来在上海办画展,还获了奖。出于好奇,我才留心仔细地观察它们,这花,便从我的眼睛,走进我的心里,开满了我心里的整个世界,还带着芳香。
我父亲曾经领着我,指着正在开花的黄豆苗说,多好看啊!别急,花蒂的后面就是豆角了。这话,我听着有些诗人的意味,这不像一个农民的语言,倒洋溢着朦胧的诗意。我仰脸看着父亲,他竟没有丝毫的得意,依然还是灰头土脸的朴素样子。
我们都习惯于把瘪着的青豆角称作假角或画角,究其原因还是它肚子里没有东西,瘪着,像画上的,才被称作是假的吧!而大人们不那样认为,他们总是抱着希望,和瘪豆角一起孕育着饱满的豆粒。
有时候,期待也是一种幸福。
上仁的过程就是青豆角孕育的过程,就像人类的十月怀胎,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豆角的肚皮慢慢地鼓起来,这个过程充满了期待。
生吃,有股腥味。拔一抱放在院子里,一颗颗摘掉,剥开,用油一炒,就是乡下人下饭的佳肴。那阵子,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是青豆当家,条件好的,带点肉末啥的,吃起来格外的香。
不过,我们上学回家的路上也会偷吃,直接用火烧出来,虽然是缺油少盐,却保留了最原始的青豆味,舌尖上的反应很多时候和童趣结合起来,就充满了野味和回忆,黑乎乎的嘴唇上除了青豆的回甘,更多的,是洁白的牙齿漾出的微笑。
老师也偷吃,是吃我们烧好的。大老远看见老师走过来,害怕挨批,慌忙把火灭掉,拔腿就跑,等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回头看看老师,他们一个个正坐在田埂上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我敢说,他们一定会幸灾乐祸,吧嗒着嘴,嘲笑我们这群胆小鬼为他们准备了这么好吃的零食。他们不知道,靠威力抢走我们的盛宴,我们的心里有多难受,更不知道,我们都在内心里鄙视他们。那种恨,灭亡了他们的笑声。
黄豆由青变黄是它最短暂的成熟过程,仿佛一瞬间就完成了。大清早的,村口的王瘸子翻着他的小眼睛,趴在黄豆秧上看了几眼,就大惊小怪地说道,天啦!黄豆这么快就熟了。还有这叶子,说黄就黄了。我父亲就笑,笑他的近视眼还能看清黄了的叶子,笑他木橛子一样楔在黄豆地里,从不明白那些浩荡的大词正在列阵,等待人们的检阅。
由春播到夏收,每一个过程都是流畅的。而此时,那一粒粒坚硬的豆仁,长成这个季节饱满的顿号,用以标注丰收的来临。它披着坚硬的铠甲,驻足在季节的转弯处,等待午后的炸响,该是多么开心的事。
砍黄豆不是好活,需要一个人拿出最大的虔诚,腰要弯得老低,不停地为它们叩首。黄豆比麦子和稻子坚挺,粗壮,砍起来废镰刀。一把镰刀,被父亲磨得透亮,为的是砍起来省力,手起刀落的瞬间,满足就躺在地上。
我们小孩力气小,镰刀就在黄豆面前屈服。一会儿卷了口,一会儿钝下来,需要不停地磨。那一刻,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磨洋工,偷懒,有时候不是刻意的,而是不经意间发现的。带着理由的偷懒,很多时候会得到大人恩准和原谅。
豆角扎手,砍起来时不时地疼一下,那细小的疼痛,顺着指尖一下子跑到大脑里,带着表情,带着欢乐。
收黄豆最怕的是到了中午,太阳火辣辣的,像要把大地点着。汗水冒出来,掉在地上,立即被干渴的土地抢走,不留一丝痕迹。我们有一刀,没一刀地砍着,砍了父亲一肚子的火。他挥挥手,我们便迅速地逃了回去。
路,是连着黄豆田和村子的一条线,我们就是那条线上会跑的词语。大人喊吃饭的声音,就是这条路,伸着胳膊递过去的。
大豆躺下来,它在田地里的一生就完了。豫中平原开始空旷,堆在地里的是秸秆,收回家的是粮食。几个月的辛劳和期盼,此刻,都变成了金灿灿的欢喜。
大人们爱说,黄豆属于小粮食,有小家子气,被乡下人当作副食。
小粮食是农家的生活补白。在众多的粮食里,黄豆最多是配角的角色,但就是这样的配角,让人们的生活丰富起来,有了滋味。
早上,卖豆芽的和买豆腐的人,会准时挑着挑子在村口叫卖。家家户户的人,一个个端着盛满黄豆的葫芦瓢或瓦盆,睡眼惺忪打着哈欠,踩着豆腐匠和豆芽匠的眼神,用黄豆换回全家人爱吃的鲜豆芽和嫩白的豆腐。
乡下人买东西不用钱,都是用粮食换。那些利用农闲做些小生意的农人,就用黄豆、绿豆、芝麻换些零花钱。以物换物的生意是传统的,沿袭了祖先的规矩。收进来的时候,称总是压得低低的,售出去的东西,称总是翘得高高的。这个时候,黄豆便充当了友谊使者,让乡亲之间的情谊一下子看得清清楚楚。称,这时候称的不是重量,它掂量的是友情和厚道。
漫漫岁月里,黄豆见证了辛劳和友情。无时无刻,它都在用生命的全部喂饱为它付出的人。然而,这世界,需要它的人太多了,呵护过它的,没有呵护过它的,都一股脑的拥有了它。早上,直接磨碎的豆浆和油条搭配,成就了每天的开始;每个家里,豆芽的滋生让黄豆花开一度,或炒或蒸,给人以最原始的本味;华丽转身的各种豆腐,花样更迭,充盈着每个人的味蕾;还有豆腐脑,还有豆油、豆酱、豆粉,黄豆在哪,哪里就有旺盛的生命……
也是,黄豆的变身为的是给人以命。命,是让人活着,它让人尝到了做人的滋味。它养人,人养它,一粒粒黄豆,一颗颗饱满的心,相互转换,轮回间,喂养了这个世界……
米
米,是脱光衣服的稻,养活了天下人。
米是好东西。我父亲时常端着碗感叹。他这辈子经历的饥饿太多了,看见米,就看见了亲人。
我上学时,家里每星期给我6斤米作为伙食,菜金也在里面。不够吃,我就从家里用罐头瓶带咸萝卜干和炒熟的萝卜叶子下饭。
学校的食堂一并排放着十几个装满大米饭的大木桶,米粒一个个晶莹剔透,远远就可以闻到米香,这种诱人的香味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中学时代。真的很羡慕那些和打饭师傅有亲戚关系的同学,只要他们的手少抖一下,就会多盛好多米。饿,带着响声,把体内掏成空壳。吃饱,是年少时最大的奢望。
河水浇灌的水稻总是那么的饱满,金黄,米质上乘,入口香甜,带着人情味。村子里,大人吃饭,哪家小孩的碗空着,两个筷子一拨,就可以让小孩吃饱。外乡人讨饭,大人用手在缸底一抓,一把白花花的米就递了过去。都困难,相互接济一下是最陌生的爱。
天底下有多少米,地上就有多少人。
米,是人间的仙丹。人类有了米,就有了骨气和辉煌。古人不为三斗米折腰,今人更为五斗米狂生。人,吃的是米,挺出来的是傲骨,每个民族都被米护佑,每个民族都被米养成不屈。米的性格很软,但它能用养分搭建起人的骨骼。
超市里摆着的白花花的大米产自各地,有集体亮相的味道。每次从它身边经过,都会忍不住上手摸摸,粮食的丰满有踏实的感觉,心里的热爱和米一样明亮着。
米的一生是穿越整个夏季的。热,让它们更加丰盈。父亲择稻种,一粒一粒地挑。他把最好的稻子当成来年的种,那里面有他的汗水和饱满的真情。父亲简直就是庄稼的时令,开春的水还是冷的,他就赤脚下到苗床田里,一遍一遍,把稀泥平的像镜子一样光滑。他心疼稻种,给它们安一个最好的窝。
稻芽一直起身子,父亲的腰就弯了下去,他在眼尖着找秧苗里的野草。苗床肥,野草偷吃了养料,长得飞快,如不尽早拔掉,它们就会吃掉秧苗。
我不喜欢插秧,腰都弯断了,还不见功。父亲不,他能坚持下来,秧苗捏在手里,心里已经看到了金灿灿的稻谷。这是信念,也是希望。多年后,我终于明白,父亲直不起腰,是他一直对米保持恭敬的表现,劳损永远保持了劳动的姿势。
稻子在水里养大。水是稻子的同胞姐妹。分蘖、抽穗、扬花,稻子每成长一步,父亲的头发就白一根。我甚至怀疑,父亲的头发可是稻子的根系。父亲老了,那些包着米的稻子也老了,都勾着头,在田埂上打瞌睡。乡下,有稻子生长的地方才是鱼米之乡。米,喂饱了乡村。
凋落的老街有一家刘记米铺,早年很是红火。老板守着一个大埠口,把各地的米运过来,售给居民。他的心不黑,米价低,老百姓都去买。卖米的人,手上掌握着乡亲的性命,自然会用米修德。心一黑,米就变质了。后来听说,刘家成了望族,出了好几个大官不说,他的后代,都移居到海外去了。而那些吃他米的人,还在念叨着他的好。
米,就是良心。
老年人爱在我们面前讲富贵人家施粥的事,我们都当作了旧事,不懈于心。如今,生活好了,没有人会到有钱人家门口讨碗粥喝。有年,旅游到寺庙,偶遇寺庙施粥,想不到等着布施的人竟排起了长龙。人,在关爱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贪婪,这是本性么?
一个人喜欢上米,他就会被米俘虏。米,在人的一日三餐里活着,把人养坏了。糖尿病人被米惯坏了,只能把米当作宠物养在心里了。米,是他们身边的过客。更多的人,和米相伴终身。米,是穿肠的饱嗝,有一股仙气。
父亲的米都含有他的汗味,每一粒都是熟悉的。米,是他一辈子的伙计。他和米共生,米的热量让他精神矍铄,他让米活出了人样。
米,喜欢变着花样养活人。可以熬粥,可以做大米饭,可以做米饼,可以和菜联姻,做出不同口味的食物填饱人心。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米,一走出去,就混了,米面成了南北方主食。米,也会迷路。走不出来的米就变成了酒。它会让人乐,让人哭,让人醉。变成酒的米就是妖怪,让人成为鬼。
我好多次和长辈一起用餐,都会发现他们伸着笨拙的手指捻掉在桌子上米粒吃,受过苦的人,对米格外的珍惜,米,就是他们的命。
市场上的米都经过了美容,抛了光,有卖相,好像没红火几年。吃惯了米的人,开始返璞归真,老糙米又找了回来。
米,有一颗透明心,他和人心连在一起,让这个世界永远不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