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
鱼恋湾,鳖恋滩。他爱深圳。
他说得最多的是这句:“哎呀,主要是公司离不开我啦!”
也确实的是这样。他大学毕业来的深圳,凭着流利的英文和出色的业务能力,很快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随后在深圳买房买车成家,能说不爱吗?
工作之外,他最大的爱好是钓鱼。周末,时间紧就在立新湖或观澜河钓,时间充足就跑梅林水库,或者去盐田。
有钓友约:“老徐,去河源钓鱼不?”
他摇头,一脸的不屑:“是立新湖的鱼儿不够肥,还是深圳湾不够大,劳累你开车两个小时跑河源?”
尽管钓友一再鼓动:“万绿湖是垂钓胜地。找一钓点,高粱小米打好窝,挂上红虫蚯蚓之类的活物,光是提渔获,能把手提到发软。”
他不语。只顾着低头拌他的饵料,弯他的鱼钩,磨他的铅坠。
从此没人约他跑河源了。
他听人说过万绿湖,也上网查过。那湖最开始并不是湖,听说是一个火山岛。在火山停止喷发后,大量的植物残骸和雨水堆积在火山口上,后来岩层变薄,地下水涌出,形成了一汪浩瀚的绿湖。水呢,听说非常清澈。
可人们也常说:水清无鱼。以他的经验,确实如此,有鱼也难钓。况且又不近,往返就要大半日的时间,他不想费事地折腾,去做那所谓的“空军”。
那一年,他负责的涉外订单全线关闭。一夜间,他从公司的骨干成为闲人。老总有意让他去接手川南基层线,他愤然拒绝了。从头做起,他磨不开这脸。
时间充裕后,他钓鱼也不像从前那样满载而归了。无论换海钓还是上矶竿,春钓滩也好,夏钓湾也罢,屡屡都是“空军”。
他变得焦躁起来。妻子的埋怨开始多了。
想去一趟万绿湖,是临时起意。那天特别烦躁,和妻子吵过一场后,他任由导航引领,在一个叫东星的地方停了车。天仿佛与他作对,毫无征兆地下起了雨。他窝在车上,烦躁如同长在荒野的草,更密了。
雨停,他下了车,漫无目的地乱走。在一道垭口,隐约有水流声传来,他沿着清澈的溪水往山上走,听到山中倾泻的激流猛烈撞击潭底发出的浑沉声响。近了,又看到潭边腾起绿浪,飞溅的水珠雾样散在崖畔,笼罩着水蕨、蓝耳草和一些不知名的花草,宛若仙境。
他的心境逐渐好起来。
当发现自己迷路时,他已无法顺着溪流找到来时的路。他在山上打转,每次都来到一片一望无际的水边。让他感到讽刺的是,清澈的湖里,竟然有无数的鱼在游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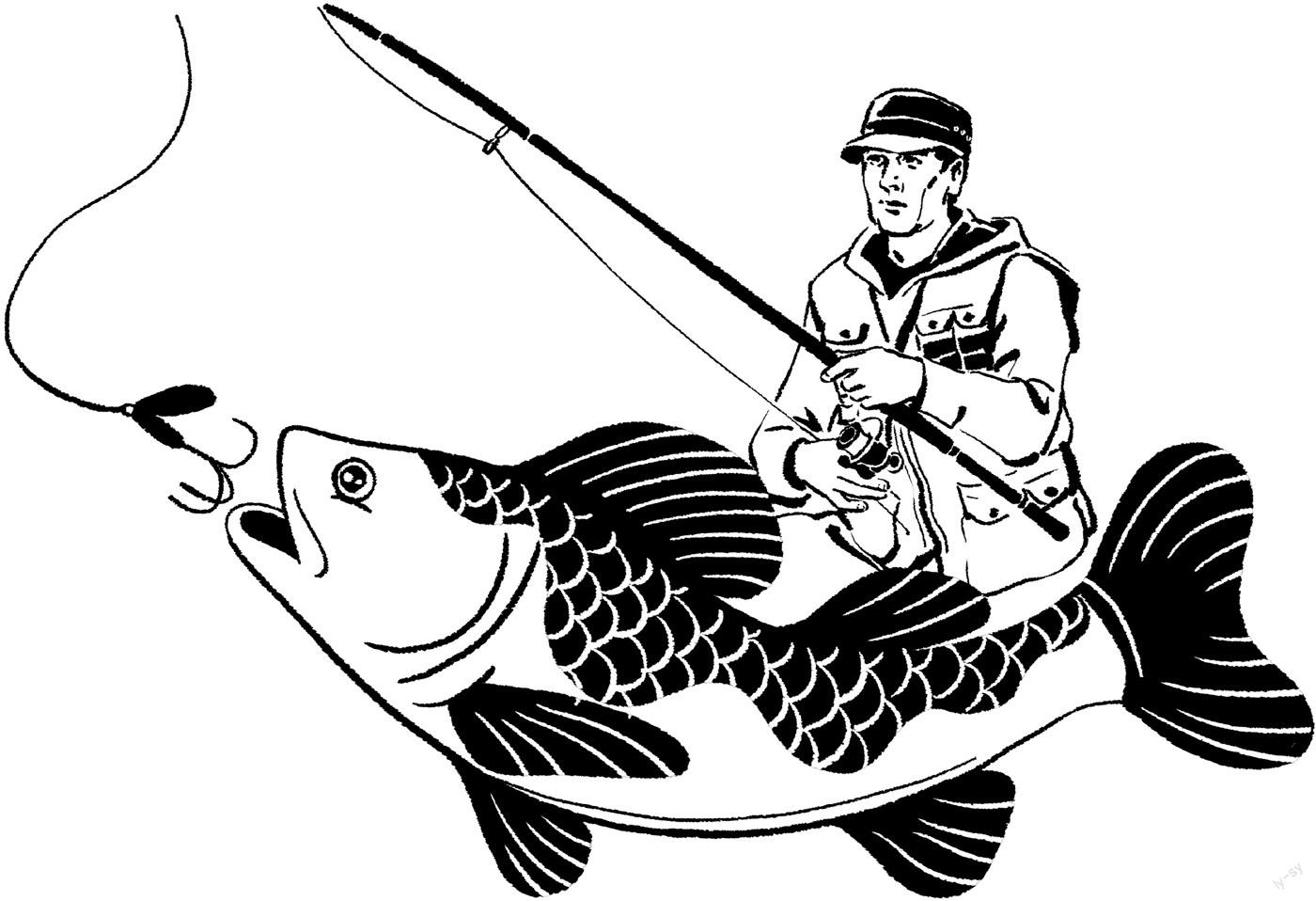
他是沿着那条仅两脚宽的小径往草木更深处走时看到人的——准确来说,也是钓友。钓友,多么熟悉的称谓,尽管是一个陌生的钓友。钓友的渔获似乎不错,鱼篓里隐约有十几尾。它们在水篓中游动,似乎觉察到了他的到来,那只最大的土鲮几次试图往外跃。
见钓友让一条鱼脱了钩,他找了处平地坐下,没话找话:“你刚刚若是‘溜一下就好了。”
钓友转过头冲他笑:“咳,行家啊!”
他有些小得意:“哈,不过是玩了十几年野钓的经验。钓鱼嘛,最怕的就是脱钩,惊扰到了窝子内的鱼,切线断竿不说,钓点也难再上鱼了。”
“可不是嘛,都有好大一会儿没渔获了。”钓友有些沮丧。
“中鱼后不能直接飞竿,得先顶,让鱼线有些拉力,再牵引着拉鱼出窝。这样做,就避免了鱼脱钩闹窝子。”他的话变得稠起来,忘却了自己之前屡屡成为“空军”。
“是啊,是啊,溜鱼的过程跟做人一样,进退有度才能一击即中嘛。说到钓鱼,其实鱼咬上钩那一下才是最过瘾的:掂掂鱼重,猜猜鱼品——鱼没上岸,一切都是未知数。”釣友的话也多了。
他连连点头,突又一怔——鱼没上岸,一切都是未知数,何尝不是这理呢?如果他放低姿态接手川南基层线,会出现如今在公司闲架、在家受妻子白眼、整天无所事事的窘态吗?他想起前几天老总找他谈话时说的:“说不定川南会成就你的另一番天地呢。”
钓友已经收好竿,连连向他招呼:“走,上我家吃饭!我家的竹寮就在附近,中午做了煮鱼,清水湖的鱼,味道很是鲜美的。”
他脑子里闪过多个画面,开始期待起来。
[责任编辑 王彦艳]
徐建英,1980年出生于湖北通山,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小说集《守候一株鸢尾》,《大地的声音》获《小小说选刊》2021年度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