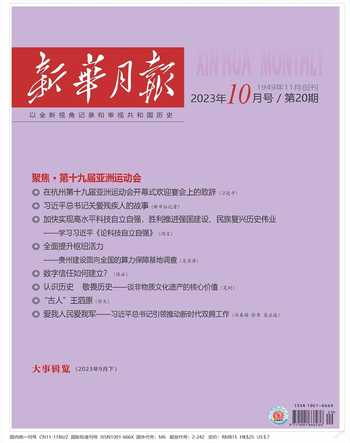节衣缩食为藏书
吕坚
一
1986年夏天,在父亲吕振羽去世六年后,母亲江明作出了一个对全家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即把家中近三万册珍贵藏书及北京城中心四合院住所全部赠与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吉林大学。这充分体现了母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也圆满实现了父亲的生前意愿。这得到全体家人的赞同。吉林大学校领导十分重视,决定在北京老校长故居建立吕振羽纪念室;在吉大图书馆设立了“吕振羽江明藏书纪念室”,专门保管这些图书古籍。30余年来,吉大吕振羽江明藏书纪念室接待了不少国内外的来访学者、各级领导,在学校教学工作中发挥了有益作用。如今《吕振羽江明藏书书目》经过吉大图书馆老师们悉心整理,即将出版发行。我闻讯十分高兴,这些书目出版既可供社会广泛利用父母亲珍藏的古籍图书,也会很好地适应今后学术界人士的各方面需求。
父亲从青少年起即酷爱读书,嗜书成癖。1926年9月自湖南大学工科毕业后即投身北伐,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戎马倥偬之余,他都要挤出时间读书、研究和写作。他从1928年7月来到北平,先从事编辑著述,1929年后先后到朝阳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开始了繁忙的著述、教学活动。在北平期间他搜集了大量的图书资料,相继有《障碍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等一系列有政治、学术影响的论文发表,同时还有《中国外交问题》《中日问题批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专著陆续出版。在古代史研究领域他首创“殷商奴隶说”“西周封建说”。
这一段在北平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是他一生学术成果不斷涌现的黄金时期。听母亲说,当时为了研究学术问题,父亲常常带着几个烧饼,终日呆在北平图书馆看书、抄卡片。在北平中国大学担任教授期间,他曾住在西单牌楼西南“东太平街一号”中的一个小院。院中有几间北房为卧室,靠南有一小土山,山上有两间小房子作为书房兼会客室,即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自序》中称的“风雨频袭之一小楼”。他在此会见友人、学生和进行著述研究(《长留雅咏足三湘·荣孟源〈我的老师吕振羽〉》)。
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父亲得悉名列敌伪缉捕名单,不得不化装离家脱险,九年来辛苦搜集的大批图书资料、笔记、卡片连同《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手稿都遭损毁遗失。1937年9月,他奉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长沙,创办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938年9月,他提议并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在家乡武冈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由于讲学院革命影响日渐扩大,后来被国民党派兵查封,所撰讲稿及图书资料等尽被国民党以“赤匪”名义搜出禁毁(所幸族人从废纸堆中捡出少许图书资料,包括《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手稿三册、《少年烬余录》等得以保存下来)。1939年9月,他奉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调令来到重庆从事统战、宣传工作,曾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1941年4月“皖南事变”后奉周恩来指示,经香港、上海赴苏北新四军军部,在中共华中局党校任教。1942年3月,他奉毛泽东电召,随刘少奇从苏北出发,长途行军,历时九个月到达延安。曾任刘少奇政治秘书。1943年1月到延安后,他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他的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在延安新华书店再版发行,该书出版得到了毛泽东的关心。1942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出版工作时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394页)。1945年“八一五”后他主动向党组织要求奔赴东北解放战争前线,先后亲历冀热辽剿匪反霸、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参加“三人小组”谈判(为冀热辽解放区争取了大批救济物资)、辽东省城市管理与农村土改。从1937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他虽然有一些论著发表或刊印,但可惜都因战争环境和条件限制,上述文献资料大部分个人都没有保存下来。
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活安定,因著述的需要,父母亲在东北工作时就开始购置和收集少量古籍图书。父亲几次因公出差来京,看到隆福寺等处地摊中杂陈的图书、碑帖经历风吹日晒,十分痛惜,对母亲说:“这是祖国的宝贵遗产,很快就要成粉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收集起来。”1955年7月,父亲因患病(不明原因头疼,彻夜难眠,久治不愈)经高教部批准从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任上来京离职休养。高教部曾安排他住原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旧居,遭到他拒绝,后住在地安门中国科学院干部宿舍。9月他率中国科学院东方学代表团赴民主德国开会,得会议之便赴东德眼科医院会诊,诊断为患脑下垂体肿瘤。之后经组织批准转到苏联莫斯科神经外科医院进一步住院治疗。经过苏联医生长达半年的精心治疗,父亲的脑部肿瘤得到缩小,头痛消失了,视力、视野逐步得到了恢复,1956年6月回到北京。
父亲因脑病治疗需要安静场所,又不愿增加国家负担,经组织同意,父母亲用自己多年积蓄和稿费购买了西城区府右街附近一所四合院(原址为西单石板房甲19号,后改为西黄城根南街50号)。自此有了宽敞的著述、藏书条件和幽静的生活环境。院内南边种有一株老枣树、一株海棠树,北边种有两株梨树,中间有一小花坛。北房五间为父母亲书房及卧室,东房三间用来藏书和会客,西房三间为子女住房及餐室,南房中间一间存放杂志、报刊,东西各一间为公务员、保姆居住。经过回国后进一步治疗,父亲的脑瘤明显缩小,视力得到了恢复,可以进行研究与著述。

那时父亲收入比较高,刚到北京时他的每月工资为380余元,后减为350余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津贴每月100元,母亲每月150多元,两人合计有600余元。此外父亲还有数目不等的稿费收入。但是父母亲自奉节俭,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每月只留100余元用于全家生活费、报刊费及子女亲友学费外,其余500元及稿费全部用来购买藏书,有时还不免赊账。“年关各书店结账,目前还没想出办法偿还。”(《吕振羽全集·十卷·致李野吕修齐信》652页)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公务员包坤记录的当时生活账本,每天的一笔笔开支十分详细,十天一小结,一月一大结。如1957年12月份共花费123.1元,其中包括每天“肉菜、鸡蛋、茶叶费、米面、食用油、牛奶、水电、蜂窝煤”等日常开支。再如1959年7月6日至8月4日共花费90.51元。在账本上还留有父亲“上月结余9.49”字迹。
那时家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奢侈品,只有一台北京牌电视机,应该是1959年买的,那一年北京有了电视台。家中也没有电冰箱。大夫建议我父亲喝酸奶,是采用牛奶煮沸后凉却加菌种自制来喝。“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专案组人员多次来家搜查所谓有问题可疑证据,曾拿走一些高层人士的书信、照片及书。他们都是军人,也没有开具字条。我记得有一位打开了大衣柜,吃惊地对妈妈说:“你们就这么些衣服?”
三
当时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地古旧书店及私人书店是他们休息时常去的地方,有的书商如吴世寅等与父亲成了好朋友。经过多年来的收集,家中藏书已蔚为可观。从甲骨金石、考古、艺术、民俗、社会调查到稗史杂记、笔记、游记、民族史料、党史、地方志、碑帖等均在收集之列(还有各地旧报刊不下数十种)。内容涵盖文、史、哲、经、宗教、自然科学各方面。除马列精平装书1万余册外,线装古籍书近2万册,多元、明、清珍善本。在所藏清康乾刻本1300多册中,以康熙钦定《词谱》、武英殿本《西清古鉴》为代表。其中尤以钤有“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于右任书章”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甫里集》抄本为少见珍本。其他如千册一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九通》《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等均属善本之列。此外北房外东边小房还保存有不少解放区旧报纸,按年月装订。1960年左右这些报纸都捐给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前些年著名元史专家周清澍曾来父亲纪念室参观。他回忆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经历往事:著名文献学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生和他们说过:“吕先生家有藏书三万多册,很了不起。”
由于长期阅读古书,父亲对古籍善本也有一定鉴别能力。如1957年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吉林视察,抽时间去东北人民大学与师生見面。之后又特地去校图书馆参观。凡外出开会,父亲都尽可能去各地图书馆看书,了解藏书及版本状况。1961年7月受乌兰夫同志邀请同中央民委访问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参观时,他特地去内蒙古大学资料室参观。同年10月应邀去湖北出席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与吴玉章、范文澜等同志又赴河南郑州、洛阳访问,参观了河南图书馆。并在日记中对此特别作了记述。
1962年11月他应邀赴长沙出席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尽管日程紧张,临回北京前他还特地抽时间去中山图书馆,“看了一些宋、元、明善本书。旋即馆长室,看邓绎《云山读书记》稿,颇有所得。邓氏学说确有不少进步的东西。邓之著作,似是多在旅行与活动过程中写的。”(《吕振羽全集·十卷·湖南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日记》499页)
为购书,母亲也自学了鉴别版本和碑帖方面知识,不少名刻古籍都是她力主搜集的。侧重版本精良和著述需要是他们购书、藏书的主要原则。为了妥善保存藏书不致霉变虫蛀,需要及时晾晒、放药,这耗费了母亲不少精力。因为她在故宫博物院党委工作,为业务学习需要,有意搜集了一些明清字画,有宋旭、张瑞图、李方膺、郑簠等人(1991年母亲将家中珍藏明清字画12件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古籍藏书,母亲还从北京古旧市场精心购买了三四十个带玻璃的硬木书柜及樟木书箱,如今也捐献给了吉林大学。
凡家中藏书,不论平装、线装,一般在图书封面钤盖“明羽图章”、扉页盖“振羽江明图书”印记。由公务员包坤负责盖书章。很多书籍上都留下了父亲阅读时的批注、跋文,多达几百、几千字不等,也有的整本书都有批注,充分反映出他博览群书、好学不倦的治学精神。如在阅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两书几乎每页都留下他用红或蓝笔的批注、勾划与评语。反映他极为重视并仔细研读郭老、范老的著作与自己学术观点的争鸣。前几年编辑父亲全集时我特意搜集了他在一些书籍上的批注、跋语,内容涉及版本、史料价值、思想倾向、对著者评价等方面(详见《吕振羽全集·九卷·批注、跋语》762至779页)。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已有《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八部学术专著和一百多万字论文发表;1949年后一些旧著不止一次再版,大都经过修订补充,并撰写新作。1955年至1962年来北京后这一段时期,是他学术事业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这也与生活安定,摆脱行政事务,同时收集了大量古籍藏书有很大关系。以1959年版《简明中国通史》为例,在母亲的协助下,修订本与初版本相比,内容增加了20多万字。为便于读者阅读、研究,对引文题解增加的注释就有一千多条。其广征博引大多来自家中藏书。1963年1月,父亲因“历史问题”受到组织审查,但家中全部藏书仍由母亲精心保管,按时施放防虫药或晾晒。有的古籍书店曾上门提出转让一些善本图书,遭到母亲严词拒绝。她还继续购买文史方面图书(主要是平装书),为父亲今后开展研究工作做准备。
四
在“文化大革命”空前浩劫中,尽管母亲一度也蒙冤受屈,但庆幸的是,家中藏书等在母亲和家人尽力保护下并未遭到损坏遗失。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1970年因母亲要下放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为家中藏书事向中央办公厅打过报告。中办决定藏书由中办秘书局保管,存放在中南海。1979年父亲经中央平反后,搬回旧居,全部藏书及生活用品得到归还。听中办秘书局同志说,毛主席曾借过其中线装书看过,在书上画了圈。周总理也借阅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看过(我见到该书中有中办王良恩写的周总理借书的还书条,系用铅笔写的)。估计是总理那时听到毛主席对《十批判书》有评论,特意看一看。
关于日后如何处理家中藏书的安排,父亲先后曾有过如下想法:1962年2月致侄吕显楚信中提到:“我到莫斯科治病时,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同志们曾提出,希望我将来把个人的图书赠送该所……我自己又有这样打算,将来不能使用时,全部送给中央高级党校或送给塘田市第四中学。”(《吕振羽全集·十卷·致吕显楚信》653页)1976年后他曾对我说过:“我买这些书是为了工作与著述的需要,一可省去借书的时间,二也可以减轻图书馆的压力。我如果不在了,这些书就留给妈妈使用。妈妈不在了,就把它们交给国家。”多少年来他一直保持不喝酒、不讲吃的生活习惯,出国诊断得脑瘤后就戒了烟。在我记忆中,父母亲从不下饭馆,唯一的一次,是二姐爱梅结婚时在西单的曲园酒楼请亲友吃了一顿饭。有至深关系的师友如李达先生等来家,至多去附近的砂锅居买两个菜。他一生不喜交游,除了偶尔看看京戏,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研究、著述上。父亲的一生,亲历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在大连大学、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东北人民大学、中央民委、中央党校担任过一些行政、学术工作。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一名学者和读书人。
母亲的经历也大体如此,1937年她在民国学院读书时即加入进步组织,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在大连沙河口区委、长春市委党校、中央文化部、故宫博物院工作。她担任党务工作之余,倾力支持父亲的藏书嗜好。总之,从爱书、读书到藏书是父、母亲数十年来的共同追求和爱好。《吕振羽江明藏书书目》的出版,正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真实写照。2010年以后,有十余位学者参加,共同编辑《吕振羽全集》,历时四年。为保证出版质量,全集编委会规定凡出版过的图书古籍引文,应进行史料校核。据我所知,全集中大多数古籍引文都是根据北京吕振羽纪念室的藏书校核的。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同志说过,“吕振羽走进书斋是学问家,走出书斋是革命家”。
父亲的一生,是学者与革命者的一生。
(摘自4月19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