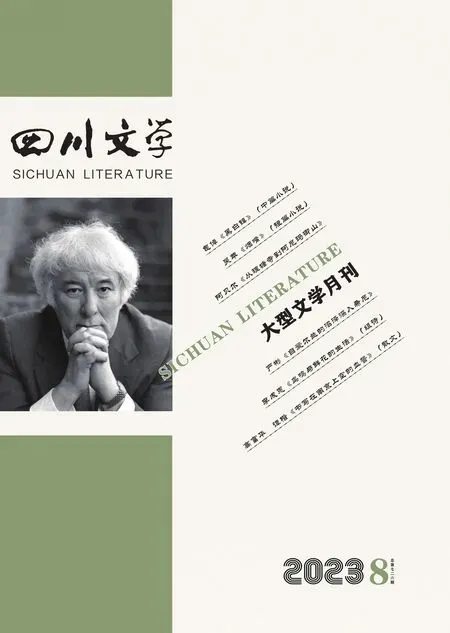植物的战争
□文/詹文格
一
凡是带有入侵属性的植物,似乎都有一种王者霸气,它们出手凶狠,行事果断。不论是纵向开掘,还是横向延伸,那种扩张势头,大有独霸天下、唯我独尊的锐气。
我一直以为,漫山遍野的植物,默默生长,岁岁枯荣,就像修行的老僧,养成了平和淡泊的佛性。谁知我的认识仅停留于浅表,所看到的只是肤浅的假象。草木用朴拙的外表,隐藏了深重的心机。人非草木,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自我炫耀,在某些方面人不一定比草木高明。
人类并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在大千世界中,还有广阔的区域存在疑惑,在大量的空间留下未知,所有的空白地带为我们提供了无限想象。
在名目繁多的植物界,其实不乏暴戾乖张的种类,那些平淡无奇的植物,一旦争斗起来,惊心动魄,毫不手软。相互撕咬的根系藤蔓,纠缠不休,你死我活,植物争斗的凶猛程度,丝毫不比血腥的动物逊色。
从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到寒凉清瘦的高原植物,随处都有明争暗斗的对头冤家。它们为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多吸收一些阳光雨露,不断挤兑,反复较量。那些性格野蛮的物种,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会不择手段,排除异己,大有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德性。
当强者一旦占据绝对优势,就会摇旗呐喊,乘胜追击,继续对弱者展开围追堵截,折腾厮杀,直至彻底清剿为止。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物种最为丰富的乐园,同时也是植物竞争最激烈的决斗场。它们为了获得成长的权利,拼命争抢阳光,尤其是伏于地面的植物,只能从枝叶的罅隙中,获取一丁点儿微弱的阳光。面黄肌瘦地挣扎在地面,它们心有不甘,翘首仰望,苦苦等待破土而出的时机。
当一棵衰朽的古树轰然倒地,百年一遇的时机终于来临。就在阳光洒满大地的那一刻,如同听到起跑线上的枪声,一场新的生存秩序重新建立,所有蓄势待发的竞争对手,重返赛场。它们裸露隆起的肌腱,迈开腿脚,当仁不让,迎头冲刺。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贪婪地吸吮阳光雨水,用强攻的方式,抢占空间,为种群的后代繁育创造条件。
二
在庞杂的植物界,无论木本、草本,还是藤本,它们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不断演化,笑傲江湖,暗中练就一招制胜的独家秘籍。
从它们的招式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的入侵路径和攻谋手段。那株沐浴在朝露中的龟背竹,正努力生长着碧绿的叶子,尽情吸收金色的阳光。在它旁边晃荡的藤蔓,看上去稚嫩纤瘦,如同邻家小女,看不出有任何企图和危害。
春深时节,青藤伸出粉嫩的玉臂,朝龟背竹亲切地挥手。它说:大哥呀,你别只顾着自己往上蹿,快来搀扶弱者一把,给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让小妹也有攀缘而上的机会。
挺拔的龟背竹不知藤蔓心藏诡计,对楚楚动人的芳邻,毫无提防警惕,一不小心就被迫不及待的藤儿搂住了脖子。藤儿借着晨雾的滋润,又亲又啃,死死缠住了俊朗的大哥。
这种以身相许的搂抱,看上去像是生死相随,托付终身,显得无比温柔。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攀附成功的藤蔓,迅速勒紧大哥的腰身,踩着它的肩膀,缠绕而上,很快便成功登顶。
接着疯长上蹿的藤蔓又披纷而下,一展英姿。龟背竹原以为这是一次激情搂抱,谁知变成了致命缠绕,很快龟背竹就枝叶萎缩,呼吸不畅。一株被唤作大哥的植物,眼睁睁窒息在青藤的臂弯里,欲哭无泪。它后悔当初心太软,不小心招惹了灭顶之灾。
草木葳蕤,混迹山林。多样性的植物,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鱼龙混杂,暗流汹涌。无论是卧底的密探,还是策反的间谍,哪一个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时难见分晓,一切要看是谁笑到了最后。
铺天盖地的藤蔓肆无忌惮地宣泄在阳光之中,接下来有一种植物即将出场。它迅疾的速度,如迎风的箭镞,噌噌地往上飙升,很快就超越了所有的植物。
这种疯长的植物叫轻木,它的叶子可以长到四十厘米,雨伞一样挡住阳光,阔大的叶片,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剥脱了周边植物生长的机会。
轻木看上去已经稳操胜券,然而争斗远没有结束,紧接着又有一株植物在它旁边伺机而动。有人形容这是一个准备套马的汉子,手中挥动着套马索,在寻找下套的机会。它的卷须上有十几个像钩子一样的倒刺,任何一个倒钩,只要钩中了目标,其他钩子就会开启疯狂的缠绕模式。在这样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如果可以攀上轻木,那等于如虎添翼。由于轻木的叶片上长满了绒毛,不仅扎手,而且特别光滑,外物很难黏附上去。就这样轻木扫除了身边障碍,打败了众多的竞争对手,畅通无阻挡地继续它的野蛮旅程。
迎风生长的轻木,只需一年左右就能蹿到十几米高,在同样的时间里,大多数树木只能长高两三厘米。不过万事都有两面性,虽然轻木生长神速,但同时也因欲速则不达,带来了极大的存活隐患。
由于质量过轻,哪怕刮起一阵不算猛烈的风,轻木都将拦腰折断。当一株轻木倒下,它的周围一片敞亮,给地面苦苦挣扎的植物带来了生机。同时也预示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植物界再次打响,新的霸主很快又将出现。
三
第一次听到水中暴君的名词,我不以为意,认为这是炫耀者夸张的修辞。然而在接连不断的深入探访中,面对真相我认可了暴君这个词语,看到了植物杀手的厉害。
初春时节,在那片平静的湖面上,我遇见了一些布满毛刺的小叶片。当时我对亚马逊王莲一无所知,也许是湖面太大,叶片太小,没有谁会在意它的存在。王者初始,并无特别,从颜色到形状,根本窥视不出任何异相。再残暴的君王,它的幼年依然是满身翠绿,一派鲜嫩。谁知这种天真稚嫩的样貌里,早已隐藏了无尽杀机。
淤泥堆积的湖底,养分充足,在这个水生植物繁茂的地方,充斥着对抗和竞争的紧张关系,它们表面上在争夺水面,其实是在争夺阳光。
战争爆发的前夕,依旧是风平浪静,潜伏在水底的杀手悄然行动。开始,周围的植物并不在意,它们没有领教过王莲的凶猛和恐怖。野蛮生长的王莲,很快就显现了它的戾气,它借助武装到牙齿的精良装备,称王称霸。特殊的叶子像气球一样充盈,每天以超过二十厘米的速度在膨大扩张。最大的叶子可以长到两米多,在水上的承重能力高达六十余斤。一个半大的孩子站上去,如踩舢板,自由漂动,在辽阔的湖面上,亚马逊王莲无疑是水生植物中的航空母舰。
更厉害的是,它有超强的新生能力,一株亚马逊王莲,在短短几个月内能够繁育出四五十片叶子。一株王莲以魔幻般的扩张方式,碾压水中所有植物,成功抢占一方水面,不给其他植物一丝露头的机会。
王莲硕大的叶子不仅能抵御风吹日晒,还有抗拒水汽腐蚀的能力,它自带循环排水系统,再多的雨水也不会聚集于此。
王者归来,凡是它覆盖的水面,就像如来的手掌,谁都没有翻身的能力,就连繁殖力超强的水葫芦也被无声剿灭。
当我见识了这样的植物后才明白,莲中之王的命名准确而贴切,没有一点夸张的意思。铺展在湖面的王莲,如同一群冷面杀手,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四
为了跳出思维的偏见,我提醒自己不要在植物的身上寻找动物的影子,不要用人类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它们的对错。
我对强者的反复描述,并非为了赞美,而是出于好奇。其实我更关注纤细的弱者,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些卑微的种子和孱弱的根苗,在九死一生的抗争中,是如何幸免于难,得以存留的?
在云贵高原我曾幸遇过成片的桫椤,这种从侏罗纪地质年代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在那片向晚的夕阳中,闪烁着钻石般的光泽。
其时,我们一行人踩着潮湿的落叶,踏上松软的腐殖层,去见识植物的始祖。在桫椤的周围生长着一圈高大的灌木,像站岗的卫兵,丛生出杂草和枝条。树冠张开,犹如巨伞,叶片呈羽毛的形状,凝珠带翠,树形华美。远远看去,挺拔高挑的树貌,有一种铅华洗尽、大难不死的苍劲。凝视着这样劫后余生的物种,我感觉它们不像一片简单意义上的树木,更像一排穿越历史的碑林,每一棵桫椤都长成了时光的纪念碑。
一群珍稀的物种,在云雾缭绕的山坳中,如同修行的隐者,沉默不语。慧根深藏的桫椤,散发出一种超尘脱俗的表情,被众多国家列为濒危保护植物,无疑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考古界认为,桫椤最早出现在三亿多年前,算起来比恐龙的历史还要早1.5亿年,它是名副其实的“地球活化石”。
外形类似于椰树的桫椤,它还有个特别的名字——蛇木。站在桫椤面前,我突然冒出“地老天荒”这个词语。作为公认的冰川前期蕨类,桫椤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何等幸运!它竟然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让纯正的根脉得以延续。
三亿年的兴衰存亡,生而为“树”的桫椤,有着怎样的长寿秘诀?连凶猛称霸的恐龙都已灭绝消失,而它却顽强地活到了今天。没有谁知晓这个过程,所有的结果只能是推演和猜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行星撞击,尘埃飘上了大气层,屏蔽了阳光和空气,让强大的恐龙遭遇绝境,而蕨类植物不需要任何昆虫和风雨为它们授粉,它的种子是以孢子的方式进行繁殖,当大气层的尘埃重新落下时,它的生命再次开始进化重生。
桫椤不开花、不结果,没有种子,靠孢子真菌繁衍后代。与常见的灵芝、鸡枞、虫草一样,它们生之易,正如那句老话:“好货不留种”。
五
人类还是低估了植物的威猛,尽管它们没有飞翔的本领,但人类、鸟兽、虫类却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它们的翅膀,让远方的物种跋山涉水,远渡重洋。
强敌一旦跨越国界,它们就能畅通无阻、所向披靡地完成入侵作战,实现殖民野心。
2001年,在河北衡水一带发现了一种植物,开始人们以为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杂草,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随后在邯郸、邢台、保定、石家庄、廊坊等地相继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对这种刚刚出现的植物一无所知,看见它生长在路边,像一片金黄的野菊,非常好看,可不久这种名叫黄顶菊的植物开始显现出它恐怖的面目。
原产南美洲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黄顶菊,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充满了破坏的心思,大有一举占领地球的野心。它根系发达,抢夺肥水,具有耐盐碱、耐干旱、强抗逆性、高繁殖力的特性。在生存能力上,黄顶菊无可阻挡,一株黄顶菊能产出数万至十万以上颗种子,即便有再多的天敌,再大的屏障,也架不住它的“花海战术”。
细小的种子借助风、水、行人、车辆等媒介的推动,很快就传播开来。从南美洲蔓延到北美洲南部以及西印度群岛。后来又入侵到了埃及、南非、法国、英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
不讲武德的黄顶菊,进入我国以来,由于没有天敌,繁殖速度惊人,生长肆无忌惮,轻而易举地挤占了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
最致命的是,这种不走正道的黄顶菊,在生长过程中还会释放毒气,产生化学物质,这种物质会干扰或抑制其他作物的生长,甚至直接导致死亡。有数据显示,黄顶菊对于棉花的致死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黄顶菊扎根的地方,其他植物难以生存,因此它臭名昭著,人们给它冠以“生态杀手”“霸王草”这样的恶毒之名。就连铲除黄顶菊的人员,在劳作之后也得十分注意,需要认真检查鞋子衣服上面是否落有种子或沾有根茎残须。只要有一点挂上行人或野兽的皮毛,它就能走遍田野畦垅,占领更多的阵地。
黄顶菊,这种野蛮透顶的植物,它的恐怖之处不止一个,不仅生长迅猛,而且还喜欢拈花惹草,打怪升级。由于黄顶菊的花期与我国本土的菊科植物交叉重叠,出现菊科植物之间的天然杂交进化现象。别小看这种杂交现象,它可以让外来优势与本土优势强强联合,生出一种危害性更大的新物种。
六
谈到入侵植物,我就会想起我们村的革命草——它的传播者,竟是我的父亲。
作为一名走村串户的兽医,在那个粮食匮乏年代,农民放下镰刀饿肚子的事情经常发生。没有饲料,缺少米糠,外出打猪草也得起早摸黑,农民养猪喂鸡很不易,对于农民的艰难,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一时又想不出啥办法。
后来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县里派他参加省农干校脱产培训。培训结束前,组织学员到实习基地参观,发现有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无论是荒山野地,还是田边沟渠,它都长势喜人,一片青绿,为此人们称这种植物为革命草。
离开基地时,父亲获得了十几根草苗,提着几根青草,他如获至宝,兴冲冲地带回了家乡。很快革命草就在家乡落地生根,不久开始繁茂起来。开始大家对这种草以礼相待,非常客气,在空闲的地块上助其生长。有些人家甚至把它视为座上宾,请进了肥沃的菜园,植入了疏松的苗圃,当成远方的贵客,好吃好喝进行侍候。
这种即使没有阳光也灿烂的革命草,一旦获得扎根喘息的机会,立马就呈现燎原之势。几年过去,当人们发现它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毒草时,扩张的趋势已经上升成了灾害,根本无法遏止。
几十年来,革命草不知被多少人诅咒,火烧、药杀、锄挖,人们用尽了各种方法,依旧无法铲除。现在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区,只要有水土的地方,就有革命草的身影。
去年秋天,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偶然间在一本植物志里发现了革命草的记载。当时仿佛看到有人在身边揪出了一个老谋深算的卧底,让人大吃一惊!原来这种所谓的革命草,它也是由北美传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为解决牲畜饲料来源,我国曾尝试种植。革命草的种植显然非常成功,种植成功后发现该植物不仅含有毒性,不适合做饲料,而且还会抢夺农作物阳光、水分、肥料和生长空间,造成严重减产。可是等人们发现后已经来不及了,革命草已经四处蔓延,危害极大。
回头来看革命草,它的生命力极强,不怕旱、不怕涝,只要有一小段落进水土,很快就会疯长起来。就连进入猪牛肠胃的草料,从粪便中排出的草节,它也能还魂再生,照样长出碧绿的草来。
七
我国的林草生态系统屡遭攻击,已经确认发现的外来入侵物种高达六百六十多种。无论是通过风媒、水体、飞禽、走兽、昆虫、植物种子或微生物发生的自然迁移,还是人为有意引进的,植物入侵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生态问题。
国内有如此之多的入侵物种,那么国外情况又如何呢?是否同样出现了入侵植物?以美国为例,就有一种入侵严重的植物——野葛。野葛的入侵对美国人来说,那是典型的自作自受。
美国原本没有野葛存在。1876年,日本人把葛藤带到了费城世博会,有一位美国人看到了葛藤花,经受不了它的美丽诱惑,偷偷地掰下一个葛藤芽头,带回去栽种,于是培育出了第一株小葛藤。接着出于好奇,美国人开始人工种植,直到1935年,美国人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这个决定导致了葛藤在美国出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
当时美国南方普遍遭受了虫灾,大面积的种植园出现荒芜,造成水土流失严重。为了保护水土,美国政府呼吁农民广泛种植葛藤,每种植一亩就可获得八美元的补贴。短短一年时间,葛藤开始泛滥成灾,四处蔓延,所有植物都被葛藤覆盖,给美国生态造成瘫痪性危害。
对于如此疯狂的葛藤,美国人无可奈何,他们把葛藤形容为“绿色恶魔”。从此,野葛成为入侵美国最严重的物种之一,几乎想尽一切办法来消灭野葛,一直都没有效果。后来想利用一物降一物的方法来消灭葛藤。听说引进一种叫“筛豆龟蝽”的虫子能把葛藤吃光,谁知这种虫子引进来,非但没能消灭葛藤,反而给美国大豆产业造成巨大损失。“筛豆龟蝽”从此在美国成了另一种入侵物种,可谓是雪上加霜。
常言道: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本来有了前车的失败教训,人们应该更加警惕和审慎起来才对。可惜这些年我国还是出现了人为引进有害物种的惨痛例子,比如福寿螺、水葫芦等。
松线虫,被称为“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病,是由外来入侵生物松材线虫引起的一种世界性重大检疫性森林病害,原发于北美地区。
1982年我国在南京中山陵首次发现松材线虫病,四十年过去,现在对我国近九亿亩松林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松材线虫病是一种毁灭性的松树病害,其破坏力极强,松树一旦感染,只要四十天左右就会死亡,而且完全不可逆转。目前尚无有效药物可治,因此,被称为松树的“癌症”。近年来,松材线虫病传播扩散日益加快,呈现向西、向北快速扩散,最西端已到达四川省凉山州,最北端已蔓延到吉林。同时还入侵了黄山、泰山、张家界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危害日趋严重的松材线虫病,已造成数十亿株松树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
八
面对凶猛的入侵植物,绝大多数人都是漠不关心的观望者。正因为对入侵者持模糊不清的认识,在日常生活中毫无防范意识。
八月上旬,我家小女儿与班里同学结伴郊游。她们来一个山村,钻过大片的草丛,穿越一条河谷,找到了一块开阔的河滩。
在河滩上孩子们停了下来,高高兴兴地准备野餐。刚摆好水果、面包、牛奶、鸡腿,准备正式开吃,我女儿与另外一名同学突然有了情况。感觉身体奇痒不止,特别是耳朵、眼睛、鼻子部位出现红肿,接下来头痛欲裂、鼻涕直流……
幸亏她们的班长有些经验,第一时间拨通了家长电话,我们及时联系就近医院,把孩子送去治疗。原来孩子是因豚草花粉过敏,引发严重过敏症状。后来听医生说,豚草过敏是很严重的事,它不仅是枯草热的主要病原,同时还会引发肺气肿等疾病,甚至造成死亡。
豚草在我国有了很长的入侵史,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那年在杭州首次发现。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豚草,是世界公认的有害植物之一,它危害惊人,素称“植物杀手”,不仅引起甘蓝菌核病、日葵叶斑病,诱发大豆病虫侵害,使农作物严重减产或绝收,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
如此诡异的植物,不由想起那款著名的游戏——《植物大战僵尸》,以及流行的绘本故事——植物战争。
在地球上,植物的演化从未停止,在演化过程中,有的成了杂技运动员,不停翻滚;有的成了蛇蝎美人,美丽凶悍;有的成了盗贼,专门窃取其他植物的能量;还有的成了骄纵的毒博士,杀死了自己的邻居……
植物,看上去沉默不语,其实它们的战争惊心动魄。一场横跨百万年的生存之战,看不到任何的硝烟战火,找不到厮杀较量的痕迹。但是那确实是一场兵戎相接的比拼。
植物的秘密武器有时会藏在地下或存于根部;有些则配备在摇曳的枝叶、待放的花蕾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事实证明,优胜劣汰的法则不仅是动物界的显性现象,同样是植物界的通行原则。如此看来,新生与死亡,疾病与健康,战争与和平,永远是相生相克两大阵容。在辽阔的星球上,没有真正的平静之地,即便是寂寞的旷野、无边的沙漠、寒冷的冰川,同样存在着无声的战争。
——桫 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