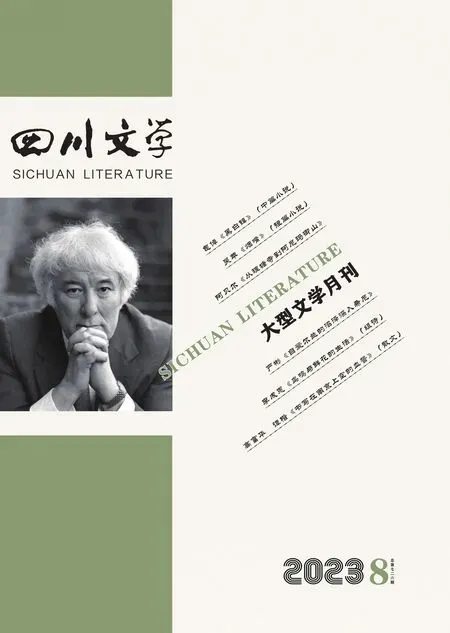文学语言的视觉型与非视觉型
□文/林渊液
数年前,我们几个朋友有一场共读。除了我,另外三位都是理论与创作兼长的青年学者和作家,他们分别是陈培浩、林培源、陈润庭。当时陈培浩倡议共读的是一位“60后”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我们以此为名,专门聚在一起办了一个小型沙龙,后来话题四下发散,竟至于酣畅地聊了个通宵。此次活动留下了一个梗。当时对于那部长篇小说的语言,四人分为两派。陈培浩和林培源是欣赏派,他们认为语言醇厚、中正、有韵味、守护了汉语的美。我和陈润庭是反对派,认为它老套、规矩,没有活力和新意,因为语言的问题,我们一开始的阅读存在障碍,大约三分之一篇幅之后才开始进入阅读状态。陈培浩对此颇为惊讶,他大概多表达了几句强化自己的观点,我为了反驳也加重了语气,说那语言尽是陈腐之气。两位欣赏派是“80后”,两位反对派分别是“70后”和“90后”,也就是说,这个分歧并不是代际审美造成的。
因为语言感知的默会性,当年并没有展开讨论,但陈培浩认定我和陈润庭对此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当他约写这个话题时,我不禁心虚,对语言我向来是凭直觉的、囫囵的,这要从何说起。重新去找当年共读的那部长篇小说来看,故事完全不记得了,但读了几页,自己打脸了。语言感觉很舒服,与乡村题材也是适配的,表现力也颇强,除了被偶尔的几个成语硌到,未觉有陈腐之气。这令我对自己当年的判断产生怀疑。是我对文学语言的审美发生了嬗变,还是另有干预因素?
当年的阅读我是纯粹的读者式感知,感知本身是模糊的,传达是有障碍的,作为读者的身份,表达是任性的。到了今天,我的阅读其实是写作者式理知,理知是相对精准的,表达是通畅的,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表达是节制的、充满了对同行的体谅。这种感觉,或许与当年的陈培浩、林培源更为接近。这里产生了两对有趣的关系,一对是感知&理知,一对是读者&写作者。感知与理知在阅读与写作中的转化到底是怎么样?当我以充满同理心的理知体谅了写作者的不容易,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语言审美也已认同?其实并不是,重读也到此为止,它并没有召唤起我继续阅读下去的兴趣。那么,我是否恪守着某些隐秘的阅读标准,它们是否有解码的可能?
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所有的自然语言都需要感知。我们只有依靠感知才能够写作,才能够阅读。所有的感知,都是“有我之知”。这也意味着感知天生带着一种主观性,并与经验联系在一起。而理知,通过道理知道,它恰好相反,它不带主观经验,而是带着客观性。从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看出,写作与阅读是以感知为主,表达和探讨却主要靠理知,它需要归纳和推断。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感知?我们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眼光所及,大量的文学语言,都是视觉感知为主,非视觉感知其实极少。感官感知最为集中的作品,干脆就是写感官感知本身。有几个写非视觉感知的小说,印象甚为深刻,分别是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长篇小说《香水》,何大草的短篇小说《裸云两朵》,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
《香水》是嗅觉型的感知,男主角格雷诺耶是一位气味王国的天才怪杰,他是香味的感受者、收藏者和制造者。为了提取香气制作香水,不惜杀害二十六名少女。格雷诺耶即将出生时,他母亲替他迎来了第一阵特殊的气味,臭气。“她并没有闻到臭气的臭,而是闻到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麻醉人的气味。她觉得,就像一块田里的百合花,或是像一间狭小的房间养了太多的水仙花产生的气味。”当时,她正在圣婴公墓那里的一个鱼摊旁,为掏去内脏的鲤鱼刮鱼鳞,阵阵恶臭把尸体的臭味淹没了。也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把生下来的儿子像扔掉的鱼肚肠一样撂在宰鱼台下。这阵臭味,几乎是格雷诺耶生命背景的暗喻。他有一个尊贵的鼻子,以嗅觉为毕生事业,所有事情在他的记忆里全部以气味的形式呈现,连梦影也是气味的一部分。然而,从恶臭到奇香,他的嗅觉美学却呈现出一种病态特征,需要以杀人为代价。他对于奇香的迷恋,到了令人感动的地步。“夜里他躺在小屋里,再一次回忆这种香味,把它拿出来——他经不住诱惑——沉浸在这香味中,爱抚着它,同时自己又被它爱抚,如此亲密,如此接近,仿佛他真的占有它,他的香味,他自己的香味,他爱抚它和被它爱抚,经历了一个迷人的美好的片刻。”
何大草的短篇小说《裸云两朵》是听觉型的感知。音乐学院的老师苏娘是一位归侨,她是女中音,花腔,“我”听她唱完一首歌,“说不出的厚实温煦,如一朵春天的云,在天上舒卷。礼堂安静得可怕,在歌声停下来的那一小会儿里,安静抵达顶点,石垒的墙壁仿佛都在膨胀着……”音乐天才赵小青是她的学生兼情人,在苏娘受批斗时揭发了她,致使她撞墙而死。苏娘的养女桑桑熟知这个男人的耳朵追求声音百分之百的纯粹,她最终用塑料薄膜摩擦玻璃的噪音把赵小青逼得跳楼。“有吱吱的声音从桑树林里传过来。那声音并不太响,但又滞又涩,让人心慌,我睡意全消,后来干脆坐起来,等那声音消失。但它并没有要消失的意思,响得极有耐性,停了一小会,我刚重新钻进被窝,它又回来了,好像就在你的耳边聒噪。……我刚上床,声音又来了,……而且声音拉得更长了,艰涩得像一根锥子直往耳鼓膜里钻。”那泡沫擦玻璃的声音,在文中一再渲染,渲染成一种令人窒息令人绝望的氛围。
这两篇都是直接写感官,一根长矛直戳过去,那感觉凌厉而恣意,入木三分。如果说《香水》和《裸云两朵》对于非视觉型感官是主动出击的,那么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则是被动的。《推拿》写的是一群盲人的故事,他们是没有视觉型感知的人,所以,其他感官的感知特别发达,听觉、嗅觉、触觉、温冷觉等经常轮番出场,或者一齐出场。比如,小马对嫂子的感觉。
“(他)对嫂子的气味着迷了。小马不知道怎样才能描述嫂子的气味,干脆,他把这股子庞大的气味叫做了嫂子。这一来嫂子就无所不在了,仿佛搀着小马的手,走在了地板上,走在了箱子上,走在了椅子上,走在了墙壁上,走在了窗户上,走在了天花板上,甚至,走在了枕头上。”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在这些写感知的语言里,通感是经常使用的手法。而且,非视觉型感知,大都需要通过视觉来表达。田里的百合花、天上舒卷的春天的云……《推拿》中,盲人泰来摸了女朋友的脸,被问到怎么一个好看法?泰来的盲是天生的,憋半天用宣誓一般的声音说:“比红烧肉还要好看。”《香水》中,格雷诺耶配备了一种奇特的香水,它的气味不像一种香味,而像是散发着香味的一个人。更奇特的是,“假如一个本身具有人的气味的人用了这种香水,那么我们会觉得他带有两个人的气味,或者比这更糟糕,像个可怕的双重身体的人。”这一段对于视觉的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是为什么?视觉是所有感官里的通货,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在它这里获得估值和兑换。这与视觉的独特地位有关,所谓的“眼见为实”,我们在法庭上当证人,说我听到那个人的声音,闻到那个人的气息,那是不能为凭的,只有看见了他的人,才能确认他到场。所以,视觉与其他的感官系统并不是平等的关系。文学作品中大量的视觉型语言,其实是基础性语言。而且,视觉型感知的表达最为发达,有大量的词汇和意象可供选用,占据了极大的优势,相比较起来,非视觉型感知的表达,可供选择的非常稀缺。可是,一经出手,却又令人十分惊艳。
除了稀缺性,还有其他缘由吗?
视觉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依据,它比其他感官天生地带有一种更为周正、更为符合道德、礼仪和文明的设定,有着更多的受众。视觉美学是一种穿了衣衫的美学,是遮掩与掀开的比例之美,而非视觉美学是赤裸裸的率性美学。D·H·劳伦斯是一位擅写触觉型感知的作家,他借查泰莱夫人之口说道:“要紧的是,永远都要紧的是,把虚假的羞耻感烧个干净,把身体里最沉重的杂质熔化,净化,用纯粹的欲望之火。”原来,我看重的是非视觉语言中更具生命感的美学,是温热的身体和舌头,是带着战栗的触须,是文字里的多巴胺和内啡肽。
另有一点,视觉型感知偏于具象,而非视觉型感知更具抽象性的可能。
《推拿》中盲人小马对时间的感受,是视觉型感知所不可能完成的。“时间有可能是硬的、也可能是软的;时间可能在物体的外面,也可能在物体的里面;咔与嚓之间可能有一个可疑的空隙;时间可以有形状,也可以没有形状。……在时间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瞎子。要想看见时间的真面目,办法只有一个:你从此脱离了时间。小马就此懂得了时间的含义,要想和时间在一起,你必须放弃你的身体。放弃他人,也放弃自己。这一点只有盲人才能做到。”
毕飞宇直接把视觉型和非视觉型的差异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他认为:看不见是一种局限。看得见同样是一种局限。
列举了这么多我个人甚为欣赏的非视觉型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仅仅推崇非视觉型语言。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文本什么样的语言。针对不同题材和思想,语言的选择并不可能是固定模式。非视觉作为弱势感知,其实也有着很大的缺憾。不论是听觉、触觉还是嗅觉,与它们相关的词语和意象十分有限,可供探险的山麓并没有太多。很多时候,因为通感的使用,视觉型和非视觉型之间也呈现得界限不清。但非视觉型语言对“有我之知”中的“我”更为强调,更合适现代主义作品。而视觉型语言偏向于客观描述,更合适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视觉型语言作为一种基础性语言,像是一杯通兑的白开水,如果没有足够的警惕,很容易就写得平庸、刻板和无趣。在这一点上,非视觉型语言可达至的纯粹而热烈的生命感,像一面光洁的镜子。
这种生命感其实不太好表达,我只得借用两种与爱情相关的激素来阐述,多巴胺与内啡肽。多巴胺是激情来临时传递亢奋与欢愉的,内啡肽是在激情消失之后,让人感觉平静温暖、历久弥坚的。好的文学语言,想必就是这样的爱情激素的交替。
通过这一番梳理,我相信,当年对那位著名作家长篇小说的不满意,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与其语言适配的思想和故事并不是我所欣赏的美学风格。在理知上我充满了理解和认同,但在感知上,我并没有与文本产生深度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