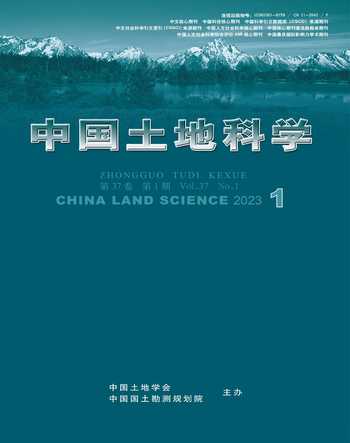“准征收”视域下耕地开发权管制的法律表达
摘要:研究目的:探求我国耕地开发权管制的本质,为我国耕地保护立法提供妥适的制度设计方案。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研究结果:改革我国现行耕地开发权管制法律制度,是我国耕地保护立法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法理上,严格限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地用途管制,其实质是对耕地开发权的管制。从财产权“准征收”角度审视,着眼于“对象识别基准”“结果识别基准”和“综合识别基准”,考量平等、比例等原则,积极回应当下城乡关系发展态势,应承认我国现行的耕地开发权管制构成对耕地开发权的“准征收”。研究结论:我国耕地开发权管制法律制度的建设,应在构建耕地开发权“准征收”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系统性展开,这是提升其规范性、体系性,实现我国土地法学从传统政策性研究范式向现代规范性研究范式转型的内在要求。我国耕地保护立法应以此为导向展开相应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表达,如此方可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进而助推粮食安全目标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准征收;土地法学;耕地开发权管制;耕地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58(2023)01-004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法律问题研究”(21BFX134)。
我国于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立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取代了之前的“统一分级限额审批制”的用地管理模式[1],标志着我国对土地资源的管理迈入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实践证明,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在解决土地资源利用不相容问题、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2]。然而,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要素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财产权价值的不断释放,多元化的土地市场主体利益诉求正日益凸显。实践中,为追求农地非农化利用带来的增值利益,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从事开发建設的违法现象有禁不止[3]。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因其管制的低效率,而逐渐步入了制度运行失灵的困境[4]。然而,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对此并未作出实质性修改。法理上,基于权力与权利的逻辑关系,以限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为内容的土地用途管制,其本质是对耕地开发权的管制[5]。因而,土地用途管制的失灵,其实质乃是耕地开发权管制的失灵。
目前,无论是官方抑或学界对于耕地开发权管制需要改革已无争议,但在确立何种改革方向,如何设计改革的具体路径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可供采行的方案[6]。从域外经验看,围绕耕地开发权管制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在立足于财产权“准征收”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法律制度规范体系,以此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从而确保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行。为此,本文尝试从财产权“准征收”角度出发,并结合域外相关经验,遵循中国的地权结构形态,立足于我国耕地保护立法的时代背景,从法理层面就我国现行耕地开发权管制是否构成财产权“准征收”,在构成财产权“准征收”情形下如何改革等法律问题展开系统性的法理研判,期冀为我国耕地开发权管制法律制度的深化改革、耕地保护立法的顺利推进、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有效实现提供理论参考。
1 财产权“准征收”的一般原理
鉴于我国现行实定法尚无“准征收”的规范表达和制度安排,学理上围绕这一议题的研究亦仅处于初级阶段,在“准征收”的生成逻辑、概念界定、构成要件等法律问题上尚处于争议状态。是故,本文首先从法理层面对财产权“准征收”原理进行释明,以揭示这一原理的基本谱系,进而为下文的理论展开提供逻辑前提上的助益。
1.1 财产权“准征收”概念界定
尽管目前学理上就财产权“准征收”概念的界定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所谓财产权“准征收”主要是指未经正当的征收程序而使私有财产权遭受实质性剥夺(taking)、物理性侵占或者不合理的限制时,权利人如何寻求补偿的情形[7]。换言之,当政府行使公权力限制私有财产权达到一定程度致使其价值大大减少或者允许公众利用私有不动产时,虽然此时该不动产并没有被直接剥夺,但权利人却可以因此主张政府行为构成了征收而寻求补偿救济。简单而言,当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构成实质上的剥夺,致使财产权人为此而承受特别的牺牲时,可以将其界定为财产权“准征收”。从实践看,谢哲胜曾指出,除了既成道路外,尚有公共设施保留地、古迹保存规定、“森林法”限期造林规定、机场周围和高速道路两旁承受噪音情形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禁止贩卖野生动物规定等,这些不同的情形,权利人均在“国家”以公益名义的限制下而受有特别牺牲,虽无征收之名,但有征收之实的情形,故可将其界定为“准征收”[8]。本质上,财产权“准征收”乃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有财产权的变相剥夺,财产权人为此而承受特别的牺牲,且“这种损害是严重的和不可期待的”[9]。
1.2 财产权“准征收”基本样态
从财产权“准征收”呈现的基本样态看,“占有准征收”(possessory takings)和“管制准征收”(regulatory takings)是其两种主要类型。前者发生于当政府本身或其授权的第三者,物理上的侵入且占有私人不动产,理论上其偏重于保护财产的“占有”;而后者系用于经济管制法规和大部分形式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以及其他在土地使用限制情形,理论上其偏重于保护财产的价值[8]。显然,在“占有准征收”中,由于对财产权物理性的永久占有,本质上即构成财产权“准征a收”,较易认定,一般争议不大。而“管制准征收”,作为英美判例法上的概念,是指国家对私人财产权采取过度的限制性法令措施而造成的征收,就其设立的目的而言,是在政府管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私人使用不动产的权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征收理论。只有当符合一定的标准才能认定政府对私人使用不动产的“管制”转化为“征收”,即出现“管制征收”[10]。
1.3 财产权“准征收”判定基准
对财产权“准征收”而言,由于在认定的时候会牵涉到诸多需要考量的因素,比如对象、结果、社会观念、国家政策等,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围绕其判定基准的设定一直存在较大争议①。从域外经验看,关涉财产权“准征收”法
2.3 从“综合识别基准”切入
耕地开发权作为土地权利人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在法律性质层面,宜被界定为一项“准物权”[21]。就这项财产权自身而言,并无内在的危险性,并不属于法律所禁止行使的财产权序列;此外,伴随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耕地权利人的财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强化,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所践行的单一命令和服从式的强制性管制模式,已难以回应多元化的土地市场主体利益诉求,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如何改变农村相对落后的面貌,从而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然成为国家在政策和制度设计层面面临的重大性议题。
这在英美等国家也体现得很明显。早期,美国主管机关认为土地使用分区的划设与用地编定根植于“警察权”(police power)行使的基础上,对土地使用限制的权源系国家主权的一部分[22]。申言之,限制土地区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并不能对所生的损失享有求偿权,这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典型的案例支撑。然而,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财产权保障思潮的兴起,土地分区管制背景下的土地使用限制被美国法院视为具有“管制准征收”(regulatory taking)的效力,出现了诸多未予以损失补偿而被宣判为违宪的案例。是故,处理好财产权“准征收”下的补偿问题意义重大。鉴于此,为摆脱传统土地分区管制带来的“暴损——暴利的困境”(“windfall-wipeout dilemma”),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应运而生,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和较完善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23]。可以说,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构成了土地分区管制的配套性制度,是對分区管制构成“管制准征收”情形下的一种具体补偿模式,以此实现在坚持土地分区管制前提下的公私利益平衡目标[24]。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在保护稀缺的耕地资源、维持有限的开放空间、保障公共绿地以及历史文化遗迹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25]。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财产权“准征收”的认定牵涉到偏向“财产权保障”和偏向“公益维护”或者“财产权社会义务”两大向度,如果从偏向“财产权保障”角度来看,对财产权“准征收”的认定可以持相对宽松的立场,但如果从偏向“公益维护”或者“财产权社会义务”向度而言,对财产权“准征收”的认定宜持相对严格的立场。显然,在个案中究竟是偏向“财产权保障”向度还是偏向“公益维护”或者“财产权社会义务”向度,与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观念以及国家的政策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看,偏向“财产权保障”向度,将土地用途管制视为对耕地开发权的“准征收”,更能顺应当下社会发展的态势和诉求,更能体现财产权价值保障的社会共识和价值诉求。
从我国当下现实看,因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不足,与工业品等其他产品相比缺乏市场价格优势,加之国家对粮食价格的调控,相同数量的土地和资金从事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收益要远远低于其他产业[20]。可以说,在当下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大多呈现出城市的‘强者姿态和乡村的‘弱势地位”的非均衡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在生产、生活等利益分配方面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国家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良好保障,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享有明显的优势,而农民却无法分享国家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利益,只能通过土地解决其生产和生活的基本需要。在这一情境下,考虑到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需要[26],倡导“城市包容乡村”的发展理念,甚至是“城市利益让渡”与“城市援助乡村”的发展战略,以充分发挥城市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容器”功能,应该值得尝试[27]。实际上,改革开放至今,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商业,农村、农业和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现阶段,在政策上,给农村、农民一些优惠的待遇,即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无疑是顺势而为的理性抉择。由此,在坚持对“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的理念下,顺应国家在当下处理城乡之间关系政策的需要,承认土地用途管制构成对农用地开发权的“准征收”,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制度构造走向理性化、科学化的本质要求。
总之,在现行土地用途管制背景下,耕地权利人对土地享有的开发权这项重要财产权受到了实质的剥夺或者损害(substantial damage)。而该制度正是为了保护稀缺的耕地资源,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这一全体社会成员的重大公共利益,并且受到限制的对象仅为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耕地权利人。众人的负担由少数人承受,正是“准征收”制度所欲防止的对象。鉴于此,将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对耕地开发权的管制认定为对耕地开发权的“准征收”,不仅具有法理正当性基础,而且也符合当下社会发展趋势,顺应社会情势的变迁。
3 “准征收”背景下我国耕地开发权管制的法律表达
上文已从多方面证成我国耕地开发权在形式层面所受到的管制,类似于实质上的剥夺,构成了耕地开发权的“准征收”。因此,在耕地保护立法的时代背景下,构建耕地开发权“准征收”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确保耕地权利人被剥夺的开发权的独立财产权价值的有效实现,应成为我国耕地开发权管制法律制度建设的理性路向。为此,将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法》宜对以下议题作出积极回应。
3.1 明定耕地开发权法律制度体系
承认耕地开发权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并对其法律性质、内容和归属等问题展开具体的规定,以推动其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建设,是“准征收”背景下我国耕地开发权管制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我国现行实定法并无耕地开发权这一独立的财产权类型,但无论是从理论发展的诉求,还是从土地管理改革实践看,都有必要在未来的耕地保护法中明确规定耕地开发权这一独立的财产权类型。就这一权利的生成逻辑而言,学理上存在究竟“属于土地所有权的固有内容”抑或“由国家的土地规划管制权而产生”两种观点之争[28]。显然,这两种观点之争的背后,是关于土地开发权究竟属于土地所有权人还是国家的分歧。本文主张,在应然层面,承认耕地开发权属于土地所有权的固有内容以及耕地开发权的生成乃是土地所有权处分权能之权利化的结果,这是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未来理性选择[29]。实际上,我国近年来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呈现土地开发权下放并回归集体土地权利人的显著趋势。譬如,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赋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位,其本质就在于回归土地开发权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所享有,尽管其范围仅限定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层面[30]。
就法律性质而言,应将耕地开发权这一财产权界定为一项用益物权。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耕地开发权的客体为特定地块的空间容量,对特定地块的空间容量能够在法律上实现其直接支配效力和排他效力,耕地开发权符合用益物权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从实质上看,耕地开发权的用益物权定位不仅是拓展和深化土地权利体系的需要,亦是我国土地管理市场化改革实践的需要。同时,这一定位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制资源,推动其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建设[31]。就权利归属而言,立足中国语境,应践行耕地权利人享有耕地开发权的权利归属模式:一方面,我国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主体虚位、权能缺失以及法律保障机制缺位等诸多弊病,虽然学界亦提出了诸多的破解方案,但争议并未因此而化解,因此,如果确定耕地开发权归集体所有,亦会面临权利主体“虚化”的困境,并有可能发生村委会等村集体代表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这显然是在沿袭和重复过往的模式,与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化”的背景下,确定耕地开发权归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享有的权利归属模式,究其根本,是由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
3.2 确立耕地开发权“准征收”制度
引入财产权“准征收”法律制度,承认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对耕地开发权的管制构成了耕地开发权的“准征收”,是“准征收”背景下我国耕地开发权管制法律制度建设的关键举措。我国现行实定法确立的财产权征收样态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征收,即以剥夺财产权利为常规手段,而对于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国家公权力对私有财产权过度限制构成的“准征收”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可以说,财产权“准征收”在我国现行实定法层面处于法外空间,因此而产生的纠纷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因此,基于对现实诉求的积极回应,有必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引入财产权“准征收”制度,以改变传统财产权征收制度适用范围偏狭的弊病,进而实现公益征收的二元化样态——传统征收+“准征收”。前已述及,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对耕地开发权形式上的管制构成实质上的剥夺,耕地权利人为此而承受了特别的牺牲,故从保障受限耕地权利人的利益角度出发,应将其界定为耕地开发权“准征收”。我国正在进行的耕地保护立法应确立耕地开发权“准征收”法律制度,无疑是必要而又迫切的。
3.3 建立耕地开发权交易机制
对于受剥夺的耕地开发权,应基于财产权保障的理念,借助“耕地开发权购买”和“耕地开发权转让”等方式来保障其受损的财产权价值,是“准征收”背景下我国耕地开发权管制法律制度建设的配套举措。在证成了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对耕地开发权管制构成“准征收”后,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耕地权利人受限的开发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比较法切入,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日等国家,“耕地开发权购买”和“耕地开发权转移”是较为常见的做法。所谓“耕地开发权购买”是指国家对受到限制的耕地开发权人所承受的特别牺牲而给予的补偿,这一做法在域外被称为“购买农地保护地役权模式”(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conservation easement,PACE)[32]。而“耕地开发权转移”主要是指开发商或者私人业主与保护区业主(开发权受限制地区土地权利人)之间达成开发权转让契约,由前者购买后者的开发权并用于特定地区(一般是具有进一步开发潜力的地区,可以是旧城区,亦可以是郊区或者农村)的土地开发[33]。从域外的经验看,开发权转让的价格与开发权购买的价格相类似,即以土地开发后的净收益与土地开发前的原有用途之间的差值为大体标准。开发权转让后,开发商凭借购买的土地开发权数量,可以在指定的开发区内进行超越原有的配额标准进行开发建设,其开发的密度包括原有规划许可分配的开发权指标加上从保护区购买的开发权指标[34]。通过“开发权转让”不仅可以实现开发权受限地区土地权利人利益的保障,促进规划区内的土地开发建设,亦能有效地实现土地分区管制运行目标,达到保护农业区的土地用途不变,以及对湿地、生态脆弱地等环境敏感地带和各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基于财产权“准征收”原理的内涵,无论是“土地开发权购买”还是“土地开发权转让”,其本质上都是土地开发权“准征收”补偿的两种模式。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较为妥当地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35]。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耕地开发权购买”还是“耕地开发权转让”模式,其适用都是有条件限制的,并且其功能亦是有限度的。具言之,对于“耕地开发权购买”模式而言,虽然其对公共资金具有明显的依赖且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压力,但在实践的运行中具有相对简单、效果相对确定等优点;而“耕地开发权转让”虽然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制和多元主体资金,但存在明显增加交易成本和诸多潜在的不确定因素等弊端。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引入这两项模式,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加以运用,而不能一刀切地采用单一模式。
4 结语:亟需提升耕地开发权管制制度的规范性、体系性品格
近年来,法学研究方法转型的议题备受学界关注。学理上,在“事实问题规范化、规范问题体系化、体系问题秩序化”的要求下[36],法學研究范式应从立法论为中心转向以解释论为中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我国当下的土地法学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转型层面似乎显得较为迟钝。脱离规范品格和思维的土地政策型研究较多,法体系语境要求下的教义法学分析较少。这不仅不利于这一部门法制度的内在逻辑和规范的理性化展开,而且因其学科独立话语体系的缺失而影响其独立性地位和司法功能的发挥,更遑论其“内价值体系的融贯性”[37]。
本文所探讨的耕地开发权管制议题就是一典型例证。学理上,围绕这一议题研讨的文献,几乎一致采行的是“动辄得咎”式的政策性话语,而从法的规范性、体系性等角度研判者较少。鉴于这一背景,本文尝试立足权利义务的逻辑平台,从“准征收”视角对这一主题展开系统性的法理研判,并借此契机,希望土地法学界能够顺应当下法学研究方法转型的时代背景,尽快从土地问题的传统政策性的研究范式转向现代规范性的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吸收法教义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现有文本规范内在的逻辑和理路。唯有如此,我国土地法制度规范体系方可得以建立和健全、土地法学话语体系方可得以独立化、土地法的规范效应和司法功能方可得以进一步彰显和提升。
參考文献(References):
[1] 卞耀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8.
[2] 沈守愚.土地法学通论(下)[M]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2:456.
[3] 张先贵.我国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法理求解[J] .法学家,2018(4):96 - 107,194.
[4] 郭洁.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J] .法学研究,2013,35(2):60 - 83.
[5] 李家才.论保护农田的土地开发权交易政策[J] .社会科学,2008(12):40 - 45,183.
[6]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79 - 81.
[7] GARNER B A. Blacks Law Dictonary[M] . 9th.ed. West:West Publishing Company,2004:332.
[8] 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7.
[9] 孙聪聪.《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立法体例与实体要义[J] .中国土地科学,2022,36(2):19 - 27.
[10] 王玎.论管制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J] .法学评论,2020,38(1):160 - 173.
[11] 宦吉娥.法律对采矿权的非征收性限制[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19(1):41 - 55.
[12] 金俭,张先贵.财产权准征收的判定基准[J] .比较法研究,2014(2):26 - 45.
[13] 谭荣.价值、利益和产权:百年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治理逻辑[J] .中国土地科学,2021,35(12):1 - 10.
[14] 岳文泽,钟鹏宇,王田雨,等.国土空间规划视域下土地发展权配置的理论思考[J] .中国土地科学,2021,35(4):1 - 8.
[15] 陈柏峰.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J] .法学研究,2012,34(4):99 - 114.
[16] EAGLE S J. The four-factor penn central regulatory takings test[J] . Penn State Law Review,2014,118(3):601 - 646.
[17] EAGLE S J. Property tests, due process tests and regulatory takings jurisprudence[J] .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7(4):899 - 958.
[18] 张千帆.城市化不需要征地——清除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宪法误区[J] .法学,2012(6):19 - 24.
[19] 杨惠,熊晖.农地管制中的财产权保障——从外部效益分享看农地激励性管制[J] .现代法学,2008(3):70 - 79.
[20] 陈小君.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关内容解读[J] .法学研究,2014,36(4):4 - 25.
[21] 张先贵.容积率指标交易的法律性质及规制[J] .法商研究,2016,33(1):65 - 73.
[22] 谢哲胜.从美国法上的土地准征收论既成道路公用地役权之妥当性[J] .经社法制论丛,1995(14):177 - 194.
[23] 陈佳骊.美国新泽西州土地发展权转移银行的运作模式及其启示[J] .中国土地科学,2011,25(5):85 - 90.
[24] GARVEY M P. When political muscle is enough: the case for limited judicial review of long distance transfers of development rights[J] .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2003,11(3):798 - 841.
[25] RICE R D. By what we have destroyed: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s[J] .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Law Review,2013,52:153 - 198.
[26] 段浩.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8):87 - 91.
[27] 刘祖云,李震.城市包容乡村:破解城乡二元的发展观[J] .学海,2013(1):20 - 28.
[28] 张鹏.规划管制与土地发展权关系研究评述[J] .中国土地科学,2010,24(10):74 - 78.
[29] 张先贵.中国法语境下土地开发权是如何生成的——基于“新权利”生成一般原理之展开[J] .求是学刊,2015,42(6):85 - 91.
[30] 张先贵.土地开发权与我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J] .北方法学,2017,11(2):110 - 119.
[31] 张先贵.土地开发权的用益物权属性论[J] .现代经济探讨,2015(8):74 - 78.
[32] 王玉,吴昭军.论耕地保护用途管制的法权基础——以管制性征收和公共地役权的组合为路径[J] .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2(1):53 - 67.
[33] LITTLEWOOD W H.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trpa and takings: the role of TDRs in the constitutional takings analysis[J] . McGeorge Law Review,1998,30:201 - 234.
[34] STENVENSON S J. Banking on TDRs: the governments role as banker of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J] .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8,73:1329 - 1376.
[35] 张先贵.中国语境下土地开发权内容之法理澄清——兼论土地资源上权利群与权力群配置基点的转型[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報),2020,38(5):73 - 87.
[36] 张先贵.中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内容之法理释明——立足于“新型权利”背景下的深思[J] .法律科学,2019,37(1):154 - 168.
[37] 张斌峰,周胤娣.《民法典》体系解释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规则研究[J] .政法论丛,2022(3):30 - 39.
Legal Expression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Regu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verse Condemnation”: Thought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ZHANG Xiangui
(School of Law,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 regulation, to provide a proper institutional design scheme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normativ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reforming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regulation in China is an unavoidable and important issue i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Legally, strictly restricting 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 into construction land is essentially the regula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 cultivated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rse condemn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current regul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constitutes “inverse condemn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In conclusion, the reform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regulation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launche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inverse condemn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which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improve its normative and systematic natur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design, so as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he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inverse condemnation; land law;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regulatio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本文责编:陈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