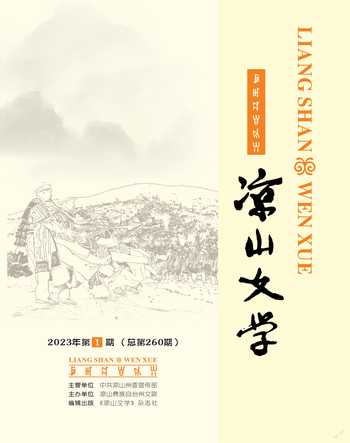相遇·与万物、与自我
沙辉
让我走进
让我走进幼时故土的
那一片金黄的秋天
庄稼们都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风和草木以及泥土
同幼童埋头游玩属于他们的游戏
那时,父亲母亲们风华正茂
让我走进那一首歌
那首属于草原山川溪流的
悠长乐曲
时间跨在上面、飞翔
耳畔有呼呼的风声
风声里有着只有你我
听得懂的哀伤和欢乐
让我走进岁月深处
遥望它的逝者如斯夫
却不曾遗忘来时路过的
每一片草原每一条小路
每一座山冈每一条河流
与鞋底相濡以沫的
每一粒尘土
与双肩共同扛过的
每一场风雨
和你的每一声呢喃细语
哪怕你已忘记
哪怕这个世界都已忘记
心藏故地行走江湖
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
名字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舌尖游走
每一个说过三遍以上
此处地名的人
它都是他的故乡
他都是它的孩子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名字
不仅用来命名属于这里的人
也指引从他乡寻它而来的人
询问着而来
如今我们所走的路,所到的地方
都曾经是父辈们的江湖
今夜
我沉醉在春风十里路
醉里鼾睡痛饮三百杯的
江湖豪杰卧榻之侧
只不过來去时的奔驰汽车
再不会在半路遇到
“此路是我开”的拦路绿林
解读“时光”
诚实的古人
也难免说了假话
或者说
其实古人
也早就会玩“穿越”了
你看崔颢就说: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一去不复返是真
即使复返也不再是
崔颢或崔颢之前的当年
那一只了
白云千载空悠悠
空悠悠是真,是常态
千载的白云
却不再是原本的白云
此时的白云
根本已不是彼时的
白云了
刘禹锡也说: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岂是旧时王谢堂前燕
“旧时”的晋朝
到刘诗人的唐代
已过了两三百年的时光
不要说当年的王谢堂前燕
就是当年王侯将相的子孙
那时差不多
都已再无可寻
我在迁徙,
故乡也在迁徙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回头望
我历来就不属于故乡
故乡也历来就不属于我
回不去的故乡
都只在我们的梦中
梦中的故乡才最真实和不变的
我在忙于迁徙
故乡也在忙于迁徙
我们都在迁徙的路上
偶尔在迁徙的路上相遇
都在
笑问客从何处来中
暗自热泪盈眶
各自独怆然涕下
然后各奔东西
要是时光可以倒流
要是时光可以倒流
我就和活了41岁的陈子昂
一起登幽州台
告诉他,你活了41岁
然后和他抱头同吟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
是千百年来
最会将胸中一口悠悠之气
用短短两句22字
淋漓尽致地吐出的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要是时光可以倒流
我就和活了61岁的李白
一起游历大川名山
(纵然没有他才高八斗
也要跟着他做他的跟屁虫)
告诉他,你活了61岁
然后跟他一起独坐敬亭山
相看两不厌
李白
是自古至今
最会将有限的生命
寄情于山水自然之人
他遇到我会坦言:
除了他自己
世上唯有我最懂他
相遇
昨夜一段梦
飘渺如风,又真实如昨
浓缩半生,起起伏伏
梦是相
是生活和心相的简易版
(简易版,也是精华版)
回顾如今这副模样的形成
人生那样步步惊心
又如此顺理成章
江南垂柳依依之际
漠北寒雪飘飘
总有一个人
成为它们若隐若现的背景
相信或者说期盼
一片春暖花开的时候
你我相遇在
人间的那一片明媚阳光里
犹如
万物总是命定地相遇在
那一片时空里
词语与财富
好久没有感受写诗的快乐了
那种——词语的突然降临
犹如突然间有星星落入怀中的感觉
那种——词语的降临
犹如让人受孕一般沉实的感觉
真的是太奇妙了
灵光的闪现总是让我成为富有者
让我一夜暴富
这样的感觉真的非常美妙
没有诗歌降临的一天
就是没有财富入账的一天
也就是让我惶惑不安的一天
因为没有财富进账就不再是真正意义的
富翁
同样,没有诗歌收入的人
就不再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了
故乡,我的无数个的故乡
一个人的故乡
或许不止是原初的那一个
我的祖先和我的故鄉
或许并不重合
而一条迁徙之路
犹如军事地图上的迂回线路
或隐或显于时空深处
同样,一个故乡
不止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故乡
我们的所幸,是大地从未荒芜
我爱每一片土地
犹如我如此真切地爱着我的祖先
爱着那曾经和如今
都如此真切地属于我的
每一个日子
世相也是心相
时间是静止的
不信你一早醒来你看窗外的那一片
静谧天空
时间是空天一样的那一片大海
游动的不过是鱼群般的我们
隔空的两代人
世界好旷远啊
那时候
你西出阳关总是无故人
世界热闹啊
如今一个箭步
我们就到了世界的任一角落
并且让我们惊讶的是身边
到处都是熟悉的人
这样也好
因为到处是人海
没有一个人是孤岛
即使隔三差五有一些灵魂升天了
活着的人也不再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人比黄花瘦,断肠人在天涯
因为身边依然
人山人海
有时候,非常想一个箭步
穿越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的
你那里
一个箭步穿越到
远方的孤单的你那里
却发现
我们依然是隔空的两代人
爱语
不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
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而是“每一个不曾耳鬓厮磨的
日子
都是对你和爱的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