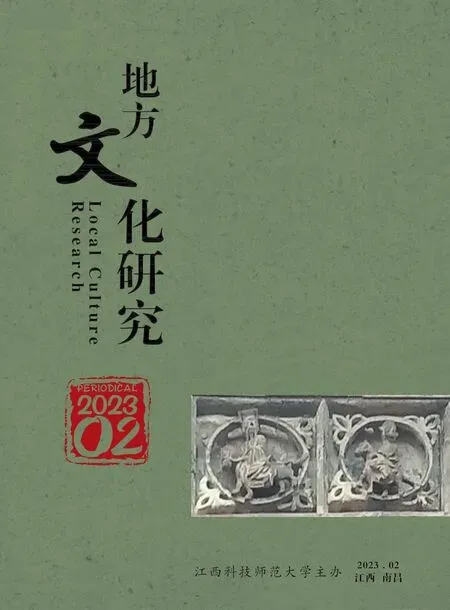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欧阳绍清
(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江西 吉安,343009)
仪式古已有之,而仪式学则是现当代才兴起的学科。经过百余年来的发展,仪式研究成果丰硕,仪式学理论已有相当成熟的范式并反哺仪式研究。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新兴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符号阐释学”的研究取向,仪式学已从宗教范畴转向世俗社会范畴,仪式表述范围亦越来越大,生活需要仪式感的“仪式化”社会将为仪式学带来更大、更广的阐释空间,同一个仪式可能被宗教、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青睐,从而产生与之相适用的研究观点。对仪式的关注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末,民族音乐学吸纳人类学的仪式研究视野,将仪式音乐作为一个特定的专题,近年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热点领域,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仪式音乐的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为调和“局内与局外”的不适,解读“思想与行为”的关系、阐释复杂的仪式现象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仪式音乐理论与方法的形成是在描述复杂的仪式过程中,不断调适和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仪式学理论的有力补充,更是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就。
一、从音乐到音声:仪式音乐概念的不断延伸
“仪式”是一个具有理解、界定、诠释和分析意义的广大空间和范围,研究者大多数从研究对象出发来理解仪式,其结论也大相径庭、千姿百态并自成一家。总体来说,无论如何解释仪式的概念,习惯性会出现“经典性阐述”和“一般性阐述”的分野,出现格尔茨所谓的“仪式的窗户”论,认为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与仪式的理解一样,有关仪式音乐的界定,学者们也有自身的理解与表述。首先,对“音乐是什么”早已不是20世纪以来乐理教科书上的那种表述,而是“一个不断填充新意的概念”①张振涛:《音乐——一个不断填充新意的概念》,《音乐与表演》,2015年第2期。了。民族音乐学的贡献就在于超越了“音乐是声音的艺术”这个单纯从技术上的狭隘理解,把对音乐的理解置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一种“站在哪里说音乐”的音乐理解观。我们应把音乐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而非艺术语言,才有“音乐作为艺术、音乐作为文化、音乐作为工具”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音乐观念在判断“音乐是什么”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和与声音发生的人以及声音发生的语境有关。所以,布鲁诺·内特尔说:“一种声音是否是音乐是由一定社会范围的语境来确定的”。其次,从音乐与环境的共生关系上看,我们习惯将音乐分为民俗音乐、仪式音乐、宗教音乐、艺术音乐等不同范畴。仪式音乐和艺术音乐不同就在于仪式音乐强调信仰行为中的功能以及特定的象征意义。因此,仪式音乐这一概念就需进一步界定和解读。曹本冶提出“仪式中音声”和“音声境域”概念,以面对和处理仪式展现中研究者“听到的”和“听不到”的音声。仪式中“听得到”的“音声”主要包括“器声”和“人声”两大类,“器声”包含具有特定仪式含义的“法器声”和“物件声”以及与民俗活动共享的“乐器声”;“人声”则包括各种程度的近似语言、近似音乐、似念似唱或似唱似念、连唱带哭或连哭带唱的音声。②曹本冶主编:《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45页。这里只对“听得到”的音声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而对“听不到”的“音声”,曹氏基于他在道教仪式研究中所捕捉到的、局内人存在着的“心诵”和“神诵”一类的不向外界发声的音声观念,也同属于仪式中有意义的声音。因此,他用“仪式音声”来概括仪式现场的一切声音。乔建中教授在肯定“音声”概念的价值后,也从广义上提出“凡是民间仪式活动中使用的音乐,无论是歌唱(声乐)、演奏(器乐)或带有宣叙性的念诵,我们都没有理由将它排斥在民间仪式音乐之外,而应称为‘民间仪式音乐’。”③乔建中:《中国华东地区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综述》,载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上),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第 55页。这里主要强调了“念诵”类声音也应作为仪式音乐考察的范畴,这和曹氏“音声”所涵盖的声音范围相一致。
正如音乐概念多元化一样,仪式音乐作为音乐的次级概念,也有多种释义。薛艺兵教授在分析了音乐的艺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综合曹氏“仪式中的音声环境”的观点之后,认为“仪式音乐是在形式和风格上与特定仪式的环境、情绪、目的相吻合的,可对仪式参与者产生生理和心理效应的音乐。仪式音乐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及其文化传统,并依存、归属和受制于社会和文化传统。仪式环境中的各种声音都可能具有‘音乐’的属性而成为仪式音乐研究的对象。”④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3页。这一创造性的界定虽从“局外人”的视域出发而提出,但它却可以有效引导民族音乐学者如何去研究仪式中出现的对“局内人(执仪者或参与者)”产生一定“灵验”效应的、而对“局外人”所理解的声音。台湾蔡宗德教授在研究宗教仪式音乐时,面对在某些宗教和文化里并没有一个完全与“宗教音乐”和“音乐”相对应的概念,使用“类音乐”概念来区分西方所谓“音乐”的概念,以此来解读“对局外人是音乐、但对局内人却不是音乐”的仪式表演。⑤蔡宗德:《音乐与宗教》,《艺术欣赏》,2005年第1期。这种“类音乐”既包括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形式,也包括宗教仪式中的唱诵等非音乐性的声音。由于民族音乐学是“对音乐与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共生关系”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要更加合理地界定“仪式音乐”必须考虑“局内人”和“局外人”在认识上的差异问题。孟凡玉教授在界定“仪式音乐”时采用狭义和广义两种认识,这是在原有仪式音乐认知的基础上的一种丰富。狭义的“仪式音乐”是指应用于仪式之中、伴随仪式程序而存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广义角度的“仪式音乐”可以包含能够听到的和听不到的一切音响、曹本冶先生用“音声”概念加以指称,其中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也包括各种非音乐的声音、甚至还包括想象之中的音乐、声音。⑥孟凡玉:《民间仪式音乐与乡土社会秩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第17页。可见,孟氏所谓的广义的“仪式音乐”的概念和曹氏“音声”概念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有学者将仪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类体裁,从教学需要将仪式音乐理解为“在特定典礼的程序中运用的音乐”,并主要指“在我国宗教仪式(如佛教仪式、道教仪式等)、民间仪式(如祭祀仪式、敬神仪式、婚丧仪式等)中,因特定的典礼程序而运用的,与其特定信仰有关的音乐。”①蔡际洲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9年,第124页。
关于仪式中“听不到”的音声,萧梅教授以广西靖西“魔仪”中的“默声”述之,认为“默声”在信仰仪式中普遍存在,它不仅对信仰者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认同和能量的含义,也是信仰“现声”的特别形式,甚至孕育着仪式之力量。对于这类靠“心听”的“默声”如何辨识和解释,她引用“体验的音声民族志”的方法,期望用有形的言说转述无形的默声。②萧梅:《体验的音声民族志:以音声声谱中“默声”的觉察为例》,载曹本冶主编:《大音》(第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 51-75 页。其实,笔者在赣南考察“跳觋”仪式时,也观察到仪式在“藏禁”环节时执仪人与装有花童象征之物的“陶罐”之间的“心诵对话”,即属于这类“听不见”的音声。对于执仪人来说,这是整个“跳觋”仪式的关键环节,执事是否“灵验”,完全取决于作为“觋”的执仪人如何以“无声”的力量来传达神灵的“旨意”。应该说,不论“听得见”与“听不见”的声音,都是仪式展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氏“仪式音声”概念的提出,对于仪式音乐研究理论具有重大突破,作为仪式音乐研究的核心概念,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仪式音乐研究中已广泛使用。
应该说,“音声”概念在仪式音乐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典范式意义,据笔者研读的有关仪式音乐研究的著述中,“音声”一词引用率最频繁,其缘由在于“音声”打破了“音乐与非音乐”之间的界限,成为“仪式缘何现声音”最佳的阐释方式。正如有学者指出:“音声”的概念调和了作为“局外人”的仪式观察者和作为“局内人”的执仪者和参与者对“音乐”所持有不同概念的矛盾,同时将“音声”覆盖于整个仪式境域之中,打破语言与音乐两者之间的分界,将仪式中的所有的“器声”“人声”“默声”等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来考察。③李萍:《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研究综述》,载曹本冶主编:《大音》(第3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46页。
其实,相对于音乐学界,民俗学界对民间信仰和民间仪式的研究更早、成果也更多,且大部分成果都涉及音乐方面。关于“仪式音乐”的表述,姜彬先生在研究吴越地区的民间信仰与仪式时以“仪式歌”称之,“仪式歌源远流长,可以说是人类诗歌史上最古老的歌了。它脱胎于原始巫术与原始宗教,并随着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和变化。它与民间习俗相融合,广泛渗透到民间生活的众多领域。它是民间信仰的产物,又带有民间创作的文艺特色。”④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这种表述形式在民俗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礼俗歌”“风俗歌”等称谓可见一斑。
仪式音乐作为一个研究范畴,统摄仪式中出现的一切声音。不同的研究者因仪式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阐释,综上各种有关“仪式音乐”的界定与解读,曹本冶先生提出的“音声”和“音声境域”概念尽管还有其待完善之处,但对当下仪式音乐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张振涛认为:“‘音声境域’的提出是完善仪式架构、拓展范畴的基础概念;……从历史层面拓宽了一般意义上的音声或者现代音乐家观念中对音声的认识。‘音声境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视角,从中存在音乐学与民俗学、音乐理论与历史真实深刻结缘和良性互动的机缘。其理论意义在于让中国音乐学家从西方概念、西方阴影中走了出来,回到了真实的本土”。⑤张振涛:《噪音:力度和深度》,载曹本冶主编:《大音》(第5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3-23页。他表达了仪式音乐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创见。
二、仪式音乐的分类研究
由于民间仪式的复杂多样导致其仪式音乐也纷繁复杂,且种类繁多,仪式研究者对仪式音乐的分类也因分类标准、分类体系的差异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已呈现多角度、多层面的仪式音乐分类的局面,这些分类对于仪式音乐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在学界,杨荫浏先生是仪式音乐的先行者,主要集中在宗教仪式音乐领域,并开创了仪式音乐研究的“音乐范式”(孟凡玉语)。之后,仪式音乐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仪式音乐和宫廷仪式音乐方面,而对于众多的民间祭祀仪式研究则是近二十余年逐步累积而成。因此,仪式音乐分类也体现了研究的广度及深度。早在1998年,甘绍成教授将仪式音乐按使用群落划分为“宫廷仪式音乐、宗教仪式音乐和民间仪式音乐”三大类。①甘绍成:《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存在的问题——兼谈仪式音乐研究的范围及方法》,《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乔建中研究员曾将民间仪式音乐依照音乐与仪式关系的松散或紧密、功能或非功能、对应或非对应,分为两大类:一为对应的、功能性的、紧密的,即“专曲专用”型;二为非对应、非功能性的、松散的,即“一曲多用”型。②乔建中:《中国华东地区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综述》,载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上),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第 55页。
近年来,孟凡玉教授对仪式音乐作了全方位、多层面的分类研究。他采用了四种分类标准形成四种结论。一是基于音乐自身内容和形式,仪式音乐可以分为仪式声乐和仪式器乐两大类;二是联系仪式背景及音乐实际功用,它可分为“声响性仪式音乐、场景性仪式音乐、信号性仪式音乐、介质性仪式音乐、符号性仪式音乐”五种形式;三是基于“五礼”视角,依据仪式性质将仪式音乐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形式;四是基于当代人类学视角,依据仪式的主客体对象将仪式音乐分为“人生秩序、自然秩序、鬼神秩序、社会秩序、综合秩序”五种形式。③孟凡玉:《民间仪式音乐与乡土社会秩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第94-129页。以上分类形式对于仪式音乐研究提供了新的分类可能性,可供建构仪式音乐分类体系作参考。
长期以来,人类学的仪式研究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解读与诠释,对仪式分类也趋细化和个性化。它们突破了涂尔干式的“积极/消极或神圣/世俗”二分模式、常见的“工具性仪式/表述性仪式”二分法、特纳的“生命危机/减灾仪式”二分法等仪式分类形式,形成一种多元化认识,如贝尔的六分法模式等,体现了新的社会价值和学术理念以及学者的不同视角。仪式音乐分类的多样化特征与仪式分类基本属于互文状态,也融合了音乐学者对仪式中音声的认知。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三、仪式音乐民族志研究
一般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学科的标志,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民族志既是人类学者对他文化的具体描述,也是基于田野调查的一种方法。换言之,音乐民族志也是音乐学者关于他者的田野考察报告、也可视为一种从田野观察到案头写作的思考过程。音乐民族志对音乐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杨民康、萧梅、刘桂腾、杨殿斛、杨曦帆等学者从理论、方法和实践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科学详细的阐述,成为学科发展史上的基石。音乐民族志方法在仪式音乐研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在界定什么是仪式音乐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采用什么方法对仪式及其音乐展开研究的问题,民族志作为“不同文化群的志”,对于仪式个案的描述与探究,自然成为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已出版并具代表性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华南卷、华中卷、东北卷等)、《大音》(共15卷)以及诸多仪式研究的硕博论文,都是在田野考察基础上形成的仪式音乐民族志文本。
常言道,没有理论与方法的资料堆积不是民族志。音乐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研究中书写音乐文化的样式之一,也有学者将二者视为两种研究趋向,音乐民族志侧重于常规方法及实践性研究,而音乐人类学侧重于文化哲学观及理论性探索。不过,关于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学者们趋向于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的论述:“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阐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历史;而音乐民族志则是如实记录对人群音乐的认识,它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演绎,而只需要假定对音乐进行描写是可能的和值得的。”④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4页。这一观点有效区分了二者的异同,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书写音乐文化的模式,前者侧重书斋,后者侧重田野。时至今日,随着民族志的观念的变化,当下的实验民族志已进入“深描”或阐释的时代。音乐民族志已融入新的理念,借鉴文化人类学的学术思维,开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尤其是仪式音乐)的研究思路。纵观仪式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
它是由杨民康研究员在已有的音乐分析观念及方法论体系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经历了提出观点(2008)、阐述内容(2012)、形成体系(2021)三个阶段。 作者指出:“‘音乐文化本位模式’是根据前辈学者所谓的‘文化本位法’原理提出来的方法论概念,主要涉及了现代民族音乐学时期以来,由许多民族音乐学者运用‘深层结构—表层结构’‘主位—客位’‘历史—社会—个体’以及‘观念—行为—音声’等文化或音乐研究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以活态的‘音乐文化活动文本’及‘音乐表演文本’为主要分析范围,以内文化持有者自身(主位)观念为观察对象和出发点,并在分析过程中注重采纳‘音乐模式—模式变体’和‘对文化持有者阐释的再阐释’等分析思维和手段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方法。”①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传统音乐研究的范式与分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167页。按照杨氏的分析思路,该体系还涉及“减幅—模式”“增幅—变体”和“减幅—增幅:模式与变体”三类基本分析模型。从理论上,该模式可以运用于各种不同的音乐分析中,尤其是仪式音乐研究与它有着天然的适应性和嵌合性关系。在当下的仪式音乐民族志书写类型中,杨氏认为主要有以侧重“观念—行为—认知”和“方法—分析—产品”两种不同的分析思路。
(二)由“体验/感觉—表演”的音乐民族志书写
随着田野考察(觉察)的逐步打开,一个个仪式个案展现的音声境域让“局外人”有时无所适从。面对音乐与文化的叙事去言说无形的声音,萧梅教授认为,体验会是一种尝试的出路,从而提出“体验的音声民族志”。她在研究魔仪中的“默声”时感受到,身体感在音乐构成、音乐接受、音乐分析中始终贯连,以身体和身体行为为基础是仪式研究的重要观念。因为,仪式是“具身的”,并非是执仪者单一表述的本文提取,其研究不仅仅是将仪式行为知识化的符号学,……不能剥夺展示过程中的各种感觉和情绪状态,应去把握一个完整的“心之境域”。②萧梅:《体验的音声民族志:以音声声谱中“默声”的觉察为例》,载曹本冶主编:《大音》(第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 51-75 页。2010年,萧梅教授以四个音乐故事的感触“从感觉开始”再次论述“体验的音声民族志”,③萧梅:《从感觉开始——再谈体验的音乐民族志》,《音乐艺术》2010年第2期。论及如何在田野的情境中,以“缘身性”的实践本体论表现普遍意义的人性与特殊意义上“他者”间多种互译的关系。之后,在经历多次田野觉察和理论思考后,2019年,她提出“音乐表演民族志”,④萧梅,李亚:《音乐表演民族志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音乐》2019年第3期。完成从“体验/感觉—表演”的音乐民族志书写模式。它强调音乐“体验”的描写与表述,将“自我身心”投掷于世界是音乐表演民族志写作的出发点。杨民康研究员在论述“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时也有明确界定:“以仪式化音乐表演为对象和路径,借以观察和揭示人们在其音乐表演活动中如何经由和利用音乐表演行为,将观念性音乐表演模式转化为音声表象的过程和结局,并辅以必要的阐释性分析和文化反思。”⑤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一种从艺术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民族艺术》2016年第6期。这两种观点都是人类学“实验民族志”中强调“双主体”格局的表现,前者强调以胡德式“双重音乐能力”的介入,以研究者“自我融入”表演主体中而获得的无限接近“局内人”的操演行为和表述方式,得出音乐表演民族志文本;后者主张以“参与观察”介入,借鉴阐释人类学方法,对表演事项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与分析,而形成音乐表演民族志文本。总之,音乐表演民族志是从“以乐谱文本为中心”的静态式分析研究到“以动态表演为中心”全方位的民族志分析范式的转型,强调音乐表演语境中的文化持有者、表演者、参与者、观众以及学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这种民族志书写范式得到新生代民族音乐学者的采纳。
(三)“声音建造—听觉感受”双向研究模式
齐琨教授在思考如何以声音景观的研究方法观照仪式中的音乐与非音乐的声音而提出,强调在音乐民族志写作中对音乐感受—音乐聆听,进行记述和阐释的重要性。她指出:“作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和音乐民族志的撰写者,需要从声音的生产、制造、集成、运作——建造者出发,可以探讨建造者对声音的编码方式,选择建造不同声音编码的原因,建造者以声音作为社会阶层标志的愿望等;也需要从声音的感受者——聆听者出发,可以探讨听者感受声音的方式,选择声音的原因,聆听者以声音作为社会阶层标志的现象等。因此,以声音作为研究媒介,可以联结声音建造者和声音感受者,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包含理性分析和感性体验之双重内容。”①齐琨:《“声音建造—听觉感受”双向研究模式》,《音乐研究》2020年第6期。这种模式还需强调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声音与听觉两个方面的不可或缺;二是从声音到听觉和从听觉到声音的双向路径;三是在声音建造和听觉感受过程中人对声音的主观选择。(其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声音建造—听觉感受”双向研究模式
齐琨教授在历史民族音乐学、仪式中音声、声音如何表述等方面有很多真知灼见,提出“声音建造—听觉感受”双向研究法目的是寻找民族音乐学与声音景观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契合点。这是她自提出“灵验的音声(2008)、仪式空间表演(2010)、仪式音声表述(2011-2016)、文献表述模式分析(2019)、文献叠写分析(2019)”等学术概念后,又一次跨学科对民族音乐学及音乐民族志作出的学术创见,对于仪式音乐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后现代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后,阐释人类学开始反思传统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并脱离科学民族志的束缚而开辟新的方向,由重在客体转为重在主体,摆脱了所谓“科学性”而进行主体解释性的意义探求。笔者认为,在国内人类学界,具有典型意义的后现代民族志以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关于“对蹠人”系列研究为代表。他提出“主体民族志”模式,采用“裸呈”的表述方式,其基本要义是“让他们自己说”。②朱炳祥:《他者的表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3页。对于这类后现代思维的民族志,有学者将其表述为“自我民族志”(蒋逸民、徐新建等)。后现代民族志不论如何表述,都是基于阐释人类学背景下的“深描”,从传统民族志走向以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的,并对研究者亲身经历和观念进行学术反思的一种书写模式,它要求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只能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而非引导者、提问者。反观国内民族音乐学,有关后现代音乐民族志研究成果才刚起步,虽有管建华、宋瑾等学者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影响,但具体的民族志研究由于受到经典民族志模式的影响而鲜有成果。上文提到的“音乐表演”“双向模式”虽有后现代音乐民族志的思维,并未完全摆脱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将“人”这个创作主体为中心。总体来说,后现代音乐民族志是一种多方合作而发展的综合性文本,是不同话语和语境的审美整合。在这方面,杨红、赵书峰等学者的“路文化”音乐研究具有代表性。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学者对仪式音乐民族志作出了探讨。刘桂腾教授倡导人类学式的“定点民族志”,③刘桂腾:《以身试法:定点·追踪·个案——田野实践中的音乐民族志方法》,《中国音乐》2017年第1期。认为“参与观察”依然是民族志理论框架的脊柱,理想的音乐民族志作业应该搭建起通向他者的桥梁,在对他者音乐文化的呈现中,使同具本己文化背景的人理解异己文化并树立多元文化价值观。苗金海博士提出的“全息式”仪式音乐民族志,④苗金海:《书写“全息式”仪式音乐民族志——鄂温克族敖包祭祀仪式音乐研究反思》,《民族艺术》2018年第6期。倡导在仪式过程实录的描述文本与深描书写中,除了通过视觉和听觉感知到的信息,还要尽可能多的收录,补充观察者通过嗅觉、味觉、肤觉捕捉到的重要信息。在仪式音乐研究中,“影像音乐民族志”“微信(网络)民族志”也正在兴起。
四、仪式中音声研究是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方案”
仪式本是人类学与宗教学研究的主阵地。而仪式音声的研究却是民族音乐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且形成了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术热点。回望中国仪式音乐研究历程,杨荫浏先生对无锡和苏州道教中的吹打乐所进行的锣鼓谱的整理,开启仪式音乐研究之先声。近二十年来,仪式中音声研究形成有学术组织、有理论范式、有研究队伍、有研究成果的持续发展局面。
在学术组织方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已成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平台,为世界民族音乐学提供了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
在理论范式方面,主要有曹本冶教授首创“音声”概念,提炼“信仰—仪式行为—仪式音声”的“三元论”模式;薛艺兵研究员对“仪式的内涵、仪式音乐的界定、仪式音乐的功能与特征”等方面的阐述;萧梅教授提出“仪式音声是信仰存在的一种方式”旨在以音声作为理解信仰仪式的整体性实践;杨民康研究员从“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角度,以仪式化音乐表演为对象和路径,借以观察仪式表演行为,将观念性的音乐文化深层模式转化为音声表象的过程和结局并作必要的阐释性分析和文化反思;齐琨教授提出“空间是仪式音乐分析的一个维度”,将空间从物质、关系和意识三个层面建构仪式音声的描述与分析,从而关注局内人通过音乐风格、音乐行为、音乐意义建构的有形与无形空间;项阳研究员从“民间礼俗”角度探讨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空间,强调借助“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方法、强调“接通”意识去认知在礼乐文明制度下,中国音乐文化中的音声技艺样态;刘桂腾教授从“地方性叙述”的音乐人类学角度,聚焦使用“单面鼓”为共同特征的中国萨满音乐文化研究,成为世界萨满音乐研究的“中国样板”(《鼓语》2019)。他们都为仪式音乐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与智力支持。
研究队伍方面,在学术群体的薪火传承中,涌现了以曹本冶、萧梅、薛艺兵、刘红、杨民康、齐琨、刘桂腾、钟思第(英)、周凯模、孟凡玉、赵书峰、杨玉成、杨红、魏育琨、邓光华、胡晓东等一批学者为代表,也取得了载入史册的重大成就。
在研究成果上,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道教等宗教仪式、民间祭祀仪式领域,主要成果有: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华南卷、西北卷、东北卷、华中卷;《大音》十五卷;瑶族等少数民族仪式研究;大量的民间祭祀仪式个案研究以及数量可观的硕博论文。
值得肯定的是,仪式中音声研究将随着仪式学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出现新的研究理论与范式,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即通过分析思想行为的互动关系,而达到对人类的认知。中国话语体系的仪式学将为仪式音声研究打开视野、提供语境,但在民族音乐学体系下的仪式音声研究必须明确“文本—语境—表演”的关系,有选择地借鉴仪式学理论,最终回归“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之主体,关注音声对仪式表演的有效性、关注音声在仪式整体中的功能及象征意义,以此回答“人是如何制作或创造音乐”的终极问题。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