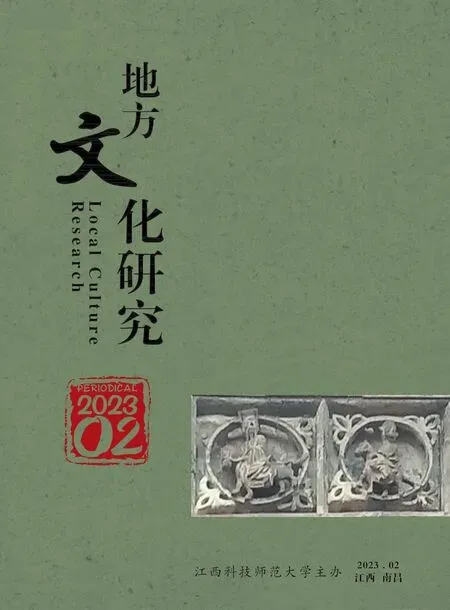三星堆青铜文明特色与影响
黄剑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 成都,610041)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主要特点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界曾有过多次重大考古发现,从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上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更是举世瞩目,成了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一道最绚丽的光彩。
众所周知,古蜀的历史因为缺少文献记载,而被长期笼罩在传说的迷雾之中。譬如,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记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事迹都极其简略。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揭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面纱,从此以后再也不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蚕丛和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叹,终于被考古发现的巨大惊喜所取代。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数量的庞大,种类的繁多,文化内涵的无比丰富,以及其展示的鲜明而自成体系的地域文明特色,都是罕见的。湮没数千年之久的古蜀青铜文明,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竟然是如此灿烂辉煌。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
三星堆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造像群。先民们铸造这些青铜造像群,显然不是简单的游戏之作,而是表达了古代蜀人丰富多彩的意识观念和传统习俗,具有强烈而浓郁的象征意义,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我们知道,黄河流域夏商周时代的帝王贵族们是用青铜礼器,特别是九鼎来象征统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青铜礼器在器铭中通常称为彝、尊,据《说文解字》解释,大都为常设于宗庙中的祭器。在中国奴隶制时代,祭祀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殷商王朝祭祀上帝和鬼神,以及祭祀祖先,视为贵族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与中原殷商时间大致相同的三星堆古蜀王国,祭祀活动同样盛行,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内容,而且同样祭祀鬼神,祭祀祖先。但在祭祀方式以及神权与王权的象征表现方面,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三星堆也出土有青铜器物,如铜尊和铜罍,但数量不多,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铸造精美数量众多的青铜人像。这些翔实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古蜀王国显然不是依赖和利用青铜礼器来维护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而是精心铸造了大量代表大巫(蜀王)和群巫(各部族首领)以及神灵偶像的青铜造像,并赋予这些生动逼真的造像以丰富的象征含义,供奉于宗庙或神庙之中,或陈设于祭台之上,进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古蜀王国统治阶层所控制的神权与王权便正是通过这些青铜人物造像群而强烈地显示出来,而这显然也正是古蜀王国维护等级制度和有效统治各部族的奥妙所在。
三星堆古蜀王国用青铜造像群作为祭祀活动和日常供奉的主体,中原殷商王朝用青铜彝器作为等级象征与祭祀供奉的宗庙常器,这应是古蜀文化和商文化最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祭祀形式上,而且也反映在祭祀内容上,以及祭祀活动进行的过程中。若从深层分析,这也充分展现了古蜀王国与殷商王朝在国家体制、统治形式、政权性质、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差异。早期的古蜀社会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政治局面的出现。从三星堆考古发现提供的大量资料来看,古蜀王国也已形成明显的阶级分化。权力和财富都为统治阶层所控制,但其社会形态与制度则与殷商王朝有所不同,很可能正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实施的是“共主制”或“酋邦制”。由此可知,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强盛的王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自成体系。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与文化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和相互影响。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充分显示了古代蜀人在青铜造型艺术方面的独创性,展现了杰出的才智和高超的技艺,具有浓郁的古蜀特色。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将军盔”,是熔铜用的坩埚,这种容积不大的坩埚,在熔化铜液和浇铸大型青铜造像和青铜器物时,需要很多技术熟练的工匠一起操作互相配合同时进行才行。这说明古蜀国当时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还有采矿、运输、后勤人员与之协作,提供保障,可见当时的手工行业已有明确的分工和完善的管理。无论从冶金水平或是从制作技术上看,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同一时期的殷商文明青铜器处在共同的水平线上,相比毫不逊色,并显示出了自身的鲜明特点。显而易见,古蜀王国也是中国冶金术起源最早并成功发展的若干个中心之一。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与玉器,也显示了古蜀与殷商在文化内涵方面的差异。殷商王朝日常的巫术活动主要是占卜,从文献记载看,殷商王朝已设有掌占卜之官,如《周礼·春官》中就记载了负责祭祀与占卜的各项官职。甲骨文中最常见的掌占卜的官是贞人,从武丁到帝辛(纣王)时,据统计有120个左右。古蜀王国就不一样了,考古发现很少有占卜的材料,而象征大巫和群巫主持的祭祀活动则占据着主导地位。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石器,其使用方式和象征含义,也有着古蜀王国自己的浓郁特色,与殷商王朝的礼制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琮和牙璋之类,在祭祀活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和青铜人物造像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青铜人物造像群在祭祀活动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玉石器则是从属性的器物。金杖也一样,它可能是权力的象征,也可能是祭祀用的法器,如同有些学者们所解释的,但它也是从属于青铜人物造像群的器物。金杖上的人头像,二号坑出土一件玉璋上的人物图案,都展现了人物造像这一主题。玉璋上的几组人物图案,更是生动地表现了巫师祭祀的场景,洋溢着浓郁的古蜀文化特色。
青铜人物造像群在三星堆古蜀文化中占据着突出而重要的主导地位,这不仅说明了古代蜀人对人物造像的偏爱,也显示了他们特别擅长于形象思维,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还为我们研究古代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揭示了古蜀王国是由蜀族和其他结盟部族构成的共同体,在信仰观念和祭祀方式上都与众不同独具特色。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表现的是以蜀族为主体的多部族形象,应是无庸置疑的。蜀族是古代蜀国的主体民族,而在蜀国的范围内还应包括和蜀族结盟的其他兄弟民族。蜀王是蜀国的最高统治者,而在蜀国的统治阶层中,自然也包括其他结盟部族的首领。所以古代蜀国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时候,既有华贵显赫群巫之长(蜀王),又有威武轩昂的群巫(各部族首领),还有蜀族和各部族共同崇拜信仰的神灵象征。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所表现的,便是这样一个生动精彩的场景。
概括起来说,作为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源远流长,高度发达;二是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三是在南方文化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四是和中原文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汇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五是展现出百科全书式的丰厚文化内涵,特别是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值得强调的是,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反映出当时的古蜀王国已拥有高超复杂的制造技术和繁荣强大的生产能力。三星堆青铜造像群还反映了古代蜀人独特的审美心理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的辉煌杰作,也在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在世界雕塑史上,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等,在雕塑艺术方面都有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也正是由于古希腊和古埃及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的绚丽景观,而使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等世界东方国家在人物雕像方面的成就,甚至认为中国古代雕塑主要表现在器物装饰上。自从有了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的考古发现,则有力地纠正了这一偏见,说明古老的中国同样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铸造出了大量神奇精美的千古杰作。
二、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中原的交流
由于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文化观念的影响,自上古以来即盛行中原诸夏王朝为正统,很长时期都将中原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丰富资料日益增多,中华文明起源呈现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格局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三星堆考古发现便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提供了重要佐证,揭示了古蜀国就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四川盆地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自成一系的古文化,而且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已有了既同中原夏商文化有明显联系,又独具特征、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载于《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44页。
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蜀文明具有自成一系的鲜明特色,与中原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或差异,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观念习俗、宗族或部族构成、社会生活、艺术情趣等诸多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中原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使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具特色。古蜀文明作为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虽然与中原文明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文献记载或是从考古资料看,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密切关系,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都是源远流长的。
上古时期已有黄帝和蜀山氏联姻的记述,夏禹治水曾多次往返于岷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尚书·禹贡》对此有较多的记载,有学者提出了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见解。考古资料也揭示了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所出器物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譬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同二里头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又如陶豆,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还有三星堆出土的“将军盔”,即熔铜的坩锅,其形状同殷墟第一期的非常相似。这些都说明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源远流长,与夏商关系十分密切。
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中期与晚期,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既有典型的蜀文化特征的青铜造像群,又有来自中原的一些青铜尊与青铜罍,还有来自温暖海域的大量海贝,充分说明了殷商时期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同时也揭示了古蜀与中原的联系,以及古蜀和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商周之际,古蜀曾出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②《尚书正义·周书·牧誓》,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1980年9月第1版,第183页。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其中的蜀国由于疆域的辽阔和物产的丰富,其势力显然是当时西南众多部族中最为强盛的。《战国策·秦策一》就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①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3版,第91页。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如果说陶盉陶豆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那么铜尊铜罍则显示出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二是这种文化传播和交流在殷商时期变得更加密切了。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盉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
古蜀与中原的关系,特别是古蜀王国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从文献记载看,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897页。孔子所述,见《论语·述而篇》。关于老彭,《世本》中有“在商为藏史”之说,《大戴礼记》卷九亦有“商老彭”之称。顾颉刚先生指出:“老彭是蜀人而仕于商,可以推想蜀人在商朝做官的一定不止他一个。古代的史官是知识的总汇,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应当都懂。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古书里提到蜀和商发生关系的,似乎只有《华阳国志》这一句话。可是近来就不然了。自从甲骨文出土,人们见到了商代的最正确的史料,在这里边不但发见了‘蜀’字,而且发见了商和蜀的关系。”③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19页,第31页。除了殷墟卜辞中有许多蜀的记述,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中也有蜀字。文献史料还记载,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叫苌弘的蜀人,担任过周室的史官,博学多才,也很有名。《左传》从昭公十一年到哀公三年就有很多关于苌弘为周大夫的记述。孔子于周敬王二年(前518)来到成周,恭敬地拜访了苌弘,向苌弘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司马迁《史记·乐书》对此就做了记载。④司马迁:《史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1228页。《孔子家语·观周》亦载:孔子“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⑤见《百子全书》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7页。韩愈《师说》中曾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⑥见《全唐文》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2500页。可见,苌弘为孔子之师,已成为后来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典故。蜀人苌弘在春秋时期做周朝的史官,连孔子都要向博学多才的苌弘请教,也说明当时蜀地文化的繁荣,才能涌现苌弘这样的人物。这些史料记载,都说明了蜀地与中原在商周春秋时期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
考古发现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印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等形制,玉石器中的璋、戈等形制,都显示出对商文化的模仿,反映了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说明了这是古蜀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三星堆出土器物告诉我们,在接受商文化影响的时候,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应是我们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三星堆古蜀青铜文明和中原殷商青铜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关键所在。
三星堆古蜀青铜文明与中原青铜殷商文明之间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而顺长江上下则是一条主要途径。徐中舒先生认为:“古代四川的交通有栈道和索桥,并不如想象的困难,而且长江由三峡顺流东下,更不能限制习惯于水居民族的来往”。考古出土资料显示:“从黑陶遗物陶鬹、陶豆出土地址的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上下的。”⑦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5页。李学勤先生也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①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看,和湖北、湖南所出类同,也是很好的证据。来自于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曾对南方地区进行了较为强势的传播,在安徽、湖南、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青铜罍,就展现了商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牛首尊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尊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龙虎尊

安徽阜南出土的铜尊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罍

湖南岳阳出土的铜罍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北经汉中之地或通过陇蜀之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西周初武王伐纣,联合西土八国会师牧野,古蜀国人马就是由这条途径参与征伐行动的。在开明王朝开凿石牛道之前,古蜀国北面的交通显然早就存在了,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都为此提供了印证。扬雄《蜀王本纪》中有“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的记述,②《全汉文》卷53,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1958年12月第1版,第414页。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也是对这种交通情形的一个说明。《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杜宇时期“以褒斜为前门”,开明三世卢帝“攻秦至雍”。褒斜即褒谷与斜谷,在汉中之北的秦岭山脉,雍城则在秦岭之北的宝鸡,③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96页。或说在今陕西凤翔县南,④见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86页注文。都说明了古蜀国北面的交通状况。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有学者认为:“是时雍蜀之间已有商业之发展。下至石牛道之开凿,以蜀绕资用,南御滇僰,西近邛笮,栈道千里,无所不通。”⑤邓少琴:《巴蜀史迹探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56页。从考古发现看,陕南城固出土的铜器物群中,既有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如鼎、尊、罍、瓿、簋、戈、钺等;又有属于早蜀文化的器物,如青铜面具、铺首形器,以及陶器中的尖底罐等。这也说明殷商时期陕南是商与蜀接壤,两种文化交错共存的边缘地区。三星堆出土的铜罍与城固出土的铜罍在器形和纹饰上都相似,显然便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果。在陕西宝鸡地区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处发掘出土的一批西周时期国墓地,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文化面貌,也是很好的例证。⑥参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上册第6页,下册彩版二三。值得注意的是,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青铜人,那夸张的握成环形的巨大双手,完全继承了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双手造型的风格;也充分说明古蜀青铜文明在与殷商青铜文明接壤的地方产生了重要影响,留下了富于古蜀青铜文明特色的遗存。

宝鸡茹家庄 国墓地出土的小型青铜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兽首冠青铜人像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模仿商文化的礼器,数量较少,只有龙虎尊、羊首牺尊、铜瓿、铜盘等。二号坑出土的礼器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增多,据发掘报告介绍有圆尊8件、圆尊残片3件、方尊残片1件、圆罍5件、圆罍残片2件、方罍1件等。据一些学者研究,一号坑相当殷墟早期,二号坑相当殷墟晚期。显而易见,随着历史的发展,古蜀青铜文明与殷商青铜文明的交流也比以前增多了。如果我们再结合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物来看,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强烈了。这显示的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统发展的历史趋势。古蜀青铜文明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趋势中间,逐渐融合到了全国统一的文明进程中去。但在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明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显示出其国势足以与中原殷商王朝相抗衡,是相对独立同时又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与经济方面的交流往来,是分属于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文明中心。
总之,古蜀王国与殷商王朝的关系和文化交流,应该给予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认识。古蜀青铜文明接受殷商青铜文明的影响,主要来自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长江中游以及陕南地区。殷商王朝崇尚礼容器,发展出一套繁复的系统,在全世界青铜文明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古蜀王国也同样重视青铜,同样有礼容器,可是礼容器在整个资源运用系统的角色中只扮演次要的角色而已。正是三星堆青铜文明与殷商青铜文明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展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随着相互间的交流融合,从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青铜时代杰出而又辉煌的篇章。
三、三星堆青铜文明对滇文化的影响
上古以来,我国西南地区就部族众多,是世界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将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统称之为西南夷,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又说“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①司马迁:《史记》第9册,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1版,第2991页。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对此也有相同记述,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作了相似记载。
古蜀可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②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75-176页。从出土资料看,蜀人确实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古蜀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古蜀经历了夏商周的发展演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古蜀王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也都是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将汉晋时期的夷越之地称为南中,也记述当时仍是“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③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335页。应该是一种比较真实的情形。蜀与滇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古蜀王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王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经过远程贸易还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王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
通常认为,汉代所谓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族属上包括夷、越、蛮三大系统。例如将氐羌系称为“夷”,将百越系(包括濮或僚)称为“越”,将南蛮系苗瑶语族称为“蛮”。总体来看,整个西南夷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滞后。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记述可知,滇国因为当地有滇池而得名,滇池区域也就是滇国的主要聚居区。滇和昆明都是云南古代的主要部落聚居之邦,历史虽久,势力范围则有限,对周边的影响不大,在西南夷地区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受到了中原王朝的注意。同巴、蜀、楚相比,滇确实是一个弱小之邦,僻居一隅,地沃人稀,邑聚而耕,很容易遭到强邻的侵入。在汉代之前,滇国就曾遭到楚国的入侵并被攻占。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楚国曾派庄蹻率领军队扩张疆域,向西南进兵略取巴国、黔中以西的地区,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占领了滇国。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对这段历史也有记述,《太平御览》卷一六六与卷七七一,以及南宋叶梦得《玉涧杂书》也都引用了常璩的记载。我们由此可知,庄蹻不仅占据了滇池周围地区,也占据了夜郎,建立的统治包括了云南与贵州一带。文献记载说庄蹻王滇时,“变服,从其俗”,说明了庄蹻的入乡随俗、以便同滇国少数民族和谐相处,有利于加强统治。随着庄蹻军队的侵入和长期驻守于滇,也带来了楚文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为滇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与之相应的是,来自中原与巴蜀的文化也进入了滇国,对滇文化与西南夷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蜀与滇的关系,相互之间很早就有了交往。文献记载杜宇是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的蜀王,就与来自云南朱提(今昭通)的梁氏女利联姻,壮大了力量,从而称雄于西南地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①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82页。常璩说的南中就是云南,可见望帝杜宇的蜀国疆域是包括了云南很多地方在内的,说明古蜀王国的统治与影响已经由朱提而扩大到了南中地区。殷商时期的古蜀王国已经有了灿烂的青铜文明,从铜矿的开采和青铜的冶炼都已形成了规模,青铜铸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朱提(今云南昭通)是铜矿蕴藏富足之地,朱提以西的金沙江流域也有大量铜矿,古蜀王国的青铜来源可能有多处,其中之一也可能来自于朱提或金沙江流域,将开采的铜矿辗转运输到了蜀国都城,然后再开炉冶炼铸造的。这也说明了古蜀王国与南中关系的密切。
古蜀王国对黄金的开采利用也很重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有金杖、金虎、金面罩、金璋、金鱼、金叶、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等种类较多的金器,有的还刻有神奇绝妙的图案纹饰,说明当时黄金的制作工艺已相当高超。《华阳国志·蜀志》有蜀地产金的记述,但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并不产金,产金的地方主要在四川盆地周边的丘陵河谷与西部高原以及金沙江沿岸地区。按照《天工开物》中的说法:“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难于枚举。”又说“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水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古名丽水),此水源出吐蕃,绕流丽江府,至于北胜州,回环五百余里,出金者有数截。又川北潼川等州与湖广沅陵、溆浦等,皆于江沙水中,淘沃取金。”②宋应星:《天工开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第1版,第336页、337页。由此可知,古蜀王国南面的金沙江,川北的嘉陵江、涪江等外都是产金之地。关于金沙江产金,《韩非子·内储说上》已有记叙:“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又设防禁遮拥,令人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③韩非:《韩非子·内储说上》,见《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1150页。这段记载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对丽水产金的严格控制,从中也透露出金沙江流域黄金产量的丰富。通过考古发现,并参照古籍记载可知,金沙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古代蜀人采集黄金的地点之一,很可能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就有古蜀先民于此采金了。古代蜀人在金沙江流域采金的历史,明显是要早于楚人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金器在时间上比楚国出土的金币与黄金制品要早数百年,就是显著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庄蹻的政权已控制了丽水,当时的蜀国为了继续获得黄金,是否与之发生过争夺尚不得而知,但“窃金不止”者很可能既有当地人,也有蜀人。
我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是著名的半月牙型文化传播带,童恩正先生曾指出:“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所处的环境也是很有特点的。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即中国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方向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就使四川自古就有众多的民族迁徙栖息,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①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3页。徐中舒先生也说:“古中国西部人民为适应高山峻岭与横断山脉的环境而创制了栈道和索桥”,这种“开辟道路,向外发展”的做法,早在战国之前就开始了。②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页。西南民族走廊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的原因,与古蜀和氐羌的迁徙活动也大有关系。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源流处与河湟区域,远古时期生态良好,曾是古羌的栖息繁衍之地,后来古羌的若干分支向南迁徙,便是经由横断山脉和川滇之间的民族走廊进行的。古蜀和古代氐羌的关系非常密切,都曾栖居于岷江上游,都有石棺葬之俗。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③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81页。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即与古代氐羌和蚕丛氏蜀人有关。石棺葬与大石墓在安宁河流域和云南的滇中与滇西北等地也有分布,这种葬俗很显然来自于古蜀和古代氐羌,是沿着民族走廊迁徙带来的。考古发现揭示,石棺葬与大石墓的年代跨度较长,大约从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延续至汉晋时代依然流行。
从云南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据李昆声先生介绍:“根据近半个世纪的考古资料,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为4种类型: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和红河流域地区”,“根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布在全省70多个市县,共约200多个地点,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在万件以上。”④李昆声:《云南艺术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51-61页。云南的青铜时代起始于商代晚期,结束于西汉晚期,绵延约千余年。考古界大多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云南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其考古学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或商周之际。之后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出土有春秋时期的早期铜鼓,出土青铜器最多的是在滇池区域,其时代大约从战国延续至汉代。就现有考古资料看,滇池区域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大体东至宜良、路南一带,南到新平、元江,北抵曲靖、东川,西达陆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是晋宁石寨山滇国墓,从1955年至1960年先后4次发掘50座墓葬,出土器物达四千余件,1995年对石寨山进行了第5次清理,共清理了36座墓葬,出土了五百多件文物。1956年在石寨山六号墓中发现金印一方,刻有篆书“滇王之印”四字,这和《史记》所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在云南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史实相合,可见滇池区域出土的这些青铜器,确系滇人的遗物。⑤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376页。江川李家山也发现有数量众多的滇人墓葬,1972年发掘了27座墓葬,1991年发掘了59座墓葬,截止2000年共发掘了86座墓葬,出土各类器物三千多件。在呈贡天子庙、曲靖八塔台、昆明羊甫头、安宁与东川等地也相继发现有滇文化墓葬,出土了很多器物。此外,滇西地区也发现有很多从战国早期至汉代的墓葬,既有大石墓与石棺墓,也有青铜文化遗址,出土有数量较多的各种器物,其中尤以陪葬器具和兵器之类居多。⑥云南省博物馆:《十年来云南文物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277-278页。滇西青铜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很广,西至怒江、澜沧江沿岸,南抵保山、昌宁一带,北达宁蒗、德钦,东至楚雄、禄丰,和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相衔接。从考古发现揭示的时代顺序来看,剑川海门口遗址是最早的,滇西青铜文化的年代也略早,然后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呈现出由北向南扩散传播的形态。而从中国整体青铜文化发展的格局状况来看,中原华夏地区殷商青铜文化、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在时间上明显要早于云南的青铜文化。如果结合民族走廊与文化传播来做深入探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蜀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南传,可以看到三星堆青铜文化对滇国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云南青铜器的来源问题,过去曾有人提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是战国晚期楚将庄蹻带来的楚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和四川的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还有学者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是古代僰人创造的,或认为是濮人文化,或认为是古代越人创造的,反映了我国南方“百越”民族文化特色。⑦李昆声,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探索》,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9-10页。其实,周边文化对滇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以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了。从考古资料看,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物是编钟之类,这在云南很少发现。云南各族最流行的音乐器物是铜鼓,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出土的铜鼓数量众多,与楚文化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由此可见楚文化对滇文化虽有影响却并不显著。中原文化的青铜器物在云南也很少发现,同样说明在汉代之前中原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也不明显。而古蜀文化最典型的青铜器物就是青铜雕像和鸟兽动物形象了,这在殷商中期和晚期已达到极其娴熟与精美的程度了。云南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最突出的也是人物雕像,许多器物上都雕铸或镌刻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图像,就其活动内容而言,有祭祀、战争、狩猎、纳贡、上仓、纺织、放牧、饲养、炊爨、演奏、舞蹈、媾合等场面,几乎涉及到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滇国青铜器注重人物雕像的青铜文化特色,与三星堆青铜雕像可谓一脉相承。

云南李家山出土祭祀场面贮贝器
从时代沿袭和传播路线来看,三星堆青铜文化在殷商中期和晚期已极为昌盛,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商代晚期与商周之际才出现,云南剑川海门口是滇西青铜器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滇西与滇中地区的青铜文化到了战国与汉代才逐渐兴旺,很明显地呈现出了由北向南发展的态势。从出土的滇国青铜器来看,战国与秦汉时期,滇国的青铜文化最为发达,明显继承了古蜀青铜文化中崇尚人物雕像的传统与特色。这些真实状况,充分揭示了古蜀青铜文化进入云南后,开始向滇中和滇西的传播路线。这种传播很可能是渐进式的,可能延续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传播的过程中和本地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在滇池区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滇国青铜文化。在青铜器和人物雕像的铸造工艺方面,譬如泥范与失蜡法的采用,滇国青铜器也很明显沿袭了三星堆青铜雕像的铸造技术与工艺特色。
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通过西南民族走廊进行的迁徙活动和文化传播,主要是由北向南的迁徙和传播,相关的文献记载在这方面便透露了很多信息,大量的考古资料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殷商时期的古蜀青铜文化已经非常灿烂,对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南夷地区自然而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强势的传播与渗透,其实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到了汉晋时期,发祥于蜀地的道教也很快传入了南中地区,为各个少数民族所接受和尊崇,这对于由北向南的文化传播情形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