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所收潘岳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陶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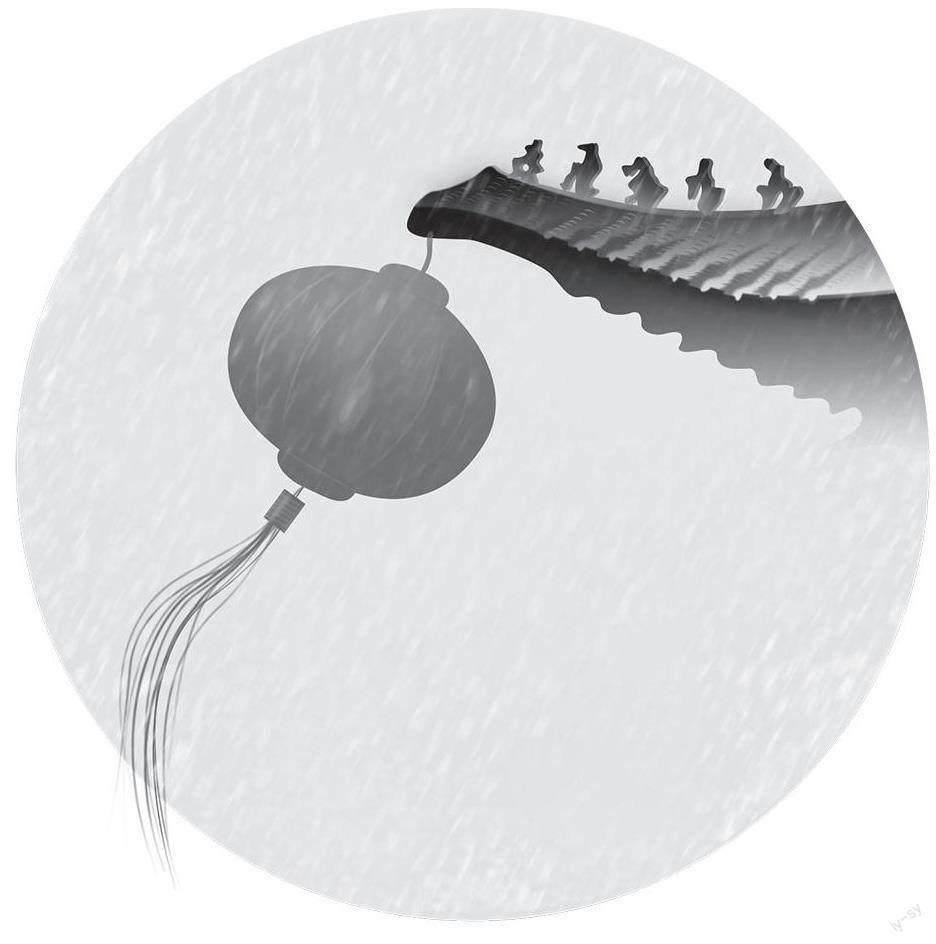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提到王粲、徐幹、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八人为“魏晋之赋首”。就《文选》所收这八人的“赋”而言,萧统在选文时,选取了潘岳的《籍田赋》《西征赋》等八篇,左思的《魏都赋》《吴都赋》《蜀都赋》三篇,陆机的《叹逝赋》《文赋》两篇,其余五人大多选取一篇或不选。作为西晋太康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潘岳文学创作成果显著,其作品善缀词令,基调独特,历来受到不少文人志士的赞誉。钟嵘的《诗品》不仅将其诗列为上品,还对其有“潘才如江”的高度评价。而其作品所表现出的鲜明风格特色在《文选》所选的八篇赋中可以探究一二。
一、《文選》所选潘岳赋的作品风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一文中将“赋”分为“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和“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的小赋。潘岳的赋又可分为叙事写志的大赋和咏物抒情的小赋。《文选》所收潘岳的赋文,无论是大赋还是小赋,都能体现其作品鲜明的艺术风格。
(一)大赋叙事纪行,强调政治功用
刘勰认为,左思与潘岳“策勋于鸿规”(《文心雕龙·诠赋》),在大赋上很有成就。而《文选》所选潘岳赋中,可以归为大赋范畴的是耕籍类的《籍田赋》和纪行类的《西征赋》。这两篇赋都符合上文刘勰所提到的大赋“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的内容和“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特点。
潘岳的《籍田赋》创作于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晋书·潘岳传》载:“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赋以美其事。”汉末以来,天下纷乱,四分五裂的社会局势使得古老的籍田仪式不能正常进行。直至西晋王朝建立,晋武帝司马炎才于泰始四年重拾坠绪,举行了亲耕籍田的仪式。在《籍田赋》中,潘岳不仅大力赞美籍田场面的宏大,宣扬皇权思想,歌颂晋武帝为民造福、用孝治理天下的功德,还借“田父”之口对籍田礼的意义进行阐释。只有重本抑末,农业才能获得发展,国家才能巩固的见解无疑契合了晋武帝举行籍田仪式的初衷。无论是大加赞颂天子功德,还是抒发大德伟业的政治见解,潘岳都因其作品中宣扬的皇权思想深受身为太子的萧统的认可,此赋被选入《文选》又单列一类就不足为奇了。
《西征赋》是潘岳于元康二年(292)任长安令,自河南至关中途中所作,故名“西征”。全文记述其从洛阳前往长安的一路所见所感,这一路线涉及商、周、秦、汉、魏等多个王朝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虽然纷繁复杂,但是潘岳叙述得井井有条。这篇赋文最大的写作特点是抚今追昔、因地怀古。与汉代班彪的《北征赋》等相比较,《西征赋》在继承了前代作品特色的同时又对其有所突破,这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历史的反思方面。与《北征赋》中“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的注重情景交融不同,潘岳在《西征赋》中更加重视在深沉的历史反思中进行对比思考,“人之升降,与政隆替,杖信则莫不用情,无欲则赏之不窃”,以史家的眼光看到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及对当政者执政的建议,显示出他的“位本”和仁政思想。《文心雕龙·才略》评价“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由此可见,《西征赋》被收入《文选》就成为必然的事了。
(二)小赋咏物抒情,凸显典雅文风
潘岳的小赋又可分为咏物和抒情两类。相较于大赋的强调政治功用,咏物赋和抒情赋更凸显了其作品典雅的文风。潘岳的咏物赋更注重在日常生活层面选取对象,《文选》所收《射雉赋》《秋兴赋》《笙赋》便是最好的说明。《射雉赋》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相比,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继承了汉代苑猎赋的写作方式,但是与他们大篇幅赞颂游猎盛况不同,潘岳重在田猎过程的描写,变此前的赞美讽谏为娱情悦性,从民俗生活的微观处着眼,对所提动物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用写实的手法详细叙述琅琊地方捕猎野兽的技巧和方法,颠覆了汉代大赋铺张扬厉背后的虚无,从而多了一种真实感。在语言方面,虽不乏汉大赋的华丽,但更加日常口语化,通篇四字句和六字句穿插使用,整体风格清新典雅。《秋兴赋》收入《文选》的物色类,以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推移极力描写萧瑟冷落的秋天景象,说明自然界中的天象进入西晋赋家的视野,使得西晋赋的题材有了新的取向,构成西晋赋史发展的特点之一。《秋兴赋》以宋玉《九辩》中的悲秋名句为契机,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慨,全文笔触细腻,行文流畅,写景抒情与用典议论巧妙结合,使得此赋文风典雅的同时立意高远,为后世相关创作提供典范。《文选》音乐类的《笙赋》咏诵的对象是文人生活中常见的乐器,以此为写作内容,可见这一时期对前代音乐赋的创作传统的继承。枚乘的《七发》首发就以音乐为题,他的写作模式与审美取向被认为是后世音乐赋的源头。潘岳的《笙赋》也继承了《七发》的写作模式,但与其对乐器“面面俱到”的写法不同,潘岳重点是在所写笙的笙音上,这也算是对前人所写音乐赋的创新了。
《怀旧赋》《闲居赋》《寡妇赋》更是西晋抒情小赋的典型。《怀旧赋》中,潘岳没有像传统写赋一样去罗列典故和堆砌辞藻,说是怀旧,却从登车上路写起,先引出与所怀之人的情谊,再转回现实环境的描写,然后抒发感情,由“无语”的间接怀念到涕泗横流的直接伤怀,使感情变化具有明显的层次感。辞赋创作自东汉以后就有了新的发展倾向,由原来对事物的描摹刻画逐渐转向对思想情感的抒发,《闲居赋》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之一。作为潘岳抒情小赋中极具特色的作品,《闲居赋》通过绚丽而鲜美的景物描写来表现他的乡居情趣和对闲居生活的向往,全赋以名人典故的罗列和华丽辞藻的铺陈为特点。元好问评其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三十首》其六)虽然西晋赋的表现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不少文人仍然在模拟前人赋作,在模拟中有所突破,从而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目的。潘岳《寡妇赋》就是如此,其序中说道:“昔阮瑀既殁,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余遂拟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据李善的注可知,《寡妇赋》中许多句子是从丁廙(《文选》中作丁翼)妻同名赋作中转变而来,但是潘赋在模拟的基础上,改动了字词,又变换和叠加了意象,使得语言更加精美,意境更加动人,情感更加细腻,所达效果远超他所模拟的范本,从而入选《文选》。虽选择旧有题材,但是能创出新意,这也算是促进西晋辞赋繁荣发展的一大举措了。
二、《文选》所收潘岳赋体现的萧统的文学观
《文选》序中的内容集中反映了萧统的选文标准和文学观。在肯定文学发展趋势的前提下,萧统提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重要选文标准,突出“以悲为美”的审美观的同时强调文质并重,与前文有别于经籍子史的“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文学作品相呼应。除此之外,《文选》序中还提到了“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文学思想,突出了文章的娱乐功能。探究潘岳的赋,我们可以从中体会萧统的文学观的具体表现。
(一)以悲为美的审美观
汉末以来兵祸频发,动乱的社会背景反映到文学领域就是大量哀时伤逝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而汉魏六朝“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更是使得哀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文坛占有很高的地位。《文选》赋、诗条目下都设有哀伤一类的分类安排,可见萧统对这类题材作品的重视以及对这种审美观的认可。《文选》“赋”中收入的《长门赋》《思旧赋》《叹逝赋》《怀旧赋》《寡妇赋》《恨赋》《别赋》都是这类作品中具有影响力的代表,其中《怀旧赋》《寡妇赋》均为潘岳所作。《晋书·潘岳传》中提到:“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钟嵘《诗品》也将其列为“文多凄怆”的《楚辞》一派。虽说潘岳常写哀,但他选材范围广而具体,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叙悲模式,且在描写过程中注重环境烘托与渲染,结尾处再加以或长或短的人生思考,这也就形成了潘岳“悲而不伤,哀而不怒”的创作基调。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中高度评价其哀辞:“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身为太子的萧统,自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所提倡的“哀而不伤”的感情基调自然也是他所推崇的,而潘岳的《怀旧赋》和《寡妇赋》无论是语言的风格,还是情感的表达,都契合了他这种“以悲为美”的审美标准,自然受到萧统的重视。
(二)文质并重的文学观
文质并重,即文章的内容与文采同等重要,这种文学观在萧统的文学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其作《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他提到:“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这与他在《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观点相一致。《文选》所收入的潘岳的赋可以使我们更直观、具体地感受到萧统“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内容上,潘岳的赋不是在叙事写志宣扬皇权思想,就是在写景咏物抒发自己的感情,抑或哀而不伤,以哀情引出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选材丰富而具体,感情充沛而真实;语言上,四言句、五言句、六言句兼有,注重对仗与偶句押韵,行文自然流畅,用典浅近贴切,既有骈偶句,又杂有散句,参差有致,富于变化,符合南朝文学追求华美艳丽的辞藻的特征。这点在他体物写志的大赋和咏物抒情的小赋里都有明显的体现。在叙事大赋中,《籍田赋》《西征赋》用华美艳丽的辞藻铺陈用典,宣扬皇权思想,并从诸多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语词华美,充分显示赋体物铺张、宏大壮美的一面的同时又加以议论劝谏,体现赋的实用性特色和劝百讽一的目的;抒情小赋中用浅近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蕴涵的正视人生有限的哲理—“人居天地间,飘若远行客”(《杨氏七哀诗》)。《闲居赋》《秋兴赋》《怀旧赋》在具有“以情入文”的真情实感的同时还兼有清丽婉畅的艺术风格。这就与萧统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完美契合,潘岳赋被收入《文选》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三)强调文章的娱乐功能
从《文选》的实际收文情况看,“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只能说是萧统选文标准的重要部分,不能算是全部。至少细看《文选》序后,我们发现,叙述完文体后,萧统还表达了“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的观点,他将《文选》所分的赋、诗、骚、颂等文体比喻成动听悦耳的乐器和美丽悦目的珍品,这种从娱乐的角度看文章的观点与刘勰的“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文心雕龙·程器》)的强调文章的实用性有很大的不同。潘岳的《射雉赋》从创作目的开始就直接体现了萧统的“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文学思想。在杨晶瑜的《魏晋南北朝狩猎赋综论》中,《射雉赋》被认为是晋代狩猎赋的代表之一。但是,与以往狩猎赋铺排夸饰,借大篇幅描写狩猎场面以达到歌颂赞美帝王功绩或对天子活动进行讽谏的目的不同,潘岳的《射雉赋》语言清新浅近,变进御讽谏为娱情悦性,明显写出个人娱乐式的狩猎。潘岳在《射雉赋》序中写道:“聊以讲肄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这说明此赋自娱自乐的创作目的,之后正文开篇以“涉青林以游览兮,乐羽族之群飞”奠定全文“乐”的感情基调,结尾又以“乐而无节,端操或亏。此则老氏所诫,君子不为”进行以“乐”为主题的劝诫,虽然还是旧有的题材和写作内容,但潘岳的重点不再是讽谏劝诫,他将以往政治色彩强烈的狩猎赋变为了娱乐性质的咏物赋,突出了文章的娱乐功能,与萧统的“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观点相一致,所以此赋受到了萧统的青睐。
“六朝论西晋文学者,必以潘、陆为首。”(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作为西晋文坛的代表人物,潘岳的文学创作成果显著,以其独有的文学成就占领西晋“半壁江山”。但与其他作品相比较,潘岳的赋文学价值更高,所以刘勰称其为“魏晋赋首”。雖然潘岳的赋在题材和写作模式上对前代赋家多有承袭,但他在文章内容和艺术风格上进行了创新和开拓,形成了其独有的作品风格,提高了其文学地位的同时,也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典范。除此之外,其部分赋入选《文选》,也为我们更深入了解萧统的文学观提供了研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