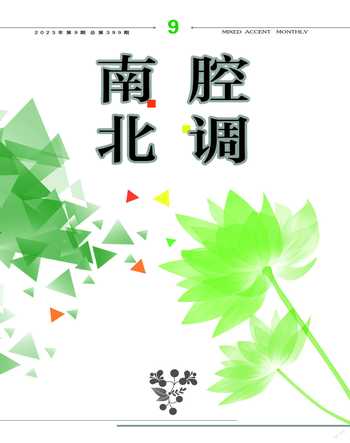从个体失语到文化失语
朱滢
摘要:华人电影导演王颖在其作品《千年敬祈》中,采用一种类似纪录片的纪实拍摄手法,以双重视点的设置实现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跨文化碰撞與交流。影片聚焦在美国新一代华裔居民的心理变迁和家庭伦理上,从个体失语到文化失语,隐藏在这种失语症候背后的却是创作者对传统伦理文化深处的反思与救赎。本文从隐喻符号、表意空间、心理机制和创伤记忆这四个方面探讨影片如何呈现从个体失语到文化失语,从而形成电影文本的隐性进程,并以此来挖掘其背后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王颖;《千年敬祈》;文化失语;心理变迁;家庭伦理
在众多家庭伦理片中,都不乏华裔作品的影子。2006年,著名华裔旅美作家李翊云的同名短篇小说《千年敬祈》由同样是华裔的著名导演王颖翻拍成电影。电影讲述年迈的史先生千里迢迢从北京飞往美国,想要帮助移民美国的女儿宜兰走出离婚阴影、重拾生活信心的故事。然而今非往日,说着一口地道英文的女儿虽然也会中文,却始终无法和父亲交心。
影片《千年敬祈》并非像其他多数华裔作品着重展现传统的中国习俗,而是聚焦于美国新一代华裔居民的心理状况以及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主题,着力呈现在东西文化碰撞的大环境下,普通华裔居民所经历的聚合、别离、欢乐、悲伤等种种遭遇,挖掘其背后暗藏的文化底蕴。自小就经历过文化碰撞的导演王颖采用一种类似于纪录片的纪实拍摄手法,对史先生和宜兰这对沉默寡言的父女的日常琐碎进行记录。影片从头至尾以一种极其平淡的风格呈现着一切,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众多家庭伦理片中脱颖而出,并于2007年获得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电影金贝壳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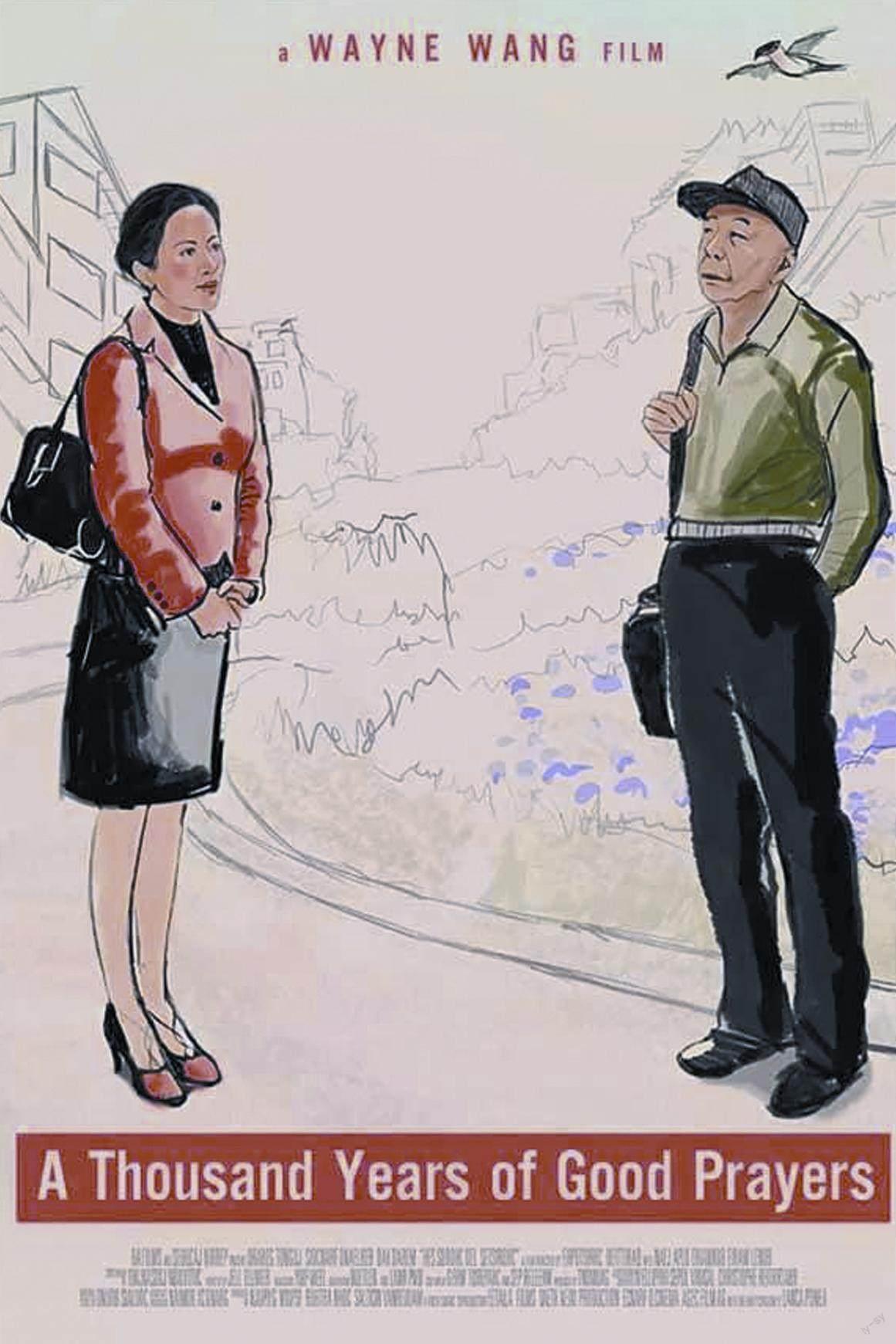
电影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集中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信息,传达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时代观念的更迭和社会意识的变化[1]。如何通过虚拟的影像文本把现实困境表达得更彻底、传达其背后的深层意蕴,这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极为高超的叙事造诣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完成对所处时代现象的反省使命。多族性、多地域的生活经历,使得王颖能够同时立足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越界者的身份让王颖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又从这种悬置状态中获得了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有利地位[2]。于是,异质文化背景下华裔族群的心理嬗变、生存状态以及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伦理观念等主题的呈现,成为其电影的一大特色。王颖生活于现代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之下,深受西方文明的熏染,对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和换代有着切身体会。在中西、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和抗衡之下,我们民族文化深在的不合理与脆弱性都不免会显现出来,而这种影响是不容抗拒的。在某次访谈中,就中国导演与西方导演拍摄家庭片有何不同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时,王颖曾这样回答:“西方的家庭就和中国的家庭很不一样,他们里面的细节、情感和人际关系都有很多差异。东方家庭里很多话都不讲明,就算讲出来,也会有不同的讲法,这在《千年敬祈》里面有提到过。”[3]正如影片中一个简单却横亘30余年的误会,背后却是汉语的收敛与朦胧、是中国人的含蓄与迂回、是内敛的民族个性却不善于遗忘和原谅、是丰富的语言文化却欠缺沟通的表达艺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影片所表达的并不沉重的父女矛盾背后,深藏的却是对传统伦理某些不合理与脆弱性的反思和救赎,从而形成其主流叙事背后的隐性进程。
一、深固和游走的隐喻符号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最先提出了符号学概念:“索绪尔把记号看作被区分的、被隔离的和被封闭的个体,它们是真正的单子,其中每一个在自身的圈子里——在其存在中——都包含着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4]罗兰·巴尔特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分析的文本从语言拓展至现实的具象物体(例如广告、海报、电影等),并提出二级表意法这一概念。二级表意法是除了结合索绪尔能指、所指概念,更强调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次“读解行为”[5],视为“意指分析”。意指分析包含两个层面——直指层面和涵指层面。直指层面指的是某个现实事物的外延意指,涵指层面则是该事物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罗兰·巴尔特巧妙地将现实事物的外延意指,通过符号分析,使得创作者的情绪价值与文化价值产生交互,从而演绎出事物深层的隐喻含义。这一分析概念挣脱了最初语言系统内“所指”和“能指”分析的羁绊,为媒介文本赋予多样化的含义,并能够“成为现代世界的思想方式”[6]。
《千年敬祈》这部影片通过深固和游走的隐喻符号,在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深固是沉淀的、固定的表意符号,游走是离散的、被寄托情感价值的意识理念符号。影片中充斥着红领巾、中式炒锅、中餐、福字等中国元素,而在跨文化的语境之中却显得既深固又游离。正如华裔内心深处根植的中国传统观念和家庭伦理文化,与游走在异国他乡时所逐渐融入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机制之间的碰撞,常常重新激发出矛盾的存在。在拥有跨文化视野的同时,复杂的文化心理构成和强烈的文化身份困惑,更是导致现实处境的困囿。影片开头,刚到美国的史先生把红领巾系在托运行李箱上做标记,女儿宜兰心生不悦但为了缓解尴尬这样说道:“用红领巾做记号啊,还挺有创意的嘛。”红领巾是女儿儿时才佩戴的,史先生仍然保留着这些旧物,意指女儿宜兰依然是他心目中那个听话懂事的小女孩,殊不知这份不善于表达的爱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早已无声地破碎了,只留下宜兰对之的不解与不屑。随后,史先生为了给宜兰做中餐,购买了中式炒锅;为了防止油烟弄脏橱柜,又往墙上贴了报纸。镜头中,史先生烧的饭菜与宜兰闲置在角落的一箱可乐相呼应,两处静物意指着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隔膜,更是两代人内心之间隔膜的隐喻,表征着个体成长嵌入社会巨大变迁中的生存状态[7]。除此之外,史先生还把从北京带来的福字挂在门上,宜兰的第一反应是愠怒,不假思索地摘了下来,但几秒之后又悄无声息地挂了回去。福字是美好祈愿的象征,但在宜兰看来,门上的福字是史先生横加干涉自己生活的隐喻。福字被摘下露出了父女关系的裂痕,福字被再次挂上是宜兰内心早已深埋的家庭伦理和传统观念的外显。
在中国长大的宜兰被抑制着表达内心想法的诉求,渐渐导致个体的失语。在美国生活了10余年之后,父女之间的关系断层、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断层又不断刺激着个体失语转向文化失语。这不仅是宜兰更是新一代华裔居民共有的困境。这种群体特征来源于强调中庸和适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沟通中则体现为喜怒哀乐皆有所压抑,语言和情感表达讲究意会和含蓄[8],但最终结果却是家庭关系的貌合神离和文化失语的无法挽回。电影一开始,宜兰接机时的无所适从、父女俩日常生活中的疏远、餐桌上的沉闷,无不体现了美国华裔家庭相处模式下的失语症状。这些隐喻符号散发着无形的现实张力,在充当着传达思想感情载体的同时,更是将沉淀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解构。
二、情感断裂的表意空间
王颖在《千年敬祈》中采用的是类似纪录片的纪实拍摄手法,影片的每一幕都按照时空顺序、顺其自然地延续呈现给观众,而影片中人物的情感却在这一幕幕中发生着断裂。由国内到大洋彼岸的地理空间,由幻想自由到生活中误解拉扯的情感空间,由纠缠过去到现实离散的心理空间,每一幕场景的切换,导演在不断展现着个体与个体在时代变迁下的情感联系。
影片开头,史先生刚下飞机,面对父亲的到来女儿宜兰也只是客套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便是长久地沉默。随后,父女间的拘谨和尴尬这一僵局很快就被打破了——史先生在飞机上遇到的美国女旅客主动地过来交谈和握手,这一对比足以显现出东西文化的强烈不同。氛围的营建效果在影片中格外凸显:每次父女相处,尴尬的情绪都充斥着每一处。影片中父女一起吃饭的场景共出现了四次,然而餐桌上的沉默是父女俩永恒的“交流”,尽管史先生不断地抛出新的话题,宜兰却总是敷衍了事。满桌的美味佳肴对她似乎并无多大的吸引力。甚至在穿衣打扮方面,当与父亲同处时,宜兰也是尽可能地保守。从起初主动打电话告知史先生不会回家吃饭到只在深夜电话留言,父女俩之间的隔膜愈加难以戳破。而宜兰不在家的时候,史先生却会主动地和各类人群打交道,不管是上访的传教士、公交车司机、公寓管理员,抑或楼下的邻居和伊朗老太太,这些交谈总是显得那么愉快。语言与思想表达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影片想要呈现出的颇为有趣的对比:语言的使命是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史先生和伊朗老太太都不是熟练的英语表达者,尽管如此,他们也能夹杂着手势进行沟通。而宜兰只有在使用英语时才能够吐露心声、畅所欲言。这种矛盾的对比使得本片的意蕴更为深刻。影片最后聚焦在父女俩分别在各自房间里对话的场景,史先生終于道出了这个横亘30年的误会:那是一个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时代,史先生是一名火箭工程师,一心想着如何报效祖国,为此他长期和妻女分居。工作的保密性这一特殊情况使得他只能把对妻女的爱藏匿在心底。多年以来,女儿留在美国生活又遭遇了离婚风波,他无法释怀当年没有尽到的作为父亲的责任,于是来美国探望女儿。而父女之间始终彼此沉默着,这么多年来的误解非但难以消除更是互相回避着。
影片最后的几分钟内,父女之间积压的矛盾终于得以释放和解决。原来父亲并不是个冷漠的人,他在美国用心学习着周围的一切只希望能和女儿同频交流,却不知宜兰一直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内心逃避着一切,对父亲充满了怨恨。直到最后她才明白,当年父亲并没有背叛自己与母亲,相反,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家庭,选择告别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做了一名普通文员。宜兰获悉这一真相,积压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电影把历史注入其中,增加了其深度,关于中国家庭的失语,也是双向的。对于中国家庭而言,失语是一种通病。尽管中国处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与全球文化不断进行着交融冲撞,家庭内部的表达方式却不曾随之改变。若两代人都是敏感、抑制而内省的,那么失语将变成一种习惯。
三、文化无意识下的心理机制
文化无意识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对其相应个体或群体的潜移默化和深植,使之成为文化心理沉淀,从而表现出来特定的观念与意识。个体对文化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及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密不可分,全球化时代中民族的文化不断交互影响,个体的文化意识也在不断调整,反映着时代的变化[9]。导演王颖潜藏着溶于血液的母语文化,对母语文化有着深在体悟和“旁观者清”的无意识。通过其作品客观、真实、深入地探讨母语文化的内在意蕴,反思其存在的脆弱性,透过虚拟的影片文本尝试将新一代移民身份进行挖掘,实现文化的拯救与反省。
影片中,史先生和宜兰的交流寥寥无几。在史先生发现女儿结交了一个俄国情人后,父女俩之间的矛盾冲突爆发到顶点。宜兰在镜子前哭诉着说:“如果你从小生长在一种语言环境之中,但根本没人教过你怎样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你自己,那么你一旦学会一种新的语言,就会觉得,用这种语言表达起来会更容易一些。”而史先生却对此不理解:“我们养育了你,可是我们没有向你提供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去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你要找一种新的语言,去找一个新的情人?”宜兰回应道:“你跟妈妈就从来不谈你们婚姻中的问题,所以我也就学会了不谈。”文化无意识更清楚地指出了文化的内涵中静态和动态的两个方面:静态部分涵盖社会的物质文明;动态部分囊括社会通过教育、生活经历和意识形态教导等形式影响人类生活的过程[10]。上一辈压抑着的情感互动是中国传统家庭沟通方式的典型,更是无意识构建了母语语境对宜兰的压制。宜兰从小压抑着表达情感的欲求,这种文化无意识是家庭伦理和传统观念在宜兰内心投射而形成的潜意识,造成宜兰无法使用母语来正确表达自己的内心,陷入无意识的沟通窘境。而融入西方社会后的宜兰深受西方崇尚自我表达的文化影响,进而可以熟练地使用一种新的语言来自如表达自己的情感,文化无意识被转为潜意识模式隐藏了起来。然而,父亲的到来,使得宜兰再次压抑自己的内心,无法敞开心扉与父亲进行交流,潜意识再次以显性的方式浮现。文化无意识隐藏与显现的交替形成宜兰个人失语的困境,也进一步暗示着文化失语的根源。
王颖电影中的华人移民形象,不仅仅是后殖民社会人们的典型,也是广大第三世界人们的代表。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性的移民浪潮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全球性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人们在经历系列的错位、误置、脱域、集体记忆丧失和文化移入的痛苦过程[11]。王颖通过影片,对东西方文化在语言、心理、价值观等层面进行诠释,在观察和审视母语文化的同时,呈现出东西方文化冲突与尝试共存相交的现状。失语的困境是在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无法避免的难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文化差异的探析和文化的调和与圆融。
四、创伤记忆下的家庭叙事
个体的创伤记忆在汉语文化中似乎总是缺席。在时代的宏大叙事面前,我们孤独的个体缥缈如沙。个体所承受的创伤被叙述成整个国家、民族的创伤。于是,“实实在在受伤的身心反倒像旁观者” [12]。压抑记忆成为“旁观者”唯一的选择,而对于苦难的隐忍、对于创伤的漠视、对于本土文化深处不合理与脆弱性的遮掩,必然导致创伤记忆的一再重复,个人失语也终将过渡至文化失语。
《千年敬祈》展现了家庭性的创伤延续,张志扬在《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中曾指出:“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20世纪中如此巨大的创伤记忆,以为不靠文字像碑铭一样建立的反省、清算、消解而生长、置换、超越的能力,就可以在下一代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中悄悄地遗忘、抹去,这除了不真实和不负责任,还说明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已在历史的惰性中无力无能承担他自己的遭遇,从而把无力无能追加在历史的惰性中作为欠负的遗产弃置给了下一代。”[13]《千年敬祈》并没有直接描述史先生上一代人的创伤,而是通过宜兰这一个体所忍受的创伤倒推出史先生所代表的上一代是如何把创伤记忆“弃置”给了下一代。《千年敬祈》的叙事构造将传统家庭模式与创伤记忆带来的双重影响囊括在内,通过父女两代人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绘的是宜兰代表的这一代人与史先生代表的上一代人的隔阂与冲撞。宜兰经历了自身的婚姻失败,史先生想要帮助女儿走出生活阴影,却连走进女儿心里这第一步都无法迈出。原来,史先生在宜兰儿时所展现出的婚姻危机、家庭氛围的尴尬与缄默在无形中改变着宜兰。在本土传统中,“一个公民并不是为他自身活着,而首先是为他的家庭活着”[14]。史先生对待婚姻是隐忍的,女儿宜兰在这种“传承”下,对待自己的感情也选择了回避的处理方式。在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史先生默认的家庭模式如何又一次在宜兰身上重塑以及重现,创伤记忆又是如何在家庭系统中传递的;影片的第二部分是在史先生和宜兰的矛盾爆發中开启的。当宜兰质问父亲为何从不和母亲谈论婚姻问题,史先生这才醒悟过来:上一代的压抑已无形中遏制了女儿的情感诉求。这一部分的叙事结构是极具对话性的,史先生对宜兰回忆起那个年代的事,女儿也得以了解自己所曲解的真相,史先生和宜兰心里的阴霾逐渐散去,“传承”下来的创伤记忆也在不断被“医治”。我们也更能探究到史先生和宜兰所遭受的创伤记忆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从回避创伤、直面创伤再到医治创伤,《千年敬祈》不仅是反思母语文化的传统弊病,更是剖析并直面本民族深藏着的创伤记忆。从个体到家庭再到文化,直面创伤才能斩断文化深处的不合理与脆弱性,避免文化失语的僵局。
四、结 语
巴赫金曾经说过:“在文化领域内,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异族文化只有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15]在全球文化碰撞的今天,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封闭的民族文化,任何文化都需要在不断地融合各种文化的过程中得到吐故纳新的发展。而这种“外位性”恰恰可以使本族文化看到因身在此山而无法看到的封闭性和片面性。影片《千年敬祈》置于现代和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将潜藏于中国传统观念和家庭伦理文化中的某些精神侧面从文化无意识的深渊中浮现而出。而我们看到,在双重文化的冲击下,必然会露出这些精神侧面的脆弱之处,王颖正是通过对其的解构,实现对传统伦理某些不合理性的反思与救赎,从而形成其主流叙事背后的隐性进程。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那些被我们视为情感价值依托的传统伦理所带来的是进步还是固步自封?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形态,虽曾经具备强大的约束力和伦理力量,但是否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历史的尘烟?如果一种文化的积淀带给我们的只是对现实的无法应对与内心的封闭,那么这种状况是应该受到反思和救赎的。
参考文献:
[1]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3-164.
[2][11]荣欣.王颖电影中的文化身份探寻与重塑[D].陕西师范大学,2012:28,36.
[3]王颖,梁茹冰.《雪花秘扇》: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王颖访谈[J].电影艺术,2011(05):60-64.
[4][5][6][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符号学历险[C].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1-162,165,167.
[7][8][9][10]唐蕾,俞洪亮.文化无意识与身份建构——基于美籍华裔获得语作家的个案考察[J].外语研究,2018,35(05):85-91.
[12][13]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40,69-70.
[1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9.
[15][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白春仁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410.
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