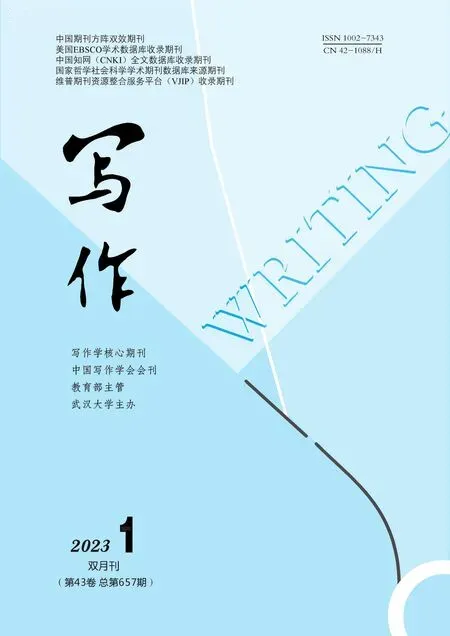疼痛的生命诗学
——罗振亚诗歌创作的精神样本与审美品格
吴井泉
现代诗歌的终极指向是生命,而每一次生命体验都可以化作诗歌灵感的源泉,表现诗歌的基本主题和普遍意义。现代诗歌追索一切与生命有关的信息,触摸生命的脉搏,聆听生命的回声,感受生命的温度,与生命保持着永恒的对称,无论是辉煌的生命还是困顿的人生。现代诗人正是透过生命的纷杂,穿行在生命幽秘的森林里,感知、思考生命的意义,在希冀、追问的同时也不乏焦虑和挣扎,努力在最高的层面上实现生命的叩问。兼具诗人和诗评家双重身份的罗振亚先生对生命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理解。其中既有诗性的敏感和细腻,又有理性的深邃和超越,二者的结合成就了独属于他的动人诗篇。疼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亲历的感知,但将疼痛作为诗歌叩响生命之门、探询生命意义的密钥的诗人却不多见。罗振亚先生也许就是手握密钥的诗人之一,他的诗篇可以引领我们贴近生命,同时也能感受到他那内敛深沉却也激情满怀的人生世界。
一、生命的疼痛:罗振亚诗歌写作观的生成
罗振亚先生说:“我还是视诗歌为永远的亲人,每逢自己生活中遇到什么大事,在最幸福或最悲痛的时候,总会适时地把心里的话向她倾述。”①罗振亚:《罗振亚谈诗歌创作与研究》,《创作评谭》2017年第4期。罗振亚先生诗歌的“亲人观”,表明他对待诗歌的态度是真诚的、严肃的,也是不需要佩戴面具的,即真实情感的流露、本真生活的关怀和生命的感动等。“真诚与朴素,这是罗振亚的底色,也是他诗歌的基本品格和写作态度。”①霍俊明:《这一次,批评家拉开了自己的诗歌抽屉》,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罗振亚诗歌写作的“亲人观”是其长期诗歌创作实践中生成的审美观念,它既不同于“主情说”“载道说”,也不同于“经验说”。罗振亚的“亲人观”有自己的审美系统和精神创造,主要表现在诗人放弃了占据精英位置的姿态,不唱高调、不装腔作势、不自我异化,回到生活的“原处”,回到血缘、真情,回到切肤之痛和切肤之爱中去。罗振亚“亲人观”的核心基础是情感。霍俊明认为:“罗振亚大体属于‘存在型’的写作者。北方(乡思)、家族(亲情)以及人生世态是罗振亚主导性的精神背景,这也形成了他诗歌中的基于精神出处的回望姿势——饱含深情、时时掂量的记忆和本事成分。”②霍俊明:《这一次,批评家拉开了自己的诗歌抽屉》,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赵思运也认为罗振亚诗歌的抒情品质是不“绮靡”的“缘情”③赵思运:《“缘情”而不“绮靡”——罗振亚诗歌的抒情品质》,《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饱含深情”是罗振亚诗歌的显著特征,然而“饱含深情”对罗振亚来说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使这种滚烫的情感渗透到他疼痛的生命中去,使之形成一个生命与艺术和谐共生的诗歌命运共同体,并具有崇高的精神品格。这才是他所要追求的诗歌境界或诗歌美学。诗人郑敏先生曾说过:“诗和生命是这样密切的相关联,我在诗里往往寻找生命的强烈震波。”④郑敏:《诗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因此,我将罗振亚的诗歌美学界定为“疼痛的生命诗学”,即感动、爱、孤独、痛苦、悲伤、乡愁等都属于这种生命疼痛的题中之义。从美学归属来说,“疼痛的生命诗学”属于崇高范畴。康德指出,“(崇高的情感)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它“‘痛’中求‘快’”显示了人的精神的崇高性⑤[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疼痛的生命往往要比一般的情感更深沉、更稳定,也更具有力量。如果没有生命的灌注、生命的关怀与生命的疼痛,诗歌怎么会有灵魂,又怎能抵达人类的心灵深处?
罗振亚先生在谈到创作初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他说,1983年7月,他20岁大学毕业便选择了支边——赴黑河师专任教。当时,黑河地区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处处“透着荒凉”,他倍感痛苦与孤独。“由于透彻骨髓的孤独作祟”,他开始痴迷写诗,缓解精神的焦虑。(他的诗歌创作,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其《父亲》(组诗)还获得了黑河地区文学创作一等奖⑥罗振亚:《罗振亚谈诗歌创作与研究》,《创作评谭》2017年第4期。。虽然《父亲》(组诗)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至今读起来仍然使人感怀不已。由此可见,罗振亚的诗歌创作,甫一开始便具有了这种生命疼痛的质感,并在40余年断续的创作中延续着这种美学路线。罗振亚先生说:“对我而言,写诗绝非像有些人那样属于‘无病呻吟’的产物。……或许是平素里都力图使所写的诗歌成为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栖居方式,觉得只有从心灵里流出的情感才会再度流向心灵,若想打动读者的灵魂,首先必须打动自己。”⑦罗振亚:《罗振亚谈诗歌创作与研究》,《创作评谭》2017年第4期。2012年以来,他创作的《一株麦子的幸福》《和老爸聊天》《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他已经不认识我了》等作品就是记载他生命疼痛的精神样本,从中能读出他对父亲的感恩、怀念和失去父亲的悲伤之情。这是从他疼痛的生命里流淌出来的歌唱,更是饱含了生命质感和亮度的深沉歌唱。
陈超认为“诗歌是估量生命之思无限可能性的尝试”,并进一步强调说,“从生命最本源中释放出的鲜红的质素,构成了诗人创造和伸展的双重源头”⑧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罗振亚的诗歌就是沿着这样的生命道路走来的,如《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写的是父亲晚年患上阿兹海默症,连“我”也不认识的感伤情形:“不知从哪天开始/他已经不认识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朝我要西瓜/边吃边端详着我/你看见振亚了吗/西瓜他小时候最爱吃/你让他回来看看我/说完就躺在床上等/屋子一下子安静得瘆人/猫慌忙躲到墙角/马蹄表仿佛也不再敢走动/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天突然就黑下来了。”①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8、27页。这是一首催人泪下、让人疼痛的诗篇。父亲种种不寻常的行为在某些人的眼里也许是荒诞不经的,但对振亚先生来说,却是泪涌的爱,生命的痛。2018年12月,罗振亚先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的“中国好诗·第四季”首发式暨分享会上亲自朗诵了收入与诗集同名的《一株麦子的幸福》这首诗,当他噙满泪水用“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天突然就黑下来了”结束朗诵时,“现场的观众无不感动、唏嘘,诗集的责编老彭更是紧握先生的双手,颤抖着说不出话来”②许仁浩:《在“临照与回望”中航行——罗振亚最近新作的一种读法》,《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可见,好诗一定渗透着生命的疼痛,一定是指向内心的,也一定能引起人们的共情。因此,诗歌评论家李犁先生有这样准确而中肯的评价:“作为前沿理论家的罗振亚诗写得非常朴实,诗的方向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凝聚,不是远涉,而是返回。……诗像越攥越紧的拳头,掰都掰不开,这就是有与实的写作。尤其是在虚假盛行的时代,这种真实就更有力量和价值。”③罗振亚:《创作谈:说说自己的诗,《写作》2018年第4期。罗振亚的诗歌自有一种内在的摄人心魄的力量,就像越攥越紧的拳头,似乎能把生命攥出血来。
二、对话的多重交响:生命疼痛的精神样本
有学者将罗振亚的歌唱界定为多重身份的交响:“他把诗歌情调定位至黑土地的赤子,天津卫的异乡者,怀念父亲、孝顺母亲的儿子,教导儿子有博大情怀的父亲,感恩妻子的丈夫,心念师恩的学生,具有社会敏感性的诗人……《一株麦子的幸福》涵盖罗振亚除批评家之外的十几种社会身份。”④陈国元:《入城村民心理形态的农村社会学价值——论罗振亚诗集〈一株麦子的幸福〉》,《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罗振亚先生对每一种身份的体认都充满了深情,甚至用疼痛的生命予以守护。
(一)生命疼痛的自我承受
诗人对自己生命疼痛的歌唱,主要是以独白、倾述等方式直接呈现,主观色彩浓厚,并以真实、坦诚的生命向自己敞开、向世界敞开,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和理想主义精神。20世纪80年代初,刚满20岁的诗人就要远离父母独自去边疆工作、生活,而母亲却希望他能回家乡工作,最终母亲这一简单朴素的愿望还是落空了,显得非常悲伤,诗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满怀愧意地安慰母亲:“妈妈 您别再悲伤/当太阳再度升起时/我将走向远方的梦想/也许我只会是一个迢遥的梦/深夜里悄悄把您探望/妈妈 我是属于您的/但我更属于北方”⑤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8、27页。(《妈妈 原谅我吧——写在大学毕业支边时刻》)。其中“妈妈 我是属于您的/但我更属于北方”这句写出诗人矛盾复杂的情感之痛、生命之痛,表现了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大学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事业、亲情、道义和责任等多重的考验与感情的煎熬,那就不能感同身受地体悟到诗人的这种生命之痛。
罗振亚先生对自己这种生命疼痛的直抒胸臆的歌唱,还表现在《巴掌·木棍》《我的父亲啊》《别》《我说过我们还会相见》等诗作中。如“身后的山轰然倒下/我只能站起来独立行走//杜鹃声里/跪着的阳光/怎么也追不上踉跄的风//窗前老榆树的疤痕/烙在六月十九日的额头”⑥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8、27页。(《我的父亲啊》)。全诗虽短,仅七句,却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体验。诗人的父亲虽是农民,但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诗人一遇到困难或困惑时,总是先与父亲商量。父亲是诗人的知音、守护者。因此,父亲就如一座大山成了诗人安稳依靠的精神港湾。可是父亲的离去,使诗人感觉到“身后的山轰然倒下”,今后,“只能站起来独立行走”。诗人在诗中既表达了对父亲离去的不舍,也有失去知音的无奈,这种复杂交织的情感不断地咬噬诗人的心,正如“窗前老榆树的疤痕/烙在六月十九日的额头”,成为他生命中永远的痛。
(二)他人生命疼痛的抚慰
这种对他人生命疼痛的歌唱,主要是以诗人主客观平衡或以客观为主的视角表现世界的。诗人的歌唱更多呈现出多声部的交响,具有复杂多变的复调色彩。他真诚地写出了父母、妻子等生命的疼痛,而这些疼痛如同施加在诗人身上一般,刻骨铭心。父亲一生辛勤劳作,晚年疾病缠身,但其生命疼痛也一样强烈。“那天我藏起稚嫩的书包”“偷偷去田间锄草”,父亲得知后“撅断锄把”“破天荒理了短发/谦恭地给班主任递烟”。晚上,“一向沉默寡言的他”,“二两白干”,“就喝得滔滔不绝/泪水打湿了烦躁的蝉鸣”①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28、29页。(《父亲的妥协》)。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走出山村的希望。因此,父亲对儿子的逃学行为非常悲愤与伤心,否则也不会当着全家人的面痛哭流涕。如《老宅倒了》一诗:“老宅是用来取暖的/昨天一场大风/站了五十年的它倒了//父亲说倒就倒了吧/之后便趴在三楼窗口发呆。”②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28、29页。老宅倒了,意味着残留在他脑海里的“家”自然也就没有了,这对父亲来说,其内心的痛楚是难以言表的。
在《母亲简历》一诗中,诗人对母亲一生疼痛的生活经历有过准确而形象的书写,“一岁时她母亲去了天堂”,“十八岁她尝受儿子夭折的滋味”“二十到三十五岁她属于五个孩子”,“三十六到五十六岁她亲近庄稼”,“五十七岁她进城……除儿子媳妇孙子连楼房也不认识她”,“好不容易她能找准东南西北/又遭遇老伴儿的失忆症发作”,“到了七十二岁孩子们四处忙/她常一个人在花坛边数花苞儿”③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28、29页。。母亲尽管经受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如幼年丧母、晚年失伴,却深明事理,从不给儿女们增添负担,也从不将这种生命的疼痛表现出来,然而行动却不会隐瞒,如“父亲走的那晚上过马路/她抓我胳膊的手轻轻一颤/我六月的心一下走进冬天”④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28、29页。(《过了年 您就七十七了》)。母亲的手“轻轻一颤”,这一动作包含了她无以复加的生命之痛,这既有失去老伴的痛苦,也有对今后日子的恐惧,更有对儿子的依恋,种种复杂的情感因素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揪心之痛。
罗振亚先生与妻子杨丽霞女士感情甚笃,令人称羡。罗振亚先生说:“在我最难的时候,是她帮我肩起了生命的天空;虽然我很少表白,但内心始终对她充满了依恋和感激,她为我和孩子做出的一切,或许是一生也无法偿还的,尽管她并不需要。”⑤罗振亚:《罗振亚谈诗歌创作与研究》,《创作评谭》2017年第4期。生活中杨丽霞女士对先生关爱有加,全身心地支持他的事业,甚至为此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学工作。当年她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先生。尽管她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命的疼痛,却也从不抱怨。2016年,一场来自医院“误诊”的虚惊之后,杨丽霞对生命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在平遥古城观看大型情景剧《再见平遥》,剧情十分震撼,她一边看一边流泪,出了剧场,只记住剧中刚生下孩子就死去的年轻女子说的台词“生都生了,死就死吧”。《妻子的头发》一诗描绘的就是当时的这种情境,罗振亚先生写出了妻子这种生命疼痛的悸动。诗中对她“跳秧歌”和重复剧中女子的台词“生都生了,死就死吧”这两个情节的描写,实则蕴含了丰富的意味,从中传递出她对生命的渴望、人生无奈的喟叹。
对师友及底层人等生命疼痛的歌唱,同样体现出罗振亚对生命与生活的理解。吕家乡先生是罗振亚的硕士生导师,罗振亚读书期间与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和友谊,并对其人格、道德文章感佩不已。吕先生时运不济,始终都在与苦难进行斗争。“八十六年不算短的距离/几乎都在测量苦难的深广度/人们担心先生羸弱的肩膀能否承受/可他讲起历史依旧云淡风轻……看先生送客用拐杖询问道路/背驼得和地面越来越近/这虽吻合先生一向谦和的态度/但我还是心疼自己不是他手里的木棍。”①②④⑤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168、169、192、188页。“看先生送客用拐杖询问道路/背驼得和地面越来越近”之句,形象地表现了吕先生年老体衰,但仍与困厄进行抗争的生命形态,令人动容。“但我还是心疼自己不是他手里的木棍”,表达了诗人不能为恩师分担苦难而内心产生的疼痛和遗憾。龙泉明先生是罗振亚的博士生导师,可惜,龙先生英年早逝,壮志难酬。“没拍到五十三岁的肩膀/正走着的山突然坍塌了。”②(《您再那个世界不发烧了吧——悼念业师龙泉明先生》)龙先生患病期间,诗人满怀焦虑与疼痛地写道:“低烧却始终赖在您身上不退/面对无胆英雄/医生也只好将双手摊开。”多年后,诗人仍为龙先生的低烧而疼痛不已。对生命疼痛的歌吟,源自诗人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恩师不舍的情怀。
对农民工生命与生存的关注,也是罗振亚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是“依托于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群体,但确切来说却不归属于任何一方,其自我认同与归属存在障碍”③张广胜、张欢、周密、江金启:《农民工焦虑感会自我平抑吗》,《人口与发展》2017年第3期。。作为“边际人”的农民工一般要经受两种文化的逼迫与考验,其灵魂注定进退失据,所以他们生命的疼痛也更为剧烈:“可是老家恐怕很难再回去了/父母永远走了责任田亲戚承包/出来太久连庄稼都不认识自己了。”④(《和一位水暖工交谈》)诗人揭示了远离故土的中年农民工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和内心深处的痛。“虽然我每天负责把钢料焊接在一起/三妞还是怕跟我受穷闹分手/和西屯跑运输的二蛋搞起了对象。”⑤(《二十岁的焊接工睡着了》)可见贫穷就像一个肿瘤,它不但侵蚀人的肌体,也摧残人的精神。这对于一个出身于农村原生家庭的贫寒子弟更是如此。“罗振亚对农民工沉痛心态刻画之作具有典型意义,向读者展示了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象的敏识力,痛触‘当代噬心主题’。”⑥陈国元:《入城村民心理形态的农村社会学价值——论罗振亚诗集〈一株麦子的幸福〉》,《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三)世间万物生命疼痛的体味与吟唱
恩格斯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曾有过深刻的认识,他明确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998页。,而后,他又进一步强调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998页。。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互为一体、和谐共生的。“罗振亚的诗歌也依旧接续着与自然的亲缘。……诗人视天地万物皆有灵性,把生命移植给外物,这种与自然同根生的诗学生命对话在《一株麦子的幸福》中交织回旋,从无形的对话中确立了诗的在场感,从与万物的联动中找到了一种精神呼吸的语言。”⑨卢桢、刘莎莎:《学者型诗人的乡土观照——以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文艺评论》2021年第5期。罗振亚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和灵性的,他把它们视为人类的亲人,与人类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人类的主奴。罗振亚对自然万物始终怀有温情、敬畏和悲悯。
因为对自然万物有与生俱来的亲近,自然生命体成为罗振亚歌吟生命疼痛的天然载体。诗人以人们司空见惯的“蒲公英”入手,写出了“蒲公英”的悲剧命运,寄寓了诗人悲悯情怀:“不知道经历过几世的轮回/根才扎入水泥森林中柔软的缝隙……如果成熟穿越了春天/种子们化作舞蹈的白色绒毛/乘着风的‘高铁’飘向未知之域/那绝对不能叫流浪/说不准还会奏出一阙还乡曲/只要灵魂能够飞翔/安定与漂泊生和死/在辞海里原本是一个意思。”①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84-85、81-82页。(《高楼旁一棵蒲公英的灵魂在倔强地飞翔》)这首诗通过对城市里艰难生长的,“只要灵魂能够飞翔”,无论“安定与漂泊生和死”的“蒲公英”疼痛的生命形态进行了描写,表现了蒲公英灵魂的倔强和“向死而生”的牺牲精神。诗人清晨拍照时不小心碰落一朵杏花儿,这让诗人心有戚戚然,毕竟一朵鲜活的生命“可如今还没结成青涩的果/夭折的铃声就从五月的麦芒上传出”(《清晨不小心碰落一朵杏花儿》)②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84-85、81-82页。。“杏花儿”夭折,最痛苦的莫过于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杏树,“离开树身的花儿在无奈坠落”“杏树的枝条在猛然抖动”,这一细节描绘出杏树母亲生命疼痛的情状,表现了诗人对生命疼痛的哲学思考,诠释了人类“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沉重的悲剧性主题。或许爱才是这悲剧色彩中的一抹温暖亮色,给人以希望和前行的力量。
三、敞开疼痛的生命歌唱:罗振亚诗歌创作艺术揽胜
“敞开”是罗振亚诗歌创作的突出特点,即把自己的情感、生命向生活、读者和世界敞开。因此,他的作品不是“向内转”和“不及物”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和体验性的,或者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当代性。在注重个人艺术的前提下更关注这个世界,关心当下社会的伦理价值和世道人心,是罗振亚诗歌写作不变的追求。因此,进入他诗歌中的人事景物就不是他虚构的产物,而是有着生活的基础——原型或本事的成分,应该归属于非虚构写作范畴。罗振亚先生的诗歌之所以感人就在于真实,如那些亲情诗、乡土诗等。对真实世界的呈现与挖掘外,也有自己的特点,即以“个人的真实体验为基础去书写与探索,……力图呈现出一个‘小世界’的内部”③李云雷:《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罗振亚的诗歌写作是在场者的写作,也是观察者和思考者的写作,因此,他的写作视角融合了内、外两个视域,呈现出“我”与“他”浑然相融、和谐共生的精神合体,并以此加深我们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沟通与理解。
(一)捕捉细节:直戳生命痛点的书写
书写生命疼痛的诗歌一定是建立在生活疼痛的深刻体验基础之上,没有生活的疼痛也一定不会有生命的疼痛,乃至文学的疼痛。同时,文学又是强调细节的艺术,没有细节的刻画也同样不会产生感人的力量。罗振亚先生在诗歌中刻画了许多生命疼痛的生活细节,并引发我们的共情。在《老宅倒了》一诗中,诗人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老父亲得知乡下那座50年的老宅被大风吹倒了,而后便趴在三楼窗口发呆。这一细节非常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父亲内心疼痛的情形,这一特写镜头胜过万语千言,堪称经典之句。再如《过了年 您就七十七了》中,诗人也写到这样一个细节,令人泪目:“父亲走的那晚上过马路/她抓我胳膊的手轻轻一颤。”母子连心,诗人将母亲晚年失伴和没有安全感的疼痛生动地传递出来。“轻轻一颤”这一动作细节细腻生动,任何语言在它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和营构画面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诗歌不及物的缺憾,“及物使得他所描绘的细节和流露的情感更为清澈明晰”④刘波:《诗与思的内在呼应——论罗振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使诗歌具有饱满的生命质感。一是塑造人物形象。《和老爸聊天》中的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有一回我在村边摔得天旋地转/您愣是铁着心不肯搀扶/还说是爷们永远不该跪着/我站起后至今再没有弯过腰。”①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6-17、105页。这个细节是写父亲的“狠”,并将父亲正直的形象表现出来。父亲这种“不近人情”式的家教方式比较特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形象在诗人笔下除了“严厉”之外,更多的还是爱。父亲患阿兹海默症多年,已经忘记了许多人或事,其中也包括“我”。但他仍然能记住“我”小时候爱吃西瓜,并期盼“我”尽快回家看他,“那年夏天日头真毒/东北土路也开满刺眼的白花/您递给我半个消暑的西瓜/至今我口里还有香甜的味道”②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6-17、105页。(《和老爸聊天》)。二是推动情节发展。如诗人在《父亲晚年最怕提“老家”两字》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当一提到“老家”这个敏感的词汇时,父亲就激动不止,“过去多年的人事细节就会复活/从他的嘴唇上纷纷站起/想按都按不下去”,他“一会开口大笑/一会泪流满面”,“每逢这时,我和弟弟都相视一笑”,便转移话题,聊聊其他,“这样他就会安静得像贪睡的孙女/习惯地看看墙上挂钟的走针/开始又右手数左手手指”③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6-17、105页。。三是营构画面感。在《看望恩师》中诗人以白描的笔触再现了吕家乡先生驼背的画面,令人心酸:“看先生送客用拐杖询问道路/背驼得和地面越来越近。”捕捉细节,直戳生命痛点的书写在罗振亚先生的诗歌中俯拾即是,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可以说,细节描写是罗振亚先生诗歌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具有鲜明的文本辨识度。
(二)节制抒情:迂回传递生命疼痛的书写
罗振亚先生是新诗研究的著名学者,尤其对先锋诗歌的优劣得失有卓越的创见,并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同时,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自成风格,既有先锋诗歌中的优质元素,也保留了自己的抒情经验。其中节制抒情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经验之一。节制抒情不是说诗歌不要情感,“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④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页。,正如诗人所言,诗歌“不仅仅是情感的抒发,也不仅仅是生活的表现,还不仅仅是感觉的状写,它有时更是一种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⑤罗振亚:《罗振亚谈诗歌创作与研究》,《创作评谭》2017年第4期。。完全赤裸情感的诗歌作品貌似拥有压迫的力量,实则苍白无力。“我每一次写诗都尽量地顺应现代诗的物化趋势,给情感寻找一件相对合体的衣裳。”⑥罗振亚:《罗振亚谈诗歌创作与研究》,《创作评谭》2017年第4期。罗振亚先生主要运用想象逻辑与事态逻辑表达情感,节制抒情,使其诗歌作品散发着隽永的生命光芒。想象逻辑主要凭借意象或象征行动的演进结构全篇,在技巧上多采用隐喻、暗示、拟人、通感和知觉化等手段,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等内宇宙世界。如《清晨不小心碰落一朵杏花儿》《高楼旁一棵蒲公英的灵魂在倔强地飞翔》等诗就是想象逻辑的经典之作。
“事态逻辑”既是罗振亚诗歌写作的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他诗歌批评中的专属创造语汇,他经常运用主观化视角和客观化叙事视角两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独特思考。如《一株麦子的幸福》中诗人叙述了父亲与麦子、麦田的血肉联系,同时表明“在父亲呵护的那块麦田里/我已长成饱满的麦子”,虽然历经坎坷和痛苦,却幸福无比,表达“我”对父亲的感恩,叙事中饱含感情。而《阴阳先生》一诗则是客观化视角的经典之作,诗人叙述了一个“一辈子全凭说话吃饭/能让人间和冥界两边点头”的阴阳先生的事迹,写出了他的善良和“生财有道”的品质。有一天读小学的孙子问他:“‘爷爷这么厉害/我爸妈咋还用去南方打工/咱能不能把平房卖了进城’”,阴阳先生“捋捋七十岁的胡子”笑道:“‘都怪当初你太爷死那会儿/我选坟址时没看好风水’。”⑦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6-17、105页。阴阳先生诙谐自嘲的回答,表现了他的睿智与良知,当然也有生活的无奈。诗人在阴阳先生身上寄寓了对社会良心、伦理道德的期许。
(三)构筑崇高:敞开生命疼痛的书写
康德把“美”区分为“优美”和“崇高”两种不同性质的美。“优美”是直接产生的令人愉快的审美感。而崇高则是间接产生的“愉快感”,即通过情感的阻碍、对抗而达到生命和解的审美活动。因此,崇高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审美情感。罗振亚先生的诗歌作品就具有这种崇高品质。
一是真挚的情感。首先,作品中的人事景物都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诗人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诗人书写他们不是以戏谑、虚化的态度,而是饱含真情的,这是他诗歌作品最原始的情感基调。其次,诗人表现的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自然情感。他写父母、写妻子、写师友、写故乡、写土地、写自然万物的诗歌作品无一不是有感而发的自然歌唱,很少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最后,诗人表现的是诚意的情感。他的诗歌作品总是抽离了情感中的水分,呈现出瓷实的内核,保留了诗人最厚重的诚意。如《在家乡的一片麦地前我低下了头》一诗写道:“习惯在城中昂首走路的我/面对记忆中从未高过童年的麦田/突然低下了头/天边有一道白鹭的灵光飞起”①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87、44页。,表达了诗人对麦子的致敬与感恩,真诚而亲切。
二是朴素的情感。罗振亚先生曾说:“我始终认为最优秀的诗歌都是直指人心,以朴素晴朗的姿态示人的……那种在诗歌里装神弄鬼、诘屈赘牙者,虽然不能说不是一种探索,但恐怕永远也不会打动人。”②罗振亚:《创作谈:说说自己的诗》,《写作》2018年第4期。罗振亚诗歌表现的不是那种漂浮在云端的,光芒万丈的情感,而是散发着生活气息的朴素情感。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形容是非常恰切的。首先,诗人选择的意象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人事景物,几乎没有怪力乱神之象;其次,作品的语言清新质朴、内敛、不喧哗,彰显了一种风骨,“属魂的文字总是拒绝被过度包装。他所创造的正是那些清除语言暴力后剩下的部分,干净偏瘦,但足够有力”③刘波:《诗与思的内在呼应——论罗振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诗人还多用口语入诗,强化了这种朴素情感的表达。如“看着她头上飞雪的瞬间/我说‘理个短发,去去晦气吧’”④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87、44页。(《妻子的头发》)。最后,诗人善用白描笔法,寥寥几笔便能将对象的精神气质勾勒出来。
三是悲悯的情感。“罗振亚先生的诗歌始终有一种温情,这不完全是他既定的美学,更与人性有关。温情里有悲悯之意”⑤刘波:《诗与思的内在呼应——论罗振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悲悯中又隐含着矛盾性与反思性。《和一位水暖工交谈》一诗中表现了诗人对水暖工这类城乡跨界边缘人的理解之同情,对于他们的生命疼痛感同身受,诗人本身的境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希望他们早日结束这种身心分离的矛盾之苦,而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他又无能力改变他们目前的生存处境,甚至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这表现了诗人的反思与内在的矛盾性。比如,他对父亲饱含深情,很早就将父亲接到了省城哈尔滨,可谓尽到了孝道。但父亲在城市里不适应,晚年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再加上诗人一家搬迁到天津,而父母一直都与诗人一家生活,这次却因要照顾在哈尔滨工作的次子,故没有选择去天津。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了父亲过早地得病离世,对此诗人总感到良心不安,愧对父亲的养育之恩。他在诗中除了表现对父亲的悲悯之外,还有对自己的反思与自责,使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悲壮色彩。
诗的起点在于生命体验,一首诗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的亲历行为的记录。生命因体验而精彩,变得更有意义,而诗歌就是一次重返生命的过程,生命因诗而升华,人生因诗而充满期待。罗振亚先生的诗歌以情感为依托,在现代人本思想观照下,探寻回归生命本真的路径,谛听内心真实的声音,由此把握有限生命中的恒远意义。同时,这种重临诗歌崇高价值与尊严的诗歌写作,也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抒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