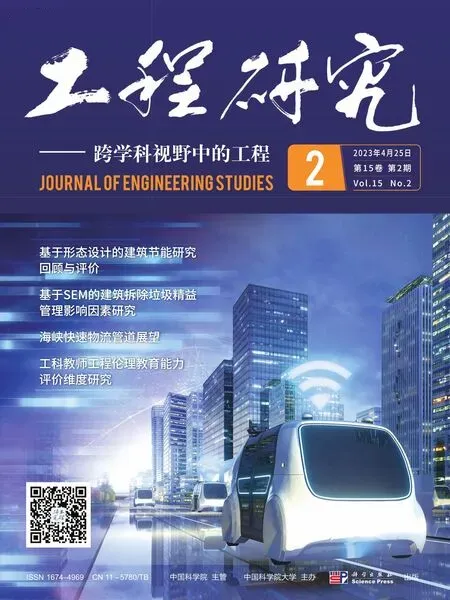论古代工匠的职业特征、技艺传承及社会地位之变化
——由柳宗元的《梓人传》谈起
厚宇德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太原 030006
1 柳宗元及其《梓人传》
工程师指具有从事工程操作、设计、管理与评估等能力的技术人员。首席工程师则是整个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是工程师们的管理与指导者。在中国古代的工匠群体中都料匠或总工匠的职责类似于现代的首席工程师或总工程师。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公元773—819年),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一贬再贬的官场生涯中,他的生活和思想愈发接地气,因此能够更加关注和了解社会底层。他了解捕蛇者(《捕蛇者说》[1]138)、他说车(《说车赠杨诲之》)[1]140、他关注种树之道(《种树郭橐驰传》[1]145)、他知悉黔无驴(《黔之驴》[1]165)、他写《进农书状》[1]325、还代人写《进瓷器状》[1]325、他关注种甘树[1]365、种木槲花[1]366、种朮[1]375,等等。本文从聚焦于他的《梓人传》[1]146-147开始。
唐贞元21年(公元805年,这年8月后即改为唐宪宗元和元年),33岁的柳宗元,随着唐顺宗于该年正月即位,迎来了自己在长安李唐王朝参与政事的巅峰时期,官至尚书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陆质、吕温等成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至7月唐顺宗禅位,唐宪宗登基,王叔文政治集团败北,9月柳宗元受牵连被贬邵州刺史,人未至而11月再贬为永州司马。在此期间柳宗元的著述中有1篇《梓人传》。在明代嘉靖时期刻本《河东先生集》①柳宗元撰,(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龙城录、附录各2卷,集传1卷)明嘉靖年间郭云鹏济美堂翻刻宋廖氏世彩堂本。该本雕镌精善,摹刻逼近原刻,世称善本。第十七卷中,为本文注曰:“公盖托物以寓意端为佐天子、相天下,进退人才者设也。”(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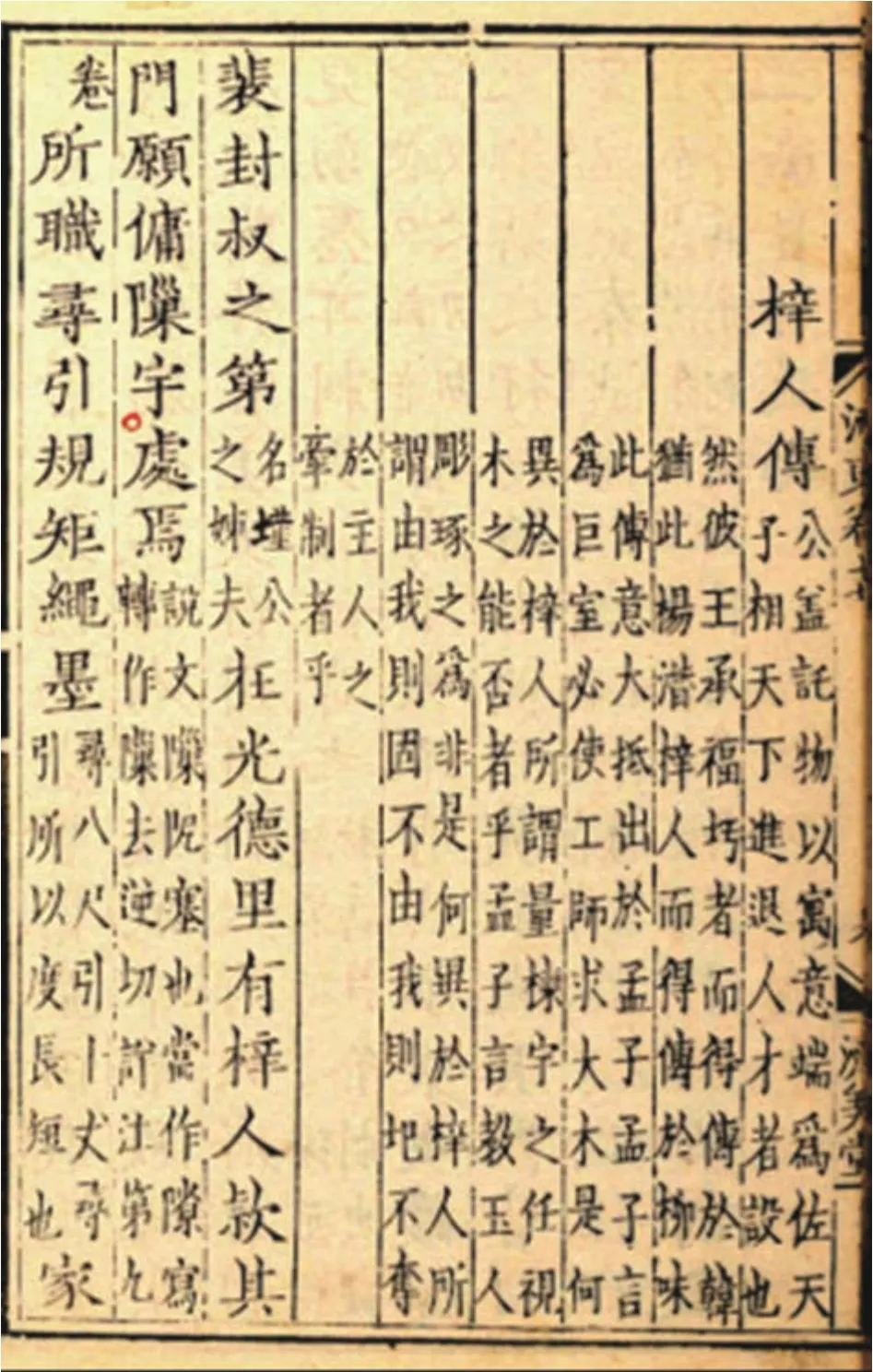
图1 明嘉靖年间郭云鹏济美堂翻刻宋廖氏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中《梓人传》首页Figure 1 The front page of “Ziren Zhuan” in Hedong Xiansheng Ji.Reprint edition by Guo Yunpeng’s Jimei Hall from Song Liao Shi’s Shicai Hall edi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jing of the Ming Dynasty
可见,柳宗元撰写《梓人传》之用意不是为梓人树碑立传,也不是讨论工程问题,而是依托谈论梓人的故事,阐述自己的政治观、人才观与贤相观。但是由于该文对工匠群体尤其对梓人的描写细致、专业而形象传神,因此也不失为了解古代匠人群体的重要文献。梓人在中国古代一般指建筑、乐器制造以及印版雕刻等领域的木工匠,在《梓人传》中,柳宗元所说的梓人却具有与此不同的含义。柳宗元对梓人和普通工匠做区别对待,文中工匠简称为“工”,如在“将求他工”“会众工”“执用之工”等说法中,“工”均指工匠;全文没有混同“梓人”与“工”之处,还在文末特别指出:“梓人……今谓之都料匠云”,强调文中的梓人不是一般工匠,而是专指都料匠或总工匠。站在今人的视角,过滤掉柳宗元文中的政治寓意,再看《梓人传》,其最为突出之处无疑是揭示了梓人即首席工程师的职业特征,以及首席工程师与一般工匠在职责与作用等方面的根本区别。
在巧妙地刻画梓人方方面面之后,柳宗元借助一个比方,开始点题:天下各级官员(六职百役),“犹众工各有执伎以食力也。”[1]147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天子的宰相,则类似于梓人:“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1]147于是继续阐述宰行当如梓人,天下六职百役应效仿众工的政治主张。
2 柳宗元笔下的唐代梓人即首席建筑工程师
在《梓人传》中,柳宗元借助与梓人接触过程中梓人自己的叙述、在梓人家里以及建筑工地的耳闻目睹,言简意赅阐述了这位梓人的特点、能力与作用。
梓人介绍自己的本领时,首先说明,他善于根据建筑工程的结构与规格,去准确估量各部分所需建材的适当尺度,因而能给工匠们具体而正确的工作指令:“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1]146他不忘加一句话强调其不可替代性,以及其工作的不可或缺性:“舍我,众莫能就一宇。”[1]146梓人还通过描述自己的待遇,再次强化了他远超普通工匠之上的特殊地位:“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1]146柳宗元对这些说法将信将疑,而他在梓人家里见到的却是:“其床阙足而不能理”。这不能不让柳宗元对梓人产生怀疑、露出质疑的眼色,而梓人的回答是:“将求他工(修之)。”[1]146至此柳宗元对梓人产生了坏印象:“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1]146梓人是一位无能却说谎吹牛的家伙。
然而在堆满建材、聚集大量工匠的建筑现场的一次见闻,又令柳宗元大跌眼镜。这位梓人吆五喝六、左右一切,而工匠们各个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1]147在梓人八面威风、大显身手的过程中,大厦不差毫厘地逐渐耸立起来:“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 ’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1]147这场景与当初梓人的自我介绍如出一辙,不会修床断腿的梓人真的有他所说的本事和气度! 工程结束,整个建筑只落款梓人的名号,而与那些累得气喘吁吁的工匠无关:“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1]147这是古代建筑的一种规程,既彰显匠人的声名,也是一种责任担当。
梓人这样一番惊艳的表现,令柳宗元不禁由衷感叹:“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1]147亲眼所见使柳宗元对梓人与普通工匠的区别有了深刻的认识:那些普通工匠,是在梓人的指令下才可以按照要求或斫或锯的劳力者,而梓人则是指挥这些劳力者的劳心者;梓人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地告诉工匠们干什么、如何干,整个建筑工程的蓝图都在他心里;在这样的劳动场面中,普通工匠如同他们手里的斧、锯等,成了无须劳心动脑的工具人,而梓人则是指挥整个工程的智能中枢,是智者。
柳宗元对唐代梓人即都料匠的描写,是否符合古代建筑界的实际情况? 这会不会仅仅是他为了阐述宰相作用之方便而做的文学虚构? 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可以肯定地说,柳宗元对梓人的形象描写符合中国古代建筑界的实际。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描写过宋代最著名的都料匠喻皓:“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皓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皓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2]明代谢肇淛之《五杂俎》载:“国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动声色。尝为内殿易一栋,审视良久,于外另作一栋。至日断旧易新,分毫不差,都不闻斧凿声也。又魏国公大第倾斜,欲正之,计非数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余石置两旁,而自与主人对饮。酒阑而出,则第已正矣。”[3]欧阳修和谢肇淛在各自书中记载的关于都料匠相似的人与事,进一步使我们相信,对于古代建筑工程而言,都料匠的确是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掌管着建筑的标准、督办建造过程;在整个建造工程现场,都料匠是绝对的技术权威,一切均按照其指令行事。柳宗元认为官场宰相的作用很像建筑工程中的梓人;反之,在建筑工程中梓人的作用也像官场的宰相。柳宗元对梓人即都料匠的描写,符合这一职业的历史真实。
3 梓人即古代首席建筑工程师的专业特征分析
一名现代总工程师,在领导管理方面需具有决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人际协调等能力;在智力与天赋方面,要具有较强的观察力、出色的记忆力、擅长逻辑思维、富有想象力[4];在知识积累方面,要有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在阅历上有丰富的工作实践。现代总工程师所具备的这些基本特征,在柳宗元描写的梓人身上,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所体现。梓人即古代总工程师“都料匠”所具有的基本专业特征可分析概括如下:
第一,都料匠熟悉建筑材料的性能,知道建筑结构中的某个部位,需要采用什么尺度的建筑材料。这就是《梓人传》里梓人所说的:“吾善度材”[1]146。总工程师的专业能力、观察力、记忆力与想象力等在此都有所体现。
第二,都料匠脑子里有特定建筑的“图纸”,他对于特定形制、特定种类的建筑的“参数”了如指掌。这就是在《梓人传》里所说:梓人能“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1]147;以及“视栋宇之制”,而知“高深、圆方、短长之宜”[1]146。总工程师的专业能力、个人素质以及其实践阅历在这一条进一步得以深入阐述。
史料表明,中国古代建筑业,应该许多有不著于书、不传于外的专业“理论知识”,比如某种特定规格的建筑所需材料的计算方法。宋代笔记小说中有这样的故事:“郭忠恕画殿阁重复之状,梓人较之,毫厘无差。太宗闻其名,诏授监丞。将建开宝寺塔,浙匠喻皓料一十三层,郭以所造小样末底一级折而计之,至上层余一尺五寸,杀收不得,谓皓曰:‘宜审之。’皓因数夕不寐,以尺较之,果如其言。黎明,叩其门,长跪以谢。”[5]大名鼎鼎的喻皓在设计建造开宝寺塔时,设计与预算有疏忽,而精通建筑设计专业理论的郭忠恕根据喻皓的建造小样,从塔最底一级“折而计之”就发现了其中的纰漏。能“折而计之”想必应该存在可靠的标准算法。因此,梓人即都料匠应该掌握着一般拉锯抡斧的匠人所不具备的更多高深专业技术知识。
第三,都料匠是建筑工程项目的现场总指挥,工匠们在都料匠的调度和指挥下工作:“指使而群工役焉。”[1]146工匠们的工作必须在都料匠的指挥和监督下才能进行,而绝不能私自轻举妄动:“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1]147此处展示的主要是总工程师的现场组织与指挥能力,由此可以感受到梓人丰富的实践经验。
第四,都料匠在建筑工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技术权威性。都料匠所具备的以上专业能力,不是一般工匠所能掌握的。因而都料匠得以成为建筑工程中的不可或缺者:“众莫能就一宇。”[1]147梓人作用的不可或缺性,是其能力与素质超众、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非常人所能掌握这一事实的间接反映。
第五,梓人与一般工匠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梓人是动嘴而不动手的待遇优厚管理者,而工匠们是依计而行的被管理者,二者的地位存在巨大差异。从贡献方式上讲,梓人是靠大脑吃饭的智慧劳心者,而工匠们则是靠手吃饭的劳力者[1]147。柳宗元将二者的这个差异做出了极限性的描述:独撑整个建筑场面的梓人,竟然可以连工匠最基本的工作能力都可以不具备——家里的床腿断了都不会修。这种本质区别所反映的仍然是梓人工作的高度专业知识性与高度智力性。
第六,都料匠具有极为丰富的建筑实践经验。这在前几条中已经有所体现,明代谢肇淛著作中记载的关于宋代喻皓的故事更加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喻皓最工制塔。在汴起开宝寺塔,极高且精,而颇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盖汴地平无山,西北风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钱氏在杭州建一木塔,方两三级,登之辄动,匠云:‘未瓦上轻,故然。’及瓦布而动如故,匠不知所出,走汴,赂皓之妻,使问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必不动矣。’如其言,乃定。”[3]1586
梓人(都料匠)具有与现代总工程师的诸多类似性,说明他们的确隶属于同一职业。但随着现代科技不断向工程中的输入,当代工程专业化程度与复杂程度都进一步加深,现代总工程师还具备古代梓人(都料匠)所不具备的其他职责。如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效益等等[4]15-17。这些任务在古代往往是无需梓人(都料匠)考虑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工程,比如宫殿、庙宇与楼塔等在形制和格局上有诸多必须遵守的限制,与此相关,梓人(都料匠)的工作具有更多程式化的色彩,相对而言无需过多的创新与变革,更需要的是记忆与依图造物能力。
4 古代工匠技艺传承与社会地位等问题试析
4.1 技艺传承观念、技艺传承难题对技艺传承的影响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手工业社会,包括都料匠在内的工匠是任何朝代都不可或缺的职业。但技艺巧夺天工的能工巧匠又一直稀缺如凤毛麟角。明代谢肇淛认为历史上能工巧匠不乏其人:“今人语工程之巧者,必曰鲁班所造,然鲁班之后,世固未乏巧工。”[3]1586然而,巍巍两汉、大唐盛世也不过数人:“汉之胡宽、丁缓、李菊,唐之毛顺,俱载史册。”[3]1586300年赵宋王朝则只有1人而已:“宋时木工喻皓,以工巧盖一时,为都料匠……识者谓宋三百年一人而已。”[3]1586谢肇淛要阐述“世固未乏巧工”之见解,然而展示出来的却是“世固乏巧工”的局面。“世固乏巧工”基本上符合史料展示的历朝历代能工巧匠的现实生态。决定这一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表面看来,技艺传承是其中最直接的因素。
在中国古代拥有一项高超的手工艺技能或其他技艺,不仅可以保证自己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往往还可以闻名于世,甚至足以为子嗣后代的生活提供保障。清代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的阮葵生认为技艺有成的匠人们的生存状态,远远超越了没有一技之长、一事无成、默默无闻的读书人:“昔人治一业、攻一器,足以传世行远而不朽,较之抱兔园一册,饱食终日,老死牖下,淹没而无闻者,不可同年语矣。”[6]阮葵生列举了他所处时期治玉、治玛瑙、治犀、治金、治银、治铜、治锡、治铜炉、镶嵌、治竹、漆竹、治扇、治琴、治镜、治墨、治砚等众多手工艺领域的代表人物,说这些人:“皆名闻朝野,信今传后无疑也。”[6]2964不无赞许和羡慕之情。阮葵生的认识符合中国早期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如《考工记》所言:“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7]宋代人说:“三代之时,百工传氏,孙袭祖业,子受父训,故其利害如此详尽。”[8]然而在中国古代技艺失传也不是稀罕事,也常可见之,如“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9]这说的是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故事。
技艺是否传承有时是技艺拥有者的个人行为。有的人积极招徒传授,有的人甚至著书立说而使自己的技艺流行于世,宋代的喻皓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行于世。”[2]603对于高超的技艺而言,技艺拥有者即使想传于后人,也未必能找到足以掌握这高超技艺的继承人。《庄子》中说的造轮巧匠就没有办法将他的技能传授给其子:“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10]这种传而不得其人亦可造成失传。宋代笔记小说载,黄振是宋理宗时的著名宫廷琴师,他也没有办法将他的本事传给其子:“琴师黄震,后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指宋理宗)悦其音,命待诏御前,日给以黄金一两。后黄教子,乃以他艺入。语以‘尔子不足进于琴耶? ’黄喟然叹曰:‘几年几世,又遇这一个官家! ’黄死,遂绝弦云。”[11]值得留意的是,宋理宗问黄振为什么不把琴艺传给儿子,而当黄振说其子学琴属朽木不可雕也后,宋理宗未再问为何不寻他人而教之等问题。可见,在宋代绝技内传已经是司空见惯的风俗。绝对的不可学是不可能的,谢肇淛的说法更为真实——悟性和天赋欠佳或不足者,虽然可以继承一些技艺规则,但是难以获得技艺之神似与真谛,久而久之“渐失玄妙”,近乎失传:“梓匠轮與,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至于穷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即几希之间,难于登天。若曹元理、赵达算术,再传之后,渐失玄妙,非不传也,后人聪明无企及之故也。”[3]1586在技艺传授与学习这对矛盾中,多数例子说明的是由于学习者天赋不足而导致的技艺失传;也存在相反的即受传授者表达能力限制而不能顺利传承的例子。柳宗元所撰《龙城录》载,李照好古博雅,不愿意做官却乐于搜集和研究古器物,自战国至唐的精制奇巧器物,“谱所载者十得五六”,清楚器物的传承及机巧原理,后世无人有此造诣(后世莫迨)。遗憾的是由于李照“颇为文思涩”,而无法将他收藏的器物及对它们的独到研究付诸文字。柳宗元对此极为感慨:“设诸勤求古器心在于文书间,亦足以超伟于当代也。”[12]
想传尚且未必能传,而不想传的结局必然是失传。南宋周密说:汉代张衡发明的“候风地震之器曰地动仪者,无传焉。”[13]究竟是张衡不传还是欲传而不得其人,难以断定。唐代笔记小说载王潜是明确有绝技而不传的人:“王潜在荆州,百姓张七政,善止伤折……其术终不肯传人。”[14]宋代的李处士也是这类人:“石晋时,关中有曰李处士者,能补石砚。砚已破碎,留一二日以归,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传……”[15]技艺拥有者不传技艺的理由可能多种多样,出于家族层面对技艺传承的限制,核心在于保护家族利益。宋代亳州有实例,这里有两家曾长期垄断着轻纱纺织技术:“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俱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16]在医学方面清代萧山韩氏垄断特效药方,为的也是保护家族利益:“癫狗、毒蛇咬人者多死,方书虽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萧山韩氏所传五圣丹获效如神,救人不可胜数。韩氏惟制药施送,秘不传人。”[17]
传统手工技艺及医术垄断,维护的是技艺拥有者个人或家族在特定地区的垄断地位,直接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或家族的利益。古人尚不能明白,放弃技术垄断并合理竞争有利于强化家族的进取心,带来区域性技艺领先和整个行业的繁荣。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个人和家族反而会获得更多更恒久的利益。据笔记记载,宋代善医的官员高文庄就曾带动整个郓州医学人才的辈出:“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孙兆、杜壬之流,始闻其绪余,犹足名一世。文庄,郓州人。至今郓人多医,尤工伤寒,皆本高氏。”[18]文献记载,明清时期在我国多地出现了多处手工业之乡,有的地区的手工技艺闻名遐迩,极大地带动了一方的繁荣。如明代笔记说:“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19]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20]从一个行业侧面揭示了苏州地区手工制造技术底蕴之深厚。而清代笔记说:苏州“百工士庶,殚智竭力,以为奇技淫巧……”[21]说明苏州地区的手工艺传承后继有人,保证了一方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堪称奇迹,历史上有些地区曾有过我们今天很少知道的手工业繁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以传之久远。五代笔记中记载的淮南地区就是这类地区的代表之一:“淮南,巨镇之最,人物富庶,凡所制作,率精巧,乐部俳优,尤有机捷者。”[22]明清时期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亦曾是学界讨论的热题之一。总之,单从历史上技艺视角总体来看,中国古人的技艺传承观念,对于技术的深刻革新和工业化进程,都存在着不小的阻碍。
4.2 匠人的社会地位对技艺传承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肯定的是在商周时期工匠和医生在体制内具有较高的地位。如《考工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7]117在《周礼》中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均位于天官之列[23]。然而随着两周的礼乐崩坏,这些社会规范不复存在。在后世的正史中掌握特殊技艺的社会群体中的佼佼者,仍有机会载入列传中的“方技”环节,但其社会地位明显不如前。春秋时期管子还很重视“工”阶层的社会作用,将其与士农商并提:“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4],但是明确强调:“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24]230士农工商之间的不同社会等级观念已经十分明显。不杂处则使得“士之子常为士”[24]230、“农之子常为农”[24]230、“工之子常为工”[24]230、“商之子常为商”[24]231,从而社会阶层得以稳定和相对固化。到了唐代,“方技”之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低落,有时候一个读圣贤书成绩出色的人,如果还掌握某种特殊对社会有价值的技能,那这特殊的才能不但不能给他带来名利,还会严重影响他的社会地位。据载孙思邈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朱子《小学》笺注云:思邈唐之名进士,因知医理贬为技流,惜哉! ”[25]宋代人继续贯彻管子的思想,使工士农不杂处:“工在衢,士在朝,而农在野。”[26]而“商”甚至被驱除于四民之列。虽然为“方技”人物设置了“伎术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了官称的伎术官就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了,宋代笔记明确记载:“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并列),贱之也。”[27]
明代初期,“百工”的技艺开始沦为“鄙事”之列。刘基编撰的《多能鄙事》一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日常实用技术。在理念上明代仍然肯定和宣传源自管子士农工商不能杂处的主张:“《管子》以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吪,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于田野,处工必于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28]明代人还明确指出达官必须与包括巫祝匠艺类人保持距离,并以具体事例论证这种做法的重要性:“当官不接异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疏绝,至于匠艺之人,虽不可缺,亦当用之以时,不宜久留于家,与之亲狎。皆能变易听闻,簸弄是非。儒士固当礼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辞,或假字画以媒进,一与之款洽,即堕其术中。如房琯为相,因一琴工黄庭兰出入门下,依依为非,遂为相业之玷。若此之类,能审察疏绝,亦清心省事之一助。”[28]1123然而事实上,这种主张在明代已经难以严格执行,所以才出现明代人的如下感叹:“呜呼,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业,则民志定矣。民志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28]1025对于明代出现的观念改变留待下节再叙。
那么,匠人社会地位的持续走低,对于手工技艺的传承有何影响呢? 宋代人说:“三代之时,百工传氏,孙袭祖业,子受父训,故其利害如此详尽。”[8]3151这类叙述都含有一个言外之意:在古时候,人们重视技艺,其传承因而有序,但是到了后世,匠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随之技艺传承的重要性也自然“昔非今比”。清代徐大椿认为中医自唐宋以来,总体水准是一路走低的。在他看来,中医整体水准江河日下根本原因就是医术越来越不被看重而成为“小道”,行医者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卑贱:“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业不甚贱乎? ”[29]医术以及医生社会地位的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优秀人才不再乐于从医、悬壶济世:“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29]自序:9.;“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29]自序:10中医从业者由此别无选择而都是“贫苦不学之人”[29]96,从医者素质低下“不能深通经义”[29]96,看不透前代医藉、无法继承前人医术,其必然结果是:“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29]自序:10某一行业的社会地位高开低走,最终导致这个行业后继乏人、整体式微,徐大椿由中医变迁揭示的这个道理,对于其他行业手工业同样适用。可以仿此对其他具体行业后继有人与否以及行业的整体走势,做类似分析。
4.3 匠人职业态度和精神对技艺传承的影响
古籍所载告诉我们,古代“方技”的职业态度和敬业精神,总体上也呈现滑坡的趋势。明代谢肇淛认为学者、士大夫沉不下心来“精究”学术,是导致“古乐不复作”的重要原因:“古乐不复作矣……至于今日,上之人既不以为急务,而学士大夫亦无复有深心而精究之者。”[3]1761-1762清代的阮葵生对比古今匠人所造之物,得出后世之人苟且做事态度导致器物今不如昔:“古人作事精致,不吝工夫,非若后世贱丈夫苟且成事。故古器必款细如发,而匀整分晓,无纤毫模糊。……尝见旧家所蓄数器皆然,及观赏鉴家所藏,亦无弗然者。”[6]2955
如从刻版印书行业去看,这一变化的历史线索非常清晰:中国古代书籍印刷业质量空前绝后的巅峰出现在宋代,在其之后,总体一代不如一代。当然这也不排除在后世有特殊典籍印制极为考究的少数特例。宋代朱弁比较前世和宋代的书籍后说:“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30]这可证实宋代书籍质量优于前代的可信事实。后世人也持此观点,如明代的朱国祯说:“刻书,以宋板为据,无可议矣。”[31]肯定了宋代刻版印刷大权威性。明代的谢肇淛更加细致地说明了宋代刻板印刷受世人推崇的原因有三——刻版字如书法,印纸择上乘,校对求精准:“书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3]1776
谢肇淛不仅研究了宋代刻版印书成功的原因,将宋代和明代两相对比,他还解释了明印书籍多有粗制滥造的原因——宋代人精益求精,以求传世为目标;而明代人刻印书籍,意在急切赚钱取利:“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而丑恶极矣。……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靡,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3]1776这个事例说明,求利润而不存在行业良好竞争机制时,特殊时期商品质量下降似乎是在所难免的。20世纪在我国开放市场经济之初的一段时期里,有的地区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而著称也是一个现实例证。在这样一个连产品(书籍)质量都不在意的商业背景下,技艺传承还会有精益求精的高质量保证吗? 人们还会很尊重技艺并在乎技艺的传承吗?
4.4 明代匠人社会地位的明显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如前文所述,虽然在理念上依然在奉行管子士农工商不杂处的理念并将百工所为归于“鄙事”,但是有证据表明,在明代至少有些领域的“方技”人的社会地位有显著的提升。首先在明初医生、匠人和府学生一样有资格参加乡试:“应天府乡试,国初自府学生、增广生、监生外,如未入流官吏、武生、医生、军余、舍人、匠之类,皆得赴试,皆得取中。”[32]这是从体制上对学医、为匠者们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
不仅如此,在明代著名的工匠除了会获得皇家或官府的名誉认可和物质奖励,他们还可以直接进入高级官员行列,这与明代以前的唐宋等时期相比,已经有了难以设想的进步。苏州人蒯祥是皇家木工首,后来因为营造有功一路擢升由工部营缮司主事员外郎到太仆少卿,再到工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最后“其禄累加至从一品。”[33]另有《五杂俎》载:“国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3]1586;不仅如此,“又有蒯义、蒯刚、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3]1586。除了木匠还有高升的石匠,如沈德符说:“宣德初,有石匠陆祥者,直隶无锡人,以郑王之国,选工副以出,后升营缮所丞,擢工部主事,以至工部左侍郎。”[34]
在明代,木匠和石匠出身者一个个擢升为国家高级官员,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明代,至少营造类的匠人只要有超人的技术,可以如同读书人一样步入仕途,还可以在官场飞黄腾达。毫无疑问这是对这些行业从业者社会地位的极大提升。这种社会现实即使不能改变世人对于百工的固有观念,至少使营造匠人鄙贱的观念不攻自破。如果考虑到这一层,再看明代出现的“木匠皇帝”明熹宗以及他的行为,也就不会再那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先帝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可惜玉体之心思精力,尽费于此。”[35]一个皇帝,常常与一班大臣探讨家具制造与发明,无疑会对这一行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熹宗出于爱好在此领域废寝忘食无可厚非,需要被指责的是他的动机和做法:喜而思,思而朝夕营造,但是却“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和特权阶层的任性,而丝毫没有考虑他的研究对整个社会营造业贡献些什么,为天下苍生创造些什么。
只有了解到在明代至少某些领域匠人社会地位的明显提高,再看明代家具制造、铜器制造取得的空前成绩,在逻辑上才会萌生较为自然的感觉印象。
5 余论
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观念认为,中国古人只重视应用技术而不注重理论思考与建设,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且不论重视应用是否为抑制科学诞生与发展的根本力量,以史料为依据去做较为细致考察,有助于看清中国古人是否真的做到了持续而理性地重视和发展应用技术。在古代社会,价值观、是非观、善恶观、美丑与贵贱观等等,主要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在现象层面,封建社会高层统治者的观念与喜好,对全社会的基本观念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会波及并影响有些行业及其技能的社会地位,成为影响古代匠人、艺人荣辱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现实社会需要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不低于某个水准的基本保障,丧失这一基本保障,就不能维持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农工商以及其他一些行业和技能自然地应运而生。这些行业及其积累的经验与技能是社会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根本支撑。依照通常的逻辑,封建统治阶级理应对这些行业及其积累的经验和技艺极为重视。但现实中有两种态度可供他们选择:第一,投入人力物力,重视并持续支持社会所需要行业的存在、创新与发展;第二,不遏制,但是对于生产技术,只以满足社会存在的基本需要为目标,而并不鼓励其持续创新与发展,也不追求通过技术革新推动全社会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而从总体看来,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选择了后一种态度。这一认识可以通过一个极端视角予以反映。中国古代多个中原王朝都无法摆脱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侵扰。按照常理,国家因此一定会以史为鉴,极为重视军队的武器性能以及国防设施,并设专门重要机构时刻监视敌对势力的军事实力。然而,事实上却见不到任何朝代思路清晰的对能左右战争的主导武器的积极、持续的高投入研发,国家也不存在对周边敌对势力武器装备等情况有效的密切监视。而失去这两点,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就做不到对外拥有绝对的军事压制力。所以,历史上多次重演和亲、和谈、割让、赔款甚至亡国的剧本。对于足以决定国家安危的军事技术,封建统治阶级尚且采用如此态度,对其他行业技术更缺乏真正的重视就不难理解。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国家层面明晰主导的技术发展理性策略。
在科学技术与艺术等领域,中国人充满智慧和才华。正如笔者曾指出:“只要社会价值体系对社会活动(生产、发明、创造、艺术创作与表演等)具有高收益回报的激励,就会有人投身这一社会活动中。只要给予持续的激励,并营造合理的竞争氛围,相关事业就能从一个高度向另一个高度不断发展,造就繁荣和行业巅峰。在中国古代社会凡是存在这种持续激励机制的领域,如玉器雕琢、瓷器烧造、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人们就有动力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创造奇迹;相反在不存在这样持续激励的领域,人们就没有动力将时间、智慧投入其中,因此就不会出现繁荣,即使偶然有所发现与发明也是昙花一现。”[36]如果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不尽如人意处,几乎都出于同一原因——缺乏科技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