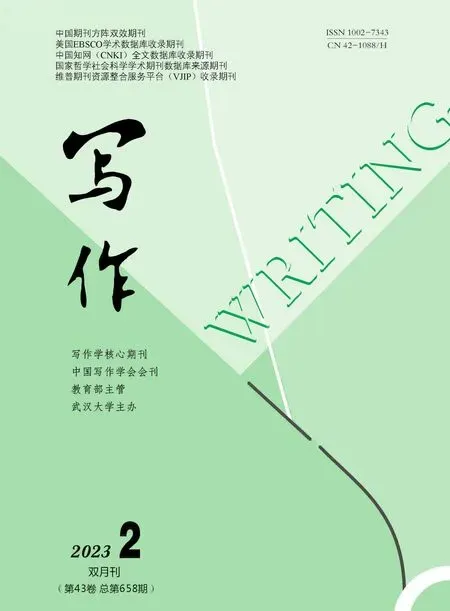在阅读经典中写作
——文学创作对谈
涂慧琴 丁小龙
丁小龙是一位优秀的陕西青年作家。他从24 岁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几十部作品,以中短篇小说居多,也有文学随笔、诗歌和文学评论,另翻译并发表了托妮·莫里森、科尔姆·托宾、萨曼·拉什迪与珍妮特·温特森等人的中短篇作品。2022年12月9日,他与湖北工业大学英语系2020 级文学方向的学生分享了他的写作和阅读体会。此次分享会由涂慧琴主持,并邀请影评家、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张阅作为会谈嘉宾,就“在阅读经典中写作”展开了精彩讨论。本文基于此次会谈内容整理而成。
涂慧琴:丁老师,你好!你的小说集《世界之夜》和《岛屿手记》深受很多读者的喜爱,并在读者群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世界之夜》,采用了一种寻根溯源式的书写,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时空差距感,具有探索性和先锋性。请问你在创作过程中,受到经典文学作品的影响有多大?
丁小龙:《世界之夜》是我在二十四五岁时写的小说集,包括三部中篇小说和一篇后记。第一部中篇小说是《空心人》,有8万字;第二部是《世界之夜》,有4万字;第三部是《押沙龙之歌》,也有4万字。这三部中篇小说代表了我当时的文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也由此显现出自己当时的心境与体悟。《空心人》的灵感源于T.S.艾略特的同名诗歌。作为西方现代诗歌的大师级人物,T.S.艾略特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并影响了后世的很多作家和艺术家。他的代表作有《荒原》和《四个四重奏》。我很喜欢这两部作品,读过英文原著和中文译著。《四个四重奏》和《荒原》是属于20世纪的典范之作,也属于它们还没有诞生之前的世纪,更属于人类的未来时代,是越过时间的经典作品。所谓的经典作品,就是能够同时面对过去、当下与未来,其属于所有的时代,并且具有超越时间性的精神特质。读完艾略特的《空心人》后,我同样受到了强烈的心灵震撼:这首诗写的不就是我吗?那些面对世界,面对虚空,面对存在,面对时间的整体性的想象,但这种整体性的想象又带有碎片性的现代特质与解构性的后现代色彩。当我准备写《空心人》这部小说时,我还没有想好这个故事的具体内容与结构。在读了艾略特的同名诗歌后,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空心人”这三个字。我凝视着这三个字,感觉它们在召唤我去写一个属于我的故事,也属于更多人的故事。那个下午,我又听了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内心涌出了一种在黑夜里被照亮的感觉。面对空荡荡的文档,我静坐冥想,等待着灵光的降临。经过半个小时的内心跋涉后,我在文档上敲下“他们都说我是一个罪人”。随后,小说的内容从无意识的深海中慢慢浮现。创作是神灵附体。这个神灵指的是一种更高的超越性存在,是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注入你的身体,注入你的灵魂。于是,你进入一种忘我境界,一种无我状态:写作,就是从“我”到“忘我”,最后抵达“无我之境”。写下第一句话后,记忆的窄门被打开了,而我有种被启明的感觉。那时候,我过上了双重生活:一边是日常性的工作,一边是神圣性的写作。如同史铁生所说的“写作之夜”:你走进了窄门,你遇见了更多的自己。
第二部小说是《世界之夜》。当时要给杂志写一部中篇小说,于是我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翻看眼前的书,心里是空空荡荡的原野。之后,我的目光停留在了海德格尔的某部作品中,里面有一句话触动到了我:“世界之时的夜晚已趋向其夜半。世界之夜弥漫着黑暗。”①[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我凝视着这句话,仿佛深渊凝视着我。这句话照亮了我,也打开了我。我特别钟情于现代作家,对现代作品更有感觉。我想让《世界之夜》更具有探索意味与先锋色彩。于是,我采取了一种戏剧结构,一种时间倒流的形式,从主人公的衰老和死亡时刻,倒流到他的出生时刻。第一幕是他的中老年时期,第二幕是他的青年时代,第三幕是他的童年时代,最后一幕则采用了未出生孩子的视角。结构决定了作品的整体性框架。在把这个结构想清楚后,写起来就比较顺畅了。在写作时,我们的心底要有一个整体性结构,而这个结构要有象征意味,对主题有升华作用。只要把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了,内容、语言、形式和主题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所推崇的中长篇作品,都拥有独特的结构与非凡的形式。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是真正的结构大师,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有创造性的结构。在外国当代作家中,阿特伍德和库切是这个领域的文学大师。
最后一部小说叫《押沙龙之歌》。因为当时要写一部带有儿童成长性质的小说,但我又想和前面两部中篇小说写得不太一样。经过一番思索后,我选择从儿童的视角入手,并且带有自传色彩。刚开始写作时,这部小说一直没有确定的名字,之前想的四个名字被我否决了。小说的名字特别重要,是小说的眼睛,也是小说的灵魂。写到三四千字的时候,我的目光游离在了书架上的福克纳作品集。福克纳有一部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相对于《喧哗与骚动》和《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不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但是体量相当庞大,象征意味也非常浓烈。看到“押沙龙,押沙龙”这六个字后,我突然被点亮了,眼前的黑暗也烟消云散了。押沙龙是《圣经》中最美的男子,而“押沙龙”和我所要写的这部小说在主题上是相契合的、是有共鸣的。我走出了黑暗密林,走进了写作的新天地。有时候你可能暂时想不到好的题目,但是请耐心等待,灵光会在恰当之时降临。经过长久跋涉后,你终究会遇见光。写作是对耐心的考验。只有你写到1000字,写到3000字的时候,有些东西会在路口或者拐角处等着你:这就是所谓的灵光时刻,也是所谓的繁星时分。
这就是我第一本书的大概情况:三部中篇小说是三种方法,也是三种艺术探索。写作是对世界的想象,是对自我的探寻。三部作品所受到的影响也不太一样。《空心人》受到T.S.艾略特诗歌的影响,也有加缪的《局外人》和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的启发。《世界之夜》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也受到李沧东的电影《薄荷糖》的启发。《押沙龙之歌》受到了里尔克诗歌的启发,也受到了《小王子》《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芒果街上的小屋》等小说的影响。
涂慧琴:你的《世界之夜》受到这么多作家的影响和启发,其实也体现了你平时的阅读量。大量的文学阅读使你的视野更加开阔,写作思路愈发清晰。你怎样看待平时的阅读量呢?
丁小龙:写作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祈祷。在写作的时候,你的灵感、你的想象、你的资源来自方方面面。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并没多少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大量的阅读是我重要的写作泉源。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读过的书像吃过的饭一样,感觉读完了就没有了,不见了,消散了。然而呢,你不知道哪一天它突然会从你的内心生长出一棵大树,甚至是一片森林——写作就是林中寻路,海上觅岛。你当下的写作,是对前辈作家的回应和回响。你的阅读史和心灵史,彼此会构成镜像关系。不仅要阅读文学经典,也要阅读哲学经典、心理学经典,甚至更广泛地讲,要阅读经典电影、经典音乐、经典美术。扩大自己的阅读量,以此来拓展自己的精神疆域。当你的阅读达到一定境界时,那些营养就是你的扶梯,是你在写作之夜的微光。你在写作中会遇到更多个自我——写作就是寻找自己、发现自己与创造自己的过程。
涂慧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吸引住大量的读者,肯定有其独特的文学性和艺术魅力,这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作家必须具有创造性。请你谈谈作家的创造性问题。
丁小龙:我特别看重作品的创造性。为什么莫里森的作品能流传下去?福克纳的作品能流传下去?卡夫卡的作品能流传下去?因为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与风格。每一个时代,包括19世纪、20世纪能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有着共同特点:第一是具有创造性,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风格;第二是显现了时代精神与心灵真相。比如,莫里森捕捉到了黑人的生活真相与精神历史。从《宠儿》到《所罗门之歌》,从《天堂》到《恩惠》,她为时代精神与个人心灵赋予了微妙且深刻的艺术形式,也丰富了文学创造的可能性。《宠儿》的写作技艺是多么精湛美妙,作品内涵是多么丰富深刻。更为重要的是,她捕捉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多年后,卡夫卡变得越发重要,而我们越发领悟到《城堡》《审判》《变形记》等作品的伟大启示。卡夫卡不仅抓住了他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也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这也是杰出作家的共同标识。哪个作家能抓住人类的精神状况,并用创造性的方法将其显现,同时又可以给人类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新目光与新视角,那么,他的作品就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就有可能进入艺术的万神殿。
文学也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情,绝大部分作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淘汰、被遗忘,因为这些作品其实是对时代的复制,并没有开创性的精神价值。有的当时很热闹,很畅销,但没有抓住最本质的东西,所以很快就会被大众遗弃,被时间淘汰。只有极少数的作品能够留存,这便是艺术的真相。所谓的文学经典,就是其同时面对过去、现在与未来,而时间则是一座通往彼岸的浮桥。如果要写作,还是要多阅读文学经典、艺术经典,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如何将私人体验转换为公众体验,这是每一个创作者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如果你要创作的话,你就要懂得创造性地去吸收经典作品的精华。只要把这些经典作品装在心里,你就不会惧怕任何东西,你就会拥有一种笃定的信念感。当你把《红楼梦》《神曲》《浮士德》《复活》《魔山》《城堡》《百年孤独》《所罗门之歌》等作品装进自己的心里,你就可以面对任何文学作品,你就可以面对任何人生问题。把经典装在心里,你就会获得一种清静之心、恒远之心、慈悲之心。在面对后来的作品时,你就会与经典作品进行对照。把经典作品放在心里以后,你会对自己的写作提出很高的要求。在你写作时,托尔斯泰、卡夫卡、伍尔夫、马尔克斯、莫里森等作家会在耳边呼喊与细语,会形成你的参考体系与精神坐标。如果自己写得太烂,你都不好意思示人。
涂慧琴:如果我们对经典作家有更多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也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可以说,作家与作家之间存在着影响与经典传承的关系。
丁小龙:对,《喧哗与骚动》的标题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押沙龙,押沙龙》源于圣经传统。《八月之光》中“光”的概念源于《圣经》与美国南部的民间传统,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写作就是要把现实与神话,把本我、超我和自我,把时间与存在等多种关系同时打开,也就是要打开外部世界的空间和内心经验的空间。作家要做海洋,把自己放在最低处,接受所有的河流。福克纳与圣经传统、西方人文传统、现代思想思潮有相当深刻且微妙的关系。这也是作家之间传承的问题。福克纳是开山辟地的大师级人物。莫里森的研究生论文研究的是伍尔夫和福克纳的文学作品。把她的研究对象、精神来源弄清楚后,你就不会感到惊讶,为什么《宠儿》走了这条路,而《天堂》选择另一条路。莫里森受到的影响很多,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继承了福克纳和伍尔夫的现代派写法;第二是圣经传统;第三是非洲文化的滋养。当然,也包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些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波与思潮讨论。她巧妙地吸收这些资源,并在写作中融会贯通。当你写作时,你所知道的一切会同时向你涌来,于是你要成为大海般的作家。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的思想资源,他的精神资源,他的写作资源是丰富多样的,而他拥有创造性转化这些资源的能量与天赋。
这几年,我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文学体验。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沉迷于外国文学作品,尤其喜欢伍尔夫和卡夫卡。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以后,我开始系统地研读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也读中国古代的作品,包括《易经》《道德经》《论语》《金刚经》等等。如何将东方丰富的思想资源与西方优质的精神财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对于当下的中国作家而言尤其重要。我特别喜欢赫尔曼·黑塞。他对德国文化,包括欧洲的那些精神性的东西,领悟得尤其深刻。与此同时,他对道家思想、佛教文化、印度教义等也有相当精深的研究。他的作品创造性熔炼了这些思想中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与人的心灵世界密切相关,于是收获了无数的读者,成为不朽之作。比如,他的《悉达多》来自东方思想,讲述了一个古印度觉醒者的人生历程,而他从西方人的视角去写,显现出更多的精神意味。再比如《荒原狼》,写的是一位西方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这部作品借鉴了荣格的心理学,也吸收了东方的思想精华,并试图为人类的困境寻找文学上的出路。为什么黑塞的作品一直被人反复阅读呢?这是因为他写出了存在的本真与虚无的本义,同时也创造性地吸收了多方面的精神资源。
陈忠实有一本关于《白鹿原》写作的札记,名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在这本书里,他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精神性的剥离。在写《白鹿原》的时候,他进行了大量的有规划的阅读,进行了所谓的精神性思考。如果你立志于写作,就要多阅读,多思考,多领悟,在领悟中,抵达写作的岛屿。
涂慧琴:其实,我们湖北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陈应松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一部短篇小说时,就被这部小说吸引住了,并决定以后一定要去阅读他及其他湖北作家的作品。作为一名陕西作家,你觉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陕西作家们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丁小龙:因为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百年故事的写法,所以我先讲贾平凹。在贾平凹出版的18 部长篇小说中,《老生》的名气不是最大,但我对这部小说情有独钟。首先,它的历史跨度比较长。他的作品一般聚焦当下生活,譬如《秦腔》《废都》《高兴》,但《老生》对准了历史,写的是秦岭地区的百年故事。其次,他在《老生》中引入《山海经》,把《山海经》当成叙事的参照性背景,并由此构成作品的神话时间,与个人时间、历史时间和作者时间形成镜像关系,意味深长。这部作品具有神性与灵性。贾平凹的作品具有灵性,这是当代文学史公认的事实。那么,神性是什么呢?所谓的神性,并不是说是关于上帝的本性。这里的神是一种超验性的理念,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贾平凹解决的是生和死的问题,这个神性体现了他的观看视野与精神意蕴。他以人情人事的视角来平视这个世界。与此同时,他也用了一个更高的视野来观看、来俯视、来思索整个百年历史。他是高产高质的作家,也是求新求变的作家。《废都》聚焦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秦腔》表面上是乡村的鸡零狗碎之事,但内核则是对乡土文明的想象与思考;《老生》是对中国百年历史的文学想象与思考;《暂坐》是关于西安城的故事,其多视角的写作方式让这部作品有了更多的解读空间;《秦岭记》是以小说的形式为秦岭作传。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有新的尝试与探索,这是让我特别敬佩的地方。
我很喜欢《白鹿原》。大一的暑假期间,我读完了《白鹿原》,大受震撼。在这部作品中,我看到了作家的良心,看到了作家的智慧与慈悲。在写作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不同的人物。他理解作品中的所有人。很多小说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所写的人物面目相同,没有参差感,而《白鹿原》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写《白鹿原》的时候,陈忠实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报纸,也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对自己进行了精神剥离。路遥的作品对我也有启发,特别是那本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阎安对我的写作也有影响,他的诗集《玩具城》《整理石头》《自然主义者的庄园》显现出了一种包容万象的精神格局。
涂慧琴:刚才我们谈的基本上是小说方面。谈到诗歌写作,张阅老师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前段时间,你还参加了一个国际诗歌作坊活动。请你谈谈经典诗歌和经典诗人对你的影响。
张阅:我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开始喜欢诗歌的。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喜欢波德莱尔,大学时接触了T.S.艾略特。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T.S.艾略特对法国象征派的传承与超越。那时,我希望在研究T.S.艾略特的同时能够理顺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这一派系诗人,看看自己的诗歌创作还要走到什么方向。年轻的时候,人写诗都是宣泄情绪的,都是内心有什么情感和秘密都宣泄在诗里,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会觉得诗歌不能老这么写了,这不是个好方向。T.S.艾略特是相反的方向,他克制、消解情感。朱光潜先生有一本专门谈诗的书,他在书中就说我们学写诗也不要老是学浪漫派,如果要学浪漫派,可以学一下济慈,学华兹华斯也还好,就是不要学拜伦和雪莱,他俩太以自我为中心。我大学时候读到他们的生平故事,也觉得他们都非常自恋、自私,感情上都很伤人。我们现在去看过去那些诗人,一定要把他们看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能把他们看成抽象的人。虽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作品有可能非常美,非常有价值,能触动到人心的某一个共通点。这些作品可以一直流传下去,让后世的人继续得到安慰、得到理解。经典作品应该具有这样的价值,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生命里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去读这些经典作品,感觉这个遥远的作者是理解你的。这个作品可能是小说,可能是诗歌,也可能是戏剧,任何一种文体。
同时,诗歌往往也是诗人逃避情感的一种方式。诗人有时逃不过内心的波澜,他可能在生活里逃避做选择,但他可以把这些波澜写进诗中进行消解。譬如,T.S.艾略特、约翰·邓恩,他们后来都找到了宗教,宗教是他们诗歌里一个非常重大的题目,也是他们给自己找到的精神出路,使自己走向越来越深的内心深处。我想诗人持续写诗会慢慢突破他自己的。当他看到更多人的悲苦,把它写下来之后,他可能会考虑他的诗歌要不要给别人看。这是他心里的一些想法,一些秘密,这些想法和秘密要不要给别人看便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慢慢他们会发现,有些诗歌只能给小部分人去看,只是在小范围内分享他们对世界的思考,可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写出至情至性、真挚诚恳的诗,保持对诗的忠诚。
涂慧琴:的确,诗是诗人内心的一种坦白,是诗人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思考,体现了很强的主观性。有些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但其在世时并未呈现于人前。譬如,美国著名的女诗人狄金森,她和惠特曼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但狄金森的诗具有很强的内向性,是她内心情感的一种自我追问,惠特曼的诗则具有外向性,传达了他对民族、对世界、对全人类命运的关切之情。狄金森一生写了近1800 首诗,而她在世时只发表了7 首,并嘱托妹妹将其诗作烧毁。幸好她的妹妹没有听从其遗嘱,不然世间就少了一位如此具有创新性、独特性的女诗人。
丁小龙:狄金森的作品之所以很经典,是因为其显现了时代精神与心灵真相,并且具有相当高的创造性与原创性。为什么经历了一百多年,我们依然还在阅读她的作品?是因为她写的是内心的风暴,是一个人最真切的想法与情感,是她对恐惧、对死亡、对生活、对时间、对诗歌的一些最本真的想象和思考。她从最核心的问题出发,与当时的流行写法背道而驰,所以她不被当时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但她在未来找到了知音,找到了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是诗歌先知。狄金森和卡夫卡有点像。卡夫卡的小说当时出来后,除了他的好朋友以外,能读懂的人很少。卡夫卡曾自嘲说他出了一本书叫《变形记》,在书店里一年只卖掉了三本,其中两本还是自己买的。这本书现已被公认为世界经典,是现代小说的典范之作,但当时很少有人理解这部作品。因为卡夫卡写的东西不一样,特别超前,普通读者很难消化这种全新的作品。每一个作家的道路不同。像卡夫卡、狄金森、佩索阿这类作家在当时可能不太被人理解,但后来的读者慢慢理解了、领悟了,会把他们的作品视为经典。
涂慧琴:我们班上谢志聪和邱雪辰两位同学在研究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请你谈谈这位作家及其作品。
丁小龙:在石黑一雄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就读了他的部分作品。他是我喜欢的作家。他所坚守的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他的写作不是区域化写作,面对的是全世界读者。石黑一雄的作品不是特别多,目前出版了8部小说与1部小说集。他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和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与日本有关,源于长辈故事与档案资料,带有日本文学的哀婉风格。虽然评论界把石黑一雄、奈保尔和拉什迪并称为“移民作家三雄”,但他不把自己当成只写母国的移民作家。《长日留痕》写的是一个英国管家的故事,这部作品获得了“布克奖”,还被拍成了电影,并获得奥斯卡奖、金球奖等多项大奖提名。《莫失莫忘》是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了电影。《我辈孤雏》聚焦于英国间谍在上海的故事。《被掩埋的巨人》是发生在公元6 世纪的英格兰故事,带有浓烈的寓言色彩。他最近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但思考方向与写作路径与《莫失莫忘》不一样。他的每部小说都有新的探索,但也有共通之处,即时间中的记忆与遗忘主题。这是他特别感兴趣的主题,也是他所有小说的共同主题。《远山淡影》写战争给日本人造成的精神创伤;《浮世画家》写时间中的艺术与谎言的关系;《被掩埋的巨人》其实是被掩埋的记忆,带有幻想小说的特点;《莫失莫忘》也与时间主题有关,是对复制人命运的反思。他以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对这个主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变奏。石黑一雄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求变。有的小说家不求变,他们的每部小说都差不多。譬如,简·奥斯丁,她的6部长篇小说都是关于爱情与婚姻,理智与情感。这种不变也是一种写作姿态。但是,石黑一雄就是在挑战自己,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在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比村上春树要走得远一点。我特别钦佩他。
涂慧琴:除了刚才提到的作家和作品,你可以给学生们推荐一些经典作品去阅读吗?
丁小龙:我建议热爱文学的同学去读一读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这两本书与今天所讲的主题相契合。《西方正典》是大学者、大批评家用自己的方法论写出来的西方正典,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也饱受争议。不管大家是否同意他的观点,都可以进入他的文本阐释空间,这为你们的学术研究、文学批评和文艺评论提供别样的视角。另一本是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作为一名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文学大师,卡尔维诺以小说家的视角来阐释为什么读经典以及怎样读经典,带有浓烈的方法论特质。
我最近重读里尔克的唯一的小说《布里格手记》。这本书非常出色,具有诗歌特质,是精神性小说的典范之作。这部传世之作,以手记的方法进入人物内心深处,把人物的精神景象与心灵风景呈现出来,带有启示录的意味。我还推荐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与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这两本书是经典的写作导读课,是两位大师为写作提供的道路与风景。
涂慧琴:今天,我们在虚拟的世界里相聚,一起讨论阅读经典与写作问题。期待下次我们能面对面地交流。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位同学有所收获,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经常阅读经典作品。感谢丁小龙和张阅两位老师的写作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