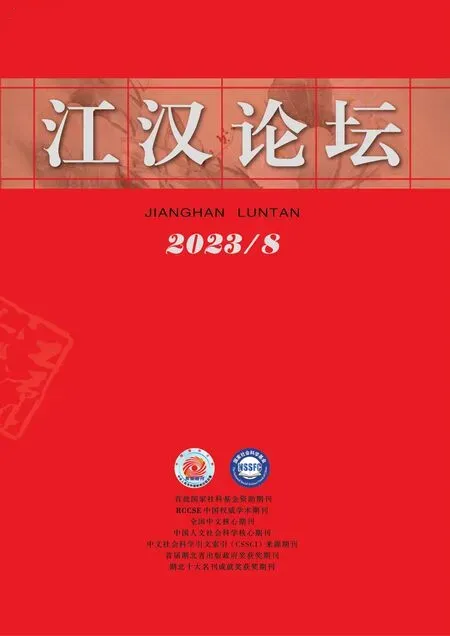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三重维度
——基于《伦敦笔记》的文本分析
梅文韬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的编辑出版,国际学术界对《资本论》理论生成史的认知有了更丰厚的文献支撑。在经历1848—1849 年的中断后,马克思在伦敦重新启动政治经济学研究。(1)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共写作了24 本笔记,并把它们按罗马数字进行编号,此即著名的《伦敦笔记》。除了摘录原文和马克思添加的一些评注外,笔记中还有两份原稿,这些内容有助于弄清马克思当时在劳动价值理论方面所达到的理论成熟程度。(2)《伦敦笔记》内容丰富,马克思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李嘉图学派的全面研究;对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的研究。(3)也有研究者以价值问题为中心,将笔记的内容归纳为三组: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前7 本笔记归为第一组,它们包括货币和货币流通问题的一些经验材料;把《反思》、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摘要和第7 本笔记中的大卫·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的第二部分,归为第二组材料;第三组材料是马克思对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的著作摘要,特别是赛·贝利、托·德·昆西、托·罗·马尔萨斯、罗·托伦斯、约·格雷、皮·莱文斯顿、托·霍吉斯金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摘要。(4)在《伦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通过蜜蜂采蜜式的摘录,自然地引出了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坚定地捍卫劳动价值论,在价值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为他的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马克思对于货币、地租等价值形式的研究,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中价值形式理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德国学者、MEGA 编辑促进协会主席黑克尔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形成概括为三个阶段,认为伦敦时期是第二阶段的开始,马克思自此深入地研究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呈现了自己的论证。(5)
一、货币职能:理解价值的货币形式
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这样描述自己从伦敦时期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48 年和1849 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 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6)。贵金属作为突然增加的“随时随地的财富”,与作为一般劳动所产生的财富应该是不同的。如何看待贵金属作为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实际财富相对应的货币财富之间的差异,这是货币理论中亟需加以说明的问题。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在劳动二重性等理论上取得突破,但是通过对李嘉图货币数量理论的批判,已经在“科学地论证劳动价值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7)。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格、货币的价值都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这在当时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货币理论。它认为货币自身的价值与其数量成反比,而商品的价格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也就是说货币的数量越多,货币本身的价值越低,商品的价格则越高。这种价值理论实际上是将社会财富的价值高低与社会劳动割裂开来,单纯从货币的供给数量中寻找价值的规定性。在这里,李嘉图已经抛开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则指出,货币数量的变动与流通中的货币运动无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取决于每日的贸易额、流通手段、信用等,也就是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它所代表的价值并无直接关系。相反,货币数量与贸易额的大小、货币流通速度,以及社会以货币为债权与债务双方的信用有密切的关系。基于此,“从原则上批判李嘉图的数量理论,对马克思来说也是出于进一步制定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必要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已经在质上高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李嘉图在理论上主要对货币的数量方面感兴趣,而马克思已经把货币看作历史地形成的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关系。”(8)
马克思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摘录了有关货币学说的一段话:“金银价值之所以波动,是由于发现了新的更为丰富的矿藏;……是由于开发矿场〈或采矿本身〉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和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进;……是由于矿的产量的锐减”,“它们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最终“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们运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9)在这里,李嘉图将金银作为劳动产物的价值与劳动总量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的金银产出因其稀缺性,生产金银的劳动量显然与生产其它劳动产品的劳动量是存在稀缺的倍数关系的。马克思摘录这段话,正是看中了李嘉图将金银与劳动总量所建立的关系。但李嘉图并没有将劳动与金银价值之间的关系前后贯通起来,相反,他直观地将价值与货币的数量建立起了联系。
李嘉图主张货币数量论,认为黄金的价值是由流通所需货币的多少决定的;至于流通中的金属是量多价值低,还是量少价值高,是无关紧要的。针对李嘉图的这一观点,马克思评论到:“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许多价值低的金属还是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紧要的。”(10)对于前者,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让货币数量的变动影响了商品的价格,但是“其实借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况决定的”(11)。对于后者,马克思则指出,随着交换过程的增多,对流通手段的需要也会提高。货币数量不决定货币的价值,但并非与货币价值无关。如果只有价值高的货币,它所提供的流动性是不够的。
这一时期真正使马克思深入开展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关键点,就是“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关于价格和货币理论及政策的争论”(12)。1847 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承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恰当的表达,“劳动时间确定价值……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13)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充分理解劳动的二重性,而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劳动二重性称之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4),他的货币理论在1847 年还有不足之处。当时,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还没有明确地以物化在货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确定货币的价值,而是承认货币的数量是构成货币价值的要素。克服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困境就成了马克思阐述自己经济理论的重要起点。(15)经过研究,马克思断言,“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在理论上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1843—1847 年出版的《价格史》一书中没有发现任何的论述。”(16)马克思的研究结果证明了由货币数量决定货币价值的观点不成立。
如果货币的数量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无关,那么,金银条块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作为价值而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呢?通过对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摘录,马克思发现金银条块作为财富具有贮藏职能的特性。“贸易的巨大和终极的结果,不是一般财富,而主要是银、金或珠宝的富足,它们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商品那样容易变质。它们不论何时何地都是财富。而酒、谷物、家禽、肉等等尽管很多,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因此生产金银等等这样的商品和经营会使国家获得金、银等等的贸易比经营别的贸易都有利。”(17)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获得的贵金属作为贮藏的货币,更值得期待。贸易“好处最大的,是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而且不论何时何地都被当作财富。时间上普遍不变,空间上长久存在。货币是永恒的商品,所有商品只是短暂的货币;货币是普遍的商品,商品只是地方性的货币。”(18)金银由此获得了“普遍的商品”的属性,或一切商品的抵押品的性质。在马克思的笔记中,特别“指出了配第的重商主义看法,即认为商业最大和最终的效果,不是财富一般,而主要是剩余的金、银和珍宝,这些东西不像其他商品那样短暂和易变,而是永恒的和普遍的财富。”(19)这里的摘录内容后来被马克思引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即货币主义——重商主义不过是它的变种——的创始人,宣布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他们正确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从简单商品流通观点来看,也就是形成既不蛀又不锈的永恒的财宝。”(20)因此,金银作为永恒的商品同样凝聚了一般商品的劳动,不从劳动量的多少来看待货币,而仅从货币数量本身来看待货币的价值显然是对货币贮藏功能的误解。
“关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金银条块》中被说成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并在原则上说明,对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来说,价值的相对稳定是很重要的。许多关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间接表述,是与关于信用、信用货币、支付差额等等的摘录相联系的。”(21)在研究休耳曼的著作时,马克思碰到了有关金银转变为货币问题的论述。马克思认识到,货币兑换,即金银变为铸币或铸币变为金银,已广泛流行。“当商人周游外国市场时,为了用现金支付起见,他们带上未经铸造的纯银,金也可以。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把得到的当地铸币换成未经铸造的金银。因此,兑换业务,即把未铸造的贵金属转换为当地铸币或者把当地铸币转换为未铸造的贵金属,成为非常流行的、有利可图的行业。”(22)
在摘录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时,人们对贵金属的崇拜而导致作为支付手段的金银的异化,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贵金属必然充当交换中的抵押品,人们把它们变成神,越来越多的财物、需求,甚至人都成了它的牺牲,人们不是把它们用作贸易的仆人、奴隶,而是把它们变成贸易的暴君,通过货币的作用,天然的秩序被歪曲了,货币成了一切物品的刽子手,货币的罪行在于他们想成为上帝,而不是成为奴隶,布阿吉尔贝尔把高利贷者同炼金术士相比,后者为了得到金而把一切物体化为灰烬。”(23)作为支付手段的金银原本应当成为交换中的抵押品,但它一旦被赋予“一切商品”的特性后,就使得具体的财物退场,而贵金属占据了交换的中心位置。
从前人的大量研究中,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货币作为一般商品体现社会关系性质的观点。与所有资产阶级货币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在1850 年代已发现,“货币并不是物的神秘属性,而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社会关系。货币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过渡阶段的特殊方面,货币的历史虽然明显地比资本主义长,但货币在资本主义下才成为普遍的、引起所有社会关系的现象。”(24)这种普遍现象在雇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基本关系中以货币作为中介而无处不在。人类也陷于他们自己产品的统治之下,人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作为物(以货币的形式)与他们相对立,赚钱成了所有阶级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从布阿吉尔贝尔的“货币是一切物品的刽子手”的论断中看到,“这主要是针对财政制度而言的,这种制度消灭了大量商品,远没有在货币形式上把它们归入国库。”(25)“为了获得货币,所有必须亏本才能售出的商品都被销毁了。这样,生产停止了,这是崇拜银这位神明的那些献身者的活动的结果。”“由于货币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富裕的情况下产生匮乏,交换遭到破坏,生产无利可图从而停止。虚构的价值破坏实际的价值。”(26)由此可见,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或贸易不是为了使体现使用价值的具体商品增加或流通,而是为了获得作为一般财富的价值,这对于《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价值增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通过对约·格·毕希《银行和铸币问题论文集》中有关汇率、国家货币交易、现金、银行贴水问题的梳理,马克思看到了这些金融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性质。“每个个人在货币上占有的是一般交换能力,借助这种能力他可以自行决定自己在社会产品中应得的一份。每个个人都拥有这种在他的口袋中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社会权利。要夺取物的这种社会权利,就必须把这种统治人的权利直接给予人。因此,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发展。在货币权利成为物和人之间的纽带以前,纽带必然是作为政治、宗教等等纽带组织起来的。”(27)的确,货币是工业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发展的前提,它既是统治人的社会性权力,也是人能够独立运用这种权力自行决定自己在社会中占有财富份额的媒介,它代替了政治、宗教等以往的纽带,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白而简单。
马克思在摘录中加深了对货币价值尺度的理解,这为劳动价值理论的确证奠定了基础。货币的价值尺度是将不同商品的价值通约为质的方面相同而可以进行比较的量。马克思在赛·贝利的《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中摘录了如下关于货币性质的内容:“ (1)货币(α)是每个人用来为自己弄到其他商品的一般商品。(β)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γ)价值尺度。 (2)货币价值经常发生变化这件事丝毫不影响充当价值尺度。用一个不断变化的尺度总是可以把两种不同的关系对一种尺度的关系表现得很好,就像用一个不变的尺度来表现一样。”(28)在1844 年《经济学家》中摘录了“必须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因为金和银互相间没有不变的相对价值。然而,金对它本身来说才具有这种价值,每一块金币对另一块金币来说才具有这种价值。但是,标准应当划一不变。”(29)在《伦敦笔记》第VI 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约·格雷《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指出“货币必须使每个人在他愿意的时候能买到同货币本身一样价值的商品”(30)。这样,在接受约·格雷观点的同时,马克思将货币的价值锚定在劳动上,“劳动是唯一的价值尺度。每一种标准生产必须确定一个能用货币支付的最低劳动价格。如果每星期的最低工资为20 先令,那么1 镑就是一星期最低劳动的标准尺度”(31)。马尔萨斯则提供了货币价值的初始来源,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农业劳动的价值”(32)。约·格雷的“并没有人反对用金银作交换工具,人们只是反对用金银作价值尺度”(33),“金和银不同于其他的尺度。它们可以留在买者、卖者或其他个人的手里。然而,银不仅仅是进行买卖的尺度,还是使买卖成交的东西,它以一定的量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它同时又是交换中既定的价值等价物。”(34)所以,马克思认同毕希所认为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抵押品”(35),货币在每一次交换中都是等价物,但它并没有在任何一次购买中消耗掉,总是能够重新充当等价物。显然,“毕希反对价格决定货币数量,或决定于货币储备。”(36)
马克思还考察了货币的信用问题。无论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还是作为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货币都是以信用为前提的。“信用的基础是相互信任。信任的增长表现为采取一切措施来方便划拨清算,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37)当然,货币作为社会财富的锚定物或一般商品所体现的信用,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马克思对亨·查·凯里的《法国、大不列颠和美国的信用制度》的吸收,体现在《伦敦笔记》第V 笔记本中,“劳动要求以金和银来支付工资,信任金银。在商业中普遍地同样缺乏信任。因此,立法和政府干预交换活动。(官方审查商业账目,担保证券经纪人、辩护人、公证人的正直和名誉等。)通过这些保证,从国家中排除小资本家,使大资本家有可能富裕起来。”(38)这表明货币信用的建立离不开国家的强力支持。
二、级差地租:理解价值的地租形式
这一时期,马克思获取了相当多的历史材料来分析级差地租理论,他进一步确证了级差地租受土地产出价值的劳动量影响,而与土地贫瘠程度无关。在李嘉图看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开发的土地自然条件会越来越差。在这个过程中,愈肥沃的土地获得的地租就愈多。另外,他还认为当等量的资本和劳动追加到旧有土地上时,地租同样会产生。尤其是李嘉图在他的地租理论中对1770—1815 年的几种发展趋势进行了概括。工业革命是随着主要集中在工业密集地区的人口的增长而发生的。人口的增长提高了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谷物价格和地租也相应地提高。同时,土地所有者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通过保护关税阻止外国便宜的粮食进口。(39)
地租在何种程度上与劳动价值理论相一致,这个问题同生产发展水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经营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时间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像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获得较少的产品。劳动必须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40)这样,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地租。在这里,地租的形成与劳动时间的多少(即生产费用)相关。较好等级的土地可以生产出成本较低的产品,由此产生的额外利润转化为土地所有者的级差地租。(41)正如马克思1851 年1 月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地租不过是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42)。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赞同李嘉图的观点的,但他否定了李嘉图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差是产生地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正确地看到“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43)。马克思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发现李嘉图面对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地租也随之提高不过是历史某一片段中的事实,而非历史的普遍现象。马克思得出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土地的“一般肥力”并不是在下降而是在提高。这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44)既然肥力并不是总在下降,级差地租形成的原因就只能是不同土地直接肥力的差别。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的生产费用也就下降,当供求相适应时,土地的生产价格也就下降了。因而,尽管单位产品的地租下降了,但是由于产品数量增多了,从总体来看地租的绝对值也增加了。
在马克思看来,詹·安德森是级差地租理论的真正发现者。在第XII 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安德森的两本著作:《关于至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1779 年爱丁堡版)、《论农业和农村事务》(1796 年爱丁堡版)。安德森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农学家。他坚决维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45)安德森认为,土地肥力不是自然界固有的,而是可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加以改善的。土地肥力是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的统一,同样大小的地块在消耗同等数量的劳动和资本的情况下会获得不同的收益。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有:土地的地质情况,气候,与销售市场的距离,机器耕作土地的方法,灌溉,施肥,地块的大小和地租条件。”(46)在马克思所摘录的这两部著作中,安德森阐述了他在1777 年发现的级差地租并用农业生产发展的新材料进一步充实了这一理论的内容。安德森从提高农业生产产量的可能性出发,认为为了满足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必须耕种最坏等级的土地,这类土地的产量也能够提高,从而使粮食的价格下降,而没有像他的后来者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样,认为级差地租取决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
马克思把技术的发展“看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形式的物质内容,在这种形式下工人阶级是主要的生产者”(47)。他在这一时期对技术的研究是结合探讨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其成果反映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天才地预言了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从未忽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形式规定性和它们推动社会的能力”(48)。
重视科学技术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促使土地收益发生变化,对于落后国家或地区来说,社会进步更为明显。以印度为例,“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49)马克思以约翰·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印度的铁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中的事实指出了人工灌溉在印度农业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在高止山脉附近地区,经过灌溉的土地也比面积相同而未经灌溉的土地多纳2 倍的税,多用9—11 倍的人,多得11—14 倍的利润。”(50)马克思借助这个事例在他的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了人工灌溉在东方的特殊作用,也强调了铁路对发展灌溉设施的意义:“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的地方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51)基于此,马克思看到了在印度遏制饥荒的可能性。查普曼在著作中所叙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产量的增长之间的联系,更坚定了马克思对“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拒绝态度。(52)
马克思从帕·詹·斯特林的《贸易哲学》中吸取了“自然的利润率是农业中的利润率。其他一切利润率都是按照它来调整的”(53)观点。显然,他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有经济部门的利润率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而且,以投资农业资本的利润率作为基准。这实际上启发了马克思将地租变化与社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联系在一起的思路。“18 世纪,每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比17 世纪高不了5 便士,而资本的利息率下降了。地租不是谷物价格高的结果;地租的每一次上升和利润的每一次下降都是由于投入土地的资本所获收入的减少造成的。谷物的高货币价格只是结果。”(54)
马克思认为,“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55)后来在第VIII 笔记本中对《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作摘要时,马克思再次详细地摘录了李嘉图的地租观点,并明确地评判:李嘉图的“整个论点是大有问题的”。(56)
马克思在对佩顿著作的摘录中关注了14 世纪苏丹统治区德里在不同统治者治理下地租的发展情况。阿拉-阿尔-T. 穆罕默德·卡尔吉从l4 世纪开始,把地租任意提高到收获的50%,结果是农民贫困化。他的继承者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继续提高税收,这样的政策使人民日益贫困,全部田园都荒芜了。而下一个王位继承者菲罗兹·沙·图格鲁克,用大量资金发展灌溉设施和重新开垦荒地,又使情况恢复正常(57)。这些摘录表明,“即使是亚洲的独裁者也不能任意规定地租。地租的数额取决于获得的剩余产品和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地租数额高于获得的剩余产品,那么甚至会妨碍社会的简单再生产。”(58)这说明即使是残酷的剥削也要受到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制约,任何政权的稳固程度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密切相关联。
马克思在1851 年写给恩格斯的信(59)中指出,李嘉图提出的地租理论,实质上不过是:在最坏土地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土地产品所得到的价格之间存在差额,这是对的。级差地租并不是以土地肥力递减为前提的,而仅仅是以土地肥力各不相同,或者连续使用于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的。只要是土地肥力不相同,或者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不同,就会产生级差地租。这样,马克思就把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改造得比较科学了。(60)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往来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级差地租新解释的态度。恩格斯略带自嘲地说,尽管他也不信服李嘉图的解释,但由于他“在理论方面众所周知的懒惰”,他并没有去尝试探求问题的实质。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新解释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有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61)。运用新的级差地租理论,马克思找到了一把解释许多看似自相矛盾的复杂经济现象的钥匙。
三、劳动时间:形式背后的价值实体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62)。而社会性时间也即是生产某种商品所必需的平均时间。
第一,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多少的观点。马克思赞成李嘉图对“对外贸易是价值增值的源泉”观点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价值永远也不可能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63)此外,进入马克思分析视野的问题还有流通过程和价值生产的关系。马克思在摘录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时看到,对外贸易行为,无论是从外面或者输入商品,或者输入货币,或者输入收入,都必须在国内进行交换,才能转化为实在的收入,也就是“和现有的劳动和土地的[产品]交换。因此,所有这三者的价值都是由劳动和土地的[产品]的价值来衡量的”,“价值永远也不可能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64),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得以确证。尽管流通过程不会增加新的价值,但是流通过程却是实现价值创造的前提。资本家购买劳动商品,是在流通过程实现的。而使用劳动商品之后,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了新的价值,需要让包含这种新价值的商品成功进入流通过程,才能完成价值的实现。
第二,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在摘录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三版“论价值”的有关内容时,李嘉图认为:“确定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是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它们的不同数量,或者是相应地体现在它们中的劳动量。因而,只要这种劳动量增加,就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劳动量减少,就降低了商品的价值。劳动的价值和[这劳动所生产的]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并不是相等的,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因此,劳动的价值不像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因此,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决定各种商品的现在的和过去的相对价值’。”(65)在这里,李嘉图区分了“劳动的价值”与工人报酬之间的差异,看到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不相等的,这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李嘉图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他利用资本家通过生产率提高降低产品成本进而获得竞争优势地位的例子,讨论了商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额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体现在资本中的劳动量的变化,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很大变化。‘节约使用劳动总是使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不论节约的是制造商品本身所需的劳动,还是构成生产这种商品的资本所需的劳动,都是一样。’”(66)商品生产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这一原理,也会由于使用机器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的参与而有很大改变。“第一,是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不同,第二,是维持劳动的资本与投在机器、工具、厂房上的资本的不同比例。这两种情况决定了:除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外,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也影响商品的价值。”(67)此外,马克思也赞同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某种物品的效用和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虽然是绝对必要的,但它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商品从两个源泉获得它的交换价值:(1)它的稀少性和(2)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68)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仅转向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包括了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导致“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实是,马克思轮流摘录这两位作者的著作,所以也就是同时进行阅读”(69)。马克思注意到斯图亚特区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生产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马克思也注意到他对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而作出了明确的历史评论。(70)马克思认为:“斯图亚特比自己先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71)这种区分奠定了马克思将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区分开来的基础,只有个别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社会认可的使用价值量时,它的交换价值才有可能实现。
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在价值规定中忽视了交换的作用,发展了他自己关于商品的价值在交换中得到最后决定的思想。李嘉图没有看到“交换使商品价值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任何以交换的新的对象,归根到底其本身就是新的价值。所以会增加价值量。……交换的能力创造新的劳动。”“不然的话,这就等于说,似乎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提供的,所以,即使商品还不是可以被交换的,它也是价值。”(72)马克思在这里对商品的互相交换性作出了界定,并看到了商品价值并不是先验地由劳动时间和生产费用决定的。
第三,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在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寻找价值的余额是徒劳的。余额早在生产过程中就已经产生,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呈现出的表象那样——利润和价值的余额一样,是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无论是利润还是工人工资的分配,都不能说明价值余额的来源,“为了做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在。他们以欺诈的办法弄到的相对利润,只不过是全部余额的不平等的分配罢了。但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因此,虽然个别的特殊利润可以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73)即使工业资本家可以对土地所有者阶级进行欺骗而使一个国家里的利润不断地增大,“但是,每一个有产阶级的原有收入必然来自生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是利润或工资中的一个扣除额。”(74)尽管资本家可以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别的产品,但必须清楚每一个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余额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20 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 个等值工作日的产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资的价值按同一比例降低。”(75)
第四,马克思指出了李嘉图对概念的混用,如对“财富”和“价值”的混用进行了辨析。李嘉图曾说:“资本是用于将来生产的目的的那部分国家财富,它可以和财富按照同样的方法增加。追加资本,不论是通过提高技术和改良机器获得的,还是通过在生产上使用更多的收入获得的,它在将来财富的生产中都有同样的效力。因为财富总是取决于生产的商品量,而与获取生产上所用工具的便利程度完全无关。”(76)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则取决于生产的难度。马克思也认识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商品价值量的下降。但认为“李嘉图在这里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77)这说明李嘉图始终不能理解,价值以及资本怎么会增加,而同时又不像地租的情况那样,一人的所得就是他人的所失。马克思始终将价值纳入生产过程中来考察,也就是说,要使价值增加,除了增加人口,提高资本的生产力,减低工人的相对工资,还必须按比例地增加劳动的使用方式,全社会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78)
四、结语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以金银贵金属为代表的货币、中世纪利息、高利贷、兑换业务、地租、技术、生产、流通等的研究,对这些范畴的历史发展,以及对它们在价值构成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把握。这些范畴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要久远。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这些范畴的资本主义内容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这样,“马克思就为社会形态的理论获得了关于经济关系的历史形成和消亡及其范畴形态的表现的论述和事实。”(79)从《伦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当时亟需加以经济理论诠释的热点问题密切关注,通过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马克思取得了经济理论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一是对于贵金属作为突然增加的“随时随地的财富”与实际财富相对应的货币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说明。他通过丰富发展货币职能,梳理了货币数量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批判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决定价值的理论,将劳动价值论贯穿到贵金属所代表的财富价值中,消弭了货币数量决定论与劳动价值论内在的矛盾,重塑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
二是科学地回答了地租的产生与劳动价值论是否相一致的问题。马克思接受李嘉图的地租是不同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的观点,进一步看到地租的这种市场价格规律反映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社会关系而已,地租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但他否定了李嘉图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坏是产生地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看到,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的一般肥力不是在下降而是在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级差地租得以形成。
三是马克思在接受李嘉图的“确定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是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它们的不同数量”(80)的观点时,看到了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不相等的;同时,强调维持劳动的资本与投在机器、工具、厂房上的资本的不同比例对劳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影响;否定了庸俗经济学家在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寻找价值余额的观点。
马克思的这些深入研究,都集中地指向了价值余额产生的源泉,它们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注释:
(1)(6)(20)(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4、414、553、452 页。
(2)(4)(21)(22)(24)(52)(57)(58)(60)(69)(70)(79) 周艳辉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4 卷):经济学笔记研究II》,中央编译出版 社2013 年 版,第126、126、350、70、346—347、79、79—80、80、19、141、143、72 页。
(3)(12)(62) 顾海良、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48—50、53、50 页。
(5) 张秀琴: 《21 世纪德国学界最新〈资本论〉价值理论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3 期。
(7)(8)(15)(19)(23)(39)(41)(45)(46)(47)(48) 武锡申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 卷):经济学笔记研究I》,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369、263—264、397、397—398、279、279、337、338、386、386 页。
(9)(10)(11)(56)(63)(64)(65)(66)(67)(68)(72)(73)(74)(75)(76)(77)(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73、81—82、82、103、117—118、117—118、90、91、91、90、118—119、140、140、140—141、110、111、111—112 页。
(13)(40)(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93、183、183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 页。
(16)(42)(44)(55)(59)(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 版 社2007 年 版, 第176、155、156、160、155—161、171 页。
(17)(18)(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53)(54) 马克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裘挹红等译、张钟朴校,《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 年第2 期,第1、1、3—4、4、21、22、38、50、51、43、51、43、15、14、29、29、52、52 页。
(49)(50)(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7、248、247 页。
(80)[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