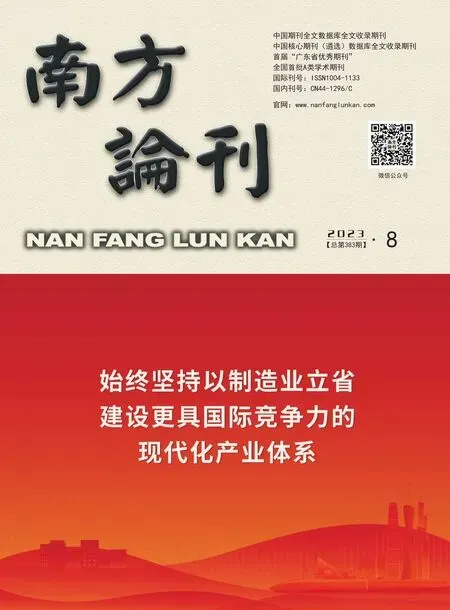试论毛泽东早年的“新心学”观(中)
——以《毛泽东早期文稿》为中心的考察
方绪银 姚大斌 吴玉梅 葛翠茹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茂名 525000)
阳明心学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也是“知行合一”这个“立言之大旨”,但其中的“知”已被扩展为德性论与知识论有机统一的“知”。如前所述,严复所编译的《天演论》,目的在于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论等新的科学理性之“知”来唤醒和激发中国人所固有的生生不息、“自强保种”的“本心”“类本能”,以此“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集全民族之力与西方列强争胜,实现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复兴大业。他虽然对王阳明的“心物”关系论有所批评,但他以西学新知“归求反观”儒家圣人的“精意微言”,实际上却是自觉不自觉地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类本能”特征作了“科学论证”,对青年毛泽东“读懂”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因为和《天演论》一样,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也有许多章节涉及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与人的道德起源的关系的论述,青年毛泽东读后可谓心有灵犀,就此写下了许多批注。与严复不同,毛泽东早期是一个王阳明、谭嗣同“心力论”的自觉的信仰者。他那篇备受其恩师杨昌济激赏的“满分作文”《心之力》,虽然至今尚未找到,但它的主要内容似为毛泽东当时对其多达1.2 万多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的体系化阐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心力论”——“心”如何才能“发显”为“至伟至大之力”的视角来解读这篇批注及相关文稿。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心之力”来自于人“所得于天之本性”的“自然冲动”亦即“类本能”。他说:“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此即“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疎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1]这些激情澎湃的议论,把“心之力”——人的“本心”“类本能”的伟大力量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与孟子的“浩然正气”和王阳明的“好德如好色”“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宁为狂人,不为乡愿”之论显然是神韵相通的。
青年毛泽东认为,“心之力”是一种情感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因而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孟子的“四端”论以及王阳明对“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道德端倪的揭示,讲的都是情感乃道德产生和养成的基础,也是道德实践的力量源泉,目的在于激活儒家士大夫从“为己”到“利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通道和动力。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人生的目的在于“自卫其生”,使“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仄”[2];“四端”之类的道德情感乃至人的所有七情六欲,都是为实现这个目的的需要而产生的精神驱动力。他进而以哲学思辨给人的道德情感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创造性转化了王阳明对“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论证”方式——人的利他情感和意志属于精神范畴,体现的是人的精神需要,亦即精神上的自利之心,而且对至情至义者而言,满足精神上的自利之心才是最要紧的:“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之价值。利精神在利情(感)与意(志),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3]显然,这些话语与王阳明论述心学乃“为己之学”“自得之学”时的意蕴极其相似,其中的“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吾情始浃,吾意始畅”等,以及在《批注》其他处所写的“人类、生类和宇宙都是一大己”等等,都是对陆王心学核心话语的引用或化用。《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编者如果以此视野来写文稿“注释”,至少可以增列数十条。
在青年毛泽东的视域里,“一切外铄之事”都必须契合于人“善其生存发达”的天性、“本心”,所以也就有了不断探求“真的、自然的、实在的”新知识的需要。传统心学没有把“四端”“良知良能”“仁义礼智”三者作清晰的逻辑辨析,而往往一概归之于“无须外铄”的“天理”,对“良知”之“知”的内涵界定也往往囿于道德范畴。而在毛泽东看来,“良知”实质上是、也必须是人“善其生存发达”的“良好的‘知’”“正确的‘知’”“合规律合目的的‘知’”,因而是与“变化万殊”的“外铄之事”密不可分的:
“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今所以有时不一致者,以吾人从知识与经验之所得,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生存其中至为不易,在一种时候及场所,如实依冲动所命,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以渐制为训练及习惯,加本原于冲动之良心,以特殊之形状,遂有与冲动相冲突之事,此或因吾人对于此住世之事,不得其法。或本可不与冲动相冲突,而亦能善其生存发达,未可知也。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也。唯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谏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是也。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故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自后天之训练习惯,矫枉过正,乃有不循自然与冲动反对之事,致使良心之本来与冲动同原,同为真的、自然的、实在的,变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此则矫枉过正之咎也。”[4]
这就是说,人的“良心”并非是“无须外铄”的,而是社会环境、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对人心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人的自然冲动是人的情感和意志的源头,社会所塑造而成的“良心”虽然已往往呈现为人们的习惯、“第二天性”(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遵从来自社会的道德意志、“道德律令”),但如果超过了如节制“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之类的合理界限,从而与人“善其生存发达”的情感和意志产生了根本性冲突,就会“变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亦即“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就会失去其为自然“冲动之所驱”的内在动力,就会危害人的“生存发达”;这种经不起内省、反思的所谓“良心”实际上是一种“盲目道德”,是中华民族出现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危机的思想和道德根源。那么,如何既防止“矫枉过正”,又解决好“良心”与“与冲动相冲突之事”呢?青年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有赖于“新知”的探求和指导:“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5]在青年毛泽东的意蕴中,这个“新知”必须是“揆之天理而顺”的“宇宙之真理”,是“裁之吾心而安”的“心以为然”者,是能“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是能够“附丽”于“吾人自具有可以酿成之本性”[6]之上的“真知”。
人们有了这种“善其生存发达”的“新知”,又如何才能使其见诸于“类本能”般的行动呢?青年毛泽东的解决之道是把这种“新知”升华为信仰:“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7]亦即要“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8]。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学者(若)信得良知过”,就必须“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不同的是,毛泽东在把“良知”之“知”的内涵扩大为道德目标与实现目标的知识手段两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已明确地把王阳明的“良知信仰论”转化为“真理信仰论”,把“知行合一论”转化为“知信行统一论”。“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9]——通览《毛泽东早期文稿》,“真理信仰论”可以说是贯穿其始终的唯一主线,并且通过“‘见夫宇宙之真理’的‘立志’论”“‘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的‘大真诚’论”“实现自我最高可能性的‘至善’论”“‘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的‘意志力’论”等等理念,构成了一个既具有原理性又具有行动力的开放性学理体系,昭示了他后来成为一个具有无坚不摧、改天换地伟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必然性。
三、“功夫”:从“拔本塞源论”到“大本大源论”
阳明心学所说的功夫就是致良知的功夫。王阳明认为,只要人人都把这个功夫做到位了,那么就会“满街都是圣人”,整个社会也就能回归到“羲皇之世”“大同圣域”。在《拔本塞源论》[10]中,王阳明集中揭示了妨碍人们致良知的一系列思想性、社会性问题,认为数千年来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和欲壑难填的学风官风,严重阻隔了人们对良知善根的体认和扩充、芜塞了圣人之道的流贯和通达,因此必须做正本清源、固本疏源的大功夫。这篇有着强烈批判精神的纲领性文献,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既直接又独特,他的《致黎锦熙信》(1917.8.23),完全可以用《大本大源论》作篇名,并与《拔本塞源论》构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双璧”。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而言,中华民族及其思想家最独特的精神特质,就在于自古以来就有着最强烈的人人相亲相爱的“大同情结”、“大同梦想”,这既是基于对长达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原始公社时代道德风尚的理想化的历史记忆,又是出于在返观内省中形成的对“人性本善”信念的执着。《拔本塞源论》对这两方面都描写得最为详明和完备,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杰出的空想共产主义经典文献。王阳明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卷中),这不仅是“圣人之心”,也是人皆有之的“本心”,是成就远古大同盛世的大本大源;然而,“三代之衰”后几千年来,“圣学晦而邪说横”,大行其道的根本不是尧舜禹和孔孟的圣人之教、圣人之学,而是毁坏人的“本心”这个“大本”、阻塞“本心”“发用流行”这个“大源”的种种歪理邪说,使得“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圣人之道遂以芜塞”,从而导致了“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不自知”的悲惨社会现实。所以,他希望豪杰之士“闻吾拔本塞源之论”,能够感到“恻然而悲,戚然而痛”,能够因此“愤然而起”,以“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之力,摒除一切“拔本塞源”的“功利机智”,使良知之学大明于天下、大同盛世重现于人间。(《传习录》卷中)青年毛泽东的“大本大源论”同样是执着于大同梦想的,而且也基本上是把实现路径归结为教育问题。他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11]。后来,毛泽东对大同梦想经历了一个从质疑到重新肯定的过程——在写《<伦理学原理>批注》时,毛泽东认为,没有恶就无所谓善,善恶是相生相成的,“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所以不可能有人人都成为“止于至善”的“君子”那一天:“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但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否认“大同”是植根于人性的梦想:“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12]在他看来,大同梦想虽然“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但却是人类的“根本之欲望”、“根本之理想”,是人们“借以达于理想之事”的内在动力:“人不能达到根本之欲望,亦可谓之人不能达到根本之理想。人只能借以达于理想之事,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唯事能达到也。”[13]显然,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达于理想之事”的量变会引起社会形态的质变的观念。到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大同理想不能最终实现的观点,树立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到来的坚定信念。在1949 年7 月1 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而作、堪称新中国“建国大纲”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使用“大同”概念达7次之多。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我们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这意味着,就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而言,中华民族古老的大同梦想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并无本质不同;两者的差别不过在于是否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有效途径。到了晚年,毛泽东还对自己早年关于人类能否“安处于大同之境”的困惑进行了“回顾性思考”,作出了具有逻辑延续性的回答:人类社会必然会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那个时候也不会“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不仅还会有量变,也还会有“不断的部分质变”[14];“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15]可见,对大同社会的哲学思考,一直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
《拔本塞源论》是王阳明晚年对其平生“倡明圣学”——圣人之心、圣人之教这个“大本大源”的总结性文献之一;而《致黎锦熙信》(1917.8.23),则是毛泽东早年正式开始以“全幅工夫”寻找“大本大源”的标志。他和王阳明一样,也认为孔孟是“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的圣人、“既得大本者”:“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这些说法与阳明心学话语可谓如出一辙。但是,青年毛泽东并不认为只要像王阳明那样“倡明圣学”就万事大吉了,这还“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而并非他心目中的大本大源的主体。所以他认为,“大本大源”并不是被“芜塞”了,而是根本还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大本大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吾国思想与道德”“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16]青年毛泽东这些批判性反思,既是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也明显受到王阳明“拔本塞源之论”的启发。他通过中西学术对比,发现“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缺乏学科体系上的分门别类和规范性构建、理论概念上的界定和阐述、逻辑结构上的推理和自洽、具体实操上的应用和说明,“此所以(中国学术思想)累数千年而无进也”[17],这些认识不仅超越了阳明心学的视野,也为他研究真正的大本大源找到了新的方法。他认为,就近代和当前而言,包括他曾经很崇拜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所以“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就是因为没有他们找到“大本大源”——救国救民的根本方法和路径: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18]
那么,什么是大本大源呢?此时的毛泽东自己也还在探求之中。他认为,一个有志于寻找大本大源的人,必须努力做到内省之明和外观之识的有机统一,如果无内省之明,“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亦即王阳明所说的“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传习录》卷上),必定祸国殃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如果无外观之识,妄图“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也只会误国误民。概而言之,就是要做到起心动念慈悲纯良、谋事干事本领高强。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大本大源是“各具于人人之心中”的“宇宙之真理”,“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因而可以让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不再“茫乎未定”“歧路徘徊”,“徒费日力”;它当“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足以让人“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而不再纠结于生死、义利、毁誉“数事”。他说:有了这样的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9]
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大本大源呢?青年毛泽东认为,首先不仅要“研究哲学、伦理学”,而且要“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进而通过普及具有“大本大源”的新哲学、新伦理学,使“人人有哲学见解”,“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不“为强有力者所利用”。[20]研究和改造哲学、伦理学,绝不能“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而要“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21]《<伦理学原理>批注》集中见证了青年毛泽东“奋发踔励”地研究和改造哲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等文稿,则标识着青年毛泽东一步步找到唯物史观这个“足以解释一切”的“宇宙真理”,从而找到有效的救国救民、强国福民之方的心路历程。所以毛泽东后来回顾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22];“我一旦接受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23],真正做到了终生“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而他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正是继续以“孕群籍而抱万有”“绳束古今为一贯”的“取精用宏”之法,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中国化改造和时代化创新,是他在自己的时代所找到的颠扑不破的“大本大源”。他以这个“大本大源”为旗帜,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激发出全民族的“沛乎不可御”之力,挽救了危在旦夕的中华民族和濒临绝境的劳苦大众,再造了华夏文明的新辉煌,并且在5000 年历史上,第一次把中华民族固有的大同情结、大同梦想落实到了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上,使新中国的每一天都阔步前进在逐渐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康庄大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