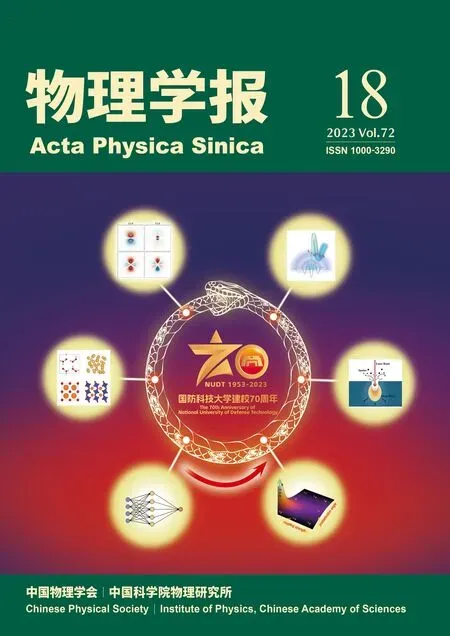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充电性能*
黄彬源 贺志† 陈雨
1) (湖南文理学院数理学院,常德 415000)
2) (贵州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贵阳 550018)
研究了基于依赖光场强度耦合Dicke 模型(也被称为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包括最大存储能量、充电时间、能量量子涨落以及最大充电功率等充电性能表现.首先考虑了能量非保守项(或者叫反旋波项)对量子电池的最大存储能量和最大充电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最大存储能量对能量非保守项权重的增加不是很敏感,但最大充电功率随能量非保守项权重的增加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进一步,研究了在能量保守项和能量非保守项是相同权重下量子电池中最大存储能量、充电时间、能量量子涨落以及最大充电功率的变化特征.通过与基于单光子和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的充电性能进行比较,发现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在充电时间和最大充电功率上强于基于单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但弱于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而3 种Dicke 模型在最大存储能量上没有一个确定的强弱关系,取决于不同的耦合常数.本文也揭示了虽然在最大充电功率上依赖强度耦合Dicke 模型会弱于双光子Dicke 模型,但在两种模型中体现的量子优势即最大充电功率与量子电池单元数满足的幂律关系是相同的.总之,本文为进一步研究量子电池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理论方案.
1 引言
量子电池是Alicki 和Fannes[1]在2013 年提出的一种新型量子储能设备,它是利用量子纠缠这一重要量子资源来更有效地实现量子系统中功(能量) 的提取.后来,Hovhannisyan 等[2]进一步阐明了量子纠缠对提取功上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它对充电功率来说至关重要,即如果要求充电功率越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产生的纠缠越多.近年来,基于各种物理模型的量子电池研究迅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如多原子系统在谐波场作用下的模型[3]、Dicke 模型[4-9]、自旋链模型[10-14]、中心自旋模型[15,16]以及三能级系统模型[17-19]等.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量子电池分为充电、存储以及放电过程.当前给量子电池充电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 并行充电[20],即每一个电池单元 (或者被称为量子单元quantum cell) 单独与一个充电器耦合进行充电;2) 集体充电[20,21],即多个电池单元共同与一个充电器耦合进行充电.特别地,Campaioli 等[21]揭示了集合充电方式中量子电池能实现快速充电的关键因素是一个整体操作(global operations),如产生多体纠缠操作,并给出了量子优势所需要满足的不等式.Ferraro 等[4]研究了基于单光子耦合Dicke 模型且以集合充电方式的量子电池,发现当量子电池中的量子单元数N较大且有限时,集合充电方式在最大充电功率(表征量子优势的物理量) 上有Pmax∝N3/2,这比并行充电方式Pmax∝N有一个幂指数的提升.Quach 等[5]将有机半导体作为二能级系统与微腔耦合首次在实验上实现了Dicke 量子电池.后来,Crescente 等[6]进一步研究了基于双光子耦合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的充电性能,发现最大充电功率Pmax同量子单元数目N之间满足Pmax∝N2,这进一步改进了量子优势,而且在充电时间上,双光子方式比单光子方式更有优势.最近,Dou 等[8]研究了一个推广单光子耦合Dicke模型,即考虑原子之间有相互作用以及有外在驱动场作用下的量子电池,发现在强耦合参数机制下,通过调节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使量子优势达到Pmax∝N1.88.他们[9]也研究了基于有腔场支撑下的海森伯自旋链模型的量子电池,揭示出通过综合调节模型中的各个参数组合,可以使量子优势达到Pmax∝N2.近来,Gyhm等[22]研究了一个一般物理模型背景下的量子优势,并进一步阐明了整体纠缠操作在量子优势中的重要性,且揭示了体现量子优势的最大充电功率Pmax∝Nα中的α必须满足α≤2 .Shi 等[23]详细研究了量子相干性和量子纠缠等量子资源同量子电池中提取功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量子电池中量子相干性和电池与充电器之间的纠缠是产生非零提取功的必要条件,且在充电结束后,量子相干性促进了相干功,而量子相干性和纠缠抑制了非相干功.最近,Yu 等[24]研究了一个开放量子电池中热库的量子相干性对量子电池中充电性能的影响,发现热库中的量子相干性对充电功率、充电容量及充电效率的改进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著名的Jaynes-Cummings (J-C)模型[25]是量子光学中的一个基本且重要的精确可解模型,它是一个描述二能级原子与单模光场相互作用的模型,适用于二能级原子与单模光场之间是弱耦合且近共振情况.在J-C 模型基础上如果加入反旋波项就是更一般的Rabi 模型[26],它适用于二能级原子与单模光场之间是强耦合甚至超强耦合情况,虽然此时激发数不再守恒,但近来显示它仍然可以在Bargmann 空间解析求解[27,28].单光子Dicke 模型和双光子Dicke 模型是在Rabi 模型的基础上推广到N个二能级原子与单模光场相互作用的模型[29].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单光子Dicke模型是一种线性耦合模型,而双光子Dicke 模型[6]则是一种非线性耦合模型.另一种非线性耦合模型是依赖强度的Buck-Sukumar (B-S)模型[30],它是考虑原子与光场的相互作用对光场强度有依赖性的J-C 模型,该模型被阐明可以更好地理解J-C模型中出现的原子翻转的周期自发塌缩和恢复现象.后来,Ng 等[31]利用幺正变换解析求解了具有反旋波项的B-S 模型.然而,同双光子耦合方式类似[32,33],依赖强度B-S 模型也会遭遇相同的能谱塌缩现象,即B-S 模型只有在耦合常数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才有定义[31,33]且反旋波项不会改变这种性质,只是减小了这个临界值[34].2016 年,Valverde等[35]建议了用库珀对箱与纳米机械共振器间的相互作用来模拟依赖强度B-S 模型的方案,这为依赖强度B-S 模型的实验实现提供了一条可能途径.
我们注意到,关于单光子Dicke 模型和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的充电性能已经被Ferraro 团队[4,6]详细地研究.但作为另一种非线性耦合方式,基于光场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简称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充电性能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未见到相关报道,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出发点.这里的依赖强度Dicke 模型是将B-S 模型中一个二能级原子和单模腔场耦合情况推广到N个二能级原子和单模腔场耦合的情况,且考虑了能量非保守项(即反旋波项)的影响.具体地,本文通过一种精度较高的数值对角化方法,求解了带有反旋波项的依赖强度Dicke 模型.首先研究了能量保守项和能量非保守项在不同权重情况下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最大存储能量和最大充电功率等表征充电性能参量的演化特征,研究发现: 能量非保守项对量子电池中最大充电功率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对最大存储能量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进一步,讨论了模型中的能量保守项和能量非保守项是相同权重情况下的量子电池中包括最大存储能量、充电时间、能量量子涨落以及最大充电功率等充电性能表现,并同单光子Dicke 模型和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的充电性能进行了比较.研究显示: 在充电时间和最大充电功率上,依赖强度Dicke 模型会优于单光子Dicke 模型,但会弱于双光子Dicke模型;在最大存储能量上,这3 种Dicke 模型各有千秋,取决于不同的耦合常数.另外也发现: 虽然最大充电功率上依赖强度Dicke 模型会弱于双光子Dicke 模型,但在体现量子优势,即两种模型中最大充电功率与电池中量子单元数满足的幂律关系上是相同的.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2 节给出了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模型以及衡量量子电池充电性能的各个物理参量;第3 节基于模型的数值结果揭示了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包括最大存储能量、充电时间、能量量子涨落以及最大充电功率等充电性能表现,并同单光子Dicke 模型和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的充电性能作了详细的比较;第4 节对文中获得的结果作了简要总结和展望.
2 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模型
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由N个全同二能级原子集合与一个单模腔场通过依赖光场强度耦合方式发生相互作用组成(它是依赖强度B-S 模型[30]中的单个二能级原子情况推广到N个二能级原子情况),其中每个二能级原子扮演量子电池中电池单元的角色,而腔场充当充电器的角色.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量子电池包括充电、存储以及放电过程.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考察基于依赖强度Dicke模型的量子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的充电性能.该量子电池的充电过程阐述如下: 当t<0 时,所有的二能级原子与腔场的耦合是关闭的;在充电过程( 0 ≤t 接下来,仅考虑二能级原子的频率和腔场频率是相同,即共振情况,如ωa=ωc,因为在非共振情况ωa≠ωc,从腔场到二能级原子系统的能量转移效率是更低的[4].鉴于研究的基于依赖强度Dicke模型的量子电池系统是一个封闭系统,这里假设N个二能级原子最初都处于基态 |g1,g2,···,gN〉a,单模腔场处于光子数态 |N〉c,这样整个系统的初态能表示成 这里,封闭系统在幺正演化下的含时波函数通过下列方式得到: |ψ(t)〉=e-iHt|ψ(0)〉.相应地,平均充电功率被定义为[37] 特别地,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刻能获得最大存储能量以及最大充电功率是量子电池表征充电性能的一些核心指标,它们被定义为[4] 另外,在充电过程中存储的能量可能存在不可避免的涨落(即能量量子涨落)也是衡量量子电池充电性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被定义为[38] 其中Jz(t) 表示算符Jz在海森伯绘景中的含时对应量,相应的平均值计算是在初态 |ψ(0)〉进行的.考虑到海森伯绘景和薛定谔绘景之间的关系,能量量子涨落Σ(t) 能被简化成其中平均值计算是在薛定谔绘景中的演化态|ψ(t)〉上执行的. 鉴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中包含了能量非保守项,这样基于该模型的量子电池在充电过程中腔场中的光子数并不守恒.一般来说,要获得该模型的解析表达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利用一种精度较高的数值方法来获得该模型的动力学演化,进而考察基于模型的量子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充电性能的表现.原则上,因为能量不守恒项的存在使得腔场中的光子数需要取任意大的整数.但文献 [4,6] 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对Dicke 哈密顿量数值对角化的过程中,只要腔场中光子数满足Nph=4N,其数值计算的结果误差在 10-5以下.数值计算中,部分利用了文献[39]中的Python 程序.下面将研究基于依赖强度Dicke模型的量子电池中充电性能的表现,并同基于单光子Dicke 模型[4]和双光子Dicke 模型[6]的量子电池中充电性能进行比较,阐明各种Dicke 耦合模型中充电性能的异同.衡量量子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充电性能表现的物理量包括最大存储能量Emax、充电时间tE、能量量子涨落以及最大充电功率Pmax等(分别用 1ph(1 photon) ,2ph(2 photon) 和ID(intensity-dependent)区分单光子、双光子和依赖强度Dicke 模型).首先,考虑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最大存储能量和最大充电功率随权重参数ξ和耦合常数g的变化关系. 图1 给出了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最大存储能量和最大充电功率随权重参数ξ和耦合常数g的变化(在数值计算的过程中,已经假设量子电池中的量子单元数N=10).观察图1 可以看到,最大存储能量和最大充电功率随权重参数ξ和耦合常数g的变化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1) 总的来说,最大存储能量对权重参数ξ和耦合常数g的增加不是特别敏感,换句话说,耦合常数g从弱耦合到强耦合机制变化时,能量非保守项对量子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最大存储能量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如图1(a)所示;然而,权重参数ξ和耦合常数g对最大充电功率有明显的影响,特别地,在耦合常数g处于强耦合机制下,随着权重参数ξ的增加,最大充电功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图1(b)所示.因此,能量非保守项的加入其实只对最大充电功率有明显的影响,而对最大存储能量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结果.2)从细节上来说,最大存储能量与权重参数ξ和耦合常数g之间不是一个单调变化的关系,而是时减时加的关系;但最大充电功率随权重参数ξ和耦合常数g的增加而单调递增.到此,我们已经得知,随着能量非保守项权重的增加,最大充电功率可以很明显地得到提高.接下来,进一步将基于依赖强度耦合Dicke模型同单光子和双光子耦合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充电性能进行比较,本文选择ξ=1,即能量保守项和能量非保守项是相同权重的情况. 图1 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a)最大存储能量 (以 ωa 为单位)和(b)最大充电功率 (以 为单位)随权重参数 ξ 和耦合常数g 的变化.在数值计算的过程中,电池单元数被设定为N=10Fig.1.(a) Stored energy (in units of ωa ) and (b) maximum average charging power (in units of ) as a function of the parameters ξ and g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 Dicke quantum battery,where the number of quantum cell N=10 is chosen in the calculation. 图2 给出了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存储能量EID(t)、能量量子涨落和平均充电功率PID(t) 在不同的耦合常数下随无量纲时间参数ωat的演化(量子电池中的量子单元数被设定为N=10). 图2 在不同的耦合常数 g=0.005 →0.1 →0.5 下,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存储能量 EID(t) (以 ωa 为 单位)、能量量子涨落 ΣID(t) (以 ωa 为单位),以及平均充电功率 PID(t) (以 为单位) 随无量纲时间参数 ωat 的演化,量子电池中的量子单元数被设定为N=10Fig.2.Stored energy (t) (in units of ωa ),its fluctuation ΣID(t) (in units of ωa ),and average charging power PID(t) (in units of ) versus the dimensionless quantity ωat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 Dicke quantum battery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where quantum cell is set to N=10 in the calculation. 图3 在不同的量子单元数(N=8 →10 →12 →14 )下,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a)最大存储能量 (以ωa 为单位)和(b)最大充电功率 (以 为单位)随耦合常数g 的变化Fig.3.(a) The maximum stored energy (in units of ωa ) and (b) maximum charging power (in units of ) versus the couplings constant g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 Dicke model in the different quantum cells N=8 →10 →12 →14 . 图4 在不同的耦合常数 g=0.005 →0.1 →0.5 下,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a)最大存储能量 (以 ωa 为单位)和(b)能量量子涨落 ΣID (以 ωa 为单位)随量子单元数N 的变化Fig.4.(a) The maximum stored energy (in units of ωa ) and (b) its quantum fluctuation ΣID (in units of ωa) versus the number of quantum cells N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 Dicke model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 g=0.005 →0.1 →0.5 . 2)能量量子涨落ΣID(t) 和.从 图2(a)–(c)中的虚线可以看到,无论在弱耦合还是强耦合机制g=0.005→0.1→0.5,随着时间的推移,量子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存储的能量都会存在一定的涨落,即能量量子涨落.怎样解释量子电池中一直会存在能量量子涨落呢? 其原因是除了最开始时刻二能级原子系统与腔场处于分离态,其后任意时刻二能级原子系统与腔场一直在发生相互作用,这导致全部来自腔场中的能量Emax=Nωa并没有全部转移在原子上(即存储能量EID(t) 总是小于Nωa),正如文献[40]阐明的一样,只有当量子电池全部充满电,才不会有涨落.另外,在不同的耦合常数下,可得到的最好的能量量子涨落为=1.577,对应的最大存储能量为=7.313 .而单光子Dicke模型中最好的能量量子涨落能达到=1.194,其对应更多最大存储能量=8.861 .为了更直观显示基于3 种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最大存储能量、充电时间以及相应的能量量子涨落之间的比较关系,将相关数据列于表1 中. 表1 在不同耦合常数 g=0.005 →0.1 →0.5 下,基于依赖强度、单光子和双光子3 种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最大存储能量 Emax(tE) (以 ωa 为单位)、能量量子涨落 ≡Σ(tE) (以 ωa 为单位)及充电时间 tE (以 为单位)等充电性能参数的比较.在数值计算中,量子单元数被设定为N=10Table 1. Comparisons of the maximum stored energy Emax(tE) (in unit of ωa ),its fluctuations ≡Σ(tE) (in units of ωa) andcorresponding charging time tE (in units of )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single photon,and two-photon Dicke models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 g=0.005 →0.1 →0.5 ,and quantum cells N=10 in the calculation. 表1 在不同耦合常数 g=0.005 →0.1 →0.5 下,基于依赖强度、单光子和双光子3 种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最大存储能量 Emax(tE) (以 ωa 为单位)、能量量子涨落 ≡Σ(tE) (以 ωa 为单位)及充电时间 tE (以 为单位)等充电性能参数的比较.在数值计算中,量子单元数被设定为N=10Table 1. Comparisons of the maximum stored energy Emax(tE) (in unit of ωa ),its fluctuations ≡Σ(tE) (in units of ωa) andcorresponding charging time tE (in units of )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single photon,and two-photon Dicke models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 g=0.005 →0.1 →0.5 ,and quantum cells N=10 in the calculation. 表2 在不同耦合常数 g=0.005 →0.1 →0.5 下,基于依赖强度、单光子和双光子3 种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最大充电功率 Pmax(tP) (以 为单位)和充电时间 tP (以 为单位)等充电性能参数上的比较,量子单元数被设定为N=10Table 2. Comparisons of the maximum average charging power Pmax(tP) (in units of ) and corresponding charging time tP (in units of )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single photon,and two-photon Dicke models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 g=0.005 →0.1 →0.5 ,and quantum cell N=10 . 表2 在不同耦合常数 g=0.005 →0.1 →0.5 下,基于依赖强度、单光子和双光子3 种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最大充电功率 Pmax(tP) (以 为单位)和充电时间 tP (以 为单位)等充电性能参数上的比较,量子单元数被设定为N=10Table 2. Comparisons of the maximum average charging power Pmax(tP) (in units of ) and corresponding charging time tP (in units of )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single photon,and two-photon Dicke models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 g=0.005 →0.1 →0.5 ,and quantum cell N=10 . 前文已经讨论了在确定的量子单元数,如N=10下,最大存储能量、充电时间、能量量子涨落以及最大充电功率在不同耦合常数下的变化特征,并同单光子和双光子Dicke 模型中的充电性能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发现,在充电时间和最大充电功率上,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优于单光子Dicke 模型,但弱于双光子Dicke 模型;而3 种Dicke 模型在最大存储能量上没有一个确定的强弱关系,同耦合常数密切相关. 其中,幂指数b反映了量子电池在充电的过程中,与并行充电方式相比具有的集体充电的量子优势.为了较为准确地获得a和b的值,这里采用线性拟合的方式.为此,在方程(10)的两边执行一个线性化处理,即 通过数值计算和数据拟合,不难确定方程(10)和方程(11)中的a和b如图5 所示.为了将依赖强度Dicke 模型和双光子Dicke 模型中的最大充电功率随量子单元数的变化进行比较,图5 中也显示了双光子Dicke 模型中的数值计算和数值拟合的结果,即.从图5 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每一个量子单元数N,从弱耦合到强耦合机制(g=0.005→0.1→0.5)依赖强度Dicke 模型中最大充电功率弱于双光子Dicke 模型中最大充电功率,即(a<α).然 而却遵守类似的幂指数规律,如(b≈β≈2).为了更清楚地比较,将相关的数据列于表3 中.因此,通过以上研究可知,虽然依赖强度Dicke 模型在最大充电功率上会弱于双光子Dicke 模型,但在两个模型中都具有相同的量子优势. 表3 在不同耦合常数( g=0.005 →0.1 →0.5 )下,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中最大充电功率 ∝aNb (以 为单位)和双光子耦合Dicke 模型中最大充电功率 ∝αNβ (以 为单位)的比较Table 3. Comparisons of the maximum average charging power ∝aNb and ∝αNβ (in units of )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 and two-photon Dicke models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 g=0.005 →0.1 →0.5 . 表3 在不同耦合常数( g=0.005 →0.1 →0.5 )下,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中最大充电功率 ∝aNb (以 为单位)和双光子耦合Dicke 模型中最大充电功率 ∝αNβ (以 为单位)的比较Table 3. Comparisons of the maximum average charging power ∝aNb and ∝αNβ (in units of )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 and two-photon Dicke models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 g=0.005 →0.1 →0.5 . 图5 在不同的耦合常数(g=0.005 →0.1 →0.5)下,基于依赖强度Dicke 模型和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的最大充电功率 (以 为单位)随量子单元数N 的变化,量子单元数N ∈[1,30]Fig.5.Comparison of maximum charging power (in units of ) versus the number of qubits N for the intensitydependent Dicke model and two-photon Dicke model in the different couplings g=0.005 →0.1 →0.5 ,quantum cells N ∈[1,30] . 本文通过一种精度较高的数值对角化方法,求解了带有反旋波项的依赖强度Dicke 模型 (N个二能级原子通过非线性耦合方式共同与一个单模腔场发生相互作用).进一步,探索了基于该依赖强度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这里,每个二能级原子作为一个电池单元,单模腔场作为充电器)中包括最大存储能量、充电时间、能量量子涨落以及最大充电功率等充电性能.通过与基于单光子和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的充电性能作比较,发现: 基于依赖强度耦合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在充电时间和最大充电功率上强于基于单光子Dicke模型的量子电池,但弱于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并且3 种Dicke 模型在最大存储能量上没有一个确定的强弱关系,而是与耦合常数的选择有关.另外,揭示了基于该依赖强度耦合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能体现量子优势的幂律关系: 当二能级原子数目很大且有限时,量子电池中的最大充电功率与二能级原子数目的平方成正比.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幂律关系优于基于单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的幂律关系,而与基于双光子Dicke 模型的量子电池中的幂律关系是相同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依赖强度Dicke 模型和双光子Dicke 模型中可能会出现能谱塌缩现象,这里讨论使用的耦合参数不是很大(采用同双光子Dicke 模型[6]中相同的耦合参数).近来,Liu 等[41]研究了通过引入一个非线性光子项对B-S 模型的影响,发现引入的非线性光子项不仅可以消除能级塌缩现象,而且对模型中光子阻塞效应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依赖强度Dicke 模型中是否可以引入一个非线性光子项来消除模型中的能谱塌缩问题,且非线性光子项对量子电池中的充电性能是有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另外,文中研究的依赖强度Dicke模型没有考虑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充电性能性影响,在其他模型如单光子Dicke 模型[8]中已经显示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最大充电功率有重要的影响.这些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3 分析与讨论
3.1 最大存储能量和最大充电功率与权重参数 ξ 和耦合常数g 的关系

3.2 基于依赖强度、单光子和双光子Dicke模型的量子电池中充电性能比较





3.3 最大存储能量、能量量子涨落以及最大充电功率与量子单元数的关系


4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