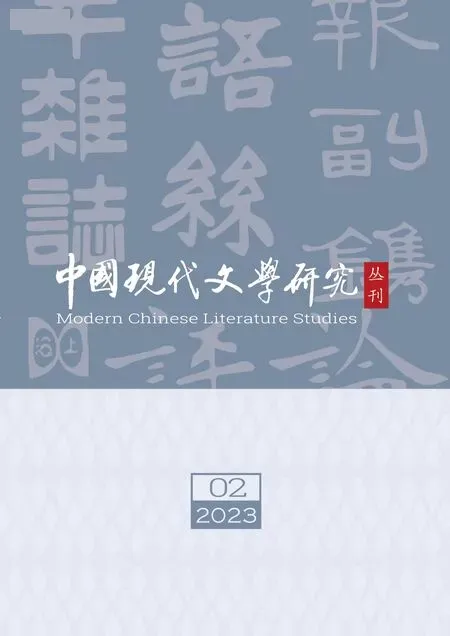触摸历史的心情、技艺及媒介
陈平原
“文献学”“史料学”“物质文化”,是三个相互关联但不尽一致的学术概念。若局限在文学史或文学研究,“文献学”主要着眼于文学文献的收集整理、去伪存真、分类编目、流通利用,其技术手段包含版本、目录、校勘等。“史料学”涉及文学及其周边资料的辑佚、补遗、校勘、考订、研究、阐释等,具体操作方式与文献学相近。“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无疑更广泛,几乎囊括所有思考及表达的物质呈现形式。十五年前,我谈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希望兼及“作为文字载体的报刊、书籍,作为生产者的报社、出版社,以及作为流通环节的书店、图书馆等”,但真正入手处,依旧还是书籍的物质形态。1参见陈平原《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此乃作者2007年12月29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演讲稿,初刊《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5月);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8期转载。唯一相同的是,在以往的文学研究格局中,这三者都属于“偏师”。如今“偏师”要求转正,主动承担更大的历史重任,除了依旧拾遗补缺,还想在某些中心地带标新立异,颠覆成说。
面对此迅速崛起的新锐之师,我没有能力披挂上阵,只能敲敲边鼓,帮着呐喊几声。一方面让先驱者不太寂寞,另一方面也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他们哪里有雷区,需要尽量回避。因此,本文絮絮叨叨,不像专业论文,更接近“白头宫女说玄宗”。
一 “经典化”与“史学化”
我曾不止一次谈及现代中国文学这个学科(兼及近、现、当代),因历史纵深不够,技术门槛不高,进入21世纪后已荣光不再了。但此学科有个好处,那就是研究者普遍对时势敏感,且善于自我反省。如何“调整自己的学术姿态,兼及外部观察与内在体验、凸显技术含量与生命情怀,实现经典化与战斗性的统一”1参见陈平原《却顾所来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北京青年报》2018年12月18日;《“新文科”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对于很多从业人员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挑战。本文无意全面论述,只想单刀直入,专谈“经典化”。
1980年,王瑶先生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有这么一段话:“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2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将近十年后,樊骏先生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连载八万字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从四个方面总结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成就,更就史料学所可能展开的方向及方法,还有常见且至关重要的不足和缺陷,做了全面阐述。3参见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408页。此文后经作者仔细修订,改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及《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从学科奠基人的学术“随想”,到第二代学者的“总体考察”,关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使用与研究,在学界内部逐渐得到普遍认可。因此,整个研究往经典化的方向迅猛发展。这一点,从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的《“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反对意见,则可举出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4参见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二文相隔十年,且使用概念不太相同(“古典化”与“史学化”之间,仍有不小的缝隙),但学术立场及趣味的差异,还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没必要上升到新时代的京海之争,或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内部的裂缝。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划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是眼下通行的做法,也是教育部确立二、三级学科的依据。如此划界,理所当然地催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学现代文学出身的,往往偏向于史学;而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则更注重批评。应该说,二者都有其合理性。史学寂寞,需要下苦功夫;批评热闹,更依赖个人才气。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认定关注近十年作家作品的,属“当代文学批评”;谈论十年前的作家、作品、思潮、现象的,可一直上溯到晚清,统称为“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史”本就兼及文学与史学,存在、挣扎并发力于二者的夹缝中,故尽可各取所需,自由发挥。只有在承认乃至凸显“文学史”的史学面向,认为其可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艺术史、民族史、科学史等相提并论时1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触摸历史的心情、技艺及媒介”这一话题,方才得以成立。
二 史料学课程的得失
假如将文学史家的主要工作视为“历史研究”,那么,需要各种知识储备与技术训练,其中就包括“史料学”。作为专业研究者,“工具箱”里的东西越多越好,所谓“艺不压身”是也。与文学创作更多倚仗个人才华与激情不同,史学研究讲究沉潜把玩与厚积薄发。
考虑到当下中国,学科基本稳定,研究思路也大致定型,不再只是简单的宣传工具(无论何种立场),这一学院派及经典化的结果是,越来越看重基本训练与技术含量(得失皆在此,但根源在大时代,个人无法扭转)。因此,我深感有必要为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史料学专题课,帮助其拓宽视野,积累学识,练习使用各种工具,期待有朝一日喷薄而出。去年春季学期,我重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第一次是2016年秋季学期)。现不揣谫陋,抄录各讲题目如下:
第一讲.触摸历史的心情与策略
第二讲.文本的生产、移动及阐释
第三讲.手稿的甄别、校勘与研究
第四讲.选本、大系与丛书
第五讲.为何以及如何编纂全集
第六讲.现代文学的版本、辑佚与考辨
第七讲.新闻报道与文艺副刊之关系
第八讲.杂志的分类、栏目及连载
第九讲.如何阅读日记与手札
第十讲.自传与年谱的对话
第十一讲.回忆录与口述史
第十二讲.查阅档案的方法及目标
第十三讲.从资料集到数据库
第十四讲.在图像与文字之间
第十五讲.声音的政治及文章
首讲开门见山,我特别推荐马克·布洛克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版)》(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取其兼及技术与境界,在强调求真的同时,悉心保存历史的诗意,以及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体悟与想象力。至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刊行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那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史料学著作,对第一章讨论史料工作四步骤及其目标——收集史料(求全)、审查史料(求真)、了解史料(求透)、选择史料(求精),印象极深,至今仍念念不忘。
考虑到讲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我着重评述以下十部著作: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朱金顺《新文学考据举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单就教学而言,最合适的,还属刘增杰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因其面面俱到,且对各家学说多有引述,便于读者进一步追寻与探究。
具体讲授时,好几讲是利用我以前的研究成果,然后再加以引申发挥,如第二讲借用《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以及《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读书》2007年第10期),第四讲借用《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现代中国》第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五讲借用《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从〈章太炎全集〉说起》(《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25日)以及《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香港]《中国文学学报》2018年第九期,2018年12月),第七讲借用《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书城》2004年第2期)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论文》(《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八讲借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2003年第1期),第十讲借用《半部学术史,一篇大文章——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九讲谈论作为文体的日记与书札时,借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六章“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至于第十四讲借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一章“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晚清画报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的位置”,以及第十五讲借用《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10月)),更是显而易见。但所有这些都只是部分采纳,课堂上必须展开来讲,因而有赖众多学界同人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介绍评述多,专深研究少,课后感觉较有心得、值得整理成文的,也就《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及策略》以及《全集编纂的宗旨、立场与边界》区区两篇。1参见陈平原《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及策略》,(香港)《中国文学学报》第十一期,2021年6月;《全集编纂的宗旨、立场与边界》,《南方文坛》2022年第6期。
最初的设想是,借助“史料学”课程讲授,养成实事求是的原则,寻求文本内外的沟通,借以获得整体感与大判断;可惜摊子铺得太大,泛论居多,实际操练不够,对学生研究能力的提升有限。但从长远着想,这门专题课值得常开(甚至不妨定为本专业研究生必修),鼓励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教授(如王风、张丽华等)接着上,以便日臻完善。
三 “触摸历史”的可能性
为何首讲题为“触摸历史的心情与策略”,那是因其中蕴含我的理论视野以及技术路线。20世纪末,我和夏晓虹合作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1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和出版社2019年[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9年[增订]版。,此书导论“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文章单刊,或题《五月四日那一天》(略有删节)。2参见陈平原《五月四日那一天》,《北京文学》1999年第5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6月。此文日后成为我的专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一章,只是添加了副题“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3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2018年版;Touches of History: An Entry into“May Fourth” China,translated by Michel Hockx,LEIDEN·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当初使用“触摸”(而不是研究、探索、阐释)这么柔软且感性的动词,很多人觉得新鲜,问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其实背后是相对理性的思考,即文学史家到底该采用何种立场、思路与论述策略,方能更好地进入历史。
在那篇写于2005年的导言“文本中见历史 细节处显精神”中,我澄清了《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着意追摹年鉴学派或新历史主义的猜想,称自己更多的是从本土的史学名家那里获得灵感;而且,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建构,不如说是史学意识及操作手法的革新。了解今人进入历史的困难,以及所谓历史重建的复杂性,不敢放言空论,因而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如广场上的学生游行、《新青年》中的文体对话、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章太炎的白话试验、北大的文学史教学,还有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仔细推敲,步步为营,这一研究思路,其实是受鲁迅先生以“药·酒·女·佛”这四个关键词来谈论汉魏六朝文章的启示。至于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更是史学研究的常规操作。只是没想到,最后竟凝聚成为一个标志性口号——“触摸历史”。时至今日,在史学论述中使用“触摸”这一动词,用来表达某种兼及虚与实、软与硬、感性与理性、考据与抒情的论述姿态的,比比皆是。
这就说到“史料学”课程传授的,不仅是若干可以重复实操的技艺,更包括视野、方法与论述策略。史料的收集、审查、了解与运用,有技术层面的评价标准,若做得很出色,确实值得表彰;可史料考辨若能促成新的论题、视野或研究思路,那就更理想了。否则,为考据而考据,总让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三十年前,我撰写《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1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日译本,中岛长文译,《飙风》32号,1997年第1期。时,被鲁迅的两句话所震撼。一句是驳斥陈西滢关于抄袭的指责,鲁迅骄傲地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2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这背后,是因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垫底。另一句则是撰史必须“先从作长编入手”3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84页。。没有编纂史料长编这样“独立的准备”,鲁迅不敢贸然撰写文学史。将史料整理与考辨作为撰写学术著作的根基,这是严肃、严谨、严苛的史学家选择的治学路径。只是学海无涯,人生有限,真能做到的,实在少而又少。而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那就是,史料工作必须有学术眼光的指引,而不仅仅是一种繁重的技术活。
遵循这一治学路径,我的许多编校,其实都是为了配合自家著述。比如与夏晓虹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是配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写作4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97年版;(新版)《清末民初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97年版;(新版)《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年版。;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是《老北大的故事》的前奏5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8年版;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5年版。;编《〈新青年〉文选》,是为了撰写《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6陈平原编:《〈新青年〉文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021/2022年修订版;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2018年版。;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是为了完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7陈平原辑,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20年版;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增订版。。将史料整理与专业著述相捆绑,有时配合默契,互相支撑;有时则劳神费力,效果并不佳。关键在于,不是所有的史料收集、甄别与考辨,最后都能有效地促成论述境界的提升。
记忆中,我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借清理晚清报刊连载的演进,讨论谴责小说“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结构方式的形成1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84页。,还有就是《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之辨析新发现的周氏兄弟为胡适《尝试集》删诗信件,论述“经典是怎么形成的”2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313页。,这两回史料的整理与阐释,确实有比较出色的发现乃至发明。可惜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并不常见。能在某个专业领域,完美地解决某个疑难问题,哪怕问题很小,也都是令人欣喜的。但如果这个考辨连着大的时代风云或思想潮流,那就更值得庆贺了。我之所以在不同场合表扬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杨镰的《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就因为那是有思想、有见识的考据。文献的收集、甄别与整理,外人看来很沉闷,但持之以恒,也自有独特魅力。要不进不去,进去了的往往会入迷,因而变得锱铢必较,见木不见林。这是个甜蜜的陷阱,最好事先告知学生。
2008年6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主持“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发表《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介绍了我们的很多业绩,但也提及可能存在的七个陷阱,其中包括:
第四,念文史的,讲究“尚友古人”,长期与屈原、杜甫或鲁迅等对话,能提升自家的精神境界及文化品位。以精英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锻炼思想,培养情趣,追求卓越。而集中精力研究报刊,对自家解读文本的能力以及鉴定作品的品位,不见得有多大的帮助。我注意到,不少专注报刊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做得不错,但日后的研究格局不大。因此,我有点担心,是否研究生阶段的这一选择,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对于报刊研究者来说,如何兼及思想史的视野、文化史的敏感、社会史的功力以及文学史的趣味,是个必须直面的难题。至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到底以“掌握技能”还是“推出成果”为主,也是个两难的选择。过多强调“填补空白”,导致学位论文的选题越来越偏,不敢与伟大作家或经典作品对话,不是一个好现象。1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有鉴于此,为研究生讲授史料学课程,我必须开宗明义,告诉同学们,这只是文学史家工具箱里的一种,必须学会,但不宜过分夸大其功用。
四 从报刊研究到跨媒介与跨文体
二十年前,我与日本大学山口守教授合作,在北大召开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会后出版的同题论文集(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反应很好,第二年还重印了。对于中国学界从文学史角度进行报刊研究,这次会议及这本论文集起了很好的作用。论文集中作为附录的《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是我在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目的是阐发北大的学术传统及同人立场,故副题为“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
文中提及“王瑶先生不做专门的史料收集与考辨工作,但充分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高度评价阿英之专注于晚清报刊以及现代文学史料辑录),这大概与其早年的古典文学研究训练有关”;更概述严家炎、孙玉石两位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及指导博士生“多从思潮与流派入手,且擅长发掘和使用报刊资料”。此外,我还特意提及我那不以史料见长的师兄钱理群,引他在《1948:天地玄黄》“代后记”中的一句话:“每回埋头于旧报刊的尘灰里时,就仿佛步入当年的情境之中,并常为此而兴奋不已。”因为,在我看来,这主要不是技术,而是心情。“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理论框架可以改变,但借助某种手段而‘触摸历史’,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却是必不可少的‘起步’。”2参见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转载。
图书馆里的旧报刊,这只是众多文学史料中的一种;作家的手稿、书札、日记,各种回忆录、口述史、田野访谈、未经披露的档案,以及声音、图像、实物等,不同类型的文学史料,难分高低雅俗,高手则善于交叉运用,点石成金。求学阶段修“史料学”课程,属于基本训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保证你走正路,守底线,多少能有成绩。就好比给你地图和指南针,然后就是你自己上路探险去了。若能经由此课程,培养学生尊重史料的心情(诚实、体贴)、搜集史料的能力(勤奋、沉潜)、解读史料的学识(敏锐、深刻),那就真的值得庆幸了。
当初我进入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很快意识到,擅长论述的(如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明显比注重史料的(如唐沅、封世辉、方锡德、商金林)更受学界关注与表彰。但在具体指导研究生时,两种路径交相辉映,完美补充。每回的开题报告及论文答辩,不同专长的导师各自发挥,开诚布公,对擅长吸收的学生来说很有帮助(相信亲历者都会有同感)。近日,钱理群为商金林即将由北大出版社刊行的《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撰写序言,有段话很值得引述: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是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学术、教学群体。它的特点和魅力就在于,每一个成员,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上,都各有特色,具有极大的独创性,又彼此补充,支持,更相互欣赏——后者尤其难能可贵。
在学术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这种求同存异、和睦共处的学术共同体,大概即将或已经成为一道“消逝的风景”。年轻一辈学人,学术训练普遍很好,但同样也会风格迥异,或擅长文本分析,或注重理论思辨,或喜欢史料甄别,希望能像前辈学者那样互相欣赏、携手同行。
2001年的北大会议,虽名为“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也涉及照片、剧场等,但主要关注的是报刊及书局;2008年的港中大会议,题为“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已将画报、唱片、电影、电视等纳入考察范围。近期因“新文科”建设以及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成立,我多次谈及自己的学术理想——“以跨学科的视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1参见陈平原《“新文科”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现代中国”的视野以及“人文史”构想》,《中华读书报》2022年10月12日。。其中“跨学科”常被提及,很好理解;需要略为铺陈的是后两者。
面对纷纭复杂的“现代中国”,到底该如何解读?传统的人文学者,偏重于文字及书籍。而实际上,“声音”和“图像”在传播知识、表达情感、影响人们的思维及审美方面,同样起到巨大作用。十年前,我在北大主持了一场《“跨媒介”如何对话》的学术座谈会,参与的嘉宾都是文学研究者,如李欧梵讲电影和音乐,黄子平讲网络文学,王风讲古琴考证,我讲图像研究等。其间,李欧梵道出我们面临的共同困境:“如何把不同学科、不同媒介的技巧及趣味糅合在一起,以达成一种新的工作目标,甚至建构一种跟今天的文学教授不一样的新的学术表达方式。”黄子平则巧用湖南某市交通管理标语自嘲:“刘翔不好当,跨栏会受伤。”1参见李欧梵等《“跨媒介”如何对话》,《现代中国》第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
同年,我写了《“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介绍自己所从事的跨媒介研究。2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7期转载。随着增订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的刊行,以及《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的完稿(将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我这方面的研究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后者的导言中,我说了一段感慨很深的话:
终于悟出来,所谓跨学科论述,必须与自家以往的研究相衔接;完全重起炉灶,不是不可以,但难度实在太大。对我来说,若想深入讨论“声音的中国”,必须与“文字的中国”相互阐释,那样方能更好地发挥自家特长。而最有可能兼及“声音”与“文字”的,莫过于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更重要的是,演说可大可小,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日常生活,也可家国大事。借助那些“纸上的声音”,研究者左右开弓、上下串联,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深入开掘其思想史或文化史意义,那是可以做成大文章的。3陈平原:《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有声的中国〉导言》,《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这里的跨学科其实包含跨媒介,借助“演说”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文学形式,我较好地实现了“声音的中国”与“文字的中国”的相互阐释,进而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研究;而在讨论晚清画报时,我虽然建立了“图像叙事”“图文对峙”“低调启蒙”等支柱,但构建起来的“图像的中国”,更像是一个独立课题,与“文字的中国”若即若离,没能有效地整合到现代中国文学进程中。
这可能是以后现代中国人文史撰述的一个重点与难点,即意识到“文字的中国”“声音的中国”“图像的中国”三者密切相关,有可能实现精彩的互动,但此前百年,各学科、各媒介的研究已卓有成效,各自形成一整套研究方法及概念术语,无形中构建起不小的藩篱,你如何优雅地跨越而不被两边学者嘲笑,这对有志于此道者是个巨大的挑战。
说到跨文体的写作,那更是我个人的兴趣,不见得有普遍意义。我说的“跨文体写作”,不是指既写学术论文,也撰长篇小说;而是述学时如何腾挪趋避,自由挥洒才华。前年我在北大社刊行《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在“前言”中特别强调:
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是。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1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这里的“表达”,可以是专著,可以是论文,可以是教科书,还可以是报刊文章,比如随笔、评论、札记、序跋等。
说这些,是因为有感于随着学院化加深,述学文体越来越刻板、单一,有时甚至变得很无趣。其中缘由,起码包括如下三点:后起的学者普遍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电子检索十分便利,旁征博引变得不太困难;学术刊物编辑日渐强势,有很多硬性要求。三十年前,我和朋友办《学人》集刊,致力于建立某种学术规范;三十年后,我又对过于严苛的规则与刻板的文体表示不满:
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札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是认可的,且曾积极鼓吹。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1陈平原:《与人论刊书》,《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
去年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小说史学面面观》,便故意保留讲课风格:“并非严格的专业论文,更接近于学术随笔,兼及个人感受,从书里谈到书外,如此琐琐碎碎,不登大雅之堂,却能使研究对象更加血肉丰满,对听课的学生来说,这些书本以外的‘闲话’或许更为难得。”各章连载《文艺争鸣》时,故意放在“随笔体”专栏,想试验“既学问,也人情,还文章”是否可行,结果还不错,学界朋友大都觉得文章“别具一格”。2参见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的“小引”及第35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之所以在此处特别强调述学文体的多样性,是因为史料学的成果不该都追求高头讲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时甚至把相关资料排列,三言两语就能解决问题。可受制于现有的学术期刊及评价标准,大凡写论文,就非端个架子不可,左盘右带,云山雾罩,越说越复杂,看着真让人着急。这一套学院派的招数,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不必太迷信。我想提醒专业训练很好的年轻一辈学者,除了专业论文,还有别的文体也值得尝试。同一个作者,既能舞长枪,也能使短棒,根据需要轮番上场,且都表演得出神入化,那才叫真本事。
(此乃作者于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大学人文论坛“如何呈现文学的‘过去’——文学史与文献学”上的主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