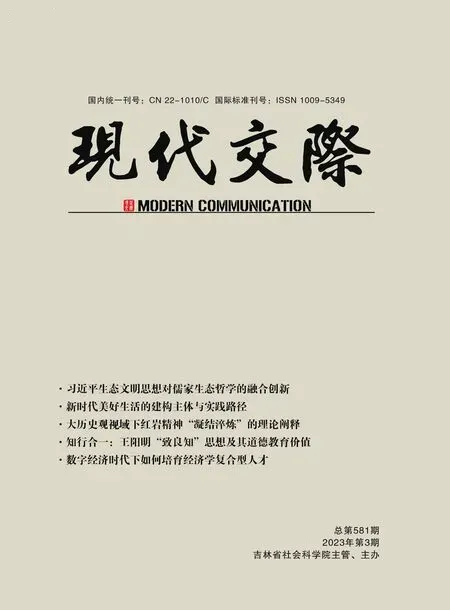儒家伦理思想的多重意义及当代教育价值
□郑香花 邱艳萍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儒家思想,更是为中国提供独有的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体系,为构建出具有丰富历史底蕴与特色的中国奠定理论基础。儒家伦理思想是源于儒家学派对人类自身修养的一种理性思考,通过将人置于社会中,研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想学说。它是当代中国教育的重要理论支撑与土壤,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客体。但随着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中国文化受到巨大冲击,探寻儒家伦理思想的时代价值迫在眉睫。儒家伦理的意义通过时代迭起论证了自身的继承性与创新性价值,也将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提供独具一格的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教育价值。
一、历史的连续性与创造性:儒家伦理思想意义的多重演变
儒家伦理思想萌芽于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动荡的社会中产生对人、家庭、国家和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通过个体与群体间的交流、传播,成为一种思想与学说,在中国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动荡的春秋时期,为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多种可能性;在社会安邦、君权稳定时刻,经过多方的斗争与权衡,儒家伦理成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为巩固朝纲贡献理论力量;在风雨飘摇的近现代,儒家思想成为新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底蕴;在全球化趋势下的新时代,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提供理论价值,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1.萌芽与发展: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混乱的现实与贫苦的生活激发了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个体产生新的思想与信念,通过群体内与外的整合、传递,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其中,儒学伦理是儒家学者对道德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考,主要探讨了道德本源、道德作用、道德评价、道德准则及其道德修养等问题,对维持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最具代表的学者分别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对于伦理思想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都将“仁”作为思想的核心部分,为社会的发展奠定和谐共处的基调。孔子是儒家伦理文化的奠基者,一生追求恢复周礼,为此他的伦理思想传承了周礼的核心思想,提出了“仁”与“礼”结合的治国理念。《论语》记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其中孔子的爱,是泛爱众,打破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脐带的爱,将爱带入社会领域[1],把家庭伦理变成社会伦理,将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相结合,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方式。孔子认为要构建出以个体为基础,并上升至家庭和社会的治理体系,必须通过“正名”。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里的君、臣、父、子是名,而君、臣、父、子的本质为实,名与实相对应就为“正名”,每一个名都有其职责与义务,每个人履行自己所需要承担的责任,社会秩序就会稳定,国家就会兴旺。孟子继承孔子的伦理思想,并提出了以“四德”与“五伦”为基础的治国学说。“四德”为仁义礼智,其中仁与礼是基础,也是最高准则,而“五伦”则是孟子在伦理思想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化为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君与臣及朋友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以亲、义、别、序、信五字加以形容和规范。孟子认为,这五类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相互的,并不存在上下尊卑之等级。他提出,若人人皆有“四德”与“五伦”,则社会和谐、天下安定。荀子的伦理思想则扩充到人性本恶,认为礼是法的一部分,为此强调“礼以制情”和“礼以定伦”,通过礼来使得人能秉公守法、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同时,他将孟子的五伦从个体之间的人伦关系扩展到群体之间的人伦:“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荀子·非十二子》)荀子的五伦不以血缘为联系,而是利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联结为理论,进一步凸显五伦的公共性与社会性。[2]虽然三人思想皆有不同,但皆以“仁”作为伦理的核心思想,认为人人都有“仁”心,就能天下太平,万世昌盛。这种“仁”的思想为当时的社会形态、制度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与可能性,被后世大一统国家作为一种国家主观意识形态,以保持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同时,为中国的“仁”“和平”奠定历史学理基础。
2.神化与异化:成为“巩固朝纲”的政治手段
汉朝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社会相对稳定,君主认为思想的统一有利于更好地治理国家。汉武帝时期起,儒学伦理思想开始从研究“人伦”关系对社会的影响转向研究如何通过儒学来构建大一统的核心价值,以此巩固皇权。汉朝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分。古文经学来源于先秦儒家现实派的延续,而今文经学则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传承。东汉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领导与主持了一项重要的儒学会议,史称白虎官会议,会议中特地大量引用纬书,自此,谶纬获得各界知识分子的认可,取得了法典地位。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的思想不再以“仁政”为重要理想与追求,而是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君权神授的天人关系为支撑点。所谓的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董仲舒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以同”“物固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说明人的异常必然引起自然的异常。[3]谶纬神学将原本的伦理关系变成“君权神授”,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进行上下尊卑的区分,构建了一个以君臣、父子、夫妇为经、以仁义礼智信为纬的新的伦理体系,借此来统一民众思想、巩固民心、团结国家,从而更好地抵御外敌。
儒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身的体系与内容,北宋时期的儒学将佛老学说的辩证思维融合到儒学纲常伦理道德中,也可以称之为道学和理学。北宋是儒家伦理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经历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后,宋明理学逐渐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的传承者,以巩固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为主要任务,对伦理提出新的观点和命题。朱熹一生注重著述《四书》,将天理作为封建道德的本源,即以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把仁义礼智作为宇宙客观本体;论述“存天理、灭人欲”伦理思想,将道德涵养看作欲望的枷锁,防止个体超过道德底线,以此维护社会、道德、民风和政风的和谐发展。[4]王守仁对朱熹的儒学伦理思想进行批判反驳,并提出良知是开展道德修养的最佳方式,将“天理”解释成人内心的德行与修养,将道德的内部、外部的传递与转化过程当作良知转化为道德的过程,将德性化为德行,强调道德的行动。虽然朱熹与王守仁在“天理”上有所争议,但其思想内涵都指向“存天理、灭人欲”,进一步诠释了宣扬儒家伦理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手段。至此,儒家伦理文化从汉朝一直到清朝末期,完全从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念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其爱国教育变成爱“统治者”教育,发展成愚昧思想,腐蚀本心,阻碍社会发展,成为如今教育者抨击封建思想的主要对象。
3.重构与回归:成为风雨飘摇下中国复兴的理论支撑
自汉朝后儒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科举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进一步推动儒学政治化、阶级化,三纲六纪的儒学伦理思想成为国家正统法典及个人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人心,减少动荡,笼络了各阶层知识分子,但也打击了为社会产生真正经济效益的其他阶层,严重阻碍了这些职业者的进取心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为此,在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出现了一批改革激进派。儒学伦理在民国初期成为封建愚昧思想的代表,对其进行极端的批判和否定,其行为与影响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相对也有改革保守派,他们认为儒家学说体现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价值观、社会体系与政治方向,承载着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心血。如果将儒家文化完全剥离中国,中国就不再是一个有着文化积淀、完整社会体系和独特政治的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它。在中国近现代时期,改革激进派和保守派一直相互拉扯,进入一个此消彼长的阶段。在五四运动时期,激进派处于上风,儒学研究停滞不前,缺少传统文化支撑的中国人开始陷入迷茫与不自信。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儒家伦理对支撑新中国文化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保守派对儒学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其中,冯友兰的新时代儒学改造对如今全球化视野下的儒学研究而言也具参考性。冯友兰先生从哲学的角度切入观点,总结出所有哲学的共有点,即“益道哲学”“损道哲学”和“中道哲学”。他采取将中国程朱理学式的中道哲学和西方新实在主义的中道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试图让二者相互解释,共同验证[5],为儒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路。20世纪20年代,公立东南大学将《学衡》作为儒学研究的中心,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号召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认同儒学伦理思想的学者进行文学复古运动。30年代,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改革激进派从消极地破坏转向积极地建设国家。国立中央大学创办《国风》杂志社,号召有志之士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抛弃陈旧、不适宜的“道统”;以民族意识为核心价值观,力图留存民族文化“伦理精神”。重新挖掘、丰富和充实儒学传统文化内在精神、伦理、制度及道德等资源,试图重新认识孔子和儒家伦理思想,为儒家传统文化辩护,以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秩序为目的,走出传统、狭小的儒学思想视野,开启具有面向未来的儒学新篇章,致力于从提高人民自我认同感和文化自信的高度去思考伦理体系的重构。[6]儒家伦理文化的复兴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促使一大批青少年于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承担个体职责与社会责任,为中国建设贡献有生力量。
4.启发与改造: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石
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中国带来了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冲击,中国若想在全球化中立足自身、化危为机,就必须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并以此为平台,涵养世界的文化。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在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体现出强大的兼容性与创新性。1958年初,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将儒学伦理文化向世界传递,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儒家伦理文化最早的世界性传播,强调了“心性之学”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虽将儒家伦理文化仅概括为“心性学”有失其本质性与完整性,但是其传播的渠道与范围确是新时代儒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其是海外儒学现实意义崛起的标准,意味着儒学的发展进入现代化新阶段。80年代后,杜维明、刘述先将儒家伦理文化与现代西方哲学新思潮相结合,提出“对话”学术理论思维,指通过抽象层面的宗教与对话、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互辩、心灵对话等方式,缓解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对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制度。新时期儒家思想以自身为载体,以经验为基点走出国门,跳出其空谈心性的理论层面,将其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中英明确提出重建传统儒学必须将儒学与现代化社会建立联系,融合西方的现代意识建立兼具伦理与管理互动的体系与机制,并将其运用到公共社会、企业治理中。[7]杜维明曾将儒家文化分成“儒教中国”和“儒家传统”两类,指出在独特制度体系的中国,儒家既可以代表文化思想层面的集大成者,也可以代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理念,政治理念是封建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被如今的学者称为封建的思想遗毒。[8]这种思想曾被杜维明称之为“政治化儒学”,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官僚制度和高度异化形态的一种道德价值。而“儒家传统”则是一种中国特色文化、精神与道德思想体系,也可以称为“儒家伦理”,认为其具有超越自我中心的思想、注重自我管理与约束,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个人与教育的进步、工作伦理与共同的努力。[9]杜维明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具有很强的人文主义理论,既不排斥非现实的“天”,也能接受现实的自然。它利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去参与政治,但不依赖政治而生存;它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也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兼容意识。从论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演变成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工具,在近现代与新时代则成为团结民众、树立中国自信与弘扬中国精神的手段。其极具更新与创造的意识使得儒家文化不仅仅成为一种文化,也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源泉。
二、多元化视角:儒家伦理思想的当代教育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的继承性特征确保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绵,为中国的文化传播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留了古代文明,而儒家伦理思想的创新性则为当代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中国构建出独具一格的社会体系,为世界全球化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力量。
1.仁礼存心:个体伦理教育价值
“仁”“礼”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思想[10],也是其对个体修养的具体要求。“仁”是爱人,“礼”则是克己。“仁”“礼”思想则是以个体自我修养为中心,通过对他人和自然的态度与其获得的反馈,确认个体伦理的发展的程度与未来指南。为此,可以从自身的修养、对他人的涵养与对自然的态度三个层次来分析。首先,自身的修养。个体自身修养是指个体达到自身的身心和谐状态。身心本为一体,二者应当相融、相互促进才能修身、修己、克己、正其身和成己。在教育的过程中,家长与学校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构建出身心一体的课程内容。其次,对他人的涵养。主要关注个体是否能与他人和谐相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人际交往结构体,有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相交。与他人的和谐相处不仅代表了心理的健康,也体现了身心的和谐。儒学中最常见的一种人伦关系为四德、五伦,就是探讨人与人之间要遵守的伦理礼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强调学习基本的人伦道德,方能入世出世,促使人们在社会群体中和谐共处。最后,是对自然的态度。所谓“天人合一”“敬畏天命”“仁民爱物”“以德配天”等强调尊重自然、对未知事物保持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让我们获得信仰,遵循社会契约,明确可为与不可为,成为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行的中国公民。儒家“仁爱和谐”教育我们身心和谐是一切和谐的基石,儒家伦理的“仁”“礼”促使我们在个体伦理教育的时候跳出惯有的个体品德范围,将个体置身于个体间、群体间与整个生态系统中,通过群体、社会、自然互融获取人生信仰与提升自我修养。
2.慈孝一体:家庭伦理教育价值
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新的时代萌发新的思想。为此,中国儒家伦理的家庭人伦关系在新的历史阶段必须激发出新的内涵与外延,以促使当代家庭与社会伦理更加和谐规范。慈孝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育的、血缘亲情催生的一种为维护长辈与晚辈利益关系的理念价值,即长辈的义务是关心、爱护晚辈,晚辈则要尽到赡养长辈、孝顺长辈的职责。[11]正确的儒家家庭伦理观念有助于构建亲子和谐、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规范。反之,持有不正确的家庭伦理观,将会导致亲子关系的僵化。部分家庭依旧以传统的“百善孝为先”或生命延续论为亲子关系指导理论,对子女的教育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用命令的口气与儿童交谈,而忽视慈与孝是一个相对的伦理范畴,是相互促进与循环的动态关系。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各国文化开始互通,形成了隐性的文化割裂,即儿童开明的亲子关系与家长传统的亲子观念的不同,这种割裂易导致父母与子女产生矛盾冲突。为此,我们要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亲子观,构建和谐、友爱的家庭氛围。首先,以儒家的“慈孝一体”为基础,传播父母与子女相互付出的观念,杜绝一方无尽索求或束缚,确立父慈子孝、子孝父慈的关系体系。其次,要与新时代接轨,运用生理学、卫生学、心理学等知识明确儿童是具有独立思维意识的个体,不因他人的意志而转移。不得将亲子关系看作附庸与延续关系,必须明白孝不是孩子的义务,而是享受权利后的责任。儿童作为成熟的个体,家长有义务以身作则引导新型亲子关系,为新时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思考,构建个体与家庭的新关联。最后,在新时代依旧要重视儒家伦理文化的教育,保留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国传统美德,将“孝”延续至中国的家庭、社会中,促使儒家家庭伦理文化得到时代性与创新性的继承与发展。
3.匹夫有责:国家伦理教育价值
从德育视角定义,责任感是人类主体对自我处于社会发展与个体成长过程中需承担的相应职责与义务的一种自我意识,是以完成道德任务为根本任务,并促使自身产生道德需要的一种情感体验。[12]一个有责任感的国家公民,能承担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任,将国家建设与自身发展相结合,将中华伟大复兴作为最终目标。要培养当代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就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国家社会意识为主导,培养具有中国社会责任意识的中国公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梦”的必经之路。“中国梦”这一伟大概念于21世纪初期提出,即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与中国儒家伦理文化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具有相似性。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体现在《礼运·大同》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不仅是“大同”社会的基石,还能为“中国梦”的实现寻找适合的发展路径,打破西方的垄断模式,促进世界文明多样化。西方哲学思想独树一帜的时期,中国汲取了西方哲学知识来治理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精致利己观的个人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显示出弊端,容易引发人的自私、虚伪、冷漠与毫无担当,与世界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儒家的“天下为公”则强调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平,在教育中贯彻儒家的思想,有助于培养具有爱心、责任心、关心社会发展、能伸张正义、有责任感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栋梁,为建设一个和平、有责任担当的国家奠定基础,为建设和谐、发展的世界提供参考。为此,树立“天下为公”的理想信念能培养当代青年的责任感,为在全球化趋势中进行爱国教育、建立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和治国伦理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三、结语
儒家伦理是一种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是世界上唯一发展至今、绵延不绝的文化,在与外来伦理文化互相交汇的时候,既能包容吸纳又能始终以本土伦理为中心。[1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文化在孔子、孟子等人的传播中凸显独特的教育伦理哲学。随着社会发展与变迁,儒家文化的伦理关系逐渐被大众接受,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汉武帝时期,儒家教育伦理思想在董仲舒和汉武帝的推动下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教育伦理思想的完善和发展,但儒家的伦理思想也成为当朝统治者统治民众的工具,至此儒家的伦理思想异化。这种异化使得儒家伦理思想从单纯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扭曲成具有阶级性的上下关系,成为封建统治者巩固自己权力的利器,禁锢了民众的思想,腐化社会风气。随着封建皇权被推翻,儒家的伦理思想遭受两千年来前所未有的、绝对性、倾斜性的批判,走入衰落。但依旧有一部分学者坚信其思想与内涵支撑着中国文化,传承着中国精神,并不断挖掘其当代价值与意义,促使其成为民国时期团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着中国,儒家伦理思想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石,促使中国立足于世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理论。儒家伦理文化随着朝代和诠释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但其本质思想从未发生偏差。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及“仁爱和谐”的核心思想内涵,在摒弃各种社会发展、政治需求及人的私利后逐渐显现出其传承性与不变性,成为中国发展坚实的后盾,为现代社会构建一套完整治国理政的理论体系,为当代个人修养教育、家庭伦理和国家秩序的构建提供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