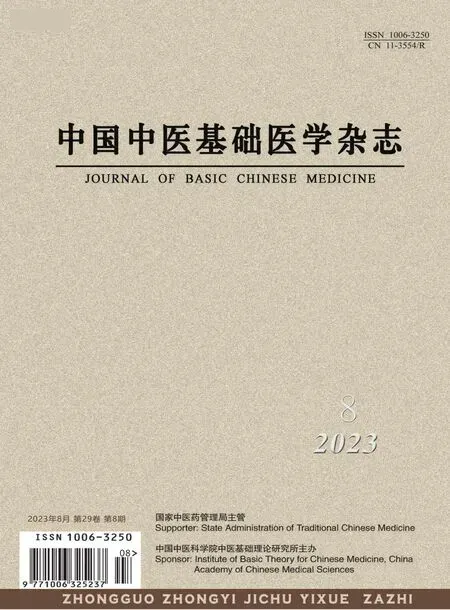黄疸病“瘀热”与“湿热”病机辨析❋
付广威,范孔莉,曲春成,韩思佳,王培基,郝俊凯,王 钊,桑希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 150040)
黄疸病,因其身黄、目黄、小便黄,易于观察的特征性症状,以及常伴发的食差、乏力等非特异性表现,是中医学认识最早的疾病之一。《灵枢·论疾诊尺》中云“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1],这即是对黄疸病症状较为全面的描述。全面的感性认识为更为深刻的理性认识提供了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历史上对黄疸病病机的论述也颇为丰富,产生最大影响的当属以张仲景为代表的“瘀热说”和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湿热说”。宋元以前,医家多以“瘀热说”为圭臬;宋元及以后,“湿热说”则渐居主导地位。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学的冲击,湿热说的病位在脾胃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肝胆。纷繁复杂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中医学发展过程中从辨病到辨证论治的转向、五行对医学理论的深入渗透以及近代以来西医对中医学的影响。本文即是通过对瘀、湿、热等黄疸病关键病理因素的分析,重新审视瘀热与湿热病机在黄疸病中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分析黄疸病论治从湿热转向瘀热的原因,以小见大,管窥中医学学术体系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1 黄疸病 “瘀热”与“湿热”病机
1.1 瘀热病机的基本观点
黄疸病核心病机为瘀热的观点,主要见于仲景的著作中。《伤寒杂病论》瘀热凡四见,其三与发黄有关。分别是《伤寒论》中茵陈蒿汤和麻黄连翘赤豆汤证都提到的“瘀热在里,身必发黄”,以及《金匮要略·黄疸病篇》中的“脾色必黄,瘀热以行”。可见仲景认为瘀热是导致发黄的关键病机,通过对仲景原文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瘀热发黄的基本观点是:热不得越,郁热内陷,伤于血分,血脉瘀滞故而发黄。正如柯琴对瘀热病机的解释,“热反入里,不得外越,谓之瘀热”[2]。相比之下,虽然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出现了湿热一词,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湿热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长”[3],但是综观仲景全书,有言热者,有言湿者,但从未提及“湿热”二字。后世部分医家将“瘀热”的“瘀”解释成“郁”,再结合小便不利等症以及仲景“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之语,曲解了湿在黄疸病中的真实作用,以湿热为核心病机解释黄疸,并不符合仲景本意,后有详述,兹且不赘。除仲景外,后世医家从瘀热病机论治黄疸者并不在少数。《诸病源候论》说“脾脏中风,风与瘀热相搏,故令身体发黄”[4],认为外感风邪入血与患者素有之瘀热相搏结是黄疸病发生的重要病机。近代医家唐容川说“脾胃太阴湿土,主统血,热陷血分,脾湿郁遏,乃发为黄”[5],更是直接点明湿邪郁滞,热不得发越所致的“热陷血分”为黄疸病的核心病机。
1.2 湿热病机的基本观点
如前所述,《黄帝内经》时期就有了湿热病机的观点,但是以湿热论黄疸直到宋及其之后才大量涌现并渐居主流。如《仁斋直指方论》说“湿与热郁蒸于脾,面目肢体为之发黄,此即疸也。疸之名有五……五者虽不同,其为黄则一……湿气胜,则如熏黄而晦;热气胜,则如橘黄而明”[6],即是认为湿热蕴蒸于脾是导致黄疸病的核心病机,并指出湿或热偏盛的不同临床表现。《丹台玉案》说“黄疸之症,皆湿热所成,湿气不能发泄,则郁蒸而生热,热气不能宣畅,则固结而生湿,湿得热而益深,热因湿而愈炽”[7],不但提出了黄疸病由湿热所致的唯一性,还论述了湿与热之间具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杂病广要》引《诸症辨疑》说“凡为之病,或因脾胃受伤,而中焦清气落陷,故使浊气浑然,以致湿热滋蔓,或饥中饮酒……湿热游于经络……身体面目俱黄”[8],不但提出了导致湿热的诸多病因,还着重论述了脾胃受伤,湿浊内生而为湿热这一重要病机。概而言之,可将从湿热病机论治黄疸的观点概括为:中焦虚损,脾气不运,湿浊内生,郁而化热,湿热蕴蒸脾胃。
2 瘀、热、湿病理因素辨析
2.1 瘀在血分是发黄的关键要素
瘀,是指血脉不利的病理状态,《说文解字》说“瘀,积血也”[9],见瘀则说明病在血分,如《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注解“脾色必黄,瘀热以行”提出“一瘀字便见黄皆发于血分,凡气分之热不得称瘀”[5]。病在血分成瘀是发黄的关键。首先,无论有无热与湿,只要病伤及血分成瘀就会发黄。《伤寒论》中所述的“伤寒瘀热在里,身必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10]80,是指由于热陷血分,血脉瘀滞导致的发黄。而《景岳全书·黄疸》所说的“阴黄证则全非湿热,总由气血之败,盖气不生血所以血败,血不华色,所以色败”[11],则非湿热引起,而是由血气败亡,气机不运,血行滞涩所致的发黄。其次,从黄疸病用药来看,治黄的常用药物也多有逐瘀的作用。如《长沙药解》载茵陈有“消瘀热而退黄疸”[12]之功。《药性论》载赤小豆有“散恶血”[13]之用。治黄名方茵陈蒿汤中的大黄,不取后下通腑而是与他药同煎,更是取其通瘀之功。最后,从现代医学来看,黄疸发生时,肝脏所出现的微循环障碍、血液黏稠度增高等病理改变,是影响胆红素代谢,导致黄疸的重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为瘀血在黄疸病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佐证。
2.2 邪热内陷是发黄的重要原因
在黄疸病的发病过程中,邪热是重要病因,邪热内陷伤于血分是黄疸病最常见的病机。邪热可由外直接感受,也可由非温热类邪气所化或由内所生。外感邪热疫疠者,多可直接入血分而发黄。《千金翼方》说“凡遇时行热病,多必内瘀著黄”[14]。且这类黄病多发病急骤,病情危重。《沈氏尊生书》说 “天行疫疠,以致发黄者,俗称瘟黄,杀人最急”[15]。而对于他邪所化或内生之热,邪热则往往需要蓄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黄。《伤寒论》说 “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10]76。风寒入里与正气相争产生化热,若汗出经气不郁,邪热发越则不会导致黄疸;但若感受湿邪,小便不利,周身经脉郁滞无汗,里热不得泻越,蓄积到一定程度,便会内陷入血分而导致发黄。《外台秘要》说“脾胃有热,谷气郁蒸,因为热毒所加,故卒然发黄”[16]。脾胃郁热蓄积过程较慢尚不能直接发黄,而当外感热毒时,在外来邪热的加持下,两热相加,才猝然发黄。邪热并不是导致发黄的基础性因素,没有邪热,脾脏败亡同样会导致血分瘀滞而发黄,但从临床黄疸病多伴有发热、烦渴等症状的现实,以及古今众多医家对黄疸病热象的描述来看,邪热无疑是导致发黄常见且重要的因素。
2.3 湿阻气分是发黄的常见诱因
湿,《说文解字》说“湿,幽湿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土而有水,故湿也”[9]1042。从字义上来说,湿是强调水入土中的弥漫状态。而这一概念引入中医学中则指津液弥漫全身的浸渍状态,是为内湿;易于引起这一状态的邪气,则为外湿。湿由津液所化,与水同类,故患湿病者病在气分。湿性黏腻,具有易于郁滞气机的特性。对于黄疸病而言,湿是黄疸病发病过程中最常见的因素之一。《伤寒杂病论》论黄疸的发病时,仲景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小便不利的症状。如《金匮要略》说“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17]59。《医宗金鉴》注解说“小便不利,湿郁也”[18]。仲景更有“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17]8之语。仲景所处的汉代多寒湿,故常人感受湿邪有小便不利的症状较为常见。看似湿邪在黄疸病的发病过程中不可或缺,但实质上其仅为引起发黄的常见诱因。《华佗神方》说“诸黄病者,谓一身尽疼,发热面色洞黄。此由寒湿在表,则热蓄于脾胃,腠理不开,瘀热与宿谷相搏,郁蒸不得消,则大小便不通,故身体面目皆变黄色”[19]。由此可知,外感湿邪闭郁气机,阻塞了邪热发越的通路,从而导致其内陷发黄,在这里湿仅仅是诱发因素,而非病机关键。正因如此,虽然感受湿邪,小便不利发黄常见,但是小便自利仍可发黄。如《金匮要略》所说的“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17]61即是明证。值得一提的是,在黄疸病的发病过程中,热伤血分,血不利则为水,也会有继发的水湿产生,即内湿。内湿郁滞气机,也会加重郁热使邪热入血。内外湿相比,外湿尚属黄疸病的可能诱因之一,而内湿仅为继发的次要病机。因此陈士铎便有了“盖黄疸外感之湿易治,内伤之湿难医,外感单治湿而疸随愈,内伤单治湿而疸难痊”[20]的慨叹。
3 “瘀热”与“湿热”再审视
3.1 瘀热病机再审视
瘀热是指血分有热、血行不利的病理状态。黄疸病瘀热病机的产生可由邪热入血分伤血所致,此时热是病因,而瘀是由邪热所致的病理产物。如《诸病源候论》说“发汗不解,温毒气瘀结在胃,小便为之不利,故变成黄,身如橘色”[4]257。瘀血由温热之毒入血、伤血所致。也可先血分瘀滞,血行不畅,郁热化热而成瘀热。《诸病源候论》说 “凡诸疸病,皆由饮食过度,醉酒劳伤,脾胃有瘀热所致”[4]297。瘀热并非外来邪热伤血而生,而是血分瘀滞而生热。值得一提的是,瘀热虽在血分,但关键病位并不在一身血脉之血分,而在脾脏之血分。若瘀热在肌肤之血分,当以斑疹、瘀块,且常见刺痛、入夜加重等为主证。若在肺脏之血分,则当以咳血、衄血等为主证。但是,黄疸病以身目发黄以及食差、乏力、腹胀、便溏等为主证,这说明病位在脾。因病在脾脏血分,故脾色外现为黄,由血及气,脾气不运,故会出现食少、腹胀诸症。正如仲景“脾色必黄,瘀热以行”之语。现代医学认为,黄疸病的病位在肝胆,而张启明通过对中西医脏腑的对比发现,西医的肝胆实质上归属于中医脾脏系统,这更证明了黄疸病病位在脾的合理性[21]。病在脾脏血分成瘀为黄疸病发生的关键,而脾脏之瘀多由邪热所引起,因此瘀热为黄疸病发生的主要病机。
3.2 湿热病机再审视
湿热,是指湿漫热郁的一种病理状态。黄疸病湿热病机的产生,可由多种原因所致。《诸病源候论》说“湿疸病者,脾胃有热,与湿气相搏,故病苦身体疼,面目黄,小便不利,此为湿疸”[4]295,即描述的是患者素有内热,又外感湿邪所致的湿热病机。而《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所说的“四之气,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疸而为胕肿”[3]163,则为在暑天直接感受湿热之邪所致。此外,患者外感湿邪,湿郁气机化热;或内生湿浊,气机不利生热;或感受邪热,邪热蒸腾津液生湿等,皆可导致黄疸病湿热病机的产生。因湿郁滞气机的特性容易导致热的产生,而热无出路易陷血分而发黄,因此黄疸病常兼见湿热病机。需要审视的是,虽然湿热病机多见,但它并不是导致发黄的关键病机。如前所述,只有当热入血分伤血成瘀的时候才会发黄,湿仅仅是常见的加重邪热入血的诱发因素。湿因其由人体正常津液所化,与血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故不能入血发黄。持湿热致黄说的医家多认为,湿与热蒸腾于脾是导致黄疸的关键病机,如《丹溪手镜》说“发黄,由湿热相交也,主在脾经”[22]264。但蒸腾便意味着病仅在脾脏气分而不在血分,不在血分便不能发黄。如李艳青通过总结发现,临床上有许多湿热病以中焦为中心,有湿热蒸腾的症状表现,但并不会引起黄疸[23]。由此可见,单纯的湿热蒸腾并不会引起黄疸,只有热入脾脏血分,伤血成瘀时才会发黄。
4 从瘀热到湿热的思考
4.1 黄疸病的辨病与辨证
在查阅古籍时,笔者发现,宋以前中医学多从瘀热来论治黄疸,而宋以后,湿热蕴蒸致疸说则日渐成为主流。仔细分析,关于黄疸病认识的转变,其实反映了中医学从以辨病为主到以辨证为主论治疾病的历史转向。辨病论治就是诊断疾病、寻找病因、分析病机治疗的诊疗方式。就黄疸病而言,宋以前医家多注重对黄疸病病因的探求,并在病因的基础上划分黄疸病的类别,如仲景就将黄疸病分为脾风黄疸、酒疸、谷疸等五种。在进行鉴别诊断后,分病论治,在辨病论治的基础上,分清病机层次,归纳出黄疸病病在血分、瘀热以行的核心病机。宋代开始,虽然对病因的探求并未间断,但是对于疾病认识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对疾病的整体规律转向对疾病阶段性证候的认识,即辨证论治。以黄疸病为例,由于黄疸病多由邪热所致,起病阶段,邪热蒸腾人体津液成湿,故常见湿热蕴蒸之烦热、舌红、苔黄厚等症。医家审证求因,见到湿热蒸腾的证候,认为湿热是黄疸病发生的主要病机。如《丹溪心法》说“疸不用分其五,同是湿热,如盦曲相似”[22]138,将黄疸病统归由湿热一种因素所致。但对于黄疸病整体的发展规律而言,湿热蕴蒸并不是唯一证候,因此后世医家多有批判。张景岳说“丹溪曰:疸不必分五种,同是湿热,如盦曲相似。岂果皆如盦曲,悉可谓之湿热耶,弗足凭也”[11],又根据证候表现,提出了其阴阳黄的理论。《景岳全书》说“黄疸大法,古有五疸之辨……虽其名目如此,然总不出阴阳二证,大多阳证多实,阴证多虚,虚实弗失,得其要矣”[11]。张景岳虽然突破了朱丹溪“同是湿热”的束缚,但其所提出的阴阳黄理论仍是根据黄疸病发病过程中实或虚的证候总结得出,从这一点来看,与湿热说并未有本质区别。
4.2 黄疸病与五行理论
黄疸病病机从瘀热到湿热论治的转变,除了与中医学主体治疗思路的转变有关外,还与宋元时期理学兴起所带来的医学论理之风有关,与黄疸病息息相关的是五行理论对中医学的进一步渗透。宋以前的中医学多以经验总结为主,论理的著作相对较少。但随着理学的发展,宋代谈事物之理之风日盛,影响到医学上便表现为出现了一大批论医学之理的著作,如张从正的“攻邪论”、刘完素的“火热论”等等。论理便需要说理的工具,于是作为工具的阴阳、五行乃至儒家的伦理观念等在论述医学之理的同时,更深入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早在《黄帝内经》时期,古人便用五行归类的方式将脾、湿、黄这几个要素连在一起。《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 “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3]11。受此影响,汉唐的古籍中虽未有黄疸病之黄与湿、脾关系的系统论述,但依然可见五行论对其散在的影响。而到宋元时期,五行论在黄疸病的论理中甚嚣尘上。《伤寒明理论》说“大抵黄家属太阴,太阴者脾之经也,脾者土,黄为土色,脾经为湿热蒸之,则色见于外,必发身黄”[24]。黄、脾、湿以及让土色外现的热,这几个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五行学说对黄疸病理论的影响体现在与黄相对应的湿的地位抬升,湿热论兴起,而血分、瘀热则逐渐远离了主流的黄疸理论。
4.3 黄疸病与肝胆
黄疸病的病机由古代到近代经历了从瘀热到湿热的转变,而现代关于黄疸病的病机,又与宋以后的说法不尽相同。当今医家普遍认为,湿热阻遏脾胃,蕴蒸肝胆,疏泄失常,胆汁外溢为发黄的主要病机。两相比较,湿热蕴蒸的部位在原来脾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肝胆,肝胆湿热被纳入核心病机之中。张启明统计了两万余例宋至近代医家的相关医案,发现肝胆湿热这一证型主要为近代医家所诊断,从而对肝胆湿热导致黄疸提出了质疑,认为肝胆湿热致黄疸是西医理论引入中国后,理论错构的产物[25]。事实上,湿热蕴蒸肝胆致黄,确属受西医影响的产物。成书于近代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说“谓脾受湿热,西说谓胆汁滥行,究之二说原可沟通也” ,又说“此乃肝中先有蕴热,又为外感所束,其热益甚,致胆管肿胀,不能输其胆汁于小肠,而溢于血中随血运遍周身,是以周身无处不黄”[26]。张锡纯所论述之肝胆当然为西医的肝胆,但当今医家将西医之肝胆引入中医对黄疸病机的解释中,与中医之脾胃并称,是否会引起对中西医脏腑的混淆,值得我们深思。
5 结语
综上所述,黄疸病的主要病机为瘀热,而湿热仅为常见的次要病机。中医学论治黄疸病经历了从瘀热到以湿热病机为主的转变,反映了从辨病到以辨证论治为主的历史转向和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将中医辨病与辨证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对待中医中的文化成分,如何正确地参考现代医学的知识、为我所用,能否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关系着中医未来的走向,更关系着中医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