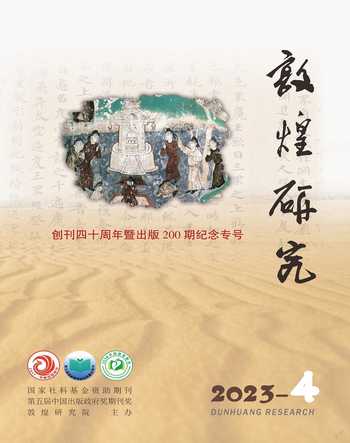敦煌弥勒经变图中戒坛与戒场
湛如



内容摘要:在广律、戒本的记载中,诸部派有关戒场与戒坛的记载有不明之处,因此唐代道宣所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对出家受戒仪轨以及戒坛的形式做出了补充且明确规定。通过对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弥勒经变中戒场受戒实际情况的考察,如莫高窟第445窟的半圆形帷幕剃度受戒场景,认为戒场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几近消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二是官方法律对僧尼受戒的严格管控。
关键词:戒场;戒坛;道宣;敦煌;弥勒经变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4-0126-10
The Ordination Platforms and Ordination Settings in
Maitreya Sutra Illustrations
ZHAN R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Among the Buddhist canons of precepts, the records taken down by different schools of Buddhism regarding the settings and platforms suitable for ordination are either unclear or inconsistent. Therefore, the text Sifenlü Shanfan Buque Xingshichao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A Revision of the Vinaya in Four Parts Created through Simplifica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written by the Tang dynasty monk Dao Xuan provides a highly pertinent supplement to these regulati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ctual practices and places by which monks were ordained by examining depictions of these ceremonies in the Maitreya sutra illustrations in both the Mogao Grottoes and the Yulin Grottoes; the painting of being ordained behind a semicircular curtain in Mogao cave 445, for example. The results point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that can explain the changes in ordination ceremony practices begin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irst is that the famous monk Dao Xuan began widely recommending the use of ordination platforms; the second is the strict control of the ordination of monks and nuns through official laws.
Keywords:ordination setting; ordination platform; Dao Xuan; Dunhuang; Maitreya Sutra illustr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引 言
佛教作为一种异域的宗教,自从进入中土之后就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适应与本土化过程。在此进程之中除了佛教的语言与经典、佛教教义与思想之外,佛教制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层面。这其中既包括比如佛教寺院制度、宗派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在地化,在佛教僧团内部的规章制度上,也呈现出一个缓慢但坚定的演化过程。本文通过以圖证史的方式,来试图从佛教制度的一个侧面,即佛教僧人受戒仪式发生的场所——戒场到戒坛的转变,来探讨在中国中古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期之中佛教教团内部所产生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既反映了印度本土宗教元素所具有的强劲生命力与影响力,同时也看到,在中土背景之下的政治、文化要素对印度原始宗教元素的不断侵蚀,并最终让中国佛教以一种全新形式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转变。
自曹魏嘉平二年(250),昙摩迦罗(Dharmakāla,活跃于222—250年间)翻译出《僧祇戒心》并为中国僧人受戒后,一部分中国僧人便开始追求戒律的正统性,以获得“如法如律”的宗教生活。法显(342—423)西行开启了向印度求取律典的篇章,到唐代这种热情仍在持续,义净(635—713)在前往印度求取广律的同时,还写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当时前往西域求法高僧的盛况{1}。在这些高僧前往印度以自己的亲身见闻,为唐代的受戒仪轨带来印度样本的同时,唐朝本土的高僧则开始通过对经文律典的钻研,试图复原出佛陀在世时受戒的仪轨。道宣(596—667)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文献的钻研,绘制出了他想象中祇园精舍的样式,以及戒坛的样式和受戒仪轨{2}。中国的受戒仪轨在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众多形态,但是随着时代变迁,道宣学说成为了中国律学的主流观点{3},其他受戒仪轨渐渐悄然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印度文明流向中土时在此留下痕迹,中华文明西出阳关时也在此打下印记。从这个角度而言,敦煌现存的资料是还原唐代受戒仪轨的最佳切入点,因此本文以敦煌壁画中弥勒经变中所描绘的受戒场景为基础,对唐代的受戒场所进行探讨。
弥勒经变是指以《弥勒下生经》的内容进行绘画创作的敦煌壁画,其中含有大量的受戒场景。壁画所描绘的众多场景中,受戒场所包含有两种状态:一是在地面为僧人受戒而建造的方形坛,即有戒坛的受戒(以下简称为戒坛受戒);二是在平地上用布围起来的场所,即无戒坛的受戒(以下简称为戒场受戒)。而戒坛、戒场的称呼,可追溯到《四
弥勒经变虽然是从经典演变而成的壁画,但是关于其中受戒的场景,必不可能是画工凭空想象,而是依据现实才能进行创作构图,因此经变中的场景虽然无法完全和文献对应,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唐代的受戒仪轨。如武德九年(626)至贞观四年(630),道宣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其中第八《受戒缘集篇》对世俗人出家时的条件和相关仪程做过详细描述,其中提及出家时“在于露地香水洒之,周匝七尺四角悬幡”{2},和弥勒经变中的受戒图像无法一一对照,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此,弥勒经变可以作为唐代受戒场所研究的一份可视资料{3}。对此本文从受戒场所这一画面中的细小场景进行探讨,以求反映唐代受戒场所的变化,并对这一变化的原因进行一些推测:戒场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几近消亡{1},根据现有史料推测,应与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以及朝廷对僧人出家受戒的严格把控有关。
笔者关注到在《弥勒下生经》的受戒画面中,受戒场所这一表现形式有所差别,因此本文从下述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弥勒经变中的剃度受戒场景之方形帷幕场所问题,指出该场景象征的应是戒场受戒;二是唐代的受戒情况。本文虽然利用《弥勒下生经》中有关受戒画面的记载,试图厘清唐代的戒场受戒,但因资料缺乏,只能确定唐代存在这一事实,无法详细分析戒场受戒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尽管如此,戒场受戒作为从印度流传至中国的受戒制度,较少受人关注,所以本文试图用有限的资料对这一制度进行探讨。
一 弥勒经变中的剃度受戒场景再探讨
弥勒经变中关于剃度受戒的场景众多,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有莫高窟第445窟(盛唐,图1、2);榆林窟第25窟(中唐,图3、4)、莫高窟第202(中唐,图5)、361窟;莫高窟第138窟(晚唐),莫高窟第61、100窟(五代、宋)。有学者曾以盛唐第445窟,榆林窟第25窟为例,对整个场景构图进行分析[8-10],此处以此为基础展开一些讨论。
首先,第445窟的壁画的出家受戒场景中,在俗者坐在半圆形帷幕中,帷幕有人出家受戒。有学者认为第445窟布局中的半圆形帷幕是与唐代帷幕相类似的物品,作用为杜绝女性出家者被偷窥,而男性场景中同样的帷幕是为了画面布局对称而画上去的,不符合出家受戒的实际场景[10]26-36。这一布局虽然成为盛唐以后弥勒经变的主要形式,但无法将该结论推广到所有弥勒经变,理由有两点:一是第445窟的帷幕为半圆形,除此之外莫高窟第202、361、138、61、100窟,所见众多图像基本为四方形,因此将第445窟的半圆帷幕作用扩展到方形帷幕,似有不妥。二是第445窟帷幕内人物全为在俗者,其他图像中,如第202窟的两个方场有僧有俗和唯僧无俗,分别代表出家和受戒场景,因此简单的将帷幕作用解释为隔绝偷窥,男性出家受戒的帷幕是为了布局对称,则太过牵强。简而言之,第445窟虽然能代表一部分洞窟的壁画场景,但方形帷幕应另有含义。
其次,设置方形帷幕的含义与功用为何?虽然众多弥勒经变中,所见剃度受戒的场景基本一致,即在围三缺一的方场中完成僧俗身份的转换,但在具体表现上仍有差别,其中莫高窟第361、138、61窟,榆林窟第25窟,都只描绘了一个方场,莫高窟第202、100窟则描绘了两个方场。这些画面中,当以第202窟(图5)最能传达方场的具体含义。该画面呈左右对称分布,分别描绘男女出家受戒的场景。以男性为例,在画面靠中间的方场中,站立众多僧俗,众人面前跪一人,此当为剃度场景。稍右侧方场中,有十位僧人,前跪一僧,此当是“三师七证”为僧人传授具足戒。受戒过程中,对求戒者的安置是方形帷幕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围三缺一的作用是为了满足受戒条件中的“眼见耳不闻处”{1},即在律典中明确规定要将求戒者安置在眼睛能看见戒坛受戒情形,耳朵听不见受戒羯磨法的地方。当然,若是在宽敞的场所中,连围三缺一的帷幕也不必要。这应当是某些弥勒经变中不画帷幕的原因。
二 唐代的受戒
敦煌做为中印文明的交接点,壁画的画面极可能同时含有中国和印度两种元素。因此在探讨壁画中的受戒场景时,不仅仅要关注本土的高僧著作,还需要关注戒律原典以及求法高僧的见闻记录。通过图像与文本的对照,可以发现,弥勒经变中所画的帷幕是戒场受戒,接下来对戒场进行探讨。
戒場是受戒场所的简称,在律典中有具体的设立仪轨。在以往的研究中{2},并未有人注意到戒场受戒,而是将戒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现有文献较少,难以知晓戒场受戒的具体操作流程,只能从弥勒经变的场景予以推测。笔者以为在平地上设立用帷幕建成的“围三缺一”的方形场所,是唐代戒场受戒的实际状况。
(一)戒场的具体状况
现存的唐代律师文献中,关于戒场受戒的记载较少,此处以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为主,辅以唐代其他律师的相关记载,利用这些戒场的相关文献,从戒场的定义、戒场的设立两个部分进行探讨,试图将戒场的具体情况复原。
受戒是成为正式僧人必经步骤,所以唐代律师在众多文献中都描述了戒场受戒。从律典的记载来看,受戒最主要的条件是“白四羯磨”(四次表白询问),即在僧团中将要举行受戒之事禀告,而后进行三次询问,若无反对者,则受戒成立{1}。为了让“白四羯磨”不被僧团外的沙弥和在俗者窃听,因此需要结戒场,规定受戒场所范围,除仪轨相关人员外他人不得进入该范围。戒场结法的相关文献较多,五分律师爱同(生卒年不明)在他的《弥沙塞羯磨本》中,详细地将结戒场到解戒场的作法列出[11]。四分律师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同样对戒场的设立有所说明[12]。此外,怀素(624?—697?){2}、定宾(生卒年不明)等律师都对戒场有不同程度的记载{3}。这些文献的存在说明唐代戒场受戒广泛存在于各个律学流派中。
虽然众多文献中都有戒场的记载,但是真正对戒场做出具体定义的是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是道宣对自己在净业寺设立戒坛的经过以及戒坛样式的记载。在文中,道宣对“戒坛”和“戒场”进行了说明:戒场是在平地上的场所{4}。而道宣之后,义净在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及他在印度所见的受戒方式,除了小坛(戒坛)外,大界(一般指寺院范围)或自然界(一般指某个自然场所范围)内受戒也可以得戒{5}。其中大界和自然界就包含了戒场受戒。此外,《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中说,若是受戒过程中下雨,可以将戒场解除移到屋根(屋檐)下{1}。综合这些记载,戒场受戒是在平地上举行的受戒仪式。
设置在平地上的戒场也并非毫无范围,在律典中有明確的结界规定。在受戒的准备过程中,最重要的前提准备工作就是结界,即规定戒场的范围。在律典中戒场的结界方法是先结戒场界,再结大界{2}。结界的过程十分繁琐,此处简单总结为先派遣四位僧人站定四个角落,高声说明戒场的具体范围的四个角落,而后以石块、木头等物标记范围{3}。除了人为划定范围外,以醒目的场所区分标记为界的自然界也是设立戒场的常用手段。在道宣的记载中,自然界有四种,即聚落(村落)、兰若(寺院)、道行(行走范围)、水界{4}。这种自然界中,在船上(水界)进行的传戒仪式就是一个极具有代表性的例子{5}。
现有资料中,未能见到戒场受戒的具体记载{6},但不论是道宣还是义净,或其他律师的记载中都承认不需要戒坛的戒场受戒,因此尽管资料缺乏,唐代存在戒场的受戒形式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二)唐代的戒场受戒衰退原因推测
戒场受戒之所以淹没在历史中无人知晓的具体原因不明,可以推测的原因之一是,随着四分律宗的兴盛,戒坛在寺院中渐渐增多,而国家对度僧资格的严格把控,导致受戒场所集中在有限的戒坛内,戒场受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道宣以前戒场和戒坛并存于世,而后关于戒场受戒少见于文献记载,可以推测随着四分律宗的兴盛,以及对戒坛的推崇是戒场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敦煌戒坛,土桥秀高、姜伯勤都曾做过深入研究{7},近年大谷由香以东大寺的现存戒坛为基础,结合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的记载,对唐代的戒坛样式进行探讨[13]。故而此处不再探讨戒坛的样式,而以《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为基础探讨道宣对戒坛受戒的推崇。《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道宣对戒坛和戒场的主要讨论集中在《戒坛立名显号第二》,文长烦引,略说如下:首先,道宣提出“坛”和“场”二者并不一致,中国人混淆了其中含义{1}。其次,道宣引用《别传》中迦叶对阿难的诘问证明“坛”才是受戒的场所,并对戒坛进行说明{2}。最后,道宣总结戒坛之名始于佛世,后因文本过多而混乱,因此他遵阿难所说而立戒坛{3}。此外,《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还记载了中印度大菩提寺释迦蜜多罗见到道宣所造戒坛,认为其符合印度戒坛的形制{4}。从道宣的这些说明来看,虽然其没有否定戒场受戒,但是他更推崇戒坛受戒,认为这才是从佛世传承下来的正统。中唐后,四分律学为正统通行天下[14],道宣被推为南山律祖,因他对律学的深远影响,其所推崇的戒坛受戒应是戒场受戒衰弱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社会角度而言,随着李唐王朝佛教制度的完善,度僧作为统治佛教的一个重要手段被朝廷掌控,这是戒场受戒衰退的另一个原因。从唐初开始,朝廷对僧团治理的法规在不断加强{5},剃度受戒则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一方面,僧人出家受戒需要有度牒,度牒是由朝廷颁发并定期核查,记载了僧人的籍贯、身份、出家年龄、背诵经典、剃度受戒时间等一系列详细信息的文牒[15-16];另一方面,朝廷又规定了剃度受戒的地点,凡未曾得到允许而私自剃度受戒的僧人被视为违法的私度{6}。对于受戒地点的要求,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载大和二年(828),全国只有两所戒坛能举行受戒仪式{7}。虽然圆仁的资料较晚,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对受戒地点有严格的规定。简而言之,朝廷为了统治僧团,对受戒的戒坛进行严格规定并定期核查度牒,因此推测相较于能够简单的在平地上结界举行的戒场,有实体建筑物的戒坛则更容易为朝廷掌控。当然,法律的规定与实际操作有所区别,特别是唐后期中央政权逐渐丧失对藩镇的控制后,由藩镇私自举行的剃度受戒屡见不鲜{8},这也可能是敦煌壁画中不断出现戒场受戒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因文献不足,戒场衰退的原因难以完全清楚。此处试图从佛教内部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以及佛教外部朝廷对佛教掌控的事实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产生,但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将来更深入的挖掘。
三 结 语
佛教从最初的东来传道发展到西行求法,这本身也是一个宗教向域外传递,并且最终实现形式转换的绝佳案例。佛教传入中国,并最终与中土文化融合无间,这中间所经历的漫长演变过程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同时也对当前宗教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从佛教制度层面来看印度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也是研究此一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虽然历史上不断的有人将印度仪轨传入中土,但中土高僧,不会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外来的制度性规范,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不断的调整各种制度。而受戒作为佛教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得到众多高僧的瞩目。在受戒过程之中,为了确保隐私性而确立的戒场与戒坛设立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历史资料的发掘,可以发现早期印度僧侣的受戒仪轨主要是在戒坛以及自然界中所设立的戒场之中实行,在此期间戒坛至少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最近的一个千年之中,中国僧侣的受戒地点则主要是以戒坛为主。这其中转换的关键阶段就在于中国唐宋变革的这一时期内。不仅唐宋整个社会出现了全面转向,即使是在佛教方面也有了诸多前所未有,并且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的转变。而从戒场与戒坛并行,再到戒坛独盛,则是其中的一个过去不为学界所注意的侧面。这一转换过程漫长而细微,现有文献材料无法将其一一呈现。在此,笔者另辟蹊径,通过敦煌这个华戎交汇与中印文化汇聚之地,以图证史的方式,以敦煌石窟弥勒经变所反映的中古受戒实景逆推还原这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的一面。因此,本文的研究,就不仅对于研究佛教制度史有所发明,或者也可为今后拓展历史研究之中的图像史料有所贡献。
在拙文中,通过对弥勒经变中的方形帷幕含义与作用进行再探讨,可得出至少如下初步的结论:
第一,笔者对莫高窟第445窟以外,壁画所见的方形帷幕作出解释。“围三缺一”的方形帷幕,是为了能让后面的求戒者既能看见前一个受戒者的受戒仪轨,又不至于听见“三师七证”传授时的羯磨法。此外,对榆林窟第25窟中的剃度受戒无戒坛的情况可能是表示戒场受戒,而并非不符合戒律的规定{1}。
第二,以往的研究中未曾注意到戒场受戒,笔者通过唐代众多律师的记载指出,在唐代存在通过在平地上结界即可舉行受戒仪式的戒场。而之后戒场逐渐消失,其原因可能是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以及封建王朝对于僧团各项制度性限制所导致。从后者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即佛教内部的制度性转换,往往要受制于政、教势力在更宽广背景下的互动。中国佛教的在地化,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推手,还是来自政治权威的不停顿的压力。它会持续直接地推动中国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即使是在看似细微之处,也往往会潜藏着来自王权的暗力。
以图证史,为文献之不足征者。虽然如此,但传世文献之不足,依然还是一个莫大的缺憾。因此,本文虽然通过图像资料,来恢复中古佛教制度上的一个侧面,但不过即是抛砖引玉。对具体的受戒细节以及其他具体情况,则仍有待来贤。
参考文献:
[1]平川彰.戒壇の原意[J].印度学佛敎学硏究(20),1962:276-296.
[2]McRae John R. Daoxuans Vision of Jetavana:The Ordination Platform Mov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G]//William Bodiford. Going Forth:Visions of Buddhist Vinay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68-100.
[3]Thomas Newhall. The Development of Ordination Platforms (jietan 戒壇) in China: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īm?觀 in East Asia from the Third to Seventh Centuries[G]//Jason A,Carbine,Erik W Davis. Simas:Foundations of Buddhist Relig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22.
[4]佛陀耶舍,竺念佛.四分律:卷35[G]//大正藏:第22册.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8:819c.
[5]僧伽跋陀罗.善见律毘婆沙:卷2[G]//大正藏:第24册.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8:682a.
[6]定宝.四分律疏饰宗义记:卷8[G]//续藏经:第42册,京都:藏经院,1912:248a.
[7]比丘尼传:卷1:晋竹林寺净捡尼传[G]//大正藏:第50册.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8:934c.
[8]沙武田,李玭玭. 敦煌石窟弥勒经变剃度图所见出家仪式复原研究[J]. 中国美术研究,2018(1):26-36.
[9]郝春文.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19.
[10]石小英. 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5-57.
[11]爱同. 弥沙塞羯磨本[G]//大正藏:第22册. 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8:214c-215a.
[12]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1[G]//大正藏:第40册. 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7:16a-c.
[13]大谷由香. 大寺戒壇院の塔[G]//東栄原永遠男,佐藤信,吉川真司. 東大寺の思想と文化(東大寺の新研究3). 東京:法蔵館,2018:112-115.
[14]王建光. 中国律宗通史[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89-193.
[15]孟宪实. 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J]. 文物,2007(2):50-54.
[16]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M]. 龚泽铣,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4:19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