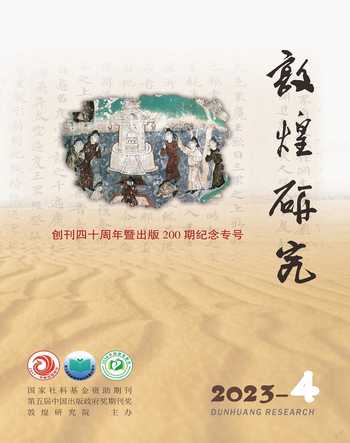敦煌学与故宫学
内容摘要:对敦煌学与故宫学进行比较与思考,重点从敦煌学与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内涵之比较、学术历程回顾、前景展望及设想等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敦煌学与故宫学皆是高度综合性的学问,以大型建筑群作为承载空间,研究对象中均有数量巨大的艺术品、文物及独树一帜的文献。二者的研究历程都肇始于20世纪初国宝文物、文献的流散以及外国学者的抢先研究,激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奋起直追的意愿;经过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努力,建立起中国学界自己的研究队伍,并最终成立了专门研究和保护敦煌石窟与故宫的学术机构,遂将敦煌学与故宫学的研究一直引领至今。展望敦煌学与故宫学前景,故宫是中華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故而应当从中国文化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和发展敦煌学与故宫学。此外,还应加强基础研究与综合研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普及。
关键词:敦煌学;故宫学;比较;中国文化;中外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4-0012-12
Dunhuang Studies and Gugong Studies
—Comparison,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WANG Xudong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Abstract: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omparative review and historical retrospect on Dunhuang studies and Gugong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of these two fields: comparison of their research objects and academic findings, review of their academic histories,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oposals for the advancement. Both Dunhuang studies and Gugong studies are highly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s concerned with huge, extremely complicated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s that contain a large amount of artworks, cultural relics and unique documents. The academic histories of both fields began at a moment when precious national treasures and documents were being dispersed abroad, and when foreign schol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had already begun advanced study of these objects. Both sets of circumstances stimulated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aspiration to conduct academic study along their own lines of thought. After pushing through decades of hardship, Chinese academia established itself, along with various academic institutions specialized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Dunhuang Caves and the Imperial Pala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se institutions and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can now be recognized as inaugur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Gugong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future of these disciplines, it is the belief of the author that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Palace Museum bears witness to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unhuang is a central lo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Finally,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basic, m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effort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while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public popularization still require greater development.
Keywords:Dunhuang studies; Gugong studies; comparison; Chinese culture;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今年是《敦煌研究》创刊40周年,上距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已123年,而距离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敦煌学”的概念{1}也已过去93载。迄今为止,经海内外一代又一代学者前赴后继的不断努力,敦煌学已取得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且从陈寅恪先生口中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发展为今日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
2003年郑欣淼先生首次提出“故宫学”的概念,至今正好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故宫学在故宫博物院以及中外学者的共同推动与探索之下,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尽管故宫学概念的形成比敦煌学要晚七十多年,然而与故宫学相关之研究(如故宫古建筑及各类馆藏文物、文献研究)的学术历程则十分久远。
本文拟对敦煌学与故宫学进行一番比较与思考,重点从二者的研究对象、内涵之比较、学术历程回顾、前景展望及设想等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并着重强调应当从中国文化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和发展敦煌学与故宫学。
一 敦煌学与故宫学的研究对象
1.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著名的“敦煌文书”,即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2},数量约5万件,内容异常丰富,分藏于英、法、日、俄、中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机构或私人藏家手中。对敦煌文书的研究,是敦煌学得以建立的起因,也是狭义上的敦煌学研究的内容。敦煌文书中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文献从公元406年至1002年,时间跨度近600年[1]。其内容更是包罗万象:除作为主体的佛教经典之外,还包括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的经典,还有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的典籍(以上多为写本或曰卷子的形态);另外还有官私文书、俗文学作品(如曲子词、变文、小说)等;汉文文献之外,还包括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巴利文、西夏文、龟兹文、突厥文乃至叙利亚文等所谓“胡语文献”。此外尚有拓本、刻本、星图、云图、信封、经帙等。藏经洞还出土了一批艺术品,如木版画、纸画、绢画、麻布画、丝织品、剪纸等。广义的敦煌文献研究,往往还外延至敦煌汉简以及吐鲁番、和田、库车、黑城等地出土的文献。
二是敦煌石窟本身,主要指莫高窟,广义上还包括敦煌的西千佛洞,瓜州(原安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以及肃北的五个庙石窟。敦煌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彩塑的洞窟共492个,内有彩塑2400余身,壁畫约45000平方米,主要分为北朝、隋、唐、五代、宋初、西夏、元等几个发展阶段。此外,榆林窟存41个洞窟,西千佛洞存16个洞窟,东千佛洞存23个洞窟,五个庙石窟存4个洞窟。敦煌石窟包括洞窟及窟檐建筑、窟内彩塑与壁画(包含文字题记),此外还有窟外一些附属文物等。对敦煌石窟的研究与保护是敦煌学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除上述两部分主要内容之外,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史(包括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也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学者认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除敦煌文书和石窟之外,还包括敦煌学理论、敦煌史地等[2],更广义的看法则认为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古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学问{1}。
2. 故宫学的研究对象
故宫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含三大部分:一是故宫古建筑群,二是故宫博物院的各类馆藏文物(包括文献),三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故宫学将以上三者视作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郑欣淼先生曾在《故宫学述略》一文中,将以上三大部分内容细分为六个方面:1. 紫禁城宫殿建筑群;2. 文物典藏;3. 宫廷历史文化遗存;4. 明清档案;5. 清宫典籍;6. 故宫博物院的历史[3]。其中第2—5条是对第二大部分即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包括文献)的细分和具体化。章宏伟先生在《作为学问的故宫学》一书中则指出故宫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故宫建筑学、故宫文物学、故宫文献学、故宫历史学和故宫博物馆学五个主要方面”[4],与上述研究对象基本对应。
故宫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拥有近千座明、清木结构建筑,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文化的集大成者。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称赞故宫“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5]。
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包括文献)逾180万件(套)。郑欣淼先生称:“其文物品类,一应倶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 金银器皿以及其它历史文物等等,可以说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3]王素先生在《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中将馆藏文物分为五大类、十八小类:一、书画(包括法书、绘画、碑帖);二、器物(包括石刻、雕塑、铜器);三、宫廷文物(包括织绣、漆器、文具、家具);四、工艺文物(包括陶瓷、玉器、珐琅器、金银器);五、其他文物(包括宗教文物、外国文物、钟表仪器、杂类文物){2}。故宫博物院藏有古籍文献37万册。此外,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故宫西华门内)的原故宫内阁大库档案(约800万件),也是故宫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之外,完整意义上的故宫文物,还应包括台北故宫的馆藏文物(约68万件/套),以及流散于国内外各处的清宫旧藏文物(包括圆明园旧藏):国内如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等处的相关藏品;国外如大英博物馆、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等处的相关藏品;此外还有大量中外私人的收藏——两岸故宫以及流散各地的清宫旧藏文物,皆应作为故宫学研究的内容。
故宫博物院,既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典型产物,也是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见证。对故宫博物院院史的研究,也是故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
二 敦煌学与故宫学内涵之比较
从上述敦煌学与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已可看出,二者均是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学问,皆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以下从四个具体方面对敦煌学与故宫学的内涵进行比较与分析。
1. 高度综合性的学问
由于研究对象的丰富性,敦煌学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李正宇的《敦煌学导论》一书列出敦煌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史地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代科学技术、文物保护科学以及“敦煌学学”[6]138。刘进宝在《敦煌学通论》中也指出敦煌学所涉及范围极广,“大凡中古时代的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科技、经济、建筑、民族关系、中西交通等各门学科,都可以利用敦煌学资料”[2]3。根据现有研究粗略统计,敦煌学所涉及的主要学科至少包括历史学、考古学(特别是石窟寺考古)、艺术史(以及艺术学、美学等)、建筑学、文献学、古代经学、宗教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民俗学、医学、科技史、文保科学等。
与敦煌学类似,故宫学也是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学问。郑欣淼先生在《故宫学述略》一文中曾指出“故宫学很显然是综合性学科,在研究中需要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建筑学、文艺学、美学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故宫学“涉及历史、政治、建筑、古器物、档案、图书、艺术、宗教、民俗、科技、博物馆等诸多自成体系的学科”{2}。王素先生在《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中则进一步对故宫学所涉及的12个学科即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宗教学、出版学、民族学、医药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古建筑学、文保科学进行了深入探讨。
由上可知,敦煌学与故宫学不仅都是综合性极强的学问,而且二者所涉及的学科有大量重合,如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艺术史、文献学、宗教学、民族学、医学、文保科学等。
2. 以大型建筑群作为承载空间
敦煌学和故宫学的另一个重要共同点,是二者的研究对象中都包含一组大型建筑群,即敦煌石窟和故宫古建筑群,它们既是研究对象,同时也曾经或者依然是承载其他研究内容的空间“容器”——敦煌文书曾经密封在藏经洞内近千年之久,彩塑与壁画则一直以石窟建筑空间作为依托;故宫的馆藏文物及档案文献在流散之前皆分藏宫中各建筑内。
但敦煌石窟与故宫古建筑群亦有着显著的差异。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寺建筑,以石构洞窟为主(当然也留存有一批木結构窟檐{3}),是通过在崖壁上“开山凿岩”获得空间,可谓一种“负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别具一格[7]。而故宫古建筑群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即由一座座木构建筑通过院落式布局形成组群。当然故宫也有少量砖石结构建筑,典型者如浴德堂;此外,故宫古建筑的台基大量使用石构件,其中最宏大的工程即三大殿台基的栏杆、栏板和御路等。因此,敦煌石窟和故宫古建筑在研究与保护方面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可以互相借鉴。
3. 数量巨大的艺术品及其他文物
敦煌石窟中的彩塑和壁画是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的大宗,毋庸赘言。需要注意的是,敦煌的壁画、彩塑与石窟的建筑空间,构成“三位一体”的整体,三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共同营造出石窟寺特有的宗教氛围。巫鸿先生的近作《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8],即在他此前反复强调的艺术品之“原境”(context)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作为空间整体的莫高窟。因此对莫高窟壁画、彩塑与石窟建筑的研究应该纳入整体视野进行深入探讨。
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种类极其丰富,除了艺术品之外还包含大量其他类型的文物,它们大多属于清宫旧藏,宫廷文物承载着中国古代悠久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作为中国历代文化之载体的性质与故宫古建筑群相同,它们同属于故宫这一“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正如壁画、彩塑与石窟建筑空间共同形成敦煌石窟的“原境”一样,大量宫廷文物与故宫的建筑空间同样构成故宫的“原境”或“原状”(典型者如皇帝宝座与太和殿、皇帝卤簿与太和殿广场、《四库全书》与文渊阁的关系等等),应被视作整体来进行研究。
4. 独树一帜的珍贵文献
敦煌学与故宫学的研究对象中,均包含独树一帜的珍贵文献,即敦煌文书与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二者皆位列近代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中,与殷墟甲骨和居延汉简齐名。与敦煌文书分散收藏在中外诸国的境况类似,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也被分散收藏,主要部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分散藏于国内外一批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1}。
这两种文献性质迥异,前者年代在5—11世纪(十六国时期至元代)之间,且内容庞杂之极,既有佛、儒、道之经典,又有官私文书及俗文学材料,既有汉文文献,又有大量“胡语文献”。内阁大库的档案则以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为主,且主要是宫廷档案,对治明清史、宫廷史意义重大。二者在年代及性质方面,恰呈互补的局面。
故宫文献除了著名的明清档案之外,还有大量宫廷典籍(现存故宫图书馆),后者除了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外,也包括宫廷刻印的佛教《大藏经》,还有尺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等,颇可与敦煌文书比较、对照研究。此外,故宫收藏的出土文献包含甲骨、金石和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其中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则是敦煌学与故宫学共同的研究对象[9]。此外,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的专为清代皇家服务的建筑世家“样式雷”的建筑图档,也是故宫档案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故宫古建筑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价值。
三 敦煌学与故宫学学术历程回顾
每个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其学术史的回顾与整理,特别是像敦煌学和故宫学这样浩瀚博大,由多学科的大批学者进行过长期耕耘的学问,其学术史本身也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的重点之一。
如果对敦煌学和故宫学的研究历程进行一番简要回顾,便会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敦煌学和故宫学(尽管早期尚未形成“故宫学”的清晰概念)进行研究的历史背景,都是20世纪初左右珍贵国宝文物的流失——即陈寅恪先生所言“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后由于外国学者的抢先研究,更激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奋起直追的意愿;经过这些先贤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努力,建立起中国学界自己的研究队伍,并最终成立了专门研究和保护敦煌石窟与故宫的学术机构,遂将敦煌学与故宫学的研究一直引领至今。
1. 敦煌学简要历程
众所周知,敦煌学的诞生缘于1900年6月22日(即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园禄发现藏经洞,以及随之而来的敦煌文书流失海外。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分别于1907、1908 年抵达敦煌,并带走大批珍贵藏经洞文书。1909年伯希和赴京,向北京的学者展示若干藏经洞珍贵文献,以罗振玉为首的一批学者先后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抄录。同年9月25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首次公布了敦煌藏经洞的重大发现,敦煌文书遂引起中国学者高度重视。尽管之后罗振玉提请清学部收集藏经洞剩余文书,得以将部分残卷运回北京并入藏京师图书馆,可是紧接着日本大谷探险队及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又分别于1911—1912年和1914—1915年从敦煌带走大批文书。1923年,面对空空如也的藏经洞,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又将一批精美壁画、彩塑从石窟中揭取、盗走(现藏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对莫高窟造成极大破坏。
以上外国探险家最早开启了对敦煌石窟和文献的研究。1907年,斯坦因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调查摄影,并对南区的18个洞窟编号,做了文字记录和平面测绘。1908年,伯希和对莫高窟大多数洞窟进行编号、记录、摄影,绘制了南区石窟立面图和该区下层洞窟平面图,抄录了部分壁画题榜,后出版《敦煌石窟图录》(六册,1920—1924)。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对莫高窟做进一步调查,增补部分洞窟的编号,逐窟测绘、记录、拍照,抄录部分题榜并摹写部分壁画,在测绘南区单个洞窟平、立面图的基础上,最后拼合出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1924—1925年兰登·华尔纳考察敦煌石窟,对榆林窟第5窟(今编号第25窟)壁画做了专题研究;1925年北京大学陈万里随华尔纳一同调查敦煌石窟,其后来所著《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10]。
彼时的中国学者们奋起直追,投入对敦煌文书多角度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罗振玉、王国维、蒋斧、曹元忠、王仁俊、陈寅恪、陈垣、向达、王重民、姜亮夫、刘半农、郑振铎、刘师培等。至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正式提出“敦煌学”概念,并指出研究目标为“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此亦可谓中国治敦煌学者之共同心声。
与之前中国学者大多从事敦煌文书研究不同,抗战期间,一批学者及艺术家(如张大千、谢稚柳、常书鸿、何正璜、向达、石璋如等)纷纷前往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特别是1942—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先后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两度赴敦煌考察。向达运用传统文献、敦煌文书和实地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完成了《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等4篇系列文章{1},为我国学者敦煌石窟研究的经典之作。石璋如按照张大千编号,对莫高窟逐窟做了文字记录,绘制平、剖面图,拍摄图版照片,后出版《莫高窟形》(三册)。
194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此后,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学人扎根当地,全身心投入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与保护之中,取得丰硕成果。1982—1987年,由夏鼐、常书鸿、宿白、金维诺与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冈崎敬、邓健吾任编委会委员,汇集中日两国多位敦煌石窟研究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册)陆续出版;1999年起,由敦煌研究院组织编写,段文杰任主编、樊锦诗任副主编的《敦煌石窟全集》(共26册)由商务印书馆(香港)陆续出版;2011年,敦煌研究院编,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编著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系多卷本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第1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0年以来,敦煌学在学术界日益成为显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杂志陆续创刊。1983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一系列敦煌学研究的专著及论文纷纷出版与发表,蔚为大观;中外各国收藏敦煌写本的大型图录也陆续出版。此外,1980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敦煌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或海外召开。
2. 故宫学简要历程
2003年10月,鄭欣淼先生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的“博物馆馆长论坛”上正式提出“故宫学”概念。尽管学科概念的正式提出要晚于敦煌学,但故宫学相关研究的肇始则要早得多。
与敦煌类似,对故宫古建筑及文物、文献的研究,也伴随着清宫文物与文献的流散(主要因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八国联军庚子之役以及清逊帝溥仪“小朝廷”的盗运等),以及外国学者对故宫古建筑的实地调查研究。
1901年,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成为首个进入故宫进行调查测绘的建筑史学者,他测绘了故宫的总平面并拍摄大量照片。之后,瑞典学者喜龙仁、德国学者鲍希曼、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与关野贞等,均得以考察故宫古建筑并发表相关图录{1}。
1921年,北洋政府出售大批内阁大库档案(即所谓“八千麻袋事件”),之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后更名“明清史料整理委员会”),陈垣任主席,沈兼士、郑天挺、马衡等学者参与其中,整理幸存档案,此为中国学者整理研究故宫档案之缘起。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馆藏文物和档案的保护、整理与研究遂纳入正轨。陈垣任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又分图书部(专管清宫旧藏图书)和文献部(专管清宫旧藏档案),沈兼士主持文献部(1929年从图书馆分出,改称文献馆,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前身)。1929年博物院创办《故宫周刊》, 连续出版510期,影响深远。为学术研究之需要,193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10个专门委员会,聘请一批知名学者担任委员。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我国学者开始对故宫古建筑及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研究:如朱启钤、陶湘、阚铎、刘敦桢、梁思成等结合故宫所藏“故宫本”“四库本”等古籍校勘北宋《营造法式》,陶湘依据内阁大库档案中发现的《营造法式》宋本残叶刊印陶本《营造法式》[11]; 梁思成结合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与故宫古建筑实例研究清代建筑,撰成《清式营造则例》(1934),为研究故宫古建筑及清代建筑之入门书;朱启钤、阚铎、朱偰、王璧文(璞子)等先后进行元大都宫苑(为明清故宫及西苑三海之前身)之专题研究{2};单士元长期从事明清北京及故宫建筑史研究{3},终成一代大家。从1934年起,受中央研究院委托,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开始有计划地测绘故宫古建筑,可惜此项工作因抗战而中辍,不过仍然留下数以千计的照片、测稿及测绘图,成为故宫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之珍贵史料。此外中国营造学社还参与了故宫角楼、文渊阁,景山五亭等建筑的维修与保护工程或计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与西迁,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写下了保护中华文化珍宝可歌可泣的篇章。而在抗战时期的北平,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委托基泰建筑事务所的张镈建筑师(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系主任时的学生)主持测绘了故宫等北京中轴线重要古建筑群,绘图七百余幅,又是抗战中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桩壮举。这套图纸(分藏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仍是研究故宫古建筑的珍贵一手资料[12]。
建国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学相关研究成果甚丰,古建筑及馆藏文物各领域皆专家辈出,不再一一列举。1979年复刊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创刊的《紫禁城》和1983年建立的紫禁城出版社(后更名“故宫出版社”)成为故宫学术成果重要的发表、出版阵地。1990年以来先后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清代宫廷史研究会” 和“中国紫禁城学会”,进一步拓展了故宫相关研究的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博物院除了主要的研究、保护与管理部门之外,与故宫学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研究机构得以逐步建立:古建筑方面有古建筑研究中心及“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各类馆藏文物方面有古书画、古陶瓷、明清宫廷历史、藏传佛教文物等研究中心及“古陶瓷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等。2005年6月,故宫举办第一次故宫研究、“故宫学”座谈会,此后相关学术研讨会不断延续。2009年正式设立故宫学研究所,将故宫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提升到新的水平。故宫出版社陆续出版“故宫学视野丛书”,包括郑欣淼《故宫学概论》、章宏伟《作为学问的故宫学》、王素《故宫学学科建设研究初探》等。
以上扼要回顾敦煌学与故宫学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学术历程,未涉及国外的研究情况。但由于二者皆以文物、文献流散海外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缘起,因而从发轫之时便具有了国际化的特点。此外,由于学科内涵包罗广大,二者皆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未来发展仍有巨大空间。
四 敦煌学与故宫学前景展望及设想
1. 从中国文化整体的视角研究敦煌学与故宫学
不论是敦煌石窟还是故宫,其古建筑、壁画、彩塑以及各类文物、文献收藏,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整体,而这一文化整体又是更为广大的中国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对敦煌学、故宫学的研究,必须首先从中国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进行探讨{1}——其中敦煌学更加偏重于討论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融合,而故宫学则更聚焦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溯源及其传承、发展等内容。
1.1 故宫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
故宫学研究,应注重从中华文明探源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以“观象授时”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是如何通过都城、宫殿的营建与一系列宫廷制度的确立{2},将那些与文明息息相关的知识与思想加以记录和传承,并最终沉淀在故宫的古代建筑群中,凝聚在故宫收藏的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物、文献之中,使故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
故宫首先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文化的集大成者。对故宫古建筑的研究,理应与中国历代都城、宫殿遗址的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以探索都城、宫殿营建传统的传承、发展与演变。特别要关注与故宫密切相关的明中都宫城遗址、明南京宫城遗址以及沈阳故宫等。此外,故宫自成立考古部以来,已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考古发掘工作,对元大内、明北京故宫等相关遗址均有重要发现。结合历代都城、宫殿考古以及故宫自身的考古工作来研究故宫古建筑,应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故宫古建筑还体现了儒、释、道文化的充分融合。除了主体宫殿建筑群之外,还包含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建筑群,如中正殿、雨花阁、宝华殿、宝相楼、吉云楼、佛日楼、梵华楼等40多处佛堂;道教建筑群,如钦安殿、玄穹宝殿等;此外还有祭祀萨满的坤宁宫,祭祀城隍的城隍庙等,不一而足。各种宗教建筑与宫殿建筑构成完美交融的和谐整体。梁思成先生在其《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提出了“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的理论体系,对于环境思想,他尤其强调了“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对于建筑群平面布局的深刻影响[5]7-15。今后对故宫古建筑的研究,更要从文化层面着眼,探索上述环境思想因素对故宫古建筑群以及宫廷制度的影响。
故宫所藏各类文物(如玉器、青铜器、陶瓷、书画等),皆为中国历朝历代物质与精神文化之精髓,与故宫古建筑一同见证了中华文化之传承有序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故宫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见证:其前身为元大都之大内,清代又作为满族王朝之宫殿,内藏大量藏传佛教建筑及文物,凡此种种,皆是民族融合的例证{1}。
故宫博物院藏有2000余件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物,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机械钟表及医学六大类。此外还藏有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的大批画作。它们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
故宫博物院院史,则与近现代中国历尽艰辛的文化转型息息相关。
从中国文化整体观之,故宫学的研究可谓对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诚如单士元先生所言“故宫是一部中国通史”[13]。
1.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从中国文化整体的角度研究敦煌学,一方面应关注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交融的重大主题;同时还特别要注意的是,敦煌实际上是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佛教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变迁。在敦煌,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得到充分体现,如:石窟外面传统的木构建筑窟檐;莫高窟早期洞窟的双阙形龛与敦煌当地同时期墓葬中双阙形象之密切关联;大量壁画的传统线描画法、粉本之运用(有的粉本据学者推测直接来自长安),与莫高窟早期洞窟受西域龟兹石窟影响而采用的“凹凸画”技法形成鲜明对照;敦煌壁画与汉代画像石(砖)之传承关系及与唐代宫殿、寺观壁画的关系;画中的“净土世界”实为中国北朝或唐宋宫殿、佛寺乃至住宅建筑的摹写;佛教造像为中土与印度、西域艺术的融合,等等。以上内容皆有大量学者曾加以讨论。
藏经洞文献除了佛经,还有大量儒、道经典。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概论》中指出,藏经洞出土的《道德经》卷子(写本)多为高僧抄录[14]。以上皆佛教与中国文化交融的例证。
与故宫类似,敦煌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见证:十六国、北朝、吐蕃与西夏时期,皆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而敦煌文书中所存各民族语言的文献,各外来宗教的典籍(有的甚至在其发源地、母语国都已绝迹),至为珍贵,它们正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一座重要的国际化都会,汇聚东西方多种文化并最终将其融合的明证。
1.3 从中国文化视角看敦煌学与故宫学研究的交流互鉴
从中国文化整体视角审视,敦煌学与故宫学研究有不少可以展开交流合作的地方。
例如结合历代都城与宫殿营建来研究故宫古建筑时,敦煌壁画中所表现的北朝至元代的建筑形象,尤其是唐代的宫殿、佛寺等建筑图像,便是极其重要的资料。在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仅有三座完整实例(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南禅寺大殿,芮城广仁王庙大殿){2}的情况下,敦煌壁画中数以百千计的唐代木构建筑图像,尤其是表现大型宫殿、佛寺建筑群的巨幅经变画,显得弥足珍贵,是研究唐代木构建筑群最重要的形象材料。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1932)[15],即是借助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所刊印的壁画照片,对唐代建筑进行初步研究。此后,敦煌的学者们对此课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16-17]。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建筑图像的研究,来探讨唐代宫殿建筑群营建的情况,将会大大推动以故宫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研究——可以说是在敦煌寻找唐代的故宫;反过来看,敦煌大量经变画中所表现的唐、五代时期宏大壮伟的建筑群,均是以二维平面来表现三维建筑空间,但是如果结合对故宫建筑群的真实空间体验,则能更好地帮助今天的人们建立对唐代宫殿、佛寺等大型建筑群宏伟气魄的想象与认知——又可以说是在故宫寻找敦煌壁画中唐代宫殿的“影子”。
无论是“在敦煌寻找故宫”,还是“在故宫寻找敦煌”,未来均大有文章可作。以上仅是举古建筑研究为例,其实从各类文物、文献的角度出发,均能在中国文化层面找到不少敦煌学与故宫学交流互鉴的方向。
2. 加强基础研究与综合研究
敦煌学与故宫学目前皆已取得丰厚的研究成果。展望未來,还应持续加强基础研究,这是每个学科赖以发展的根本。此外,基于二者高度综合性的特点,应进一步加强整体的综合研究。
2.1 考古、测绘与修缮报告的编纂
对敦煌石窟、故宫古建筑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测绘,是中国敦煌学、故宫学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巨大优势(拥有近水楼台之便),同时也是重大的责任。敦煌石窟考古报告集、故宫古建筑测绘图集以及修缮报告集的编纂,依然是敦煌学、故宫学基础研究的重大工程,也是中外学者对敦煌石窟与故宫古建筑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前提。正如樊锦诗先生指出的,科学、完整而系统的考古报告集,“将成为永久保存、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信息,乃至全面复原的依据”[10]41。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撰写是一项艰巨、浩繁、长期的系统工程,仍然任重而道远。目前考古报告已于2011年出版第1卷,但距离规划中的100卷(包括莫高窟86卷,西千佛洞3卷,榆林窟10卷和总论1卷){1}的宏伟蓝图,还有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要走。
与敦煌的情况类似,故宫也有数量巨大的古建筑,目前公开发表的测绘图仅是少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1940年代张镈主持完成的测绘图。大量1990年代以来陆续完成的测绘资料尚未整理发表,此外还有不少建筑未测。可以说,从1934年中国营造学社计划全面测绘故宫开始,迄今已过去近90年,故宫的测绘大业尚未完成,更遑论全面出版测绘图集。因此,故宫古建筑的测绘及整理出版(如计划中的《故宫古建筑实录》丛书{2}等),依然是未来故宫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
2.2 文物及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及网络公布
敦煌文献方面,目前散落各处的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已经发表,可供研究者使用。未来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应当致力于分类目录的编写(目前各收藏机构仅有带序号的总目,编目时未作分类,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不便),为各学科学者提供基本的文献检索平台。在大数据时代,此项工作比过去更具备实现的可能。
故宫方面,各类馆藏文物已出版大量精美图录(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60册等),除了继续进行文物、文献的整理出版之外,也應借鉴敦煌文献的做法,编纂故宫馆藏文物、文献目录,以及流散文物、文献目录等。此外还应借鉴英、法等国敦煌文书收藏机构的经验,为各类文物、文献(如明清档案)建立更加开放的数据库、信息平台,供中外学者更加方便地开展研究——这项工作应该联合收藏故宫文物、文献的海内外机构,共同实现资源共享——这是故宫学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全面研究故宫收藏的必由之路。
2.3 整体的综合研究
敦煌学和故宫学的研究,皆应注意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宜将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献、文物,以及分散收藏在中国其他机构的文献、文物,结合敦煌、故宫本身的收藏,以及石窟与古建筑本体进行综合研究,以期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
以故宫为例,故宫的古建筑、馆藏文物和故宫博物院是文化上的有机整体,因而治故宫学者,应重视三者之内在联系,比如注意宫廷收藏之文物与宫廷制度之关联;各类文物与宫廷的政治、礼仪、宗教活动、日常生活以及各建筑群空间之关联;各类文物、建筑空间与明清宫廷档案记载之关联;各类宗教建筑空间与馆藏宗教文物之关联等等。例如结合两岸故宫所藏康熙《皇城衙署图》、乾隆《京城全图》等珍贵的古代测绘图(舆图),可以对故宫古建筑的历史沿革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还可以和现状测绘图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故宫所藏宫廷绘画如《万国来朝图》《康熙南巡图》《京师生春诗意图》等,可对画中不同时期的故宫古建筑群及其现状进行比较研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总之,学者在专研各自专业领域的同时,应能对文化整体进行观照;各不同专业之间更应加强交流,包括国际间的合作交流,逐步迈向整体的综合研究。
3. 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普及
敦煌莫高窟与故宫都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对这两处伟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充满挑战,是未来敦煌学与故宫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两处遗产的保护,牵涉到木构建筑、石构建筑、壁画、彩塑,以及种类丰富的文物、文献的保护、修缮或修复等复杂的工作。不仅如此,两处遗产地目前已同时进入到以预防性保护为主的中国文物保护的新时代。面临上述多方面的情况,对敦煌石窟与故宫的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探索更加科学的保护理念,积极运用当代先进的保护科技,并加强国际交流协作。在此方面,敦煌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也应积极展开多方面的交流协作,如壁画、彩塑、彩画保护、木构建筑与石质文物保护、等等。
文化遗产的保护,既要充分运用当代先进的理念和科技,同时要做好公众普及工作,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二十多年来得到充分发展的 “数字敦煌”与“数字故宫”建设,都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公众普及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新成果,它们一方面是敦煌学、故宫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手段,如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不论是古建筑群还是各类艺术品、文物、文献等)进行信息采集、存档、分析、研究与保护;同时又以高度可视化的多媒体成果架起文化遗产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不断发展中的“数字敦煌”和“数字故宫”必将对未来敦煌学和故宫学的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以“数字故宫”为例,其总体目标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遵循真实、完整、可用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原则,更好地保护和展示古老的故宫文化遗产,助推文化资源的全人类共享,是21世纪故宫博物院发展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结合故宫学立足于中国文化整体的视野,未来“数字故宫”也将在“文化大数据”战略指引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内涵和元素符号,秉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开展更为多样性的线上线下数字传播、展示与服务[18]。
五 结 语
既充分尊重与继承传统,又以开放包容、博大的心胸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并将其成功融入中国固有文化之中,在敦煌石窟和故宫身上皆有着强有力的表现——这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研究与发展敦煌学、故宫学这两门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学问,同样要具有尊重传统又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以及继往开来的气魄。
与敦煌学目前所具备的国际化程度相比,更年轻的故宫学尚有一定差距,应充分借鉴敦煌学的经验,更加注意吸收海外学者的故宫学研究成果,并与之积极展开交流合作。敦煌学与故宫学未来更大的发展,皆有赖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交流互鉴,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未来故宫学亦如是。
参考文献:
[1]荣新江. 敦煌学十八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2]刘进宝. 敦煌学通论[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9:4-5.
[3]郑欣淼. 故宫学述略[J]. 故宫学刊,2004(1):8-35.
[4]章宏伟. 作为学问的故宫学[M].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9:1.
[5]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79.
[6]李正宇. 敦煌学导论:第8章[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138.
[7]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全集:22:石窟建筑卷[M].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3:5.
[8]巫鸿. 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前言4-10.
[9]王素. 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M].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57-60.
[10]樊锦诗.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编撰的探索[J]. 敦煌研究,2013(3):40-46.
[11]梁思成. 营造法式注释:卷上[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8.
[12]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M].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
[13]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2辑[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386.
[14]姜亮夫. 敦煌学概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20-23.
[15]梁思成. 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
[16]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全集:21:建筑画卷[M].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1.
[17]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18]王旭东. 数字故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21(6):52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