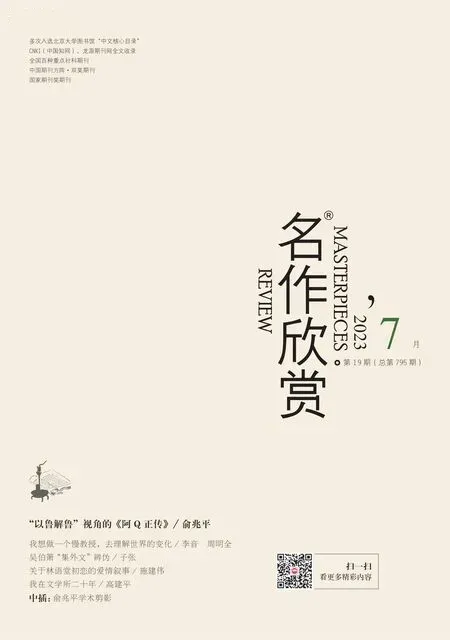家山与家国
——王跃文《家山》讨论
北京 陈慕雅 徐刚 孟睿哲 等
陈慕雅:我想从四重“家山”来开始对这部作品的讨论。
第一重家山便是王跃文心中的“家山”。《家山》的直接写作缘起,在于王跃文想要记录下祖辈经历过的真实历史。王跃文在多个访谈中都动情地谈到自己重读《三槐堂王氏族谱》,看到其中记载的祖辈往事时的动容。了解到解放前夕,家乡附近的一家大型兵工厂被土匪抢劫、史称“湘西事变”,而后家乡的地下党员与县警察局局长策动武装革命、加入“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上山与土匪头子斗争,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这些曾经为家乡解放立下功勋的祖辈、父辈,在作家过去的记忆中都是普通农民;而当作家意识到他们是英雄的时候,很多都已不在人世,于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些故事写下来。
在这样一种饱含深情的写作动机的驱动下,王跃文调动起自己的血脉记忆、故乡记忆、生活记忆、文化记忆,并且进行了翔实的史料工作和田野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十年打磨,日日掩泣”,最终完成了对他心中那座家山的书写。王跃文的家乡溆浦县,在他的心目中是一片钟灵毓秀之地;这里曾是屈原被流放的地方,屈原在此写下“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沈从文眼中的溆浦是一片耕读传家、勤劳善耕的福地:“溆浦地方在湘西文化水准特别高,读书人特别多,不靠洪江的商务,却靠一片田地,一片果园——蔗糖和橘子园的出产,此外便是几个热心地方教育的人。”这段话也印证了王跃文关于家乡溆浦的记忆,溆浦人勤劳,会干事,土地不多但却肥沃,要想繁衍生息就必须精耕细作,于是成就了这里勤劳善耕的民风,这也是王跃文心中典范性的乡村美德。
第二重家山便是书中以沙湾之地为轴心的“家山”。在《家山》中,王跃文的家乡漫水化身为“沙湾”,开篇就介绍了这里的自然山水环境:“从柚子树下望过去,望得见西边青青的豹子岭。豹子岭同村子隔着宽阔的田野;东边齐天界不远不近,隔着万溪江,山重着山,起起落落,没入云天。南边的山越远越高,万溪江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北边的山在更远的地方,人在沙湾只望得见远村的树。”这部小说在书写沙湾恬静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还在其中注入一种自然的灵性,是乡村人心目中土地、故乡、家山具备的精神图腾般的力量,也是天人合一、敬畏自然、敬畏生灵等朴素的哲学观念。不管是桃香眼中预示了祸福的燕子窠,还是充当时间使者、人事悲喜的信使的鹭鸶,抑或佑德公选中的那棵要雕成菩萨像的老樟树——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乡村记事,使得沙湾仿佛万物皆有灵,充满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式的哲思意蕴;而这是乡村人不自觉的一种诗性的生活哲学。
但是沙湾并非一个纤尘不染、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它距离县城很近,并且有官道与外界相连——“(佑德公的)屋前官道上铺着清水岩板,官道从北边县城过来,往南翻过重重大山通往宝庆府。门前南北八十多里官道上的清水岩板,都是佑德公祖上铺的。”这说明它就是一个既相对独立,由重山、古树层层遮蔽的村落,又是一个可以向外打开、外界也可进入的场所,这为沙湾长久以来的乡风,也为沙湾在现代化变局中的处境打下了基础。
在人文环境方面,沙湾是一个以亲缘为基础,又在不断分叉的演化过程中形成密切的地缘关系的人际网络,一方乡贤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祠堂在其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议事、教化和教育场域。小说将主线时间放在1927 年到1949 年之间,最末端的后叙笔触延续到了2004 年。在小说中我们会不断感受到大时代的动荡如何触动着沙湾和沙湾人的日常生活,而沙湾人又怎样在动荡不安的年月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能出钱的出钱,坚守着这一片家山。
《家山》写的是沙湾,但又不止于沙湾,至少它所映射的现象,在20 世纪上半叶的乡土中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我们便可以更进一步将其视为第三重家山——书写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图景的《家山》,并关注它在处理变与常、外部与内部、新与旧、时代与个人等问题上的一些取向。
首先,这部小说在处理方式上,主动地采取了抽离史观、先验定义,回到静水流深的生活本身的策略。王跃文在多个访谈中都表示:“我抛弃了对生活和历史的概念化的先验定义。一切认知其实都有历史时空的局限性,都会过时,只有事实本身是永恒的。所以,我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刻意要回到原生态,回到日常,回到真实的生活本身”;“我们过去对社会的认识太局限于某一种史观,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我是刻意跳出这种史观对过去、对生活的概念化的先验定义,用我自己对生活特性的认知,再去通过文学去艺术地呈现。”
所以这部小说初读来会觉得很琐碎,因为它不断地对沙湾的村庄琐事、土地关系、婚丧嫁娶、人群生活姿态进行书写;小说对时代变动的直接描写其实是很少的,小说将这些外部大事件作为引子,更多还是在关注这些事进入沙湾这个空间之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沙湾这个空间又是极具涵养力的,它将这些外部大事件极力地内化,也许村庄中正发生着齐峰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佑德公秘密转移红军家属这样汹涌澎湃的事件,但表现出来的仍然是静谧的、安然的姿态,所以说这里的乡村是静水流深的。
其次,这本书在处理新与旧、变与常、外部冲击与内部反应等众多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让人间情义、乡土根性作为沟通这一组组关系的纽带。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年龄跨度很大,他们各自所操持的话语也不尽相同,但是小说并没有刻意去凸显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人的冲突,而是为沙湾人赋予一些共性。佑德公代表的是乡绅的理想人格,有喜代表的是勤劳正直、富有德行的农民的理想人格,革命斗士劭夫、齐峰以及埋头实干的扬卿代表的是出身乡土的新青年的理想人格,还有像史瑞萍、贞一这样巾帼不让须眉的新女性,乡村社会中还有许多像桃香、扬高、五疤子这样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但以上这所有人在大是大非、家国大义面前都表现出了共同的坚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所有人,那就是沙湾好儿女,如果要整体性地来解读他们的行为动因,那就是朴素的人间情义——不愿让家乡父老生灵涂炭,不愿让家山被恶人践踏,不愿让国家动荡不安、丧失尊严。
而在沙湾外部环境激烈变迁的同时,村庄内里的结构、运转逻辑却始终保持着恒定。王跃文在创作谈当中表示,自己对所谓“宗法制”作为制度的实存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更愿将其定义为一种文化性质的约束力,也就是一种乡间的伦理规约,用小说中的话来讲,就是“老人兴起,后人跟起”。这些生活方式、民间习俗、道德规范、乡规民约的来源是什么,也许很难讲得清,但一代代的人都在自觉地遵守着。哪怕是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人物,回了村也得“夹着尾巴做人”,因为这是一个绝对的熟人社会,违背规约会被他人耻笑。而在日常生活的运转上,沙湾能够应对大事小情,处理好各种婚丧嫁娶事件,主要是靠乡贤佑德公、农会委员扬高、村长修根、知根老爷齐树、梆老倌儿齐岳等人来共同完成;不能在制度的意义上称他们是沙湾的权力结构,他们只是在村庄里各司其职,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王跃文在中篇小说《漫水》里也写到了这样的情形,村里有做寿材的木匠、接生的婆子、给逝者整理遗容的入殓师,没了他们,乡村里的生命便很难有始有终,有尊严。
如此种种,构成了一种极具内在力量的“常”;然而常的外围又是变:从舅舅不得已杀外甥到女性成为“乡约老爷”,从赋从租出到兴修水利再到水利附捐,从严守下马田上马塬的规款、到战争年月不得不破了这个规矩——从这些细微之处我们都能看出,一个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在历史变革中逐步朝着现代演进。然而也正像是舅舅杀外甥的最终化解一般,骨肉亲情是打不断的,乡土的根性也是斩不断的,纵使有20 世纪激进现代化的冲击,但乡土社会的文化核一直在延续着。
所以这部小说处理沙湾历史的倾向,就是大力展现依托于乡村日常生活的“常”,然后书写这个“常”的社会如何在外部冲击、内部自发的双重作用下经历艰难的嬗变,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经历了“变”的乡村社会仍然保有原初的伦理秩序与文化内核。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家山》是在更为广阔的视点上观察乡村真正沉淀下来的东西。
在讲述20 世纪上半叶历史这个部分的最后,我还想讨论个人在其中的生存空间。小说中有一群坚守故土、保卫家山的人,但也有一群因种种机缘离开家乡并从此几十年不得相见的人,即前往台湾的扬屹、贞一以及朱家克武、克双、克全三兄弟。小说投注在他们身上的笔墨并不算多,但是却映射出个人在大历史的浪潮下如流水般不定的命运。
贞一少女时期有过一段关于流水的想象:“我屋井里的水都会流到万溪江,万溪江的水最后都要流到东海。哥哥转战南北,他饮马处的水,说不定就有我屋井里的水。”当时她想象流水能够沟通起天各一方的亲人,哪怕是同饮一池水,也如同团聚了。这一处妙笔在结尾处贞一写给海峡对岸的孩子的信中再次出现:“娘井里的水流入儿井,从儿井又流到天井,从天井流出老宅,通到万溪江,如此绵绵滔滔,川流不息,直奔长江、东海!”看到这里其实会使人联想到《巨流河》,从辽宁的巨流河流落到台湾的哑口海,奔腾的流水最终都会在太平洋相遇。
《家山》在书写这些人的生命轨迹时,一个很突出的倾向就是写出了个人命运难以真正被个人掌握、离散悲欢不由得先决预判的无力感。去除了个人英雄主义的书写,去除对主观能动性的绝对信任,更重要的是,避免对这些像流水一般流落四方的人们进行他者视角的判断,这才是一种为生命赋予生命史意义的尊重态度。
第四重家山则是属于当下中国的《家山》。值得一提的是,与这部作品所属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几乎同时在湖南益阳启动的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写作计划”,作家王跃文也曾在谈论自己新作的同时提及这两个重点计划,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呼唤文学经典,这些经典必须是对时代的艺术再现”。那么为什么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亟待书写的同时,本部作品要后撤到20 世纪的上半叶呢?它又是如何在当下这个“讲述话语的年代”去讲述已被无数次讲述的“话语”的呢?
首先,为什么要讲史?这不仅源于王跃文记录家族往事这一直接缘由,更在于他想要写作一部具有史诗性、史志性的小说的宏大意图。而无论是对于家族往事还是民族史诗而言,忘记都近乎等于背弃;书写历史的熠熠生辉,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当下缺失了那份熠熠生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后撤性地书写历史,是为了铭记,也是为了重振。
其次,这段历史在当下被再度讲述,它的内在逻辑、叙述话语和此前众多书写近现代乡村中国历史的小说有了差异。在今年二月举办的《家山》研讨会上,杨庆祥提出,书写家族的小说经历了以革命为本位,到以文化为本位,到以日常生活为本位的过程——第一阶段例如《红旗谱》,需要勾勒阶级的生成过程;第二阶段例如《白鹿原》,意图树立起传统文化这一标杆,然而所有的历史却又最终在风水轮流转式的演化动力下归入自然史的进程中;第三阶段,也就是《家山》所代表的叙事姿态,是像此前讨论过的,尽力剥离既定史观的先验定义,回到日常生活本身;此前我们在讨论魏微新作《烟霞里》时也谈到过这一点,认为日常生活可以充当大历史和小个体之间的联结地带。所以这或许也是一种当下在讲述那些已经无数次讲述过的历史故事时能够讲出新意的一种叙述方式。
再次,《家山》要想讲这段历史,就不得不面临如何处理好这段历史遗产的问题。比如将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处理,不再刻板地书写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逸公、佑德公等田户也并没有被书写为威权式的人物,而是耕读传家、德高望重的乡贤,他们躬耕田亩,从不养尊处优;乡村社会在乱世的痛苦来源是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更为宏大的战争、自然灾害等,沙湾内部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生命整体,抵御着一切冲击。
但尽量剥离先验定义,不等于不对历史前进的方向进行书写,历史为何会做出如此选择?更进一步说,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一选择的缘由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于是小说有了这样两段前后相继的情节,红军借住在佑德公家中,军纪严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紧接着国民政府的人也来佑德公家借住,作风截然不同,为虎作伥,肆意征用。于是小说就把历史选择的缘由,化为一个亘古不变的朴素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小说中还多次出现桐油灯、煤油灯、天亮等意象:用桐油灯的熄灭、煤油灯的点燃,象征一个时代的交接;而在情节叙事中,明亮的煤油灯正是红军带来的;作者最后也写意化地将迎接解放大军的过程,同等待天亮的过程作比。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才真正完成了对共和国前史的书写。
最后,我想《家山》的当下性更体现在它对当下乡村振兴要求的回应。《家山》这部以家、以沙湾为圆心的故事,正是对家风建设的回应;而沙湾所承载着的土地与自然的厚重力量,正是千百年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的表征;以一个乡村为缩影,讲述了共和国何以成为共和国的历史选择缘由——也就是对我们来时的路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讲述,这样才能真正地走自己的路,走出乡土本色、中国本色。因此,《家山》的当下性便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最佳的言说。
徐刚:我想从三个主题讨论《家山》,第一个主题是乡村如何与现代连接到一起,第二个主题是小说去政治化的目标是否实现,第三我想介绍一下小说背后的政治逻辑。
先看第一个主题:乡村如何与现代连接到一起?我想从年轻力量的外部唤醒、媒介和内部的觉醒三个方面来介绍。先来看年轻力量的外部唤醒,小说当中可以看到受到现代启蒙的年轻一代,他们外出求学,然后返回沙湾村,对沙湾的现代化发生了关键作用。第一个重要青年是扬卿,刚刚返乡的扬卿与乡村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但李明达的出现让扬卿发生转变,他秉承中山先生遗志,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他劝说扬卿不一定非要等社会变好才去做事,他的这种务实与真诚打动了扬卿。扬卿开始对全县的地理情况进行考察,进行水利的筹备与建设,后来,在有喜等乡民的全力支持下,红花溪水库建成,当地百姓从中受益。第二个重要青年是贞一,小说中提到贞一第一次上学返乡碰见有喜,她对有喜说:“我们乡下太封闭,太愚昧,太落后了。……我们知道家谱,不知道国家,不知道世界。宗法制是落后的东西……”后来也是贞一给朱县长呈文请求禁止缠足,这才有后来县里发布的《重申禁止妇女缠足令》,该县的妇女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解放。齐峰也是一个关键青年,他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共产党。他给乡村带来一枚最重要的种子——革命的种子。在后文也可以看到,正是在齐峰的带领下,沙湾出现了具有革命性质的齐天界人民解放自卫队,最终他们与劭夫率领的解放大军胜利会师。
这是小说中予以重点呈现的三个青年,除他们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在齐峰、扬卿、劭夫等人的策划,以及逸公老儿等开明乡绅的支持下,最终新式学堂办了起来。学堂承担的是其实是启蒙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齐峰引导的革命队伍中很多是被学堂启蒙的后辈,修岳、克文等人都是扬卿在学堂培养起来的。在小说中,乡土世界不断走向现代。这一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呢?恰恰是通过这些进步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进步性又是如何获得的呢?我觉得就是小说中提到的接受教育。
乡村与现代之间的连接除了依靠年轻人外,报纸与书信的媒介作用也不容忽视。先来看报纸的作用:贞一一开始外出的野心,便是通过阅读《乡报》《大公报》《湖南公报》这些报纸;佑德公作为开明乡绅,通过《激流报》,他了解到国共之间正在发生内战;后来沙湾祠堂订购了《中央日报》《呼声报》等报纸,日本投降,国共再次发生内战,其实都是从报纸上知悉的。借助报纸获得信息,这些一直处于乡土世界中的人得以与宏大历史关联起来。
建立乡村与宏大历史关联的途径除报纸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下面的书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书信一方面让他们获得亲人的消息,一方面也让个人在历史当中获得定位。比如长沙会战期间,佑德公收到劭夫和贞一的来信,这让佑德公意识到他的家族所承担的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对改变他的认知非常重要。一开始他在小说中的很多做法是保护自己的宗族,保护沙湾,这时他意识到作为中国人要保卫国家,家与国在这里交织交融。这就可以解释佑德公为什么能够从宗族走向国家,为什么后来能很开心地把谷子捐出去劳军。
乡村和现代的第三方面连接,来自乡村内部的觉醒。我在此想重点关注佑德公是如何走向开明、走向现代化的。劭夫回乡时,他开始尝试借助自己既有的知识体系去理解劭夫所讲的东西。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劭夫讲的中山先生遗愿,不就是《礼记》上写的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佑德公作为一个“传统卫道士”能够变得开明,因为他所接受的儒家文化当中也有大同、大公。这便为佑德公的思想转变提供了一个契机,他后来愈发开明,也同意女儿贞一外出求学。小说后来多次提到佑德公越来越先进和开明。
与土豪劣绅相比,我觉得佑德公、逸公老儿能成为开明乡绅,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讲究耕读传家。他们虽然是地主,但同样投入生产,勤俭持家。他们秉承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团结宗族,受到大家的尊敬。此外,他们能够较快接受新事物,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接受过教育,他们能够识文断字,拥有阅读能力,通过阅读报刊书籍获得先进的思想。
我要谈的第二个主题是小说中去政治化的目标是否实现。我觉得小说的去政治化目标与佑德公的去政治化倾向达成了某种契合,但最终都是“欲盖弥彰”。小说中佑德公有三次登上报纸,然而在佑德公看来,他觉得登报并不一定是好事情,认为被宣传就是被利用。再如红军来到沙湾,佑德公家作为指挥部,佑德公给予红军一些照顾,后来红军对乡亲们说佑德公非常拥护红军,到处说我们红军好,但实际上佑德公并没有如此明确地表达,这种宣传也给佑德公带来了麻烦。小说中佑德公一直试图独立于政治之外,比如乡绅们联合控告县长李明达时拒绝签字,但他总是被迫卷入各种政治力量的纠葛之中,最终不得不做出选择。佑德公虽然是出于宗族大义来保护红属、保护齐峰,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做出政治抉择,后来因为天灾人祸交不起税,佑德公直接带头抗争,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跟国民党政府直接对抗,因此,佑德公试图脱离政治的目的不仅没有实现,反而与政治的关联愈发密切。实际上,佑德公在乡村世界中的经济位置、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必然成为乡村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交锋的一个交汇点,他远离政治的目的很难实现。既然佑德公的目的没有实现,小说也便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
最后我想对小说的政治逻辑进行简单概括。《家山》并不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讲的是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在我看来,小说讲的是由进步力量和开明乡绅两股内外力量相互合作,最终打开封闭乡村的过程。
归来的年轻人努力弥合乡土世界与现代社会的差距,建立新式学堂,兴修现代水利,乡土社会在这些力量的支持下,逐渐走向进步,渐趋和谐。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这一外部政治力量不断地打破乡土世界的和谐与平衡,具体表现便是国民政府要从乡村征收沉重的赋税,天灾人祸最终使乡土社会破产;这一破产在乡土世界是广泛的,连佑德公、逸公老儿这些富裕地主也破产了。与乡土社会破产同时发生的是国民党政权的破产,节节败退,乡土社会在这时候也陷入更大的动荡;在这种动荡之下,乡土世界就需要保护和拯救,需要秩序的维持。那谁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呢?小说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齐峰。他成立人民解放自卫队,承担起保护乡土社会的任务——齐峰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这样的描写下得到肯定。
孟睿哲:我首先想谈一下小说展开的历史语境。“青天白日旗在城里挂了十多年了,乡下人仍把县政府喊作县衙门。县城里的老衙门,一会儿喊作民政署,一会儿喊作知事公署,老百姓也记不住。”一个沿袭了几千年的社会组织构造在不断转变和崩溃。乡村既是旧帝国崩溃的末端,也是新民族国家形成的起点。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社会重新组织构造的运动,家山本身既是“外部”问题影响下的产物,也是外部问题的象征。慕雅把小说的叙事起点划在1927 年的国民革命,我觉得还可以再追溯一些前史。沙湾村的变动可以上溯到宣统年间成立的农会,首任农会的首领是乡绅陈远达,他的兄弟陈远逸当时是县城知县。清朝末年推行新政,国家行政能力极度低下,既没有一个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更没有一批新人才,因此所谓的新政和所有的新部门,只不过是给原来的权力阶层打开了一个新的方便之门。
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以及接受新一代教育的新式精英成长起来,结构又发生了变化。中华民国也成立了自己的农会,首领是陈远达的儿子陈扬高。“父亲离开,儿子继承”的现象当然有封建因素在作祟,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陈远达作为最后一批乡村精英,他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有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乡村第一代现代化知识分子的潜质,虽然扬高并没成为这样的人,但一般来说,和扬高出身类似的人确实有能力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陈劭夫的经历说明乡村最出色的精英已经被城市征用了,陈扬卿等人留在乡村有诸多特殊因素,总的来说执掌乡村权力的实际是有很多不良习气的陈扬高,年轻一代其实隐喻了权力的交接出现了裂痕。
其次我想谈一下维系沙湾社会运转的祖德祖风。沙湾几乎是没有贫农的,有地主而无恶霸,革命发生在江东场坪,但沙湾其实没有办法回避革命,革命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国民革命军军官陈劭夫第一次归乡。在此次返乡的过程里,陈劭夫和父亲陈佑德的对话浓缩了这个小说的精华,他们谈论了农会、佃农命运、田赋等问题,最终陈劭夫只能承认:沙湾村很好的原因是祖德祖风光大,但是整个国家还是要靠制度好。直到2004 年,年老的贞一还在感叹:“每遇家国大事,乡亭叔侄皆慷慨踊跃”,看来“祖德祖风”确实让沙湾平安度过了种种曲折。
最后我想对沙湾所仰赖的祖德祖风、乡绅道德发出一些质疑。“家山”近似一个乌托邦,这个理想村庄成立的文化基础是祖德祖风,文化必须有自己的执行人,即陈修福、陈远逸及其后代。他们是大地主,也是理想的乡绅,对上可以帮助国家组织乡民,对下可以帮助乡民向国家传达诉求。但是因为他们太理想化了,以至于让乡绅制度显得合理。于是我要问的是,换一个道德差的人会怎么样?如果当时陈扬卿和陈齐峰没有回到故乡,只凭借陈扬高和向远丰,那“家山”还会在吗?乡绅制度过于依赖乡绅个人的品性,总体来说,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在现代国家体系中的治理能力是非常可疑的。
无论如何,我个人确实觉得《家山》和《白鹿原》有共通的内核:开明乡绅、文化精魂,但似乎也没有比《白鹿原》谈出更多的东西。
李泽廷:我和睿哲的观点可能有一些重合和对话。我觉得这部小说像是一个“主旋律框架下的新历史小说”。刚刚谈到小说交代了祖德祖风和国家制度的互动关系,睿哲比较强调祖德祖风的部分,但小说强调国家制度或许也有它内在的逻辑。我很认同徐刚讲的一点:开明乡绅所代表的乡土伦理秩序和外部政治话语之间有一个合作关系。我觉得这个合作关系当然可能是作者的一种建构,但是这种建构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其实我觉得从徐刚谈到的另外一点出发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他特别提到了小说中报纸、书信这些传媒符码,但其实在乡村可能只有类似于乡绅这样的阶层才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换言之,只有乡绅才拥有和外部政治、现代化进程相勾连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可能不仅仅是孟睿哲刚刚提到乡绅作为个人的问题。他的选择,他接纳革命,不一定是因为他本身是个开明的人,很有可能恰恰是这样的开明本身是他所拥有的一种权力。所以,乡绅和外部政治话语的合作与联系也是必然的。
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思考,我发觉《家山》和《白鹿原》其实不完全一样。《白鹿原》里的乡绅,例如白嘉轩,从头到尾都坚持自己的传统道德,不曾主动与外部政治相联系,但是在这个小说当中,类似佑德公这样的乡绅肯定和政治的关系更近了,不管是因为他自身的开明,还是在认识到外部社会的情况后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没有《白鹿原》那样强的建构性,因为在20 世纪90 年代的语境下,《白鹿原》的去革命化、突出传统文化代表了非常鲜明的立场和动机。但21 世纪的这部小说却被包装为一个日常生活的叙事,虽然所谓的日常生活在小说当中的落点,那些婚丧嫁娶、儒家的乡土伦理秩序等,本质还是传统文化的东西,但却不用传统文化来作为包装点,而是将其表述为日常生活,这个在我看来是有意味的。我觉得作者或许有意要区别于20 世纪90 年代那套去革命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自己也强调这篇小说旨在剥离历史观,也包括新历史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像是一部“主旋律框架下的新历史小说”,主旋律框架其实也是极重要的。我觉得他在新时代是有意识地在和去革命的新历史主义对话,但是这种对话的有效性确实和睿哲说的一样,值得质疑。
毛玥晖:就《家山》和《白鹿原》所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的关系,我有些想要补充的。确实,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反建构的再建构,本质上说还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视角。而若是把日常生活理解为剥离历史观的表征,我觉得还有待深思;因为新历史主义已经验证了写作限度,也就是琐碎和虚无。王跃文在小说中如何处理日常生活,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日常生活的文学处理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微妙的问题,而在我看来,王跃文的日常生活书写的“静水流深”,并不像爱丽丝·门罗、黄咏梅那样指向人性幽微,而是指向村庄内部约定俗成的、制度性的伦理规矩。这是跟《白鹿原》很不一样的地方:白鹿原上的规矩是死硬欲颓的牌坊,《家山》的伦理则更多体现于乡村日常事务的流动处置中。而我觉得《家山》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以佑德公为代表的乡绅,在处理日常事务、调解乡里纠纷乃至重大事务时在权力结构上下之间协调权衡;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不逾矩的尺度,这不是官僚主义的陋习,而是在乡村上下公认的伦理规矩下,决断服众从而实行顺畅的必备基础。这样看来,《家山》的阅读感受跟《国画》那样的官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又一脉相承,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王跃文作为一个成功的官场小说作家在讲述乡土故事时会使得读者产生的阅读期待。
《家山》在中国当代乡土写作序列中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剥离历史观”而不“告别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王跃文剥离的是以“革命”或“文化”为轴的单一线性的“历史观”。相对地,王跃文书写新奇,对乡土的丰富就在于,刻画新旧更替大局中,乡村基层政治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型权力流动。县政府与乡村、乡绅与村民之间,都不是单向的上下决定,而是上正施于下、下情反于上的有机互动;而在这样的流动中,乡绅作为上下之间的节点,作为主要叙事视角,也确实贴切。而这种与官场小说一脉相承的、以权力“互动”“反馈”为核心的对革命历史的新视角,又带有第三次浪潮下,在当前人文社科研究中也属前沿的系统论趋势。这一点似乎也是这部小说能够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原因。
张闻昕:我想承接玥晖的发言来谈,因为我觉得其实刚刚玥晖已经说出了那个问题,但没有点明。方才听慕雅说到这篇小说归属于“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给了我另外的想法,因为这意味着《家山》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主旋律写作计划的要求,而它又恰巧也描写了湖南这片土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这篇小说在当年就负担着一个指导农村生活的责任,而在21 世纪,在当代文学已不像当年一样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承担如此重大责任的当下,主旋律写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想要重新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家山》为什么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为什么书中的乡绅要写成这个样子,似乎可以理解部分。《家山》写的是南方农村,小说所表现的年代离我们已经较为久远,我不禁猜想,有没有可能作者在《家山》里潜藏了一些野心,他想要将小说最后落脚在一些现实目的中。21 世纪的乡村发展到现在,所能选择的道路并不多;而在这些道路里,“乡绅治理”是一条古老的道路,南方农村直到今日也仍然相当依赖祠堂制度来进行基层治理。如果作者在进行写作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些,也许我们可以假设,他是想在小说里面重申这样一种制度,以此来为现代乡村寻找一个出路,这样也跟“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呼应与契合。
林孜:我想就新历史主义和主旋律的衔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部小说的实现方式反而落入一个很传统的激进主题,即官逼民反。《家山》在结尾处的主要笔触从老一辈乡绅转向了年轻一辈,写乡绅时王跃文的叙述质感是纯熟的、拿捏有致的,写年轻一辈起义——小说中称之为“举义”——时又转用一种更紧凑和峻急的方式。我读到这部分时,感觉其中的人心状态反而趋向古代草莽英雄的反抗状态。而且在官逼民反的主题内嵌了一个伦理的标准,即起义说到底还是因为统治者的不仁不义。《家山》的价值标准是传统伦理的范畴,它强调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是否符合传统伦理道德,它也写出了当时人们对事物合理性的判断方式和接受方式:一个新生事物被认知为合法的、合理的,正是因为它与传统伦理的相通相近。
孙逸格:乡村本身存在要进入现代化的需求,我看到小说里面有一个细节,记录佃户和田地的还是明清留下来的鱼鳞图册,它本身就昭示了征税制度的问题,即使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也是需要自行改变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扬卿是留洋回来的学者,他要修水库,也便改变了原来的那种传统的灌溉方式。我觉得修水库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了乡村必须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整个时代的那个进步。
丛治辰: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扬卿在开篇对械斗这件事情非常不屑。这一次械斗跟外部力量没有关系,这就是乡土中国的痼疾,矛盾的根源其实在于水源,扬卿看到了积弊,此后便要用现代的方案去改造。那是除了革命之外,现代的另外一面。正如逸格所说,即便没有外在的革命召唤,乡村也必须做出自身改变。但是以械斗开场的小说,其实一开始就表明了沙湾不是一个桃花源,它有它的内在矛盾。就此而言,“主旋律框架下的新历史主义”的确是很有意思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已经有了如此丰厚的乡土书写积累的情况下,今时今日为什么还要讲述这段故事?在讲述时必须要回应什么样的话语?大家谈到它和《白鹿原》的关系,谈到其中的文化因素、日常生活的因素。我倒是觉得,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日常生活,而在于它是沉到日常生活当中,用日常生活的视角而非俯瞰历史的视角去讲述故事,这就造成了它和《白鹿原》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