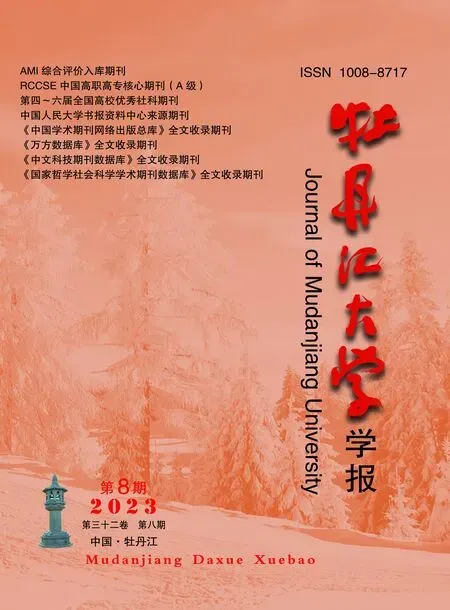威廉·库伦·布莱恩特诗歌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赵 莹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1)
威廉·库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是美国第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他引导美国诗歌摆脱了古典主义的桎梏,将简洁、清新、典雅带入美国诗歌的新时代,并为后来的浪漫主义创作奠定了基础。评论界对布莱恩特及其作品评价褒贬不一。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哈利·柯勒律治(Harley Coleridge)认为布莱恩特的诗《致水鸟》(“To a Waterfowl”)是“英语中最完美的抒情短诗”[1]59。艾弗·温特斯(Ivor Winters)认为《死亡随想曲》(“Thanatopsis”)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唯一一首真正伟大的诗歌”[2]22。吉尔伯特·H·穆勒(Gilbert H. Muller)称赞布莱恩特是“19世纪的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59。与赞扬声相伴随的是不曾间断的批评声。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批判布莱恩特的诗歌“太过流畅,太过圆滑,体现不出任何热情”[3]56。在约翰·海(John Hay)看来,布莱恩特“与同时代沃尔特·惠特曼的野蛮咆哮或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enson)露水般的放荡相比,他诗歌中韵律的准确性和冷静的沉着性在当下似乎已经过时了”[4]477。
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布莱恩特作为美国首位最重要的自然派诗人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在国内外文学批评者眼中,他的诗歌散发出恒久魅力。国外对布莱恩特诗歌作品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进入21世纪之后至今20年间,国外评论界对其关注度稳步提升。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成果丰富。一代代评论者对于布莱恩特作品的关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拟梳理布莱恩特诗歌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评述国内外学者在此研究上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索出该领域的研究空间。
一、国外研究综述
本文对国外批评家有关布莱恩特诗歌研究的综述,主要涉及主题和叙事技巧两个方面。由于布莱恩特具备诗人、评论家、报纸编辑和政治活动家的多重身份,他所关注的问题关涉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学界对布莱恩特及其作品主题方面的探讨较为充分,且主要从其中所体现的科学观、种族观、宗教观、自然观和死亡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交织等视角展开。叙事技巧方面的综述主要涉及研究者对布莱恩特诗歌中的互文性解读,其中又可细分为美国本土内外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国外对布莱恩特诗歌的主题探讨中,最早关注的是其中的科学观。1950年,查尔斯·I·格利克斯伯格(Charles I. Glicksberg)在谈到布莱恩特的科学观时提出,布氏在年轻时“对科学的发现和进步既热情又开明”[5]91,比如对解剖学、居维叶(Cuvier)学说、催眠术、各种机械发明以及科学成就对于扩大诗歌影响的作用等持有的包容态度。到了19世纪40-50年代,布莱恩特对于层出不穷的伪科学潮流,如颅相术、动物磁力等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但是到年老时布莱恩特则越来越虔诚地信奉宗教,甚至以宗教的名义反对进化论观点,即“反对科学带来的新的怀疑主义倾向”[5]96。1955年,唐纳德·A·林格(Donald A. Ringe)发现科学的出现动摇了布莱恩特宗教信仰的基础,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诗人“接受了科学发现的证据,但没有背弃宗教信仰”[6]514。看来布莱恩特的科学观在一生中并非一成不变,也非全盘接受或否定,而是辩证发展的,且其科学观受到自身对待宗教态度的影响。
第二,评论界将目光转向布莱恩特诗歌中的种族观。1961年,柯蒂斯·达尔(Curtis Dahl)发现,布莱恩特在他的诗歌《大草原》(“The Prairie”)和《死亡随想曲》中认为“土冢建造者(the Mound-Builders)根本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一种不同的、现已灭绝的族群”[7]182,但这些建造者被印第安人杀害了,“使他们的种族‘从地球上消失’”[7]179,这为驱逐印第安人提供了历史依据。2010年,安德鲁·加洛韦(Andrew Galloway)指出,布莱恩特在《大草原》创作中“使用中世纪的和中世纪研究家的素材和模式,赋予美国以自身的中世纪”[8]727,诗人以此将目光投向过去以寻求自身意识形态认同,进而发现种族和文化不可避免的消亡和解体,这样一种看待种族的方式对19世纪美国种族思想来说是一种超越[8]741-742。加洛韦的观点与达尔有异曲同工之处。2010年,作为对加洛韦的回应,克里斯托弗·汉伦(Christopher Hanlon)坚持认为,19世纪美英之间在领土争端、政治异议等方面造成的紧张关系等,出人意料地造成美国“中世纪”种族的过去与前现代英国遥相呼应,这样一来布莱恩特所构建的中世纪主义的故事,实则承载着南北战争前由于种族争议所引发的美国对英国的兴趣[9]756。汉伦实则将达尔和加洛韦的观点扩展到跨大西洋思想潮流的发展中,可谓颇具创见性。
第三,评论界对布莱恩特诗歌中宗教观的讨论也不容忽视。1968年,艾伦·B·多诺万(Alan B. Donovan)认为,布莱恩特除了将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特色带入美国外,还将“清教徒的风格融入19世纪美国诗歌的发展”[10]519,并“以一种特别生动的方式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情感和智慧”[10]520。1979年,林格指出布莱恩特诗歌中描述的美国城市兴起进程中伴随的“激情、贪婪和冲突”[11]172,以及“尤以战争形式所表达的、来自人类自私和骄傲的恐惧”[11]172,布氏基于此提出“唯一的治疗方法是让人类认识到一种超越他们能力和力量的神力”[11]172。2001年,C. 哈罗德·赫尔利(C. Harold Hurley)类比了比尔·戈登(Bill Gorton)“记住森林(woods)是上帝的第一个庙宇”的宣言以及布莱恩特在《森林颂》(“A Forest Hymn”)中的第一诗行“树丛(groves)是上帝的第一个庙宇”,从而将后者诗歌的中心问题之一与《太阳照常升起》(TheSunAlsoRises)联系起来,即“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寻求对精神价值的持续追求”[12]76。
第四,布莱恩特诗歌中的自然观也受到评论界的关注。1993年,加里利海·迈耶(Kinereth Meyer)认为布莱恩特“用自己‘野蛮的笔’书写了一首地方性诗歌,那里‘未被开发’的土地伴随着流离失所甚至是被毁灭的危险”[13]196,这是诗歌明显平静的表象下潜伏着的对荒野未知性的焦虑。1997年,史蒂文·M·里奇曼(Steven M. Richman)论证了布莱恩特诸如《年代》(“The Ages”)、《奴隶制的死亡》(“The Death of Slavery”)、《更好的时代》(“The Better Age”)以及《自由的古老》(“The Antiquity of Freedom”)等诗歌与劳埃德·L·魏因雷布(Lloyd L. Weinreb)的著作《自然法与正义》(NaturalLawandJustice)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布莱恩特的诗歌“为魏因雷布对本体论自然法的论证提供了一把钥匙”[14]23,而魏因雷布提出的本体论自然法也反过来“提供了对律师/诗人诗歌的洞察”[14]23。2015年,海以诗歌《大草原》为例指出,布莱恩特到19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历史化的自然环境观,以后期作品中复杂的、变化的和可塑的自然取代早期作品中伊甸园式的、永恒的和再生的自然”[4]478,对诗人来说,“环境的崩溃比南北分裂更具有威胁性”[4]504。这有别于与布莱恩特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自然的看法,也是其先进生态意识的体现。2015年,美国评论家卡伦·L·基尔卡普(Karen L. Kilcup)认为,由于布莱恩特在诗歌中表达出对美国东北部地区本土自然景观充满独创性、道德性和可理解性的关注,因而他的作品能够在19世纪饱受诟病的美国文学环境中盛行[15]。1998年,迈克尔·P·布兰奇(Michael P. Branch)指出,布莱恩特以诗人的身份唤起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土地作为国家文化来源的生命力”[16]194的新信念,使自然和艺术的融合合法化,这是美国环境文学直到今天仍保留的特征。他同时利用记者身份,通过他所处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平面媒体“传播自然历史信息,倡导环境保护,并培养公众对美国这片土地的美感、精神价值和文化可塑性的欣赏”[16]195。总的来说,布莱恩特通过诗歌,帮助美国人树立积极的环境意识。
第五,评论者从跨文类视角论述布莱恩特诗歌对美国民主政治方面的突出贡献。2003年,英格丽·赛特梅耶(Ingrid Satelmajer)认为《喷泉》以期刊的形式而不是以书的形式出版,表明它是“一个积极参与当时政治辩论的文本”[17]31,同时她试图证明,尽管布莱恩特目前的身份是一位文雅的诗人,但他作为一名美国公民对同时代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参与度不应被低估。2010年,加洛韦宣称布莱恩特在《晚报》(EveningPost)的编辑工作为纽约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建立做出贡献[8]727。2008年,穆勒出版了出色的布莱恩特传记《威廉·库伦·布莱恩特:美国作家》(WilliamCullenBryant:AuthorofAmerica),并在书中认为布莱恩特通过自己的诗歌、新闻和对美国精神的信仰,一步步地塑造了美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看法[2]。2017年,穆勒另一本名为《亚伯拉罕·林肯和威廉·库伦·布莱恩特:他们的内战》(AbrahamLincolnandWilliamCullenBryant:TheirCivilWar)的专著出版。这本书主要探讨林肯和布莱恩特在美国内战前后的社会动荡中如何结成联盟,并为维持联邦制度、废除奴隶制和拯救国家而努力奋斗。在内战年代,由于被交战的派系和激烈的冲突所包围,林肯“在著名的诗人兼记者的精神中找到了共鸣,即以道德正直和对联邦的承诺作为自身信仰”[18]xi。布莱恩特将目光聚焦于国家发展层面,通过自身的诗人等多重身份,积极推动美国社会民主进程向前发展,并塑造美国精神。
第六,布莱恩特诗歌中的死亡观也引起批评者的注意。2018年,崔熙苏(Hie Sup Choi)认为虽然布莱恩特似乎没有接触过佛教,但他对死亡的的某些观点与佛教非常相似[19]。同年,安·毕比(Ann Beebe)讨论了亚瑟·布朗·杜兰(Asher Brown Durand)风景画中的自然观对布莱恩特的死亡观的影响,她认为这幅画中的场景“以自然的天堂之美提供慰藉”[20]79,这与布莱恩特将死亡与自然联系起来的观点是一致的。由此观之,布莱恩特诗歌中所表现的死亡观融合了东西方的智慧。
评论界对布莱恩特及其作品中叙事技巧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对其中互文性的解读,比如诗人所受美国本土之外国家,诸如法国、英国、美洲和西班牙作家的影响,以及美国本土诗人、画家的影响。
不少评论家发现了布莱恩特对于美国本土之外文学的借鉴。1933年,约瑟夫·S·锡克(Joseph S. Schick)指出,布莱恩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古怪的法国诗人高缇耶(Gautier)诗意原则的影响,将“濒死的美国浪漫主义学派和新兴的法国高蹈派”[21]267联系在一起。1980年,罗伯特·A·弗格森(Robert A. Ferguson)认为布莱恩特受到苏格兰主教派牧师阿奇柏德·艾莉森(Archibald Alison)所倡导的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观点和美学原则的影响[22]433。2001年,安娜·布里克豪斯(Anna Brickhouse)从美洲内部维度聚焦布莱恩特多语言文学意识,认为布莱恩特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作家,也是一个美洲作家[23]4。2015年,格雷维尔探讨了布莱恩特受到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作品启发,进而发起一场美国诗歌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称赞英国新诗并提倡“close thy Pope, open thy Wordsworth”[1]58。布莱恩特在本土之外的影响来源主要是欧洲和美洲,且将主题扩展到他的诗歌作品对于文学、美学的贡献方面。
美国本土文学对于布莱恩特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没有被评论者忽视。1957年,查尔斯·L·桑福德(Charles L. Sanford)认为,布莱恩特与19世纪美国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在合作建立一种独特的本土艺术的过程中,“对自然的道德和宗教情感具有一种以崇高(sublime)概念为中心的民族色彩”[24]434。1960年,唐纳德·M·默里(Donald M. Murray)指出,布赖恩特的父亲彼得·布莱恩特(Peter Bryant)不仅激发诗人主要诗篇《死亡随想曲》的创作,而且“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卡伦诗歌中热情的导师”[25]522。2013年,劳尔·科罗纳多(Raúl Coronado)认为具有革命精神的西班牙裔美国人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José María Heredia)的诗歌中所蕴含的“揭示现代世界形成中的形而上学危机”的思想影响了布莱恩特的创作[26]。不难发现,美国本土对布莱恩特的影响不只来自文学界,还有绘画和哲学领域。
二、国内研究综述
与国外对布莱恩特诗歌的研究相比,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较少,至今没有关于布莱恩特诗歌研究的专著出版,有数篇从认知诗学、文体学、韵律和主题等角度发表的期刊论文和一篇学位论文。按照主题和叙事技巧为标准,可以将国内学者研究成果做如下分类。
一方面,国内学者对于布莱恩特作品中的死亡观、人生观和自然观的主题探讨较多。第一,国内评论者对布莱恩特死亡观的研究呈现观点的多元化。1995年,崔德民、王麦莅通过对《对死亡的看法》一诗的探究,阐明布莱恩特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死亡,同时倡导读者树立正确而坚定的人生信念,成为国内最早对布莱恩特作品展开专门论述的期刊文章[27]。1999年,龚光明以《关于死亡的冥想》为例,从诗与哲学交叉的角度,剖析布莱恩特的死亡观,认为诗人将人的瞬息存在与永恒结合在一起,这是其对死后归宿的深沉思考[28]。第二,国内学者对布莱恩特的人生观展开积极探讨。2013年,王学鹏和文晓华以认知诗学为视角,结合图形——背景理论的分离、移动和转换所构造的动态语境模型,探讨了《致水鸟》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意境,以及诗歌所传递出的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价值追求[29]。第三,对布莱恩特作品中自然观的探讨。2021年,朱新福从布莱恩特诗歌中的自然与人生、自然与死亡、自然与宗教思想以及新闻环保事业中的自然思想四个方面出发,论证布莱恩特的诗学思想主要通过对自然的描写来表达:“其自然诗歌的主题表现在对死亡的随想、对过去和历史的思考以及对美国新大陆荒野的赞美”[30]63。同年,潘莺将关注点转向国内学界较多忽视的布莱恩特的散文、书信和社论等体裁,发掘其中以保护荒野环境作为美国国家主体建构基础的生态意识[31],这种创新性的思路有助于拓展研究者对诗人诗歌内涵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叙事技巧方面,国内评论界同样关注布莱恩特及其作品的互文性解读。国内最早有关布莱恩特的论述文章发表于1993年,张禹九在其中提到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对诗人自然观的影响,即激发了诗人对自然更加深沉的热爱[32]。1999年,莫莉莉对比了菲利普·福伦诺(Philip Freneau)的诗歌《野生金银花》(“The Wild Honeysuckle”)以及布莱恩特的诗歌《致水鸟》两首自然诗,指出两位诗人在作品中表达出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积极的人生观[33]。这篇论文奠定了国内学界对布莱恩特作品中所体现的积极人生观的基调。2007年,陈玉秀将布莱恩特的《致水鸟》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致海伦》(“To Helen”)进行美学比较,总结出两首诗歌均体现出创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34],这也是对布莱恩特不断进取的人生观的阐释。2008年,许卫红从超验主义视角探讨布莱恩特诗歌中的自然观并指出,布莱恩特和爱默生在自然美、自然的理性、自然的神性以及自然对人类的启示方面均存在契合点[35]。2009年,张坤通过将布莱恩特与坡的死亡观进行对比,发现布莱恩特则不追求灵魂复活或灵魂永生,且将死亡之美刻画为宁静、和谐的美[36]。2010年,李蓓蕾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与布莱恩特二者与死亡主题相关的诗歌进行对比,认为“在布莱恩特的死亡诗里,灵魂在愉悦的忧郁中再生”[37]49,这与张坤所表明的灵魂不会复活的观点相悖。国内学者通过对布莱恩特诗歌的互文性解读,从新的角度论证了其作品中的死亡观、人生观和自然观。
三、结语
国内外学者以往对布莱恩特诗歌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价值和具备启发意义的。从主题来看,国外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其中的科学观、种族观、宗教观、自然观、民主政治观和死亡观等诸多方面,且对于相同主题,不同的研究者所持观点各异,体现出布莱恩特诗歌散发出的恒久生命力。相比于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内在布莱恩特诗歌的主题研究中,宗教观、种族观和科学观等角度的研究较少,较为集中在对死亡观、人生观和自然观三个层面的探讨,且对死亡观的探讨观点较为多元。在叙事技巧层面,国外学者相比于国内学者来说,更多关注布莱恩特美国本土或本土之外其他作家或艺术家的对比;国内对比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没有跨出英美文学界或是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家。此外,国外对布莱恩特诗歌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内部,而是将视野拓展到诸如报刊文章、散文、书信等文本外部材料,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如朱新福和潘莺等也开始关注布莱恩特诗歌之外的作品,以这样全面的文本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结论必将更有说服力。再者,在现有对布莱恩特诗歌的研究中,国内外评论者除了对《死亡随想曲》《大草原》《喷泉》和《致水鸟》等诗歌有较多讨论,对布莱恩特创作的其他诗歌仍未给予过多关注。由此看来,这个领域还存在很大研究空间。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未来学者对于布莱恩特诗歌展开的探讨将更加全面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