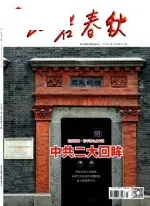白涛,我时常把你想起
杨权利
白涛,一个坐落在乌江边的小镇,它的名字,曾因816工程从地图上抹去。而今,又因816工程扬名四方。
我是参加三线国防工程建设的老兵。白涛,这个在战友们履历表里从未出现的字符,却深深印入我们的记忆。
那是三线建设时期,白涛还没修通公路,交通运输只能走水路,数万名官兵及工程人员来到这里,后勤供给压力很大。当时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简陋,有人用打油诗这样描述:“钢针镐头手不离,砂眼灰鼻满嘴泥。大米白面很少见,天天啃着棒子面。天当房子地当床,蚊子臭虫闹营房。”一人一床被子,没有垫被,下面铺的是稻草, 冬天冻得连觉都睡不着。一个排30多个人,共用三件大衣轮流穿着站岗。尽管很苦,但大家的心紧紧拧在一起。
施工中最危险的活,要数排险。排险作业一不小心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坑道里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烟雾、毒氣、粉尘无时不在威胁着战友们年轻的生命。坑道经常塌方,落石随时都有可能砸向战友们的脑袋。因为是绝密工程,战友牺牲了,往往不能及时告知亲属,导致几十年后,亲属都无法知晓亲人到底在哪儿。
我们连队的何秀金,在一次焊接施工中,因钢架倒塌,情急之下,他一把推开身边的帮手,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却倒在钢架下面。追悼会上,指导员哽咽道:“何秀金同志的牺牲,虽然没有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豪迈,但有着罗盛教舍身救人的壮举。”
多少年来,对烈士及其家属的愧疚,一直是战友们解不开的心结。今年5月,来自各地的战友会集重庆后,便驱车前往白涛镇。这儿的山,还是原来熟悉的山,这儿的水,还是原来熟悉的水。这儿的人,已经不是原来所熟悉的人了。
816洞体,吞入一批又一批游客,我们随着人流,没有多语。老连长轻轻对导游说:“这个山洞是我们打的!”导游向我们这群特殊的游客,投来惊奇的目光。出了山洞,我们要去烈士陵园,看望牺牲的战友。
车在盘山公路上盘旋了一会儿,在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打开门,一座高大的纪念碑映入眼帘,我们停下脚步,向纪念碑三鞠躬。 一抬眼,见一缕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依稀映射在长满青苔的墓上,好像在寻找昨日遗忘在这里那抹时隐时现的影,把忧伤洒落一地。几只不知名的小鸟,扇动着翅膀,在树上飞来飞去,仿佛也在和我们一起祭奠沉睡的英灵。
我们沿着墓区走了一圈,在一块写着“孟洁烈士之墓”的墓碑前停了下来。前些年,央视在播放国防教育纪录片时,荧屏上闪现一块墓碑,墓碑中间清晰写着六个大字:孟洁烈士之墓。一位正在收看电视的年轻人,看到这一幕,突然站立起来,高声喊道:“三叔的墓碑!” 这一偶然发现,终于揭开了身在何方的谜团。
我们登上返程的车,默然回望乌江边的小镇,心里在不停叨念:白涛,余生,我会时常把你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