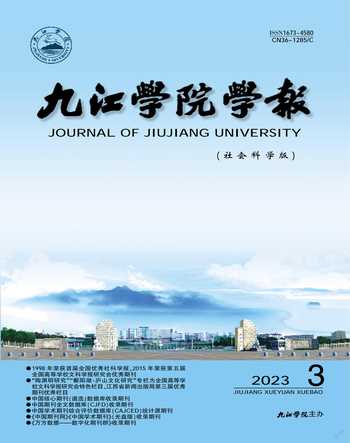再论汉晋豫章郡城位于阳
摘要:文章在《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一文的基础上,采用“豫章山”等史料继续论证汉晋时期的豫章郡城在鄡阳平原,着重论述指示郡城的方位的“龙沙”与南昌的“龙沙”完全不同。南朝时期,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但从南朝的钓圻邸阁到宋元时期的四望寨,又反映了豫章城一直得到使用的情况。元代以后,豫章郡城才被彻底废弃。
关键词:汉晋豫章郡城;鄡阳;再论
中图分类号:K8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3)03-0027-(07)
DOI:10.19717/j.cnki.jjus.2023.03.005
笔者曾撰《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一文[1],指出汉晋时期的豫章郡城在鄡阳平原上,现代发现的鄡阳城遗址(在今江西省都昌县周溪镇泗山村)乃是郡县合一的遗址,亦即豫章郡城与鄡阳县城共同留下的遗址。南朝之初,因鄡阳平原被淹没,豫章郡治被迫迁徙到南昌。这一问题因涉及面太广,论述起来非常困难。最难者莫过于南昌对汉晋豫章郡治的干扰。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将汉晋豫章郡城与南昌混为一谈,对后世形成了巨大的误导。宋代以来,人们基本上都认为豫章郡城就在南昌,并将两晋南朝乃至唐朝有关豫章郡城的记载统统归于南昌。事实上,这种做法多半出自“想当然”而不是严格的考证,不同的记载也长期存在;但因附会者太多又几乎无人提出强烈的质疑,导致“汉晋豫章郡城在南昌”的论调成为“三人成虎”式的“铁案”,对“汉晋豫章郡城不在南昌”的论证则变得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汉晋豫章郡治被“挪移”到南昌既是历史的积弊也是一种“系统工程”,单凭某一方面的证据无法拆解这个“系统”,而系统性的解构则极为繁难。有鉴于此,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连锁式的论证。本文所论有三:其一,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方位原本很清晰,宋代以来却与南昌的“龙沙”混为一谈。其二,豫章郡城在鄡阳平原的证据尚有新的发现。其三,描述豫章郡城在水患侵扰下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探索它的原貌。
一、鄡阳城为汉晋豫章郡治,郡治迁徙之后城池存在很久
笔者在《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一文中列举了大量的证据,说明汉晋豫章城在鄡阳而不在南昌。现又补充数则材料,以更好说明这一问题。
梁朝释慧皎《高僧传》卷一记载了安世高的事迹,又附带记载了“安侯道人”的事跡:“晋太康末,有安侯道人来至桑垣。……吴末行至杨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识。仍将奴适豫章,度宫亭庙神,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胁,于是而终。”[2]宫亭庙在星子县(今庐山市)境内的湖边,此处的湖面叫做宫亭湖。“适豫章,度宫亭庙神”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为“适豫章(郡境内),度宫亭庙神”;二为“适豫章(郡城),度宫亭庙神。”三国东吴时期,宫亭庙属于武昌郡柴桑县,故第一种解释是不合理的。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既反映安侯道人是在去豫章郡城的路上度化宫亭庙神的,也反映豫章城与宫亭庙相距不远,与安世高度化宫亭庙神之后“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城)”的情况吻合。
东汉建安四年(199),孙策攻占豫章郡,太守华歆投降。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孙策)还定豫章,走华歆,以从兄贲领豫章太守,留贲弟辅将兵住南昌。”[3]孙策让堂兄孙贲领豫章太守,驻守豫章城;又让堂兄弟孙辅带兵驻守南昌,颇能表明东汉末年的豫章郡与南昌不是一个地方。
距离汉晋豫章城数十里之处,有山名曰“豫章山”,此山既因豫章郡治而得名,又颇能反映豫章城的大致方位。
据梁朝释慧皎《高僧传》卷四,西域高僧康僧渊于东晋成帝之时与康法畅、支敏度等高僧“俱过江”而到南方,“后于豫章山立寺,去邑数十里,带江傍岭,林竹郁茂,名僧胜达,响附成群。”[4]支敏度亦为豫章山沙门,晋成帝时与康僧渊等入都。
唐代道士张氲假托为古代仙人洪崖先生的后身,自号洪崖子,亦曾隐居豫章山。宋代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七引《高道传》:“道士张氲,号洪崖子,隐豫章山。开元中,明皇召问:‘朕何如尧舜,先生何如许由?对曰:‘陛下道高尧舜,臣德谢许由。昔尧召由而由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来。上嘉之,拜先生太常卿,累迁至司徒,皆不受,乃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令臣追迹巢由。上许之,居于西山巨崖,乃先生旧隐之处也。”[5]张氲初隐豫章山,后得唐玄宗恩才隐居南昌西山,“豫章山”与南昌西山完全不是一个地方。《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一:“拍笑亭,《明一统志》:‘余干县西北六十里洪厓山,濒鄱阳湖,唐张氲炼丹其上,有丹井、仙坛观、拍笑亭遗迹。按张氲唐天宝间人,见张燕公《洪厓先生传》,《一统志》作晋人,讹。”[6]唐代张氲隐居的豫章山,即东晋高僧康僧渊建寺庙的豫章山。张氲得皇帝恩赐之后,此山遂易名为洪崖山,在今余干县金山嘴乡寺前刘家村附近,山上有洪崖寺、仙坛观、拍笑亭、丹井等遗迹[7]。《高僧传》卷四说豫章山“去邑数十里”,亦即距离豫章郡城数十里。按现在的距离测算,余干县的洪崖山距离南昌有160来里,与“去邑数十里”的描述极不吻合,反映当时的豫章郡城并不在南昌。洪崖山距离鄡阳城所在的泗山村直线距离有80多里,且有水道可以直达,与“去邑数十里”的描述较为吻合,颇能佐证豫章郡城就在泗山村的观点。
自南朝宋开始,豫章城的水患日益严重,导致郡治迁徙到南昌,但留下的豫章旧城则一直得到使用,各个朝代设有不同的衙门机构,直至明代方才彻底被官方抛弃。
据《水经注》引《豫章记》,豫章城东有大湖,城南有南塘,两湖本来相连,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豫章太守张躬筑堤坝以通南路,两湖遂一分为二,东面谓东湖,南面谓南塘。南塘与江水相通,此“江水”指古代赣江的最下游一段,注入彭蠡泽,一般称为“章江”,今已被鄱阳湖淹没。到了南朝初年,因江水不断倒灌,水患日益严重。宋少帝时,蔡廓任豫章太守,其大儿子即因大水而淹死。《幽明录》曰:“蔡廓作豫章郡,水发,大儿始迎妇在渚次,儿欲渡妇船,衣挂船头,遂堕水,即没。”[8]《水经注》将蔡廓误作“蔡兴宗”,蔡兴宗实际上是蔡廓的小儿子,并未担任过豫章太守。鉴于丧子之痛,蔡廓于景平元年(423)在南塘之中更筑堤坝,形成“塘中塘”,用以调节水位。有此举措之后,水患稍减。
《永乐大典》卷二千六百二十二引《豫章志》曰:
东湖,在郡东南,周广五里。郦元云:东湖,十里一百二十六步,北与城齐。回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减与江水同。汉永平中,太守张躬筑堤以通南路,谓之南塘,以潴水。冬夏不增减,水至清深,鱼甚肥美。每夏月以水泛溢塘而过,居民多被水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兴宗于大塘上更筑小塘以节水。为水门,水盛则闭之,多则泄之,自此水患少息矣。唐贞元二年,都督张廷珪奏改曰放生池而立碑焉。五年,江水逾塘一丈,观察使李巽躬率吏民,以土囊固护,立碑以志其事。碑既亡,九年,观察使齐映复加修筑。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复建南塘斗门以泄暴涨,绕湖筑堤,高五尺,长十二里。明年,江与堤平,无复水害。元和十三年,道州刺史韩衢作《东州亭记》。宣宗时,塘东有三亭,曰孺子,曰碧波,曰涵虚。乾符中,因乱悉废。今复葺。[9]
此条史料非常重要,向来未受特别关注。一方面,这段记载反映了从南朝至唐末的四五百年中,豫章郡城外的水位不断增高,而且抬升的速度很快,所以历任官员不得不反复加高南塘的堤坝以防江水侵入城池。另一方面,这段记载又反映豫章郡城到唐代尚在使用,它是江西境内水上转运的重要站点。在南塘之东建造的孺子亭,显然因徐孺子墓而得名。雷次宗《豫章記》记载徐孺子墓在郡城之南十四里的白社,历任太守建有墓道、墓碑、墓亭,《徐稚别传》亦云:“徐稚亡,海内群英论其清风高致,乃比夷齐,或参许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于稚墓首,号曰思贤亭。”[10]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曰:“《通志》载孺子墓在南昌进贤门外圣仙寺东,……本元明来传说在此,亦未知即古白社否。”[11]众多证据表明,南昌的徐孺子墓与郡城之南徐孺子墓并非一回事。
南朝宋初,因连续地震造成的地陷和水患,豫章郡治开始迁往南昌。《宋书·庾登之传》:“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临川,吏民咸相轻侮,豫章与临川接境,郡又华大,仪迓光赫,士人并惊叹焉。(元嘉)十八年,迁江州刺史。”[12]豫章郡治原本在鄡阳,与临川郡相隔一个鄱阳郡;因此“豫章与临川接境”颇能反映元嘉十八年(441)以前豫章郡治已经迁徙到南昌。但这种搬迁只是官署衙门的搬迁而已,豫章郡城仍在且一直得到使用。
东晋时期在豫章郡城之外的水滨设立了“钓圻邸阁”,用以储存、转运粮食。南朝宋初,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钓圻邸阁仍在,且得到使用。《宋书·臧质传》:“及至寻阳,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质渐猜惧。”[13]说明在南朝宋孝武帝时期,钓圻邸阁仍是江西境内的大型粮仓。
南朝梁时期,豫章郡治亦在南昌。梁元帝萧绎《侍中吴平光侯墓志》:“冠承华之楷模,迁豫章内史。法井鸾峰,甘露岁下;萧崖鹤岭,连理成阴。”[14]用南昌西山的典故形容此人任豫章内史的情形,可以反映梁朝的豫章郡治设在南昌。
隋唐之时,位于鄡阳的豫章城依然存在,人们还是习惯把它叫做“豫章城”。隋朝末年,林士弘在鄱阳聚众起义。《新唐书·林士弘传》:“林士弘,饶州鄱阳人。隋季与乡人操师乞起为盗。师乞自号元兴王,建元天成,大业十二年据豫章,以士弘为大将军。隋遣治书侍御史刘子翊讨贼,射杀师乞,而士弘收其众,复战彭蠡,子翊败,死之。遂大振,众十余万,据虔州,自号南越王。俄僭号楚,称皇帝,建元为太平。侍御史郑大节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党王戎为司空。临川、庐陵、南康、宜春豪杰皆杀隋守令以附,北尽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后萧铣以舟师破豫章,士弘独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铣败,其亡卒稍归之,复振。赵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15]《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方与帅张善安袭陷庐江郡,因渡江,归林士弘于豫章;士弘疑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恨之,袭破士弘,焚其郛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萧铣遣其将苏胡儿袭豫章,克之,士弘退保馀干。”[16]林士弘为鄱阳人,隋末反于鄱阳,与隋军战于彭蠡,据豫章而称帝,人们往往认为他占据的“豫章”就是南昌(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此“豫章”乃汉晋豫章旧城,离鄱阳、彭蠡不远。林士弘称帝之后,南昌亦被他占领;后来隋军攻克豫章,林士弘仍然占据着南昌,又颇能说明此“豫章”并非南昌。林士弘所占据的豫章,其附近有南塘,与雷次宗《豫章记》记载的郡城南塘也是同一个地方。
两宋之时,豫章郡城因荒废日久、水淹日甚,残存的建筑越来越少。与此同时,鄱阳湖的水面日益辽阔,豫章郡城控扼交通要道的功能也下降了,沦落为一个戍卫之所,主要针对湖区的治安而设。一般的船只经行到此,常常把它当作打尖、歇息的场所。此时距离豫章郡的废除已有数百年之久,人们也不再以“豫章”称之,而是称为“四望山”。“四望山”意指此处高踞湖心,四面而望,一览无余也。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二,建炎四年(1130)九月一日,“李成寇江州,(吕)颐浩乃驻军于饶州四望山。”[17]朱熹知南康军,有《乞住招军买军器罢新寨状》:“今照都昌为邑百余里,见有棠阴、四望、松门、楮溪、大孤山五寨。……乞行省罢此寨,欲将招到军兵并归四望山寨。”[18]南宋诗人杨万里有诗《明发四望山,过都昌县,入彭蠡湖》。《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百十七:“四望山寨,在都昌县东南六十里鄱阳湖中,宋元时置巡寨于此,又县西矶山下旧有大矶山寨,俱久废。”[19]“泗山村”之名即由“四望山”演变而来,明代已经出现。明代夏良胜《东洲初稿》卷七:“后奔宜阳,扶柩暨戚属归次泗山,舟阽石漏。”[20]“宜阳”即宜春,“泗山”即“四望山”。
九江科技中专的袁银初先生,多年来颇为关注鄡阳古城的出土文物,收集到不少铜钱、墓砖,其中有西晋惠帝元康八年的墓砖、唐朝的“开元通宝”、北宋的“崇宁重宝”等,与上述梳理的豫章城历史是对应的。这也就是说,豫章古城的地位虽然越来越低,但城池的荒废经历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宋朝,所以也就出土了宋朝的铜钱。
二、豫章北的“龙沙”被挪移到南昌
豫章郡始设于西汉,下辖18个县,大致相当于现代江西的全境。三国两晋时期,豫章郡被分割为豫章、鄱阳、临川、安成、南康等好几个郡,但缩小之后的豫章郡,其郡治仍在两汉时期的豫章郡城。
汉晋豫章城北有山曰“龙沙”,南北朝时期有几则史料反映了它的特点。其一,《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引《豫章记》曰:“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又曰:“郡北龙沙,九月九日所游宴处,其俗皆然也。”[21]其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赣水注》记载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曰:“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篆题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今此冢没于水,所谓筮短龟长也。”[22]
《太平御览》所引的《豫章记》,即东晋至南朝宋初南昌人雷次宗所撰的《豫章记》,“郡北”即豫章郡城之北。自两汉至两晋,豫章郡城并未迁徙,所以此“郡城”即自汉至晋的豫章郡城。根据《豫章记》的记载,“龙沙”较为高峻,位于豫章郡城的北面;又据《水经注》,龙沙西去七里半,即为赣江。
按理来说,“龙沙”指示了豫章郡城的方位,知道龙沙在哪里,就可以知道汉晋豫章郡城在哪里。然而上述记载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少,又受到严重的干扰,故而確定龙沙的位置变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豫章郡治在南朝宋时期迁徙到南昌,之后豫章旧城在很长时间内依然存在,只是被水淹没的部分越来越多、残存的部分越来越少、用处也越来越小而已。隋唐之时,人们还是习惯把残存的豫章郡城叫做豫章,且有两条史料颇能显示“龙沙”的方位。
唐代权德舆《暮春陪诸公游龙沙熊氏清风亭诗序》:“郭北五里有古龙沙,龙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清风亭。……初入环堵,中有琴书,披篁跻石,忽至兹地。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庐群峰,极目于枕上。”[23]这个“龙沙”,向来以为在南昌城北,《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八:“龙沙亭,在新建县北龙沙冈,本唐洪州熊氏清风亭,权徳舆有序。明万历中移建龙光寺南。”这一说法十分离谱。南昌城北怎会有鄱水、章江(赣江)合流的景象?怎么能看到200多里之外的庐山?
唐代诗歌中有一些写到“龙沙”,如孟浩然《龙沙作寄刘大眘虚》:“龙沙豫章北,九日挂帆过。”权德舆《奉陪李大夫九日龙沙宴会》:“龙沙重九会,千骑驻旌旗。”《腊日龙沙会绝句》:“宁知腊日龙沙会,却胜重阳落帽时。”戴叔伦《奉陪李大夫九日宴龙沙》:“莫怪沙边倒,偏沾杯酌余。”所写的“龙沙”皆为豫章郡旧城的“龙沙”,与南昌无关。如前所述,豫章郡旧城在唐朝是彭蠡湖上的转运中心,仍然颇受重视,官府多次修筑堤坝以保护之,故而唐人屡有歌咏之作。
唐代陇西人李舟,字公受,曾任处州刺史,去官之后,家于鄱阳,梁肃《处州刺史李公墓志铭》曰:“起家除陕州刺史,换处州刺史,累升至朝请大夫,爵陇西县男。既授代,家于鄱阳,享年四十有八,以某年月日遘疾捐馆。”又《祭李处州文》:“解印归来,《考槃》是卜。龙沙游衍,余干耕凿。与道为徒,以农代禄。”[24]很显然,文中的“余干”指“余干县”或“余干水”,在鄱阳附近;“龙沙”也在鄱阳附近,不可能在距离鄱阳一百七八十里的南昌。这也是“龙沙”在鄡阳一带的佐证。
《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一有《宋氏》一篇小说,也提到了 “龙沙”: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见水滨人物喧集,乃渔人得一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船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鼋耶?”曰:“然。”“身即鼋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囚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相召者,有以奉报。君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鸣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甚众,宋氏之子竟免。[25](出《稽神录》)
江西军吏宋氏在星子将一只大鼋放生,后来又在龙沙见到了它。事情虽然荒诞不经,但这种描述足以反映“龙沙”距离星子不远,不可能远在南昌。
南昌城北也有“龙沙”,宋代以来多有记载。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五已经记载南昌县有“龙沙”。曾巩《送王希序》也记载了南昌的“龙沙”:“与之上滕王阁,泛东湖,酌马跑泉。最数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阁,阁之下百步为龙沙,沙之涯为章水,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皆江西之胜处也。”[26]《续资治通鉴·元纪三十四》:“戊辰,(朱元璋)筑台于城北龙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台下。”[27]清代王夫之《南窗漫记》:“南昌城北龙沙,四围素沙环拥,如银城雪岛。中平敞,为禅室,有汤义仍手书门联云:‘池开沙月白,门对杏榆清。数十年矣,楮墨未损,悠然想见其挥毫之顷。”[28]清代陈宏绪《江城名迹》卷二:“列岫亭,在府城北龙沙,前对西山,取谢朓‘窗中列远岫之句。朱晦翁:‘过吾郡,每徘徊于此。谓列岫望西山最正,殆无毫发遗憾。”[29]
南昌城北的龙沙,今名下沙窝,在滕王阁东北面的六七里处。综合各种资料,南昌的龙沙因许逊的传说而得名。南宋白玉蟾《续真君传》:“真君垂迹,遍于江左、湖南北之境,因而为观府为坛靖者,不可胜计。或散在山林湖滦,绝有异处。如龙沙侧之磨剑池,池上沙壁立,略不湮塞。”[30]元代王义山《龙沙道院碑》:“按《豫章职方乘》,龙沙在章江西岸石头之上,与郡城相对,潘清逸有望龙沙诗。又按《神仙传》,旌阳君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郡江心忽生沙洲,掩过沙井口者,是其时也。”[31]许逊是两晋之交的方术之士,与吴猛为师友,当时名声不如吴猛,相关记载也较少。到了唐代,出现了《十二真君传》之类的著作,许逊名声大著,其传说流行甚广。宋元时期,以许逊、吴猛为祖师的净明忠孝道逐渐形成,关于他们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南昌的龙沙,即因许逊而得名,其产生时间应该不会早于唐朝,或晋朝,不可能上溯到汉朝。
南昌的“龙沙”出名之后,与汉晋豫章郡城的“龙沙”便逐渐混淆在一起。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卷四:“龙沙在豫章城北,江水之滨,白沙涌起,堆阜高峻,其形如龙,俗为重九登高处。旧有谶云:‘龙沙高过城,江南出圣人。今沙过城十余年矣。”[32]“高峻”“其形如龙”“重九登高处”等对“龙沙”的描述,出自雷次宗的《豫章记》,其他则出自许逊的传说。然而将两者糅合在一起明显是不合理的。豫章城始建于西汉初,到许逊活动的两晋时期,已经存在了四五百年。“龙沙”作为豫章郡城北的登高之处,由来已久,并非从西晋开始才叫“龙沙”的。说许逊出现之后才将这座山名为“龙沙”,显然是荒谬不经之论。南昌城北的“龙沙”起源于许逊的传说,恰好说明它与两汉时期早已存在的豫章城北的“龙沙”绝非一回事,后人把两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此外,雷次宗所说的“龙沙”是一座沙质山,也有一定的高度,并非是因涨水而涌出来的沙堆。南昌城北的“龙沙”是一个流水冲积而成的沙丘,仅仅高过城墙,既不能算是一座山,更不能称为高峻。
笔者在《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中指出,汉晋时期的豫章郡城距离庐山、星子的宫亭庙等处都很近。例如东晋时范宁任豫章太守,大建学校,派人到庐山上伐木;卢循在面对刘裕的攻击时,在都昌的左里建造水上栅栏以图固守豫章城等;又如豫章城边的钓圻邸阁因陶侃的钓矶山而得名,而钓矶山在都昌等。既然如此,只有距离庐山、宫亭庙等处不远的“龙沙”才是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唐朝权德舆等人描述的“龙沙”,“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庐群峰,极目于枕上”,非常符合这一条件。南昌的“龙沙”不符合这一条件,方位完全不同。豫章郡城的“龙沙”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得名,并形成了重九在这里登高的习俗,而习俗的形成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南昌的“龙沙”起源于许逊的传说,远比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出现晚。综合起来,只有排除南昌“龙沙”的干扰,才能根据豫章郡城之北“龙沙”的方位判断豫章郡城的方位。
笔者在《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一文中又指出,如果豫章郡城在古鄡阳一带,在这里寻找“龙沙”就是相当合理的。古鄡阳遗址北面的两三公里处有一些山峰,海拔在40米左右,比古鄡阳遗址高出30多米,适合登高,与《豫章记》所描述的“龙沙”非常接近。从这些山峰往西三四公里,就到了鄱阳湖,赣江故道就在这一带,这与龙沙古墓“西去江七里半”的距离也非常吻合。按《水经注》卷三十九:“鄱水又西流,注于赣。”鄱江在泗山村及对面的棠荫岛之间注入赣江是合理的,符合唐人“鄱章二江”合流于“龙沙脚下”的描述(鄱江、赣江的合流处现在已经被鄱阳湖淹没)。
到了现代,古鄡阳遗址一带在涨水季节均会被湖水淹没。1991年,泗山村建造了一道长达358公里、高达235米的鄡阳圩,使 6000多亩农田、5个村庄免于水患。笔者认为的豫章郡城遗址及鄡阳县城遗址,就在这些农田之中。2016年夏天,泗山村一带连降大雨,鄡阳圩外的湖水水位高出坝内近10米。由此可以想见古代豫章郡城及鄡阳县城遭受水患的情况,而“龙沙古墓”被淹没就是古代水患的一个例证。通过一系列的考察,位于豫章郡城之北的“龙沙”就在古鄡阳城一带。
参考文献:
[1]吴国富.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J].地方文化研究,2017(1):15.
[2][4]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7.
[3]许嵩.建康实录[M]//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第40辑.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6.
[5]陈葆光.三洞群仙录[M]//道藏:第3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81.
[6]谢旻.雍正江西通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50.
[7]余干县政协文史委.余干县文史资料:第5辑[M].1988:5.
[8]魯迅.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201.
[9]解缙原著,刘凯主编.永乐大典精华本:第2册[M].北京:线装书局,2016:665.
[10]鲁迅.古小说钩沉[M]//鲁迅大全集:第20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32.
[11]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1883.
[12]沈约.宋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288-537.
[1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93.
[15]欧阳修.新唐书: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7:2281.
[16]司马光.资治通鉴: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6:403.
[1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01.
[18]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808.
[19]嘉庆重修一统志[M]//四部丛刊续编:卷三百十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4.
[20]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第3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1923.
[21]李昉编纂,夏剑钦,王巽斋校点.太平御览: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280.
[22]郦道元著,张步天疏证.水经注地理疏证[M].北京:线装书局,2017:601.
[23]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1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5814.
[24]胡大浚.陇上学人文存·胡大浚卷[M].兰州:甘肃出版社,2017:300.
[25]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3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2282.
[26]曾巩.曾南丰全集:第2册[M].上海:大东书局,1936:59.
[27]毕沅.续资治通鉴[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351.
[28]王夫之.船山遗书:第8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653.
[29]陈宏绪.江城名迹[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1.
[3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9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03.
[31]王义山.稼村类稿:卷8[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5.
[32]王士性撰,朱汝略点校.王士性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308.
(责任编辑 程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