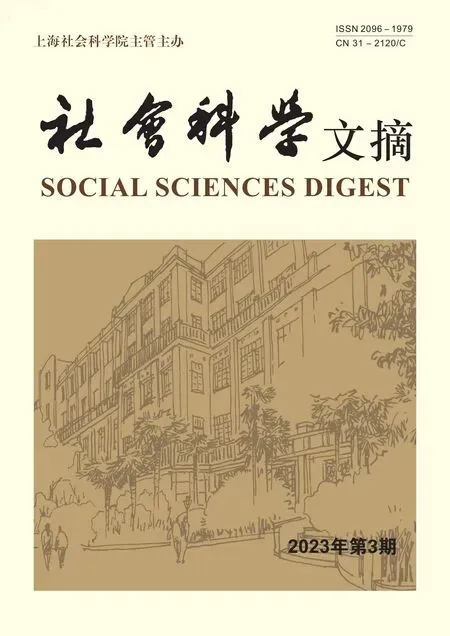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女性发展困境与政策出路
文/刘汶蓉
梳理国内相关研究可知,中国的女性解放和发展道路有着明显区别于西方欧美国家的特征,家庭现代化和趋同理论对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缺乏总体上的解释力。然而,中国当下的婚育率下降问题与世界普遍的第二次人口转型、性别革命究竟存在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仍很模糊。因此,为了在比较的视野中理解中国当下的女性双重压力和青年婚育困境,本文有两个具体的研究目标:一是通过梳理中国和西方社会20世纪以来的家庭现代化变革和女性发展脉络,来辨析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以家庭照料为核心的新社会风险与女性发展困境之间的联系,以及中国在该议题上的特殊性;二是通过相关统计和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描述当前中国女性的婚育观念和决策趋势,从支持性别平等的角度寻找家庭建设的理论逻辑和政策着力点。
西方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性别平等张力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20世纪以来,家庭的现代化之路是妇女寻求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但也是一条内部充满张力的曲折道路。
(一)现代核心家庭模式的发展与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家庭解体的问题备受关注。以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家庭需要从服务于群体转向使个人受益,家庭目标与个人抱负之间是否一致成为家庭制度能否在现代社会中持续的关键。在女性轰轰烈烈争取教育、选举、就业权利的社会运动背景下,涂尔干深刻地认识到婚姻对女性的禁锢,提出“女性与男性同等参与社会生活”,同时“强调女性家庭角色的重要性和男女分工”的家庭女性主义方案,但因为他高度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分工立场,对婚姻家庭道德功能的关切超过了对个体发展、性别平等的关切,被女性主义学者批评为忽视了家庭生活的现实复杂性。个体自主与社会团结两种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女性的自主和发展与家庭团结之间的张力并未得以成功调和。
现代性开启了家庭的个体化之路,推动了婚姻制度发生“制度婚—伴侣婚—个体婚”的变迁,也带来婚姻的情感化和心理化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大量的离婚和家庭解体危机,家庭研究的重点是个体调适,具有强烈的心理学取向。欧尼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关注内在的家庭动力,如人的自我与无意识对婚姻稳定性和不稳定的影响,以及家庭生活对个人幸福的影响等。但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国家安全和社会团结的诉求上升成为更重要的议题。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系统理论的取向下,提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妇核心家庭制度对工业社会的运转至关重要。然而,美国核心家庭的“黄金时代”仅经历了短暂的十年。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开始正式介入家庭研究。大量的基于女性生活经验的研究表明,婚姻是一种有利于男性而损害女性的制度,既有的“男主外,女主内”婚姻文化严重束缚了女性的自我实现。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离婚率、女性就业率、非婚生育率、同性婚姻比例等的不断升高,婚姻去制度化、家庭多元化等后现代家庭趋势显现。
(二)固化的性别分工与女性双重压力
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超过男性,女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成就显著提高,双薪家庭比重显著提升,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不断式微。然而,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脚步却无法匹配女性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变化。女性能否从日常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仅取决于女性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还取决于工作领域的时间体制、男性的家庭观念,以及国家社会政策的导向。
归纳起来,在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上,婚姻家庭制度一直在朝着个体化方向发展。在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导的文化框架下,市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两性之间的利益之争,掩盖了公领域对私领域依赖的这个实质。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转深刻地依赖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力再生产,但国家却不断地从儿童照料等福利领域撤退,加上商品化逻辑不断入侵、形塑育儿规范和家庭互动,继而加剧了家庭生活的压力和女性劳动的异化。
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性别平等与婚姻变革
与西方的妇女解放叙事以父权制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和女性主体性建构为中心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统领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和富强的话语之下。
(一)中国特色的性别平等话语和观念转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和家庭革命运动,以一系列制度保障、宣传教育和社会动员措施,从意识形态上将妇女就业与革命、进步、翻身、解放等挂钩,塑造了中国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劳动、争取经济独立的革命传统。
在计划经济时期,“家国同构”和“公私相嵌”的社会结构帮助女性兼顾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因为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工作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国家有责任缓解劳动者的工作—家庭冲突。因此,妇联与政府大力兴办托儿所、幼儿园,各大工作单位也兴建食堂、婴幼儿托育机构、子弟学校等。当时这种高度的传统熟人社会特点,大大减轻了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和监管责任。
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强调自由竞争的话语逐渐凸显,女性因为兼顾家庭责任而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婴幼儿数量减少,以及单位制的瓦解,政府也大幅削减了公共儿童托育设施和服务。虽然以妇联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始终坚持“参与是妇女发展的根本途径”,继续提倡男女成员合理分担家务劳动,但支持性的政策和实践难以满足群众需求。在公私领域分离、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机制下,女性依靠个体力量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困难越来越大。“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出现回潮。
然而,近十年来的性别观念发展却没有延续传统回归的趋势,反而在结婚和生育方面表现出去家庭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是全球新社会风险危机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特殊的性别平等关系的再一轮反思。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始大力倡导家庭建设,倡导妇女实现家庭贡献与社会贡献的统一。这不仅是对中国“家文化”传统社会底蕴的回归,也是对当前妇女面临家庭与事业两难争议、国家面临人口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一种顶层回应。
(二)婚姻自由的法律改革与性别平等矛盾
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自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家庭革命理想。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婚姻改革中发展出了“婚姻自主”的实践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婚姻自由和情感化的进程在国家制度层面得以确立和强化。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宣布彻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1980年通过的新《婚姻法》进一步强调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原则。
在计划经济时期“公私相嵌”的社会结构中,因为私人生活和个人情感发展的自由空间有限,婚姻自由原则并没有威胁到婚姻的稳定性。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婚姻并非只是个人问题,还具有鲜明的社会管理意义。市场经济改革开启了婚姻“私事化”进程,行政力量从婚姻干预中退场。
吊诡的是,婚姻私事化的进程并没有推动青年人大踏步走向婚姻自主和婚姻爱情化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城乡男女已经基本实现婚姻自主,婚姻自主者在城市超过九成,在农村超过七成。但21世纪以后,青年人的婚姻自主性发生了变化。在结婚的经济成本不断攀升、婚姻市场挤压和竞争激烈等背景下,父母以经济支持、安排相亲等方式影响子女的择偶和婚姻决策。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代际的经济依赖会强化婚姻匹配的同质性,以教育、户籍、收入为指标的阶层内婚配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延续并有所趋强。
当前中国女性去家庭化的婚育实践和价值观
中国当前婚育率下降的本质是现代化道路上婚姻私事化导致家庭生活缺乏价值认可和正式制度支持的结果,也是在社会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女性发展再上台阶的空间不足而产生的社会性焦虑。
(一)显著推迟的婚育趋势
历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青年人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的趋势在增强。尽管终身未婚的人口比重在世界范围属于较低行列,但已经从“普婚早婚”模式转变为“普婚晚婚”。与晚婚相伴随的是难以提振的生育率。2022年的人口出生率降至6.77‰,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生育政策调整未能实现预期,主要是二孩、三孩出生的增长幅度远小于一孩出生的减少幅度,其根源在于结婚率的大幅下降。从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的粗结婚率自2013年以来持续下降,从9.9‰降至2021年的5.4‰。
(二)理性权衡的婚恋决策
多项抽样调查显示,当下中国青年人并非不再渴望婚姻。对18~35岁青年人的调查显示,虽然对“结婚是私事”的观念认同度较高,婚前性行为和包容度提高,但结婚意愿并未下降,终身婚姻仍为大多数人的理想,自愿不育的比例很低。
观念与行为宏观趋势上的背离在微观个体层面体现为广泛的婚姻焦虑。与“不想结婚”相比,“理想婚姻不可得”的困扰更甚。在婚姻风险化和市场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当下青年人的婚恋决策表现出谨慎而保守的特点。对择偶梯度的研究发现,“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和匹配定式虽然在观念测量上有所松动,但在现实婚配上表现甚微。而且,婚姻的性别化差异期待未受挑战。这方面的证据包括:未婚青年的择偶观念依然呈现出明显的“男才女貌”倾向;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30岁以上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可能性越低,印证了高学历女性面临婚姻挤压的事实,也印证了性别刻板印象的延续,年龄依然被视为女性最重要的婚姻资本;农村青年,无论男女都会主动采取“彩礼竞争”的策略,折射的是农村社会严峻的婚姻挤压和风险化,以及日益高企的养儿育女和家计维持成本。
这些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普遍的婚恋困境背后是青年人工具理性与浪漫情感交织的复杂婚姻观,是对自我实现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高度期待,是在现实利弊权衡之下的浪漫佳偶难求。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人在亲密关系上并没有发生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情感关系“纯粹化”的转向。
(三)事业优先的价值选择
在个人效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之下,青年人将结婚生子视作个体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而非结婚生子本身具有不可规避性。“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倡导塑造了中国女性就业、独立、实现社会价值的革命传统。时至今日,与欧美、日韩相比,中国女性对就业和经济参与有着更加强烈的文化期待,且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强。201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一项全国城乡妇女调查结果显示,18~65岁的女性中有53.2%的人认为“目前对自己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收入”,且越年轻的女性越看重经济收入对生活的影响。另外,18~65岁的中国女性对“平等进取”价值观的赞同程度显著高于对“家庭导向”价值观的赞同程度。
结合前面对青年人婚恋决策理性化的分析来看,当女性面临工作—家庭冲突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会选择为工作和事业奋斗。家庭导向观念与年龄显著正相关表明,年龄越大的人越会看重家庭经营。而对于女性来说,生育是有一定生理和年龄期限的。因此,为了拼搏事业而错过最佳婚育年龄既是女性个体理性选择的悖论,也是整个社会支持体系缺乏回应女性价值诉求的后果。
建构女性友好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政策环境
综上所述,当下的中西家庭都面临着国家支持不足及商品化和竞争逻辑的裹挟,女性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家庭平衡压力。然而,与西方的家庭现代化和性别关系主要被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所推动不同,中国的家庭革命与女性发展道路主要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目标所引导和塑造。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中国的家庭变革和女性发展道路具有高度的压缩性,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发展与家庭意识形态之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在高度压缩变化的时空背景下,女性面临的精神困境和价值冲突也更为突出。与国家—市场—社会三个部门分割和对立的西方思想传统不同,中国的家国同构、公私互嵌、家庭主义等思想为解决现代化道路上的家庭团结与女性发展之痼疾提供了资源。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更高目标之下,个人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的利益纷争在理论上可以实现整合。但是,我们要对实践层面的矛盾和张力充满警觉,避免价值立场摇摆不定和具有功利性特点的国家主义立场。需要合理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对关系中处于弱势位置的一方予以支持,比如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公私关系中的家庭。
首先,在政策理念上需要进一步明确支持女性发展的概念。近十年来,中国女性在社会决策和管理领域的发展缓慢,损害了女性的发展自信,也影响了她们投入家庭生活的信心。
其次,厘清相关政策法规中婚姻家庭的主体性定位。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认可和保护,即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认可和保护,包括家庭成员中儿童对父母、老人对子女,以及夫妻之间的依赖关系,且这种关系具有天然合法性和神圣性。目前这种认可还远没有达成共识,“家庭”无法在观念以及制度构造中获得主体性存在,不仅造成青年人价值选择上的困惑,也造成家庭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价值两歧。
最后,大力发展支持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的社会政策体系。降低生育成本、提振生育意愿,不仅要降低家庭养育的经济成本,更要解决女性自身的发展问题,降低女性生育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