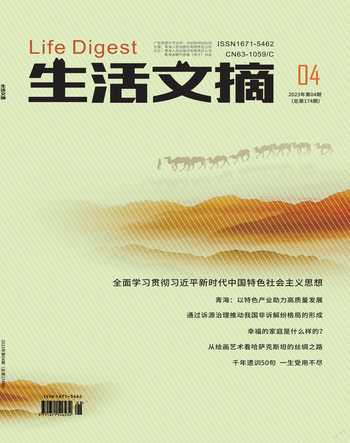愧对父亲
春节期间,看到日渐苍老的父母,特别是重病在身的父亲,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内疚和不安……
这几年,由于父亲进城看病,每年都要从乡下来我这里小住一段时间。最近,我把父亲接来,一方面想尽一点儿子对父亲的孝心,一方面也给我的儿女做点榜样。可还不到一个月,执拗不过父亲意愿,又送他老人家回乡下去了。这一回,更平添了我惭愧、内疚的思绪。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粮油供应制度的消失,我和妻子儿女的口粮大都从乡下老家往来捎,父亲常常磨好上等面粉、玉米糁子和母亲亲手酿制的粮食醋,等候有顺车回家时捎来,而且乐此不疲。我能给父亲的只是常回家看看。
5年前,村里调整土地,好强的父亲在村上分给二老的口粮田外,还承包了北壕一亩多边角地,以确保我们城里一家人口粮。冬去春来,寒来暑往,经过父亲一镢一镢挖土平整,一车一车拉粪追肥,一遍一遍锄草浇水,昔日茅草地变成了米粮仓,村民们纷纷交口称赞。也就是在这块地,给父亲引发了严重的疾病,留下了终身疾患,给儿女留下了心灵创伤和遗憾。
1996年8月的一天,正是伏天大旱,禾苗蔫枯,父亲和乡亲们一样,心急如焚,冒着酷暑,顶着烈日,给他苦心耕耘得凹凸不平的这块庄稼灌水,灌过水的玉米枝叶渐渐舒展、泛绿,几处灌不上水的玉米耷拉着头,憔悴不堪,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迟迟不忍离去,于是取来了盆子端水浇灌,一盆一株,一株一盆,直到所有玉米都能喝足吃饱为止。也就是在这时,父亲眼前发黑,头重脚轻,舌头僵直,不能自已了。军奇弟赶来报信,我匆忙赶到挂着吊瓶的父亲床前,次日医院大夫告知,父亲是“脑血栓形成”,我们如梦初醒,尽力医治,经过月数天治疗,还是给父亲留下了后遗症——左半身麻木,行走不灵便,这是我们的终身憾事。
父亲和伯父自幼失去祖父母,听父亲说他当时才7岁,伯父不到10岁。祖父母旧社会在眉县槐芽镇做生意,被土匪活活烧死并抢劫,父亲和伯父成了孤儿,流离失所,相依为命,曾在长房堂伯家打工度日,曾在槐芽镇当相公娃(站铺子)谋生,后来父亲偷心学艺无师自通,学会了油漆绘画手艺,给人们油门窗、漆家具、画棺材,他的油漆绘画手艺传流方圆十里八乡,千家万户,成为远近闻名受人尊敬的大漆匠、大画匠。父亲没有师傅,却甘为人师,先后带过10多个徒弟,本村就有四五个,常常乐于传技授艺,诲人不倦。逢年过节,常有徒弟拜年看望,有的徒弟还送来字画牌匾,深受徒弟和亲朋的敬佩和爱戴。在我眼里,父亲是多么的无私,多么的伟大。
父亲没有文化,却看重知识、崇尚文化,刻苦自学识字和珠算,并将打算盘教给了我和妻子。他和母亲节衣缩食,任劳任怨,饱受艰辛,抚养我们成人,教我们做有文化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通过努力,我们兄弟俩先后考上了中专、大学,这在我们家里,我们村里,当时算得上新闻,人人奔走相告,个个羡慕不已,父亲和乡亲们脸上都有了光彩,父亲的形象也高大了许多,我也领略了“光宗耀祖”的荣光。
我们上学之后,工作之后,父母亲的确高兴过,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也的确忧愁过,忧愁得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女儿出嫁,儿子进城,庄稼谁来作务?农活谁来干?老来谁在身边问饥问渴?问寒问暖?双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养儿防老”虽是传统观念,却是中国农民的最低要求,最樸素的人生哲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和健全,这一最低要求是十分自然的,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乎法度的(赡养法)。也就在这个担忧上,真的出了问题。如今,父亲患病,虽然有母亲照管,但母亲毕竟年迈体弱,也多病,儿女虽说离得不远,还能常回家看看,但毕竟还有单位,还有工作,还有小家庭,不可能天天守候在父亲身旁,端水送饭,揉腰捶背,真让人痛心不已。
曾记得,父亲为生计奔波常常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冒着生产队“割资本主义尾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走乡串户,给人们做油漆活,挣钱养活我们,供我们上学。
曾记得,父亲为了挣生产队的高工分,同安文大哥,一天跑镰割麦8亩多,当时队长郭俊大叔怎么都不相信,亲自背手跨步丈量核实。
曾记得,父亲为给母亲治病,无钱输血,竟不顾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勇敢地献血抢救母亲于危难之中。
曾记得,父亲为了我们能调回家乡工作,特别是为了我妻子的调动(当时我在西安进修学习),冒着严寒,穿着弟弟从部队捎回的10多斤重的大头鞋,经过4个多小时,步行20多里路,送来调动工作有关手续。
没有忘记,父母亲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干好工作,却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养鸡产蛋,养羊挤奶,喂养照管了两个孙女,一直到上学读书。
没有忘记,父亲第一次教导我的一句话,那是我高中毕业去大队代销店上班时的叮嘱:“咱家的烧火棍比别人家的椽壮,把公家的事看重些。”正是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成了我做人修身的准则和座右铭。
没有忘记,这几年来,父亲去绛帐镇看病、买药,艰难地走在车站、走在半路上,常常被郭管上下两村的兄长、乡亲,或自行车或农用车载去、送回。
没有忘记,父亲在重病染身,卧床不起的日子,常常念叨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照顾过我家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嘱咐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想到这,我觉得我有愧于父亲,有愧于全村父老乡亲,有愧于培养我的祖国。古人说“忠孝不能两全”,我却觉得我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多少年来,父亲给了我那么多,那么真,那么实在的东西,让我一生受用不尽,我却不能给他解除和减轻病痛的折磨;祖国培养教育了我那么多年,我却没有干出什么成绩使父亲欣慰、让乡亲高兴、为祖国添光彩。我真想哭,就是哭不出来,只是眼里常常饱含着泪水。
近两年来,每次回家之后,临走之时,年逾古稀的父亲,总是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站在门口,目光呆滞地望着我说:“啥时回来?”我明白父亲、理解父亲,风烛残年的父亲需要儿子,病困交加的父亲离不开儿子,需要儿子常回家看看,这就是父亲最大的心愿。我强忍着眼泪,强忍着酸楚和苦痛,强装着笑容,安慰父亲说:“过两天就回来。”
从这一刻起,我忽然觉得,我这一生欠下父亲无法弥补无法偿还的感情债。
父亲一步一个磨难,一生一把辛酸;当孤儿历尽坎坷,为人父父爱无限。唯有父亲是无怨无悔的,也是不愧不欠的。
我愧对父亲,愧对乡亲,愧对亲朋好友,愧对生我养我的家园。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儿子没有给父母丢脸的。
我工作在肩,俗务缠身,不能守在父亲身边尽人子之孝,只有默默地为父亲祈祷!为父亲祝福!
作者简介:
郭军仓(1957—)男,汉族,曾任杨陵区政协办公室主任、秘书长,退休后任杨凌示范区慈善协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喜欢舞文弄墨,独品岁月静好,曾主编《后稷传人》(2、3辑),《杨凌颂》诗词集和“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原创诗歌集,著有《邰城议政》文集和《心归慈善》文集(电子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