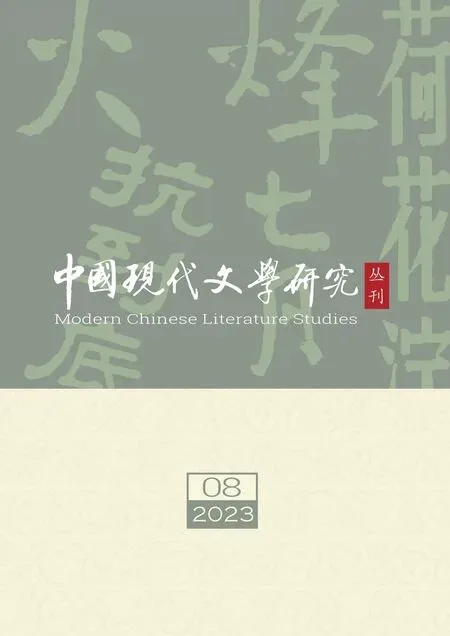追寻“自觉之声”※
——从德语《世界文学图史》到鲁迅《摩罗诗力说》
崔文东
内容提要:青年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借鉴域外文化资源,创成其独特的思想论述,《摩罗诗力说》就是典型的例子。以往的研究揭示了日文、英文材源形塑《摩罗诗力说》的关键作用,本文则强调以舍尔《世界文学图史》为代表的德语世界文学史为鲁迅的书写思路提供了参照。一方面,《世界文学图史》糅合了赫尔德与黑格尔两种关于世界与民族的论述,鲁迅以章太炎的“不齐而齐”“文学复古”思路为中介,接受了赫尔德尊重民族特殊性、复兴民族传统的立场,借助重构世界文学体系催生民族自觉。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图史》浸透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观,张扬想象力与民族性,推崇拜伦主义诗人。鲁迅既标举“神思”“心声”,借文学贯通个体与民族,又以“反抗”“复仇”为依归,建构摩罗诗人谱系及形象,着力激发中国文学的“自觉之声”。
青年鲁迅苦心经营的《摩罗诗力说》在诞生之初备受冷落,但是其思想光芒终究穿透了时间的层云,引发后世读者击节叹赏,激励几代学人精研细究。迄今为止,中外学界已经积累丰厚的解读,研究者或是将文章定义为青年鲁迅揭橥自由精神的发端,或是将其视作横空出世的比较文学名篇,或是辨析作者对于中国诗学理论的贡献。1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德威《现代中国文论刍议:以“诗”、“兴”、“诗史”为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7年第65期。日本学者北冈正子提醒我们,青年鲁迅的精意覃思并非妙手偶得,而是在阅读参考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剪裁熔铸而成。经由她的持续发掘,我们得以了解青年鲁迅如何借鉴吸收域外资源——包括日文、英文编译的民族诗人传记与民族文学史等——撰写《摩罗诗力说》。2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北岡正子:『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摩羅詩力説」材源考』,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版;北冈正子:《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不过,上述研究犹有未竟之意。《摩罗诗力说》蕴含横跨亚欧、纵贯古今的时空体系,连缀跨国的浪漫民族诗人谱系,展现广阔而又独特的“世界”视野。在此框架中,鲁迅凝结出关于世界与民族、天才诗人与民族文学的精妙思考。这一迥异于中国传统的书写思路,是否也参照了域外资源?北冈正子确认的日文与英文材源聚焦于单个作家或国别文学,无法圆满回答上述问题。近年比较文学界对于十九世纪以来“世界文学”资源的探讨层出不穷3参见张隆溪《什么是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引导我们重新审视鲁迅曾寓目的德语世界文学史——约翰内斯·舍尔 (Johannes Scherr)《世界文学图史》(IllustrierteGeschichteder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图史》虽未构成《摩罗诗力说》的直接材源,但是为鲁迅提供了谋篇布局的宏观参照,也赋予了推陈出新的思考基点。概言之,鲁迅透过借鉴德语世界文学史的书写思路,为《摩罗诗力说》确立论述框架,思索如何追寻中国文学的“自觉之声”。
一 德语《世界文学图史》与青年鲁迅的相遇
舍尔如今声名不彰,但在十九世纪德国,实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作家。他尤以擅长书写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而著称,其影响力与《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作者布克哈特不相上下。借助新近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把握其思想主张。4Andrew Cusack, Johannes Scherr: Mediating Culture in the German Nineteenth Century, 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21.首先,舍尔是坚定的民主共和派。181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的符腾堡,一直致力于建立共和联邦制度,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长期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其次,他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德国于1871年方才完成统一,此前一直只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 (Kulturnation),舍尔著书往往旨在强化德国文化认同,他的《日耳曼尼亚:德意志民族两千年生活史》(Germania:Zwei JahrtausendeDeutschenLebens, 1876)就是突出的例子。最后,他秉持人文主义立场,对十九世纪唯物主义、科学主义风潮怀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
在舍尔的文化史著作中,世界文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比较文学学者纷纷指出,舍尔是十九世纪德语世界文学史书写的重要推手。1Peter Goβens, Weltliteratur: 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Jahrhundert, Stuttgart: Metzler, 2011;Theo D’haen, 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B.Venkat Mani, Recoding World Literature: Libraries, Print Culture, and Germany’s Pact with Book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Michel De Dobbeleer, “Old- School Transnationalism? On References to Familiar Authors in World Literary History: East(-Central) European Literature as Presented by Johannes Scherr”, in Dagmar Vandebosch and Theo D’Haen (eds.), Literary Transnationalism(s), Boston: Brill, 2019.但是迄今未见到关于《世界文学图史》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回应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召唤,先编辑各民族诗歌选本,题为《世界文学画廊》(BildersaalderWeltliteratur,1848),广受欢迎(1869年、1885年再版)。随后编写《文学通史》(AllgemeineGeschichtederLiteratur, 1851),迅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世界文学史著作。此书新版往往有所扩充,1895年第9版增加大量插图,遂更名为《世界文学图史》。2此书至1921年共发行11版。Theo D’haen, 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pp.16-17.虽然上述著作展示了广阔的世界主义视野,但其实具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世界文学画廊》就强调德意志民族最能够欣赏与理解“世界文学”,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可谓“世界文学的拥有者”(die Besitzer der Weltliteratur)。3Johannes Scherr, Bildersaal der Weltliteratur, Stuttgart: Becher, 1848, S.vi.舍尔也在著作中推崇民主价值,批评现代文明,足见他的世界文学史书写不仅承载文学追求,也寄托文化与政治理想。
鲁迅与舍尔著作相遇,有赖于明治日本的中介作用。众所周知,明治后期日本大举学习德国文化,德语书籍广泛流布,德语世界文学史也颇受关注。丸善书店《学镫》杂志1904年曾刊文介绍此类著作,作者三并良将《世界文学图史》第10版列在推荐书单之首。4三並良:「世界文學史」,『學鐙』8卷3號,1904年3月。鲁迅赴日留学时受此风潮影响,得以按图索骥,汲取新知。周作人曾如是追忆鲁迅购书经过:“(1906年重返东京后)在旧书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买到一大本德文《世界文学史》(注:第10版《世界文学图史》1熊鹰:《鲁迅德文藏书中的“世界文学”空间》,《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版版本信息为Johannes Scherr,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teratur, Stuttgart: Franckh’sche verlagshandlung, 1900。为免烦冗,文中引用时直接标注中译书名及页码。)”2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47页。,“大概著者是谢来耳(注:舍尔)吧。这些里边有些难得的相片,如波兰的密支克微支和匈牙利服装的裴彖飞都是在别处没有看到过的”3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327~328页。周作人提到鲁迅还购得凯尔沛来斯(Gustav Karpeles)的三卷本《文学通史》,即《文学通史:从开始到当代》(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auf die Gegenwart, 1901)。。
由于晚清中国与十九世纪德国处境类似,都面临打造民族国家、重建民族文化的使命,《世界文学图史》应该颇能引发青年鲁迅的共鸣。4熊鹰:《鲁迅德文藏书中的“世界文学”空间》,《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张钊贻:《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契合的两个案例》,《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不过上述研究皆未聚焦于《摩罗诗力说》。首先,青年鲁迅同样反对专制制度,标举自由反抗,推崇民主共和,致力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其次,青年鲁迅深受章太炎影响,坚信民族传统关乎国家命运,试图以文化手段重塑国民性,践行文化民族主义。最后,鲁迅在留学期间,已经意识到十九世纪文明的弊端,引入文明批判的视野,大力抨击“物质现代性”。我们若聚焦于《摩罗诗力说》,会进一步发现两者思想的亲缘性。鲁迅致力于评介世界文学,塑造民族文化认同,不仅与舍尔异曲同工,更直接从其书写思路中得到启发。正如周作人所言,“这种书籍那时在英文中还是没有的”,德语世界文学史呈现了英语——也包括日语——等其他资源所不能企及的视野与架构,从而为鲁迅的文艺事业提供了“许多助力”。5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327~328页。
二 青年鲁迅对世界文学体系的重构
《摩罗诗力说》涉及的时空极为宏阔,上至古代东方,下至十九世纪欧洲。在我看来,这一书写框架并非鲁迅向壁虚构,也无法从民族文学史、民族诗人传记中获取,而是源自《世界文学图史》蕴含的世界文学体系——更确切地说,是诸多民族文学构成的世界体系——的启发。鲁迅借鉴其书写思路,反思民族与世界的辩证,重构“偏至”的世界文学图景,尝试激发中国人作为“反抗者”的民族自觉。
我们如果仔细辨析《世界文学图史》的篇章结构,会发现舍尔糅合了两套关于世界与民族的学说。其一是赫尔德的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论述。赫尔德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开创者,也是“世界文学”的倡导者。他认为民族语言千差万别,民族文化与文学因而各具特色。他批评启蒙运动倡导的普遍主义与理性主义,从感性、经验的角度体察各民族文化,为其特殊性辩护,强调它们共同促成历史朝向“人性”发展。他坚信民族文学最突出地体现民族精神(Volksgeist/Nationalgeist)与民族性(Volkscharakter/Nationalcharakter),强调民间文学——包括民歌、神话、民间传说等——实为民族传统的载体,只有激活传统(并非摹仿传统),才能复兴民族文学。各民族文学不断交融,最终汇成世界文学的潮流。1Karl Menges, “Particular Universals: Herder on National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Hans Adler and Wulf Koepke (eds.),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Rochester: Camden House,2009, pp.189-214.他编辑的《民歌中各民族人民的声音》(Stimmender VölkerinLiedern)印证了上述思路,书中收录包括拉脱维亚、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法国等民族民歌,展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学图景。德国当时处于分裂状态,赫尔德宣扬民族文化之独特与民族传统之珍贵,其实旨在对抗法国启蒙主义影响,激励德国人重建民族文化认同。
其二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体系。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Geist)不断发展完善、获得自我认识的过程,而精神的本质则是自由。对于黑格尔而言,并非所有民族都参与历史进程。以《历史哲学》为例,书中建构了一个相对封闭、线性进步的世界体系,将世界历史分为东方、古代与日耳曼三阶段:中国、印度等东方专制帝国见证了历史的开端,但是这些民族无法认识自由的意义,历史停滞不前;古代希腊、罗马人开始确立民主与自由原则,将历史推向新的阶段;历史最终在日耳曼民族——以英国、德国为代表——那里达到终极状态,人人意识到自由的价值,精神最终获得自我认识。换言之,唯有日耳曼民族精神才真正具备认识自身的能力。2庄振华:《黑格尔的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177页。如此书所言,目前学界一般遵循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之四分法来把握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体系,本文依据舍尔的论述结构采用三分法。与赫尔德的思路不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体系是线性的、目的论式的,他对不同民族精神的评价相差巨大,尤其强调普鲁士精神的优越性,他的论说也被视作欧洲中心主义的典范。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民族精神、民族性等议题上吸收了赫尔德的观点,但是就基本思路极而言之,两者体现出一元与多元、理性与感性、先验与经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等差异。
舍尔在书中能够将上述两套不无矛盾的思想体系整合为一,主要依靠其独到的论述逻辑。《世界文学图史》与前述《世界文学画廊》的思路并无二致:书中展示的世界图景越广阔,包容的民族文学越丰富,就越能体现德国人独一无二的吸收能力,越能增进德意志民族作为世界文学拥有者的文化认同。换言之,他以文化民族主义统摄世界主义,用世界视野证成民族优越性。
循此思路,他参照赫尔德的观念搭建《世界文学图史》的表层结构,尽可能将各民族纳入其世界文学体系:第一部包括东方、古代世界(希腊和罗马),第二部涵盖罗曼语地区,第三部为日耳曼语地区,第四部包含斯拉夫语地区、马扎尔语地区(匈牙利)和新希腊。具体说来,东方纳入中国、日本、印度、埃及、犹太、阿拉伯、波斯等,罗曼语地区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日耳曼语地区包括英国、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等,斯拉夫语地区涵盖捷克、波兰、俄罗斯等。舍尔引用了海涅的评论:“赫尔德将全体人类视作伟大工匠手中的巨大竖琴,将各民族视作调定的琴弦,他能够从纷繁的音调中体察出普遍的和谐。”1《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216、394、407、399页。他自己的思路与之类似:“文学史是人类本身的理想历史,因为不同民族的文学是其本性的最充分发展,也是其文化事业最佳和最美的成就。”2《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12、2页。
与此同时,舍尔引入赫尔德的民族观念,“民族文学实为民族性的表达与反映”3《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12、2页。,文学作品依据“独特的民族精神与音调”(einen eigentümlichnationalen Geist und Ton)相区别4《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12、2页。。在每章节开端,他都努力结合语言特征与历史处境,概括各民族性,随后论述民间文学,宣称这些作品奠定了民族文学的基调。以斯拉夫人为例,舍尔将其民族性概括为“忍耐”(Duldmut),认为其民歌富有“凄美忧郁的基调”(ein ergreifend melancholischer Grundton)5《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216、394、407、399页。。具体到各节,他又细化判断,譬如波兰文学的特征是“宗教—天主教和民主”6《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216、394、407、399页。,俄罗斯民歌展现了“农民民族”(ein Bauernvolk)特性7《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216、394、407、399页。。在舍尔笔下,民族性并非一成不变,英国就不断通过民族融合汇聚成“强有力的民族性”(einer tüchtigen Nationalität),包含多元的文学特征。1《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4、4页。伴随着文化交流进程,在现代诗歌中,“独特的民族音调”(“eigentümlich-nationalen” Töne)2《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页。往往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学的民族性不再一目了然。舍尔看似以平等的姿态把握各民族文学,在尊重特殊性与差异性的前提下趋近世界文学的理想。
然而就深层结构而言,《世界文学图史》高度依赖黑格尔的论述。3十九世纪德国世界文学史大多受到黑格尔世界体系影响。Matthias Buschmeier, “Western Hist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 Vol.3, No.4 (2018), pp.524-551.舍尔笔下的世界体系不仅关乎地理空间,也隐含黑格尔式的历史进程,呈现了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以及一元的线性进步观念。换言之,全书呈现了“精神”展开的过程,具有“精神史”的特征。4范劲指出弗·施莱格尔也采用“精神史”模式书写世界文学史,影响深远。舍尔是否也受其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范劲:《中国文学史的世界文学起源——基于德国19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史书写的系统论考察》,《文艺研究》2020年第2期。首先,东方、古代与日耳曼世界“三分”结构在书中清晰可见:东方诸国文学大多持续发展到十九世纪,但是只能摆放在文学历史开端的位置;希腊人创造了古代文学的巅峰,受到高度赞美;在欧洲诸民族中,日耳曼文学最受瞩目——德国文学毫无疑问是其代表,英国文学的基本性格也属于日耳曼5《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4、4页。,占据约四成篇幅。其次,舍尔的世界体系奉欧洲文明为圭臬,依然具有封闭性。美洲原住民属于半开化民族,只有绪论稍稍提及;非洲民族则属于未开化之列,甚至没有进入世界体系的资格。
舍尔对民族性的评判也内蕴着黑格尔的声音。舍尔对东方民族颇多偏见,将中国民族性概括为“中庸”(Mittelmäszigkeit),中国人精明、讲求实利,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同样是中庸原则的实现,一成不变。6这些观点反复出现在当时各类德语世界文学史中。范劲:《中国文学史的世界文学起源——基于德国19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史书写的系统论考察》,《文艺研究》2020年第2期。相对于中国人的“理智清醒”(Die behäbige Ruhe),印度民族性体现出“过度的流动性”(einer maβlosen Beweglichkeit Platz),“一种不安分的运动将我们带入令人目瞪口呆的陶醉状态,带入令人窒息的幻觉中,这种感觉在美丽和粗鲁、崇高和卑贱、优雅和丑陋之间摇摆不定”。1《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7、104、104、2、8页。同样是古代文明,他对希腊就推崇备至。书中引用黑格尔的名言,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2《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7、104、104、2、8页。。舍尔强调希腊是自由、人文主义与美的土地,认为希腊人尊重人性,以之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希腊人清晰、适度、统一的精神对应着克制、和谐、透明的形式,它紧贴内容,宛若湿衣衫紧贴着浴女的身体”3《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7、104、104、2、8页。。就欧洲近代文学而言,他着力凸显德国民族精神之优越,既富有世界主义胸怀,“被赋予聆听理解世界诗歌语言的普遍接受力”4《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7、104、104、2、8页。,又极具民族主义内涵,“祖国是所有文化工作的灵魂以及文学的基本母题”5《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27、104、104、2、8页。。如此看来,舍尔的平等姿态有其限度,全书终究还是以欧洲中心、德国中心的视角呈现世界文学。
鲁迅书写《摩罗诗力说》,同样构建了民族文学的世界体系。如北冈正子所言,文章从诸多日文、英文民族诗人传记、民族文学史采撷片段,用作材源。但是将其连缀成篇,就不能不依靠宏观的论述架构,舍尔的世界文学视野恰好为他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文章开篇论述古国文学之衰落,涉及天竺(印度)、希伯来、伊兰(伊朗)、埃及、震旦(中国)等东方民族,与《世界文学图史》第一部相呼应。诸如“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6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6、68页。鲁迅将文章收入《坟》时增加了西文原文,本文引用时均删去。,“其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7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6、68页。鲁迅将文章收入《坟》时增加了西文原文,本文引用时均删去。等论述,更是阅读东方文学衰落史的直观感受。文章主体转入“新起之邦”文学复兴史,尤其是摩罗诗派的跨国流动,涉及日耳曼语地区(德国、英国)、斯拉夫语地区(俄国、波兰)以及马扎尔语地区(匈牙利),与《世界文学图史》的第三部、第四部相映照。与此同时,在论述各民族文学时,鲁迅同样突出其民族性(鲁迅据日文称为“国民文学”“国民性”),譬如摩罗诗人的作品,就“各禀自国之特色”。8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6、68页。鲁迅将文章收入《坟》时增加了西文原文,本文引用时均删去。虽然文章采用《新民说》之类论说文体式,但是连缀不同民族文学、不同民族诗人生平及作品的写法,依然流露出世界文学史的特征。
以世界文学体系为基点,鲁迅得以充分思索民族与世界的辩证。他以中国的历史处境为依归,试图在与世界诸民族的对照中、在反思传统中寻求中国文学的方向。与舍尔不同,鲁迅笔下的各民族皆具有认识自身的能力,只要把握住民族与历史、与世界的真实关联,就能够获得民族之自觉,复兴民族精神(鲁迅据日文称为“国民精神”)。一方面,他认为必须将自身摆放在世界之中,与其他民族相比较。他说:“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67、65、82页。透过深入体察世界文学,中国人将真正理解需要继承何种民族传统,如何引接域外新潮,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他强调必须反思民族文学传统。只有批判性地承继古代文化,才能够新古结合,改造民族性,“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涂,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2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67、65、82页。。如此一来,鲁迅同样打通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67、65、82页。建立世界视野,张扬世界主义,正是发扬民族精神的基础;提倡民族主义,并非旨在证明本民族的优越性,而是试图确立以古老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石的民族自觉。
在上述思路引导下,鲁迅事实上重构了舍尔的世界文学体系。他拒绝欧洲视野下的中心与边缘之分,呈现依据中国视角绘制的“偏至”世界文学图景。4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就古代文学而言,鲁迅开篇即动情回顾印度等东方民族(文中称作“古民”“古国”“古文明国”)的辉煌成就,将其视为世界文学的开端,显示出强烈的连带感,却忽略了舍尔笔下欧洲文学的直接源泉——希腊。就近代文学而言,舍尔书中极为突出法、德两国文学,鲁迅对前者只字未提,对于后者只列举两位反抗法国侵略的爱国诗人。鲁迅在分论中先将重点放在英国,在承认浪漫民族主义由中心流布至边缘的前提下,遴选出扶助弱小、反抗强权的摩罗诗人拜伦、雪莱。随后重心移至俄国、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反抗压迫的国家,将这些民族文学塑造为中国人参照的典范。总的说来,鲁迅最为关切的是受压迫民族如何摆脱奴隶地位5关于青年鲁迅对“奴隶”的论述,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第一章。:对于拜伦而言,“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6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67、65、82页。,其使命即扶助希腊民族重获独立;俄国与波兰皆属斯拉夫民族,“久见屈于强邻,受鄙夷特甚”,“西方奴子 (slave) 一言亦从此出”,1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陈子善、赵国忠编:《周作人集外文》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2页。两民族文学之复兴标志着从奴隶到自由人的转变;作为匈牙利民族诗人的裴多菲,其诗歌的核心意涵之一正是“誓将不复为奴”2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65~66、66页。。结合《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批判“兽性爱国”“崇强国”“侮胜民”的言论3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35页。,可以更进一步看出鲁迅从根本上反对弱肉强食的“主奴结构”,崇尚锄强扶弱。就此而言,鲁迅笔下的“偏至”世界文学体系实为“反抗强权”的民族文学共同体,置身其中能够激发中国作为奴隶/反抗者的民族自觉。
与此同时,鲁迅也打破了目的论式的世界历史进程,消除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截然对立。鲁迅固然承认东方文学的衰落,但其根源不在于民族性之窳劣,而在于遗失抒发心声的能力,“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流转异域,如亡人也”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65~66、66页。。更严重的危机则在于这些古国沉溺于过往的辉煌,自高自大,缺乏自知之明,“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5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65~66、66页。。鲁迅因此转向“新起之邦”寻求启示,他先后将目光投向德国、英国、俄国,但是最为关注的还是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文学的复兴暗示了东方民族的新生,原因在于波兰遭受亡国的命运,与印度互为镜像(《摩罗诗力说》提及“印度波阑之奴性”,《破恶声论》指出“至于波兰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6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35页。),匈牙利乃是黄种,实为中国的同类(鲁迅和周作人曾宣称:“匈加利故黄人”,“匈加利独先氏后名,大同华土”7周作人:《〈匈奴奇士录〉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8页;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 10 卷,第170页。)。既然波兰和匈牙利诗人已经重振文学,那么处境类似的印度与中国也能够复兴民族,将深厚的文化传统转化为卓越的创造。个中关键就在于,中国能否获得作为衰落文化古国的自觉,能否摆脱妄自尊大的成见,打破现状,别求新声。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大体认为,青年鲁迅在借鉴《世界文学图史》时接纳赫尔德的思路,拒斥黑格尔的体系。之所以有此取舍,可能因为鲁迅受到章太炎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章太炎以“不齐为齐”界定平等,将万事万物的独特性、差异性作为平等的前提和条件,与赫尔德尊重民族性的思路相通。1近期有学者论及章太炎与赫尔德的思想联系,参见尚晓进《启蒙与浪漫的张力:民族内部的更新——兼谈鲁迅国民性批判之主题》,《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具体说来,章太炎既反对整齐划一、抹平差异的普遍主义,又排斥承认不平等秩序的强权主义,而是尊重差异,视之为平等的基础。他对于语言文字的态度即是如此:“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2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也即是说,语言文字的性质关乎各民族文化的独特认同,虽然民族有强大弱小之别,语言并无高下之分。3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张志强:《“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论章太炎“齐物”哲学的形成及其意趣》,《中国哲学史》 2012年第3期。正是沿着章太炎的思路,鲁迅拒斥强势文化,反对优胜劣败的世界格局,以尊重差异的平等姿态欣赏各民族文学,甚至更进一步推崇弱小民族的独特文学,突出“偏至”的世界文学体系。
其次,章太炎与赫尔德相似,重视传统资源,尤其是久远的文学传统。他倡导“文学复古”,一方面将“文字”理解为“文学”的固有本质,批判浮华文饰,推崇“质”;另一方面将“国粹”“汉学”“国学”视作种族革命的文化基质,以“小学”为依归,探求古字古义,以激发民族的活力。4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风:《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虽然青年鲁迅对文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他接受了“文学/文化”作为国家民族独立基础这一逻辑,从古代汲取资源。就像赫尔德将古代民间文学视作民族精神的渊源一样,鲁迅认为获得新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在怀古的基础上得以保持民族性,光大民族性。他宣称:“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5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正是以怀古为依归,他吸纳域外资源,探寻民族文学的新路。
三 青年鲁迅对浪漫民族诗人谱系的重塑
对鲁迅而言,《世界文学图史》的参考价值不仅在于呈现世界文学体系,还在于全书浸透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观,描绘拜伦主义的跨国流动。相较于鲁迅选取的日文、英文材源,舍尔之作规模庞大,论述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观最为充分,描绘浪漫民族诗人谱系最为完整。1北冈正子曾指出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论及拜伦主义在斯拉夫民族中的影响,可能启发了鲁迅。不过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和鲁迅藏书目录推断,青年鲁迅应该未曾读过此书,舍尔笔下的谱系应该是鲁迅最直接的参照。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第41~42页。在我看来,鲁迅正是以此为参照,再结合日文、英文及本土资源构建贯通个人与民族的文学观,重塑发出“自觉之声/反抗之声”的摩罗诗人谱系。
舍尔书中对于文学的理解,兼及审美与政治,勾连个人与民族,既富有浪漫主义特质,又蕴含民族主义色彩。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着眼,这两种思路皆可以追溯至赫尔德。首先,赫尔德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与新古典主义彻底决裂的第一人。他反对摹仿论,极力推崇天才诗人的想象力与独创性,这一思路构成施莱格尔兄弟等德国浪漫派的精神源泉。2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舍尔在书中反复援引的正是“想象”(phantasie)3钱鍾书指出这一词汇源自古希腊人的phantasia,本来可与古罗马人的imaginatio并用,到中世纪后期,前者开始指涉高级的、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后者则专指低级的幻想或梦想。在浪漫主义潮流中,这一区别被肯定下来并广为接受,只是在不同语言中用词不同,德语分别使用Phantasie与Einbildungskraft,英语则使用imagination与fantasy或fantasie。钱鍾书:《关于“形象思维”的资料辑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3页。、“独创性”(schaffenden Originalität)、“天才 ”(Genialität)等概念,并且直接将上述理论观点归功于赫尔德,对德国浪漫派反而评价不高。与此同时,赫尔德开创了民族主义文学观。他以语言的共通性为中介,强调诗人个人的独创亦是民族的创获,诗人可谓民族的创造者,为同胞开辟可视的世界,将他们的灵魂握在手中,引领他们走向未来。4Karl Menges, “Particular Universals: Herder on National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Hans Adler and Wulf Koepke (eds.),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Rochester: Camden House,2009, pp.189-214.就此而言,诗人的想象力体现了民族的想象力,诗人的声音凝聚着民族的声音。
舍尔评骘民族文学、作家、文学潮流时,完全以想象力与民族性为标尺。在东方文学中,舍尔冷落中国而肯定印度,原因在于中国人注重实利,毫无创造性,印度人则想象力丰富。中国部分着重介绍儒家经典,只有《诗经》勉强符合浪漫主义的文学定义;印度部分则高度评价《吠陀经》、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戏剧《沙恭达罗》(舍尔特地引用歌德赞美此作品的诗歌)等。在古代西方文学中,舍尔推崇希腊文学而贬低罗马。前者既具想象力,又富民族性,后者则以摹仿著称,又局限于贵族阶层,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同样是“想象力”,由于民族性的差异,也存在高下之分,譬如东方民族的想象力“无法获得艺术的节制与和谐的自我克制”1在东方文学部分,舍尔又往往使用“幻想”(Einbildungskraft)一词,似乎暗示东方民族想象力较低级。《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11页。,希腊人的想象力则富有秩序感。
就作家而言,舍尔继承了赫尔德与德国浪漫派建构的经典体系,极为推崇但丁、薄伽丘、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卡尔德隆、歌德等富有想象力的天才,又尽可能将他们塑造为民族诗人的典范。其中最符合舍尔标准的作家是莎士比亚。舍尔一方面赞美其具有“源源不绝的丰富想象力、思想的深度与热情、能够洞察人类心灵最为隐秘褶皱的眼睛”2《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31、33页。;另一方面将其定位为民族派戏剧的代表,充分吸收民间戏剧的传统,代表作《哈姆雷特》更被视为“日耳曼式深刻的杰作”(das Meisterstück germanischen Tiefsinns)。3《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31、33页。换言之,莎士比亚最为充分地展示了日耳曼人的想象力与民族性。4并非每一位经典作家都能够完全符合舍尔的评价标准,他在论述但丁时就指出:“他的伟大诗篇不是从民族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在深奥博学的温室中生长出来的,意大利人的感性民族性格对此无动于衷、有所怀疑。”《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315页。
就文学潮流而言,舍尔对激发想象力与民族性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推崇备至:
随后轮到英国富有健康元素的新旧诗歌——尤其是莎士比亚诗歌——滋养德国古典主义。以此为开端,也同样以踵继其后的德国新浪漫主义为开端,熠熠的光辉照耀了各国。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伪古典主义被推翻。这些民族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新希腊人——特别是成就最卓越的英国人——利用新浪漫主义民族文学的视野振兴其文学。1《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7~8、454、8、206页。
在舍尔笔下,浪漫(romantik)并非专有名词,而是往往等同于想象力。因此,他将中世纪文学称为浪漫主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则是新浪漫主义。一方面,新浪漫主义具有普世性格,释放想象力与独创性,推翻崇尚摹仿的古典主义。另一方面,新浪漫主义能够与民族性充分结合,足以恢复民族精神,重振民族文学。舍尔视英国为新浪漫主义的中心,对其高度赞赏。他认为彭斯、司各特等作家不像德国浪漫派一样沉溺于对中世纪的怀旧,而是从民族诗歌中汲取源泉,复兴了英国民族文学。在论述新浪漫主义向边缘流动时,舍尔尤为关注东欧诸民族的热烈反响,譬如在匈牙利,浪漫主义“将目光投向过去,借助过往英雄的形象来努力强化民族意识”2《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7~8、454、8、206页。。与之相对,舍尔反感崇尚摹仿的古典主义,对十九世纪兴起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也不以为然:“自然科学对文学施加了更强烈的影响,科学越发带来偏执和缺乏思考的唯物主义追求,很大程度上促成现代文学从在一定范围内完全合理的现实主义转向平淡无奇的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3《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7~8、454、8、206页。这类作品层出不穷,很可能压制民族文学发展。他转而对十九世纪末涌现的富有心理主义、象征主义、浪漫化神秘主义的新文学寄予厚望。
在新浪漫主义诸潮流中,舍尔又特别突出拜伦主义(Byronismus)。他将其理解成一种具有普世性格的风格与主题,构成前后相继的跨国链条,法国作家夏多勃里昂最早奠定基调,又经拜伦、雪莱之手发展成熟,流布四方,“在德国经由海涅与所谓的青年德意志派而发展壮大,在法国的代表是雨果、缪赛和乔治·桑(Aurore Dudevant),在俄国是普希金与莱蒙托夫,在波兰则是密克凯维支、加辛斯基(Garczynski)和克拉旬斯奇”4《世界文学图史》第一卷,第7~8、454、8、206页。。具体说来,舍尔常常用“怀疑主义”(Skeptizismus)与“厌世”(Weltschmerz)来概括拜伦主义——尤其是西欧拜伦主义诗人。以拜伦本人为例,其诗歌核心是失望之情,包括对世界、对人类、对自己的失望。在拜伦生活的年代,旧的体系被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所摧毁,民族精神的复兴又未开出新路,他的怀疑与厌世正是此现代处境的产物,他借助诗歌抒发时代的苦闷,其作品“富含世界性色彩,这对于真正的现代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1《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80、83、412、412页。。当然,拜伦的诗歌并非只有消极意义,舍尔也借用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的负面意见突出其反抗性:“他们凭借病态的心灵与堕落的想象力,对抗人类社会最神圣的秩序”,“激发对宗教的仇恨”,“他们建立的诗派应该称作撒旦诗派(satanic school)”,“以高傲自负、鲁莽不敬的撒旦精神为特征”。2《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80、83、412、412页。
拜伦主义作为新浪漫主义文学的支流,同样刺激民族文学的复兴——尤其是俄国、波兰等斯拉夫民族文学的兴起:“拜伦是连结全部斯拉夫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秘密纽带”3《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80、83、412、412页。,“拜伦创造的类型在斯拉夫人手中层出不穷,并产生了更崇高的形式”4《世界文学图史》第二卷,第80、83、412、412页。。以密克凯维支为例,作为斯拉夫民族最具天才的诗人,他最早打破波兰文坛的古典主义摹仿之风,结合拜伦式(舍尔特别强调并非施莱格尔式)的浪漫主义重振民族文学。密克凯维支饱含忧国热忱,从民族性的角度重思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所以没有陷入拜伦式的怀疑主义,而是以爱国、悲悼为主题。在俄国,自由主义理想与沙皇专制的对立带来的失落促成拜伦主义的流行。作为俄国诞生的最伟大诗歌天才,普希金着力结合拜伦式英雄与民歌传统。莱蒙托夫赓续其道路,在作品中探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感慨天才在社会中的处境。
反观《摩罗诗力说》,我们可以确认文章蕴含了同样的文学评价标准,也同样以诗歌作为文学的典范。概言之,青年鲁迅的文学观既是浪漫主义的,也是民族主义的。毫无疑问,这一思路融合了多种资源5勃兰兑斯《波兰》一书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对鲁迅同样颇有影响。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鲁迅为文学作出定义时,参考了诸多资源。张勇:《鲁迅早期思想中的“美术”观念探源—— 从〈儗播布美术意见书〉的材源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3期。,《世界文学图史》的意义则在于提供一套思维框架。这从文章的核心概念“神思”“心声”可见一斑。“神思”典出《文心雕龙·神思》,指代诗人创作时的形象思维活动。鲁迅标举这一概念,意指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6本文对“神思”的理解与伊藤虎丸一致。伊藤虎丸:《早期鲁迅的宗教观》,《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张猛、徐江、李冬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与《世界文学图史》的核心概念phantasie遥相呼应。“心声”典出扬雄《法言·问神》与《文心雕龙·夸饰》,意指文章或文采。鲁迅在这里侧重外在的抒发表达,可能借鉴了日文材源滨田佳澄《雪莱》的用法1北冈正子:《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第49~50页。,又受到章太炎强调声音之于汉字意义的影响2季剑青:《“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也与舍尔笔下反复出现的声音(如ton、klänge)意象颇有共鸣。
与舍尔的“想象力”“音调”一样,鲁迅所谓“神思”“心声”不仅专属于诗人、天才,也为整个民族所共享,连通个人与民族。相对于舍尔以语言的共通性来证成文学的影响力,鲁迅更突出文学的情感力量。天才诗人是先知先觉者,他们运用神思,抒发心声,“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70、65~66、65页。。心声能够感染他人,原因在于诗歌之于人心就如同乐音之于琴弦,情感受到诗人之声的触动,文学就足以“移人性情”“撄人心”:“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70、65~66、65页。结合《破恶声论》所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5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6页。。我们可以进一步厘清鲁迅的观点:文学源自真实的情感,因此能够促成个人之自觉,又因为情感足以触动他人,文学将最终促成民族的自觉,甚至可以超越国界,激发处境类似的民族。6季剑青:《“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以这套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观为标准,鲁迅评骘古国文学。前节论及,鲁迅打破东方与西方的截然对立,因此在他笔下,各民族皆具有想象力,皆能够发出心声:“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7鲁迅:《摩罗诗力说》,第65页。在《破恶声论》中,他认为神话也源出古民之“神思”,泽被后世:“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2页。东方古国“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最早涌现卓越的民族文学,“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夐,称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希伯来)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8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70、65~66、65页。遗憾的是,“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9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70、65~66、65页。,古国之民渐渐丧失了抒发心声的能力。鲁迅依据同样的标准,衡量中国文学的得失,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他与舍尔类似,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成就评价不高,但是中国人绝非毫无想象力的民族。之所以缺乏杰作,只是由于儒家诗教与社会习俗的压制,“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71、68、102页。他举出《世界文学图史》完全忽略的屈原,称赞其“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2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71、68、102页。,可谓在儒家正统文学之外另辟蹊径。换言之,中国文学亦曾蕴含浪漫民族主义的种子,只是由于环境严苛,未能开花结果,诗人难以充分抒发真情实感,遑论将个体心声传递给整个民族。
同样以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观为依据,鲁迅对拜伦主义/摩罗诗派情有独钟。如前所述,舍尔笔下的拜伦主义最能够激发民族想象力,恢复民族传统,鲁迅对于摩罗诗派的定义更进一步,突出其反抗色彩:
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71、68、102页。在鲁迅笔下,摩罗诗派不再是一种流行风格和主题,也与怀疑主义无涉,而是代表了一种共通的人格典范与文如其人的书写方式,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足以清除压迫奴隶的权势结构。换言之,鲁迅重新厘定了浪漫主义的内核,理想的浪漫诗人出于个体处境的自觉,不屈不挠地对抗强权,为自我及被压迫者争取自由。与此同时,摩罗诗派相较于拜伦主义,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更为紧密,“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加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71、68、102页。诗人的自觉也预示着民族的自觉。用声音意象来描述,他们的作品可谓“声之最雄桀伟美者”“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既是诗人神思的表达,也是民族神思的凝结,既是个体的心声,也是民族之声。凭借其“美伟强力”,有可能引发中国诗人的反抗之声,打破中国的萧条状态。
循此思路,鲁迅事实上重塑了摩罗诗人谱系,与前节所述“偏至”的世界文学体系相对应。舍尔笔下拜伦主义诗人遍布欧陆,鲁迅以“反抗”“复仇”为依归1北冈正子:《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第79页。,完全忽略了作为拜伦主义先导的法国诗人,也未提及德国浪漫派,而是直接以拜伦为摩罗诗派宗主,以雪莱为后继,“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极力突出他们战斗的一面,“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此言始于苏惹,而众和之;后或扩以称修黎以下数人,至今不废”。2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5、85、99页。鲁迅依赖木村鹰太郎《文界之大魔王》与滨田佳澄《雪莱》的描述,将拜伦、雪莱对于宗教正统的背叛转化为世俗意义上对自由的追求,对强权的反抗,以及对奴性的拯救。
鲁迅同样关注摩罗诗力在东欧“反抗强权”民族中的回响,先“入斯拉夫族而新其精神”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5、85、99页。,随后激荡“沉默蜷伏之顷”的匈牙利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5、85、99页。。透过诗人的引领,这些民族先后摆脱奴隶的状态,张扬自由精神。在俄国部分,鲁迅纳入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依据多种日文、英文著作,着重突出富有反抗之情、渴望战斗的莱蒙托夫形象。在波兰部分,鲁迅依据勃兰兑斯《波兰》英译本,选择了密克凯维支、斯洛伐茨基两位“复仇诗人”,刻画亡国之民对于异族统治的报复。将裴多菲界定为摩罗诗人更是出自鲁迅的发挥。因为在舍尔之作以及作为直接材源的李德尔《匈牙利文学史》英译本中,裴多菲都与拜伦主义无涉:前者称其为“匈牙利的彭斯”,后者只提及他的作品与拜伦、雪莱有相似之处。鲁迅将裴多菲纳入谱系,又特地依据德译本概述其小说《绞吏之绳》的复仇情节(舍尔认为此书不值一提),刻意强化了摩罗诗人的复仇特质。
至于摩罗诗人“自国之特色”为何,鲁迅并未充分论述,他更关切的是如何借摩罗诗力激活具有反抗特质的中国民族传统。一方面,鲁迅借用进化论的“返祖现象”,将反抗强权的摩罗诗人之涌现界定为普遍现象:“抑吾闻生学家言,有云反种一事,为生物中每现异品,肖其远先,如人所牧马,往往出野物,类之不拉,盖未驯以前状,复现于今日者。撒但诗人之出,殆亦如是,非异事也。”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6、82页。摩罗诗人不仅仅代表了人的精神进化的方向2北冈正子:《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第82页。,更象征了一种被压抑的反抗传统的复归,一种未驯服状态的返祖现象。另一方面,鲁迅多处暗示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可以汲取本土反抗资源。首先,摩罗作为印度神话中的天魔,是撒旦在古代东方的对应,已经蕴含了复古的色彩。换言之,反抗与复仇诗人不仅仅是西方特产,在东方也有其渊源。其次,鲁迅论述拜伦的性格时,借用木村鹰太郎的文字引入义侠之性,与中国上古侠之传统遥相呼应:“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6、82页。最后,鲁迅在总论中批评了儒家诗学观,暗示屈原开创的文学传统富有独特价值。就此而言,鲁迅期待中国诗人打破儒家诗教的束缚,以“反抗强权”的浪漫民族诗人为参照,汲取对应的本土与域外资源,开拓崭新的文学书写。无论是“至诚之声”还是“温煦之声”,皆能够激发人的自觉、民族的自觉,皆足以打破中国当下的萧条局面。
结 语
青年鲁迅为思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孜孜不倦地汲取域外资源。以往的研究突出日文、英文书刊的关键作用,本文则强调舍尔《世界文学图史》等德语世界文学资源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涵括的世界文学体系与民族性论述、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观与拜伦主义诗人谱系,正是鲁迅酝酿《摩罗诗力说》论述架构的重要参照。一方面,《世界文学图史》糅合赫尔德与黑格尔两种关于世界与民族的论述,鲁迅以章太炎的“不齐而齐”“文学复古”思路为中介,接受了赫尔德尊重民族特殊性、复兴民族传统的立场,构造出“偏至”的世界民族文学体系,试图激发中国作为衰落古国以及奴隶/反抗者的民族自觉。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图史》浸透浪漫民族主义文学观,张扬想象力与民族性,推崇拜伦主义诗人。鲁迅在类似的思路下张扬“神思”“心声”,以文学贯通个体与民族,期待借助文学的感染力引发中国人的“自觉之声”。同时建构以“反抗”“复仇”为特征的摩罗诗人谱系,赋予“自觉之声”以具体内涵。
以鲁迅对《世界文学图史》书写思路的借鉴与重构为例,我们能够进一步辨析鲁迅借鉴域外资源时的创造性。依据今日的眼光来看,《世界文学图史》并非一流之作,但是书中吸纳了赫尔德与黑格尔等杰出思想家的观点,尤其是赫尔德关于世界与民族、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在在引发鲁迅的共鸣。1最近有学者论及鲁迅与赫尔德的思想关联,但同时指出鲁迅并未直接阅读其著作。本文试图揭示鲁迅接受赫尔德思路的路径。李音:《作为民族之声的文学——鲁迅、赫尔德与〈朝花夕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2期。在构思《摩罗诗力说》时,鲁迅以中国处境为依据,既吸收舍尔转介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体系,又拒绝蕴含其中的西欧中心论,既接纳舍尔转介的“浪漫民族主义”标准,又重新厘定“浪漫民族主义”的内涵。不同于舍尔借德国人的世界视野证成德国民族性的优越,鲁迅几乎是在回溯到赫尔德原初思路的基础上开展其思考,在把握世界的同时审视民族传统,探寻民族自觉。由此可见,青年鲁迅善于借助纷繁芜杂的二手研究,提炼一流思想家的观点,并在对话的基础上锤炼自身的论述,以世界为参照锚定民族的出路,以民族为依归拥抱世界。这样的探索不仅体现于《摩罗诗力说》,更见证了鲁迅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