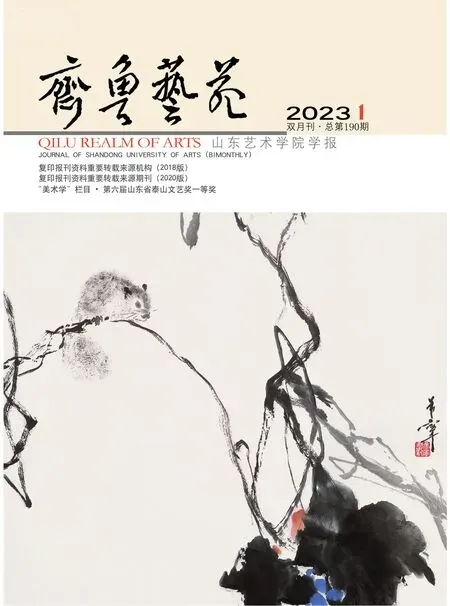冷眼/恻隐,解构/建构:张爱玲与许鞍华审美创作之异
王 颖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如果把张爱玲的三部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第一炉香》和许鞍华由此改编的三部同名电影做比较,可以看出两位不同媒介的创作者审美理念和创作手法层面的诸多不同,这种不同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旨的表达上。张爱玲“冷眼”看自己的人物,对笔下的角色不留情面也绝不伪饰,冷静而疏离;而许鞍华则对人物有“恻隐之心”,习惯性地“为主角讳”,宁肯压扁人物的深度也要增加其道德感。与之相对应,张爱玲的小说致力于解构意义,尤其是解构“人性的庙堂”,人物追逐虚荣、情爱、物欲满足,而最终总是堕入虚无之中,没有救赎的希望。但许鞍华总是在张爱玲的废墟之上重建庙堂,讲述正面故事和真挚情爱。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张爱玲的小说与许鞍华的改编电影之间有着40—80年的时间差,但许鞍华的审美和创作手法更为传统和保守,张爱玲的小说则具有更多的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特征。
一 、《倾城之恋》:反讽小说与明星偶像剧
按照傅雷的看法,《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一个“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1](P404-419)范柳原则是张爱玲作品中男性“空心人”系列中的一个。《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金锁记》中的四爷,与范柳原一样,都属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畸形的男女经济和政治地位所造就的“空心人”角色,被财富(或者对财富的欲求)所束缚、失去真正付出感情的能力。白范二人一个精明世故,企图通过“爱情”为自己谋得一个安全的经济地位,一个则在拥有财富之后空虚无聊,无法满足于普通的男女关系,想“调更高级的情”却不愿为此负责任。但电影版《倾城之恋》显然有意将两个角色的人物光谱调亮,补充女性角色的“前史”使其所作所为更令人共情,强化男性的担当和责任感来掩盖其性格中的轻浮。在对张爱玲小说的三次改编之中,许鞍华这种重塑人物的理念一以贯之,从未改变。
在电影中,成年白流苏出现之前,首先出现的是幼年白流苏,她随父母去看戏,却在人流中与父母失散。俯视镜头中小小的白流苏站在马路中间,孤独而迷茫地看着四周。显而易见,将小说中一笔带过的人物前史郑重地放在片首,是许鞍华给白流苏所定下的人物基调。从这种带着恻隐之心的角度看过去,人物的种种“疲乏”“苟且”“小智小慧”都可以被理解、接受和共情。也是从《倾城之恋》始,许鞍华形成了相当固执的给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追讨“前史”的癖好。“前史”的补充,使人物的行为更加容易得到观众的原宥,减少人性的黑暗面而增加其道德感。而范柳原在电影中也变得更有担当。小说中描写两人在香港沦陷时被困在浅水湾饭店,一起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躲避子弹:“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2](P48-84)电影中则强调范柳原在英日两军对峙时处处保护流苏,甚至和英军一起并肩战斗。人物光谱的调亮和“追光”,使得电影《倾城之恋》的质地,更类似于俊男美女的明星偶像剧。
二、《半生缘》:世情小说与中规中矩的爱情电影
《半生缘》是张爱玲对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十八春》的改写。《十八春》1951年连载于《亦报》,在张爱玲的作品系列中,属于不多的偏“通俗向”的世情小说。在这个故事中,张爱玲似乎收敛了她一贯的“冷眼”,出乎意料地塑造了近乎完美的人物和爱情。世钧和曼桢对感情专一认真,两个人不爱钱,也不爱慕虚荣,爱情的失败多半应归咎于命运的阴差阳错和旧宗法社会中的世俗偏见。这对善写“戴着金子枷锁的囚徒”的张爱玲来说,算是难得的心慈手软。《半生缘》偏“通俗向”的写作方法,让这个故事的气质和许鞍华的审美取向更为接近。电影《半生缘》虽毁誉参半,但在许鞍华的三部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作品中,仍然属于接受度最高的一部。然而,张爱玲对人物少见的“宽容”与许鞍华对角色在道德感上的要求,似乎仍旧有一定距离,她仍需对人物按照自己的创作理念做一番修饰和润色——将男女主角进一步完美化,并赋予反派角色丰富的“前史”以增加其道德感。
在张爱玲的原作中,世钧的被动、怯懦甚至孩子气,都给以细节化呈现。他的不成熟导致他在事实上无力抵抗自己的旧家庭对于曼桢家庭的偏见,是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小说写到他第一次带叔惠回南京时,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两个人和翠芝看电影,翠芝鞋跟坏了,要他帮忙回去拿替换的鞋,世钧对原本就讨厌的翠芝心生怨怼,拿鞋回来后便任性地甩开两人,一个人重新看了遍电影。而在电影中,世钧是主动要求去拿鞋子。电影中的世钧,显然更为完美,没有近乎孩子气的任性,是深情、诚恳而善良的理想恋人形象——爱情故事中的标配。相对于男主角世钧,电影版《半生缘》改动更大的是女主角曼桢。在小说中,曼桢后来又主动嫁给了强奸自己的鸿才。张爱玲写到这个情节时,似乎又恢复了一贯的冷峻,曼桢做出这个选择,除却绝望、自暴自弃甚至自虐,还夹杂着女性的虚荣心,误以为自己在鸿才心中和别的女人“总是两样的”,他做犯罪的事是因为“爱的她太厉害的缘故。”(1)“曼璐从前曾经一再地向她说,鸿才对她始终是非常敬爱,他总认为她和任何女人都是两样的,他只是一时神志不清做下犯罪的事情,也是因为爱的她太厉害的缘故。像这一类的话,在一个女人听来是很容易相信的,恐怕没有一个女人是例外。曼桢当时听了虽然没有什么反应,曼璐这些话终究不是白说的。” 参见:张爱玲.半生缘[M]. 北京:北京文艺出版社,2019,P281。女性常常过于轻信“男人爱自己”“自己和别的女人总是两样”,从而导致某种喜剧性的悲剧时刻,是张爱玲所常常描写的。这是同样作为女性的她,对于自身所处的性别最深的观察,最彻底的“自嘲”。这一笔既是近乎完美的曼桢的污点,也是曼桢作为一个角色最有人性深度的一幕。而在电影中,这个情节被有意识地淡化,只以曼桢的画外音——“我决定留下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孩子”一笔带过,曼桢在这段荒唐的婚姻中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都省略不谈。许鞍华近乎执著地维护着曼桢的纯洁,为“主角”讳,拒绝去表现人性中最复杂和隐晦的地方,这是编导对人物的体恤和同情,但也体现了她过于保守和传统的创作观。电影上映时,即有影评人评论“不拍这一大段,减少了难堪,尊重了人格,但不是《半生缘》的全貌,少了一层最重要的人性转折,全片剧力亦轻了浅了。这小说还可以再拍,编导显然要有更大勇气和技艺,才能把这段拍得成功”[3](P283-284)。
小说《半生缘》中,曼璐和《金锁记》中的七巧、《第一炉香》中的姑妈属于同一个系列的人物——“带黄金枷锁的囚徒”。她们都近乎本能地扯上其他人给自己殉葬,“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4](P85-124)。张爱玲在这部总体偏“通俗向”的小说中,虽对曼璐手下留情,但仍勾勒出了一个七巧的影子,曼璐是小说《半生缘》中最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她决定牺牲妹妹、吊住鸿才的心理,类似于七巧拉拢儿子长白,(2)“她这次是抱定宗旨,要利用她妹妹来吊住他的心,也就仿佛像从前有些老太太们,因为怕儿子在外面游荡,难以约束,竟故意地教他抽上鸦片,使他沉溺其中,就像鹞子上的一根线提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他飞得远远的不回来了。” 参见:张爱玲.半生缘[M]. 北京:北京文艺出版社,2019,P200。她离间世钧和曼桢的手法,也和七巧离间长安和童世舫类似。在小说中,世钧到鸿才府上寻找曼桢,曼璐的出场在作家的笔下是非常郑重、浓墨重彩的。在漫长的气氛渲染和等待之后,曼璐从房间的另一头远远走来,在世钧看来,此时的她是恐怖的“红粉骷髅”。这不禁令人想起《金锁记》中童世舫到长安家里拜访的一幕,童世舫看到七巧的瞬间,“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5](P85-124)。然而在电影中,许鞍华体贴地为曼璐安排了前史,讲她为了养活一家子人,如何痛心疾首地结束她和豫瑾的恋爱。在小说中,仅用一笔带过的略述,被扩充成具有丰富细节的情节段落之后,曼璐不再是七巧那种“彻底”的角色,“骷髅”和“疯人”的意象不复存在,她的冷酷和心理变态,某种程度上变得可以被理解和被宽宥。
三、《第一炉香》:苍凉沉郁的处女作与浮夸崩坏的青春疼痛电影
作为三部改编之作中口碑最差的一部,《第一炉香》的改编,暴露了原作者和改编者之间审美取向和创作理念的巨大分野。许鞍华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出于“温情”和恻隐之心,致力于填补人物身世背景的“空白”,以期美化人物的感情,为人物的心理变态,寻找值得同情的原因,并把一切复杂幽微、处于变化之中的两性关系,固化为爱情——这种极其传统和守旧的审美理念及过于固执和单调的创作思路,消弭了原作对人性和命运所做的细致深刻剖析,也失却了其苍凉沉郁的美感,从而导致了电影的全面崩坏。
作为张爱玲小说处女作的女主角,薇龙的形象是独特的。虽然《第一炉香》本身脱不了对《红楼梦》的模仿与“鸳鸯蝴蝶派”的影子,然而“薇龙”这个角色却完全是新的,她的堕落,既不属于旧小说,也不属于“五四”之后的启蒙小说,她的选择和困境充满了现代性。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上了另一个人的当,看着自己体内的贪欲、情欲和虚荣被唤起,却像被束住了手脚一样无能为力,只能任自己掉入深渊。薇龙的清醒和她行为失控之间的反差,是小说《第一炉香》最具有现代意味的部分。人物命运的悲剧底色,来自于理性后面黑暗而广漠的潜意识能量。薇龙的悲剧,本质上是一场自我杀戮。然而在电影中,薇龙这个人物被扁平化、庸俗化,她的每一步通向地狱的选择,都是为了爱情飞蛾扑火,人性里那些复杂、幽微的部分和不可理喻的瞬间,都被实实在在地正面表达出来,当女主角在电影结尾的时候对着夜空喊出“我爱你,你这个没良心的!”这句粗俗而乏味的话时,中国现代小说中珍贵稀有的人物形象“薇龙”便已经彻底死亡。
小说《第一炉香》在全知叙事视角之外,主要采用了薇龙的限制视角来叙事,乔琪乔的角色在文本中主要存在于其他人的叙述之中,很少脱离其他人的视角而独立出现,当他第一次正面出现在园会的时候,小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但电影则花更多的笔墨塑造乔琪乔,目的便是给“空心人”“填空”,似乎要力证“空心人”只是表层,撕去这表层之后,便是真实的血肉。为此,编导给乔琪乔创造了一个遥远的、“在葡萄牙的某个山头放羊”的妈妈,他内心深处思念她,用她留下的梳子梳头发,保留着她的镶嵌在精美相框中的照片,甚至在父亲夺走他心爱的宠物蛇的时候,发泄一般地大声喊妈妈。在原作中,乔琪乔是怕蛇的,但是许鞍华特地叮嘱编剧王安忆,按照何东家族的传说,为乔琪乔设计一个养蛇的细节,他养蛇三年,看到蛇就会露出不属于“空心人”的发自内心的温暖笑容,被“误读”为“冷血动物”的人类与真正的冷血动物之间有着感情交流。当蛇被父亲令人放走,他无奈而无助,此时又用大特写给出父亲对他冷冷关上的窗。这种种细节,包括他在无聊时给无名墓献花——都是在给他性格上的缺陷做注解。原生家庭爱的缺失、对金钱和未来的不安全感,使他的冷酷和阴沉变得情有可原,而这与张爱玲的创作理念背道而驰。原作的悲剧感,很大程度上附着于这个事实之上:薇龙天真地以为自己的真情可以唤起乔琪乔的真心,然而他表层是个“空心人”,内里也是空心,没有奇迹发生。畸形的社会和与人类共生的人性弱点,造就无可救药的“空心人”,“空心人的心真的是空的”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前所述,小说《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和七巧、曼璐一样,是“黄金枷锁的囚徒”,她一出场就是性格变态的,“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6](P1-47),一方面对所谓“爱”需求无度,一方面又做事不择手段,戕害亲人时格外有报复的快感。许鞍华贯彻她给人物追讨前史的创作习惯,为姑妈补充了两段有关葬礼和婚礼的闪回,并且经过精巧的设计,力图使姑妈和薇龙之间,构成镜像关系。第一段闪回被放置于乔琪乔和薇龙初会的夜晚,平行蒙太奇中,薇龙尝试了初夜的滋味,奏响“地狱进行曲”,而姑妈仿佛对此有所感知,在噩梦中惊醒,独自一人在客厅中逡巡,其父亲葬礼上的情景,在此时作为闪回插入——家人鄙弃甘于给人做小的她,愤怒和屈辱令她战胜悲痛,扔掉断了跟的鞋,走上和整个葬礼人群背道而驰的道路。这倔强的“背道而驰”,甚至让姑妈的形象,附着上了女性独立的意味。第二段闪回则被安插在薇龙和乔琪乔的婚礼之中,看着侄女被自己一路操纵送入地狱,她想起自己作为姨太太嫁入梁家时所遭受的屈辱。这两段闪回,都在为她性格的畸变背书,力争要挖出畸变之后那作为女性的曾经纯洁而无助的时刻。同时,这两段闪回的设计,又提出了一个在原著中并未被涉及的命题:姑妈和薇龙真的是互为镜像吗?为了强化这个观点,电影结尾时,在上海酒店正式走上交际花道路的薇龙,幻觉中屡屡和姑妈迎面走过。“互为镜像”“命运轮回”并不总是能够深化悲剧。在原作中,姑妈的悲剧是属于传统中国的,但薇龙的故事里包含着潜意识、本能的狂热和命运的无力,更具有现代性的悲剧美感。一定要把两个女性角色以“镜像”的形式勾连在一起,看似是对电影结构的强化和主题的深入,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庸俗而刻板的叙事俗套之中。
作为一篇4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第一炉香》改编成电影,显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充实。许鞍华将她塑造人物的惯用方式,延续到配角人物的塑造上,周吉婕、睇睇和睨儿的形象,经过改造之后,都变得面目全非。在小说中,周吉婕只出现了一次,身份是乔琪乔同父异母的兄妹,她不快乐,对自己的混血儿身份非常讨厌。这个人物作为混血儿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困境——精神上处于文化的无依之地,身体上又困于强烈的欲求而不得自由,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乔琪乔性格的注解。电影中的周吉婕更改身份,成为乔琪乔的亲妹妹,除了作为薇龙和乔琪乔关系的“吹哨人”的形象出现之外,主要承担的是救赎功能——许鞍华所提出的对混血儿精神上失乡和肉体上困于欲望的最终解决方式,是让周吉婕做了修女,皈依于宗教。在纪录片《好好拍电影》中,许鞍华说:“我自己觉得所有的电影,其实都指向救赎,就是说,你怎样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超脱出来,而不是沉溺在这个地方。”救赎常常是经典小说的主题,然而张爱玲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真正有效的救赎。“救赎”和张爱玲所有作品的指向背道而驰。救赎的主题是经典然而又是保守的,它是创作者对人物的体恤和同情,也是创作者凌驾于人物本身的性格和命运之上、对人物做出的难免会有一厢情愿和居高临下嫌疑的升华。但许鞍华在《好好拍电影》中也讲过:“我不会指示别人找宗教解脱。”理念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似乎凸显了许鞍华从业多年却从不做自己导演作品的编剧的弊端。
小说《第一炉香》中,梁太太身边有两个丫鬟睇睇和睨儿,其人物塑造看得出是取自《红楼梦》中的晴雯和袭人,有意味的是,电影《第一炉香》对睇睇和睨儿的改编,暗合了晴雯和袭人在当代各种影视版本中被解读/误读的形象。小说里描写睇睇被打发走的一幕,薇龙远远地看到睇睇站在院子里,等着父母领她走:“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脸上薄薄地抹上一层粉,变为淡赭色。薇龙只看见她的侧影,眼睛直瞪瞪的,一些面部表情也没有,像泥制的面具。看久了,方才看到那寂静的面庞上有一条筋在那里缓缓地波动,从腮部牵到太阳心——原来她在那里吃花生米呢,红而脆的花生米衣子,时时在嘴角掀腾着。”[7](P1-47)命运瞬间跌落谷底的女仆,在若无其事一般地吃花生米——这里的世界是混乱、矛盾、不可理喻的。但在电影中,这一幕却被表现为色调明确而单一的底层女性对主人的阶级对抗——犹如现代影视剧中晴雯的被逐出常被简化为晴雯和王夫人之间的阶级矛盾一般。在小说里,睨儿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她不但能把梁太太哄高兴,还能和薇龙闺蜜一般相处,转眼又能和乔琪乔老练地调情。但她在电影中也不免于和睇睇一样角色被简化的命运,和乔琪乔私通事发之后,她在姑妈面前像烈女一样要自梳明志,当乔琪乔婚后又想上她的床的时候,她则摇身一变为拴着红头绳的白毛女,甚至险些要“以死抗暴”。
四、“解构”中的悲悯与“建构”中的单一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力来。”[8](P172-177)而出于对人物的体恤、同情,以及对人物命运的恻隐之情,或许更多是出于审美和创作的惯性,许鞍华“代替他们创造力”,洗脱他们阴暗和毁灭的气质,“校正”每个人物的光谱,将其调亮并给以追光,力求让每个人物都变得“情有可原”。这样的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只能停留在爱情剧的层面上,张爱玲所一贯的对两性关系、爱情传奇的解构,在电影中又重新被建构起来,一切复杂暧昧的情绪、氛围,都变得具象化简单化,原作中的沉郁和苍凉消失殆尽。
张爱玲善写两性博弈。《倾城之恋》中,女性在博弈中完全落了下风,如果不是香港的陷落,这故事本来要以女性的惨败而告终,“不明不白,猥亵,难看,失面子的屈服”[9](P135-137)。然而在电影中,原作中的反讽消失不见,两性博弈变成了真正的“倾城之恋”,月夜调情拍成了持西方爱情自由观的男性对守旧女性的启蒙,侥幸的所谓“成功”拍成了励志的鸡汤。
事实上,许鞍华对此有过反思。在接受采访时,她谈及《倾城之恋》的失败:“最大的教训是我没抓住作品的精神,那个作品的精神其实是很西方、很讽刺的,而不是缠绵的大悲剧。像它的名字(连名字都是讽刺的):说两个狗男女,他们互相斗智,到最后突然就不斗了,因为打仗了,然后就成全了他们的姻缘。就是这么简单,但你若拍成大的英雄美人,就全错了。可是那时候,我还残留着浪漫小说的概念,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拍得很浪漫。”[10](P1-36)
然而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两部改编作品中,许鞍华显然没有能够吸收《倾城之恋》失败的教训,仍然孜孜不倦地将原作所解构的意义,在电影中再一一建构起来。《半生缘》在西方没有得到理想的评价,许鞍华自己在采访中说:“《半生缘》就被威尼斯电影节拒绝了,他们本来满怀热情请我把这部电影带到威尼斯,看过之后却觉得这是一部很普通的爱情电影。”在美国,《半生缘》则被评价为像《罗马假日》那样“感人的、中规中矩的爱情片”[11]。
《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同样是写两性博弈,“是很西方、很讽刺的,而不是缠绵的大悲剧。”但许鞍华从创作伊始,就认定“这个故事如果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它就没有骨感、没有剧情了。”甚至想要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弥补“从来没有好好爱过”的人生遗憾。[12]为此她修饰和润色人物,薇龙带一点自私和顽固的沉沦,变成了对爱痴情,乔琪乔那行尸走肉般的放浪也消失不见,两性博弈变成了两个原生家庭残破的孤独男女、畸零人互诉衷肠,沉沦变成了为爱牺牲。制片方在宣传的时候,也是以”爱不是一个人的卑微,而是两个人的勇敢”“给爱而不得一个纪念日”作为主题来推广这部影片。
对改编自小说的电影而言,忠实原作既不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也不是判断改编是否成功的标准。但原作者和改编者之间审美理念和创作手法过于不同,则会使改编的结果充满不确定的变数。张爱玲的创作是以“解构”为目的的。她致力于解构各种经典叙事模式,《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即是有意识地对“终成眷属”的爱情传奇的解构。她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长篇《小团圆》,题目即来自对中国传统戏剧故事中所谓“一美、二美、三美、大团圆”的解构。然而,解构一切之后,张爱玲在废墟上还是要点亮一根蜡烛,废墟之中昏暗摇曳的灯光是她尽力要表达的感觉。《小团圆》通篇在解构所谓爱情,但张爱玲言“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13](P1-13)。白流苏和范柳原结婚是为了“长期饭票”,但也并不是没有爱;薇龙看透了乔琪乔,也明白自己的牺牲没有意义,但“她也有快乐的时候”。然而就许鞍华的审美思维看来,这点幻灭之后的东西,显然不够以支撑一个故事,必须对人物进行调整和校正,务必建构起实实在在能够支撑人生、产生意义的两性关系。张爱玲的解构里藏着深切的悲悯,许鞍华对人物的“原宥”和对“建构”的执着,虽厚道却难免单调。
结语:大众文化建构与艺术审美内驱的迭合博弈
许鞍华曾经说:“很多时候文艺创作同读者是一种缘分。你特别觉得某作品有吸引力,就应该拍它,因为这肯定是你自己的看法跟作品有共鸣,你才觉得作品特别吸引人。拍它即是拍自己的体会,很值得。我看事物越来越接近她(张爱玲)的attitude。”[14](P75-90)如今看来,这或许是自我误读而导致的对他人文本的误读。作为风格多变的导演,许鞍华最令人称道的杰作《女人四十》《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都是用温情现实主义风格,讲述充满日常生活感的故事,胜在形式朴素而情感内敛,这样的作品才令人感受到许鞍华的“作者性”和属于她自己的“attitude”。
另外,除却原作者和改编者本身审美理念和创作手法的不同,“建构”和“解构”,与小说和电影作为不同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又有着关系。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被大众所接受才有再生产的能力,而“建构”是大众文化的本质。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被公认最成功的一部——李安的《色·戒》,也是将原作中所解构了的“家国”和“两性”关系重新建构起来,并将两性关系的建构作为意识形态对个人剥夺之后的唯一救赎之可能。因此,除却改编者的审美和认知的限制,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亦是对作品最终呈现状态的重要限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