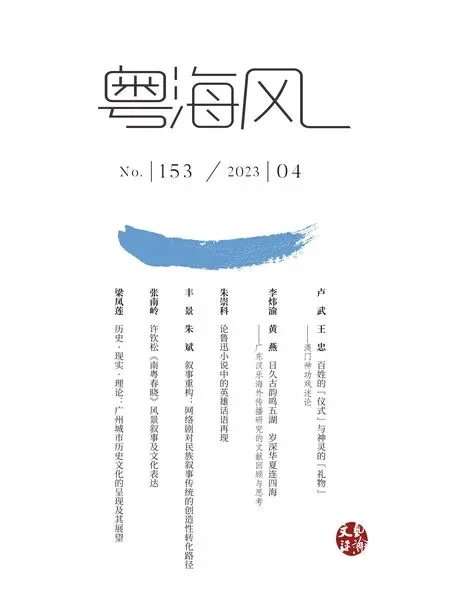百姓的“仪式”与神灵的“礼物”
——澳门神功戏述论
文/卢武 王忠
说起戏曲,就不得不谈被誉为“南国红豆”的粤剧。2009年粤港澳联合将粤剧成功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大湾区一张生动鲜活的文化名片,也是联结粤港澳三地民众情感的纽带。粤剧主要以剧院粤剧、私伙局粤剧(民间自发组织的曲艺社)、神功戏粤剧三种方式存在。时至今日,粤剧已成为澳门本地文化的重要印记,其在澳门依然活跃的表演形式主要是神功戏。整体来看,有关澳门神功戏的研究较为稀缺,几乎都被囊括在粤剧研究中,或泛泛而谈,或一笔带过。神功戏粤剧的传承与发扬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建人文湾区”的重要举措。澳门目前仍有七间庙宇的神诞保留着上演神功戏的传统,在传统习俗式微的现今,这份坚持尤显难能可贵。
一、神功戏在澳门的发展论述
粤剧在澳门起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早在400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便在著述中论及澳门的一种戏剧表演。他在1582年首次抵澳,“他(利玛窦)说的戏剧表演,极可能就是粤剧的前身。”[1]最迟到19世纪30年代,粤剧在澳门已十分普及并深受民众欢迎。[2]中国戏曲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揭示了中国戏曲和巫觋祭祖的关系,认为戏曲脱胎于宗教仪式、巫术舞蹈与神灵崇拜。依据澳门议事厅、澳督的谕令以及报章记载,澳门戏曲特点之一便是酬神演剧多。据1852年的《中国丛报》所载,澳门的莲峰庙、火神庙、妈阁庙、土地庙、金花娘娘庙等处都有戏曲演出,一次演出通常持续四日到七日不等。[3]

图2 农历四月初八谭公诞,谭公庙前架起的花牌和彩旗。
千百年来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都会有一些类似祭天祭神的活动,这是戏曲的发源,戏班对天地鬼神的敬畏更为虔诚,无论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均如此,神功戏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神功戏这个名字实际是广东班的叫法,一般农村碰上大祭或者神的诞辰,就得请戏班来演神功戏。神功戏又称酬神戏,“神功”的意思是神做的功德,是百姓为酬谢神恩、祈福禳灾而举行的一连串活动。神功戏按筹办性质可以分为神诞庆典、太平清醮、盂兰打醮、庙宇开光、传统节庆等。神功戏在澳门主要以神诞庆典的形式存在。为神灵的诞辰举办庆贺活动,从来不是澳门地区独有的仪式,不论南北地区,贺诞总是离不开出巡仪式、表演娱乐和大摆宴席,仿如一场为神灵而设的“嘉年华”。当然,由于各个地区环境不同,内容也有差异。虽然澳门地区贺诞的规模远逊于内地,但仪式更为原汁原味,百年的传统一直在戏棚之中传承。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已有400余年,当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众多中式庙宇与西洋教堂兼容并存的盛况,作为岭南地区的华人社会,供奉佛祖、观音、天后、北帝、关帝、女娲、吕祖、土地、太岁、三婆、鲁班、金花、济公、包公、华佗、医灵、华光、财帛星君、谭公、康公、石敢当等神祇的庙宇、宫殿、神龛一应俱全,出现了“一庙供诸神”的奇观。
澳门神功戏历史悠久,关于神功戏活动的记载有较直接的文献可考:沙梨头土地庙大殿内撰于嘉庆年间的《重修澳门沙梨头社稷神坛碑记》、公局新市南街关帝庙刻于道光年间的《重修三街会馆碑记》、十月初五日街康真君庙的《澳门康真君庙创建暨奠土各收支数总列碑记》《康真君庙奠土喜捐醮戏金碑记》(时间不详)均有记录,河边新街福德祠保存有一块光绪年间由“演戏公司”赠送的木匾,莲溪庙也有道光、咸丰年间演戏值理的贺匾,这些都是佐证。澳门贺诞酬神的历史,早在17世纪时已传到欧洲,1695年意大利旅行家杰梅利·卡雷里(Gemelli Carreri)游历中国后,回国编写了《环球旅行记》,其中记录了在澳门上演的一场大戏。[4]1839年在澳门旅居的法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尔杰(Auguste Borget)曾详细描绘澳门各消费层次的市民观赏神功戏的情形,他写道:
允许在庙宇附近搭戏台……和尚们常常在庙院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看戏……社会各阶层的人混杂在那里,有乞丐,有瞎子,有海员,有游客,甚至于还有穿着豪华的阔佬。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大家熙熙攘攘挤成一团……观众对戏极其有兴趣,倒不是鼓掌和嘈杂声说明了这一点。[5]
中国人太喜欢看戏了,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就爬上了戏台的竹棚上。后面来的人则要那些已经爬在竹棚上的人再爬高一点。这样竹架上像戏院里的包厢一样挤满了人。尽管他们需要使尽全力才能使自己停留在那危险的地方,他们还是全神贯注地看戏。[6]
神功戏是市民的文娱消遣,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每年的神功戏,吸引众多街坊前去观看,澳门神诞已成为澳门民众的狂欢节。神功戏及所衍生的各种游戏、歌舞等民俗活动,凸显了神诞与神功戏的世俗化和娱乐化。澳门的神功戏往往与舞龙舞狮、飘色巡游、摊位游戏、敬老宴会等同场举行,神圣信仰背后是民众世俗的、喜庆的娱乐和狂欢,澳门各时期神功戏活动的兴盛在文献中均有记载:
照得本澳前数日华人建醮庆闹,经有中外数万人之众前来看会,所见多是华人。因此次四方杂处,中外云集,幸藉平安,并无忧心之事。[7]
连夜澳中各商户虔奉关壮缪、包孝肃、华元化先医、康真君各神牌像,巡游全澳,自十四晚而止。每夜灯光灿然,明星万点,皆系各行店备烛助庆,遣伴随行。[8]
十四晚在火船头旷地内,某八九行迎致小狮,在此跳舞,焚烧炮竹至数千万响,计时约一打钟之久……于时旦见火光一片,金鼓喧腾,并炮竹声而震耳……围而观者至数百人,皆拍掌而喝彩。[9]
由此可见,澳门神功戏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据史料记载,莲溪庙、莲峰庙、康公庙、火神庙、包公庙、金花娘娘庙、石敢当庙、药王庙等都曾举办过神功戏。目前澳门主要有七间庙宇的神诞仍在举办神功戏,包括沙梨头土地庙和雀仔园福德祠的二月初二土地诞、凼仔北帝庙的三月初三北帝诞、妈阁庙的三月廿三天后诞、路环谭公庙的四月初八谭公诞、大三巴哪吒庙的五月十八哪吒诞、新桥莲溪庙的九月廿八华光诞。其中百姓对土地和妈祖信仰尤甚,土地与海洋正好反映当地百姓对生存生产的基本欲求,文献记载:
沙梨头土地庙前搭起了高大的七彩牌楼,四周张灯结彩。中午,众街坊善信扛着整只烧猪,带备三牲酒醴、庶馐饼饵和香烛纸钱等祭品,到土地庙虔诚上香酬神贺诞。[10]
查旧日到庙贺诞之烧猪,每逾三四百只之多云。而海上渔民,以天后为海神,故对天后诞,更为高兴。当澳门渔业兴盛时期,妈阁海面,帆樯千百,密泊如织。盖渔船出海捕鱼,虽至远亦必归来贺诞,灯笼串炮,瞩目喧闹。[11]
庆贺活动通常会持续几日,其中又以神灵的诞辰之日最为热闹非凡,上演的神功戏剧目繁多,故事性、审美性与思想性兼备。中国百姓具有“乐天”精神,所创作的戏曲也往往具备乐观色彩。体现在神功戏中,一方面要安排一些喜庆热闹场面,另一方面则喜好大团圆结局。内容上大多包含善恶到头终有报、有志者事竟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等主旨以符合传统戏曲“劝人伦,成教化”的道德追求,这些是民众期待、信赖因果循环的结果,既可以满足百姓的娱乐需求,又可以增强他们的生活信心,引人向善。剧目大致可以归纳为4种:一是演绎经典传说,如《七月七日长生殿》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演绎;《断桥》是白素贞和许仙人妖之恋的演绎;《将相和》讲述了廉颇和蔺相如的传奇佳话;《六国大封相》则讲述战国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二是弘扬传统美德,宣扬忠、孝、仁、义、礼、信等传统美德体现的是神功戏的教化作用,“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观念在剧目中尤为凸显,如《目连救母》《宝莲灯》《仕林祭塔》等。三是蕴含美好祝愿,如《祭白虎》寓意着“驱邪避凶”,《香花山贺寿》寓意着“健康长寿”,《天姬送子》寓意着“人丁兴旺”,《跳加官》则由“天官”来赐福百姓,天官手中的条幅上书写着吉语,除了有传统的“加官进爵”“步步高升”外,条幅内容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例如清朝时有“一品当朝”,民国时期又有“民国万岁”“天下太平”等。四是娱人市井剧目,时过境迁,人们不再恪守旧有的仪式,神功戏的剧目和场次也逐渐发生变化,原有的庆贺剧目也会被替换成较为世俗的市井剧目,“酬神”的宗教色彩越来越弱,“媚俗”的娱人成分逐渐增加,如展现宝黛之恋的《情僧偷到潇湘馆》等,娱神的功利色彩已经被置换为娱人的现实目的。
二、澳门神功戏的功能与特征
(一)神功戏的功能
1. 愿望的寄托
澳门百姓的信仰是多神信仰(polytheism)与泛灵信仰(animatism)的复合重叠,无论是儒道释诸神,还是民间创造的本土神,甚至是西方教派的神,一律都拜。百姓运用戏曲的重要目的是把自己的生活、人生和神圣化的他者联系在一起,将美好愿望寄托在神灵身上。人们希望通过神功戏来趋利避害、祈福禳灾,反映了他们希望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美好愿望与追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人类文化的发生是“出于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形式上逐渐分化”,且“一物品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1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神功戏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广大百姓的信仰需求,在浓墨重彩的神功戏曲中,在异彩纷呈的贺诞仪式中,人们把自己的愿望随着笙歌一同送至神灵面前。神功戏作为一种媒介,象征性地向神灵祝贺,并且赐福给请戏者和观众,让社会文化的需要和个体的需要都得到满足。在原始巫术思维的影响下,祈福是人类向神灵祷告以求诸事顺遂、福寿延年的一种信仰;禳灾则是人类通过一定的仪式解除面临的灾难、厄运的一种信仰活动,祈福禳灾本质上表现了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福”在中国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概念,除了长寿、安康、好运,还涉及子嗣、功名、财富等。神功戏祈福禳灾的功能,在剧目《八仙贺寿》可见一斑,根据记载,贺寿唱词如下:
渐渐下山来,黄花满地开,一声渔鼓响,惊动众仙来……(汉钟离)门外雪山顶宝,(吕洞宾)金盆放满羊羔,(张果老)天边一朵瑞云飘,(曹国舅)海外八仙齐到。(铁拐李)先献丹砂一粒,(韩湘子)后敬王母蟠桃,(蓝采和)彭祖八百寿年高,(何仙姑)永祝长春不老!
美好寓意除了在剧目情节、唱词等方面表现出来,还尤其体现在演员的服装道具上,或者说是“神仙”扮演者的“宝物法器”上,如汉钟离手持芭蕉扇、曹国舅手持云阳板、铁拐李身系葫芦、何仙姑手捧莲花,它们带有更浓郁的超现实色彩和浪漫气息,与后世体现为金玉钱币等现实财富的宝物观念有所不同。灵芝、丹药、蟠桃、仙草、美酒等食物饮品,牙笏、葫芦、如意、拂尘等器物,甚至仙鹤、麋鹿等动物(坐骑),往往具有超常能力,在信众看来这些都能够给他们带来福气,驱除秽气。
2. 献礼的仪式
戏剧起源于仪式。在西方,从阿尔托到格洛托夫斯基、巴尔巴、谢克纳,戏剧与仪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格雷姆斯(Grimes)指出,当仪式不再是一种直接的体验,而变成了模仿、虚构和扮演,或当仪式仅仅成为一种传统习惯时,戏剧便历史性地出现。戏剧与仪式的关联,无论国度,无论民族,可以说殊途同归。早期中国戏曲和仪式相关联,如先秦的“方相士”“蜡祭”乃至宗庙大典、礼天祭地等,无一不是戏剧与仪式的融合。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研究资料中得到一些佐证,如古希腊戏剧源于祭祀“酒神”的节庆活动,俄国戏剧源于祭祀“春神”的仪式表演,日本歌舞伎源于行脚巫女表演的“念佛舞”,等等;又如中国少数民族中藏族的“跳羌姆”、蒙古族的“好德格沁”、羌族的“莫恩那莎”和“克西格拉”,等等。中国作为一个礼俗社会,千百年来礼俗互动是重要表现,神功戏作为百姓酬谢神恩、恭贺诞辰而向神灵敬献的礼物,在一系列民俗活动中形成了一套无形的礼制。例如,在神功戏中,还伴随着向神像上香、请(戏曲行业的)祖师爷、投掷圣杯、进宝焚化、为神像“妆身”(清洁并重新打扮)、游神等一系列礼制仪式。
3. 礼物的交换
莫斯(Marcel Mauss)认为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以礼物交换为中心的,形成了人与神、人与物、人与人混融一体的礼物社会和礼物文化。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13]礼物附带有赠送者的“一部分灵魂”,“礼物之灵”会迫使受礼者回赠礼物来作为回报,由此可见,礼物交换的实质是双方间社会关系的互动和精神情感的交流。“礼物馈赠和其他互惠交换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14]仪式表演中的礼物是双向的,百姓将神功戏作为贺诞的礼物献给神灵,向神灵敬奉供品即向神灵传递信仰,而神灵则赐给人以福气或满足人们的愿望,回馈给信众尚飨后的供品。经过神灵尚飨后的供品成为新的礼物,信众相信其具有灵力,分享共食是常态,尤其是和自己的家人,这样使得每个人都具有神的祝福和灵力,而分食供品的行为实际上是分享神赐的礼物。如同基里亚克人分享熊图腾餐的意义:“我们吃熊肉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使熊的力量转移到我们身上来。”[15]神功戏被百姓作为“礼”献给神灵,神灵又将“灵力”蕴藏于金猪、瓜果等供品之中,赐福给看戏的百姓。以交换作为核心,围绕礼物的流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礼物流动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提供了“礼物”流动的土壤,也是“信仰”传播的中心。神功戏,是戏,是仪,是礼,戏台和祭台互相转位,仪式和戏剧合而为一,祭品与礼品相互交换。神功戏的展演目的是敬神、谢神、祈福,是一场向神灵献礼的仪式,其与宗教酬神祈福相关联的仪式过程,实际上是“神为我用”的实用观念体现。信众抱着明确的功利性目的而来,获取与神的交换,信众一旦祈福成功,则需要经常来朝拜,若不持续来朝拜,等同于接受礼物而不回礼。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是信仰之间的交流,神功戏作为礼物勾连着人与神,是信俗互动和因果机制的产物,也是集体记忆的物化。

图3 神功戏吸引市民、游人驻足观赏,人神共乐。

图4 农历二月初二,雀仔园福德祠旁搭起戏棚上演精彩的神功戏。
4. 集体的交流
神功戏整合了宗教仪式、娱乐活动、教育意义、社会互动等功能。在中国宗教祭祀活动中,祭品是沟通人与超自然的重要媒介。祭品作为献给神灵的礼物,是信众向神灵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和心理意愿的载体,是人与神进行交换并相互认同的途径和手段。通过祭品这一象征符号作为桥梁,把世俗与神圣世界有机地连接起来,构建一种和睦共处、相互依赖的人神关系,创造出一个“人神交流”的神圣时空,这套象征体系便是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所谓的“集体表象”。[16]演戏过程中,祭台与戏台共同构建了一个特殊的时空,戏台上的演出和祭坛前的宗教仪式交相渗透,互相转位,戏剧和祭礼融为一体,难分难辨,每个人都借助仪式媒介对不在场的神灵进行想象,形成一种特殊的人神交流幻象。除了人与神的交流,还有人与人的交流,传播“灵迹”使在场信众们拉近自己与神灵的距离,亦可以展示信仰。灵迹既可以是自身或亲朋好友的经历,又可以是远古时代口口相传的事迹。通过向周围人传播神灵的信仰,由此获得群体身份认同。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指出,“只有仪式能够把我们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中拽出来,为一个社会世界(的存在)创造可能。”百姓的愿望最终由个人愿望升华为希望家人和睦,希望社区(村庄)平安,希望国家安泰,回归真善美的普世愿望,而百姓通过参与仪式进行族群身份的确认,获得归属感,建构共同体。观看神功戏的观众多以老者居多,所以现在的贺诞活动增加了敬老孝亲的内容,如设敬老宴、敬老折子戏专场、向长者派发礼物等,社区文化交流和综合服务的性质更加明显,而神功戏系列活动也成为当下乡土自治实践的典型模型。
(二)神功戏的特征
1. 宗教性
澳门曾先后属南海郡番禺县、新会郡封乐县、广东省香山县等地,与广东有着密切关联。广东很早就有戏曲活动和宗教信仰相关记载,如《广州府志》载:“岁为神会作鱼龙百戏,共相赌戏,箫鼓管弦之声达昼夜”,[17]又如《化州志》载:“各神庙、街市俱张灯结彩,士庶嬉游,下户妇女亦往观焉。初十后,每夜奉神出游,锣鼓喧闹,灯光如昼,放火花,烧爆竹,打秋千,直至月底方休。自光绪七年后,踵事增华,诸神出游,以三夜而毕……张灯演戏,纸醉金迷,国有长春,城真不夜,亦太平之润色也。”中国民间曲艺表演,不但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配合着宗教节令,在这些节庆中,从最早的驱邪祈福、报赛田社的祭祀及一般的神祇的信仰、庙神的庆典,乃至于喜庆婚丧的仪式,戏曲技艺表演都是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与艺术活动。[18]鼓乐歌舞一直是沟通人神两界的重要手段,神功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宗教信仰提供的土壤,澳门宗祠寺庙林立,宗教文化浓厚,宗教信徒众多,有助于神功戏在澳门扎根、流传。目前澳门主要有七间庙宇的神诞有神功戏,从各主保神祇所属宗教可知,澳门的神功戏以道教为主,合以佛教色彩。由于神功戏主要是做给神灵看,所以戏棚的搭建位置一般要正对着庙宇,以方便其看戏,为神灵提供最佳“观众席”也是神功戏与其他类型戏剧戏曲的重要区别。神功戏的观众,他们首先的身份是宗教信徒,其次才是戏曲观众。在他们眼里,神功戏和敬神用的香烛、纸钱、鞭炮、金猪、花果贡品等“祭祀用品”一样具有宗教属性,也一样具有“答谢神恩、取悦神灵、祈求保佑”的功能。
2. 艺术性
艺术性也可谓“观赏性”。戏曲广泛地调动了小说、诗词、歌曲、器乐、舞蹈、武术、杂耍、绘画、雕塑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表现力,将其有机融合,呈现出一场视听盛宴。视觉上,神功戏化妆的颜色以红、黑、白、蓝、黄为主,

图5 舞台正在演出神功戏《六国大封相》。

图6 神功戏演员正在化妆,做登台前的准备。
代表着勇敢、忠义、奸佞、凶猛、彪悍的个性特点,通过生旦净丑等角色的动作
身段、台词语气、妆容扮相或夸张或写实的呈现,即可知道出场的人物是正义之神还是邪恶之妖。听觉上,“当民众在戏台、戏棚较远处时,也可由敲击音乐的喧闹程度知道主角即将出场,或剧情到达高潮,民众就及时回来看戏”。[19]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提出,“相似律”是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之一,巫师仅仅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情。[20]通过虚拟手法,神功戏演员既可上达天庭,下至龙宫,又可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如剧目《六国大封相》,在有限的舞台上,用上下场、绕圆场来处理戏剧的时空关系,用一系列的马鞭表演牵马、上马、勒马、下马、拴马的象征动作。在舞台上,帅旗代表着千军万马,桌椅代表着山脉城池,一转身便是十万八千里的迢迢路程,一云旗便是骁腾战场上的勇士列阵,时间、空间、地理位置、自然现象等等都可以通过想象表现出来,不可思议却又惟妙惟肖,所以说神功戏具有和其他类型戏剧戏曲一样的艺术属性。
3. 民俗性
澳门神功戏的演出已经与贺诞民俗交织在一起,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部分,甚至是重要步骤。过去的生活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娱乐活动并不多,特别是农村地区。百日之蜡、一日之泽,神功戏作为民俗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百姓朴素简单的娱乐需求。“任何民俗符号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民俗表现体和它(们)所表现的具体的民俗对象与抽象的民俗含义或概念结构而成。也可以说是由民俗表现体和它所表现的民俗内涵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成为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21]寺庙、神像、纸钱、香烛、供品、花牌等,以及热闹喧嚣的锣鼓、华美端庄的戏服、五颜六色的旌旗,这些都是神功戏的民俗符号,也包含着祥和、喜乐的节庆内涵,已经形成了“祭祀-科仪-民俗-演剧”的文化景观。[22]老百姓看社戏的民俗古已有之,正如古诗中所记“箫鼓追随春社近”“太平处处是优场”,就是说村民看到搭建起来的戏台,听到喧天的锣鼓,便知社日将近;太平盛世又适逢社日,处处都在上演社戏。
4. 集体性
集体性可从神功戏所属的社区以及文化空间(Community & Cultural Space)中得见。在中国,任何社区/村庄都有一个或多个地方保护神作为集体的象征,对这些神灵的崇拜仪式成为社区宗教生活的中心。神功戏是集体参与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有人是组织者,有人是出资者,有人是联络者,有人是观看者。神功戏的“集体性”体现在:首先,神功戏是百姓集体意识的统一,神功戏的观众来自各方,也许素未谋面、互不相识,但他们的目的都非常明确——在神诞之日“献礼”以求自己所需;其次,神功戏是百姓情感的集体宣泄,百姓一方面希望向神灵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另一方则希望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所犯的错误能够得到神灵的宽宥,通过这一仪式,百姓的需求得到满足,精神得到解放。在一定的聚居范围内,根据地方保护神的诞辰来举办酬神活动,强化集体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即使是漂泊他乡的人也不例外。演出神功戏的庙宇是文化活动场所,是集体的认同象征和社区的核心组织。
5. 地域性
神功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里可以联系另一种和宗教有关的剧种——“傩戏”。傩戏起源于商周时期,也旨在“酬神还愿”,广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傩戏流行地区广泛而分散,神功戏流行地区则相对集中,主要是粤港澳以及广西部分地区。神功戏发源于广府地区,主要由本土剧团出演,由于演出所使用的语言为广府地区的方言——粤语,神功戏很难向粤港澳之外的地区扩散,影响力也逐步减小。也正因如此,才造就了神功戏在广府地区独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强化了其民俗性。神功戏作为一种特殊的粤剧,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6. 商业性
马克思将“艺术”和“生产”联系起来,首次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神功戏既是粤剧表演,又是艺术商品。神功戏剧团的演出可以看作是艺术生产,能够给剧团带来收入,而支付酬金给剧团来唱神功戏,可以视作艺术消费,这一点,作为艺术的神功戏与作为商品的“物”相差无几。各个剧团外出演出,首要目的是追求最高的商业利润,因此,每个剧团都会打造自己的“招牌戏”来充分发挥神功戏的“商品”属性。所谓“招牌戏”也就是剧团独有的拿手好戏,或剧情独特,或编排精彩,或由名伶出演,用独特的“看点”来吸引眼球,观赏性高于其他剧目,以招徕更多观众,彰显贺诞活动的盛况,更好地提供服务,满足客户需求。根据记载,以前在上演剧目《跳加官》时,若适逢达官贵人及土豪乡绅前来看戏,就会临时增加戏码,“天官”手中的条幅会是“生意兴隆”或“某某人万岁”来迎合大人物,以此“讨封”(红包打赏),商业色彩明显。
三、澳门神功戏的保护与启示
(一)对“人”的保护
对“人”的保护主要侧重于对神功戏“从业者”“传承者”的保护,神功戏离不开薪火相传。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澳门就有很多专业的大佬倌(演员),因为澳门市场较小,他们后来都到香港寻求发展。而后,改革开放促进了省港澳的文艺交流与繁荣,《华侨报》载:“今春接连有两个戏班来澳,在永乐戏园登台贺岁”,[23]形成了“曲来曲往,人来人往”的局面。1945年成立的“黑鹰”文娱体育会和“雀联”体育会是澳门最早的曲艺社团,“黑鹰”在1989年、1999年土地诞期间受礼聘至雀仔园演出神功戏,期间寒风冷雨,不阻观众热情。[24]而后“黑鹰”特设粤剧组面向民众展开培训,《华侨报》载:“随着曲艺爱好者的要求日增,该会将增设粤剧组,请上粤剧界资深人士卢冰女士为培训导师……该粤剧组欢迎有兴趣者参加。”[25]1992—1995年,澳门粤剧团体由十余个发展至六十余个。[26]澳门粤剧业余社团众多,直到2004年澳门粤剧曲艺总会成立,才改变了澳门业余社团没有统一组织的状况。时至今日,澳门神功戏本土专业剧团仍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主要还是邀请广东、香港的粤剧团来唱神功戏。澳门每年的神功戏,除了得到坊众、善信、企业的支持外,还得到了市政署、文化局、旅游局、澳门基金会、霍东英基金会等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的支持,这对于神功戏的保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7]如1989年澳门文化学会(文化局前身)曾举办粤剧化妆课程、1990年澳门文化司署曾举办粤剧表演形体课程等,要坚持“政府搭台,百姓唱戏”的实践方针,提高神功戏的“附加值”。
(二)对“神”的保护
对“神”的保护即对神灵“信仰”的保护和对地方“人情味”的保护。现在的神功戏贺诞,多增加敬老内容,设敬老宴和敬老折子戏专场,当然,如今的戏棚内已少见有售卖小食和各种小玩意的流动小贩,戏棚外也不再有赌局。上演神功戏不仅仅是对鬼神天地的敬畏,也是对传统的敬畏,神功戏体现了民众崇尚自然、天地合一、社会和睦的生活习惯及态度,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世界观、伦理价值道德观和审美意识,多演绎国泰民安、邻里和睦、父慈子孝、美好生活等正向主题,借此向百姓传递价值观念和教化向善。
(三)对“戏”的保护
对“戏”的保护即是对神功戏“文化”的保护。随着社会变迁,神功戏不断发生改变,庙会民俗活动与商业逐利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显现。现在的神功戏剧目大多经过简化,如剧目《送子》,根据酬金多少又分《大送子》《小送子》,《大送子》从七仙女上场眺望凡尘开始,到董永高中状元游街,再到七妹与董永结合,被逼回到天庭,最后将孩子送回董永等一系列剧情;《小送子》则只有两人上场饰演七妹和董永,重点演绎交还孩子的桥段,情节相较更为简单,出场人物也少得多。可以看出,神功戏已经逐渐被简化成仪式化的“躯壳”。神功戏要守正创新,勿受浮躁的社会风气侵蚀,在传承发展时要保留原有的艺术表演特色及基本唱腔,在传承中要去其糟粕,挖掘整理优秀剧目和表演技艺,要积极发展新剧目,汲取现代艺术创意,创新自身的传承方式与管理模式。
澳门的奇妙之处在于,一个个老旧街区中,在高厦楼宇间,往往静峙着一所古老的庙宇,气定神闲地历经人世变迁,可谓沉默的时代见证者。庙宇代表着所处社区中人们的共同愿望:营营役役的人,希望一本万利、生意兴隆;遭逢疫病灾祸的人,希望惨痛消除、雨过天青;要向大海讨生活的渔民,祈求风平浪静、逢凶化吉、满载而归……为此,需要形形色色的神祇、法力无边的大仙。在祭祀祈福的同时,人们理解到相互间的艰苦和危困,由此知道守望相助、福难同当,庙宇由此确切地将社区的人们凝聚、团结起来。人们在祈求神灵的同时,亦知道要适当酬谢神恩,以示饮水思源、不忘其初,于是就有了各种神诞节庆。“还神”,更是对平日辛勤劳作的慰劳,因而举办起各种赛会、巡游等活动,甚或请来戏班,在庙前搭棚唱曲演戏,请神灵观看,娱神娱人。神功戏具有“愿望的寄托”“献礼的仪式”“礼物的交换”“集体的交流”等功能,上演的剧目或演绎经典传说,或弘扬传统美德,或蕴含美好祝愿,集宗教性、艺术性、民俗性、集体性、地域性、商业性于一体。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神功戏作为粤剧独特的表现形式,我们应该从人、神、戏三方面予以保护,让神功戏在澳门更好地扎根、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