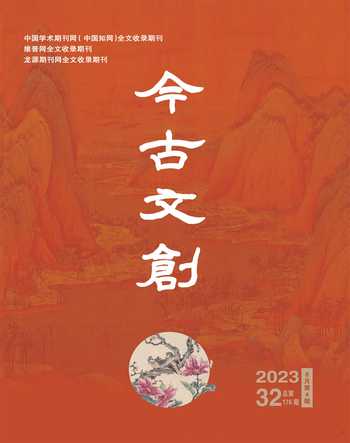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全息玫瑰碎片》中的赛博格身体建构
翟浩然
【摘要】科幻短篇小说集《全息玫瑰碎片》蕴含了作者威廉·吉布森对于赛博格身体的独特理解,探析了近未来视野下身体的危机。科技的应用与欲望的膨胀相结合,催生出人兽同形、人机耦合、灵肉分离的消解中的身体。赛博格身体在极权资本的场域下,被极度符号化,陷入身份混乱和审美趋同的困境。吉布森用隐藏在冷酷机械下的人文关怀为在迷茫中崩溃的主体指明道路,以身体自主、身体尊重、身体追求三个层次的隐喻向充满活力的身体发出请求,期待本体论身体的到来。
【关键词】赛博朋克;赛博格;威廉·吉布森;后人类身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23-06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07
1984年,威廉·吉布森发表了被奉为“赛博朋克圣经”的《神经漫游者》,横扫科幻界文坛,成为一举包揽了“雨果奖”“星云奖”和“菲利普·K·迪克奖”三大科幻小说大奖的著作。布鲁斯·斯特林曾评价道:“他的职业生涯虽短,却已奠定了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中的地位……(《神经漫游者》)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才华——他总能刺中社会的敏感神经。”[1]
相比较之下,作为集吉布森创作生涯之大成的短篇小说集《全息玫瑰碎片》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但吉布森本人在自序中将摇滚单曲和短篇科幻作喻,强调了科幻的最佳载体是经典短篇。在作品中,吉布森撕碎了传统科幻小说所信奉的技术真理的面具和所畅想的科技铸成的乌托邦,以此为棱镜,折射出经过多轮技术革命的近未来世界对“赛博格小人物”的异化。
作为窥见后现代人类的通路,“身体”成为展现后现代思想浪潮的集中舞台。《全息玫瑰碎片》探讨了处在不稳定变形中的赛博格身体,在某些界限逐渐消解的过程中,身体表现出人兽同体(人体兽化)、人机耦合、灵肉分离的特点,并以此延申出对被蚕食主体性的身体的问题的思考,寄希望于身体成为自身新的拯救者来破除困境。
一、处于界限消解的身体
从身体的价值历史来看,身体曾经在相当一段长的历史时期备受压制,在生命的颓废中变得更加消沉、暗淡,而“在身体的否定史之后,身体的肯定史到来了”[2]。欲望的解放激活了身体中原先被压抑的部分,造就了赛博朋克小说中的身体盛宴。“种种奇观具备后现代世界的典型特征,那就是通过身体来表演一切性欲、艺术以及政治形式,玩弄编码/解码、组合/再组合的一切可能性形式。”[3]在《全息玫瑰碎片》的身体描写中,行迹散漫的赛博朋克近未来空间致使了身体某些界限的消解。“在自然、社会、文化之间打开了一系列‘有裂缝的区分,它穿越了动物/人的有机物和技术机器的边界,但它也质疑物理世界和非物理世界之间的边界”[4]。身体见证了近未来世界生物科学的技术跃进,基因改造、智能义体、器官移植等技术开辟了赛博格身体的新状态。
(一)人兽同体的身体
为了追求欲望的解放,身体中人与兽的界限在不断消解,以此来复归到野蛮、无序、原始的兽性时代,将被意识压制许久的身体本身解放开来,赋予了身体被早已剥夺了的力。
在《約翰尼的记忆》中,低科技族信奉野蛮原始,从外表上将自己打造成原本的兽。莫莉的朋友狗子“口中慢慢伸出一截又厚又长的灰舌头,舔着突出的犬牙”,他通过生物技术移植杜宾犬的牙胚,甚至以语言能力为代价“让他看起来简直不像人类,而像野兽”[1]。低科技族依靠先进科技来追求其信奉的兽性乌托邦社会,未免有些讽刺。他们像蝙蝠一般蜷缩在夜城的穹顶之上,以温热的金属板和湿漉漉的胶合板为栖息地,发挥能动性将自己的外型塑造得尽可能兽化,以求得表现尼采哲学中身体即生命即权力意志的信仰,“但他那对犬牙、满脸可怕的刀疤,还有深陷的眼窝,让他看起来简直不像人类,而像野兽。弄出这么一张脸来,可是件费时费力的活儿,还得有点创意才成。看他的举动,这个怪脸人好像过得挺开心”[1],他们追求兽性的举动彰显了权力意志,肯定了肉体的本能欲望。
低科技族排斥现代科技,呼唤原始兽性的回归,妄图从外至内打造出他们所渴望的另类乌托邦,但最终的结果是虚假的乌托邦的外壳轰然倒塌。技术上,他们热烈追求原始兽性雕琢身体的行为依赖于生物高科技,“他们怎么能把移植杜宾犬牙胚的技术列为低科技呢”;社会联系上,低科技族的胶合板社会并无任何生产活动,最终还需要依赖现代科技社会的市场来维持,“他用一盒厨房用火柴给我点上,我趁机瞅了一眼香烟牌子:颐和园过滤嘴香烟,北京卷烟厂。看来低科族也在做黑市买卖”[1],低科技族以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联系着现代科技社会。
虽然低科技族社会是虚假的,但其身体解放真切存在,也就是说在现代科技的介入下,人与兽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赛博格身体试图成为独立的力。此外,赛博格身体除了人的兽化过程,还吸引着兽的人化过程。赛博格海豚“琼斯”,曾被海军强制染上毒瘾,身体被加装传感器和装甲片,并可以链接视听显示系统传达信号语言。虽然形式上是被动的,但在动物赛博格身体人化的过程中,开放着的身体接纳了不同向度的变化,挣脱了长久以来的束缚和压抑,走向生命意志。
(二)人机耦合的身体
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中,得益于技术的发展,机械能够弥补缺失的机体或增强机体的功能,呈现出将“肉身”向“物”的不同程度塑造转化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技术介入下身体与机械的地位问题。
《整垮铬萝米》中“自动化“杰克在滑翔中被激光枪烧掉一条胳膊,为此他装配杜拉铝肌电假肢弥补缺失的机能。《冬季市场》中的莉丝则体现机械维持生命的功能,她由于残破的身体流落到垃圾场,只能依靠黑色聚碳酸酯的外骨骼弥补功能,依靠电维系身体的正常运作。
除此以外,机械强化了工作和生存的必要功能。《约翰尼的记忆》中,莫莉在千叶接受身体改造手术,不仅为眼睛植入了银色镜面镜片,还将弹射利刃埋入十指;日本技术员杀手“从指关节下方截断,换了一个人工指尖,在里面安上仙台小野公司出产的仿金刚石线轴和底座”[1]。这些经过人机耦合后增强部分功能的身体,成为杀手职业的物质基础。另外,约翰尼则为生存和工作则通过一系列外科手术将客户需要储存的信息灌入头脑,以至于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就算切开脑袋也无济于事,甚至约翰尼本人对内容也无从知晓。为求生存,约翰尼的身体被异化为机器般的信息保险箱,充当极权大公司信息战争的记忆容器,甚至是战利品。
赛博格身体在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机械福祉时,也在走向极端工具化的结局,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蚕食殆尽。
(三)灵肉分离的身体
在场的身体被逐渐强化追求自由的过程中,缺席的身体逐渐变形为意识的牢笼。依赖于发达的信息技术,赛博空间应运而生。
威廉·吉布森将赛博空间解释为“一个由共同的幻觉创造的空……是由人类系统的所有计算机中抽取的数据形成的画面”[5]。在此场景中,意识从肉体中逃脱,成为无形无畏、绝对自由的独立体。在独立体漫游电子信息组成的矩阵空间时,肉体仅作为躯壳落得了不同程度的被抛弃的下场。
在中文版小说集的同名短篇小说《全息玫瑰碎片》中,人的感觉被编排和剪辑,制成商品——“感官体验”售卖。主人公帕克通过德尔塔脑波诱发器进入前女友的感官,代入她的身体,从而进入“欧洲大陆的阳光和陌生城市的街道”,享受与前女友的温存。[1]但怀疑屡次造访,“欧洲旅行的几个瞬间被遗弃在空白磁带的灰色海洋里。他终于也去过那里了,可是她因此变得更真实了吗?他们之间因此变得更亲密了吗?”感官体验在过程中无比真实、无比迷人,则更加使得“断电之后醒来发现自己困在一具完美的躯体中”[1]的现实更加无趣。
《整跨铬萝米》中的瑞琪向往进入感官体验行业,希望成为行业巨星。经济窘迫的她为了昂贵的蔡司眼球,借助感官体验切断自身的感觉,“去体验磁带中录制下来的官能感受”[1],而肉身则在“蓝色光芒”会所以低廉的价格出卖,成为客人的性欲玩偶。“赛博空间为后人类提供了强烈的神经刺激体验和供意识自由流动的无限平台,由此助其逃离了现实物理世界”[6],而与现实的落差则驱使人深入“沉浸”的状态,缺席的身体逐渐边缘化,呈现出笛卡尔式心灵与身体相分離,身体被心灵支配的特点。
从鲍德里亚的观点来看,这正体现了超现实对现实的驱逐的更深层次。人们将现实和虚拟逆转,现实世界提供的真实感远不如赛博空间的超真实,被蛊惑的人们倾向于相信虚拟世界带来的超真实,对身体的抛弃则成为必然的结局。
在《冬季市场》中,莉丝因不治之症不久于人世,由她制作的感官体验《沉睡之王》风靡市场,由此她被资本选中以意识的形式留存于赛博空间。成为程序后,她即是《睡眠之王》,“她真的超越了一切,她是我们的高科技圣女贞德……她抛弃了自己的残躯败体”[1]。除了主人公,在所有人眼中莉丝都是完美无瑕的赛博上帝,这与之前需要外骨骼维持生命,“被聚碳酸酯和可恨肉体束缚”的她相去甚远。只有主人公无法接受,“如果我没有看见他们,我就能接受后来发生的一切,甚至可能为她高兴,信任她之后变成的(或照着她的形象制作的)无论什么东西——一个假扮莉丝的程序,假扮到它自己都相信自己是她”[1]。现实被信息不断篡改,移植到赛博空间,赛博空间的再修改将人变得面目全非,最初的摹本即莉丝已经沉没在信息的海洋,中介完全取代人本身,超现实彻底将现实扫地出门。
除了感官体验,赛博空间提供了灵肉分离的另外一种方式——黑客。在《整垮铬萝米》中,黑客鲍比和“自动化”杰克侵入了铬萝米的虚拟城堡。他们通过模拟器控制台接入充满几何形状的模拟矩阵,成了“没有形体的我们”。他们在矩阵中自由变化,“伪装成一个审计程序和三张传票”,以极速攻破了铬萝米的冰层,“那种感觉就像在侵入程序的波峰上冲浪,悬浮在沸腾的伪电子信号上空”,此刻他们的肉体“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一间拥挤的阁楼里”[1]。依据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由感官体验到畅游矩阵,“仿真使我们进入了由模式、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后现代社会”[7]。鲍比在物理世界是生活糜烂,等待希望的穷困黑客,在成功整垮铬萝米的那一刻后,他内心的满足感瞬间消失,“鲍比软塌塌地坐在转椅里,对着他的显示器,看着属于他的一长串零”[1],他所渴望的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意识自由地在矩阵中滑行,他迫不及待地等待下一次“整垮铬萝米”行动。赛博空间的极度刺激使人的现实显得如此无意义,与其说是缺席的肉体被驱逐,不如说缺席的肉体是自愿离开的。
总体来说,赛博格身体正如哈拉维所界定:“既是动物又是机器,生活于界限模糊的自然界和工艺界”[8],以人兽同体、人机耦合以及灵肉分离的方式体现为重塑、增强与被抛三种身体形态,这种现象的本质则在于人与他者界限的消解。
二、处于困境的身体
“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及其自觉能动活动,是社会中各要素、关系、组织等得以结为整体,获得生命与活动,并自觉展开为有序的社会活动,不断自我发展与完善的中心、纽带和关节点。”[9]这是人的主体性所在,而在吉布森所塑造的近未来世界,人的主体性被蚕食,引以为傲的技术则成了帮凶。
威廉·吉布森在小说中多次描写权力滔天的跨国公司:《约翰尼的记忆》中约翰尼因为脑中的信息而被日本黑帮追杀;《新玫瑰旅馆》中,主人公和桑迪不得不被卷入“那些财阀——控制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彼此之间明争暗斗”;《冬季市场》中,“自主领航”公司作为资本的代表将生命转译为商品……他们代表着强盛的极权资本主义力量,共同点在于所掌握的一切都落脚于“信息”与“数据”。
在这种极权资本下,技术统治着人类,主体性的丧失导致人文主义信仰下的“人”的概念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浩劫,具体表现为“身体则完全陷入异化的困境,沦为被权力征服、奴役、规训的对象”[6]。
(一)身体符号化
在资本权力视域下,赛博格身体或成为被利用的实用工具,或成为被玩弄的取乐傀儡。
在《约翰尼的记忆》中,主人公约翰尼通过一系列超微外科手术储存秘密信息,通过为财团和黑社会走私信息来谋生。芯片所带来的“白痴——明白人机制”保障了信息的绝对安全,只有唯一的客户可以通过密钥解锁信息。就算在接收信息和导出信息的过程中,约翰尼也只会“吟诵着一首人工语言谱成的诗歌”,而后便丧失全部记忆。约翰尼曾自述:“这辈子的大半时间里,我都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容器”,“我知道自己已经收购了做别人容器的日子”[1]。从资本视角来看,约翰尼除了是保证信息万无一失的保险柜外毫无个性和主体性,也就是说约翰尼的身体被物化为纯粹的工具,仅在需要时起作用。
在《整垮铬萝米》中,瑞琪为了踏入感官体验行业,主动将自己的身体贩卖到“蓝色光芒”,将自己物化为任由消费者玩弄的游戏傀儡:“在类似于深度睡眠的状况下工作三个小时,她的身体和一部分条件反射机制负责这份工作。客人永远都不会抱怨她在伪装,因为那些是货真价实的性高潮。但是,她自己感觉不到——即使能感觉到,也只是睡梦边缘一丝浅淡的银色光斑。”[1]切断了一切官能的瑞琪的价值在消费者看来,仅剩满足性的需求,其个性消失殆尽,由完全的人转变为性工具。
在《蛮荒之地》中,主人公托比是接收信号的中介“媒介人”,他被植入骨导电话,从而接收来自宇宙四面八方的信息。“媒介人”必须到达工作地点“天堂——“即内层金属柱……它更是全球经济伸出的贪婪讹夺,渴求新鲜信息”[1]。在工作时,作为“媒介人”的个体受尽折磨:“惨叫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反馈信号在我脑袋里横冲直撞”;甚至需要身体经受可能泯灭的痛苦“那些管道就像一束束肌腱,被束缚,却不断膨胀,随时可能痉挛,碾碎我的身体”[1]。原本充满生命意志的个体的身体也屈服于资本,被迫成为一次性的传输工具,并在物化中走向必然毁灭的结局。
此外,资本索求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身体。在信息流窜导致托比升入“天堂”后,他的工作对象——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中校也无可避免地被纳入物化的进程中。“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我们的奇点女神,‘高速公路的主保圣女”被认为“简直是《真理报》上刻画的太空劳动者的理想形象。她无疑已经超越了性别,成为史上最上镜的宇航员”[1]。然而,这样一位被资本塑造成无比高尚的女神,也因为资本对信息价值的疯狂追求,尸体无法安息,“研究人员自然不可能放弃,他们越努力尝试,她的身体就变得越薄。最终,因为他们迫切的探索欲,她珍贵的遗体填满了所有图书馆的冷藏柜。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圣女被切割得如此精细:单是普列谢茨克实验室就收藏了她身体的两百多万个组织切片”[1]。更可悲的是,由于奥尔加身体的死亡,“几十个物理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个比一个诡谲高深,每种理论都希望抢占主流殿堂”[1]。从经济到科学再到学术上,一具死亡的身体带来了大繁荣,而身体的本人奥尔加,永远失去了崇高的女神地位,她在太空迷失的两年间的痛苦与恐惧却无人提起。在资本的注目下,个体除价值外的一切都被刨除,彻底被物化为权力和财富对峙和表演的历史注脚。
赛博格身体在掌握高度集中权力的资本控制下,从生走向死,从活力走向暮气,从人性走向物的属性。作为符号的身体,丧失了一切个性和选择的权利,完全成为不断生产价值的机器,服从于极权资本主义的发展利益。
(二)身份的混乱
“‘身份认同指的是人们在个人层次或者集体层次上,自认为自己是谁,这种认识方式受文化建构方式的影响。身份构成形式有两种情况:一是个体层次身份,每个人会在内心塑造一个自我形象并对其进行评估,然后会将这个主观形象放在社会结构中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以获得身份认同;二是集体层次身份认同,任何一个社会群体要想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必须要有群体内部的共同特征,这种共同特征会形成群体意识,成为该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10]身份认同即是对“我是谁”问题的具体回答。身份认同一直是赛博朋克作品的热议话题,不论是电影《银翼杀手》中的罗伊,还是小说《神经漫游者》都将笔墨倾泻在“身份”上。
不过与吉布森其他小说对比,《全息玫瑰碎片》中的身份混乱的困境更为含蓄内敛,作者并不热衷于将“阿米塔奇” ①式的遭遇强加在故事的主人公头上,而是把混乱的程度控制得若即若离,而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对象则是赛博格身体。
在小说集《全息玫瑰碎片》中,导致主体陷入身份混乱的途径主要有消费和记忆两种。《酒吧里的归栖者》描绘了一幅异形以身体为中介进行身份表演來融入社会群体的画面。主人公科雷蒂被一个叫安托瓦妮特的女孩吸引,从而跟随她穿梭于各式各样的酒吧,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女孩能够随意变换形状以成为每个酒吧的“土著”,最后由于好奇打开了通往“栖息地”的门而被同化。在这里,“她将自己浸泡在酒瓶、高脚杯和旋转上升的烟圈里,它们构成了她生命的半衰期”[1]。这类异形通过变形与换装装饰了酒吧,在一定程度上也附属于酒吧,他们将个人无意识领域的主观形象投射到酒精中,在社会情境中与酒吧中的其他人比较,来确定自己属于“归栖者”的群体,达到个人层次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阉割了自身族群的特征与习俗,隐藏了深潜者式的混沌与兽性,拒绝了所有自主(autonome)的品质”[6],族群的群体身份认同被抛弃,使得自身处于矛盾的通过抛弃原有身份迎合新身份的博弈中,身份的混乱就此发生。科雷蒂的被同化过程体现了群体身份认同的混乱。“具备某一群体的共同特征也是定位身份的重要方式, 个人必须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群体特征才能获得归属感”[10]。科雷蒂为了寻找安托瓦妮特跑遍了城市的每一家酒吧,甚至已经成为他习惯,在见不到她的时间,他食欲不振,毫无干劲甚至因为被辞退而窃喜,造成科雷蒂现状的原因是无法获得“归栖者”群体的归属感。而当他再次见到安托瓦妮特时,“科雷蒂对她以及她的同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钦慕之情和一丝诡异的自豪感”,他的归属感被满足。
在文章结尾,科雷蒂感受到先前的脉冲,“那个忧心忡忡的科雷蒂仿佛又回来了”[1],而他本身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同化,这也预示着他的身份处于丧失原生的群体身份认同和获得嫁接的群体身份认同的叠加状态的混乱困境中。
赛博格概念瓦解了原有的人的身体与野兽、机械等的界限,使得人的记忆在技术的侵入下不断修改与重构,身份困境由此产生。吉布森在谈论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提道:“我的小说中的电脑只是人类记忆的隐喻而已。我感兴趣的是记忆的方式和原因,如何界定我们的身份,如何轻易地被修改。”[11]
在《冬季市场》中,莉丝一个从需要外骨骼维持生命的病人转录为“自主领航”公司的硬件程序,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渐渐疏远莉丝,“我们从不交谈,只有工作室里的对话”[1]。正如忒修斯之船一样,他人对于莉丝的记忆被重构,主人公求助于别人来证明莉丝的身份,“鲁宾,如果她给我打电话,那还是她吗?”而得到的答案则是模糊的“天晓得”,这也导致主人公对于身份的困惑:“我觉得谁都可以住在这里,可以拥有这些东西,一切都可以互相交换: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和任何人的生活……”[1]记忆所导致的身份困境不只反映在主体本身,更存在于与主体联系着的任何人。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整垮铬萝米》中,瑞琪换上蔡司眼球后离开了鲍比从事感官体验行业,杰克对于瑞琪的记忆逐渐模糊,“她总在蔓延的城市和浓烟边缘,就像一个全息影像,粘在我的视网膜上”[1]。记忆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导致主体性的消失,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我们也不再有主体,因为身份的复制消除了主体的区分。”[12]
(三)审美趋同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布鲁斯·斯特林介绍吉布森是“隐形的文学”观点的拥趸,“这个世界中的‘大科学并不只是魔法师的奇迹之源,而是无处不在,渗透一切的决定性力量”[1]。换句话说,大科学背后的极权资本将科学报告、政府文件和专业化广告渗入人的生活,在潜意识里塑造了文化与审美,他们制造了种种予人便利与幻觉的商品,并借此控制人的思想。
在小说集《全息玫瑰碎片》中,一方面人往往被科学技术赋予权力,另一方面人运用这些权力来剥夺自己的自由,身体则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资本剥夺了审美多样性的话语权,人受到了资本的限制和迷惑,将身体作为演出台,依赖长足进步的技术将其塑造为审美趋同的身体。
媒介通过身体的审美展示,诱导和唤醒大众的身体审美欲望,为大众提供了自我完善的审美想象,最终引导大众对标准化身体的规划,身体成为流水线上的物品,大众困守于无止境的身体游戏中无法自拔。
在《约翰尼的记忆》中,拉尔菲的买来的那张脸属于雅利安人雷盖乐队的克里斯蒂安·怀特,“克里斯蒂安·怀特:典型的漂亮脸蛋,皮肤细嫩,颧骨突出”[1],成了人们所追求的整容模板。
资本常常通过杂志或者广告为人们提供了众多身体的规范和要求,以此引发众多消费者跟随趋同的审美,《整垮葛罗米》中瑞琪的伙伴泰格就是其中之一,杰克评价“他的五官长得很好看,是那种去了七次整容诊所换来的千篇一律的‘好看。我想他下半辈子的任何时候都会与最新时尚杂志的封面有些相似,并没有明显的抄袭的痕迹,但也毫无特色可言”[1]。审美趋同是一种结构性暴力,极权资本将某种物品打上高端阶层的标签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以满足对个人实际肉体和思想的控制。瑞琪沉迷于鲜艳的宣传单上移植蔡司伊康眼笑容可掬的女孩,在这时,瑞琪的身体并不再具有以往那样美丽动人的个性,也走向了美的反面。
三、身体何以救赎
吉布森的科幻小说绝非太空歌剧般的宇宙英雄罗曼史,而是“借想象的外衣来审视真实的当下”[13]。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近未来社会投射出他对人类境遇的忧思,他将赛博格身体连同身体的困境暴露在文化视野里,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当今人的身体何以救赎。在《全息玫瑰碎片》中同样也隐含着他本人对身体拯救的独到见解。
(一)身体自主
福柯认为,身体是可塑的,它被微观意义上的隐形权力所规训,而作为个体的人并非真正的拥有自己的身体。
《空战》讲述了无业游民德克意外与高智商的富家小姐南斯结识相爱并依靠南斯的高科技和亢奋剂在空战游戏中战胜残疾的退役军人泰尼的故事。控制欲极强的父母给南斯安装了贞操锁,一旦她与异性接触就会头痛欲裂,长时间被压迫、束缚、禁锢的南斯无法释放自己的爱欲,只能通过高科技创作表现无声的反抗:“德克眨了眨眼,残像里都是人,微小的、漂亮的、赤裸的人,都在做爱”[1]。受規训的身体无法满足主体的活力,激发了夺回完满身体所有权的宣告。身体的挣扎虽然无济于事,但开辟了表达爱欲的另一条路径,德克用裙子覆盖住自己所有的皮肤,二人隔着巨大的泰迪熊起舞。南斯被这突如其来的爱的舞蹈触及,“她渐渐流下泪来,脸上仍然带着微笑”[1]。被压抑的身体自主地觉醒象征着从内而外的反抗力量,从而发掘出了隐藏在身体内部的意识形态潜能。
在小说中,极权主义视域下的身体,其工具性被无限放大,原本的自主性随即消失,身体僵化为完成指令的机械臂,可以视为福柯所说的规训身体的极端情况,身体本应有的不断奔涌的力被束缚。
在《约翰尼的记忆》中,约翰尼被视为记忆容器而使用,“储存在我脑子里的信息还是万无一失”[1],这种职业自豪感虽然证明了其技术可靠性,但也蒙蔽了主体的能动性。之后经过一系列危机,约翰尼最终决定留在低科技族中,“在他来之前,我的生活是多么空虚。我知道自己受够了做别人容器的日子”,而他最希望的则是“找个外科医生,让他把我脑子里的那些芯片全部抠出来。到时候,我的脑子里保存的,只有我自己的记忆”[1]。约翰尼抛去既定身份,暂时脱离了技术与资本的约束,身体回归主体,夺回身体的所有权。更进一步地,约翰尼回归原始兽性,身体信奉热情奔放、活力满满的狄奥尼索斯,重新充满了力与力的竞技。
(二)身体尊重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在人的内部本性中存在不同层次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其中包括尊重需要,尊重需要包括自尊与他尊,即人对自己的尊重和在此基础上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一方面,身体作为凝聚主体意志的生命载体应当得到主体的尊重。《整垮铬萝米》中的“蓝色光芒”是瑞琪为了得到足够的钱够买蔡司益康眼而去充当性偶的色情会所。作者借杰克的第一视角叙述表现对她抛弃身体自尊的反感,“我努力不去想象瑞琪在‘蓝色光芒会所的模样”;在杰克不小心弄乱瑞琪用遮瑕膏掩盖的手术疤痕时,他“突然感到无法呼吸,这场合说什么都不合适”[1]。尽管深爱瑞琪,但杰克依旧难以接受瑞琪出卖身体提供色情服务的事实。瑞琪“用身体去创造,用身体的元素、表面、体积、厚度去创造,一种没有规训的色情主义:它属于活力四射變幻不定的身体,充满偶然的相遇和毫无计算的快乐”[14]。被剥夺感觉的瑞琪甚至无法获得这种“快乐”,已经彻底轻贱了身体,杰克的无法接受是必然的。吉布森这种否定式的对身体自尊的关怀充满了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
另一方面,身体作为充盈生活经验的生命载体希望得到客体的尊重。鲍比虽然一遍一遍说他有多爱瑞琪:“我是为了她才这么做的,这一点你很清楚”,但实际在老相识杰克的眼里,鲍比对瑞琪的态度已经被识破:“我知道他总是把女人作为游戏里计分的筹码……瑞琪出现的时机正好……所以,鲍比把她当成了一个象征符号,象征他想要但未曾得到的一切”[1]。与鲍比对瑞琪的冷落和符号化不同,杰克更为尊重瑞琪的身体并发现她的身体作为生命意志的动力,在他温情的审美眼光下瑞琪“是一个活生生的、完全真实的人,她如饥似渴、精力充沛、百无聊赖、美丽动人、兴奋不已……”[1]此刻瑞琪的身体在杰克眼中充满魅力,应当得到客体的尊重。缺失了自尊与他尊的身体不再活力满满,而不得不从生命中退场,走向“夜色和城市的边缘”。
(三)身体追求
身体是承载美的力量的重要媒介,舒斯特曼认为身体美学指向“活生生的、敏锐的、动态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15],并且要让这具身体富有生命力和良好的审美体验。吉布森与其不谋而合,通过多样化的身体演绎表现出对身体美的追求,表现在对原生身体的珍视和对技术侵入身体的抵制。
小说《全息玫瑰碎片》原标题Burning Chrome,其中Chrome意为元素铬,在小说中共出现36次,除20次作为名字出现,剩余16次都为高科技的象征。在《整垮铬萝米》中,铬萝米的名字已经暗示她的身体早已被技术侵入,传言也印证了这一点:“她长着漂亮的心形脸庞和一双世上最邪恶的眼睛。在大家印象里,她看起来也就是十四岁的样子,像是某个大型程序的正常形象。”[1]相较于有着钢铁娃娃脸却带给人重压的冷艳人工美人铬萝米,吉布森的代言人——杰克选择用瑞琪的照片覆盖住,这张照片也透出原生身体的美:“她穿着褪色的迷彩工作服,脚踩半透明的玫瑰色凉鞋,正弯腰在尼龙工具袋里找东西,赤裸的背部曲线玲珑……”[1]在杰克温情和充满爱意的注视下,瑞琪本原的、不经污染的身体与日后标准化的“商品”身体相比,充盈着体验性与人文主义的美。
赛博格的身体议题并非只是文学一隅的狂欢,而是危机前的警钟。从人的历史来看,技术的侵入伴随人的发展,“身体”这一概念不断被技术解构重组,到现在美国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就是“赛博格”[16],宣告后人类时代已经到来。
吉布森的小说中作为本体论的身体概念在赛博空间和数据流中自我分解,践踏传统的身体伦理,呈现出人兽同体、人机耦合、灵肉分离的特征。重建中的身体在极权资本主义的压制下极度工具化、符号化,滋生了身体审美的同一化,间接将身体推向迷惘,陷入身份混乱的漩涡。当人的身体成为技术的附属品时,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将充满虚无的人文主义疑问。但吉布森对此并不悲观,他不是将未来的异化身体作为吸人眼球的卖点进行展览,而是从人文主义关怀出发,在故事中暗含警醒的话语,希望人们能够把握好赛博化的平衡点,呼唤被冷落的身体书写人的能动性,重回价值的巅峰,重振身体的荣光。
注释:
①“阿米塔奇”出自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书中人物的记忆被完全篡改。
参考文献:
[1]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
[2]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胡继华.赛博公民:后现代性的身体隐喻及其意义[J].文艺研究,2009,(07):84-92.
[4]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Gibson,William.Neuromancer[M].New York:Penguin Putnam,1984:51.
[6]伍文妍.博弈·异化·救赎:《全息玫瑰碎片》的后身体书写[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02):24-32.
[7]李铖.威廉·吉布森赛博朋克小说中的“拟像”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21:10.
[8]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M].陈静译.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9]欧阳康.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J].哲学动态, 1988,(04):43-44.
[10]李韦韦.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与身份认同[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学版),2008,(01):26-28.
[11]威廉·吉布森.虚拟偶像艾朵露[M].符瑶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4.
[12]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M].王晴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13]HENTHORNE T.William Gibson:A Literary Companion[M].London:rland&Company Inc,2011.
[14]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5]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6]N·凯萨琳·海尔斯.后人类时代:虚拟身体的多重想象和建构[M].赖淑芳,李伟柏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