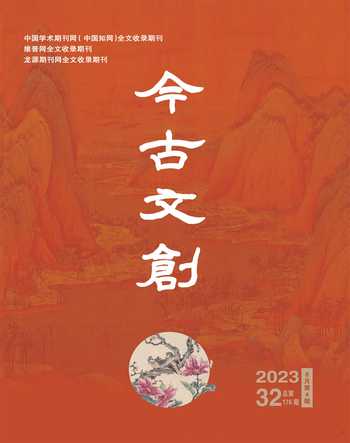试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波德莱尔印记
【摘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因为其作者林奕含而得到关注,现今更因为其对儿童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书写而活跃于大众的视线。人们开始注意到女性在成长阶段和婚姻生活中可能受到的伤害并思考应该如何减少这类悲剧的再发生。除了社会意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展现了林奕含极强的文学功底,经典文学典故信手拈来,令人惊叹的修辞及词藻层出不穷,她以细腻的笔触游走于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之中,将读者带入少女房思琪被摧毁的“乐园”。本文从小说的文学性出发,试分析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通感、象征以及审丑美学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印记。
【关键词】《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波德莱尔;印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04
林奕含,台南人,因自身经历而常年饱受精神病折磨,两次考上大学但皆因健康原因而中断,2017年自杀身亡。《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其绝唱。小说主要讲述了信仰文学的少女房思琪被补习班国文老师李国华诱奸直至精神崩溃的故事。
作为文学中少有的聚焦少女性侵犯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激起了评论家们从道德角度对儿童性侵犯的谴责,也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和性教育的重视,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文学性,从小说的标题设置、主题意象和具体文本细节都体现着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以及世界文学作品对其的影响,波德莱尔便是其中之一。林奕含认为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中的“一个词、一句话、一个词的声韵和联想、一句话的画面和联想……”都能够让读者“作一场悠远的白日梦”(林奕含,2021)。此外,《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出现的作家、文学作品或文学人物等文学事物也包括波德莱尔,书中在呈现思琪与怡婷的关系时说她们都读波德莱尔而不是《波特莱尔大遇险》,这是她们与其他同龄人的不同,幸好她们还有彼此可以倾诉自己对世界的想法,否则她们要被噎死了(林奕含,2018:25)。少女的友谊被文学加固,波德莱尔是她们早慧的友情的见证,也对林奕含创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产生了影响。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是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著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和《可怜的比利时!》等。他重新赋予通感生命力,用象征和审丑美学奠定了自己在欧美文坛的崇高地位,下面将试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这些波德莱尔印记。
一、印记之一:通感
首先,“通感”是“应和”的分支。“应和”这一概念并不是波德莱尔创造的,19世纪40年代的文坛已经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刘波,2004)。对波德莱尔来说,“应和”是一个相当重要并且值得运用于写作中的概念。他在《恶之花》中的《应和》一诗里谈论了自己对“应和”的理解。视觉、嗅觉、听觉等相互联系、相互转换,便能够使世间万物形成为和谐的整体,使用“应和”的作品能达到精神与感官的统一(Gusto,1993:19)。经后续理论的发展,“应和”被分为“垂直应和”与“水平应和”。“垂直应和”是指从一个物体或者其所带来的感官感受出发,上升到对应的概念以及情感体验,比如从色、香、声出发探寻它们背后的概念或情感。“水平应和”则指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感受之间的水平转换,比如用与颜色相关的形容词来描绘声音(李丹,2017)。前者是应和,后者即是通感。事实上,即使没有通感这一概念,以细腻浪漫著称的中国古代诗歌中已经有“春风又绿江南岸”(出自宋代王安石《泊船瓜洲》)、“大珠小珠落玉盘”(出自唐代白居易《琵琶行》)这样的诗句。前一诗句中的“绿”字将春风拟人化,把春天到来万物复苏的勃勃生机生动地展现出来;后一诗句则把琵琶声以珠子落盘的动态之姿再现,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可见运用通感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融合多种感官体验,将眼、口、鼻、耳所感相转换以让读者获得多维度感受,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三位主要女性角色房思琪、刘怡婷和许伊纹均是痴迷文学的,她们孜孜不倦地从文学中摄取养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观察和体悟世界的方法,她们思维和语言中的通感则很好凸显了她们的文学内涵,也让角色更加生动立体。思琪脑海中的通感大多出现在她被侵犯时,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也表现出角色在被伤害时所出现的感知混乱。李国华通过思琪的作文发现了女孩强烈的自尊心,他明白自己不会被揭发。于是在讲解作文时,他开始悄悄摸上思琪的手又让思琪帮他从书架上拿书从而用身体包围她,这时思琪形容老师的声音“跟颜楷一样筋肉分明,捺在她身上”(林奕含,2018:45)。变得禽兽的老师的声音都仿佛长出手扒在自己身上,既表现出思琪意识到了危险,第一次开始畏惧一直“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老师,一个“捺”字也让读者体会到思琪面临侵犯时动弹不得的巨大恐惧和無助。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第一次被侵犯时思琪写道:“我被逼到涂在墙上”(林奕含,2018:23)。触觉与视觉的互通放大了未成年女孩面对成年男性施暴行为时的压迫感与窒息感,她的肉体似乎要被屈辱抽到真空,与墙融为一体,这一处通感的使用能够让读者获得同感,体会思琪身心所受的巨大创伤。以上这些通感的运用能让我们最大程度体会到思琪的痛苦,产生对李国华的厌恶,进而反思青少年性教育和保护的不足,小说书写未成年性侵犯的现实意义得到了更好的实现。
作为思琪“灵魂双胞胎”的文学少女怡婷则经常用通感来表达自己对周遭一切的观察和想法。在好友思琪因痛苦而精神失常之前,怡婷是天真雀跃的小女生,她唯一的烦恼是认为思琪和老师背着自己相爱了,她感到被背叛,她感到一点点嫉妒,但没有痛苦和压抑。她的世界总还是有少女的活泼可爱,比如在听伊纹读中文书时,她“感到啃鲜生菜的爽脆,一个字是一口,不曾有屑屑落在地上”(林奕含,2018:14)。用爽利的吃生菜的口感来形容伊纹念书声的清晰,不仅准确,而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怡婷文学少女异想天开的魅力跃然纸上。
伊纹作为三人中年纪最长的姐姐,是思琪和怡婷的文学引路人。她真挚地喜爱和关心两个小女生,她也最先洞察到李国华与思琪关系的不正常,但每次面对思琪总是没有勇气追问下去,因为自己也深陷于长期被家暴的泥淖,隐藏着秘密,耗尽了救己救人的信心。伊纹是有极强的自尊心的,丈夫清醒时的温柔又每每让她心软,这些因素都导致她不会轻易向他人寻求帮助,而是选择自我消化苦痛。小说里有一处伊纹在摸搪瓷时的心理描写,“手轻轻拂过去,搪瓷摸起来仿佛摸得到里面的金属底子,摸得牙齿发酸”(林奕含,2018:37)。搪瓷下有金属,这就如同自己在他人眼中光鲜亮丽的生活下掩藏的另一幅面貌,摸着搪瓷感到了金属,立刻从触觉转向味觉“发酸”,暗示伊纹自我品咂之下生活的酸涩,这样与伊纹被家暴的事实前后相联系,读者对伊纹的同情便从细微处积攒起来。
综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通感的运用往往会融入不同叙事进程下的人物状态,无论是房思琪、刘怡婷还是许伊纹,每一个角色的遭遇、个性和想法都能够以更加新奇特别的方式展现出来。
二、印记之二:象征
1886年《象征主义宣言》诞生以后,象征主义在法国蔚然成风,随后越来越多国家的诗人加入了象征主义的阵营。虽然象征主义并不是由波德莱尔提出和发扬光大的,但是正是在波德莱尔应和理论的基础上,诗人们开始关注并书写万事万物中所蕴藏的精神内涵,进而走入探索人类精神世界、反映思想观念的象征主义(李丹,2011)。象征是西方文论中应用广泛、含义极其丰富的一个重要概念。简单地说,象征就是用具体事物来表达特殊意义(Pulver,1982:19)。以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名篇《信天翁》为例:“海员刚把它们放在甲板上面,这些笨拙而羞怯的碧空之王,就把又大又白的翅膀,多么可怜,像双桨一样垂在它们的身旁。这插翅的旅客,多么怯懦呆滞!本来那样美丽,却显得丑陋滑稽”(钱春绮,1991:17-18)!信天翁被水手抓来放在甲板上逗趣,不同于以往“美丽”“碧空之王”的形象,显得“怯懦呆滞”“丑陋滑稽”,波德莱尔以此来表达自己被嘲笑、不被世人理解的孤独感。比起直抒胸臆,象征看似更为含蓄,但借用象征抒发的感情往往更加浓烈,同时文学性也更强。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主人公房思琪就有许多以象征来表达的情感,这些自白贴合思琪深受文学影响的思考方式,也更容易让读者共情。在遭受李国华的侵犯后,思琪觉得自己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林奕含,2018:86),她的痛苦不言而喻。在书中,除了这样典型的用来代表少女的花朵,林奕含也使用了一些非传统、新奇的喻象来象征房思琪、房思琪的状态以及她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口香糖和岛。
思琪精神失常被家人带去台中疗养后,怡婷怀念思琪,摸到思琪留下的物品时,她觉得“就像扶着古迹的围墙白日梦时突然摸到干硬的口香糖”(林奕含,2018:22)。口香糖黏在古迹的围墙上,摸到让人不适,也让人瞬间从置身古代的遐想中回到现实,被侵犯的思琪如同被咀嚼过、随意粘在墙上的口香糖,思琪发疯这个事实也如同墙体上无法剥落的干硬的口香糖黏在怡婷的记忆里,读者很容易明白在怀念与思琪的点点滴滴时怡婷突然想起思琪的悲惨遭遇时被拽回现实的痛苦。
“岛”是李国华的想象,他在侵犯思琪时想到补习班的其他学生,她们已经十六岁,而思琪才十二三岁,还是“洛丽塔之岛,他问津问渡未果的神秘之岛……趁她还在岛上的时候造访她”(林奕含,2018:42)。在李国华变态的想象中,远离人烟、未被踏足的岛象征着思琪的纯洁无瑕,也正是思琪如同远离世外的岛一般的原始诱惑力,勾起了李国华的情欲。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李国华是懂文学的,他用文学包装自己露骨的欲望以掩饰自己的丑陋。
总的来看,象征运用在小说中俯拾皆是,除了经典意象,林奕含也会选择对读者来说生异的意象进行创作,但读来十分贴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文学性和内蕴感也都得到了丰富。
三、印记之三:审丑美学
波德莱尔有著名的审丑美学,即与传统的以和谐、优雅、愉悦、完整等为美的理念背道而驰的以忧郁、痛苦、丑陋、厌恶等为美。在他眼中,人们普遍认为美好的事物不一定有值得歌颂的价值,丑陋的东西反而有值得挖掘的深层内涵。波德莱尔在《论泰奥菲尔·戈蒂耶》一文中称赞了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3)把丑陋上升到美的能力,他认为戈蒂耶所获得的审美幸福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丑陋在艺术加工下所形成的美丽,能够使欣赏者在精神上获得极大的快乐,这便是艺术的奇妙之处(波德莱尔,2008:77-78)。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化而为美,这便是波德莱尔持定的美学决心。
毫无疑问,李国华的所作所为是丑陋的,但作者在写作中却用了极美的笔触,让读者一层层剥开这个故事时获得审美的快感。林奕含使用了“初恋乐园”作为小说的标题,故事中的三個部分又分别被冠以“乐园”“失乐园”和“复乐园”,我们可以联系到英国作家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两部作品,在《失乐园》中米尔顿讲述了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被撒旦引诱偷食禁果而被上帝放逐的故事,在《复乐园》中他讴歌了耶稣禁受住撒旦诱惑带领人类重返伊甸园的成就。乐园即是伊甸园,与性相关,是永久的乐土。这样三个标题让小说在不断闪回的叙事中显得精妙且结构鲜明,但当读者掩卷便会发觉书中没有“乐园”,只有“地狱”。高雄金碧辉煌的大厦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创痛:性侵犯,家庭暴力,狭隘的婚姻,邻里间的冷漠自私虚伪算计,反讽之意便力透纸背(林奕含,2021)。
抛开导致思琪彻底发疯的房、李二人的最后一次接触不谈,林奕含笔下关于思琪与李国华相处的叙述多是美的,比如关于场景的描写:“金碧辉煌”“金色的流苏”“天花板像溪舟上下起伏”“黑夜伸手游进来”等等。当我们摒弃自己对故事的已有了解,恐怕很难猜到这么美、这么安宁的氛围中将要或正在发生对少女的性暴力。
此外李国华对思琪所说的话也并不全是污秽、粗鄙的,其中许多话语反而是高度文学化、艺术化的,比如引诗句告白、借用胡兰成的句子形容自己和思琪之间的关系,再比如思琪被雨淋湿后,上了出租车,李国华对她说“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林奕含,2018:65)。思琪觉得这个比喻很美,她被文学唤回一点快乐,打趣道:“我们隔了一个朝代啊”(林奕含,2018:65)。李国华没有回答,而是突然向前探身说:“你看,彩虹”(林奕含,2018:65)。如果只看这一段,他们的对话仿佛来自一对甜蜜的情侣。不难发现,李国华在丑恶的性侵犯中借用诗意的语言说服思琪爱上自己,合理化自己的暴行,以完成自己对思琪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强暴。以至于有些时候,思琪会突然恍惚,她似乎爱上了老师,老师从一个侵犯者变成了爱慕对象,自己对老师生出了柔情而非恨意:思琪坐在地板上观察老师睡觉,“看见他的鼻孔吹出粉红色的泡泡,满房满室疯长出七彩的水草”(林奕含,2018:95-96)。可以说,李国华在一定意义上成功了,李国华精美语言系统背后淫邪、狡诈、虚伪的面目也暴露无遗,他预想到思琪会说服自己爱上他来减轻痛苦,因为她不愿相信教授文学的老师会背叛文学犯罪。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对“乐园”的反讽妙用,对罪行发生地、加害者看似美好的描写,以及对房、李两人细小对白的浪漫化都将丑用美展现出来,给读者阅读上的审美体验,更凸显着美丽少女的悲剧遭遇。
四、结语
根植于故事中主要人物房思琪、刘怡婷、许伊纹、李国华与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作者自身的才气,《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文学气息氤氲缭绕,其中波德莱尔的创作特点的再现便是重要一缕。林奕含善于运用通感、象征以及审丑美学来帮助呈现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状态,调动读者全身上下感知细胞浸入与丑陋暴行截然相反的文字之美,思琪所遭受的身心强暴便逐渐显现出来。结合作者个人经历来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小说,也是现实;它在讲述一个虚拟角色的故事,也在再现千千万万个“房思琪”的经历。在笔者看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部极为优秀的小说,文学性与社会意义兼具。从书名到标题再到每一个文字,人们都能感受到作者超凡的文学功底、敏锐的感知力和艺术创造力。它触及了较少被书写的儿童性侵犯和家庭暴力,敦促着人们反思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Gusto,J.P.Charles Beaudelaire—Les fleurs du mal[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3:19.
[2]Pulver,M.Le Symbolisme de l'écriture[M].Paris:Stock,1982:19.
[3]波德萊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M].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7-18.
[4]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7-78.
[5]李丹.通感·应和·象征主义——兼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J].文学评论,2011,(1):179-183.
[6]李丹.通感、应和论与味、诗味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1):123-129.
[7]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8]林奕含.林奕含全部文章整理[DB/OL].2021-06-21/ 2022-11-09.
[9]刘波.《应和》与“应和论”——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基础[J].外国文学,2004,(3):5-18.
作者简介:
张泽,男,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2021级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