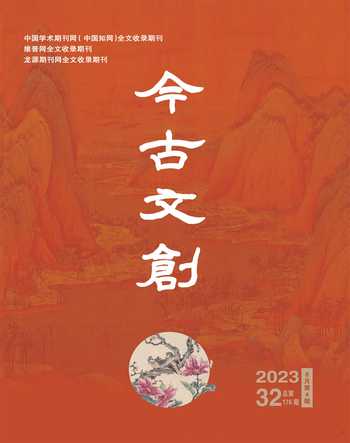张爱玲的复杂现代性
【摘要】张爱玲的《传奇》具备一种复杂暧昧的现代性,它产生于小说里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并置,通过时间、空间、人物三个维度表现出来。在时间上,体现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达成平衡,古老记忆与现代体验同时被激活。在空间上,体现为中西错杂、新古并置的细节与风格对照。在人物上,体现为在中西文化的拉扯之间挣扎与彷徨的一系列形象。
【关键词】张爱玲;《传奇》;现代性
【中圖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01
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话题,关于其内涵以及在不同作家笔下的表现已经有诸多论述。在这之中,张爱玲的观察视角尤为特别,她同时从有着中西烙印的文化和现象中汲取灵感,从正在经历新旧转换的社会中挖掘出了一份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因此她的现代性书写注定无法简单地用某种思潮、流派加以界定。本文以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为中心,探讨她笔下的现代性如何在时间、空间、人物主体的配置中得到展开。
一、时间:过去、当下和未来
“五四”时期为中国树立的现代性,意味着新与旧的截然两分,它号召人们告别昏沉的旧时代,拥抱与世界潮流接轨的新时代。这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产生的新的历史意识,它基于一种信奉着进步理想的线性时间观,暗含着今胜于古、新胜于旧的价值判断。但张爱玲拒绝做出如此斩钉截铁地处理,面对社会历史的巨变,她没有急于在新与旧之间做出选择,而是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找到了耐人寻味的连接点,古老记忆和现代体验在她的文本中同时被激活。例如,《金锁记》的开头写三十年前的上海,为读者娓娓道来一段家族恩怨,而结尾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①暗示过往和当下、未来之间有着不能割舍的联系,在新旧时代的交替处,人们携带着古老的记忆继续生活。《金锁记》是一个悲怆的故事,其首尾呼应的结构很容易使人想到历史的循环往复。但对于张爱玲而言,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呼应还有着更丰富的意味,比如在《中国的日夜》里,她写申曲唱词里描摹了一个“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使她心中产生稳妥的欢喜。她的盛世理想倒也并非怀古伤今,当她拎着吃食走在路上,她庆幸无论快乐忧愁,“总之,到底是中国” ②。对古中国的悠远怀想,和对现世中国的切实把握,就这样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张爱玲的时代体验。而在《倾城之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有着更为多层次的体现:女主角白流苏秉承古老的生活哲学,从当下找寻凭依之物,以应对潜伏在未来阴影里的惘惘地威胁。
《倾城之恋》开篇便是新与旧两个世界的时间的鲜明对比:“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 ③时钟将两个意象勾连在一起:高速率运转的都市,和落后于时代、散发着昏暗腐朽气息的大家族。在白公馆的时间中,千年时光也如同一日,于是离婚的白流苏为了寻求再嫁的机会,从静止的古中国的时间里脱身,前往香港重新拨动生命的时钟。但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并非发生在由静到动的线性时间之中,而是在凝固的瞬间。港战爆发,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千疮百孔的墙下躲避炮火,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④二人在生死关头经历了彻悟,充满不确定性的挑逗、试探,在这一刹那终止了。故事的终点,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瞬间。白流苏成功嫁给范柳原,得到一张长期饭票。结尾暗示范柳原依然在外拈花惹草,白流苏的将来想必也不会一帆风顺。但结尾处她只是笑着站起了身,把蚊香踢到了桌子下面,一副已经十分满足的模样。白流苏的故事最终定格在了一踢之间。纵使前路危机并未完全解除,似乎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一刻的满足。这两个重要的瞬间,代表着张爱玲对“现时”的意义的肯认,而这份意义可以在范白二人对未来的不同想象中得到更明白的阐释。
白流苏最初与范柳原接触时心态十分急切,但她没有从他那里获得立即的承诺。相反,范柳原把两人修成正果的时间节点安排在了未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⑤直达末日的思考深度显然与范柳原并不相称,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内心的突然表白。但张爱玲并未留滞于文明尽毁的怅惘之中,而是快速地将笔锋一转,拉回到了流苏的视角。流苏未解深意但也不以为意,只觉得恋爱中女人不懂男人,但结婚后的家务事女人比男人在行,于是找回了心理平衡。从文明毁灭到“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故事的基调在想象的跳跃中产生了两个面向:思考未来与讲求实用。人们在广漠的荒凉世界中常怀惴惴不安之心,但现世事务带来的充实感,又帮助他们重建了对生活的信心。
有学者指出张爱玲的思想中存在和一战以后西方文学中常出现的“现代末日意识”相近的一面 ⑥。张爱玲在香港求学期间亲身经历过战乱,这或许是她的末日想象诞生的契机。另一方面,她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十分熟悉,这也构成了她的思想资源之一,比如她的作品里多次提及以擅长构想反乌托邦的威尔斯。战争带来的震悚,让西方作家的人文理想走向破灭,转而刻画社会人生的荒谬和灰暗,张爱玲与他们有部分相通之处,她感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⑦。张爱玲不抱有线性前进的乐观展望,但也不会长久停驻于反理性的荒原,于她而言,日常生活中的分分秒秒里就保留着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它是某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在白流苏这样的女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白流苏自诩一个过时的人,范柳原则意味深长地评价道,真正的中国女人是最美的而且永不过时的。白流苏的生活智慧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韧性,她就像张爱玲所说的“蹦蹦戏花旦”:“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怡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 ⑧由此便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她的现代性不在于否认过去、走向未来,也不在于抛却希望、陷入幻灭,而在于古老却历久弥新的蹦蹦戏花旦的哲学。
二、空间:异质与对照
《传奇》中的篇目,多以上海和香港两地的都市生活为背景,这也是张爱玲实际生活过的两座城市。在现代文学流派中,新感觉派最常将都市尤其是上海作为书写对象,这一派作家笔下的都市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堆砌,给人以声、光、电的感官刺激,将都市塑造为迷人而危险的欲望森林。在新感觉派的浮华都市以外(这或许更像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想象,而非现实的中国都市),张爱玲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都市形象,它不依托于舞厅、夜总会、影院、红男绿女等典型的都市意象,“相反,她那些细腻的居住空间意向突出的是占据‘时代总量的日常生活场所” ⑨。她常常不厌其烦地描述空间内杂错的中西物象,在物件的陈列和生活的细节中自然而然地勾勒出西方文明影响下现代中国的变与常。比如《花凋》里写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郑公馆:洋房里有无线电、留声机、最新的流行唱片,开饭的时候下仆们却一同挤在八仙桌的长板凳上。追随时尚潮流无法掩饰郑公馆的衰颓之势,拥挤的八仙桌将它的狼狈和促狭暴露无遗。新鲜闪亮的西方器物和八仙桌,对于彼此而言都是异质的存在,然而郑公馆的人们就在如此不协调的氛围中生活着,用华丽的物件粉饰着朽坏的生命,从而衍生出一幕幕悲剧与闹剧。《留情》里杨老太太的房间,也体现了一种新旧之间的诡异对比。房间内有金属写字台、金属圈椅、文件柜、冰箱、电话等各式新颖的外国东西,但里面摆着抽鸦片的烟铺,躺着穿扎脚裤的老太太。物质的极大丰富没有为这里吹入开放的新风,相反,这里凝聚着“阴阴的,不开窗的空气” ⑩,旧时代的阴森气息始终挥之不去。
《传奇》里的许多角色,对西方和现代的认同是高度基于物质的,但无论他们怎样热情地追求象征着先进性的物质,被其界定为旧时代遗存的东西,依旧如影随形,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便是《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他把“物”视作某种生活方式的标志和本质,因而他对西方文明的仰慕之情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于物质的狂热。他将崭新烁亮的医生器械、精致的电疗器、整洁的白外套等同于洁净、高雅、文明的生活,自认为他可以凭借“高人一等”的物质趣味,与庸俗土气的家人区隔开来。所以他路过华美的洋房时,听到里面传出与他的现代想象格格不入的绍兴戏,便不屑地以“文化的末日”稱之。当他继续前进,途径唱绍兴戏的公馆时,再次响起的熟悉腔调却让他开始反省:“绍兴戏听众的世界是一个稳妥的世界——不稳的是他自己。” ?无论在洋房还是公馆,绍兴戏都能找到它存在和生长的土壤,可见传统里某些根深蒂固的成分,并不会因晚清以来短短数十年的冲击而受到动摇,这就导致潘汝良那种迫切渴望新旧两分的现代性追求,迟迟无法向古老的记忆告别。当他看到自己所爱慕的西方女子沁西亚不过也是嫁了普通的丈夫、过着拮据的生活时,西方文明于他而言,就像因卧病在床而神色恹恹的沁西亚一样,完全褪去了神秘的魅力。
在张爱玲眼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或许已经在她的好友炎樱所做的《传奇》封面里尽数展现——一个高大的摩登女子从栏杆处探出身来,窥视晚清仕女图中所描绘的古中国生活场景。现代人的目光、古时人的底子,二者互为异质性存在,但又奇妙地出现于同一个空间内,两种风格的相遇与碰撞,在张爱玲笔下演绎出耐人咀嚼的风味。
三、人物:交织与拉扯
张爱玲说自己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透过他们,读者可以体味到社会人生在传统和现代的过渡期发生的变化。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多重文化因素交织,在转型期中国的躯体上留下分裂的痕迹。
第一组有代表意义的是从国外归来的男子形象,包括范柳原、童世舫、王振保等。他们切身感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但内心仍然时刻受到来自保守的传统的召唤。范柳原声称自己是一个比正统的中国人还顽固的“中国化的外国人”,他最欣赏的女人类型就是白流苏这样“真正”的中国女人。然而他对家乡抱有的幻想,在亲眼看见这里的现实情形后荡然无存。中国的“现代”面貌令他失望,于是他转而向他自己的“古典”中国想象寻求慰藉,并将这种心理投射在白流苏身上。童世舫留洋归来,在长安身上看到了他怀念的古中国,被告知长安抽鸦片的时候,他顿时感到了幻灭和落寞。王振保对天真活泼的玫瑰虽有心动,但因为觉得她这样的女人在中国属于异类,又狠心拒绝了她。范、童、王并未接受国外的新思想的感召,他们理想的婚恋对象,仍是符合中国传统社会规范的女性,这种追求甚至可以上升到精神皈依的层次。“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 ?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他们反而更愿意求助于某种永恒的价值,并为价值的失落而深感痛苦。
白流苏、吴翠远的故事可以看作对于“娜拉出走”这一母题的回应。伴随着五四时期女性独立意识高涨,“娜拉出走”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现代文学意象,它象征着女性与传统家庭告别、追求自由与个性的勇气。而关于娜拉走后如何,张爱玲的回答是“走到楼上去”,现实为女性谋生设下的重重障碍终将让她们在出走后走上复归之路。白流苏不是新式革命女性,她出走的动机并非追求自由独立,而是寻找一个男人做她的庇护所,对她而言生命的第二春就是离开衰颓的白公馆,组建新的家庭,尽管这算不上一个“大彻大悟”的结局,但也是白流苏能为自己谋得的最佳出路。《封锁》中的吴翠远是真心渴望冒险的,封锁期间的电车为她创造了暂时逃离家庭和社会规训的空间,但随着封锁的解除,生活恢复正轨,她的自由也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由革命话语塑造的光明的娜拉形象,在现实中往往无路可走,她们在现代社会的见闻并不能转化为足以使她们脱胎换骨的能量。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传奇》中比较少见的竭力与旧时代阴影抗争的角色。他厌恶自己的出身,他渴望诞生在父母自由恋爱的家庭中,和飘荡着晚清淫逸气息的原生家庭一刀两断。他心中真正的父亲是他所仰慕的教书先生言子夜,通过“换父”而重获新生的妄想最终导致他的疯狂,他在极端苦闷中选择对从小生活在他的理想家庭中的言丹朱施加暴力,发泄对人生的愤懑绝望之情。尽管他有意反抗,但作为旧式家族的后代,他的结局已无可逆转,他命中注定要成为时代更替中的可悲牺牲品。
《传奇》中的角色是老中国步入现代纪元之际的彷徨者,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中经受着惨烈的拉扯,或将古老记忆视为永恒的精神故乡以寻求心理安慰,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放弃幻想与抗争。旧时代在他们的心灵和命运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阻碍了他们成长为真正的时代新人。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揭示了“现代性”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所必然具有的特殊的一面。
四、结语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地事物不过是例外。” ?张爱玲对时代的敏锐观察,决定了她笔下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它并不完全是古老记忆的对立面,相反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爱玲在社会历史的惊天巨变之中,重新与旧的交织地带处,发掘出了丰富的可供表现的对象。她的《传奇》构建了一个古中国气息与现代经验交错的时空,为那些徘徊在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多种对立选择之间的灵魂提供了立足之地,让他们复杂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得到了表现。
注释:
①③④⑤⑦⑧⑩?张爱玲:《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第46页,第81页,第65页,第287页,第289页,第299页,第245页。
②???张爱玲:《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第175页,第176页,第175页。
⑥刘志荣、马强:《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2期。
⑨刘琅、桂苓编:《女性的张爱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传奇[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2]张爱玲.流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3]刘志荣,马强.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J].中国比较文学,2000,(02):19-34.
[4]刘琅,桂苓编.女性的张爱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作者简介:
王思炜,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