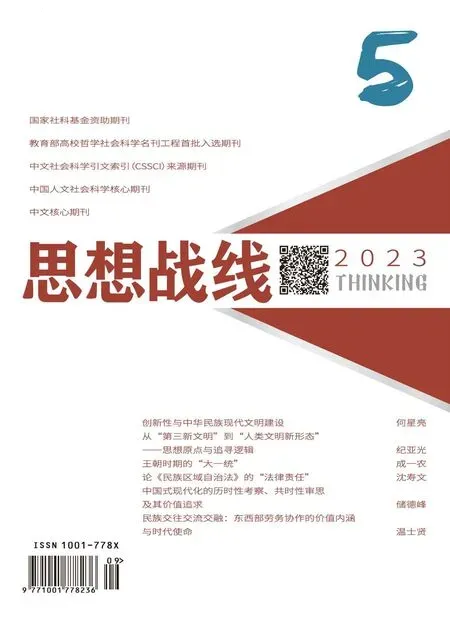对戏剧及宝卷中关羽形象的跨文本研究
李永平
以禳灾角色为内核的斩妖、伏魔仪式遍布全世界。弗雷泽《金枝》“替罪者”一节介绍了世界多地居民或巫师驱赶魔鬼(妖精)的活动。(1)[英]弗雷泽:《金枝》,汪培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58~899页。王宪昭在《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有“斗妖魔”(W8830-W8869)母题。(2)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95~1399页。与中国的傩戏斩妖、伏魔一样,西方的狂欢节,巫师们佩戴面具舞蹈来驱魔除邪。在德国、瑞士的德语区,人们举行狂欢节来驱除冬天的魔鬼。(3)[法]班文干:《中国的傩戏与欧洲的狂欢节》,新月,春熹译,载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中国傩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总第12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4~97页。中国则流传方相氏打鬼、钟馗伏魔、关羽斩妖、包公审鬼等。关羽被儒家认为是“忠义仁勇”的代表,因此更容易进入中国民间信仰,为流民社会、商帮所敬重,赋予他多种角色,如战神、治水神、正义神、科举神、财神、行业神、送子神。在诸多神祇之中,民间信仰的祈禳、逐疫功能,是诸仪式、角色扮演的核心。
俄罗斯学者李福清(B.Riftin)对关羽伏禳灾魔文本有细致的分析,涉及关羽出世传说、庙宇传说等,显灵传说中有关羽斩妖、伏魔事迹。(4)[俄]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明滨编选,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7~99页。美国杜赞奇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关羽神力的扩大和围绕关羽形成的不同类型民间叙事的层累问题,他将其称为“复刻”(superscription)。(5)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39~148.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鲁愚等编《关帝文献汇编》(6)鲁愚等编:《关帝文献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包含了关圣帝群圣迹图志全集、关圣帝君汇考、关帝圣迹图志、关圣帝君征信编、关帝全书、关氏家谱、关圣陵庙纪略,可以说是关帝文化研究重要资料的汇编与集成。重要的是,这些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关羽斩妖、伏魔。黄华节在《关公的人格与神格》第6章关羽的神职与神能中提出,“关公的神格化,发端于北宋末,大定于元明间,至满清而登峰造极”,(7)黄华节:《关公的人格与神格》,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85页。并且将《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第9卷中关羽的56则神迹分为武功、斩妖两大类,以及治水旱天灾、救人疾病、惩治淫邪不孝及济助忠义孝慈等小类。洪淑苓考查关羽救灾神迹中的解池斩妖、拯救水灾,治病去邪疫类中的去疫、驱邪均涉及关羽斩妖、伏魔的相关传说。(8)洪淑苓:《关公民间造型之研究——以关公传说为重心的考察》第5章,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年,第349~415页。
以忠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学界论述很多。以斩妖、伏魔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传统,这些传统文本包括神话、民间故事、图像、仪式、传世遗迹等活态文本,与产生这些符号综合体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一起,构成“互动仪式链”,我们称之为“文化文本”(cultural as text)。它作为隐蔽秩序,支配着特定民族民间文化中的言说与书写。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文本研究,要在文化大传统更为深远的文化原型或文化原编码系统,包括语词文本、语词的活态语境(即仪式歌舞展演和语词所指对象)、物与图像及其证据间性呈现出的动态的意义生成空间,通过具象的文化符号尤其是核心符号物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因革,重建文化文本衍生脉络,凸显中国文化的意义生成“隐蔽秩序”。本文搜集与关羽相关的部分文化文本,分类梳理,揭橥蕴藏在文本中的禳灾神话,探讨这些文化文本与祭祀仪式之间的跨文本旅行。
一、仪式剧中的关羽禳灾、逐疫
面临极度干旱、地震、瘟疫等令人恐惧的自然灾害,经历恐怖、暴力等意外伤害,深陷阴谋、诈骗、诅咒、构陷等境地,这些就像躲在边远(边缘)山区的盗猎者那样,从陌生阃域发出的现实的或想象的威胁和焦虑,使人类从远古以来就形成受迫害的集体想象和深层焦虑,它孕育了成年礼、禁忌、禳灾、献祭等一系列仪式活动及潜意识等象征性编码体系。(9)李永平:《禳灾与记忆:宝卷的社会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4页。这套编码体系成为文化大传统,它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持续影响民间文化流传的逻辑。继商周方相氏之后,民间的拣选机制形塑了颛顼、关羽、天师、钟馗、包公、城隍等形象。镇魂祭祀戏曲及各类表演艺术,最接近角色装扮和仪式搬演,担当着娱乐神灵、驱祟逐疫的责任。每当遇到灾荒、年馑、瘟疫等不幸时,先民就会用古老的禳灾逐疫形式——傩戏来祈祷神灵,驱除邪祟,恢复平安,这类禳灾驱瘟戏曲就包含关公戏。
宋高承《事物纪原》称周时岁终的“索室驱疫”是驱傩之始,可见沿门逐疫是民间傩仪中最早、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在全国很多地方,掩门逐疫时百戏杂陈,队伍庞大。关公戏至少在宋代已经出现,元代关羽故事被大量搬上舞台,至明清时,已有相当数量的以关羽为主角的杂剧、传奇和地方戏。中国戏曲史上因此出现专门演出一个人的事迹的剧种——“关戏”。(10)宋洁:《关公形象演变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年,第152~154页。与沿门逐疫相对应,关公戏的搬演同样有祓邪除祟、禳灾逐疫的功能。元代戴善甫创作了《关大王三捉红衣怪》。(11)该剧本已佚,剧名见于《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参见钟嗣成《新编录鬼簿》卷二,楝亭藏书,民国十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康熙扬州诗局重刊本;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二,涵芬楼秘笈。后者中剧名记为《红衣怪》。明代万历二年(1574年)《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简称《礼节传簿》)中关羽斩妖的戏剧有《破蚩尤》《关公斩妖》《关大王破蚩尤》3种。(12)《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明万历二年(1574年)手抄本影印,载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中华戏曲》第3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礼节传簿》中出现的关公戏共有队戏《破蚩尤》(后文有杂剧《关大王破蚩尤》),队戏《古城聚义》,正队《过五关》(后文有杂剧《五关斩将》),队戏《斩华雄》,队戏《关公斩妖》,队戏《斩关平》,队戏《单刀赴会》,队戏《独行千里》(后文有正队《关大王独行千里》),队戏《挡曹》,队戏《关公出许昌》及舞曲《关大王破蚩尤》(以在原文中首次出现的先后为序)这11种。这表明在明代为迎神赛社而举行的祭祀仪式中已经存在相当数量的关羽逐疫戏。
莆仙连台戏《三国》第十六出《三妖成铁》中,关羽指点降服“男女难以禳治”的三妖——白鹤精、青龙精、白蛇精。(13)吕品,王评章:《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第12卷剧本,杨美煊校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山西晋南一带的锣鼓杂戏,其中《白猿开路》有关羽以火德星君的身份帮助人们收服鱼精的情节。(14)窦楷:《锣鼓杂戏——一种色彩淡化了的傩戏——兼谈〈白猿开路〉》,载中国戏曲学会,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中华戏曲 中国傩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总第12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7~238页。
在驱邪除祟的仪式性表演场合下,关公戏体现了逐疫禳鬼、祓邪除祟的仪式功能,“祭中有戏,戏中有祭”,例如《五关斩将》《关云长大破蚩尤》《古城会》等。(15)容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戏剧扮演的二重身份,决定了戏剧演员介于人神之间。从这个角度而言,关公戏演出就是一场降神禳解的演剧仪式。(16)陈志勇:《“关公戏”演出禁忌的生成与禳解》,《戏曲研究》2008年第1期。
在民俗仪式下,关公戏的功能在于驱邪逐疫,这多表现在傩戏和特殊的仪式中。浙江省、江西省、安徽部分地区的开台、扫台仪式,山西省上党队戏、广东省正字戏、安徽省池州傩戏等等,这些地区的关公戏其实就是“祭祀的仪式场景”。开台、扫台仪式中多出现关羽、周仓、青龙偃月刀,演员在舞台的四周挥刀,有时还会出现扮演妖魔的演员或道具,这些仪式正是通过关羽(周仓)扫除妖魔而具备禳灾功能,这承载了人们对身体健康、平安吉祥、作物丰收的美好期盼。再者这些仪式中演出关公戏,其中有大闹的场景,戏剧中关羽大杀四方也意味着关羽扫除邪魔,保护着人们的平安。浙江省新建戏台或重修旧戏台的开台仪式中,关平、周仓引关羽上台,关羽口中念着:“……四方恶鬼必须远避,胆敢违抗者,青龙刀下取尔性命。”念完舞刀,舞毕又念“四方恶鬼都被驱赶远避,不敢再来……”扫台仪式中,由戴关羽面具的演员手持青龙刀舞“摆四角”,每扫一下,都要顿一下脚,大喊一声,完成“摆四角”,结束洗台。(17)徐兆格:《平阳戏曲史略》,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100~101页。以前温州昆班演出于正戏之前的祝福节目——打八仙中有关羽、周仓和关平,而洗台仪式中,戴关公面具的演员同样要拿青龙刀圆场,舞四角,鸣放鞭炮。最后一场如果是关公戏,洗台仪式则可以省略。参见吴新雷《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0页。有的地方祭新台时,关羽手拿青龙偃月刀与韦陀一同杀向台上的天煞、地煞,青龙偃月刀上挂有一大串点燃的千响鞭炮,关羽从上台角到下台角来回挥刀。关羽下台,扫台也就结束。(18)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浙江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1997年,第650~651页。
江西省戏班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会由花脸扮关羽拿大刀出来扫台,东南西北四方都要扫到,口中念道:“天皇在,地皇在,玉帝命我扫花台,一扫风调雨顺,二扫国泰民安……”意味着将妖魔鬼怪扫除干净,保障一地安宁。(19)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年,第697页。上饶等县每年农历八月、九月会演出“太平戏”,以演戏的方式庆祝丰收,祈求平安清吉。演戏结束时,关羽要用大刀扫台,表示将恶鬼冤魂扫地出门,保佑地方太平清吉。该地演“太平戏”的风俗延续至今,不过目前不再举行扫台驱邪仪式。(20)熊良华:《上饶民俗风情荟萃》,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26~27页。民间信仰认为瘟疫的流行在于人的道德堕落、不讲诚信、奢侈浪费,人们要想躲避病魔,就必须讲究诚信忠孝,颂经祷告。
安徽省池州傩戏演出结束,便是“逐疫送神”仪式。各个村子的逐疫仪式不一,有的是关羽驱疫,有的是钟馗捉鬼……正月十五的仪式性演出中,有驱邪逐疫仪式的关羽斩妖,还有送瘟神仪式的放河灯等。(21)张媛媛,江小角:《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在贵池、青阳地区的傩祭仪式中,《关公斩妖》属于以“娱神”为题材的剧目,内容为驱逐疫鬼。结束全部演出活动之前,必须演出《关公斩妖》,以求驱邪、祈福、丰收,这样整个仪式活动才能宣告结束。(22)董诗珠:《皖南山区的古老剧种——傩戏》,载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戏曲研究》编辑部编《戏曲研究》第6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279~284页。以关羽斩妖为主题的驱邪逐疫仪式参与者,通过仪式实现自我更新,与过去的危险和污染划清了界限。
二、关羽“斩妖”“逐疫”仪式中的禳灾“圣迹”
与关羽相关的宝卷说唱同样数量繁多,其社会功能和傩戏中的“唱神歌”功能一样,有逐疫的功能。据学者调查,当代河北冀中平原多个县镇的农村中有在酬神、祈福以及行丧仪等民俗活动中演出的“音乐会”组织。他们进行的演出活动中有演唱宝卷这一项,其中就有《伏魔宝卷》。(23)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53~254页。该活动所演唱的宝卷除《伏魔宝卷》外,还有《后土娘娘卷》《后土皇帝宝卷》《东岳泰山十王宝卷》《白衣观音送婴儿下生宝卷》等。而酬神、祈福、行丧仪这类民俗活动也多带着禳灾的目的。
《护国佑民伏魔宝卷》(24)《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的版本主要有12种。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06~107页。可以降妖、逐疫,供奉、宣讲(读)、抄写、助刻《伏魔宝卷》的仪式也有扫邪除魔的效果。例如“请真经,宅内供,邪魔不侵”(品第四)。“诸魔邪神,一扫无踪”(品第九)。“圣天子,封伏魔,斩妖除怪”(品第九)。“斩妖魔,扫宅内,显应昭昭”(品第十二)。“想先年,有妖魔,混乱世界。我一怒,显神通,剪草除根”(品第十七)。“有邪魔,要宣读,《伏魔宝卷》”“夫听讲伏魔宝卷,伏魔者降伏,诸魔不侵,诸邪不染,邪不能侵”(品第二十四)。(25)濮文起:《民间宝卷》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486~578页。
同样的,《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26)据车锡伦先生统计,《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的版本主要有3种。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参见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85~583页。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吾今助叙,正为此经,能扶国救民,降邪伏魔,远镇海外,近服中华”。(27)《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68页。(达摩祖师叙)
(1)“堂前供奉一卷,亦能镇伏邪魔。”(28)《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79~480页。(司命张大仙叙)“人有能受持斯经者,真实宣诵灵文,邪魔闻声远避。”(29)《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95页。(纯阳祖师叙)“雷声震动,魑魅魍魉,妖魔神怪,闻声远避,谁敢探头背听,而窃视也。更有多年狐精,媚附善良,有能诚信,宣伏魔宝卷,立有家宅灶神,报于大帝,急差天帅,来扫出宅门,而再不犯境也。”(30)《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28页。“身体力行(吾经),上可以成仙作佛,中可以扶国佑民,下可以制伏邪魔。”(31)《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60页。(关圣帝君叙)
(2)吾帝之经,上可以报答皇王,享太平之鸿福。中可以降伏邪魔,而除灾病。下可以供而奉之,逢凶化吉。(32)《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04页。
(3)偈曰:降序刻经动圣天,只为降魔镇三关。飞龙跨虎游天外,择人造物掌握间。(33)《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04~505页。(岳武穆序)
(4)要有人请真经,宅内供奉者,凡人有诚信者,请伏魔经宅内供奉,可避妖邪,可免灾祸,诸凶不侵也。(34)《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注解》,马西沙《中华珍本宝卷》第3辑第29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34页。
一方面,《伏魔宝卷》产生年代,至少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关羽被敕封为“伏魔大帝,远镇天尊”之后。另一方面,《伏魔宝卷》作为关羽宝卷的代表,充分发挥着禳灾的功能。(35)李永平:《禳灾与记忆:宝卷的社会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另外,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在越南河内发现一册题为“礼关圣伏魔真君科”的民间科仪卷手抄本,据他推断应当是祭祀关帝以驱邪逐疫所用。(36)[俄]李福清(B.Riftin):《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尹锡康,田大畏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关羽宝卷的数量繁多,前文以宝卷为代表展开论述,由于宝卷属于劝善禳灾的善书的一部分,下文主要以各类善书文本展开考查。
与戏剧、宝卷相表里,斩妖、逐疫的神话、传说遍布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民族的斩妖、逐疫的神话、传说的主角不同,他们大多具有本土特色,围绕这些角色的形成,有极具地方性的文化编码传统。某一特定的神灵——战神,要连续地受人尊崇,其必须具备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连续阐释的内在品质。关羽逐疫、驱魔、斩妖“圣迹”神话主要裒辑于《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关帝事迹征信编》等善书中,依照时间先后,笔者梳理了关羽“圣迹”。《关帝历代显圣志传》有关羽斩妖、逐疫灵应的“圣迹”,随文附有多张“圣迹图志”。其中“解州大破蚩尤神”“延庆寺显圣诛淫僧”“燕南丹救贾一鹗父母”“广平城击妖救水灾”“福清县神像斩山魈”“秀水县两救陈孝廉”“潞河率龙神救客船”(37)《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古本小说集成》之《关帝历代显圣志传》,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26页、第43~53页、第70~79页、第145~149页、第190~199页、第222~230页、第230~240页。等7则故事与关羽斩妖、伏魔有关,涉及的神话母题有洪水母题、禳解母题等。
《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38)卢湛:《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卷三《灵应考》,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敦五堂重刊本。(简称《圣迹图志全集》)卷三灵应考共53则关羽神迹传说,其中有9则斩妖、伏魔传说,两则与《关帝历代显圣志传》相同。涉及的禳解母题主要有旱灾、瘟疫、洪水、疾病等。“圣迹”的主要情节见表1。
《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圣迹图志全集》等善书中留存的关羽斩妖逐疫的“圣迹”比较丰富,其他典籍的文本则比较分散。这些文本多生动、有趣,充分体现了斩妖、伏魔的母题,并且多次出现瘟疫、疾病、洪水、旱灾等母题,背后蕴含着斩妖、伏魔的神话观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8世纪,社会精英阶层崇拜救世神,扶乩成书的现象广泛存在。很多新的经书由救劫神祇乩占而成,有鸾书、谶文、圣人传记等。其中以扶乩形式而来的“神授天书”,是经典制造者使信众相信教义唯一性的方式。《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是在《忠义经》基础上附加了具有强烈驱魔意味的训文《三界伏魔关帝忠孝护国翊运真经》所形成的复合体。(39)[法]高万桑,Luoyang:《关帝乩文的经典化》,《道教学刊》2019年第2期。除了经书和图谶,19世纪初期还产生了大量关帝训文。训文赋予关帝禳灾—救劫联动的社会角色。
三、关羽“斩妖”“逐疫”仪式的跨文本演变
传统中国世俗权力本位的社会结构,形成对文化价值的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关羽成为传统民间社会价值建构的重要靶标。为了消除灾异,民众求助于外力——神秘或特殊力量的鬼神,认为灾异由神秘力量操纵,只有正义的神灵压胜或者斩杀作恶的妖魔,灾异才能解除,这便形成人(神)和妖的二元对立。赓续自远古的降妖伏魔神话观念,无疑是禳灾英雄信仰形成的逻辑基础。在禳灾、逐疫、祈福纳吉的民俗活动中总能看到关羽的身影。学者杨庆堃认为民间英雄崇拜有“三个阶段周期性发展模式”,即:
首先,信仰始于一场危机,以及需要以诸如爱国、勇气和自我牺牲之类的主导性价值,号召民众应对严峻局势。其次,发展出以神秘力量和神话传说为基础的信仰,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第三,新的危机会使政治集体化价值再次凸现出来,与神秘信仰和神话故事交织在一起。(40)[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成都:成都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6页。
关羽崇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非常接近该模式。关羽生前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是他有着自己的人格魅力。他正直、勇猛、讲义气、坚强,最后以身殉国。即便他死后,也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以不同文本形态在民间流传着。经历代帝王的不断加封,明清关羽崇拜发展到了顶峰,各种关羽显灵的神话、善书、图谶和关庙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这种循环重复,强化了英雄逐疫的社会正能量,并逐渐向着禳灾的深度模式——醒世救劫、护国佑民的方向演变。
以劝善救劫为主要角色的善书有关羽斩妖、逐疫救劫的文本。清康熙初年成书的《关帝忠义觉世真经》(41)《关帝忠义觉世真经》,王见川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影印本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6年,第1~56页。劝化民众遵守“纲常伦纪”,做到“忠孝节义”“若负吾教,请示吾刀”。其中多处提及关羽或善书本身可以斩妖、除秽、禳灾逐疫乃至护国佑民。比《觉世真经》《明圣经》面世稍晚的《指路宝筏》中有一篇很长的神启文章,其中不断向我们强调着“关公救世”的主题。这段神启文字的开头详细描述了关羽的身姿,他的青龙偃月刀,还有他的赤兔宝马,然后讲述了关羽一生的忠义,尤其是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仪式事迹。接下来,这篇文字以诗歌体裁直抒主旨:
钦承佛命下天庭,不惜临鸾谕众生。各把杂心齐扫净,还原返本去修真。
下元末劫起刀兵,水火虫蝗瘟疫临。无极天尊心不忍,悲悲切切度残零。
一为善良除孽障,二为国家定太平,三与诸生把善积。指明孚路好回程。(42)《指路宝筏》,第38a-b(566)页。
关羽在当时的制度性框架中扮演着扶危济困者的角色,而这一制度性的框架极其适合传播道德教化类的训谕,因为当时朝廷允许人们在“宣讲”仪式活动中聚众听讲。就这样,除了原本就有的人间道德监督者的角色,关羽又承担了某种护国佑民救世的角色。汉学家田海对此评价认为,我们并不能直接以“弥赛亚”来解释这个角色,因为此时这一神祇道德启蒙和监督的色彩依然是隐晦不明的。(43)[荷]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王健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第294页。
《五圣伏魔真经》(44)《五圣伏魔真经》,王见川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影印本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6年,第531~599页。(又名《五圣伏魔灵经》《五圣伏魔经》)中有多处关羽扫邪除秽、斩杀妖魔的例子。以下诸例中,例5提到关羽“诛盐怪剿蚩尤”的功绩。对瘟疫、旱魃、山精、水魅等妖魔的降伏,恰恰体现着关羽斩妖文化文本蕴藏的斩妖、伏魔、禳解以及旱灾母题。
(1)斩妖缚邪,杀鬼万千……魔王束手。(45)《五圣伏魔真经》,王见川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影印本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6年,第538页。(净天地神咒)
(2)法灭魔精,内魔既荡,外魔亡形……一切魔魅,永化尘风。(46)《五圣伏魔真经》,王见川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影印本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6年,第539页。(伏魔神咒)
(3)李凝阳赞曰:“……大帝垂经施法雨,妖魔齐服免冤缠。”(47)《五圣伏魔真经》,王见川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影印本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6年,第558页。
(4)魔王束手,鬼魅潜行,灾消祸灭。(48)《五圣伏魔真经》,王见川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影印本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6年,第559页。(玄蕴咒)
(5)……时显灵异,除邪歼怪,保国卫民。自唐宋以迄于清,时多显应,如诛盐怪剿蚩尤,其尤著也。故封崇宁……妖魔慑服……(49)《五圣伏魔真经》,王见川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影印本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6年,第590页。
(6)山川震陷,盗贼妖魔,何以召之。民德偏颇,何以解之,大帝伏魔。(50)《五圣伏魔真经》,王见川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影印本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6年,第593页。
前文所及,不仅仪式剧本身有逐疫的功能,其中扮演关羽的演员有“显圣”的角色担当。当“关羽”出现在诸如《斩颜良》《过五关》《战蚩尤》这样的武戏中时,他更多地被视为神而非一位历史人物。这使得这些戏剧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斩妖逐疫“显圣”救劫的功能。即使在封建社会晚期的世俗性城市戏园中,那些扮演关羽角色的演员也被认为是神灵,他们会遵守禁忌,并且在演出中举行“坐龛”仪式,以表明他们将成为神祇以及他们再次回归普通人的阈限时间。吴真搜集资料发现,咸丰二年武打身段场面的《青石山串头》,为彰显神灵关羽的威仪,扮演关羽的演员一直端坐于高台神龛内,场上关平、周仓带领众神将与狐妖及小妖仪式性打斗15场。“坐龛”成为晚清时期昆腔、高腔、京剧舞台演出《青石山》的固定程式。(51)吴真:《禁忌、行当、剧场:近代戏曲的非文学演进机制》,《文艺研究》2022年第1期。大型戏剧总会包括一些仪式性的短剧以及相关的崇拜行为,以此来驱赶舞台上的恶灵,为演员和观众带来好运,而其中绝大多数的角色并不带有神圣性。(52)[荷]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王健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第186页。
从神话观念角度看,神话观念的核心内容会随着社会情境获得持续的阐释。这种特定的演进形式被称为“刻划标志”。通过增加或重新发现新的因素,或者是给现有的因素一个特定的倾向,这样确立新的解释。关羽生前是一名猛将,又极具正气,当然会对鬼怪起到震慑的作用,因此人们将关羽作为驱邪神供奉,请他驱邪逐疫,承担道义,扶危济困,救助社会。(53)郑土有:《关公信仰》,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即使是新的解释能占据主导地位,以前的看法也不会消失,而是与之建立新的关系,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神话的“阐释领域”,它们的地位和作用都会被解释并重新确定。(54)[美]杜赞奇:《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参见[美]韦思谛(Stephen C.Avefill)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四、结 论
明清传教士把关羽信仰看作是迷信,这掏空了中国民间禳灾文化的功能,但是民间文化的结构却顽强地延续着。把危险人物辨识为妖魔并将其驱逐,是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猎杀动物的负罪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受报复的集体受迫害想象和深层焦虑,(55)[英]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胡亚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32页。这种焦虑孕育了一系列仪式活动及潜意识的象征性编码体系,这一系列仪式活动包括禳灾、献祭、礼物交换、逐疫、代言等等。
首先,按照人类学的理解,污染和秩序势不两立,祭祀仪式以阈限的形式隔绝污染重组环境,因此避免污染蔓延,重回正常秩序。经过调查,传统社会禳灾逐疫的方式有许多,中国有傩仪、祷辞、戏剧仪式等。禳灾逐疫的仪式中,人神沟通的语言具有特别的法术能量。
其次,结合中外的禳灾祭祀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这些文本背后的祭祀仪式与说唱逐疫传统。为了理解地方民众被动员的方式,我们眼光不能局限在传播故事的最初动机上,而要调查他们的原初情境。(56)[荷]田海:《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赵凌云,周努鲁等译,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310页。从巫术仪式到戏剧象征、圣迹神话,三者之间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借用社会人类学的术语,这个过程可以描写为“阈限连续体”(liminal continuum)或“中间状态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在时间空间上的表现包括庙会、社火和傩戏仪式等民间祭祀和节庆仪式活动。(57)《古典文学(小说与戏剧)访谈》,参见赵晓寰《戏剧、小说与民间信仰: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域外观照》绪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25页。
最后,文化传统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涉及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当然也包括认知科学等诸多学科。只要深入中国实际,我们就会发现相当一批仪式文本,它们与社会愿景、表演情境一起构成“互动仪式链”。仪式在文学故事讲述、民间信仰、社会实践、民众的道德生活之间搭建起了桥梁,架起禳灾的文化空间。只有摆脱逻各斯的纠缠,还原中国“大文学”观念,方能回到可以抚慰创伤、救赎灵魂的文学本来面目,回到中国文学真正的“生活现场”。
致谢:本文得到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濮文起研究员的支持。另外,确定题目后,研究生同明英参与收集了部分材料,在此一并致谢!
——河西宝卷整理的回顾与反思